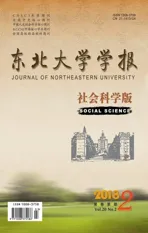论理查德·赖特小说中“看不见的女性”
2018-04-13方圆
方 圆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美国非裔作家理查德·赖特是抗议派作家的始祖,以描写城市黑人男性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受到阉割并积极抗争的故事见长。半个多世纪以来,批评家们对赖特的创作思想、主题、语言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诸多重要成果,研究视角涉及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创伤书写、精神分析学、流散文学等。在其作品的意识形态力量得到井喷式赞誉的同时,赖特对于黑人女性形象的贬损也受到很多批评家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诟病。批评家们认为,赖特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是“平面化、角度单一”的刻板角色,主要是作为“男性人物的附属角色”[1]出现的。她们任由生活摆布,碌碌无为,麻木不仁,成为男性角色成长的绊脚石。年长的女性大多沉迷于宗教,年轻的女性则沦为男性发泄性欲的工具。赖特小说中大多数的黑人女性呆板、天真、愚笨,“她们并非是男性平等的伙伴,也没有被当人看,她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让男性人物解决难题或是陷入更深的困境”[2]。女性被固化为等待男性拯救的沉默的女性这一刻板形象。有学者认为赖特小说中的南方黑人女性“代表了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严峻考验中遭到践踏和扭曲的南方妇女阴暗的一面”[1]。著名美国非裔小说家佐拉·赫斯顿(Zora Hurston)也曾在赖特批评她的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是民间浪漫主义之后,毫不客气地指出赖特创作中的极端大男子主义,她认为《汤姆叔叔的孩子们》“或许可以满足所有的黑人男性读者的幻想”[3]。
对于赖特在创作中表现出男权主义倾向的原因,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这受他的母亲和外祖母的影响,还有少数则把这归咎于赖特的性取向或其他原因。著名学者杰瑞·沃德(Jerry Ward)在2008年出版的《理查德·赖特百科全书》中指出,赖特的创作受他童年经历影响很大,“他对于自己父母和外祖母的观察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他对于女性角色的创作。他笔下的女性角色,要么沉迷于宗教,要么陷于不道德的淫乱活动,极少有例外”[4]414。迈克尔·韦斯特(Michael West)认为,赖特成长于一个女性掌权的家庭,她们是他“追求个人自由和实现文学抱负道路上的障碍”[5],这导致他对人尤其是女性有一种防御心理和不信任感。赖特的朋友玛格丽特·沃克(Margaret Walker)则认为,有种种迹象表明赖特有双性恋倾向,他对女性的矛盾心理和他的性取向是导致他在创作中“虐待”女性,以及尤其“仇恨”黑人女性的重要原因[6]。
然而鲜有批评家注意到, 赖特虽然在女性人物刻画上存在局限性, 他笔下的女性却是男性人格发展不可或缺的源泉和向导。 女性气质在男性主人公的主体构建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赖特作品中的很多男性人物在现实中屡屡碰壁, 精神生活荒芜, 虽然种族歧视是罪魁祸首, 但这也和他们压抑自己内心的女性气质和情感有莫大关联。 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小说《成人礼》(RiteofPassage,1994)中, 赖特首次赞扬了黑人女性对于男性人格发展的积极作用。 罗伯特·巴特勒(Robert Butler)认为《成人礼》中只有主人公约翰尼才能看见和听见的黑人女性形象正是赖特小说中存在着的“看不见的女性”[7]。 笔者认为“看不见的女性”意即男性角色灵魂深处的女性意向, 这是研究赖特小说的一个被忽视但又很重要的视角。在赖特被屡屡诟病的性别政治背后, 他作品中的雌雄同体和阿尼玛原型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一、 消极阿尼玛和积极阿尼玛
androgyny(雌雄同体)这个英文单词来源于希腊语,是将希腊语中“andro”(男性)与“gyny” (女性)两个词融合在一起构成的新词,在神话与宗教故事中都得以直观展示,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就曾用古老的雌雄同体故事来表达爱情的神秘*在《会饮篇》(Symposium)第14章,柏拉图借悲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之口精心设计了一个人类起源的神话:人类最初有三种性别:男人,女人和阴阳人。最初的人是球形的,长着四只手和四条腿。后来宙斯为了削弱人类力量,把人类劈成两半。人类在被劈开以后都非常想念自己的另一半,因此每个人都在寻找和自己结合的那一半,以恢复最初的完整状态。这样凡是由原始的男人和女人切开而来就成了同性恋,而原来的阴阳人被劈开后则产生了异性恋。这种对成为整体的希冀和追求就是爱情。。著名分析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则从心理学层面揭示了人类身上的雌雄同体倾向。他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雌雄同体的原始人变为了人格统一的象征,……每一个个体都是源自阳性与阴性基因,以及性别是由相应基因的支配所决定。”[8]139也就是说,除了我们意识中的性别特质,还有一个异性性别特质存在于我们的无意识中,它预先存在于人的情绪、反应和冲动之中。雌雄同体这一人格统一象征的背后是他提出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原型。荣格认为:“每个男人的无意识中潜伏着一个女性人格,而每个女人的无意识中则潜伏着一个男性人格。每个男人身上都有女性的一面,一个无意识的女性形象。”[8]225荣格将这个男人身上的女性人格称为“阿尼玛”,它在女人中的对应物为“阿尼姆斯”。阿尼玛是男性无意识中通过遗传方式留存的女性的集体形象,代表了祖先传承下来的所有女性真实经验的积淀,作为隐藏在意识之下的无意识的人格化表象,她是男性个人通往内心灵魂的桥梁和无意识世界的引导人。
荣格认为,阿尼玛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她既可以成为男性向上成长的动力,也可能成为他堕落的诱惑者。积极阿尼玛对男性的意识是有益的,她以一种理想女性的形象出现,是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调解者。她是男性灵魂的向导,能引导他进入更高的人生层次和精神世界,对男性的个性发展和主体建构有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消极阿尼玛是有害的,消极阿尼玛就像古希腊的海上女妖一样,是危险的化身,诱使男性脱离现实,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狂想。若男性对消极的阿尼玛着魔,则会损坏他们的意识,正常的婚恋关系也会受到严重的干扰。
赖特的作品中有很多消极阿尼玛的形象,笔者把她们分为两类。一类消极阿尼玛是以爱之名束缚男性思想和行动、不仅自己深受宗教麻痹还强迫男性人物接受宗教的年长女性,这一类多是母亲阿尼玛,比如《土生子》中的托马斯太太和《局外人》中的丹曼太太。托马斯太太早年丧夫,丹曼太太则在生下儿子克洛斯之后就被丈夫抛弃。作为黑人单亲母亲,她们必须要承担独自抚养并教育孩子的重任。她们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就是对他们进行宗教洗脑,希望他们能像自己一样接受宗教这一麻醉剂。托马斯太太一直否定儿子的价值,逼着他去道尔顿家做事,从来不考虑儿子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她把宗教作为精神的庇护所,遇到事情除了祷告上帝什么也做不了。她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皈依宗教,听从上帝的指引。在儿子杀人被捕之后,她则一直劝说他向主祷告,甚至让牧师充当说客。别格以扔掉牧师给的十字架这一举动拒绝接受母亲的宗教洗脑,在生命的最后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宗教的虚伪。丹曼太太给儿子取的名字“克洛斯”意为十字架,带有浓浓的宗教意味。在年纪轻轻就被丈夫抛弃之后,她把儿子当成丈夫的替代者,她密不透风的爱让儿子感到窒息;而她一直孜孜不倦的道德说教更是让追求自由的克洛斯烦不胜烦。“她以自己充满抱怨和指责的灰色生活来影响儿子的生活,想要通过夸大自己被抛弃的悲惨经历来唤起儿子的同情,尽管这并不奏效。”[9]34她正符合荣格对于散发负面能量的消极阿尼玛的定义:“在这些男人的灵魂中,消极的‘母亲-阿尼玛’将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我是虚无,一切毫无意义……’这一容易让人产生呆滞麻木情绪的主题,常令男人产生一种对于疾病或突发事件的恐惧。这样一来他的整个生命也将呈现出一种悲惨的、烦闷抑郁的特征,甚至可能诱使他去自杀。这时,阿尼玛便演变成致人死命的恶魔。”[10]对于克洛斯而言,母亲阿尼玛对他的消极影响是一辈子的,她从克洛斯童年起就把恐惧和罪恶感植入他的内心,“他无力抵抗”,“她赐予他的这一重大礼物……,逐渐形成他生命的轮廓,影响了他所有可能拥有的未来……”[9]151。最终克洛斯的整个人生都陷入悲观和怀疑中,虽然他知道母亲很爱自己,自己也是爱母亲的,但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总是疏离的,正如后来霍斯顿指控他的那样,他已经在内心中杀死了母亲。
赖特作品中另一类消极阿尼玛形象是没有思想、依附男性、要靠男性来拯救的年轻女性,比如《局外人》中的多特和《长梦》中的格拉迪斯。多特最初吸引克洛斯的就是她的柔弱美丽,她总是很安静地听克洛斯说话,几乎不发表什么意见。这看似是她善于倾听,其实是她完全没有主见和思想,和克洛斯完全不能在精神层面交流。她的形象也为后面夏娃的出现作了铺垫,因为夏娃才是唯一能走进克洛斯敏感脆弱的灵魂的女性,而多特只是想找一个在经济和生活上能长期依靠的男人。她想以怀孕为筹码逼迫克洛斯和自己结婚,在克洛斯不买账之后就处心积虑想要以强奸罪起诉克洛斯。多特这位消极阿尼玛对男性人物的直接影响就是让他更加不信任女性,加速了他的出逃。《长梦》中的格拉迪斯是黑人女性遭受白人男性强奸之后生下的女儿,外表看起来皮肤白皙很像白人,这也是她吸引主人公菲西比利的地方。但在精神状态和心理上,她还是麻痹不仁,愚昧无知,接受现状,把自己的生活寄托在男人身上。格拉迪斯遭受了和自己母亲一样的命运,生下一个混血女儿,但她完全接受命运的安排,从来没有想过抗争。菲西比利总是想启迪她对于种族压迫多一些认识,但她完全不为所动;而在菲西比利想把她带出妓院时,她非常高兴,表示不求名分愿意永远忠于菲西比利,不管他让自己做什么。这种对男性的一味顺从和低姿态正符合父权制对女性的要求。格拉迪斯这种消极阿尼玛给菲西比利带来的影响就是让他变得自我膨胀,把自己当成拯救女性的救星,同时更加享受身边有“白人女性”相伴的快感。但事实证明,最终一切都是一场幻影,菲西比利最需要拯救的其实是自己,他需要把自己从对白人女性的欲望中解救出来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建构。
另一方面,积极阿尼玛能帮助男性实现婚姻的幸福和人格的健全。荣格认为阿尼玛的演变分为低级和高级阶段,低级阶段和纯粹的性本能联系在一起,高级阶段阿尼玛则是智慧的化身,是男人内在的创造源泉。“她是种秘密的知识或者潜藏的智慧”,“里达·荷加把‘她’称作‘智慧的女儿’”[11]70。赖特的短篇小说《黑色长歌》中的女主人公莎拉和长篇小说《局外人》中的夏娃就是智慧阿尼玛的代表。《黑色长歌》主要讲述了黑人女性莎拉被白人推销员诱奸从而导致莎拉的丈夫塞拉斯和白人互相厮杀的故事。塞拉斯属于黑人男性中的佼佼者,忍辱负重和白人做生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使得他的妻子莎拉不用像其他黑人女性那样劳作,同时这给了上门推销的白人男性诱奸莎拉的机会。莎拉是一个虽然沉默但是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女性角色,小说以赖特作品中少见的女性视角展开叙事,这也足以可见赖特为被压抑的女性他者发掘言说潜能的努力。表面看起来,莎拉愚昧无知,受自己内心欲望的驱使,轻易就被白人销售员引诱,导致自己的丈夫塞拉斯在和白人的英勇抗争中死去。但事实上,莎拉是《汤姆叔叔的孩子们》这本故事集中最富有智慧的角色之一。她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能敏锐地感知到自然和世界的变化,她的创造才情从作者对她心理活动诗化的描写中也可见一斑。而莎拉超越黑白二元对立的种族观正是其潜藏的智慧的表现。莎拉为黑白之间的互相残杀感到难过,想尽可能地阻止这种永无休止的残杀----她想要提醒白人推销员第二天不要再出现,还想要劝说塞拉斯和她一起逃离,但都以失败告终,这种延续了几百年的黑白对立观根本不是她能撼动的。“人类,黑人和白人,陆地和房子,绿色的庄稼和灰色的天空,喜悦和梦想,都是让生活美好的组成部分。它们就像马车车轮的轮辐,全部连接在一起。她觉得是这样的,她知道是这样的。”[12]352莎拉本能地觉察到白人和黑人就像白天与黑夜、大地与天空一样,是双方都不可或缺的平衡体。可惜塞拉斯和那些白人男性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陷入相互的仇恨、对立和厮杀中,最终两败俱伤。从《汤姆叔叔的孩子们》五个故事的发展主线来看,黑人和白人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后,终于由一开始的相互纠缠到最后的联合。莎拉这位智慧阿尼玛就像作者内心的代言人,寄托了作者黑白融合的美好愿望。
《局外人》中的夏娃也是一位智慧阿尼玛的代表。小说主人公克洛斯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借一次地铁事故的机会,切断了自己和家人朋友的一切联系,改名换姓来到另外一个城市。他独来独往,不愿意和任何组织及个人产生关联。为了实现对自由的追求,克洛斯把社会文明禁忌抛诸脑后,他一次次用暴力犯罪对抗专制、虚无和权力,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但即使如克洛斯这样的男性,仍离开不了女性的拯救力量。赖特在小说中直接点出,“他需要女性的力量和帮助”[9]448。夏娃正是作为克洛斯理想的阿尼玛形象,把克洛斯从虚无厌世的生活中拯救出来,让他开始重新相信生活和爱情。夏娃是一位聪明、敏感、善良的白人女画家,克洛斯和夏娃之所以惺惺相惜,是因为他们都有一颗敏感孤独的内心。与克洛斯通过暴力犯罪转移孤独感不同,夏娃通过绘画发泄她的孤单。虽然夏娃身上仍然带有赖特笔下女性的一些共性,比如无助、需要男性的拯救等,但仔细审读文本后可以发现,她才是男性的拯救者和治疗者。“他无名的重疾要靠赢得她的信任和爱才能治愈,……他想要她的爱来救赎自己的罪恶,……让她敏感的心灵成为他的引路人,引导他远离罪恶的泥潭。”[9]385警察、检察官霍斯顿、妻子和儿子都无法让冷酷的杀人犯克洛斯开口承认罪行。然而在夏娃无原则的信任和爱面前,罔顾法律、刀枪不入的克洛斯打开了自己坚硬的内心,向她坦白自己犯下的罪行,恳求救赎和帮助。夏娃不仅把克洛斯从无尽的犯罪深渊中拯救出来,还给予他希望,是他“生命的目标……,引导他走出绝望的泥潭,奔向希望的未来”[9]392。克洛斯原先觉得生活是无意义的空虚的,女人只是身体的代名词。在遇见夏娃之后,克洛斯开始厌倦自己隐名埋姓的逃亡生活,渴望能和夏娃组成真正的家过安稳的生活。夏娃代表了克洛斯坚硬外表下所隐藏的女性气质,是他灵魂深处的柔软一面。夏娃这位智慧阿尼玛不仅阻止了克洛斯人性中的兽性因子进一步肆虐,同时还唤醒了克洛斯内心被抛弃的人性和情感。
二、 母亲阿尼玛:黑人男性成长中的保护神
荣格的学生埃利希·诺伊曼在《大母神-原型分析》中指出:“考虑到女性基本功能的整个范围----赋予生命、营养、温暖和保护,我们才能够理解女性何以在人类象征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女性之所以被表现为伟大,是因为那些被容纳、被庇护、被滋养者依赖于它,并且完全处于它的仁慈之中。看看婴儿和儿童,他们把母亲的地位等同于大母神。”[13]他在这里高度赞扬了母亲原型的重要地位,他认为阿尼玛形象就是从母亲原型中分化出来的。荣格也认为,男性内心的阿尼玛原型来自母亲的影响。“阿尼玛原型首先与母亲意向相融合,总是出现在男人的心理状态之中……,对儿子而言,阿尼玛隐藏在母亲的统治力中,有时她甚至会使儿子产生一种情感上的依恋,这种依恋会持续一生并影响他成年后的命运。但在另一方面,她又会刺激他远走高飞。”[8]68与此同时,如果母亲对儿子有消极的影响,他的阿尼玛就常常表现出暴躁易怒、多愁善感和优柔寡断;而如果母亲的影响是正面的,那么其阿尼玛就内化成儿子“梦中情人”的形象。
赖特成长在一个白人主导的社会和一个缺乏成年男性引导的母系家庭中。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抛妻弃子,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也大都成长在父亲缺失的环境中。虽然很多评论家都认为赖特对黑人女性的偏见很大一部分来自自己笃信宗教的母亲埃拉的影响,但不能否认埃拉在赖特的生命中起到了很多积极的作用,赖特在内心是珍视这段母子关系的。他在1941年以他母亲的名义接受了斯平加恩奖章(Spingarn Medal),他说:“她做了很多报酬微薄的工作,牺牲了自己的健康”。而在他的代表作《土生子》的前言中,赖特提到“这本书献给我的母亲,她在我孩提时代教会我敬畏所有奇思异想和有想象力的事物”[4]420。赖特在成为一名作家之后也一直恪守儿子的职责,赡养自己的母亲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可以看出他对母亲有一种情感上的依恋,母亲在他的童年时代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仔细审视赖特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会发现虽然她们遭受男性同伴的鄙视、侮辱甚至殴打,但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男性同伴的母亲的角色,照顾他,成为他在白人社会受挫后的避风港,就像母亲的子宫一样温暖。
别格和克洛斯的母亲阿尼玛虽然给他们带来消极的影响,但还是帮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醒悟到人生的价值。别格在被捕后见到家人,才知道母亲每天以泪洗面,终日为他祷告,而妹妹因为遭受同学嘲笑也不肯去缝纫班上课了。他这才意识到:“他过去的生活和行动都基于他只是一个人独来独往这个假设上,现在他看出并非如此。他的所作所为也给别人带来痛苦。不管他怎么渴望着他们忘掉他,他们是做不到的。他的家庭是他的一部分,不仅在血统上,而且在精神上。”[14]别格最终才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是相互联系的。无独有偶,在克洛斯临死之前,他终于意识到个体只有在和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定义个人身份,完全自由的个体是不存在的。克洛斯意识到母亲一直唠叨着的那些宗教话语其实是真理。在他死于枪伤之前,克洛斯不断强调的正是他笃信基督教的母亲常说的话,只不过他之前一直拒绝接受:“生命是一个许诺,儿子。上帝把它许诺给我们,我们必须把它许诺给其他人。没有这种许诺,生命什么都不是”[9]28。一直在寻找个体价值的他意识到,“对个体价值的寻找是无法独立完成的,永远不要一个人”[9]585。
赖特小说中最典型的母亲阿尼玛形象当属《成人礼》中的无名黑人女性。《成人礼》是一部关于黑人青少年成长的小说。主人公约翰尼还在母亲腹中就遭到父亲遗弃,生下来后就被送到寄养家庭,在那里遇到了对他关怀备至、温柔细心的黑人养母。在学校他是优等生,得到白人女教师的鼓励和关爱。然而,这个温暖安全的世界在他15岁这年突然一下子坍塌了----白人当局要求约翰尼必须离开现在的寄养家庭到一个新的家庭。他一下子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非常崩溃,于是选择了逃离。他加入了一个以抢劫为生的黑人青少年团伙,并因为打架厉害成为头领。《成人礼》和赖特以往的抗议小说一脉相承,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典型的赖特式主题:黑人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价值体系中沦为他者,迷失自我身份;白人政府和社会机构对黑人残酷冷漠;黑人主人公诉诸暴力作为种族主义社会的生存策略等等。但很多批评家都忽视了,在这部小说中,赖特首次赞扬了黑人女性对于男性发展的积极作用。美国黑人学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认为黑人女性是家园的建设者和黑人社区的核心角色,“她们是我们的主要向导和老师”[15]。《成人礼》中的女性就扮演了灵魂向导和老师这样的角色。约翰尼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受到女性的培育关爱和积极引导,包括他的老师和养母;而男性家长角色一直是缺失的,不管是他的生父、养父还是男老师。在实施暴力的过程中,约翰尼始终能看见一个黑人女性在召唤他,总是能听见她斥责他们的声音,有时候在他抢劫别人时甚至还能看到那个黑人女性和被抢劫人站在一起。在《成人礼》的后记中,阿诺德·兰佩萨德(Arnold Rampersad)提到了黑人女性在这本小说中的象征作用:“她代表了爱,正直和家庭的温暖……。与赖特的其他小说不同,《成人礼》中的黑人女性身上具有人类最美好的品性,……她呼唤他回家,出于关爱而责备训诫他,在他犹疑不决的时候把手轻轻放在他的前额。这本质上是一种母子关系,……赖特在这里创造出了一个孕育人类的女性形象”[16]127128。黑人女性在这里充当了训导孩子的家长角色。约翰尼内心反复听到的黑人女性的声音正是一直以来给他积极影响的女性声音,也正是他灵魂深处的阿尼玛人格,是他潜意识的人格化。荣格曾提到这样一个病例:一个青年人被埋在雪洞里,进入梦一般的状态,并感到虚脱。昏迷之中,他忽然看见一个光芒四射的女人。“她告诉他所有他需要知道的事情,后来还成为他的保护神,帮助他借助外部的力量完成困难的工作。”[17]《成人礼》中的黑人女性就像梦中才能看见的光芒四射的女人一样,成为约翰尼的保护神、他成长中的重要引路人和人生迷茫时刻的明灯。约翰尼内在的女性气质和情感也正是源于母亲阿尼玛的投射。
三、 男性人物对自身阿尼玛人格的压抑和认同
由于阿尼玛存在于男性的无意识中,很多时候是被男性排斥的。荣格也指出:“一个男人抵制他的阿尼玛是完全正常的,因为阿尼玛代表着无意识和所有迄今被排斥在意识生活之外的心理倾向和心理内容。”[11]381剖析赖特小说中的男性角色,会发现他们大多压抑了自己内心的阿尼玛。荣格指出阿尼玛是双面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然而赖特小说中的黑人男性们在毁灭了负面的阿尼玛人格的同时,也把正面的阿尼玛人格拒之门外。这些黑人男性漠视甚至憎恶黑人女性,其实是在拒绝阿尼玛意向的投射。他们在白人社会受到精神阉割,男子气概受到践踏。正如《长梦》中的泰里平时在妻儿和下属面前是威严不可侵犯的形象,但在白人面前为了保住性命嚎啕大哭,苦苦哀求。一方面他们被迫把自己的女性特质暴露在白人面前;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这种女性特质感到厌恶并排斥,而他们排斥的方式大都如出一辙,要么通过暴力犯罪等极端行为彰显自己的男性特征,要么贬低、侮辱甚至殴打自己的情人或者妻子。他们压抑和排斥自身的阿尼玛人格,否定自身的雌雄同体,这让他们的人格发展很不健全,最终导致自身的悲剧。赖特笔下的黑人男性们在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社会想努力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用外表的阳刚之气抹去其无意识中的女性人格,结果反而不仅成为白人社会受到精神阉割的对象,也丧失了在自己的种族中爱和信仰的能力。
《土生子》中的别格在白人主流社会感到恐惧和压抑,他厌恶自己的无价值感、恐惧和无助等阿尼玛特质,并毁灭了这些特质;但与此同时也毁灭了自己灵魂深处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爱与被爱、善良等积极的阿尼玛特质。于是别格痛殴自己的伙伴,蔑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最后更是通过不断的杀人才找到自己的存在感。罗伯特·巴特勒认为,别格不仅把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性排斥在外,还毁灭了自己的女性特质,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一系列犯罪行为。在小说最后,他终于愿意去拥抱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这也是他人性复苏的开始。《今日的主!》中的杰克把自己生活中的受挫感都发泄在妻子丽莲身上,他不停地殴打她,威胁要杀掉她。这其实正源于他内心对阿尼玛人格的排斥----杰克想要毁掉自己身上无助、软弱和不独立等女性特质。“他的外在态度越是有阳刚之气,就越是想抹去其女性特性。这种现象解释了为什么正是那些很有阳刚之气的男人却最有可能为特有的软弱所主宰。他们对于无意识的态度有一种女性的弱点和最易受影响的特性。”[18]杰克一方面在外表上表现出阳刚之气和大男子主义,他总是和同伴一起讥笑黑人女性,在受到邮局委员会调查时唯恐被当成汤姆叔叔;另一方面他在工作中受到来自白人世界的监视,在工作之余找不到让生活有意义的事情,他常常感到“一种巨大的不能抵抗的压力在击垮自己”,但是却“无能为力”,这让他对自己感到“很愤怒”[12]143。小说中多次出现杰克睡觉或者做梦的描写,即使他醒着的时候,也很多时候是半睡半醒的,并不清楚周遭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不管他是在和朋友们打桥牌,侃大山,还是在邮局工作的时候,杰克总是处于疲倦和昏昏沉沉的状态。杰克的这种状态虽然很大程度上来自种族歧视带来的创伤,但也和他没有办法平衡内心的两种性别特质导致人格不健全有很大关系。
《成人礼》中的约翰尼是赖特笔下为数不多的主动寻找并认同自己内心阿尼玛人格的男性角色。在他加入暴力团伙之后,他内心一直有两个矛盾的自我在斗争:一个是受女性影响的那一部分自我,相信爱和道德,她呼唤他迷途知返,不要伤害无辜;另一个则是受男性影响的那一部分自我,他要求自己通过暴力行为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这象征了他内心中过度膨胀的男性特质和积极的女性特质作斗争的过程。约翰尼非常纠结,而他内心本能地想要向黑人女性求救,他想要“对某个年老的黑人妇女跪下哭泣:帮帮我吧,我再也受不了了”[16]102。同时约翰尼也一直看见一个黑人女性在呼唤他,阻止他滑向犯罪的深渊。约翰尼没有被自己的男性人格完全主宰,成为一名别格一样的罪犯,他“看见了”自己的阿尼玛人格----也就是那个在呼唤他的黑人女性。虽然赖特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结局,但读者明显能感觉到希望,那就是约翰尼会依从内心阿尼玛人格的呼唤,离开这个犯罪团伙。
赖特的小说总是交织着对黑人文化的疏离和美国黑人生活中的冲突和暴力,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谋杀、背叛和暴力。也正因此他作品中超越二元对立的对平等和谐的追求常常受到评论界的忽视。赖特的作品绝不是简单的对种族不公的讨伐,而是对现代社会心理问题的审视和揭露,以及对黑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意义和伦理关系的关怀和思索。赖特作品的艺术魅力不仅存在于其意识形态力量上,也表现在作品对于性别二元对立的解构和两性和谐共处的伦理诉求上。只有两种性别特质和谐发展,相互合作,人才能有健全的精神生活。如果两者失衡,压抑自己的异性性别特质和情感,就会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内在心理过程,也无法完成对自己灵魂的认同,最终会导致人格的不健全。在赖特笔下充满暴力的男性世界中,积极阿尼玛是摆脱不掉的“看不见的女人”,她像男性贫瘠的精神荒漠上的绿地,她信仰“美和善”,她是黑人男性人格发展和完善的源泉和向导。雌雄同体不仅存在于神话中,更真实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灵魂中。只有尊重和认同灵魂中的异性人格,才能找到通往无意识的桥梁,成为一个精神生活健全的人。
[1] Willis M D. Avenging Angels and Mute Mothers: Black Southern Women in Wright’s Fictional World[J]. Callaloo, 1986(28):540.
[2] Keady S H. Richard Wright’s Women Characters and Inequality[J].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 1976,10(4):124.
[3] Hurston Z N. “Stories of Conflict”: Review of Uncle Tom’s Children by Richard Wright[J].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1938(2):32.
[4] Ward J W,Butler R J. The Richard Wright Encyclopedia[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8.
[5] West M D. The Purported and Actual Meanings of Richard Wright’s “Big Black Good Man”[J]. Orbis Litterarum, 2011,66(5):345.
[6] Walker M. Richard Wright: The Daemonic Genius, a Portrait of the Man; A Critical Look at His Work[M]. New York: Amistad, 1988:179182.
[7] Butler R J. Review of Rite of Passage[J].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1996,30(2):319.
[8] 荣格C G.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荣格文集(第5卷). 徐德林,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
[9] Richard Wright. The Outsider[M].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3.
[10] 常岩松. 人类心灵的神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106.
[11] 冯川,苏克. 荣格文集[M]. 北京:改革出版社, 1997.
[12] Wright R. Richard Wright Early Works: Lawd Today! Uncle Tom’s Children, Native Son[M].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1.
[13] 诺伊曼 E. 大母神-原型分析[M]. 李以洪,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41.
[14] 赖特 R. 土生子[M]. 施咸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345.
[15] Hooks B.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5:77.
[16] Wright R. Rite of Passage[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4.
[17] 荣格C G. 人类及其象征[M]. 张举文,荣文库,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157.
[18] 荣格C G. 心理类型[M]∥荣格文集(第3卷). 储昭华,沈学君,王世鹏,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