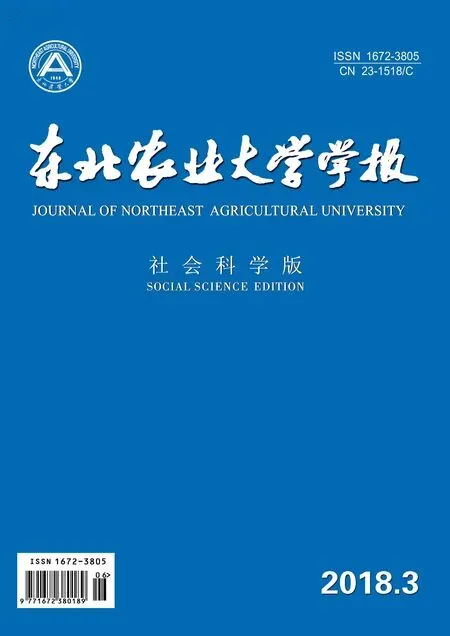身体地理与20世纪中国文学城乡转换中的味觉身份建构
——兼论陆文夫《美食家》
2018-04-13岳璐
岳 璐
(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76)
身体地理作为思维范式的转型研究方法,给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带来的不仅是局部震荡,更是整体学术范型的转换。国外身体地理研究可追溯至1989年,首先以女性主义地理学为视角。2000年后,开始出现身体和关怀地理学关联研究,主要研究身体界限、边界和能力等。国内研究也于此时开展,主要在人文地理领域研究身体与情感地理及旅游地理间关系。目前,许多批判地理学家,女性主义、反殖民主义地理学家认为,身体研究可成为改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的有效途径。身体地理学与其他学科领域不断交叉发展和相互拓展,为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路。本文通过追溯身体地理与中国文学味觉地理关联建构兴起与形成的社会历史及知识谱系的学术背景,阐释身体空间作为地理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城乡空间转换中味觉变迁的内在关联,同类型研究并不多见。研究立足于现代性带来的中国城乡空间结构转换问题,反思中国现代性城乡空间转换中身体地理与味觉变迁关系,及其中蕴含的国家、民族与自我身份认同建构的深层次意义。
以陆文夫《美食家》中20世纪中国地理空间震荡重组中味觉变迁的历史叙事为例,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城乡转换中味觉变迁蕴含的民族及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一是在古代中国身体地理空间中,阐释古代文学中味觉变化蕴含的个体和国家伦理身份确立;二是在现代中国身体地理空间裂变重组中,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城乡转换中味觉怀乡蕴含的民族归属性意识建立;三是审视陆文夫中篇小说《美食家》中身体地理与味觉变迁间的交织互动关系,特别是以味觉地理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模式蕴含的自我身份认同。
巴尼·沃夫(Barney Warf)编著的《人文地理学百科全书》阐释地理学家对身体和空间关系的理解,指出“身体是社会空间关系、表征、认同的重要节点”[1]。身体地理形成有三个空间形态:实体空间中,身体被视为个体占有的场域、位置;隐喻空间中,身体成为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节点;情感空间中,身体又是包括迷茫、愁苦等各种情感建构的场所。笔者认为,身体地理导致的文学思维范式转型,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饮食味觉研究更趋向身体地理两个空间形态,即关注隐喻空间中因实体空间裂变产生的民族及自我身份认同和情感空间中的味觉乡愁、迷茫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文化启蒙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及现代性表现的矛盾冲突几乎同步。纵观中国现代性发展,始终伴随大规模现代化时空重组。在空间裂变与重组中,城乡空间裂变和重组最具标识性。在现当代文学城乡二元空间结构书写中,中国文学家开始以现代眼光观望世界,考量个体自我身份认同危机意识产生的地理根源。以味觉在空间转换中的变迁思考中国社会城乡分化和变异,不仅使问题更具现实性,也可避免历史叙事的宏大模式,直接进入个人和时代的味觉记忆体验场域,体验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变迁。
一、身体地理与中国古代文学城乡转换中的味觉身份确立
中国古代文学对味觉的追求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伊尹以“至味”讽谏商王汤。思想家晏子由调和五味说明君臣协调,以此比喻社会和谐,进而推渲至天人合一,阴阳燮理思想。由调和五味的汤文化衍生出中国古代哲学“中和”思想。形而上的食物话语完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饮食由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升华”[2]。在“中和”思想指导下,人们开始重视饮食与人际交往间的亲和性,宴会、聚餐成为身体地理酬酢、交往的必要形式。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记载很多人际交往的“饮食宴乐”,及宗教祭祀后的宴饮。在宾客满朋的宴席空间,身体地理蕴含的身份地位及尊卑等级等社会属性在早期宴饮中显现。如《礼记·少仪》记载,就餐先奉尊长食,并小口咀嚼,“燕侍食于君子,则先饭而后己;毋放饭,毋流歠。小饭而亟之,数噍毋为口容”;《礼记·曲礼上》要求在宴饮空间中,身体座次方向排位遵从身份等级,“席南乡(向)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3]。先秦饮食礼仪繁琐旨在培养“尊让契敬”精神,要求社会不同阶层均遵循礼的秩序。身体座位排序与身份五伦关系、味觉的先凉后热及视觉的先简后繁等礼仪顺序,均体现中国古代“礼之初,始诸饮食”(《礼记·礼运》)的内在伦理精神。
进入汉代,与民休息的农业政策促进粮食产量提升,充满“以乐侑食”的味觉审美精神需求,且确立“礼”和“道”结合的汉代士大夫身份。“礼”主张严谨有序,“道”崇尚乐观豁达。“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迁认为身体享乐意味着生活质量提高,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利于国家政治安定。司马迁还积极倡导饮食贸易,认为其“上可富国,下可富家”,由此推动中国古代味觉地理初步形成。饮食贸易打破身体地理的封闭场域,促进多味觉融合,由味觉开启的身体享乐促成地理空间转换,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得到积极发展。
唐宋是中国古代身体地理空间加速开放并建立与味觉地理关联的重要时期,亦是大城市味觉形成期和市民身份建立期。大唐盛世声誉远及海外,与南亚、西亚和欧洲国家均有往来,为中外饮食交流提供便利空间。通过开放味觉地理,人们逐渐认识到身体地理的重要性,开始重视人与环境关系。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出人地关系对于饮食至关重要。玄奘将饮食作为了解地域、国家、民族最重要的切入点。此时,身体地理成为考查味觉文化变迁的重要维度。正是身体地理的分延拓展,促进味觉空间结构性变迁。唐宋是中国古代大城市集聚发展时期,国家空间敞开进一步加速城市市民生活空间建立。大城市人们不再满足于自烹自食的饮食行为,更多人进入饮食市场开展商品交易。唐代城市逐渐兴起食店饭馆,扬州、长安等城市可见“街店之内,百种饮食,异常珍满”[2]。至北宋,异族商人和移民进入中国,种族和数量均远超唐朝,城市间味觉交流异常活跃。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城饮食之繁华,全天下异味聚集于此,“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南宋建立后,北方饮食习惯随身体地理方向南流,“东都遗风”促成中国历史上味觉习俗与烹饪技法交流,完成味觉地理变迁。敞开的味觉空间,不仅贯通南北地理空间,同时促使中国城市味觉空间建立,并开启世界视阈,在世界空间中确立中国的中心身份认同。
随着先进地理技术的开发,明清时期南北味觉地理进一步交融扩大。元朝时南北大运河全线沟通,将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四大流域连在一起,为南北空间贯通和全国物资尤其是味觉地理交流创造有利条件。中国近代地理学创建人徐霞客从探险者、旅行者饮食问题窥视社会资源分布及各地风俗,成为中国从身体地理视角探究空间转换中味觉变迁第一人。《金瓶梅》《红楼梦》等长篇小说则从微观生活空间记录一个时代的味觉景观及味觉身份在城乡转换中的变迁。施耐庵的《水浒传》从乡间食宿、市井食貌,到皇家御宴、官府菜肴的味觉地理空间描写,显示元明社会阶层身份建构,形成一幅味觉身份全景图。
二、身体地理与中国现代文学城乡转换中味觉怀乡的民族身份认同
民国时期味觉变迁与中国身体地理空间的现代性嵌入关联密切。中国社会步入现代进程以来,伴随大规模现代化身体地理的裂变与重组,身体生存体验和文化感受方式相应发生变化。现代性植入使传统中国城乡地理发生巨变,如李鸿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描述:“时至今日,地球诸国通行无阻,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4]资本主义空间技术征服世界,中国古代身体地理意识被打破,被迫置身于殖民化全球性空间意识的接受与认同中。以商业经济为本位的全新空间形态,即现代性城市孕育而生。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殖民者身体地理大量侵入,奶油、蛋糕、牛排、啤酒等西式味觉涌入,促成近代中西味觉地理大融合,加速味觉结构向科学化转变。孙中山从中西味觉比较视角提出中国味觉变迁是社会进化结果,是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提出“是烹饪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中国烹调之妙,亦只是表明进化之深也。”[2]
现代性身体地理殖民给近现代中国带来生存危机,直接导致国土沦丧、城乡分割。在跨国界、跨民族全球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在味觉怀乡主题中探求民族身份认同,重组民族文化之路。新城市空间诞生并不意味着旧乡村图景消逝,“水稻田和村庄,可从市区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瞧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轮廓鲜明,最富于戏剧性的世界之一。”[5]此时期,城乡以巨大落差为前提戏剧化并置存在,为中国文人味觉怀乡提供了梦回故里的情感地理空间。中国文人希望通过味觉怀乡追寻传统文化踪迹,在味觉乡愁中消除由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危机产生的焦灼感、抑郁感。黄子平认为,周作人谈《故乡的野菜》时,不仅引用《西湖游览志》和《清嘉录》,甚至涉及《本草纲目》;梁实秋《雅舍谈吃》引用古籍超过二十种[6]。引经据典的味觉书写表现现代性身体地理殖民消解了宏大历史叙事方式,带给文人现代焦虑。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味觉怀乡与民族国家重构的文化空间想象贯穿于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城市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性的重要标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全球的城市化突破欧洲大陆地理场域进入中国,打破封闭保守、宁静和谐的中国乡村地理空间。现代城市陌生感、传统乡村疏离感,伴随着家国沦丧的焦灼感,中国文人将味觉怀乡作为消解身体地理被侵入的叙事途径,消解城市味觉即祛除身体地理的殖民嵌入,回到身体地理原初之点,以找寻自我身份和民族身份认同。鲁迅笔下鲁镇的臭豆腐干、梅干菜;萧红文中呼兰河畔的黄米年糕、拌黄瓜丝;沈从文书中的鲤鱼豆腐、炒鱿鱼丝,记忆体验的味觉怀乡叠加着眷恋与决绝、悲凉与哀悯、沉思与反讽等多重情感和思绪,渗透着身体地理在裂变与重组中的身份认同。
周作人作为此时期味觉怀乡文人代表,将文化构想渗透到对故乡食物的阐述中,使身体地理从繁华都市走进故乡小镇。其味觉记忆中,野菜、臭豆腐、荠菜、烧鹅甚至萝卜与白薯皆为珍贵。带有故乡情怀的野味,是朴素自然之味,城市空间无法满足其回归古典的趣味指向,谈及北京茶食的缺陷时,其言:
我们于日用必需品的东西之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7]。
在“五四”之后的迷茫中,周作人热衷经营“自己的园地”,在风云激荡的时空,投身于味觉怀乡的身体地理中,寻求士大夫身份认同及民族身份认同。
三、身体地理与陆文夫《美食家》城乡转换中味觉变迁的自我身份认同
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地理空间剧烈震荡时,为重建国家、民族空间,李大钊、鲁迅等先锋文人将市井空间、日常生活空间排斥在社会历史生活空间外。之后的“十七年”及“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市井与日常生活均被视为贪图享乐、背离革命的隐喻符号。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农村相继实行联产计酬和承包责任制,城市经济改革也同步加快。城乡改革浪潮促使文学作品聚焦于城乡转换的社会环境。“五四”新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即以建构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启蒙”悄然兴起,“旨在文学自身审美价值的不断开掘,笔触穿透社会历史发展的表面浮云,深入到天南地北的民间社会。”[8]新文学史上,以周作人绍兴味觉、沈从文湘西味觉、老舍北京味觉等为传统味觉地理书写代表。1980年后,以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等为后继。乡土和市井是文学启蒙者常借以书写味觉叙事的地理空间;乡土和市井小人物身体味觉追求建构了乡村与市井的感性空间,在城乡空间转换中形成味觉“民族性”“乡土性”审美内涵,并找寻各自身份归依。他们依托乡土、市井风土人情表达情感,回归平常生活空间,找到适合生存的合理身份。
陆文夫关注与审视苏州饮食文化即为实现此理想。《美食家》通过一个吃客经历全景再现中国现代社会味觉观念变迁的地理景观,及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结构。陆文夫祖父是道地的江北农民,靠辛劳置办起家业,其父在江南做生意。陆文夫对苏州食物的关注来自童年记忆。虽在苏州生活五十年,但其故乡并非苏州,衣胞之地是长江边上的小村庄。“少年时代在苏州读书,青年时代去苏北革命,又打回苏州城,从此长住苏州,在此工作,在此劳动,在此写作,在此触霉头,在此挨批斗,也在此获得了荣誉。”[9]伴随中国现当代社会历史沧桑巨变,陆文夫在身体地理变换中自我身份也经历多次转换,反映在《美食家》中,两位主人公人生轨迹因20世纪中国社会巨变,如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大跃进”“文革”及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交织,造成身份认同困境。小说中陆文夫详细描述苏州美食味觉来源于“鸳鸯蝴蝶派”作家对市井风味的书写。五六十年代,他与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等交往甚密,随之领略苏州的精致生活,包括美食、古董、园艺,感悟苏州市井文化。尤其是在周瘦鹃熏染下,陆文夫对苏帮菜精致微妙处展开实质性体验,“周先生每月要召集两次小组会议,名为学习,实际上是聚餐,到松鹤楼去吃一顿。”[10]此番经历使陆文夫了解苏州味觉从剔除传统味觉,到迎合大众菜味,再到恢复苏帮菜精致味觉变迁,由此促使其确立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苏州市井饕客身份。
陆文夫《美食家》以苏州市井空间为背景,通过“我”与“美食家”朱自治身体地理不同生存空间彰显对食物味觉截然不同的追求,是对中国20世纪社会城乡转换中身体地理对味觉变迁建构的真实写照。小说中的身体地理经历三段空间转换,从而完成建构味觉人生的身份认同:第一段是解放前,借助房屋空间形成靠收房租生存的朱自治和寄人篱下的租客“我”的身份不平等关系。在身体寄存空间中,朱自治身体地理游走在吃晚饭后睡觉的家空间、睡醒了吃朱鸿兴头汤面的面馆、吃饱了喝茶的茶楼、吃过中饭去的澡堂。相较而言,“我”的身体地理停留在靠帮朱自治干家务活而寄居其家的出租屋、等朱自治赏钱的酒店门口、为朱自治跑腿买吃食的各种店铺。朱自治身体地理的一天从吃开始,到吃结束,形成完整的味觉仪式。“我”从等朱自治赏钱到为他跑腿买吃食,完成由贫困到失掉尊严再到恨吃而参加革命的生存过程。在身体地理转换中,朱自治身体地理味觉体验展现为享受,“我”的身体地理味觉体验则彰显压抑。个体身体地理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叙事,成为驱动国家空间重组,进而改变现有不平等身份的心理初始地。“我”决心离家到解放区,打破身体被囚禁的空间,参与国家空间解放重组革命中,获得革命身份,实现身体地理空间的重构。在《美食家》中,国家空间重组体现为改变身体地理不平等,进而改变不平等空间中身份认同关系的合法性。
第二段身体地理味觉身份建构更为复杂。首先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作为反吃之人被派到苏州名菜馆指导如何建构新味觉,“我”获得领导吃的新身份。名菜馆的公共领域成为施展“我”打破不平等空间关系的场域:将高贵菜谱换成大众家常菜单,将带有隔断的包房拆成大食堂。“我”运用革命理性至上手段顺应时代需求,让人们获得味觉上平等的身份。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发动的味觉革命却因大众反对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看似平等的味觉身份被剥夺了差异(精致与大众差异),“我”剥夺了大众享受精致苏帮菜的味觉权利,形成新味觉身份不平等。而朱自治却在精致味觉引领下,身体地理进入国民党政客姨太太孔碧霞的女性味觉空间中,她引领朱自治过上优雅生活。
一个会吃,一个会烧;一个会买,一个有钱。两人由同吃而同居,由同居而宣布结婚,事情顺理成章,水到渠成[11]。
陆文夫让边缘女性孔碧霞的味觉空间中保留纯粹苏帮菜味觉。女性味觉既代表作家对传统味觉的留意,亦隐喻宏大革命空间无法祛除文人对日常生活空间的追求。“我”为迎合大众身体需求革命掉传统味觉,朱自治为满足个人身体享受深入到传统味觉中,强烈对比叙述强化日常生活空间之于生命存在的价值维度。超越宏大空间的叙事策略,展现出市井生活空间平庸与神奇的两面性。陆文夫运用身体味觉之刃批判味觉革命,揭示中国城乡转换中粮食经济偏狭问题:
大跃进的时候人人都顾不上吃饭,困难年人人都想吃饭了,却又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酱油都要计划供应了,谁还会对大众菜有意见?连菜汤都一抢而空,尽管那菜汤是少放油,多放盐。凡是能吃的东西人们都能下肚,还管它什么滋味不滋味[11]。
困难年代与文革时期,被剥夺味觉之后,“我”与朱自治的身体地理被安排在同一地理空间。陆文夫通过不停转换身体地理空间的叙事策略,将反对味觉享受的“我”与贪图味蕾满足的朱自治形成强烈对照,既展现人性对味觉追求的两面性,又流露出身份认同矛盾。“我”努力摆脱朱自治,但他却伴随并折磨“我”四十年,陆文夫借助二人在不同时空中的身份纠结,透露其对苏州传统味觉的记忆与怀念,及自我身份在历史空间动荡中的认同矛盾。
第三阶段是味觉地理的当代期。在复杂人生纠葛中,“我”与朱自治在新时期味觉空间中暂时和解。“我”邀请朱自治到名菜馆讲座,朱自治邀请“我”去家中赴宴。在朱自治家宴中,老领导风派人物包坤年和三位市侩气人物,同朱自治商谈所谓“烹饪学会”大事。陆文夫细致描述家宴中精致菜系和味蕾体验,及苏州园林般的就餐环境,把一众人物聚集到味觉空间中。陆文夫描述的苏州美食味觉眷恋不已的饕客身份,及其对“美食家”富有讽刺性的用词,还原了一个游离在味觉饕客之外的革命青年身份。通过对味觉地理空间的社会改造,《美食家》构筑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空间的反讽式点评,也展现出对多重身份认同的困扰。此为陆文夫之纠结,更是社会历史之纠结。囿于历史时空限制,自我身体地理只能在实体空间中占一席之地,“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身体存在方式让每个个体均无法获得超越空间羁绊的身份认同。因此,才有身体地理的隐喻空间和情感空间试图挣脱囿限,获得心之所往的身份认同,此为身体寻找安全之地的最终旨归。陆文夫在《美食家》中以苏州美食的味觉沧桑变化评点中国现当代历史,特别是以食物话语重构中国历史空间转换中的民族和自我身份认同。
四、结语
身体地理在味觉历史期待中匆匆前行,而心灵记忆却要时时回溯过去,希望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发现某种关系。身体地理在味觉变迁的历史时空中遗留下无数文明痕迹,而心灵回望则成就一部饮食文明史。不同时代背景、知识结构、历史意识,促成不同身体地理对中国城乡时空转换中的味觉身份关照,带有明显时代痕迹和特殊意味的味觉空间,为文学叙事提供一种既有历史感又颇具感性的味觉记忆。
身体地理在城乡转换中所到之地,通过饮食空间的味觉体验,折射出社会机制与主体能动性间的互动关系。在此互动关系中,城乡所谓二元关系被消解在味觉地理的感性体验中,变成历史记忆及个体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