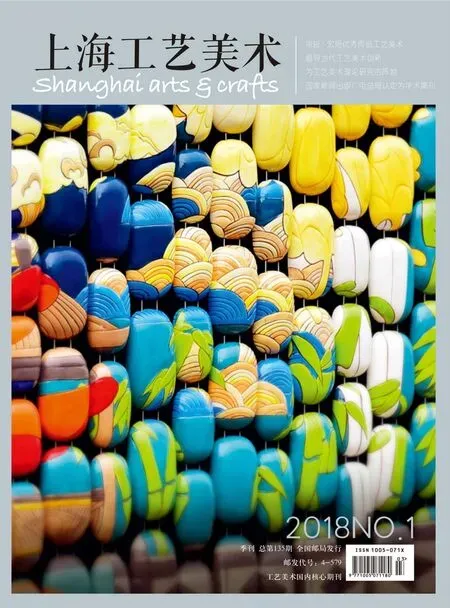守“拙”与维“新”中国工匠精神理性回归的几点思考
2018-04-13段卫斌
段卫斌
As for craftsmanship spirit, this is never simply a judgment for the right and the wrong. The fundamental path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craftsmanship spirit is taking root in the local soil, clarify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blazing the path of “modernization”.
工匠精神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伴随着质疑。究其根源,是对于“本土工匠精神”的误读,这种误读可以追溯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本土文化的断裂、西方话语的遮蔽。重提工匠精神,并非简单的是非评断,立足本土、廓清认知、寻求维“新”之道才是本土工匠精神传承与发展的根本路径。
一、“技、艺、道”一体相生的本土工匠精神
在我看来,中国本土对于工匠精神的认知理论,可以用围绕造物的“技”、“艺”、“道”三个维度概括。《庄子》中借用庖丁解牛的典故,对“道”与“技”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即“道”进乎技、“道”在“技”中,“道”、“技”合一。清代思想启蒙先驱魏源概括为:“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
“技、艺、道”构成了工匠文化体系中的三个维度,并呈逐层递进的关系,对应工匠层次的提升过程:“技进乎艺,艺进乎道”。这三个维度在不同的国度却有着近似的解读。在日本,传统手工艺行业有“守·破·离”的三重境界:“守”是对技艺的坚守和反复磨炼,“破”是对固有的程式化审美范式的突破,“离”是一种化有形的规矩为无形之“道”的超脱;古代西方匠艺文化的层级划分,也类似表现为“工匠”、“艺术家”和“大师”之间的界定。可见,“技、艺、道”构成传统工匠精神形成的三段表征,是具有哲学观的普遍性的。20世纪最具创造性的思想和政治理论家之一汉娜·阿伦特把劳作分为两类:“劳动之兽”和“创造之人”。他认为单纯的匠技不能被称为是艺术,好的作品大多灌入了匠人的思想与灵魂。而我们称之为上上之观的“道”,也是创作者基于“技”的基础将自己对生活、经历的感悟寄语作品,为作品赋予灵魂,赋予思想。
在艺术设计过程中,“技”和“艺”是“道”的基础,“道”通过“技”与“艺”来体现。一件优秀的作品是既精于“技”“艺”,又重于“道”,三者是一体相生的存在。

以传统失蜡法和制铜工艺为华特·迪士尼设计的产品
二、“遮蔽”与“断裂”:廓清工匠精神的本土框架
工匠精神在当下成为久违的热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完善激励机制,培育众多“中国工匠”,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然而,本土工匠精神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承,始终缺乏理性的认知框架,而陷于各种扭曲和误读之中,最终导致传承的断裂。工匠精神所对应的历史进程之时间轴,大致表现为从“手工艺时代”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再到“后工业时代”的序列关系。中国本土工匠精神的断裂,正是发生在从“手工艺时代”进入到“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第一环节,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受裹挟地被动西化,以及由于这种“被动”所产生的面对“现代化”的矛盾心理,使我们对于本土工匠精神的态度,长期游走于“扬”与“弃”的两个极端,而一直难以进行理性的认知。
传承一旦产生断裂,无法通过简单的复古或照搬进行衔续。廓清工匠精神的本土框架,使我们能够清晰认识到这种“遮蔽”与“断裂”,才能为本土工匠精神的回归建立理性认知的框架。一方面,“被现代化”历程中受到“遮蔽”的本土工匠精神的价值和意义需要重新审视;另一方面,本土工匠精神也需要在“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语境下进行重构。

以传统失蜡法和制铜工艺为华特·迪士尼设计的产品
中国手工业历史中并不缺乏工匠精神。相反,本土的工匠精神不论从实物遗存还是从研究著作看成果都非常丰硕。悠久的中国文明史中对古人高超的制造工艺和手工技艺有着本能的价值推崇。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孙机在其撰写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以详实的史料论述了中国古代工匠超群技艺的辉煌。然而这种辉煌在现代化来临时被西方文明遮蔽——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文明史》中认为:“古代中国发达的手工艺技术(包括一些古代科技),并未能使中国自发产生类似西方工业革命那样的‘现代化’历程。”从本土视野看,本土手工业文明自发的“现代化”过程未及发生发展,便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断或终止了。阿尔文·托夫勒曾说,“工业化像历史中汹涌的洪水,短短三百年,使之前的一万年黯然失色。”在西方现代化的强势浪潮之下,本土农业文明下积孕多年的手工业文明与本土工匠精神一道被遮蔽了,使得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只能对西方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话语权杂糅在“现代化”中,逐步令我们丧失自己的文化特质。而要坚守本土自主性,又经常被迫站在落后的农耕文明立场上抗争,这恰与时代潮流相悖。
三、守“拙”:基于技艺的职业坚守
“拙”,通俗来讲就是下“笨功夫”进行劳动和技艺磨炼。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是“劳动即价值”,认为劳动天然具有价值属性。从价值认知的角度来认识“工匠精神”,其价值源泉正是来自于人类在造物过程中最原始的“劳动”的价值。即使到了生产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蕴含“工匠精神”的制造品牌,如瑞士的制表业、法国和意大利的皮具作坊等,也能成为行业中的高端品牌闻名于世。“劳动”还是一种品格教育的有效途径。日本著名实业家、哲学家稻盛和夫在《干法》中说:“劳动的意义不仅在于追求业绩,更在于完善人的内心。埋首工作不知不觉深耕于内心,陶冶人格、磨炼心性、提升灵魂。”
高超技艺的产生,源自笨拙、机械的练习和不厌其烦的雕琢、打磨。无论发明锯子被称为木工祖师的鲁班、身怀绝技的庖丁、还是将尺长的木头雕刻成宫殿的王叔远,他们的高超技艺都是长期磨炼的结果。古人常用运斤成风、鬼斧神工、妙手偶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游刃有余、巧夺天工等词语来赞美工匠技艺之“巧”、“妙”,容易忽视的正是其背后用功之“拙”,而“拙”中所蕴含的优秀特质我们可以梳理为以下几方面:
以“拙”致“巧”。古人崇尚“拙巧”的造物精神,“拙”体现的是功夫,而“巧”是结果,两者彼此相依,即“拙”中有“巧”,拙巧相生。朱熹曰:“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磨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可见“精益求精”的造物理念,正是从笨拙的“琢磨”中体现出来的。道家之谓“大巧若拙”,即造物最终追求的“大巧”,正是来自于“朴拙”。这也回应着道家一贯“反智巧”的审美思想。
专注、精诚的态度。《庄子·达生》中有梓庆削木为鐻(一种乐器)的典故,见者皆惊叹其鬼斧神工,鲁王闻听后召问梓庆:“你是用什么方法制成鐻的?”,梓庆答:“我只是在做时用心体会,从不分心。”排除外界一切干扰的“专注”,正是工匠精神的必要前提。一入技艺之境,“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与!”以天合天,是将工匠创造的“天性”与自然造化的“天道”相合,这正是需要“用志凝神”的缘故。
“彊勉”的职业道德。“彊勉”意即尽自己所能,努力而为之。在《墨子》一书中,墨子视“彊力从事”为所有职业的道德标准,成为一种职业哲学,墨子强调上至王公大人、士人君子,下至农人、妇人等皆需做好分内之事。中国自古就有的这种对于职业的尊敬和努力投入之心,对于当下中国浮躁和功利的现状,亦或是对症之良药。

以“产品设计的工匠精神”为题的产品设计实践
质朴的工艺“温度”。有别于机械生产的产品,通过匠人之技艺制作的产品不但独一无二,而且承载着浓烈的情感、传达着手工的“温度”。精益求精的手工制作方式,在工业化的初期看来往往意味着固执、缓慢、少量、低效,而随着今天大量工业品的泛滥和充斥,到处是冰冷的金属和高分子聚合材料,传统工艺丰富而细腻的质感与情感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珍视,而背后蕴含着的专注、技艺,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更显得弥足珍贵。
四、维“新”: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工匠精神
传统的工匠精神诞生于农耕经济下的手工行业,是传统农业文明下的精神产物。直接将其照搬于当今社会显然不合时宜——其中各种时代的局限性,在我们重提工匠精神的同时也必须有清醒的认知。例如,古代社会的阶级性在手工艺行业就表现为对“装饰”的过度推崇,以致发展成与功用完全分离的“工艺堆砌”,在后期更是发展为僵化的“装饰程式”,这显然不符合近代以来的“民主设计”理念。近现代化的历史,经历了从“手工业时代”到“工业化时代”的转变,“现代性”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通识语境,以作坊为基本模式的传统手工业早已不是主流的造物方式,照搬本土传统只能成为因循守旧。
工匠精神之维“新”,首要需形成“发展”的“工匠”概念认知。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在《匠人》一书中这样解读“现代工匠”:“通过制造的物品去了解自身,体现时代的生活品质和审美特征。”在他看来,“制造就是思考”,一个人从事于某一行业而能够脱颖而出,其决定性的能力来自于他的思考力,即他对本专业的专注、对技术的敏感以及对当代审美趣味的掌控和扬弃。由此可见,“新工匠精神”的培育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培育手艺人的守“拙”精神。专注于作品本身,尊重制造的基本规律,执着于对技术及细节的雕琢。作品是创作者的人格投射,更是职业精神的物质性呈现,这是古典的精益求精态度,也是“新工匠精神”的内核。
2.培育现代性审美视野。如对于制造业来说,应注重产品功能与形式的统一、能够合理运用现代生产工艺和科技成果,符合现代审美观念,与当代的一切新技术、新思维、新生活方式俱进。以邻为鉴,一战后的日本以柳宗悦为代表的学者们,发起了影响深远的“民艺运动”,通过对民间手工艺的研究和发掘,确立了日本人的文化和审美自信。柳宗悦在“民艺运动”中倡导“Yo no Bi”式的设计,即“用”与“美”合一的设计原则,这奠定了简洁与实用的民艺美学基础,逐步成为日本社会独有的美学标准,使日本现代设计在注重科学性和功能性的前提下,形成独特的审美体验。二战后的柳宗理、喜多俊之、黑川雅之、深泽直人等几代日本设计大师,正是沿着具有日本民族特质的现代化审美路径走下去,才使日本的当代设计能独立于西方而自成一格。“用”与“美”的融合,也成为日本“职人精神”的完美写照。
3.培育团队协作能力。“新工匠精神”还应该包含现代团队协作精神和整合能力。当代产品开发的过程是精细划分协作的,具有复杂的开发流程。创新型产品的制造不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闭门造车”式的生产方式已经滞后,团队协作必然引发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从而形成合力、实现共赢。
4.培育创新性思维能力。创新型产品必须与传统不同、与众不同。创新性思维能够在重构审美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甚至能够重新定义未来。从设计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角度看,创新型思维不仅是要打破传统窠臼,精益求精地制作,还包含了不断吸收前沿的设计思想、审美观念和科学技术。
现今方兴未艾的互联网经济、定制化生产、柔性化制造等新的模式,有逐步替代前两次工业革命所确立的机器大工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等“现代化”生产模式的趋势。这是本土工匠精神回归的良好机遇。传统作坊制生产模式所具有的灵活性、针对性、匠作品质与“作者性”意识,能为产品供给侧升级改革提供很多启示。近代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曲折历史,也警醒我们在当下面临的新经济浪潮中必须坚持本土性和自主性。本土工匠精神,不仅是先人造物思想的内聚和升华,也是传统人文理想的物质表征。我们不应被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桎梏,而忽视传统人文的熏染。若将本民族赖以存续的人文精神的内核抽离,则振兴与繁荣亦将成为一纸空文。形成具有新时代特质的工匠精神,才能形成“硬实力”与“软实力”兼备的本土物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