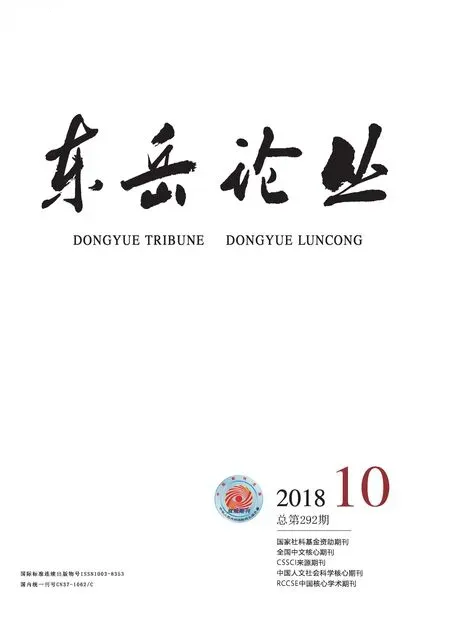《爱的教育》:从意大利到日本
2018-04-12颜淑兰
颜淑兰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引 言
意大利作家艾德蒙托·德·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 1846-1908)的Cuore出版于1886年,是世界著名的教育小说。该书主人公为意大利小学三年级学生安利柯,以日记的形式叙述了安利柯一学年中的所见所闻。小说中还穿插了安利柯父母写给安利柯的话以及每月一篇名为“每月例话”的独立故事。
该小说于1924年由我国现代教育家、翻译家夏丏尊(1886-1946)译成中文,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至23号(中有间断),题为《爱的教育》。夏丏尊不懂意大利语,译文主要是从日本教育家三浦修吾所译《爱的学校》(『愛の学校』)转译而来,“爱的教育”这一译名也是受到日译本书名的启发,且至今仍被各种不同版本的译本所采纳。夏丏尊的译文在当时受到了众多读者的欢迎,据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单行本“好评啧啧,被多数中小学校采为教本,不到三个月初版便即告罄”[注]《夏丏尊译〈爱的教育〉归本店发行》,《北新周刊》,1926年12月4日第16期。。1926年改由开明书店出版,此后的九十余年间,其在中国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1930年代,《爱的教育》被列入“浙江省教育厅师资进修通讯研究部”应修书之一,被浙江省小学教员广泛阅读,并在教员之间引起一场争论;1950年代后期至“文革”时期,它又被当作体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读物遭到批判和摒弃;1980年,该书重新回到中国读者的视野,不仅夏丏尊译本得以再版,还出现了田雅青所译《爱的教育》(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其它译本;2001年,《爱的教育》被教育部指定为中小学语文新课标课外阅读书目之一,并多次被教育部、团中央以及各地评选为中小学最佳课外读物。此后,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各种版本的《爱的教育》。
夏译《爱的教育》自发表至今的九十余年时间里,通过多种媒体和渠道,以读本、漫画、电影、有声书等多种形式,被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众多中国读者阅读和阐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身份的读者对其的解读截然不同,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意义不断发生变化。学界有关《爱的教育》的研究不在少数,但是,关于日译本及其译者三浦修吾在日本被接受阅读的情况,关于夏丏尊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关于《爱的教育》在中国不同时期被接受的情况等,却未见系统充分的论述。夏丏尊对民国教育界的批判以及关于“爱的教育”的主张,一方面生发于现代中国“儿童的发现”这一内在背景,另一方面也受到三浦修吾这一日本外在因素的不小影响。因此,如不先对三浦修吾的教育理念及其译《爱的学校》作具体研究,不仅无法全面理解夏丏尊翻译《爱的教育》的动机,对于这一文本从意大利经由美国、日本再到中国的旅行过程也难有整体的把握。有鉴于此,本文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小说内容和Cuore在意大利诞生的时代背景展开讨论,通过文本对照分析三浦修吾在翻译过程中为迎合目标语境所做的处理,最后梳理《爱的学校》在日本的接受状况,以期为国内的夏译《爱的教育》研究提供参考。
一、Cuore时期的意大利
1886年10月Cuore在意大利出版。著者艾德蒙托·德·亚米契斯早年就读于陆军军官学校,1865年参军,参加过抗击奥地利的意大利第三次独立战争(1866-1870)。他在军营中开始写作,早期作品发表在报纸《军国意大利》上,1867年离开战地后还被派到《军国意大利》工作。作品《战地生活》(1868)即由发表在《军国意大利》上的文章结集而成[注]上野山賀子:「『クオレ―愛の学校』について」,[意]デ·アミーチス:『クオレ―愛の学校』(下),矢崎源九郎译,東京:偕成社文庫,2010年版,第351-352页。。1871年离开军队专事写作,另著有《西班牙》(1873)、《荷兰》(1874)、《摩洛哥》(1879)等多种游记。其所有作品中,Cuore的销量和影响最大,在意大利发表当年即再版40次,成为许多小学的课外读物。出版六年之内就被译成西班牙语、希腊语、俄语、英语和法语等十多种语言。
Cuore中的故事发生时间被设定为1881至1882年,书中主要体现的是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的价值观。意大利半岛历史上长期受到西班牙、奥地利和法兰西的威胁,处于分裂和混乱的局面。1796年至1814年,拿破仑的入侵和统治一方面使得意大利遭受蹂躏与掠夺,另一方面也使拿破仑法典等法国管理制度在意大利得以实施。尤为重要的是,“随着旧的国家界限的消失,人民开始把自己看作意大利人,而不是托斯卡纳人或皮埃蒙特人,于是一种民族自觉的轮廓开始显露出来。”[注][英]赫德 韦利编:《意大利简史》,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31页。1859年至1870年,在撒丁王国的领导下意大利地域内的各邦国统合到全新的“意大利王国”政治体系中,由此基本形成了新的民族国家。日本学者藤泽房俊著有《Cuore的时代》一书,结合小说中的内容对19世纪的意大利作了详细介绍,多角度阐述了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形成。据其考证,Cuore出版的1886年,意大利公共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历史教育的通告,要求小学教育培养“对祖国和国王献身的国民”[注]藤澤房俊:『クオーレの時代』,東京:筑摩学芸文庫,1998年版,第7页。。这种教育方针在Cuore中多有体现。“每月例话”中的《少年爱国者》《少年侦察兵》《少年鼓手》,讲述的都是意大利少年为抵御外敌不惜牺牲自我利益甚至生命的故事。《少年爱国者》中的贫穷少年听到曾经施舍自己钱币的外国人诋毁意大利,愤然将钱币掷回——其中的三个外国人无疑是曾征服和统治过意大利的法兰西、西班牙和瑞士的象征。《少年侦察兵》讲述1859年法意联军为救伦巴德(米兰省当时的名称)与奥地利作战时期的故事。故事中的少年冒着危险爬上树梢侦察敌情,被敌方子弹打中坠地身亡。《少年鼓手》则是以1848年意大利与奥地利之间发生的库斯托扎(Custozza)战争为背景。故事中的少年为帮助意大利军突围前往本部军队送信求援,途中被敌军发现受到袭击,身负重伤但仍然坚持把信送到。这些篇章都是弘扬少年为国献身的精神。
《爱国》一篇中安利柯的父亲对安利柯说:“我为什么爱意大利!因为我母亲是意大利人,因为我脉管所流着的血是意大利的血,因为我祖先的坟墓在意大利,因为我自己的生地是意大利,因为我所说的话、所读的书都是意大利文”[注][意]德·亚米契斯:《爱的教育》,夏丏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5页。。这种说法无疑是将血缘和种族、语言、地理等因素当做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我所说的话、所读的书都是意大利文”,俨然是说意大利固有一门全体国民共有的意大利语。但正如厄内斯特·勒南在讲演《国族是什么?》中所言,种族、语言、利益、宗教相似性、地理、军事需要等要素均不足以建立民族国家。勒南道:“族类学方面的考量对于现代国族的构成毫无意义。法兰西既是凯尔特人的、伊比利亚人的,又是日耳曼人的。德意志既是日耳曼人的,又是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的。意大利在族类学方面则是最为模糊的:光是高卢人、伊特鲁里亚人(Etrusques)、佩拉斯吉人、希腊人就已经混杂在一起难以辨认了,更不要说还有其他成分”,“真实的情况是,纯粹的种族并不存在,基于族类学分析制定政策,无疑是异想天开。英格兰、法兰西、意大利这些最高贵的国家,也是混血程度最高的国家”[注][法]厄内斯特·勒南:《国族是什么?》,陈玉瑶译,《世界民族》,2014年第1期。。从语言方面来说,实际上直至19世纪60年代,现已成为意大利官方语言的佛罗伦萨语还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通用语言,除了托斯卡纳人、小部分罗马人以及其他地区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以外,不为一般意大利民众所理解。各地区的民众使用各自的方言,方言之间差异巨大,以至于不同地区的人之间沟通十分困难。不同阶层使用的语言也各不相同[注]藤澤房俊:『クオーレの時代』,東京:筑摩学芸文庫,1998年版,第153-154页。。Desmond Hartley在他1986年的Cuore英译本导论中也指出,年轻时亚米契斯就追随著名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认为佛罗伦萨的方言应该被定为标准语,他因此完善自己的佛罗伦萨式意语,并将它用于写作。可以说,正是Cuore“帮助建立了当代意大利文学语言的标准”[注]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文心〉:1920年代教师作家笔下作为教育对象的儿童》,徐兰君、[美]安德鲁·琼斯(Andrew F.Jones)主编:《儿童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
小说这一媒介对于形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巨大作用无须赘述。Cuore的读者或许互不相识,但他们却在同一时间段之内阅读着同一本小说。小说中关于意大利“建国三杰”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以及开国君主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等的叙述,均在意大利读者心中唤起共同的民族想象。换言之,Cuore的广泛传播无疑促进了现代意大利统一性的建构。
培养国民意识的自觉还体现在该书对地图功能的充分认识和利用上。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曾指出,人口调查、地图绘制和博物馆建设是形塑民族国家自我想象的三种权力制度。关于其中地图一项的功能,日本学者若林干夫在《地图的想象力》(增补版)中有详细的阐发:
地图中包含的从高空鸟瞰整个空间的视角不归属于任何特殊的个体。正因为如此,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的视角加诸其上。“不被任何人所属,因而可以为任何人所属”,也就意味着地图的视角超越了社会内部某个特定成员的视角(也即面对局部空间的视角),并由于这种超越性而成其为一种普遍的视角(也即面对全域空间的视角)。[注]若林幹夫:『増補 地図の想像力』,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09年版,第48-49页。(所引日文文献皆由笔者翻译,下同。)
确实,一个国家的国民只有通过地图才能看到国家的“整体”,地图视角的超越性使得个体能够实现与他者视角的重合,并与他者拥有共同的空间想象。因而,近代国家体制的成立需要地图将国家领土作为统一的整体可视化。
Cuore中就有学习成绩优秀的代洛西在安利柯家中背诵意大利地图的场景:“‘我现在眼前好像看见了全意大利。那里有亚配那英(即亚平宁——笔者注)山脉突出在爱盎尼安海中,河水在这里那里流着,有白色的都会。有湾,有青的内海,有绿色的群岛。’这样顺次把地名背诵,全然像眼前摆着地图一样”(《友人的来访》);教师也在意大利地图上将转学新生的家乡“格拉勃利亚的莱奇阿”的位置指给学生看(《格拉勃利亚的小孩》)。此外,Cuore中的“每月例话”以意大利各地为题材,亚米契斯有意识地将帕多瓦(《少年爱国者》)、佛罗伦萨(《少年笔耕》)、那不勒斯(《爸爸的看护者》)、罗马涅(《洛马格那的血》)、热那亚(《六千里寻母》)、西西里(《难船》)等意大利各地的地名穿插进故事中。正如Cuore的另一日译者前田晁所言,帕多瓦此前曾是受奥地利统治的威尼斯王国的一个都市,佛罗伦萨原本属于托斯卡纳大公国,罗马涅则是教皇领属[注]前田晁:「あとがき」,[意]:デ·アミーチス『クオレ』(下),前田晁译,東京:岩波少年文庫,2009年版,第293页。。而此时,这些地方全部统一进了名为意大利的民族国家之中。毋庸置疑,这些地名增强了小说“写实”和民族主义的效果——熟悉这些地名的,正是我们——意大利人——读者。借用安德森的话,这些地名“从小说的‘内部时间’向(意大利)读者的日常生活的‘外部’时间的因果推移,犹如催眠术一般地确认了一个单一的,涵盖了书中角色、作者与读者,并在时历中前进的共同体的坚固的存在”[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
除了对民族意识的强调,书中还宣扬了一种超越阶级的友爱和互助观念。安利柯的父亲告诫安利柯要多和劳动者子弟交往,说:“上流社会好像军官,下流社会是兵士。社会和军队一样,兵士并不比军官低贱”[注][意]德·亚米契斯:《爱的教育》,夏丏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2页,有改动。。但事实上,当时的意大利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和贫富分化,Cuore中的一些情节也暴露了这个事实。意大利1877年成立了贯彻义务教育的高皮诺法(Coppino Act),规定六岁到九岁的儿童必须履行下级小学一、二年级的入学义务。就是说,安利柯所读的三年级(三浦修吾和夏丏尊译作“四年级”——笔者注)已经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注]藤澤房俊:『クオーレの時代』,東京:筑摩学芸文庫,1998年版,第70-71页。。安利柯为四年级(三浦和夏丏尊译作“五年级”)结束后将不得不和许多同学别离而感伤,自己和代洛西等人要入高等学校,而卡隆、泼来可西等却不得不进入工厂或劳动界(《痊愈》)。换句话说,作为资产阶级后代的安利柯与劳动者后代的同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将来,Cuore是在承认这种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提倡超阶级的爱。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是符号化的。《少年侦察兵》中的少年,学习成绩优秀的“富商之子”代洛西,此类正面人物皆被设定为“金发”,相貌很好。而且小说多处不惜笔墨突出这一形象:少年侦察兵在冒险侦察时,“那蓬蓬的头发,在日光中闪作黄金色”,在他牺牲后军官和兵士齐声呼喊:“金发儿万岁!”代洛西是“身材高大,神情挺秀,黄金色的发蓬蓬地覆着额头”(《级长》),在上台领奖时,“金发的头昂昂地举着”(《奖品授予式》)。与此相对,从意大利南部的格拉勃利亚地区转学而来的少年则是“黑色、浓发”“眉毛浓黑”。这种差异化包含了对南部意大利人的偏见和歧视。《卖炭者与绅士》中,诺琵斯的父亲是个“身材很高有黑须的沉静的绅士”,而培谛的卖炭父亲则是个“全身墨黑的矮小的男子”。在接受绅士儿子的道歉时卖炭者表现出的谦卑,也无异于强调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
二、《爱的学校》在日本
夏丏尊在《爱的教育》译者序中明言译文“曾对照日英二种译本,勉求忠实”[注]夏丏尊:《译者序言》,[意]德·亚米契斯:《爱的教育》,夏丏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页。。关于日译本和英译本的所指也有明确说明:英译本“仍作《考莱》,下又标《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日译本“曾见两种,一种名《真心》,忘其译者,我所有的是三浦修吾氏译,名《爱的学校》的。[注]夏丏尊:《译者序言》,[意]德·亚米契斯:《爱的教育》,夏丏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页。
据三浦修吾自述,《爱的学校》是从英译本转译的[注]三浦修吾:「『愛の学校』の出版につきて」,[意]デ·アミーチス:『愛の学校』,三浦修吾译,東京:文栄閣書店、春秋社書店,1912年第3版,第12-13页。,1912年由文荣阁书店和春秋社书店共同出版。此前日本曾有几种节译本——原抱一庵《伊国美谈:十二健儿》(东京内外出版协会,1902年5月)、抱一庵《三千里》(东京金港堂,1902年11月)、杉谷代水《学童日志》(东京春阳堂,1902年12月)等。这些译本仅译出原书的部分章节,杉谷代水的译本甚至将大部分故事的背景搬到了日本,原作中意大利的人名地名等均被改为日本的人名和地名,准确地说更接近改写[注]李青的博士论文《包天笑译介教育小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15年)对以上三种日语节译本有较详细的阐述。。三浦修吾所译《爱的学校》是Cuore在日本第一部完整的译本。
三浦修吾(1875-1920)生于福冈县浮羽郡千年村(现吉井町)。1895年二十岁时进入福冈师范学校,跟随同乡野口援太郎学了约一年的教育学,1899年毕业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学习四年,毕业之后相继在鹿儿岛师范学校和姬路师范学校就职,讲授英语、教育学及修身等科目。除了译作《爱的学校》,另著有《学校教师论》《行第二里之人》《生命的教育》《真实的教育》等书,前两种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日本关于三浦修吾的研究成果极其有限,可举者仅鸟谷部阳之助《三浦修吾与三浦关造:大正自由教育者与瑜伽开拓者兄弟》[注]鳥谷部陽之助:「三浦修吾と三浦関造——大正自由教育者とヨーガのパイオニアの兄弟」,鳥谷部陽之助:『畸人——大正期の求道者たち』,東京:彩流社,1989年版,第162-187页。和上田祥士、田畑文明《大正自由教育的旗手:实践的中村春二和思想的三浦修吾》[注]上田祥士,田畑文明:『大正自由教育の旗手——実践の中村·思想の三浦修吾』,東京:小学館スクウェア,2003年版。及岩间浩《三浦修吾、关造与新教育运动》[注]岩間浩:「三浦修吾·関造と新教育運動(1)」,『教育新世界』,2005年第53号;岩間浩:「三浦修吾·関造と新教育運動(2)」,『教育新世界』,2006年第54号。等二三种。从标题即可知,这些研究主要将三浦修吾与其弟三浦关造(1883-1960)作为大正新教育运动的先驱来评价。
《爱的学校》是三浦修吾任职于姬路师范学校期间所译,在大正、昭和时期非常畅销。出版当年,教育家、成蹊学园创立者中村春二在成蹊“夏季学校”上讲给学生听,大受好评。中村因此给三浦修吾写感谢信,二人得以相识。1917年,三浦修吾应中村之邀进入成蹊实务学校任教,担任英语作文、修身等课程,同时担任成蹊内部刊物《新教育》的主编[注]岩間浩:「三浦修吾·関造と新教育運動(1)」,『教育新世界』,2005年第53号。。此外,时任文部省图书官八波则吉还将该书作为翻译典范并采纳为国语读本。
1912年8月出版的《爱的学校》第三版收录了大量关于此书的评论及推介文章。从中可见,从初版至第三版的仅两个月之间,《爱的学校》就受到姬路师范学校校长野口援太郎、《内外教育评论》主笔大岛正德、作家水野叶舟等人以及《读卖新闻》《大版每日新闻》《中央公论》《大日本青年》等十几种媒体的广泛推介。其中,大岛正德极力吹捧道:“作为日本人只要一读Cuore,谁都不能不立即注意到我国教育界的缺点。特别是现在正执教鞭的人们读此书必自然产生大耻大悟之感”,“不仅从事教育之人,如学生与父兄也开始广泛阅读Cuore,我国教育界无疑将别开新面。”[注]大島正徳:「読め、「クオレ」を」,[意]デ·アミーチス:『愛の学校』,三浦修吾译,東京:文栄閣書店、春秋社書店,1912年第3版,第2页。《时事新闻》上的《出不良少年之现时家庭的必读书》一文更是极尽赞美之词,称书中“有津津有味的教训谈,有天真无邪的社会观,有不矫揉的人物评,有不造作的抒情文,满篇皆是金玉文字,几无一处赘言。思想之稳健,叙事之深切,作为少年少女的读物真不失为近来少见的好作品。”[注]時事新聞「不良少年を出す現時の家庭に必読の書」,[意]デ·アミーチス:『愛の学校』,三浦修吾译,東京:文栄閣書店、春秋社書店,1912年第3版,第9-10页。此外,小川菊松曾在1924年2月出版的第37版中证言:“早年Cuore的电影被引进而盛极一时之时,曾擅自使用《爱的学校》一名招揽顾客,文学士出版《Cuore物语》时也不得不标上副标题‘又名爱的学校’,可见此书销量之非常,《爱的学校》这一题名也成为不可撼动的经典。”[注]小川菊松:「本書の改版に際して——「愛の学校叢書」の刊行につき——」,[意]デ·アミーチス:『愛の学校』,三浦修吾译,東京:誠文堂書店,1924年第37版,第1页。
《爱的学校》在日本影响如此之大,那么,三浦修吾翻译的动机是什么?他在翻译过程中做了哪些处理?《爱的学校》又是如何被阅读的?
三、个性教育与“忠君爱国”之间
明治末期至大正时代的日本,源自德国的赫尔巴特主义教育学由于不断普及并流于形式化和刻板化而遭到批判;同时杜威、蒙台梭利等的教育理念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日本教育界的关注。在此背景下,以私立学校为中心兴起了以尊重儿童个性和自主性为诉求的所谓“新教育”(又称“自由教育”)运动。三浦修吾即被公认为此新教育运动的先驱。三浦的著作中确实多见关于个性教育、人格教育的主张。在《生命的教育》里,三浦批判当时日本的学校教育“千篇一律、同型同色”,教师教学“模仿他人之处甚多,却不知创造自己独特之处”,其中几乎见不到“个性的活跃、生命的流动”,因而不能刺激儿童和学生的心灵。他说:
教师必须熟悉、爱好其所教的学科,也应该欢喜从事该学科的教学。进一步说,其教学必须能够体现教师独特的个性。即便运用同样的材料,讲授相同的教材,如果其中没有他人无法企及的独特之处,教学就不可谓成功,因而也就不能说是有生命的。因为生命不是从形式中产生,而应该来自教师的个性。[注]三浦修吾:『生命の教育』,東京:イデア書院,1926年版,第14页,第25页。
真正的教育,只建立在完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今日教育的当务之急,是教师和学生都卸下理智的幌子,转而以全部的人格相待。除此之外的任何手段,都绝不能赋予教育生命[注]三浦修吾:『生命の教育』,東京:イデア書院,1926年版,第14页,第25页。
三浦认为,教师的个性、教师对于所教授学科的热爱以及教师和学生人格的碰撞是使学校教育摆脱形式化并重新拥有生命的必经之道。这种主张也表现在翻译《爱的学校》上。在《爱的学校》“自序”中,三浦修吾言及翻译该书的缘起:
我国的小学教育正取得巨大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由外部开始的,虽说已经渐渐渗透到内部,但其中心不还存着空虚吗?
有人评价今日的教育好比掘池:其形状、深度、石垣的砌法等都设计巧妙,众人费尽精力深挖,一个形状出色的池子俨然已就,池边还铺着草坪,种着树木。但是,池中却没有储水。
如今的小学,也没有储水,没有蓄情。因而,教育的核心和生命还未实现。在这之前,我相信我国的教育不可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
译者曾于学生时代读到Cuore,书中对师生之爱、父母对教师的理解和同情、炽热的爱国之情以及牺牲精神都描绘得栩栩如生,于是感到我国当今之学校最需要的就在于此。
自此,我有了将此书翻译介绍给小学和一般家庭之愿望。[注]三浦修吾:「自序」,[意]デ·アミーチス:『愛の学校』,三浦修吾译,東京:誠文堂書店,1922年第21版,第1-2页。
三浦批评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空虚,将其比作徒有其表却缺乏生命之水的池子。而他译介《爱的学校》,是因为有感于书中描绘的“师生之爱、父母对教师的理解和同情、炽热的爱国之情以及牺牲精神”,并认为这是日本当时的学校教育最需要之物。换言之,他意欲借助书中传达的“爱”“同情”与“牺牲精神”来填补日本教育界的空虚,赋予学校教育以生命。
德富芦花为《爱的学校》所写的序言也推崇“爱”的理念:“我们的心灵在法律和约束的准绳内毕恭毕敬惴惴焉不堪左顾右盼上蹐下跼。唯有爱,唯有舍弃自己,唯有代人负罪,才可能有衷心的愉悦。”德富芦花认为“义理的观念”是驱动日本人的内在动力,但是义理不过是“第二义的东西”,“需知道越过此关口更有灵妙豁达的天地。那就是仁的世界,爱的天地,超越规律准绳时间空间束缚的自由自在的爱的大宇宙。”[注]「徳富蘆花先生序」,[意]デ·アミーチス:『愛の学校』,三浦修吾译,東京:誠文堂書店,1922年第21版,第1页。在这里,“爱”被理解为超越了社会规范源自内心的舍己为人的精神。
三浦修吾本人的著作也多涉“爱”的理念。三浦身为基督教徒,其所谓“爱”与基督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行第二里之人》中,“爱”被解释为基督教所说的行第二里之精神,即不满足于完成他人所要求之事,而应积极并乐于承担多于他人要求的重负。《学校教师论》中则明言:“爱他人即是为他人背负十字架”,“忍受对方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为了对方不辞劳苦直至最后。如若没有做好被对方践踏的觉悟,是无法爱他人的。”[注]三浦修吾:『学校教師論』,東京:内外教育評論社,1917年,第214-215页。
从德富芦花和三浦修吾的论述可知,二人所谓的“爱”更多指代“献身牺牲之爱”。《行第二里之人》中就曾强调“唯有在献身牺牲的爱里才埋藏着神的永恒之爱”[注]④三浦修吾:『第二里を行く人』,東京:成蹊学園出版部,1919年,第95页,第63页。。自然,“献身牺牲”的对象可以是孩子、学生抑或毫无关系的他人,而当这种爱指向国家、民族之时,就意味着主动为国献身。
吝啬的道德家对于义务要求之外的事情绝不用心。这种人实在可怜、可悲。对于此种人来说,被拉到讨厌的战场作战是件痛苦之事。但他们不知,为所爱之国家或民族而主动奔赴战斗实为一件光荣之事[注]三浦修吾:『第二里を行く人』,東京:成蹊学園出版部,1919年,第95页,第63页。
在《爱的学校》序言中,三浦强调“近来尤其意识到有必要培养小儿的国民精神和忠君爱国的至情”,指出《爱的学校》一书在这方面有着不少的贡献。这一主张也体现在《爱的学校》的译文中。以下对英译本和三浦译本中的几组译文进行比较。为便于理解,英译和日译后分别附上笔者的中文译文。
(1)英译:If it were for the Germans,I wouldn’t do it on any terms;but for our men! (THELITTLEVIDETTEOFLOMBARDY)[注]英译文引自Isabel F.Hapgood译CUORE(HEART):AN ITALIAN SCHOOLBOY’S JOURNAL,New York Thomas Y.Crowell & Company,1915.以下不再另注。根据Healey,Robin Patrick著《二十世纪意大利文学的英文译本》(Twentieth-Century Ital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1998),1912年前Cuore共有五种英译本,分别是Isabel F.Hapgood译本(1887)、Gaetano Mantellini译本(1895)、G.S.Godkin译本(1895)、Oscar Durante译本(1901)、Sophie Jewett译本(1912),其中Sophie Jewett译本为节译本。三浦修吾虽然没有明确交代使用了何种底本,但粗略比较几种译本可初步断定他使用的是最常见的Isabel F.Hapgood译本。比如,陈宏淑在博士论文《译者的操纵:从Cuore到〈馨儿就学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10年)中也指出,第一篇日记中安利柯提及自己上一年的老师,Hapgood译本中有“with his red hair ruffled”一语,Mantellini译本此处则没有叙及老师的红发。三浦修吾译文此处有「赤い髪の縮れた」一语,与Hapgood译本相对应。根据陈宏淑所举例文,Oscar Durante译本也可基本排除。G.S.Godkin译本笔者还未见到,有待进一步考证。
笔者译:如果是为了德国人,无论如何我也不肯,但为了我们自己人当然愿意!(《伦巴德的小侦察兵》)
三浦译:敵の為だつたら、どうしたつてやるもんですか。国の為ですもの。(「少年斥候」)[注]三浦修吾译文引自诚文堂书店1922年第21版,不再另注。
笔者译:如果是为了敌人,无论如何我哪里肯呢?因为是为了国家。(《少年侦察兵》)
(2)英译:poor boy!as though he heard these salutes and was glad that he had given his life for his Lombardy.(THELITTLEVIDETTEOFLOMBARDY)
笔者译:可怜的少年!好像他听到了这些赞誉,并且对自己为伦巴德献出生命感到高兴。(《伦巴德的小侦察兵》)
三浦译:(少年は)可愛さうに、人々の挨拶をきいて、国の為に命を捨てた事を満足に思つて居る様に見えた。(「少年斥候」)
笔者译:可怜的(少年),好像听了人们的称赞,对(自己)为国献身的行为感到满意。(《少年侦察兵》)
例(1)(2)是从《少年侦察兵》中选取的。《少年侦察兵》叙述1859年意法联军与奥地利作战时期的故事。例(1)中三浦修吾将英译本中代表特定国民身份的“Germans”译成一般意义上的“敌人”(“敵”),将“for our men”译作“为了国家”(“国の為”)。例(2)中则将少年为自己的家乡“伦巴德”牺牲生命译成“为国献身”(“国の為に命を捨てた”)。《少年鼓手》一篇中也多处将“The Austrians”或“Austrian”译成“敌军”。不仅如此,三浦修吾将英译本“每月例话”标题中的意大利地名都一律省略了,如THELITTLEVIDETTEOFLOMBARDY(伦巴德的小侦察兵)被译作《少年斥候》,THELITTLEPATRIOTOFPADUA(帕多瓦的小爱国者)被译作《少年爱国者》,THESARDINIANDRUMMER-BOY(萨迪尼亚的少年鼓手)被译作《少年鼓手》。换言之,日译本将意大利这一故事发生的特殊背景模糊化,转而突出一般意义上的“敌/我”对立关系,进一步彰显为国献身的少年行为的崇高性。
《少年侦察兵》在日本曾被收入吉田弥平编《现代文新抄》(卷二)[注]吉田弥平编:『現代文新鈔 巻二』,東京:光風館書店,1922年12月第一版、1923年1月修正再版、1923年11月修正第三版。“成城小学国语研究部”编《故事与听解教学资料》(下卷)[注]成城小学校国語研究部编:『お話と聴方教授資料 下巻』,東京:イデア書院,1925年版,第188-193页。收录标题为《勇敢的少年侦察兵》(「勇ましい少年斥候」)。,以及菊池宽编《新文艺读本一》[注]菊池寛编:『新文芸読本一』,東京·京都:文献書院,1929年版。笔者未查到这一文献,此处参考上田祥士、田畑文明『大正自由教育の旗手』(同前)第218页。等小学教材中。在《现代文新抄》(卷二)的参考书中,关于《少年侦察兵》一课的教学重点有说明,即在于让学生“感动于少年为了己方军队接受极其危险的侦察工作以致壮烈战死的纯真的爱国热情”[注]光風館編輯所编:『現代文新鈔参考 巻二』,東京:光風館書店,1923年版,第105页,第107页。。注释部分还提醒教员让学生注意文章结尾意军官兵给少年献花的情节,指出这是“对这个因高尚爱国行为而牺牲的少年充满同情的行为[注]光風館編輯所编:『現代文新鈔参考 巻二』,東京:光風館書店,1923年版,第105页,第107页。。另外,收录于《故事与听解教学资料》(下卷)中的《勇敢的少年侦察兵》用的虽是三浦修吾的译本,却出现了些许改动。三浦修吾译文的最后一句“可怜的(少年),好像听了人们的称赞,对(自己)为国献身的行为感到满意。”((少年は)可愛さうに、人々の挨拶をきいて、国の為に命を捨てた事を満足に思つて居る様に見えた)被改做了“军官和士兵都为这可爱的少年为国献身的行为灵魂受到强烈震撼”(将校も兵士もこの可憐な、一少年が国の為命を捨てたのをみて強く魂の震ふのを覚えた)。这样修改的意图,显然是让少年的行为不仅仅停留于其个人的自我满足,而且具有震撼他人灵魂的力量。而作品的“理想读者”则需像作品中的军官和士兵一样,感受到此种震撼。
(3)英译:Love your master;for he belongs to that vast family of fifty thousand elementary instructors,scattered throughout all Italy,who are the intellectual fathers of the millions of boys who are growing up with you;(GRATITUDE)
笔者译:爱你的老师吧,因为他是全意大利五万小学教师家庭中的一员,是和你一起成长的百万孩子们的精神之父。(《感恩》)
三浦译:伊太利全国、五萬の小学校教員は、お前等、未来の国民の精神上の父である。(略)お前の先生もその中の一人であるから、敬愛するのです。(「感恩」)
笔者译:意大利全国五万的小学教师,是你们未来国民精神上的父亲。(略)你的老师也是其中的一人,所以要敬爱他。(《感恩》)
例(3)中的划线处三浦译成“你们未来国民精神上的父亲”,而另一种版本的《爱的学校》的译者前田晁则将此处译为“和你一起成长的几百万儿童智力上的父亲”[注][意]デ·アミーチス:『愛の学校』(上),前田晁译,東京:岩波少年文庫,2009年版,第149页。原文为“おまえといっしょに成長しつつある何百万といふ子どもたちの知力上のおとうさん”。。很明显,前田晁的译文较为准确,三浦的译文则明确将儿童作为“小国民”,突出培养其国民精神的重要性。这种译法与三浦在“自序”中的主张遥相呼应。
三浦后来写的《学校教师论》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歌颂了明治天皇朴素的美德及人格之高尚后,三浦说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得不说先帝陛下是国民的伟大父亲,冥冥之中也向我们教育者展示了教育的真意。”[注]三浦修吾:『学校教師論』,東京:内外教育評論社,1917年版,第179页。在三浦的叙述中,教师和天皇都被称作国民精神之父。换言之,三浦赋予了天皇与教师作为国民精神之父的同构性,教师负有将天皇所展示的“教育的真意”传达给学生的任务。
(4)英译:“on! courage!” he shouted,following the far-off drummer with his glance.“Forward! run! He halts,that cursed boy! Ah,he resumes his course”(THESARDINIANDRUMMER-BOY)
笔者译:“继续!鼓起勇气!”他大叫到,目送着远去的鼓手。“前进!快跑!他停下来了,那个该死的孩子!啊,他又继续前进啦。”(《萨迪尼亚的少年鼓手》)
三浦译:大尉はもう遠くになつた鼓手を目送して叫んだ。『しっかりしっかり、走れ走れ、ヤ止まつたぞ。畜生奴、ア、又歩くんだ。』(「少年鼓手」)
笔者译:大尉目送已经远去的鼓手喊道:“振作振作,跑!跑!呀!停下了!畜生,啊,再走起来!”(《少年鼓手》)
(5)英译:“Go! run!” said the captain,clenching his teeth and his fists;“let them kill you;die,you rascal,but go!” Then he uttered a horrible oath.“Ah,the infamous poltroon! he has sat down!”(THESARDINIANDRUMMER-BOY)
笔者译:“快!走啊!”大尉咬紧牙齿、紧握拳头叫到,“让他们杀了你,去死吧,你个混蛋,继续走啊!”然后他发出一句可怕的诅咒:“啊,这个臭名昭著的懦夫!他坐下来了呢!”(《萨迪尼亚的少年鼓手》)
三浦译:大尉は歯がみをして、拳を固めて『行け!走れ!死んでしまへ!こん畜生!走れ走れ!』と云ふ。今度は怖ろしい言葉を出した。『エー卑怯者が!坐りこんで仕舞つた!。』(「少年鼓手」)
笔者译:大尉咬紧牙齿,握紧拳头说道:“去呀!快跑呀!去死吧!这畜生!跑!跑!”接着又说出可怕的话来:“哎!怯懦的东西!竟坐倒了!”(《少年鼓手》)
以上两组例子皆选自《少年鼓手》。大尉看到跑去送信的少年在途中突然放缓脚步甚至坐下休息,不知其受了伤,于是开始咒骂少年。“that cursed boy!”“let them kill you;die,you rascal”不仅传达了大尉的愤怒,更宣扬了这篇文章所包含的伦理精神:为了国家必须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这两组例子中,三浦的译文除了将“let them kill you”略去不译以外基本上准确传达了英译本的内容,可以认为他对此处的内容并不抱有疑义[注]与三浦不同,夏丏尊不仅将例(4)省略不译,“let them kill you;die”本该译成“让他们杀了你,去死吧”,他却译成“该死的”,语气比前者缓和得多。除此之外,夏丏尊对译本内容的概括也与三浦存在差别。与三浦在“自序”中强调书中的“师生之爱、父母对教师的理解和同情、炽热的爱国之情以及牺牲精神”相比,夏丏尊在译者序言中言及的是书中的“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并不像三浦那样强调“牺牲精神”。。
三浦修吾曾在《关于〈爱的学校〉的出版》一文中言及欲将《爱的学校》献给当地的各联队队长,请求把它作为士兵们的读物[注]三浦修吾:「『愛の学校』の出版につきて」,[意]デ·アミーチス:『愛の学校』,三浦修吾译,東京:文栄閣書店、春秋社書店,1912年第3版,第12-13页。。此计划最终是否实现目前无从考证,但这表明他翻译此书不仅为了培养儿童“忠君爱国的至情”,同时也意欲让士兵们学习这一精神,从而更好地为国家和天皇献身。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明治时代至大正初期日本初级教育的概况和相关政策。1880年,为加强政府对学校教育的控制,文部省颁布了《改正教育令》,将此前不受重视的修身置于所有科目之首。次年,根据《改正教育令》的规定,小学教育纲领出台。文部省在该纲领中首次对各科目的教学目的和内容作了规定。其中,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养成学生“尊王爱国的志气”。此后经过几年时间的准备,1886年教科书审定制度出台,政府对教科书的干涉和控制强化。1890年10月30日,在天皇的认可下,以“克忠克孝”“义勇奉公”“扶翼皇运”为核心精神的《教育敕语》颁布。翌年,颁布《小学校祝日大祭日仪式规程》,规定教师和学生在纪元节、天长节等节日必须举行仪式,向天皇和皇后的照片(“御真影”)行礼并高呼万岁,诵读《教育敕语》,参加大合唱。“御真影”当时虽并非发给每个学校,但查阅笼谷次郎《近代日本的教育和国家思想》中的资料可知,三浦修吾曾就学的福冈师范学校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之后执教的鹿儿岛师范学校都于明治早期受赐。受赐的时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为明治15年(1883年)12月26日,福冈师范学校为明治20年(1888年)12月3日,鹿儿岛师范学校则为明治21年(1889年)11月2日[注]籠谷次郎:『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教育と国家の思想』,京都:阿吽社,1994年版,第68-71页。。
1891年新出台的小学教育纲领重申了道德教育、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再次强调修身要“致力于培养尊王爱国的志气”。日俄战争开战的1904年4月,小学教科书国定制度开始实施,各学校要求使用文部省统一编订的教科书。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人的国民意识和国粹主义空前高涨,1908年9月,为响应前一年3月修订的小学校令的规定,“教科用图书调查委员会”成立。经“教科用图书调查委员会”审议通过而发行的教科书就是所谓“第2期国定教科书”。3月,文部省特别发布《小学修身教科书修订编纂教科目的贯彻法》训令。关于“第2期国定教科书”,训令指出“此次修正基于教育敕语的旨趣,特别注意阐明忠孝大义,发挥国民固有的特性”。在第2期修身教科书中,有关明治天皇的内容从第1期中仅有一课增加到七课,也反映了其“忠孝大义”的色彩[注]关于日本教科书制度的变迁参考中村紀久二编:『復刻版 国定教科書編纂趣意書 解説·文献目録』,東京:国書刊行会,2008年版,第19-88页。。
如前所述,三浦修吾在姬路师范学校和成蹊学园执教期间都曾担任修身科目的教学。当时不仅小学修身教科书,师范学校和中学的修身教科书卷首通常都收录了《教育敕语》。可以认为,三浦修吾在修身科的教学实践中也充分受到《教育敕语》的规范。
结 语
亚米契斯著Cuore诞生于意大利民族国家形成期,小说突出“尊王爱国”“为国献身”等精神,体现了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的价值观,也形塑了意大利读者的民族想象。三浦修吾翻译《爱的学校》时,为迎合日本这一新语境,培养儿童的“国民精神和忠君爱国的至情”,把故事背景中的意大利因素模糊化,并将儿童和教师统合于作为“国民精神之父”的天皇的权威下。在《爱的学校》的阅读实践中,三浦修吾翻译的价值取向也得到了贯彻和深化。
三浦修吾的著作中虽不乏个性教育等主张,但无论是他学生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抑或是教师时代从事的教育,都处于以“忠君爱国”为导向的教育体制之中。但日本已有的关于三浦修吾的研究突显了其作为“大正新教育运动先驱”主张个性教育的一面,对于后者却缺乏洞察。《爱的学校》应该看作三浦修吾的个性教育理念与“忠君爱国”的教育体制相妥协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