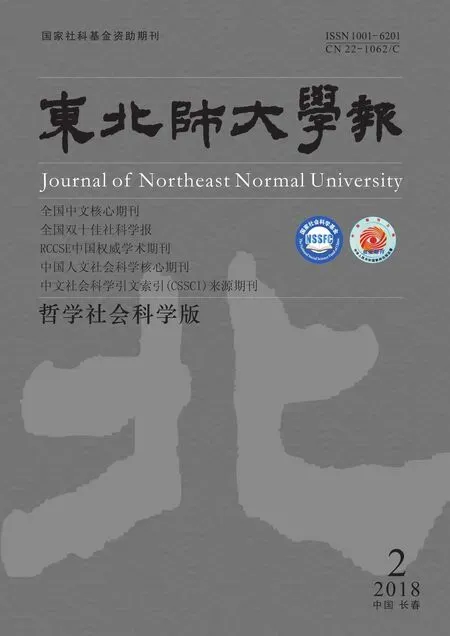他者镜像中的自我困境
——《他人的脸》之拉康精神分析学解读
2018-04-12任丽
任 丽
(1.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2.长春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2)
安部公房被誉为20世纪最受欢迎的日本作家和世界级文学大师。从《墙壁》对日本战败后徒劳反抗的悲剧性象征,到《砂女》时期审视现代性条件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安部公房的文学创作里,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他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由此引发的批判精神。从题材来看,无论是早期创作中荒诞变形的“非理性”景象,还是现代化冲击下被充满敌意的社会所包围的异化和孤独,对自我的思考一直是安部文学作品中从未间断的主旋律。
自我意识是20世纪哲学思潮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它体现在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哲学流派的反思中。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如何确立“自我”,安部公房的中后期小说中对主体的思索可以说是对这一哲学问题的有力回应。在《他人的脸》中作者采用回溯的手法,以三本手记的形式刻画了自我与他者的冲突,呈现了一个分裂、矛盾的主体形象。以往的评论家大多以战争记忆、人种为视角剖析了在充满矛盾和扭曲的世界里主人公异样的孤独感和恐惧感,而当我们探究作品背后作者的创作脉络和创作动机时,这种解读方式无疑局限了我们对安部文学中有关自我的思考。本文基于《他人的脸》并依据拉康的镜像阶段及相关主体理论,从身份危机中的自我、具有二重身份的分裂自我、走向毁灭的自我三个方面,分析日本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进程下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自我被异化时的主体意识,并追索安部公房创作思路的哲学理据。
一、身份危机中的自我
人类对“自我”的探寻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苏格拉底指出哲学应当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自我,他提出的“心灵的转向”可以说在哲学意义上发现了人类理性的力量和价值。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笛卡尔的我思哲学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他把自我与客观的外部世界相分离,并使得理性成为主体身份的重要保障,至此古希腊以来的本体论哲学模式开始转向为主体的认识论哲学模式。然而以“我思”为基础建构的主体,其一切体验从自我而出又折返于我,因此这一思想又具有浓厚的“唯我论”特征。进入18世纪,启蒙思想家把苏格拉底视为先驱和战友,要求人们以理性的方式追求自由和平等,并以理性判断和思维作为衡量自我存在的标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世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人性被扭曲,人被异化成了物的奴隶。在孤独和绝望中人们对一切传统的理性价值产生了怀疑,非理性主义思潮在此时应运而生,柏格森宣扬的“直觉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等都是其具体表现。作为现代哲学的重要表征,非理性主义认为理性和科学不适用于道德范围,强调仅凭非理性的直觉就能认识外部世界,并要求把人的情感、欲望、本能当作人乃至世界的本质。从总体上说,非理性主义是人类文化危机、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最深刻、最激进的哲学体现。而当人们回到自我的内心世界去寻找生命的本质时,最终会导致个人中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看到,社会的表面稳定、安全和物质进步,同一切人间事物一样,都是建立在空无的基础之上的。以至于欧洲人像面对一个陌生人一样面对自己。”[1]33至此,在非理性主义思潮下主体已陷入了深深的自我迷失之中。
安部公房关注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存处境。面对战后影响及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迷失,作为一名深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战后派作家,安部公房中后期的文本世界里,几乎都探讨过来自他人的“威胁”:《砂女》(1962)中仁木顺平面对“妻子”的无形压力而出走,《箱男》(1973)中为躲避他人视线而变身为箱男,《密会》(1977)中被他人监视的困扰,《樱花号方舟》(1984)中为了躲避他者而逃离故乡……可以说安部公房笔下的主人公们,在主体的“我”对世界的知觉关系中,总感到有一个先行存在的凝视者在注视着“我”,正是这一来自他者的世俗压力常常使主人公们不堪重负最终缴械投降。正如梅洛-庞蒂所言:“在这些动作后面的某处,或毋宁在它们面前的某处,或者更是在其周围,不知从什么样的空间双重背景开始,另一个私人世界透过我的世界之薄纱而隐约可见。一时间,我因它而活着,我不再是这项向我提出的质问的答复者……至少,我的私人世界不再仅是我的世界;此时,我的世界是一个他者所使用的工具,是被引入到我的生活中的一般生活的一个维度。”[2]20-21
20世纪60年代,战败后的日本处于一个特殊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然而社会、文化以及人们的思想状态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安部公房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时期人与人之间产生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与前现代的那种封闭、自足的社会不同,工业化进程下的日本社会不再使人有一种归属意识,人被抛在了这一特定情境中时刻感受到外在的强力和威胁性。置身于这样的社会链条中,就需要一种力量去消解自我意识以适应外部环境,当这一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人们就会呈现一种焦虑、恐惧的边缘人格特征。
安部公房在其长篇小说《他人的脸》中刻画了陷入身份危机的现代主体形象。小说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述,然而题目没有使用“我”而是“他人”,实际目的是为了拉开与叙述者的距离,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来审视这一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小说主人公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脸部受损,起初会“直面并习惯于整个事态”“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某些努力”[3]9,可当女助手拿起克利的题为《伪装的脸》的钢笔素描画给“我”看时,“那幅画俨然化作了映入她视线中的我自己的脸……”[3]9,在遭遇他者的视线时“我的心也被撕了个粉碎。我的内脏从那撕开的裂缝中如同腐烂的鸡蛋一般往外流淌着。”[3]9在“我”看来,脸部丧失是一种无法掩饰、无法摆脱的心里苦痛,而妻子的冷漠与拒绝,电车里五岁男童的惊诧表情更深深刺痛了“我”。这一来自于他者的凝视、评判,使“我”不停地追问“我到底是谁”“我来自哪里”。为了摆脱这一他者视线中的自我困境,“我”开始寻找某杂志的撰稿人K先生,期待得到一种外在的指引。正如K先生所言,“即使在幼儿心理学等等当中,这也成了一个定论,即人这种东西只能借助他人的眼睛才能确认自己。”[3]24这一富有哲理的言论可以说与拉康的镜像理论形成了相互映照的关系。拉康指出人类从出生就开始寻求自我之路,面对镜中的成像进行想象性认同,产生了关于自我的概念,并维持了在自我与成像之间异化的关系。源于在婴儿期对自我的错误认识,同时为了获得他人和周围环境的认同,建立自我身份,人类不得不自我异化,以试图探寻迷失的主体。因此,自我必须得到他者的承认,即我们自身必须借由他者的目光来确认自身的存在。这样一来,我们既要依赖于确认我们自身存在的他者,又要对这一外在的他者展开充满仇恨的抗争。不仅仅是面部丧失的“我”,安部似乎也暗示我们人人从生命之初就处于这样的二律背反的境地,而面部丧失的特殊事例,会愈发使“我”寻求他者的认同,也愈加彰显这一人生二律背反之境地。
通过文本细读的策略我们发现,《他人的脸》中主人公的异化焦虑,是一种社会异化焦虑的体验。拉康认为,主体的第二次分裂,是指进入语言体系时就意味着主体性的确立。在主体性形成的实在、想象和象征的三个秩序中,象征秩序起着决定作用。“要完全作为人类主体而存在,我们就得‘受制’于这个象征秩序——亦即语言或辞说的秩序;虽然我们无法逃离它,但是它却作为一个结构逃离了我们。尽管作为个人主体,我们永远都无法充分地掌握这一构成我们世界总和的社会的或象征的总体性,然而对于身为主体的我们,这种总体性却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力量。”[4]62在拉康眼里,人一旦进入象征秩序,就要求主体对社会能指体系的服从,而这一象征秩序也有其相应的能指链,即话语体系。因此,人类进入社会大他者的话语体系中,也就意味着无一例外地进入了自身的牢笼。丧失脸部的“我”永远被限定在与自己异化的境地,是被一种外在的、无法为人类自身掌控的力量所决定。即拉康所说的“大他者的话语体系”。“我”渴求在充满他者的世界里找到自我的镜像,建立一个自我的身份。面对以妻子为代表的他者,在回忆的手记中到处呈现出自我的焦虑和苦痛,“漫不经心的视线里都藏匿着涂满毒素的针。那毒素带有可怕的腐蚀性。”[3]33“……救救我!……别再用那种眼神来看我!如果老是被人用那种眼神瞅着的话,不是真的会变成怪物吗?”[3]58正是对这一异化的过分担忧,使“我”行为异常乃至精神焦虑,“我”害怕被他者“腐蚀”,更担心自己会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只有皮相而无心智的躯体,正如拉康眼中的自我与他者,在本质上是一场有关欲望与承认的博弈,我们都深陷于一个相互的、不可划约的异化辩证法中,即每个人都存在于他者的存在。
在资本主义的物化世界里,“我”遭遇了主体进入象征秩序的异化,而“我”的社会异化焦虑实际上就是对象征秩序的排斥。主人公置身于充满他者的街道“就像是在狱中”,面前的墙壁和铁窗都变成了“研磨一新的镜子,映照出自己,无论在哪个瞬间里都不能逃离自己,这的确是一种被囚禁的痛苦。”[3]63“我”已被严实地囚禁于“自己”这一口袋中,正拼命地挣扎着,而挣扎的最终结果是“我”彻底的异化,带上假面把自己变成陌生的他者。《他人的脸》中安部公房打破了写实主义的传统,对其笔下人物的容貌、表情、性格及过去经历,不肯多费笔墨,而是致力于探寻人物的各种处境,靠其丰富的想象力塑造出实验性的“自我”。小说文本世界中,主人公“我”相关资讯的缺失并不会降低人物的生动性,那个失去面部的“我”作为活生生的人,其生动性完全超乎读者想象,以至于我们完全进入主人公“被囚禁的痛苦”,并将之与现实混淆在一起。如果作家进行的只是局限于对一个人物的描写和刻画,就意味着他不是一位划时代、开拓性的小说家。小说中对他者视线的逃避、对迷失自我的探寻、“囚禁”自我又惧怕被疏离等创新性文学表现手法,都意味着安部在他的小说世界中不断地探寻着超乎个体的抽象的主体形象,这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精神分析哲学不谋而合。
二、具有二重身的分裂自我
作家安部公房出生于日本东京,在中国沈阳(当时称作“奉天”)长大,其故乡又是日本的北海道,源于对身份有着敏感的认识,同时又作为一位负有责任感的作家,安部公房在其文学作品中大量采用了二重身的文学模式,诉说现代人身份迷失的焦虑与苦痛。《墙壁》(1951)中的卡尔玛氏和名片卡尔玛氏、打字员Y子和橱窗模型Y子、乡村父亲和都市主义的于尔班教授这三组二重身形象,均以名字为“镜面”折射出分身人物的相异性,而《他人的脸》则以假面为棱镜,呈现的是“我”与“假面”源于同一躯体却具有不同价值判断的“二重身”。这一具有二重身的主人公形象,围绕自我和妻子关系折射出现代城市中丧失身份的恐惧。当“我”被他人的视线步步紧逼,感受到了自我被“囚禁的痛苦”,但随后就“心急化作了焦躁,焦躁进而发展成阴暗的愤怒”[3]63,使“我”饱受精神折磨的是“我”的内心始终感受到两股对峙的力量。“我乞求着接近你,同时又乞求着远离你。我想了解你,同时又对了解你大加抵触。我希望看见你,同时又对看见你感到屈辱,在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中,龟裂越来越深,最终深入到了内部”[3]86。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似乎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自我认知缺失的黑暗角落,而文学的二重身大多情况下都是源于心里黑暗而衍生的另一个自我。正是主人公内心两种斗争的声音造成了主体的“意识崩裂”,当假面制作完成时,带上假面的“我”正式以二重身登场。
二重身源于德语“Doppelganger”,其原意为“两人同行”,也指隐藏在人们心中的另一个自我,这一“二重身”往往是人们内心欲望的最真实的表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有两个自我,一个是和原来自己一样的自我,另一个是和原来的自己不一样的他人。18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二重身文学理论的构建。杰·保罗于1796年首次使用与“自我”相对应的“非自我”,并在小说《塞宾卡斯》中运用了“二重身”的人物塑造方式。在文本分析中我们经常使用“二重身”“双身”“变身”等,具体是指人物的内心中常常有另一个自我,它无时无刻不监视着原身的活动,并把自身的意志、想法强加于原身。当人物内心遭受外部的压力而扭曲变形时,这“另一个自我”就出来试图掌控原身。
就安部的小说创作而言,在《他人的脸》中以手记、书信等心理呈现方式的载体,对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身份危机采用二元对立的双重人格和自我分裂模式进行探讨。在拉康看来,“主体本质上是分裂的或割裂的实体:主体被他所服从的那些语言法则分裂开来,分裂到了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程度。”[5]63从存在的角度看,这一双重自我呈现的是丧失面部的自我和带有假面的“他者”的分裂。当假面制作完成,“我”对房东说“假面”是“我”弟弟时,这张假面作为现代社会中的匿名者成为一张通往他人世界的通行证。然而由于带上假面导致“水蛭窝”愈发严重,“我”清楚这一行为将会导致毁灭性的结果,于是就徘徊在双重身份之间,一边享受着不顾忌视线的优越感,同时又深陷囚禁脸面的牢笼之中。带上假面“从心灵的羁绊中解放出来”[3]72,变得“无限自由”的同时也变得“无限残酷”,没有耻辱的必要,更无须辩解,“假面”抛开了自我的道德约束而肆意妄为。这一极端的自我意识和感受,模糊了主人公的自我人格界限,此时的“假面”在象征世界中已然将原本的“我”消解为碎片而消失;回到出租屋,呈现素颜的“我”,则期待修复与妻子的关系,渴求他者的认同来证明自我的存在。这部小说的张力就体现在“我”在假面和素颜的表象下的两种心理和行为之间的逡巡。这一来自于人物自身的主体性分裂,深深印证了20世纪60年代人们内心深处的非理性。在出租屋内,当“我”摘下假面在镜中审视自己的脸时,正是对自我身份的凝视和探寻,“我”已被形塑为一个非此即彼的二重身份,这是对自我的固化,更是对现代性条件下自我真实存在的扼杀。
在安部公房的笔下,主人公从肉体到精神上都经历了双重人格的裂变,丧失面部的叙述自我在手记中追溯其过往的经验自我时,二重身的“假面”已经呈现出一个独立的姿态,这一自我二重身的对立和对话关系,在主体的意识和潜意识层面引发不同角度的价值判断和指向。一种是事后对过往的回忆和反思,与素颜的“我”保持一致,而另一种则是凌驾于“我”之上的“他者”立场。“我”和被称作“弟弟”的“假面”之间很难达成和谐统一,在与“假面”思想交锋中的询问与回答、赞同与反对的过程中,双方意识的碰撞往往以二重身另一半的胜利而终结。从理论上讲,二重身的“另外一个人”用人们的肉眼是无法捕捉到的。在《他人的脸》中只有在“我”审视镜中的“自我”时,二重身的另一人才出现在“我”视线中,而日常生活中则是站在“我”身后,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并将其想法渗透到“我”的大脑思想中。当玩具店老板试探性地向“我”出售手枪时,虽然“我”的内心惊恐万状,而“假面把我的惊恐抛在一边,向长着野兔嘴脸的店主点头示意。”[3]117显然“假面”在关键时刻已然凌驾于“我”之上,操纵着“我”的意志。
安部在文本中多次暗示处于同一身体的“自我”和“假面”具有一体性,是分裂自我的体现和互为“二重身”的关系。这二重身都试图摆脱对方的束缚,却又统一于我的身体之中,与自我与他者虽然相异却又统一于社会中呈现一种暗合。在小说中,素颜的“我”代表着现代社会下被疏离的个体,而“假面”则象征着侵入“我”世界的他者。安部在文本中刻画的栖息于主体内部的二重身,就是来往于内心世界的神圣与邪恶,描绘在自我和“他者”之间纠缠的苦痛和清醒。这一哥特式的二重身亦表明了人类在他者中找到了自我,自我就是他者。
三、走向毁灭的自我
如果说上述的分析和阐释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二重身”的运用体现了主体与其自体之间的竞争,那么这一竞争也被建立在主体“我”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上。本韦努托与肯尼迪曾说过:“在对他者的认同和竞争之间存在着一种原始的冲突,正是这一冲突开启了辩证统一的过程,从而把自我与更为复杂的社会情境联系起来。”[6]58在拉康的体系中,“欲望”很好地诠释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拉康认为,“被压制的他者是‘言说’的欲望对象。”[7]122这一欲望既包括对他者的渴望、被他者渴望,又包括对他者所渴望的东西的渴望。对于主体与他者来说,成为欲望的主体或爱的对象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成为欲望的动因。同时拉康强调,人的欲望永远是“大他者”的欲望。“大他者就是语言,亦即象征秩序;这个大他者永远都不会与主体完全地同化;它是一种根本的相异性。”[4]61齐泽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人们交往中显在的符号规则与隐形的不成文的规则,都由拉康意义中的大他者标示出来[8]89。显性规则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而隐形规则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也尤为重要。
按照拉康的观点,主体“我”只有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才能确认其存在,那么在20世纪60年代安部笔下的他者是以妻子为代表的他者,更是一种“大他者”。起初“我”遭遇身份危机,应当向妻子敞开心灵,然而“我”却囚禁于自我的世界中;当“我”试图坦白假面计划以求修复二者关系时,妻子也没能对“我”做出积极回应,而是留下一封“诀别信”。上述行为显然违反了社会交往中的隐形规则,双方关系发生动摇,并陷入难以挽回的境地。《他人的脸》中,得不到他者的认同是造成自我困境的根本所在,然而渴望他者采取背离其自身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则更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任务。当“我”把三本手记交给妻子时,渴望得到一种作为“邻人”的回应,而“妻子”的回信却远远消解了“我”的主体性。“知道你的假面剧的人,并不只是那个玩悠悠的姑娘。就连我也从那最初的一瞬间起,即从你称之为磁场倾斜并自鸣得意的那一瞬间起,就已经彻底识破了一切……我不想再折回到那种镜子的沙漠中去。”[3]213-215当主体欲望的指向变成虚无,“我”体验的正是对丧失自身的丧失,而“我”此刻也进入价值缺失状态。正如张一兵指出的:“我们无家可归,如果一个人想重拾自己的原在,他就会失去主体间的能指意义关系,如果他不把自己用无(象征符号)贴到大他者的空无上去,他反倒会作为完全无法在场的负存在从此世上消失。”[9]61
在存在主义哲学中,这一被现实追赶到的边界状况被称作“墙壁”,雅斯贝斯把这一状况命名为“界限状况”。在面对界限状况时,人们一般会采取两种行为:一是没察觉到界限状况或者是故意回避,导致了我们丧失自身的存在;二是直接接受这一界限,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力,一旦精神陷入绝望中,也能很快在心理上超越。然而小说中的“我”不属于上述情形的任何一种,由于长期遭受他者的冷漠和拒绝,“我”的心理早已不堪一击,再加上收到妻子的“诀别信”,可以说遭遇了生存的危机。科热夫曾说:“与使人处于消极的静止状态相反,欲望会使他打破平静,激发他去行动。”[10]74在这场博弈与挣扎中,“我”最终展现出激进的姿态,拿起手枪、带上假面挑战这一社会秩序,即挑战以妻子为代表的他人所象征的权威,这一行为无疑是扰乱性的、彻底疯狂的。至此,“我”已彻底沦为他者之他者,这也正是萨特的“他人即地狱”的症结所在。
一旦我们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中被卷入了大他者的欲望,就要遵循拉康的指引“不在自己的欲望上让步”,因着这一大他者的欲望而去探寻自身的欲望,以便摆脱大他者对我们的影响。齐泽克承袭了这一思想,并引用海德格尔理论指出了当人们抗争社会秩序与习俗中的持续而紧迫的陷阱时,不得不采取暴力[8]90。在这场殊死搏斗中,自我与他者都受困于这场较量,自我的死亡也将是他者的死亡,“我”只有冒生命的危险去斗争才能向他者证明自我是具有超越性的主体。这一激进行为会把人们从安稳的日常状态中脱离出来,同时也会向大他者传递一个信号,即表达主体“我”自身的哀怜、警示和承认自身有罪,因此,“我”始终无法摆脱大他者的掌控。用布朗肖的话来说:“绝对的他者和自我直接统一了起来,自我和他者在彼此之中迷失了自己……但这里的‘我’不再是至尊的:至尊性处在那唯一绝对的他者身上。”[11]12420世纪60年代,安部没能找到自我迷失的出路,其文本中主体自身的对立面是内在的,异质性似乎难以消除,“我”以二重身的决绝姿态对社会秩序进行颠覆抗争并走向毁灭。而这一象征秩序内的抗争,也暗示了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主体的本质就是异化。主人公由于自我身份恐惧而引发的边缘人格特征,折射了现代人徘徊于新秩序和旧秩序之间的尴尬处境,安部也借此抨击将他们异化和边缘化的社会。
日本的战后文学,一般不会对社会问题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而是会回到原点,以出发点和终点重合的方式来落下自己的大幕。对于安部公房来说,所谓原点,就是对自我存在进行赌注的主体尝试,就算一个主体消亡了,在其消亡的同时也意味着新的开始。
安部在《他人的脸》中通过“二重身”的文学模式展现了人类内心深处的疯癫与理性、和善与凶恶、勇敢与胆怯的二元对立,而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又蕴含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即把一切事物的矛盾本质置于最突出的地位。这一矛盾既包含着其自身的对立,又包含对事物本身的否定,在这永无止境的转化过程中,会呈现出某种新的东西,在此意义上,安部公房对“主体”的认知哲学得到了印证。其处女作《终道标》中“我就是我自己的王”,既是对自我生存决心的高度概括,又表明了自我始终无法到达自身的终点。在主体内部萌发的意识脱离了自身并变成支配“我”的一种力量,此时主宰“我”自身的,就不是最初的“我”。然而,只要“我”还持续做“我自己”的王,并在其内部生根、繁育,就会通过连续的自我否定,成为主宰自我的主体。安部公房就是用这一方式向我们宣告自我主宰的强烈决心和勇气。总体来看,在小说中,安部公房始终将自己摆在与现实社会相平行的位置上。作为小说家,他并不是一个创造者而是一个发现者。安部没有着力阐明和揭露现存的社会体系,而是要探寻历史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可能性问题。殊不知这一存在的展现更是一种伟大的预见,而这一问题也必将恒久地与人类共存下去。正因其与现实世界所保持的距离,才展现了这个时代本来的样子,小说中闪耀着的光辉的价值才更具普适性和深刻的哲学和社会意义。我们说安部公房作为作家和艺术家的伟大之处或许都是源于此吧。
[1] [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M].杨照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M].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 [日]安部公房.他人的脸[M].杨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 [英]肖恩·霍默.导读拉康[M].李新雨,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5] [英]达瑞安·里德尔.拉康[M].李新雨,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6] [美]Benvenuto,B.& Kennedy,R.TheWorksofJacquesLacan:AnIntroduction[M].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6.
[7]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2011(1).
[8] 于琦.西方文论关键词——行动[J].外国文学,2014(11).
[9] 张一兵.能指链:我在我不思之处[J].社会科学研究,2005(1).
[10] [英]爱德华·凯西,麦尔文·伍迪.拉康与黑格尔—欲望的辩证法[J].吴琼,译.外国文学,2002(1).
[11] [法]莫里斯·布朗肖.无限的谈话[M].尉光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