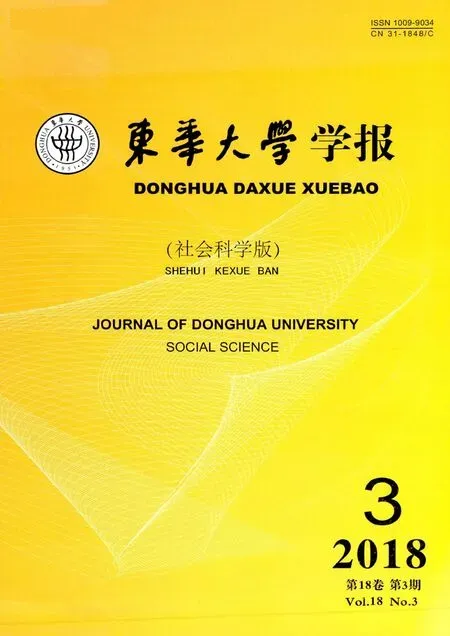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土家织锦“西兰卡普”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
2018-04-12葛英颖杨田甜
葛英颖,杨田甜
(长春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皆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西兰卡普”作为土家族民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土家族人民的群体智慧,积淀了土家族几千年来的传统民族文化,综合地反映了土家族的宗教信仰、审美观念、色彩偏好、风俗习惯等浓郁的民族性,以及土家族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生产(劳作)方式、技术水平等鲜明的时代性。本文立足于土家文化的总体框架并从历史的角度系统地阐释其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
土家族的先人(祖先),即古代巴人,至少在距今4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了简单的织锦技术,土家织锦在当时被称为“玉帛”。在演化过程中,土家织锦历经了从“賨布”(秦汉)到“斑布”或“土锦”(三国两晋),再到“峒锦(布)”或“溪布”(唐宋),最后到“斑(花)布”或“土锦”(元、明、清)的发展过程。历经岁月与历史积淀的土家织锦成为清“改土归流”后“西兰卡普”之源。虽然土家织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各异,但历经岁月积淀与差异文化熏染的“西兰卡普”成为土家织锦历史与文化的结晶。“西兰卡普”经历了“雏形于秦汉,成形于两晋,成熟于唐宋,精于明清”,“民国时的大放异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走向辉煌”的演变轨迹[1]。
一、“西兰卡普”的雏形与成形时期
据《华阳国志·巴志》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西周初,“武王即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即巴子国)”,其他“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柠……皆纳贡之”,这是关于古代巴人最早也是最可信的史料记载。秦国发兵灭掉巴蜀后,幸存下来的巴人流入今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武陵山区,并与当地的原住民进行了融合,从而形成了“武陵蛮族”“巴郡南郡蛮族”等,这些族群的一部分就是土家族的祖先。土家族民继承了巴人的纺织技术,推动了土家族聚居区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和繁荣。土家族所织的“賨布”很早就成为纳贡名品,《华阳国志》称这种布为“兰干西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提出了“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的决策,促使当时已很发达的蜀锦进一步繁荣。土家族在周围先进民族的熏陶和影响下,开始耕农种桑、纺纱织布,随着鉴赏能力与染色技术的发展,土家族族民编织出了斑斓的“土锦”,并用自织的布来装束自己,如腰围麻布条、身披五彩锦等,从而摒弃了“茅古斯”装束(稻草服)。这一时期,土家织锦“西兰卡普”开始萌芽且逐步走向成熟,这与土家族族体的形成步伐是同步的,进而演化为土家族鲜明的民族特征之一。
(一) “西兰卡普”雏形与成形时期的民族性特征
这一时期“西兰卡普”的民族性体现为:一方面,土家族服饰开始演化,即由“茅古斯”装束慢慢演变为布衣装束,并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本民族鲜明的特点。这说明,巴人流入武陵山区,为土家族族群带来了先进的纺织技术与文化,催生了土家族“西兰卡普”的产生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如“西兰卡普”在用色上就特别推崇红、黑二色(深受楚国文化的影响),并为“西兰卡普”在唐宋时期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西兰卡普”深受当时工艺技术、土家族族群所处地理位置等方面的限制,致使“西兰卡普”图案中的曲线全被转化或概括为直线或斜线,从而整合为几何形体,奠定了后世“西兰卡普”线性几何化及具体物象抽象化的基础。
(二) “西兰卡普”雏形与成形时期的时代性特征
“西兰卡普”的时代性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西兰卡普”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折射出当时土家先辈工艺技术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如土家先民曾结草为服,即“茅古斯”,后因巴人流入,为武陵山区输入了大量的先进文化及纺织技术,遂逐渐向绩织而衣演化。另一方面,“西兰卡普”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映射出当时土家族与其他民族间不断密切的技术及文化交流。比如,古代巴人是因秦楚两国的强势发展而被迫进入今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武陵山区生活的,但是巴人似乎对楚国文化并不反感。楚国尚红,传统土家织锦的颜色也几乎是由红与黑组成的,这说明古代巴人对红黑二色推崇至极,也印证了巴人对楚国文化并不反感的说法。土家织锦在色彩构成上,以暖色调的红、暖黄为主色,辅以冷色调的底色来反衬主色,给人以强烈的反差与深沉的视觉感受,楚国早期的漆绘艺术风格与土家织锦的此种配色效果极为相像。
由上可知,这一时期的“西兰卡普”,不仅表明“西兰卡普”固有的基本风格(如具体物象抽象化、几何化等)已基本树立,而且反映了当时土家族与其他民族文化、经济、思想交流的状况,以及当时土家祖先的纺织技艺、社会发展水平等的情况,呈现出兼具浓郁民族性及鲜明时代性的双重特征。
二、“西兰卡普”的成熟时期(即土家族地区的“土司时期”)
唐五代、梁开平时期,吴王打败了江西首领彭瑊后,彭瑊向楚国投诚,被封为溪州刺史,彭氏势力得以流入土家族聚居区。后来,彭瑊谋杀了土家族的族长,成为蛮夷中最大的首领,也是湘西第一代土司王。这一时期,“西兰卡普”步入了相对独立的快速发展阶段,出现了“女勤于织,户多机声”的社会风气,这在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据史料记载,彭瑊在唐僖宗时期考取进士,曾经担任过太傅、溪州刺史、武昌节度使等要职,他应该十分了解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先进器械、先进文化等。彭瑊为土家族首领是后唐朝廷册封的结果,身边的伴随者——相当数量的中原人士亦因此随其进入土家族聚居区,而这些中原人士都熟悉先进的中原文化与技术。
(一) “西兰卡普”成熟时期的民族性特征
彭瑊率众(中原地区的能人义士)进入土家族聚居区,对于土家地区而言实质上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文化输入。具体到“西兰卡普”上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图案、纹样的丰富。土老司在土家族地区不仅是行政管理人员,更是土家族人精神信仰的寄托者,备受土家族人的尊崇。土老司,土家语为“梯玛”,即中原地区的“活神仙”,据传能治病救人、驱邪除祟、禳灾祈福。土司制度的形成标志着土家族地区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农奴制(领主制)社会,其带来的先进思想、文化、技术等深深影响了土家族的每一个人,土家族聚居区的土家人将这些文化技艺、图案纹样编织进“西兰卡普”中。这一时期较为有代表性的纹样当属“神龛花”了。“神龛花”取自湘西人堂屋正中的敬神台,是土家人日常生活的产物。“神龛花”在织造时采用纵向二方连续构图,且将现实中的“神龛”高度几何化,让人很难辨识出其具象的形,纹样宽大且壮实。此外,据史料记载,唐代存在一种龟甲纹样式为六边菱形的龟甲王字纹织锦,这与“西兰卡普”中的“椅子花”等纹样极为类似。二是“西兰卡普”的配色逐渐讲究“五方正色”,即黑、红、黄、青、白,这与中原地区传统的配色方案是相一致的,结合彭瑊率众进入土家族聚居区这一史实,对此便不难理解了。“五方正色”观渗透着儒家思想,成为大家共同的信仰背景和标准尺度,成为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并赋予其吉利祥瑞的意义[2]。很多学者认为“西兰卡普”的配色是土家族女性的“随心而为”,有的甚至认为土家族女性在进行色彩配置时利用了色彩的三要素,即明度、纯度及色相。然而,“西兰卡普”在土家族聚居区是明显具有祭祀性质的纺织品,虽然极具实用价值,但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巫术性质的且具有精神层面含义的特殊物件,如在祭祀时被用作香案上的幌子,在跳“摆手舞”时被用来装饰等,因而“西兰卡普”的织造及配色显然不是土家族女性的别出心裁。再者,色彩三要素的概念起源于西方,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传入中国,而土家族聚居区环境闭塞、人迹罕至,这也印证了“西兰卡普”的五色方案源于地区传统的配色方案。从民族性来看,彭氏势力流入土家族聚居区,为土家人民带来了先进的思想、文化、纺织技术、社会生产力等,大大加速了“西兰卡普”的发展及成熟,标志着“西兰卡普”纹样趋于丰富、色彩趋于完善。
(二) “西兰卡普”成熟时期的时代性特征
这一时期,土家族聚居区的上层土司(剥削者)与下层土民(被剥削者)的服饰存在较大差异。如据《永顺县志·乾隆本》所载,下层土民不论男女皆留长发并盘为椎形的发结,穿短衣,赤脚;而上层土司则戴金冠或凤冠,佩项圈、足圈等来彰显自己的富贵。具体到“西兰卡普”上则表现为这一时期下层土民所织的“西兰卡普”必须供奉于上层土司,只有极少数用于下层土民。这不仅反映出上层土司与下层土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而且体现了两者之间极大的贫富差距,折射出封建农奴制社会下土家族内部分化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实质。“西兰卡普”的地区差异(土司与非土司地区)形象地阐释了土家族聚居区经济交流、文化交流、技术交流及社会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地域差异。非土司地区的“西兰卡普”随着汉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不断发生变化,而土司地区的“西兰卡普”则几乎未受其他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差异。一方面说明闭塞的土司地区相较于不断发展繁荣的汉族文化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非土司地区来说,经济、文化、思想及社会生产力等较为落后,深层原因在于中原地区实行“汉不入境,蛮不出峒”的民族歧视策略,以及上层土司利用各种政策对外来商人实行限制,折射出封建农奴制(领主制)具有阻碍土家族聚居区经济、社会、思想等的发展和各民族之间往来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说明开放的非土司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文化、经济、思想等交往密切,从而使非土司地区的社会得到了快速且持续的发展,非土司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文化、思想逐渐趋同,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小,本质上说明了两种社会制度(封建地主制与封建农奴制)存在极大的差异性,也说明了封建地主制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和极大的进步性。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在“西兰卡普”上的纵横向差异,皆深刻地折射出土司时期土家族聚居区的经济、生活、生产、思想、文化情况,也正是土家织锦“西兰卡普”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双重特征的集中反映;同时说明土家织锦“西兰卡普”已具有相对丰富的图案纹样、逐渐完备的配色方案及相对完整的范式和个性。
三、“西兰卡普”的精品及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是指土家族聚居区的“改土归流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
清雍正年间,朝廷为了增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力,从而加大了对土家族聚居区的控制,对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即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员对土家族聚居区进行流官管理,废除了在土家族聚居区实行了800多年的土司制度,实现了土家族聚居区由封建农奴制社会向封建地主制社会的转变。随着流官制度在土家族地区的确立,先进的明清文化、思想、纺织技术等大量涌入闭塞的土家族聚居区(大巴山、武陵山地区),这也是土家族聚居区第二次自上而下大规模地接受外来文化。清“改土归流”政策在土家族聚居区的实施,标志着“汉不入境,蛮不出峒”的禁令被彻底打破了。清政府在土家族聚居区设立教育机构,旨在传播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原文化;后来又强制向土家族族民灌输中原文化,使得中原文化在土家地区得到了广泛且深入的传播;此外,还采取严厉的措施改革土家族聚居区的民俗,致使土家族族民的服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据清同治十年的《保靖县志》载雍正八年的诏命:“……你们这每个村寨,只有两三户人家,应该谨遵诏命,即日起就将自己的衣服、鞋子换掉……本诏书公示后一年内,你们守岁、腊八、结婚、丧事、宴会等的时候,都要按照汉人的服装形制来装束自己,即男人戴红色的帽子、着袍褂、穿鞋袜;女人则要穿长衣长裙,不允许赤脚。这样岂不是有礼有节……”可见,明清先进文化的强势传入及清政府一系列的强制措施,促进了土家族聚居区纺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该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为“西兰卡普”的进一步完善优化和土家族服饰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如,随着汉族手工业者陆续迁入土家族聚居区,土家族族民当手工学徒的规模与日俱增,一反土司时期因环境闭塞而鲜有外人踪迹的状态,并逐渐产生了“攻木之工、攻石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摩之工、抟填之工”,即达到了“一切匠作,莫不有会”的境地。鸦片战争以后,国外大量物美价廉的洋纱、洋布等西洋布料被倾销至土家族聚居区,并逐渐取代了土家族自织的棉布。因此,清“改土归流”之后,土家族所用布料经历了由以麻为主到以棉为主,再到以洋纱、洋布为主,变得面目全非。虽说这一时期土家族聚居区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如土家族族民自织的土家织锦和自做的染料售卖不畅,致使家庭手工业几近停产,但外来“新潮”及质量优异的面料还是促进了“西兰卡普”的进一步优化。
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湖北及湖南各地的省政府、省府官员及大批师生等纷纷流入土家族聚居区,如恩施、沅陵等地。这些高级官员及知识分子的迁入,加速了土家族聚居区的群体流动,这对于土家族聚居区实质上是一次较大的文化及思想输入,促进了“西兰卡普”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入土家族聚居区生活的汉族(以党政军干部为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土家族聚居区的民族构成,加速了土家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土家族族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本土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族民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等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为“西兰卡普”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条件。在党中央“发展民族艺术,保留民族遗风”精神的指导下,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进一步繁荣,城乡族民选用最优质的织造材料、最艳丽的色彩,用最高超的技艺来织造“西兰卡普”。纵观这一时期的土家织锦“西兰卡普”,其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 “西兰卡普”精品及繁荣时期的民族性特征
从民族性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用于织造“西兰卡普”的材料逐渐多元化。土司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政策之后,土家族族民与其他民族间的文化、思想、经济、技术等的交往、交流、交融日益加深,致使土家族族民革新了刀耕火种的传统劳作方式,并促使土家族族民优化了桑蚕的养殖技术及棉麻的耕种方法。清朝末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近代文明的强势传播,偏远闭塞的土家族聚居区也开始使用洋布、青布、线布、洋缎等外来机织布品,如哔叽、斜纹、“灯芯绒”、“的确良”等,大大丰富了“西兰卡普”织造时的材料选择。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织造“西兰卡普”所用的原材料已开始突破“本土化”。二是“西兰卡普”的色彩随着时代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如这时期的“西兰卡普”中运用了诸如浅绿、粉红、橙黄等素净的配色,这些高雅色彩的搭配极具明清刺绣的韵味。三是“西兰卡普”的图案纹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如清朝时期,土家族族民深受中原地区蓝印花布与刺绣的熏陶,产生了诸如“喜鹊闹梅”“大(小)白梅”“鸳鸯采莲”“龙凤呈祥”等明显带有汉文化内涵的系列图案纹样,甚至出现了诸如“福禄寿喜”“寿比南山”“金玉满堂”等使用汉族吉祥用语作为主体图案的装饰纹样(“福禄寿喜”纹样采用的是八达晕的四方连续布局,把同一文字做直行排列)。可见,随着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强势文化的传播,土家织锦“西兰卡普”不断地进行自我优化与丰富,如织造材料的多元化、色彩的多样化及图案纹样的内化等,既使“西兰卡普”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情趣、色彩偏好、精神追求等个性特征,又令包罗万象后的“西兰卡普”具有极为深刻的精神文化内涵,这与土家族总体文化的演进是紧密相连的。
(二) “西兰卡普”精品及繁荣时期的时代性特征
从时代性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西兰卡普”的演化说明土家族地区历经了历史与制度的深刻变革。清王朝在土家族聚居区实施的“改土归流”政策,导致在土家族聚居区实行了近800多年的土司制度土崩瓦解,标志着土家族聚居区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封建地主制社会完全替代了封建农奴制社会,由此带来了土家族聚居区经济、文化、生活、思想、纺织技术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革。这一时期,“西兰卡普”色彩、图案纹样等的丰富与发展,是土家文化、思想、纺织技术、社会生产力等与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符合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土家文化发生变迁的历史选择。辛亥革命后,革命派推翻了清王朝,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相对于纯封建地主制社会还是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这一时期,外来的品质优异、价格低廉的纺织材料大量进入土家族聚居区,大大开阔了土家族族民的视野,丰富了织造“西兰卡普”时的材料选择。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土家族历经了两次更为深刻的历史及制度变革,对土家织锦”西兰卡普“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彻底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中央的民族政策是“平等与团结”,并在土家族聚居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得土家族进入较为自由的发展轨道,这为“西兰卡普”在新中国走向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西兰卡普”的演化说明“土汉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程度日益加深。土家族聚居区在这一时期涌现的两次较大的群体流动是以大量汉族的流入为主的,本质上是两次较大的文化及思想输入,加速了土家文化、思想、社会生产力、纺织技术等与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汉族的部分元素在经过土家族族民的提炼与浓缩后再现于“西兰卡普”之中。“西兰卡普”在这一时期的演化,反映出土家族聚居区在清“改土归流”后经历了极为深刻的历史及制度变革,且土家族与其他民族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从而使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越来越趋同,即文化认同,标志着土家文化与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日益加深。
四、结语
土家织锦“西兰卡普”在萌芽、发展、演化阶段总是充满了曲折,这与土家地区的地理环境、人员流动、社会变革等是密不可分的。但总体而言,“西兰卡普”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走向繁荣的,且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特征,符合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土家文化发生变迁的历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