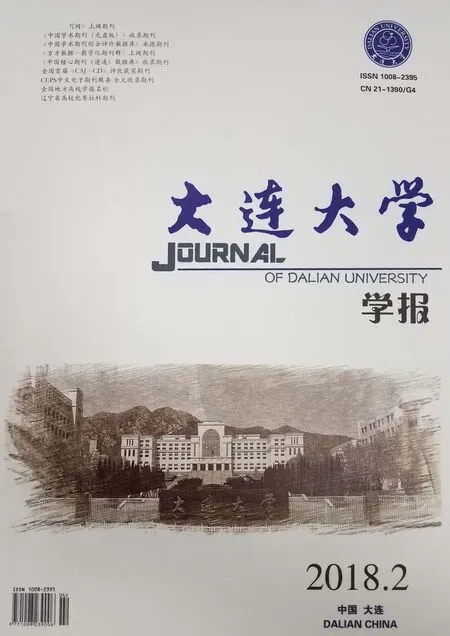论唐宋女性讽谕诗
2018-04-11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提及讽谕诗,历来认为是由男性主体创作的,针砭时弊、有益教化,具有政治功利性的,以抒写国家政事、民生疾苦和抨击社会黑暗为主要内容的诗歌作品。而古代女性作家因囿于闺阁的存在形态,一般认为国家、社稷之类重大题材与她们无关,是不具备讽谕诗产生的条件的。但细读唐宋女性诗歌,发现其中有不少诗歌是符合讽谕诗标准的。这是因为古代女性作家既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也是社稷中之成员,她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关怀着国家、人民和自身的命运,表达着对社会政治、民生冷暖以及文化处境的观感与认识,尽奉着“匹妇”的责任。但在学术史上,对于唐宋讽谕诗的研究,仅局限于男性作家创作的讽谕诗,而对于唐宋女性诗人创作的讽谕诗却关注极少。鉴于此,笔者选取唐宋女性讽谕诗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作一系统的梳理与探讨。
在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古代女性讽谕诗”这一概念有个界定。关于“讽谕诗”,徐元先生在《历代讽谕诗选》前言中认为“讽谕”是“兼有讽刺和谏谕两方面的意义”[1];杨四平在《罗绍书的审丑世界》中说:“讽谕诗,最早出处‘诗者,弦讽谕之声也’。它比讽刺诗的内涵与外延大,‘讽谕’一词兼‘讽刺’和‘谏喻’二义,由此类推,讽谕诗应包括讽刺诗和讽谏诗(谏喻诗)两类,其作用就兼有讽刺与赞美……”[2]。笔者完全赞同杨四平的观点。因此,本文所言的古代女性讽谕诗,是指那些由古代女性诗人创作的,对国家政治、民族命运、伦理道德等社会问题以及女性自身问题,表示讽刺、规谏、箴诫和批判意味的诗篇。与古代男性主流讽谕诗相比,古代女性讽谕诗的内涵和外延也更大一些,它不仅包含了男性讽谕诗的全部内容,同时又囊括了古代女性对自身社会存在形态进行质疑和对封建礼教叛逆的内容。古代女性讽谕诗源流出自《诗经》。如《鄘风·载驰》许穆夫人在卫国危亡之际,讽刺谴责那些阻挠她返卫的“大夫君子”是“众稚且狂”,表达了她拳拳的爱国之心。而《卫风·氓》则是对曾经“信誓旦旦”却“二三其德”的薄悻男子进行了辛辣嘲讽。唐宋女性讽谕诗,正是继承了《诗经》女性讽谕诗的传统,在作家、作品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
文学是面对无法发声的历史的见证,唐宋女性讽谕诗就是唐宋女性诗人对她们所生存时代的诗意抒写。作为缓慢觉醒的唐宋女性创作主体,她们审视现实反思自身,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封建女作家自身才能与生存模式的矛盾同样存在于唐宋女性诗人身上,导致了她们不同的身世命运、性格心态,最终影响着她们的社会视域,从而也影响着唐宋女性讽谕诗对不同社会现象的关注程度和反映深度。唐宋女性讽谕诗反映的主题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注国家命运,讽谏昏庸君臣。战争将一部分唐宋女诗人裹入兵荒马乱之中,使她们成为时代的受害者和苦难的亲历者。她们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记录了对现实刻骨铭心的体验和对国家社稷的关怀,表现出女性独有的不同于男性的慷慨之气。
皇帝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腐败无能甚至投降卖国,都造成人民的灾难,也成为唐宋女性讽谕诗最直接的抨击对象。后蜀灭亡,作为阶下囚的花蕊夫人,面对宋太祖的质问作《述亡国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战争使一位深处宫闱的弱女子不得不直面亡国的残酷现实,但她面对获胜暴君的羞辱与嘲弄却面无惧色,大义凛然,以“十四万人”和“宁无一个”,“妾”和“男儿”两相对照,将昏庸无能的后蜀君臣骂得痛快淋漓。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其一,将一个针砭时弊,满含爱国情怀,并拥有清醒头脑和远见卓识的巾帼英雄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李清照已身为嫠妇,贫病漂泊,却仍然“沥血投书”,冷静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明褒而暗贬,揭穿赵构皇帝虚伪的面具;“勿勒燕然铭,勿种金城柳”,把皇帝奴颜婢膝,急于求和的丑态呈现出来;同时,还将“家人安足谋,妻子不必辞”“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朝臣,与“垂衣思北狩”妥协求和的赵构皇帝形成了鲜明对比,将主战派与投降派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此外,李清照《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韵二首》其一,以唐玄宗晚年的荒淫误国,暗讽宋徽宗信任权奸、昏庸无极。李清照这两首关怀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诗歌,格调奇高,因此赢得清人陈衍的赞许:“雄浑悲壮,虽起杜韩为之,无以过也”[3]。
唐宋女性讽谕诗人不仅将嘲讽的矛头对准最高统治者,表示对国家政事的深度关注,还将视域扩大到边疆,对边防将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唐代薛涛《筹边楼》诗曰:“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筹边楼是大和四年(830年)李德裕为加强战备、激励士气、筹措边事而建造,在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任期内,唐与吐蕃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后李德裕调任离蜀,西川纠纷又起,边事不断。此诗首二句平临八方、气象万千,是对李德裕功绩的赞誉,而第三句却急转直下,对目下的西川道尽了作者心里的隐忧——唐代驻边将官好大喜功、贪婪成性,激化了民族矛盾,使西川受到战争的威胁。诗歌气象雄浑,忧时警世,充满了女诗人深重的忧思之情,有善意的讽劝,也有严正的谴责,托意深远足以让须眉汗颜。钟惺评价道:“(《筹边楼》)教戒诸将,何等心眼,洪度岂直女子哉,固一代之雄也。”[4]。
对国君的劝谏,对奸佞小臣的谴责,往往诱发唐宋女性讽谕诗人对时事体认的另一种政治见解,那就是咏怀历史上忠臣良将的功绩,表达对古代英雄敬仰和崇拜之情,从而暗讽当朝将相的腐败无能。如李清照《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项羽的故事,歌颂宁死不屈的战斗精神。南宋末韩希孟《练裙带诗》写其被元兵所掳,在“失身戎马间”时想到的是“江南无谢安”。而朱淑真的一组咏史诗,直接以历史人物作为诗题,以前朝事论当时政,其《陆贾》诗曰:“惟有君侯守奇节,能将新语悟寰衷”,暗讽宋朝缺乏陆贾那样能够帮助君主开悟治国之心的良臣。此外,朱淑真的《董生》《晁错》《贾生》《项羽》等诗,褒贬历史,直陈己见:为人廉直的董仲舒得不到信任和重用;提出正确政治主张的晁错却被枉杀;有奇才的贾生却遭排挤;英雄气长的项羽却不善用人而遭败。宋代女性的这些咏史诗,明写历史,却无一不是讽谕社会现实,警醒世人,寄托着女性作者的政治见解和理想追求。
(二)关心民生疾苦,直刺权贵豪绅。描写社会底层民众的辛劳,讽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这是元白新乐府诗也是唐宋女性讽谕诗的重要内容。如宋代蒨桃《呈寇公二首》:“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风劲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蒨桃是北宋名相寇准的侍妾。寇准生活奢侈,常通宵达旦宴饮歌舞,将大量绫罗绸缎赏赐给歌女们,蒨桃便作诗劝谏。美人轻绫不胜、织女抛梭苦寒,两相对照,将封建社会不合理的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此诗与白居易《红线毯》十分相似,颇得新乐府之精髓。但白居易是朝廷命官,蒨桃却是地位低下的侍妾,她冒着自身可能被休弃的风险,直言讽谏当朝宰相,关心百姓疾苦,这样的胸襟和胆量确实使人钦佩。因此,清代诗人陈文述在《天竺吊蒨桃墓》盛赞蒨桃“流传讽谏新诗在,寒女机窗感鬓鸦”,将她誉为“妾媵中能诗谏者”。同样承继元白讽谕诗精神的朱淑真在《苦热闻田夫语有感》写到:“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云万叠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日长饥渴喉咙焦,汗血勤劳谁与语?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无成熟。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头向天哭!寄语豪家轻薄儿,纶巾羽扇将何为?田中青稻半黄槁,安坐高堂知不知?”一面是火推日轮、地裂河枯、禾黍败死,田夫三伏天车水救田欲哭无泪、愁容满面的场景;一面却是高堂大宅、富家子弟纶巾羽扇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的画面。如此鲜明的对比,将封建社会对立的阶级关系鲜明地揭示出来。此诗与白居易《轻肥》何其相似,尤其最后一句反问,是对纨绔子弟不劳而获的声讨和鞭挞!满含着诗人强烈的愤懑之情,而对田夫却倾注了深切的同情。这对于一个深处闺闱的封建女性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厌恶扰民战争,同情戍边将士。唐宋女性讽谕诗除了讽刺权贵、关注底层人民辛劳外,还表现在对连年战事的厌恶,对戍边将士的同情以及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唐宫廷才女鲍君徽在《关山月》中这样写到:“……征人望乡思,战马闻鼙惊。朔风悲边草,胡沙暗虏营。……早晚谒金阙,不闻刁斗声。”此诗在“征人望乡”的行为中,以“马惊”“风悲”“沙暗”的场景,立体呈现了征戍环境的险恶与征戍生活的艰辛,表达了征人内心的痛苦,体现了对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又如薛涛《罚赴边有怀上韦相公二首》:“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却教严谴妾,不敢向松州。/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却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薛涛以诗才入韦皋幕府,后因得罪韦皋,被贬至松州。诗中展现了一位命如蝼蚁的乐籍女子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形象画面,大漠孤烟,黠虏暴戾,节度使不调兵遣将安镇边塞,却将一个弱女子罚赴松州。作者在此对镇守官员的讽刺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唐代张窈窕《成都即事》“故园有虏隔,何处事蚕桑”,同样表现战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立意颇高。唐代张睽妻侯氏《绣龟形诗》写道:“睽离已是十秋强,对镜那堪重理妆。……绣作龟形献天子,愿教征客早还乡。”诗歌以戍边将士妻子的身份,诉说战事造成夫妻长年分离的痛苦,表达渴望团聚的心愿,表现了委婉的讽谕意图。
(四)反思女性处境,批判封建道德。唐宋一部分觉醒的女性诗人,以诗歌表现她们对两性不平等的生存状态的反思,揭露封建制度对女性个性才能的埋没和压制,这是唐宋女性讽谕诗最突出的不同于男性讽谕诗的内容。如鱼玄机《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写道:“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作者已清楚认识到,女性身份是自己在封建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障碍,而掩藏在罗衣之下的是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才女,这是对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存在模式的有力质疑。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宋代朱淑真《自责》:“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断金针却有功。” 诗歌对社会压抑、束缚女性诗才的现象进行反诘,对女性生存权利和自身价值的无法实现提出了严正的抗议。此外,如鱼玄机《赠邻女》:“……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写得泼辣豪爽,振聋发聩,更是对封建礼教埋没人性的控诉。鱼玄机的大胆行为甚至引起男性主流社会的恐慌,以致黄周星在《唐诗快》中感喟“鱼老师可谓教猱升木,诱人犯法矣。”。
总之,唐宋女性讽谕诗人扩大的视野,为她们诗歌的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使她们具有同男性一样表达自我,关注身外,体察社会现实的主体意识。虽然封建正统伦理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阻碍,使她们摸索前行的道路曲折而艰难,但她们勇敢抨击现实反抗不公的生命意志,声气真挚,品调自然,闪烁出耀人眼目的光华。
二
男女在不同的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影响下,在文学创作领域便体现出鲜明的不同特点。唐宋女性讽谕诗具有刚柔并济、真朴自然、忧郁凝重的审美风格和独特的抒情方式与艺术表现手法,呈现了抒情主体在封建社会既要表达自我又在压抑自我的矛盾处境[5]。古代女性作家藉由书写来审视自身和外部世界,然而受限于道德要求,其创作活动在反映个人理想之同时也局限于现实之困顿与无奈。唐宋女性讽谕诗人在面对自我书写、社会认同等方面便也因此表现出诸多不同于传统主流讽谕诗人的文学与文化特质。
(一)创作动机:自发而为与异己力量。封建文人士大夫积极进取、针砭时弊的社会责任感,与幽闭于小庭深院的封建女性在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影响到唐宋男、女讽谕诗人的关注视域和行为趋向。唐宋男性讽谕诗人自觉承担社会义务,主动创作一系列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诗篇,以期实现他们兼济天下的历史使命和人生价值,是有着明确目的的自觉创作行为。杜甫创作新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傍”[6];元白倡导新乐府运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7]488;王禹偁积极追随杜甫、白居易创作讽谕诗,自称是“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自贺》);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更明确地把“道”与“百事”联系起来,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的文士,而要求文学作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8]。可见,唐宋男性讽谕诗人们将“文以载道”的传统贯穿于他们的诗歌创作中,自觉地把兼济天下当作己任,使文学创作主要成为其走向仕途,关注政治,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而唐宋女性讽谕诗人则不同,礼教对她们的影响根深蒂固,她们在封建社会的终极价值是如何在家庭中协调好“夫、父、子”对自己的权力关系。所以,唐宋女性讽喻诗人关注闺门之外的社会现实,表达不安苦命的自我愿望,更多的是来自于外界的异己力量。“由外界给与妇女的各种影响,产生妇女在文学上的各种动机的动机,由各种动机的机动,产生妇女在文学上各种的兴趣”[9]。唐宋女性讽谕诗人关注社会现实,其初始阶段大多是源自于现实带来的被动力量,譬如社会动乱、国破家亡、被人抛弃等,这些外在因素将她们从封闭而安全的围墙之中抛向离乱的现实,“飘零遂与流人伍”(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使得她们不得不面对悲惨的命运、残酷的现实。唐宋女性讽谕诗人中因战争因素关注社会现实,除了李清照外,还有裴羽仙、花蕊夫人、韩希孟、王清惠等。而鱼玄机是因为被丈夫抛弃被迫出家为女冠,不幸的命运与道观开放的环境,使她有了更多反省女性自身社会存在的问题,因而才产生了她抨击讽刺封建社会的有力作品。因此,唐宋女性讽谕诗人从事创作的动因更多是一种强而有力的社会客观力量,是被动的而非自为的,这与唐宋男性讽谕诗人自发性的创作情况截然不同。
(二)关注视野:宏大叙事与书写自我。封建社会男性以整个世界作为活动空间,在社会视域中施展自己的抱负。他们的讽谕诗总是与社会的重大问题相关,讥讽无能统治者,批判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等等,表达的是社会使命感与自我的人生价值。而古代女性诗人拥有的家国意识大多常常是在外力激发下才具备的,尽管她们时有针砭现实的作品,然而更多还是言说女性自我的情感志向,这是古代女性具体的存在方式与文化教育的共同结果。体现在讽谕诗创作中,古代男性更多将目光投向国家、社稷和民生,关注现实社会的发展问题,体现为宏大叙事的历史政治功能;而唐宋女性讽谕诗人更多地着眼于与自身相关的不平之事,倾向于边缘状态的自我境遇的书写,往往体现出平实而内敛的讽谕意味。陈子昂的《感遇诗》,讽谕内容涉及国家命运,边患战事,社会良莠,民生困苦等等。罗隐讽谕诗多把讽谕矛头指向各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其仕途坎坷、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遭遇,使他对封建科举和用人制度有较为深刻的洞察,因而写出了《曲江春感》《书怀》等优秀的讽谕诗篇。苏轼强调“言必中当世之过”[10],写下了一系列谴责官吏贪婪、反映民间疾苦的政治讽谕诗。
唐宋女性讽谕诗虽然也有像男性讽谕诗那样关怀家国民生和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但数量还是比较有限,更多的则是描写与女性自身相关的事情,表现的是封建女性生命个体与社会生存环境的矛盾与较量。因此与男性讽谕诗人关注社稷民生的崇高抒情和宏大题材相比较,唐宋女性讽谕诗人则体现出“内敛”式的文化视域。她们立足于自身生活的环境,更多表达了对自身处境的感悟和人生态度,透视出幽微的讽刺意味。如唐代赵氏《闻夫杜羔登第》:“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唐代进士及第后有到长安有名的青楼平康里冶游的风俗,赵氏此诗便是当时情景的描绘,作者以戏谑的笔触,反讽的意味,透射出女性内心敏感细腻的情愫——对年少丈夫纵游烟花巷的酸涩意味。宋代毛友妻《寄外》“剪烛亲封锦字书,拟凭归雁寄天隅。经年未报干秦策,不识如今舌在无?”这是妻子写给外出科举求仕、长年不归的丈夫的书信,在深深的关切之情外,诗中别有一种幽默讽刺而调侃的意味,隐约传递了封建社会留守在家尽奉义务的女性对丈夫的幽怨的心声。又如朱淑真《自责》其二:“闷无消遣只看诗,不见诗中话别离。添得情怀转萧索,始知伶俐不如痴。”这首诗在反讽中表达了封建社会意识觉醒的知识女性生存更其艰难和精神更为痛苦的情状。而鱼玄机在《赠邻女》中通过“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的泼辣的反讽,道出的是“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的屡经情感磨难的封建女性共同的心声,标示了诗人大胆挑战封建道德底线的叛逆精神和反抗意识。
唐宋女性讽谕诗人往往是由自身所处的环境、命运而触及到社会现实,从“家庭个体的人”到“社会大写的人”,视角由小及大,从而揭示社会本质问题。如唐代王韫秀《夫入相寄姨妹》:“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鸣机妇,耻见苏秦富贵时”,这是王韫秀在夫君元载拜相之时,衔宿恨寄给姨妹的诗作,讥讽妻族目光短浅、嫌贫爱富的鄙陋行为。可以看出,作者作此诗的目的,原本仅仅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而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批判人类趋炎附势劣根性的社会效用。
(三)接受对象:期待心理与对象缺席。男性诗人创作讽谕诗歌是功利性与价值性的结合,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清现实,从而改变现实,其指向性和目的性是十分明确的,受众也是比较广泛的。如杜甫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白居易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11];刘禹锡《萎兮吟》是永贞革新失败后,针对反对派的恶语中伤和诬陷而作;李贺的《官街鼓》是针对皇帝盲目笃信道教、追求长生不老而发。与这种讽谕诗受众的明确与广泛相联系,男性讽谕诗人在艺术上追求“其辞质而轻”“其言直而切”的凝练、简明而通俗[11],诗人在创作讽谕诗时在心目中已经期望过能够读懂并践行他们诗歌主旨的读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自述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7]2789,他的好友元稹亦称白居易“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12]。白居易了解到“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时,他认为通过创作讽谕诗批判社会现实,从而干预社会政治的目的基本实现了。而唐宋女性讽谕诗歌,首先面临的是接受对象的缺席,一般表现为倾诉对象与接收对象的重合,或者范围也仅限定在有限的女性对象的范围之内(那些传颂广泛的古代女性作品数量相对有限),因此,其女性讽谕诗在艺术表达上更多是自我言说的“独白”方式。以求得心理调节达到痛苦缓解和情感的宣泄,而真正能否有人体会、同情或者支持并不重要,她们的目的只在言说,女性诗人自身扮演了“倾诉”与“倾听”的双重身份。她们通过这种方式消解心中块垒、倾诉人生苦难,从而获取生存的力量。这也便是古代女性从事文学创作的意义与价值。
唐宋女性创作的讽谕诗,有家国之忧,民生之忧,但更多体现的是身世之忧,对自身处境相关的人和事的揶揄、讽刺、揭露以及殷切的期望、幻想成为其讽谕诗最为显著的特征,这是由其生存的封建社会文化环境导致的结果。正是这种文化心理形成了唐宋女性与男性讽谕诗在表现主题、审美风格、创作动机以及传播流变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唐宋女性讽谕诗作为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主题,应该引起重视和深入研究,发掘其蕴藏的社会现实价值与学术文化价值,作出符合历史的客观评价,给予它应有的社会地位。这对于推进女性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大有裨益,同时对于繁荣我国传统文化,构筑两性和谐社会也有积极作用。
[1]徐元.历代讽谕诗选[M].合肥:黄山书社,1986:1.
[2]杨四平.罗绍书的审丑世界[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8:71.
[3]陈衍.宋诗精华录[M].成都:巴蜀书社,1992:672.
[4]钟惺.名媛诗归·唐卷十三[M].内府藏明末刻本20.
[5]舒红霞,牛荣晋.唐宋女性讽谕诗的审美艺术[J].大连大学学报,2012(2).
[6]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二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2:255.
[7]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8]欧阳永叔.欧阳修全集·与黄校书论文章书[M].北京:中国书店,1992:488.
[9]陶秋英.中国妇女与文学[M].上海:北新书局,1933:87.
[10]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3.
[11]白居易.白居易集·新乐府并序[M].长沙:岳麓书社,1997:41.
[12]元稹.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