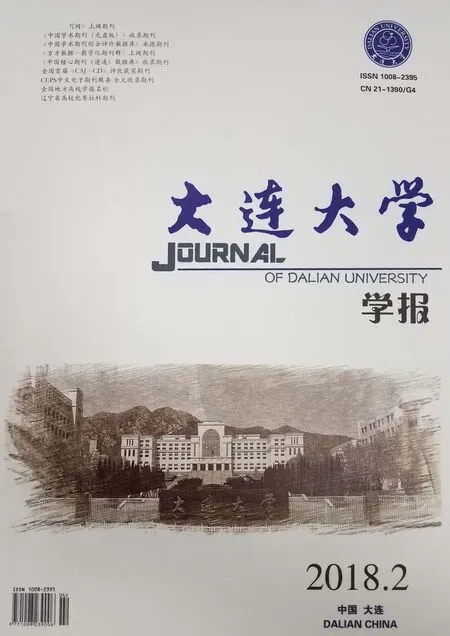中国剪纸的源流和它的文化特征阐释
——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之一
2018-04-11
(大连现代博物馆,辽宁 大连 116023)
处在生活最底线,无时不在承受生活所赋予一切的中国民间妇女,正是这些无数的中国妇女搭建构筑了民间中最为深厚和最为灿烂的文化河床。在漫长的封建父系社会时代,中华民族勤劳、顽强、善良、淳朴情感品质的塑造,是那些中国民间妇女通过生活,通过手中不断发明创作的民间艺术的过程不断实现的。她们通过手中的剪刀,悄然默默地倾注了人类最为真实的、充满了生命的情感和一生中孜孜所求的希冀与心血。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放言,自剪纸作品问世以来,它的每一幅作品都是执剪者的心灵之花,而那些看似普通的剪刀就成了让心灵之花绽放的精灵。
中国剪纸陕西延川的传承人刘洁琼在她的《女人的剪子,心灵之花的精灵》一文中,就非常形象而生动,款款深情地写到:“剪子的一张一合,一静一动,实际上表现出了对人性的演绎。”“这其中的奥妙表现的是一种女人的天性和它的自然性;也同时更加证明了剪子就是人生关口的象征,本源符号的再现。剪子一张是女人的生殖符号,一合则是男人的生殖符号。剪子一张一合,一静一动,就是男女合欢,人类繁衍的意思。所以,剪子就是女人掌管生命之花的工具;也是家庭和睦的密码。”“女人用剪子是命中注定,老天恩赐的,剪子是女人人生道路上经营婚姻的主权所在,收获胜利所在,繁衍子嗣所在。剪子是人生起源的第一关口,是人性启蒙教育的初始。常言道‘女人的世界是一把剪刀,男人的世界是一把䦆头’䦆头和剪子延续了子嗣定乾坤;䦆头和剪子辟邪镇宅定安宁。”[1]因此,当我们在欣赏与研究民间剪纸艺术风格以及它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精髓时,就绝然不会产生所谓的茫然,陷入到冥思苦想之中。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剪刀是民间妇女情感倾诉的工具,在剪子的张合作用之中,那些传统的却是自由自在的图案纹饰,以其朴素、鲜活、灵动的生命语言,讲述着女人花一样的世界。日常生活中的心动,民间中的传说故事,以及五谷六畜,花木鱼虫,飞禽走兽,都被她们剪贴到了终身不离的房舍窑洞,厅堂居室,窗棂炕边,水缸粮仓上。朴实、平静、淡如流水的人生经历与神奇、绚烂、生机盎然的心灵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单调生活与心中美好幸福,吉祥如意的精神憧憬都化作了剪刀下的一条条、一丝丝交织在虚实相间,变幻莫测的平面图纹中。在以民间妇女为主体的剪纸文化里,风格内敛,静态的线条,刻画了她们的心历路程,曲线圆形,描绘出自己的啾啾心声。在人类社会中,引以为豪最应获得尊重的生命形式,在妇女的巧手之中,化作了世间上美轮美奂的哲学思维。由此,那些生存在民间中的民俗事项,再也不是一个个简单的空间上的概念,剪纸也绝不是一种看似平淡的生活的表面形式。讲到这里,就不禁让我们回味起了古人对剪纸艺术与剪纸文化的赞美。唐人杜甫诗中有“暖水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的佳句,白居易也曾有感而发“疏流似剪纸,决壅同裂帛”。李商隐则有诗曰:“镂金作胜穿锦服,剪纸为人起晋风”。宋人方回则曰“数家祈福来浇奠,剪纸糊灯作上元”,王子俊更是心绪激荡,留下了“剪子铺平江,雁飞晕字双”的妙语。
自古以来,人们就是在翻阅各种各样的剪纸图案纹样的同时,聆听着来自先贤哲人的绝妙好辞,于生命的长河中,追寻着形式最为简单,但内涵又是极为丰富的生活画面和生命的律动。
大连地区的剪纸历史犹如奔涌的长江、黄河,同样是源远流长。它似乎也经历过萌芽期、成长期、鼎盛期、衰落期这样几个阶段。只是限于文献史料和考古发现的不足,我们还尚难以对上述各期做出精确地论述。但是,它的鼎盛期与全国的剪纸历史同步相向是不会有误的。据说,大连的大黑山剪纸流传至今就已有600余年的历史。当下,我们在探讨与研究大连地区的剪纸文化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的把目光首先投向庄河地区,其次会提到金州地区以及普兰店、瓦房店和旅顺。大连庄河地区的剪纸在2006年入选辽宁省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荣登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2010年时又被作为中国剪纸的一部分,入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庄河地区的剪纸因此而声名鹊起。
我们追溯大连地区鼎盛时期的剪纸文化的创造者们,大多主要是从山东、河北、河南、天津等地迁徙来大连的移民。因此,来自鲁、冀、豫、津等地剪纸特色中所代表着的北方剪纸中具有的浑朴古拙,粗犷刚健,大方而触目,生动而耐看和喜庆吉祥,寓意深邃的古风遗韵也就成为大连地区剪纸艺术的源头和底色。发展到今天的大连地区剪纸文化,在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洗锤之后,逐步形成了朴素、简练、概括、稚拙感强、重于图案纹样的变形夸张,喜用大的块面和粗壮有力的线条来表现自己的作品的特征。总而言之,“大连地区的剪纸具备了中国民间剪纸的艺术共性,即简练概括,夸张写神,善用比喻,谐音寓意,构思大胆,幽默取巧,富裕装饰,应物赋形。”[2]6郭沫若先生曾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剪纸文化特征给予了高度的总结,其中大连地区的剪纸不乏在其中亦占有几分天地。他说:“曾见北国之窗花,其味天真而深厚,今见南方之刻纸,玲珑剔透得未有。”[3]
大连地区的剪纸工具主要是以剪刀为主,刻刀的表现手法并不多见。而且在剪纸的过程中,好用单一的红色。在技法上,多用阳剪。“上炕剪子,下地镰刀”是大连地区的妇女生活与劳作的真实状况。这种不加任何的修饰的语言,把大连地区妇女的劳作生活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在生活当中,她们善于对自然物象进行主观改造,剪下率意畅情,造型夸张抽象,内容意境深刻的作品。“往往通过形象表达、谐音表达、文字表达等方式,将表现的对象典型化。”[2]8她们更多的是遵循着一种变形夸张的装饰造型原则,讲究剪刀运行中的简繁处理和黑白之间的关系。就大连地区所常见的剪纸种类而言,“主要有窗花、喜花、墙花、门笺、绣花样子和纯视觉观赏性的剪纸。”[2]3
在中国漫长的农耕经济社会中,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无法摆脱浓郁的农耕文化的信息。中国民众祖辈相袭的人生目标和锲而不舍的终极理想都盘桓在这种农耕经济社会所限定的小圈子里。作为偏隅一方的大连民众,也同样不可能跳跃出这个社会化的小圈子。正是在这种自给自足,安土重迁,礼让仁和,血缘至上,家族为重的农耕经济的社会中,才形成了人们对家庭和睦,家族昌盛,子孙满堂,丰衣足食,幸福长寿等等理想、愿望的强烈祈盼。这些理想、愿望经过长期的积淀和人们的梳理,就逐步的形成了涵盖整个大连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剪纸文化中所常见的“福”“禄”“寿”“喜”“丰”五个关键性的主题词[3]41。基于农耕经济社会结构下所产生出的“福、禄、寿、喜、丰”这五大主题词,也就搭建了中国民间社会传统剪纸文化里的基本功能性的意义和人们在剪刀的张合之中形成的精神价值取向。在这些基本功能性意义和精神的价值取向引导下,大连地区的剪纸文化终不能脱离其中,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剪纸文化中丰富多彩的意象体系和习俗模式中的一部分。
已经有研究者指出,剪纸之用,一般有两种途径,一为人事,二为神事。为人事者,主要取其深邃的美感装饰价值;为神事者,则取其宗教巫术价值。剪纸的装饰性在民间中主要是以鲜亮的色彩和娱乐且吉祥的图案,达到人们愉悦心情和对美好理想、愿望的期盼。“从民俗文化的演进历程看,越是古老,其宗教的用意就越是明显,世俗的内涵则较浅淡。相反,越是向后世延续,其宗教性就越是淡漠,而世俗性越发的加强”[3]19在民间口口相传的“福、禄、喜、寿、丰”,就正是人类在伴随历史行进过程中,世俗性不断日益深入人心的最好的例证。
“福”是人们心中一切最为美好的理想的核心。自古以来,在中国的民间中就有“五福”之说。从过往大连地区的剪纸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往往多以蝙蝠为主题,落到剪纸的图案之中。新春之时,人们用红纸剪出五只蝙蝠贴于门户,以“红蝠”谐音“洪福”,取意“五福临门”。还有的剪出诸多的蝙蝠,它们或翔或集,寓意“百福图”;以蝙蝠与寿字或寿桃、古钱组合成吉祥图案,取名“五福捧寿”“多福多寿”“福寿双全”;剪出童子仰望蝙蝠飞翔及纳蝠入缸的图案,隐喻“纳福迎祥”“翘盼福音”“平安五福自天来”;以蝙蝠和古钱作为图案,取意“福在眼前”。
“寿”是人们在生活当中对生命不断延续的祝愿。在以往大连地区的剪纸中,人们常见的有以松树与菊花、松树与仙鹤的构图,隐喻着“松菊延年”“松鹤常春”的吉祥语。还有的以仙人捧桃的图案,构成了“瑶池集庆”“麻姑献寿”等寓意深刻的吉祥语。还可见到用山茶花和绶带鸟的图案,组成了“春光长寿”的吉祥语;以绶带鸟、湖石、水仙的图案,组成“天仙拱寿”的吉祥语;用绶带鸟、腊梅、天竹和水仙的图案,组成“齐眉祝寿”的吉祥语。常见的还有用蝴蝶作为图案的主题,作为祝寿的题材。
“禄”是人们在生活期盼中对功名利禄的一种追求。在大连地区以往的剪纸中,常见的有以鹿和蝙蝠为内容的组合,构成了“福禄双全”的寓意;以猴子为图案对象,取其“侯”的谐音,用马与猴的组合,隐喻“马上封侯”的愿望,以母猴身背幼猴的图案,隐喻“辈辈封侯”的祈盼;以猴子爬枫树挂印章的图案,表现出“封侯挂印”的寓意。相关此类题材的内容,甚是丰富。
“喜”是人们在生活的过程中对质量的一种要求。表现在大连地区以往的剪纸中,常常见到人们以牡丹、桃花、海棠花、蜘蛛、喜鹊等作为图案纹样下剪,表达出“富贵长春”“富贵万代”“富贵满堂”“喜从天降”“喜上眉梢”等。
“丰”是人们对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的理想要求。在大连以往的建制中,我们可以见到以龙、鲤鱼、燕子、雄鸡、大象等图案,组成了“连年有余”“五谷丰登”“吉祥如意”“瓜瓞绵绵”等寓意。
应当说,早期大连地区的剪纸与中国社会民间剪纸一样,它的意象类型非常的多样并趋于复杂。在杨学芹、安琪所著的《民间美术概论》里,对于整个民间艺术作了系统的意象分类。因此就有人依据与此,对剪纸文化中所表现出的意象也做了一些的分类,而在我们的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大连地区的剪纸同样具有下例的分类内容:
“祝福祈祥类。如吉祥如意、龙凤呈祥、吉庆有余、洪喜临门、四季平安、三阳开泰、三福寿多、富贵平安、十全富贵、千载太平、鹿鹤同春、金玉满堂、龟鹤延年、青云直上等。
镇妖辟邪类。如钟馗捉鬼、镇宅狮虎、虎镇五毒、神娃护娃、神蜍啖鬼、吕祖降妖、葫芦收毒、金剪断蝎、艾虎辟邪、太极八卦等。
爱情婚姻类。如喜上眉梢、鸳鸯戏水、鲤鱼闹莲、鸳鸯卧莲、二龙戏珠、有凤来仪、凤戏牡丹、鸳鸯偶合、白头偕老、锦鸡牡丹、鸾凤和鸣等。
家族繁衍类。如莲生贵子、麒麟送子、榴开百子、瓜瓞绵绵、金鸡送子等。
神灵圣贤类。如八仙过海、麻姑献寿、太公钓鱼、刘海戏蟾、西游记等。”[3]178
在剪纸艺术中所表现出的这些强烈的深邃睿智,内涵丰富,寓意深刻集中地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哲学智慧,深刻地凸显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性格气节所在,精神魂魄所系,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人类文明的生存智慧。“福”“禄”“寿”“喜”“丰”是人们对自身存在意义的主动追问,是对主体人格的自觉追求。这种理想状态或许很难达致,但却可以激励人们不断的去追求。“这种追求,体现在哲学上就是主体人格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体现在实践中则是进取精神在积极入世中高扬的过程,进而最终实现主体人格的动态完善和社会的不断发展。”[4]从民间文化的角度上看“福”“禄”“寿”“喜”“丰”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自然观、宇宙观的体现,它包括了人们对众神万物的敬畏和想象,对生活空间的叙述和表达。循着对善灵瑞兽的正面想象,人们赋予自身走向自然的合法性和心理慰藉。敬畏在信仰中流淌,想象在仪式中演绎。大连地区过往的剪纸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乡愁记忆和口头叙事的对象。这里的乡愁,一半源于对乡土环境的依恋,一半是对人类生活叙事的传承。从那些剪纸我们所能感悟到的是,人们对生命延续和新生的渴望,反映了民众在知识有限的情况下,激发出解释事物的丰富联想。生动的剪纸形式和其内在的寓意,将动物、植物拟人化后演绎的社会生活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在剪纸中表现出的浓郁的地方色彩的风物传说,更为片片剪纸赋予了历史的厚重感与人文情怀。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道,“大连剪纸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深厚的生存土壤,生命力极强,这一方面同人们长期形成的观念意识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又同人们的生活追求密切相关。”[2]27
随着时代的进步,今天大连地区的剪纸已经突破了以往陈旧的题材,在剪纸画面的组织上,更多的是表现出与时俱进,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契合。正是这样,大连地区的剪纸艺术之花,在剪纸人的传承下,一代一代的得到了发扬光大。今天,大连地区剪纸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庄河剪纸艺人韩月琴。韩月琴1941年出生于庄河的冰峪沟,剪纸技艺源自家传,其在6岁时的剪纸就赢得长者的一片喝彩!中国剪纸高层论坛评价说“她的吉祥如意剪纸,脱形写神你,粗犷神奇,巧妙运用传统吉祥纹样将概括与夸张、比喻与谐音、寓意与象征手法生动地运用到剪纸中,达到神似大于形似的效果,把吉祥如意主题发挥到极致。”[2]9在2018年新年伊始之时,韩月琴被国家文化部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研究大连地区剪纸文化过程中,引以为豪的根本之所在。
[1]刘洁琼.女人的剪子,心灵之花的精灵[N].光明日报,2017-07-04(12).
[2]刘益令.大连民间艺术[M].大连出版社,2013.
[3]王贵生.剪纸民俗的文化阐释[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黄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性格[N].光明日报,2017-07-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