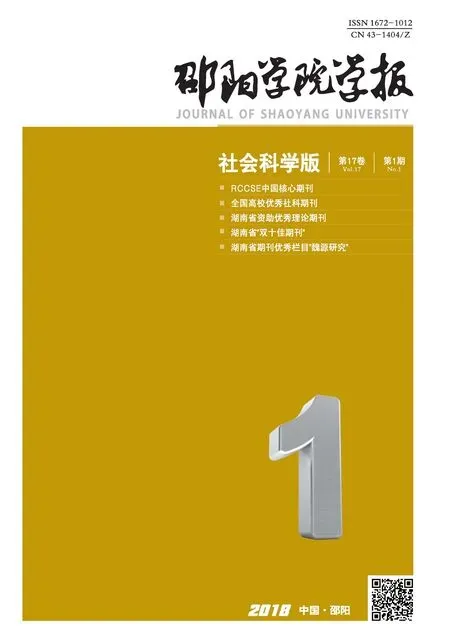论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形成
2018-04-04胡克森
胡克森
(邵阳学院 文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进行了全面阐述,从而构建起中华民族自己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理论体系,从此之后,学界逐渐将这一体系应用到其他学科领域,文化学界、宗教学界也开始有了多元一体格局的提法,但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含义,应该怎样描述,并未有人做过系统论述,刘道超写过一篇《论我国民间信仰的多元一体化格局》,认为我国民间信仰存在着多元一体化格局,所谓“多元”,是各地民间信仰表现的极端多样化,所谓“一体”,是全民族大体一致的以“天地君亲师”为至尊的信仰秩列。[1]刘道超在这里并未涉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体系。张践先生写过《我国民族宗教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文章,[2]但也只是肯定了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复合性民族,具有多元的宗教信仰与多元的民族文化认同的这一事实,并没有阐述中华民族宗教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内涵及其形成过程。因此,今笔者拟在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中华民族宗教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主要内涵
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可以归纳如下: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在内的多层次的民族实体。在这多元一体格局中,中华民族是高层,56个民族是基层。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实体。汉族尽管也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但它发挥凝聚作用将多元结合为一体。汉民族是在秦汉时期发展成熟的,其他民族是在而后的历史中逐步发展成熟的。[3]
按照民族宗教学的理论,世界上所有民族都具有宗教性,而所有宗教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文化,与宗教更是密不可分。在远古社会,宗教更是全部民族文化的载体,几乎所有民族文化都是对宗教的解释。我们研究古印度文化,就需要通过研究印度教、佛教来进行;研究古代欧洲文化,就必须研究犹太教、基督教。没有伊斯兰教,没有《古兰经》,就没有阿拉伯文化,也没有阿拉伯民族;没有基督教文化,也就没有欧洲文化和西方文明。而宗教在民族文化中的作用,正如牟钟鉴先生所指出:“宗教往往为许多民族提供价值理想和精神支柱,处于民族文化的核心或深层位置,成为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4]这就是说,宗教文化对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关键和核心的作用。据此,我们认为,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我们本文所述说的中华民族宗教文化多元一体格局构成一种对应关系。即作为高层实体的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民族宗教,汉民族及其他55个基层民族也有相对应的民族宗教,而这些宗教文化都是伴随着该民族实体的形成而形成的。金泽先生也说到:“中国宗教不仅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多元的格局,而且和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形成互动关系。”[5]金泽先生这里所说的互动关系与笔者所说的对应关系意思基本相同,都是说明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在各民族相互融合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
中华民族宗教文化毫无疑问是“多元”的,从全国来看,既有自己的本土宗教——道教,又有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而儒学也呈现一定的宗教性质。除此外,汉族以外的各民族也均有各自的民族宗教,尽管不一定每一个民族都拥有一个宗教体系,但每一个民族肯定有他本民族的宗教信仰,许多民族可能是一个民族群信奉同一种宗教,但在不同民族中却具有不同的宗教派系。如北方具有草原文化特色的萨满教,为北方许多民族共同信奉,但各个信仰民族中又形成不同的萨满教派系;南方的信仰体系更为复杂,湖南、湖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区的苗族、瑶族、黎族、土家族等共同宗奉的巫教、梅山教;云南纳西族信奉的东巴教;四川、贵州地区彝族信奉的毕摩教,还有西藏、四川等地的藏传佛教,甘肃、宁夏、新疆等地信奉的伊斯兰教。其次,除上层信奉的国家宗教之外,在下层社会还有大量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呈现多元宗教信仰与多元民族认同的局面。
那么“一体”是什么呢?“一体”就是我国古代的正宗大教,即“宗法性传统宗教”,它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6]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宗教文化格局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发展,又遵循了民族融合和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主线是首先在黄河中游形成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初级凝聚核心:华夏民族。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发展而形成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成分而日益壮大,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而形成中华民族的高级民族实体。[3]而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同样呈现这样一种发展道路。在中华远古时期,中原地区由于文明发展的先进,首先形成了一种原始部落宗教——巫教。这一原始宗教是由黄河中游地区众多民族集团共同创造而形成的,因而也可以说是华夏民族的部落宗教。这一部落宗教随着民族集团的迁徙和分裂而传播四方,在中原的随着汉民族的发展成熟而形成董仲舒的新儒学和民间社会酝酿而形成的原始道教,而恰在此时,外来宗教——佛教也传入中国,在完成其中国化的过程后,构成中华民族多元宗教文化的一元,而流徙于其他各地的巫教在隋唐以后逐渐结合各地的本土文化随着其民族的形成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民族宗教。而后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又先后陆续传入我国,从而形成宗教文化的多元格局。而“宗法性传统宗教”的“敬天祭祖”特征即酝酿于我国原始宗教之中,在历史的发展中被儒教、道教和各地方民族宗教所继承,有些核心理念甚至为佛教所吸收。因此可以说,“宗法性传统宗教”是中华民族宗教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体”。
二、华夏民族的部落宗教巫教是中华民族本土宗教之源
中华文明起源于炎黄时期,是由当时诸多民族集团融合而成的。当时炎、黄集团是最重要的集团,又叫华夏集团,是北方的部落。其居留之地,西到陕、甘,东与东夷部落交错,南与苗蛮部落为邻,是古代传说中最为显赫的部落。东方有太昊、少昊、颛顼和蚩尤九黎部落等,居住于山东、江苏及河南中部以东地区,南方的江汉流域有三苗部落集团。*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二章《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7—127页;又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8—132页。这些部落集团由于争夺领地和人口,发生了几次大的部落战争,第一次是炎黄部落集团与东夷蚩尤九黎部落的战争,蚩尤战败被杀,其部落残余败逃南方,接着炎帝与黄帝之间又发生了一次为争夺部落联盟领袖地位的战争,炎帝战败,黄帝成为黄河地域最强大的部落联盟领袖。后来又发生了中原以炎黄为主的部落联盟与南方三苗集团的战争,三苗战败南迁,黄帝在中原主宰权的地位正式确定。黄帝占据中原以后成为不断融合中原各地众多部落的核心力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华夏族,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凝聚核心。华夏民族的原始部落宗教正是伴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华夏民族的部落宗教是当时中原各部落集团共同创造的,是各民族宗教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这一原始部落宗教创立者的代表人物是蚩尤、颛顼和重、黎等。《国语·楚语下》记载的“观射父论绝地天通”[7]559-564的一段话,详细记载了中华民族原始部落宗教——巫教的诞生过程。从这段史料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一、华夏民族部落宗教的形成是上古时代多元部落集团宗教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并非某一民族集团宗教文化传统直线演变而成;二、华夏民族部落宗教是中华本土宗教之源,而后随着民族的迁徙和文化的交流,留在中原的巫教结合中原文化则发展演变为道教,流播于北方的巫教结合草原文化演变为“萨满教”,转徙于南方山地丘陵川泽文化的即演变为具有浓重巫术色彩的各色宗教,如梅山教、东巴教、萨玛教和毕摩教等;三、华夏部落宗教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宗教主干的直接源头,保留了原生性宗教的灵魂崇拜、祖先崇拜和天地崇拜等原始基本特征,与后世其他民族宗教有许多内在的共性因素,从而构成了相互认同的深厚基础。[5]
三、董仲舒的新儒学与道教是汉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
汉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凝聚中心,它形成于秦汉时期。宗教毫无疑问属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因素:民族心理范畴。而董仲舒创建的新儒学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汉民族宗教的作用。应该说,原始儒学具有相当明显的非宗教的世俗特征。儒学本是从中国巫术文化中分化出来的。“儒”原本属于民间的方术之士,主要服务于民间的礼仪活动,属于传统宗教的继承者。但到了春秋这个学术为天下裂的时代,孔子全面继承周代的道德文化传统,将传统的术士职业宗教家之“儒”改造为伦理道德之“儒”,从而形成一个儒家学派,着重阐述日常伦理之事,使其从原始宗教中彻底分化出来。*关于儒的术士宗教品格,分别见于章太炎《原儒》(《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4—107页)、胡适《说儒》(《中央历史语言所集刊》第4本第3分册)、钱穆的《古史辨》第四册《序》)、徐中舒的《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原始儒学主要讲述的是人伦关系、做人准则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内容,很少有超越现实的终极信仰问题,甚至很少讨论世俗以外的天地鬼神的抽象问题,因而遭到了鬼神论者墨子学派的批判,这应该也是儒学不被当时的封建诸侯所欢迎的原因之一。正如姜生所说,“汉代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与苛政的痛苦之后,似乎人们对于神灵与不死的渴望胜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周代传统的天神信仰出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回归趋势,神仙家们在经历了子学兴盛的‘理性时代’的压抑之后,又纷纷登台,以满足新的社会需要;思想家们在探讨现实社会人生之际,亦感到理性主义的局限性”。[8]75因此,到了汉代,董仲舒一改原始儒学的面貌,充分吸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的有益成分,开始将儒学神学化,建立起他的“天人合一”的儒学神学体系。徐复观说:董仲舒“把阴阳四时五行的气,认定是天的具体内容,伸向学术、政治、人生的每一个角落,完成了天的哲学大系统,以形成汉代思想的特性。”又说:“两千余年,阴阳五行之说,深入社会,成了广大的流俗人生哲学,即可追溯到董仲舒的思想上去。”[9]182-183
从此之后,儒学开始大谈天命,强调天的意志高于人的意志,从而为现实世界的解释找到了终极的答案,也使董仲舒的新儒学具有一定的宗教文化特征。但尽管如此,汉代处于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之中,社会思想极为复杂,战国以来“百家争鸣”所激发出来的思想并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彻底消化掉的,因此,董仲舒的“儒学独尊”只是解决和统一了当时上层社会的思想信仰,下层人们的思想信仰并没有得到整合,通过西汉后期原始道教信徒们与上层社会的交往就可看出来。如西汉后期原始道教信徒齐人甘忠可编造了一本《天官历包元太平经》,通过进献这部书提出刘汉王朝退位禅让的改革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朝臣及最高统治者的赞同,并按照原始道教经典的指导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实践,说明阴阳灾异及汉王朝退位更受命思想在西汉上层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但眭孟、夏侯京房、李翼、李奇等是阴阳灾异学的信奉者,就连董仲舒、谷永、刘向、刘歆等人不但坚信阴阳灾异谶纬学,也主张西汉退位改元。*谷永直言:“垂三统,列三证,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第3466—3467页)刘向也有“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单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的言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1950—1951页)。而这一主张最后没有被接纳的原因不是这些儒学大臣认为刘汉王朝不应该退位禅让,而是原始道教徒的身份所致,觉得他们不是上层社会所信奉的正宗儒学,只是民间社会的邪道主张。这就说明,汉代的大量民间信仰急于转化为一种理论形态,即宗教化,这就是汉代原始道教形成的社会原因。姜生先生在《论道教的成因》一文中说到:“秦汉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一种深刻的文化——信仰危机;服务于分裂时代的先秦文化,不复适合于大一统的新局面,而道教正是应于这种危机局面所出现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10]笔者在《论原始道教的两大社会源流》一文中提出汉代原始道教的形成具有两大社会源流,一部分为知识士人,属于思想信徒,主要参与对原始经典的创立,他们利用两汉的社会危机,提出了一整套救世方案,即原始道教经典,首先试图利用这部经典投靠上层,劝说最高统治者进行政治改良,而另一部分即为下层民众,属于实践信徒,他们长期活跃在民间,传播神仙术,起着宗教组织者的作用。两大源流原本互不交接,但当知识道徒多次向最高统治者进献救世经典均遭拒绝之后便走向了民间,以民间的神仙教信徒为基本信众,进行传经布道,发动教徒掀起了武力夺权的暴力革命,民间信徒即利用其教义进行广泛宣传,从而使信教队伍迅速扩大,原始道教正式形成。[11]
原始道教的形成,汉民族才真正完成了它的宗教创建。也就是说,新儒学与原始道教是汉代的两大文化创建,二者共同构成了汉民族的精神信仰,即汉民族的共同民族心理,也是汉民族的宗教信仰。英国语言学家、宗教学家麦克斯·缪勒在他的《宗教学导论》中说:“中国产生了两个宗教,各以一部圣典为基础——即孔夫子的宗教和老子的宗教,前者圣典是《四书》、《五经》,后者的是《道德经》。”[12]56尽管这种说法有很多错误,如他将老子和孔子都当做宗教家,以及将《四书》、《五经》和《道德经》都当做宗教经典,但他看到了儒教和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两大宗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从中国原始巫教中分化出来古代两大知识体系,或者说两大知识信仰发展到汉代,伴随着汉民族的形成而形成两大宗教体系。按照民族宗教学的理论,二者均属于汉民族的宗教。
四、印度佛教的传入及其逐步中国化为中华民族的多元宗教增添了新军
佛教不属于中华民族的本土宗教,而是来源于印度的宗教,可是在中国经过近1000年的历史演变,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而一变而为中国佛教,成为中国多元宗教文化的一元,而佛教在它的本土印度反而日渐衰落。佛教大约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相传创始人是古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佛。佛教,在中国史书上曾有“释教”“佛陀”“浮屠”“浮图”等多种译名。佛教以“四大”(地、水、火、风)为空,以人生为苦,以追求精神解脱为最高目标。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内地主要是佛经和佛像,但佛经的传入需要翻译,因此,陆续有印度僧人来到中国内地作佛经的翻译工作。据说,最初的佛经翻译僧人就是西汉安帝邀请来的天竺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他们在白马寺中翻译出了《四十二章经》,而东汉末年最有名的佛经翻译者是安息僧人安世高。他译出了《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禅经。再就是支娄迦谶,他译出了《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等。但三国西晋时代,佛教开始在中国流传开来,佛经翻译事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到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在中国达到了隆盛阶段。大量的印度高僧来到中国,中国内地也成长出一些著名高僧。印度高僧最著名的有佛图澄、鸠摩罗什,内地高僧主要有道安和慧远等。随着这些高僧得到最高统治者的礼遇,佛教在中国获得蓬勃发展的机会,因此众多高质量的佛经被翻译成汉文。而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以及有知识的僧徒增多,开始形成最初的佛教宗派和庞大的僧团组织。
另一方面,随着印度、西域僧人的纷纷来华,带动了中国内地僧人西行求法的热潮,在这一时期,西行求佛法者中最有名的是法显。他在后秦姚兴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渡流沙河,翻越葱岭,远赴印度。前后经过15年,游历近30国,后经狮子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泛海归国,带回大小乘三藏中的基本要籍。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经过了四五百年的传播之后,进入了宗派的形成和发展高潮。这些佛教宗派有各自独特的教义、教规,及传法世系等。如天台宗、三阶教、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和禅宗。隋唐佛教宗派的出现,使佛教的中国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尤其是慧能禅宗的创立,标志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许抗生先生认为:唐代中后期的禅宗,是隋唐佛教宗派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它融会了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精神,将佛学中国化进程推至顶峰。既融会了大乘空、有两宗的佛教思想,又融合了中国儒家的人性论、道家的直觉主义思想,乃至采取了中国传统哲学崇尚简易的思想方式等等。”[13]13张岂之也指出:“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同印度佛教相比,是突出了个体意识,把对佛的信仰移植到人们的心性之中,借以说明人的本质就是自我的发现和个性的发展。这种重视人的主体思想,正反映了儒家学说的精髓,因为儒学的思想实质是‘人学’。因此,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重视人还是重视佛,从佛向人的转移,这就是佛教中国化成熟的标志。”[14]121
随着新儒学和道教的形成,佛教传入中国,中华民族的三大思想信仰,或者说三大主体宗教均交融于汉代,随着汉民族的形成而形成,说明这三大宗教最初总体上是属于汉民族的民族宗教范畴的。
五、地方民族宗教的形成、融合及其与主流宗教的关系
在中华民族的基层民族中,汉民族形成最早,其他民族都是在以后的历史中逐步形成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十世纪以后,即宋元明清时期逐渐陆续形成的。[15]510而这些民族的民族宗教也是伴随着该民族实体的形成而逐渐形成的。从理论上来说,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宗教,但随着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的民族宗教开始与其他民族宗教合流,有的宗教由民族宗教发展为超民族宗教。由于大量的地方民族宗教文化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因此,本文在此仅对几种有代表性的民族宗教进行介绍。
萨满教:萨满教主要存在于我国北方。一般认为,萨满教起于原始渔猎时代,为我国北方古代各民族,如满、锡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塔尔、朝鲜等族所信奉。据历史记载,在十二世纪中叶,南宋徐梦莘所撰《三朝北盟会编》中己开始用“珊蛮”一词,记述女真人信奉的萨满教。说明萨满教作为一种原生性宗教,是属于我国古老民族女真族在十二世纪左右所创立的,而女真民族也恰是形成于12世纪,以完颜阿骨打建立大金帝国作为其标志,这正符合民族宗教学形成的一般规律。至于后来发展为我国北方其他许多民族所信奉,甚至为整个亚、欧两洲北部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各族人民所信仰的宗教。说明该宗教已由民族宗教发展为跨民族性宗教,或者说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
梅山教:梅山教作为一种原生性宗教,是由瑶族人民所创立的,后因民族文化融合和交流,发展为我国广大西南少数民族,如瑶族、壮族、苗族、土家族、仫佬族、仡佬族、毛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等族群所信奉的融合型民族宗教,或者叫做跨民族性宗教。据现有资料证明,梅山教起源于原始渔猎时代,唐末宋初,发展形成为一种民族宗教,启教教主叫张五郎,唐代末年人。但唐末形成的梅山教还不是一种完全成熟的宗教,它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宗教的面貌,只有到了两宋以后甚至元末明初时期,因江西道教徒移民大量迁往湖南等地,梅山教深受道教的教理教义影响,道教的大量神祗进入梅山教的祭坛,梅山教进而发展演变为一种跨民族性宗教,为西南地区广大少数民族,甚至一部分汉族所信奉。
东巴教:东巴教是纳西族人在纳西族古老原始宗教基础上吸纳借鉴藏族本教一些仪轨而创立形成的。东巴经典是《圣祖丁巴什罗传》。据传,纳西族是氐羌人南迁中形成的民族。东巴教的形成时间有唐宋、宋代、宋末元初等几种说法。但根据民族宗教学理论,作为一种民族宗教不会早于其民族的形成,同时,比较成熟的宗教一般是受到外来成熟宗教影响而形成的。东巴教应该形成于宋末元初时期。*杨福泉在《东巴教通论》中提到宋代,纳西土酋牟保阿琮(麦宗)创制了“本方文字”,而13世纪中叶,纳西地区各部落开始正式纳入云南省的行政范围,纳西族正式完成民族统一,统一的民族需要统一的精神信仰,所以我们认为,东巴教应该形成于这段时期。(杨福泉:《东巴教通论》,中华书局,2012年,第25—28页。)
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形成既有内地佛教的影响,又有印度佛教的影响。在唐王朝的7世纪中叶,汉藏交好,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都带去了佛像、佛经。松赞干布在两位公主影响下皈依佛教,建大昭寺和小昭寺。8世纪中叶开始,印度佛教开始传入西藏地区,到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客观地说,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中原佛教、密宗、本教多种宗教文化融合的产物。
彝族人民崇奉的毕摩教也是在本土宗教的基础上吸收儒、佛、道主流宗教以及受到明清时代的移民潮和“改土归流”政策的影响下逐步发展融合而成的。毕摩教大约萌发于唐宋及以前,但全面成熟可能晚至清代初年。
以上提到的这些地方民族宗教发展到唐宋以后,随着基层民族的陆续形成和民族文化融合步伐的加快,开始呈现出加速融合的趋势,在明清时期表现更为明显,这是因为明清两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集中的西南地区施行“改土归流”政策和军屯、民屯措施。正如郭净所说:“元明清时期,我国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模式日益由南北向转变为东西向。内地文化凭借封建王朝开疆拓土的势头迅速涌入多民族聚居的云贵高原。汉族人民向西南地区的迁徙至明清两代达到高潮。”郭净列举数据指出,仅明代屯驻云南的汉军就达二十九万,到贵州军屯者也近二十万人。民屯的规模更为历代所罕见,仅1389年,明王朝就下令把江南二百五十余万人迁往云南。[16]而作为主流宗教的佛教和道教就是这样凭借政权的力量强势向中部尤其是西南部传播的。
在这种大规模的宗教文化交流融合中,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各民族宗教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这种融合带有地方文化圈性质,即局部文化圈中的成熟宗教影响较低级的不很成熟的宗教,如吐蕃本教对东巴教的影响就是一个著名例子。杨福泉提到,因为唐代吐蕃军事实力一度控制了麽些人滇西北、川西等地,吐蕃苯教对纳西族产生了较大影响。再加之由于西藏吐蕃统治者实施“扬佛灭本”的政策,迫使藏第本教祭司逃亡或被流放到滇西北、川西等地,形成了本教对纳西本土宗教的进一步影响。他以东巴教传统中的4个主要神祗的排列次序为例,第一个神是“盘”,为藏族之神,第二个神是“禅”(Saiq),是白族之神;第三个是“嘎”,是胜利之神(战神);第四个神是“吴”(Wuq),才是纳西族之神。他认为神的谱系是宗教形态的重要内容,从东巴教的神谱体系中可看出吐蕃本教对东巴教的影响深刻。[17]再就是,梅山教与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宗教的关系。梅山教原本是瑶族人民创立的一种民族宗教,西南其他许多少数民族本来都有各自信奉的原始宗教,但由于梅山教的迅猛发展,逐渐影响了其他民族宗教的发展走向,有许多宗教的原始发生地逐渐发展成为梅山教的亚文化区域,到元明清时期,梅山教逐渐发展为我国西南地区绝大部分民族,即瑶族、壮族、苗族、土家族、仫佬族、仡佬族、毛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等族群所信奉的一种跨民族性宗教,这些民族的原来信奉的本民族宗教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第二种情况是宗教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即大部分民族宗教呈现主流宗教化趋向,即各地方民族宗教受到佛教和道教侵染影响,各少数民族领袖纷纷接受佛教和道教信仰。主要表现为,北方宗教被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所侵染。这是因为元代以后,统治者重视藏传佛教,蒙古族、满族等统治民族纷纷信奉藏传佛教,从而使北方的萨满教深受影响。色音在《试论萨满教与佛教的交融复合》一文中提到:“萨满巫俗与佛教习俗的交融复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萨满巫俗为主的复合,另一种是萨满巫俗退居次要地位的复合。”又说:“以达斡尔族萨满巫俗为例,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的传入,达斡尔族传统的萨满巫俗中渗透了不少喇嘛教的因素。以前祭天祭火等都是由雅德根(即萨满)来主持,到了后来有时也请喇嘛念经和祭火神。”[18]而南方各民族宗教即受到佛教和道教两种主流宗教的影响,如南方的梅山教、东巴教、毕摩教都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受道教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民族宗教与道教均是中华民族的本土宗教,有着共同的源头,有其相通的地方。所以,在一些汉人移民比较多的地区,这些民族宗教甚至呈现道教化趋向。在南方最具有影响,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梅山教在受道教影响后,其原启教教主反而被安排在较低的下坛位置,而高坐上坛的教主却是太上老君,而且大量的道教神祗进入了梅山教的祭坛,成为梅山教的神祗,故有些研究者便将这些梅山教称作道教的支派。[19]
其次是彝族的原始道教——毕摩教也深受道教影响。杨甫旺认为:道教在元、明、清以后对彝族原始宗教的渗透和影响很大,其表现,一是彝族的宗教节日更加丰富多彩,再就是反映在昆明地区的彝族撒梅人崇奉的西波教上。认为西波教是在彝族原始宗教的基础上融合了道教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最明显的特征是西波也像梅山教一样,尊太上老君为最高神祗。其下还有元始天尊、雷部总管天君、六十甲子本命星官、三十六神等道教神灵。[20]再就是,纳西族的东巴教同样深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纳西族居住的丽江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各民族交往加强,原始色彩浓郁的东巴教受到了藏传佛教、中原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的影响。在元、明两代,尊奉佛教的木氏家族成为丽江的统治者之后,建造了各种宗教寺庙,在寺庙墙壁上绘制了各种宗教故事与神像。如藏传佛教的明王、大黑天,中原佛教的观音、十八罗汉,道教的天、地、水三官和诸天帝释等。杨福泉在《佛道教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一文中提到,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道教与东巴教结合在一起对纳西族社会产生混融性的影响。多种宗教信仰在民间流行,祭司东巴、巫师桑尼、和尚、喇嘛、道士各行其道,在民间形成混融性的影响。木氏土司也兼信多种宗教,家中有东巴,举行多种东巴教仪式,但也请和尚、喇嘛、道士布道作法。杨福泉认为,佛教、道教的文化因素渗入东巴教之中,对纳西族产生混融性影响最典型的表现是表现在东巴教的丧葬仪式上,即体现为生命观的系列东巴经《神路图》和著名的长幅布卷画《神路图》,这种《神路图》所体现的生命历程观与回归祖地的传统观念杂糅在一起,呈现纳西族本土生命观与外来生命观交融并存的多元格局。如《神路图》中所反映的鬼界和惩罚罪人与汉族道教的十殿阎王和佛教的十八层地狱说有相似之处。[21]
还有第三种融合趋势也是不可忽视的,即汉民族迁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开始接受少数民族的宗教。从中国古代宗教文化发展的历史考察,汉民族的宗教信仰是道教、佛教;而从宗教的原发性来看,其他民族宗教是其他少数民族创立的宗教,不属于汉民族所有,但唐宋以后,主要是南方汉民族地区大量汉人也信仰其他民族宗教,最典型的是梅山教,不但湖南、湖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的少数民族信奉,这些地区的汉族人民同样也信奉这一宗教。正如著名的民俗学者、梅山文化的研究者马少侨先生说:“开梅山后外地汉人不断地涌入梅山地区,接受了当地土人的宗教——梅山教。千余年来,梅山教实际上左右了几乎整个湖南各族人民的思想意识。在人们的宗教信仰中,不仅超出了外来佛教、基督教,而且也超过了土生土长的道教。”[22]147
以上这些宗教文化融合的特点体现了一种地区性的文化融合和统一。文化融合具有这样一种规律性特征:任何文化融合都以若干文化圈的形式出现,初始时期,呈现无数个文化圈,尽管这些文化圈有大有小,但在这些个文化圈中,总有一些处于核心的主流地位的文化,他们在文化融合中起主导作用,其他文化即处于边缘地位,任何文化大融合的完成,首先呈现局部地区文化圈融合,即只有在各局部地区的文化融合完成之后,才会有更大更高级规模的文化融合的出现,中华民族的宗教文化融合充分体现了这一规律。
六、宋元以降民间宗教形成的主要特征
所谓民间宗教,是针对上层精英信仰系统而来的。它与上层正统宗教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马西沙、韩秉方认为,民间宗教是下层民众及其文化、信仰、风俗、风尚孕育而成的宗教。向上经过上层精英阶层的精致化进而发展而成正统宗教,而正统宗教在上层失势流传于民间又可形成民间宗教。[23]由于中国古代社会隋唐以期,属于贵族社会,佛教和道教在经过其形成、向上层传播以及理论化的一系列过程,整体上呈现贵族精英化特征,其传播主要在精英间进行,但两宋以后,整个社会加速它的世俗化进程,宗教也进入世俗化和平民化阶段,即不再以精英化的理论创新为主,而是以物质化、功利化为主要手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间宗教。也就是说,民间宗教的真正兴起是在宋元以后。这恰恰是儒释道在上层完成其融合,形成了宋代新儒教之后的产物。佛教、道教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发展,到隋唐时期达到其鼎盛阶段。道教和佛教一度压倒儒学成为专制社会所崇奉的主流宗教,但随着新儒教的复兴,开始取代佛学和道学的部分宗教功能,佛学和道学在统治上层的地位开始下降,转而走向民间。民间宗教的兴起,是宋元以后宗教文化的一个新动向,佛教道教的民间化,也就是佛教中国化,道教世俗化的过程。
我们说,民间宗教与上层正统宗教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有时候甚至是上层宗教在下层社会、民间社会的一种倒影,一种折射。如果我们说,在上层社会,对于宋明理学三教合一的宗教化功能的认识还有争议的话,或者说,孔子还未被全面彻底神化的话,那么宋元以降民间宗教的儒释道合一特征就十分明显。在儒释道共尊的文化中,儒学明显已被当成了一种宗教,而且是超过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孔子已完全成为一个宗教领袖。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提到的民间宗教大多是三教合一的。明朝的成化至正德年间,在北直隶密云卫酝酿而成的最大的一支民间宗教——罗教,开始叫无为教,就是主张三教合一的,创始人为罗梦鸿,其教义实质上是一种佛、道、儒三教合成或杂糅的产物,而无极圣祖也是融会了道、佛、儒三教有关创世说塑造出来的新神。[23]当然最具有典型性的是明代中叶,在福建莆田地区兴起的三一教,教主林兆恩是一个贯通儒、释、道的大学问家。马西沙认为,林兆恩三教合一的本质是王阳明的新学与佛道两教教义的混合物。[23]而有的民间宗教直接引孔子为其祖师,如康熙年间创立于山东单县的八卦教就直接托孔夫子为这个教门传授丹法的开山祖师,其宝卷中就有“孔子一点性居中,口传人性实真正。君子要得修性理,执得曲阜问圣公……孔夫子,下天宫,时时的,传理性”[23]748。
有些民间宗教在神祗崇拜上不一定有儒、释、道三家的师祖,但在具体教理教义上却是典型的儒、佛、道尤其是儒教的道德说教。如创立于明代末年,发展漫延于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弘阳教就非常典型。马西沙说:“在弘阳教的宝卷中,一再宣扬的伦理道德,几乎全是从儒、佛、道三教经书中撷取而来的内容。如推崇三纲五常,赞颂为臣忠、为子孝、兄弟悌、守妇道。遵守三皈五戒,防止三毒十恶,提倡禁欲等。”[23]388再如道光年间,兴起于江西大兴县的长生教、云南大理府太和县的大乘教和江西寻邬县的真空教的教义都是援引儒、佛、道三经典,糅合为其教义而成。马西沙指出:“明清时代,不只一个教门从孔孟那里寻找‘穷理尽性’的理论根据。在那些宗教家的眼中,孔孟等圣贤才是内丹家真正创始人和理论的缔造者。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品原因,是受了两宋以后理学的影响,理学家从禅、道处讨功夫,儒道两家紧密的结合,无形从中启迪了各类民间教派,于是从四书五经中寻章摘句修炼内丹的理论根据,把孔、孟奉为本教门教主成为一种风习。”[23]748
而除开民间宗教,在民间祭祀和民间风俗方面,三教合一的情况更为突出。我们在湘西南梅山教的信仰地区进行考察过程中,发现许多普通百姓的神龛上,正中间或是“天地君亲师之神位”,或是本族姓的列祖列宗,即“某某氏历代考妣之神位”,右边大都写着儒释道三教共尊,左边即为当地的民间神灵,如马法旺、陈法旺等。*马法旺和陈法旺都是梅山教的师公,湘西南地区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普遍信仰梅山教。而在民间信仰的庙宇中,也往往是孔子、老子、释伽牟尼共尊。尤其是在一些殡葬仪式中,往往是既有和尚,又有道士,师公,及儒学人士的共同参与。湘西南农村流行着儒、释、道三教,儒教为大的说法。我们访问过一些民间法师,他们都说,在一些民俗活动尤其是丧事活动中,往往涉及儒、释、道的职责分工,即凡属涉及需要动笔写的工作,如写祭文,念祭文等,以及平时的上祭、写家仙、上神龛,敬祖宗等均属于儒教的职责,在农村,甚至有一些被称为儒教的世家,而开路,即送亡灵回祖屋,属于法师的职责,念经超度等又是属于和尚,即佛教的范畴。再如杨福泉提到,在云南丽江纳西族,民间城乡的业余洞经会的演奏活动中,既有文人,也有道士和佛教徒参加;并且可以同场挂孔子、释伽牟尼和三清的神像,并陈佛道教的经书,并行不悖。[21]再就是曾广泛盛行于贵州、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广西、云南等省(区、市)的汉、苗、土家、布依、侗、毛难、仡佬等民族中的三元和会,更是一种典型的儒释道合一的活动。顾朴光在《三元和会与傩堂戏》一文中提到德江县土家族“三元和会”的民俗资料,其中的“上元和会”就是写孔子、老子、释伽之事。先叙述儒道释三教教主的出生,其唱词有:“天皇翻山释迦佛,地皇翻山李老君。人皇翻山孔夫子,三圣翻山三教生。周初元年生下佛,地皇二年生老君。春秋年间生孔子,流传三教到如今。灵鹫山前生下佛,青羊山洞生老君,尼丘山前生孔子,道行东鲁不非轻。磨氏夫人生下佛,伏宫皇后生老君。颜氏夫人生孔子,流传三教到如今。”在叙述了他们的出生之后,接着叙述有关他们三人的神话传说,其中有关孔子的传说最具有创造性。手抄本写他父母亲七十岁尚未得子,来到尼丘山求告神灵,上天派儒玉下凡投胎孔门。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担心自己死后儿子无靠,将儿子丢在深山之中。孔子的母亲颜氏夫人心中不忍,七天之后前往山中看视,只见孩子正在石上酣睡:“少时白猿来喂乳,凤凰打花盖儿身。恶虎与他来伴宿,亲身儿男是贵人。颜氏将儿抱回转,东邻西舍抚成人。”顾朴光先生认为,与上层精英社会的经典文本中的叙述相比,“上元和会”中上天派儒玉下凡投胎孔门的描写,就更显得弥足珍贵。[24]同时也说明,在民间社会,儒与佛、道一样成为了宗教,孔子已是一个宗教教主,儒、释、道三教已全面合流。而民间宗教及民间信仰这种三教合一现象的出现,又恰恰是宋代以后上层社会新儒教形成在民间社会的反映。几乎所有无论是研究民间宗教还是研究民俗宗教文化的学者都是如此认为的。除上引马西沙分析民间宗教的三教合一现象是受到宋明理学的三教相融的直接影响外,顾朴光先生在叙述了“三元和会”中这种三教合一的现象之后,分析其原因时也认为,宋代以后,二程、朱熹等以传统儒教思想为主体,兼采佛教、道教中的某些神学观点和方式方法,建立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理学,从此儒、道、释三教开始合流,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用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精神支柱,并认为民间这种三教合流现象是受到上层三教合流,即理学思想影响的一种反映。[24]
七、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发展路径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形成于鸦片战争时期,而自在的民族实体即是在宋元明清以后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宗教,即“宗法性传统宗教”,尽管酝酿于原始宗教时代,形成于夏商周三代,时间延续数千年,但其发展演变还是伴随着民族融合的逐步加深和扩大而走向完善和成熟的,遵循着民族宗教的一般发展规律。
“敬天法祖”的基本内容已酝酿于原始宗教中,进入阶级社会后,中国古代宗法礼制的发展总趋势是从封闭走向开放。具体来说,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从上层精英宗法制向平民宗法制发展,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夏商周三代,表现为王权宗法制的典型特征。夏商两代已有系统的宗法制自不待言,但未建立起稳固的宗子继承制,到周代,宗法制才全面完善起来。这一阶段的宗法制是典型的王权宗法制,其宗法礼制只适合于王室宗盟成员,且有严格的等级分隔,只有天子可以享有祭祀天地祖先等各项权利,诸侯、卿大夫和士祭祀的权利和规模成等差级递减,平民没有祭祀权利。第二阶段的宗法制开始于魏晋,延续到隋唐,是一种贵族官僚宗法体制,即只有家族中世代有一定职别的官员才能行使这种宗法礼制,才能续修家谱、族谱,才能祭祀天地和祖先。平民宗法制兴起于宋代,全面繁盛于明清时期,属于宗法制的第三阶段,所有社会成员被纳入了宗法体系之中。宗法制之所以到宋代以后可以普及普通民众,是因为宋代理学家将宗法礼制的复兴作为重建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以此来加强乡村建设,重拾人心。张载是最早提出重建宗法制度设想的。他在《宗法篇》中开篇就提出了立宗法的目的:“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子法坏,则人不自知来处。”
另一个发展趋向是由华夏—汉民族向四周民族转移扩张,这又与我国古代的移民有关。我国古代的人口迁徙,在三代及其以前,主要呈现自西向东流动,秦汉以后出现由北向南迁徙,宋代以后,尤其是元明清时期又由东、东南向中部、西南方向迁徙。明清两代统治者对西南地区所施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以及军屯、民屯措施,使民族融合大大加快,作为国家宗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中原向全国各地,尤其是中部和西南部传播,极大地影响和改造了中部和西南地区的地方性民族宗教。当然,各地区的本土宗教也大都是从中原原始部落宗教演变发展而来的,带有某些共同元素,但地方性民族宗教极具原始性,而国家主体宗教严谨的祭祀仪式,丰富的礼乐制度,完善的宗法体系对其具有极大吸引力和影响力。
到明清时代,中国民间的家祭体系全面建立,民间几乎每家每户都建有神龛,神龛的主体内容是“天地君亲师”。[25]民间家祭体系的普及及其神龛主体内容的确立说明“宗法性传统宗教”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全民信奉的正宗大教,也说明这一主体宗教是伴随着中华民族这个高级民族实体的形成而形成的。16世纪以后,天主教等西洋宗教传入我国,与中华传统信仰发生的最大冲突就是“敬天祭祖”问题。但反过来,这些宗教也开始接受中国“敬天祭祖”的宗教仪式。如利玛窦执掌中国教务时,就结合中国实际,十分明智地允许中国教徒祭天、祭祖和拜孔等仪式,从而使其传教活动能够顺利展开。[26]983尽管后来龙华民继掌教务后,严禁教徒尊孔祭祖,双方矛盾加深,最终导致南京教案的发生。但至少说明,“敬天祭祖”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不但可以为佛教徒所接受,同时也是可以为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徒所接纳的,否则就无法在中国顺利传教。这就充分说明,到明清时期,“宗法性传统宗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全民宗教,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已全面形成。
八、结语
经济学家张维迎有一篇文章,叫《理念的力量》,其中最为核心的一句话是:“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事物,都是由观念支配的。”[27]而观念便是信仰,宗教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信仰。而前文所引牟钟鉴先生说:“宗教处于民族文化的核心或深层位置,成为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宗教与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宗教问题事关族群团结、社会安定。而当今世界信教人数已占到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28]我国信仰宗教人数也超过一亿,如果将关公信仰、妈祖信仰等所有民间信仰者全都计算在内,那么其人数将远远超过这一数目。
而当今世界矛盾重重,许多地区极不安定,战火连绵,民不聊生,人民连最基本的生存环境都不能保证。正如李克强总理在第19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时所说:“当前,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乏力,恐怖主义、难民问题和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全球化进程和信心受挫,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增无减。”[29]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多与民族问题和族群冲突有关,而民族问题、族群冲突又与宗教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反观我们中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发展,国力蒸蒸日上,所有这一切,一定程度上与我国宗教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有重大关系,这就充分说明在长期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这种宗教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当前,我们必须加强对中华民族宗教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整个华人世界凝聚团结的巨大精神力量,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1]刘道超.论我国民间信仰的多元一体化格局[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9,30(4):7-15.
[2]张践.我国民族宗教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N].中国民族报,2010-3-9.
[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6(2):1-19.
[4]牟钟鉴.民族宗教学的创立[J].世界宗教文化,2010,(6):1-7.
[5]金泽.宗教与民族的互动关系[EB/OL].(2012-9-24)[2017-10-21].http://iwr.cssn.cn/zjxllyjs/lw/200912/t20091229_3113322.shtml.
[6]牟钟鉴.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J].世界宗教研究,1990,(1):
[7]韦昭.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姜生.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伦理论稿[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9]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0]姜生.论道教的成因[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3):106-111.
[11]胡克森.论原始道教的两大社会源流[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3):91-97.
[12]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3]许抗生.佛教的中国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14]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15]胡克森.融合——春秋至秦汉时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文化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6]郭净.试论傩仪的历史演变[J].思想战线,1989,15(1):74-80.
[17]杨福泉.论唐代吐蕃本教对东巴教的影响[M].思想战线,2002,28(2):53-57.
[18]色音.试论萨满教与佛教的交融复合,“佛教导航·五明研究·佛学杂论”,2009-12-25.
[19]胡起望.论瑶传道教[M].云南社会科学,1994,(1):61-69.
[20]杨甫旺,单江秀.论道教与彝族原始宗教的互动与融合[J].宗教研究,2010(1):115-121.
[21]杨福泉.佛道教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J].云南社会科学.1996,(6):68-76.
[22]马少侨.楚辞新证[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
[23]马西沙.中国民间宗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4]顾朴光.《三元和会》与傩堂戏[J].贵州文史丛刊,1987,(2):12-18.
[25]徐梓.天地君亲师源流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99-106.
[26]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27]张维迎.理念的力量[J].经济观察报,2014-05-23.
[28]牟钟鉴.重新认识中国宗教在文化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J].中国宗教.2014,(1):26-30.
[29]李克强在第19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EB/OL].(2016-09-08)[2017-10-21].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08/c_11195285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