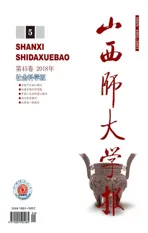欧阳修与“韩柳”“韩李”并称
2018-04-04刘城
刘 城
(广西教育学院 文学院,南宁 530023)
自晚唐杜牧诗举“李杜”、文称“韩柳”以来,文章史上的“韩柳”并称,从唐至今,一直是文学批评的主流。
韩愈、柳宗元的文章继承、改造前人之文,开启了古文写作的无数法门,确立了对后世文章的典范意义,明人陆符《四六法海序》赞曰:
先秦两汉之文,至六朝而一变;六朝骈俪偶之作,至韩柳而再变。一变而秦汉之体更,再变而秦汉之法出。故唐以后称大家者,无不以韩、柳为宗。[1]838
清代储欣在《唐宋八大家全集录》总序云:
韩柳者,文章之宗,尤八家之主也。韩柳且疏,他复何校哉?”[2]237
他指出韩、柳作为唐宋八大家中唐代仅有的两位代表,泽润宋六家又极深。韩柳文作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上两座并峙之高峰,世人多以二者并称,储欣也曾于《河东先生全集》序云:
天未丧文,不可无韩,既有韩,不可无柳,论之一定者也。[2]501
可见“韩柳”并称观念的根深蒂固。
即便如此,并非所有人都赞同“韩柳”并称。奋力矫俗者,不乏其人,欧阳修即是代表。
一
欧阳修作为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第一人,世人常把其与唐代的韩愈和柳宗元相比较。
欧阳修对于韩愈文章的学习与道统的继承,让弟子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对其发出了“今之韩愈”之赞誉[3]316。把欧阳修视为宋代之韩愈,这种观点也并非苏轼所独有,南宋学者王十朋在《读苏文》云:
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4]前集卷十九
王十朋于此共同推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四人之文,文学史上的“韩柳欧苏”并称或始于此。但是,王十朋也在此文进一步阐述:“韩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与苏好奇而失之驳。”王十朋于四人中又细划为二——“韩欧”与“柳苏”,认为韩愈与欧阳修为文“一出于正”,所以“粹然”。这里的“正”,应指儒家之道,“一出于正”,指韩愈与欧阳修作文多从儒家之道出发,义旨合于儒家道义。由此可知,王十朋视欧阳修之文乃承续韩愈而作。虽然柳宗元和苏轼与韩、欧并驾,但由于柳、苏二人为文多杂入不同于儒学之“异端”学说,故“失之驳”,显得不淳正。稍后于王十朋的罗大经在其《鹤林玉露》中对此四人也表达过类似的比较:“欧似韩,苏似柳。”[5]卷十五故世又有“韩欧”之称。
在世人眼中,无论在思想还是在文学上,欧阳修与韩愈有太多相似性,更重要的是,“昌黎文垂三百年得庐陵而后大重于世”(邵长衡《邵青门文录》卷三),故人们论及欧阳修与韩、柳的联系时,几乎都会把欧阳修视为宋代的韩愈,而常强调其与柳宗元的不同。但平心而论,欧阳修对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多有肯定,并且接受其文艺思想,如他的“穷而后工”理论是对柳宗元“感激愤悱”论的接受;于文采的认识,两人也经历了大致相似的过程及持大致相同的观点;他接受了柳宗元“文以明道”的思想,提出了“知古明道”的主张;他对柳宗元的文学作品多有接受,如山水游记、表现重大现实题材的政论文等。*关于欧阳修对柳宗元文学的接受,可参看杨再喜《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10—121页。
遗憾的是,欧阳修于文有学柳之处,但其与柳宗元在思想上尤其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的差异,导致了他对柳宗元其人及其文又多发苛责之语。中唐时期,实际已形成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关系呈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位,佛教在理论水平领先于儒道,三教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等特点。面对儒家衰弱的状况,韩、柳等人开始寻求儒学的复兴之途。*关于唐代儒释道三教发展态势,可参看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1—17页。而在中晚唐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儒学要重铸以往“独尊”之势,首先要考虑如何应对佛教的挑战。在当时的儒学内部,存在两种不同途径:一个是以韩愈为代表的辟佛路径,一个是以柳宗元为代表的融佛路径。虽说二者殊途同归,但毫无疑问,在中晚唐那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佛教义理较为熟悉的柳宗元所主张的“统合儒释,宣涤凝滞”,以儒家来统合佛教的途径更符合当时三教发展的形势,其学说也比韩愈对于佛教较为流于表面的批判更胜一筹。*关于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可参看李伏清《柳宗元儒学思想研究—兼论中晚唐儒学复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第28—48页;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第198—202页。但韩愈以儒家道统来排斥佛老,通过激进排斥佛老而独尊儒学,在对佛道的批判过程中呼唤接续儒家周孔之道,使得“辟佛”成为复兴儒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理念与勇力,得到了北宋理学先驱的极大称扬。如“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是如同韩愈一般高举复兴儒学大旗而坚决排佛者。这一风气也影响到欧阳修。作为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领军人物,“欧阳修评论佛教的基调是批判的”,“排佛立场是终其一生的”[6]110,他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继承韩愈高举反佛大旗,但又比韩愈的简单粗暴的方式更具理论深度。其中最重要的主张就是“修其本以胜之”,即通过“修本”,完善及阐发儒家教义去对抗佛教义理,从思想根坻上击败佛教,让其“无所施用于吾民也”(《本论》上)。
这就不难理解在评价中唐倡导复古的两位重要引领者韩愈和柳宗元时,作为封建正统士大夫的欧阳修,出于恢复儒道传统的历史责任,对柳宗元的儒道观所表示出的强烈不满了。欧阳修在《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云:
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然退之于文章,每极称子厚者,岂以其名并显于世,不欲有所贬毁,以避争名之嫌,而其为道不同,虽不言,愿后世当自知欤?不然,退之以力排佛、老为己任,子厚不得无言也。[7]2276
又在《唐南岳弥陀和尚碑》云:
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7]2278
欧阳修于二文中所言“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与“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已明确道出文章史上韩柳并称已被世人所接受认可,但他还是对此颇为不满:一是反对当时已成定论的“韩柳”并称;另外就是彰显韩、柳二者于儒家之“道”的异趣,甚至不惜贬损柳宗元“真韩门之罪人”,出语可谓严苛。基于这种理念,欧阳修在其《苏氏文集序》中把“韩柳”并称改为“韩李”并举,把韩愈、李翱作为唐文“始复于古”的代表:
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7]614
并在《读李翱文》再次重申:“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7]1050据“道”论文,进而以“韩李”替代“韩柳”,足见欧阳修欲矫世俗定论的勇力。
实际上,宋人论著中所出现的“韩李”并称,几乎都源自欧阳修,可见欧阳修倡导“韩李”并称的推广之功及影响之巨。较具代表者如朱熹《朱子语类》云:
韩文公似只重皇甫湜,以墓志付之。李翱只令作行状,翱作得行状絮,但湜所作墓志又颠蹶。李翱却有些本领,如《复性书》有许多思量,欧阳公也只称韩李。[8]卷一三七
该书同卷又云:
浩曰:“唐时莫是李翱最识道理否?”曰:“也只是从佛中来。”浩曰:“渠有去佛斋文,辟佛甚坚。”曰:“只是粗迹,至说道理,却类佛。”问:“退之见得不甚分明。”曰:“他于大节目处又却不错,亦未易议。”浩云:“莫是说传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气象大抵大。又欧阳只说韩李,不曾说韩柳。”[8]卷一三七
学宗朱熹的黄震在《古今纪要》释“李翱”条也有类似之语:
欧公只说韩李,不说韩柳。[9]卷一三
朱熹及黄震在谈及欧阳修只说“韩李”之时,不忘附带强调欧阳修“不曾说韩柳”或“不说韩柳”。强调欧阳修倡导“韩李”并称,不仅见于宋代,也不时见于后世,尤其以清代居多。全祖望在《李习之论》中云:“欧公之于唐人并称韩李。”[10]卷三十七秦瀛《致陈硕士书》曰:“李翱张籍皆受文昌黎。籍之文少所见,翱所传不多而其文足媲于韩。是以欧阳公称唐文之善曰‘韩李’。”[11] 文集卷二孙治撰《林玉逵集序》云:“昔欧阳子论文人之难得,以为有唐一代至元和始有韩李之徒出,而宋至天圣方有穆修、梅圣俞为古文辞。甚矣!文人之难得如此。”[12]卷五陈鸿墀也在《全唐文纪事》中说:“欧公之于唐人并称‘韩李’而其慕习之也。”[13]卷三十六
另外,欧阳修对柳宗元于“道”之苛责,难免会在比较韩柳文时发偏颇之语。方苞在《答程夔州书》云:“是以北宋文家于唐多称韩李而不及柳氏也。凡为学佛者传记用佛氏语则不雅,子厚、子瞻皆以兹自瑕。”[14]文集卷六提到柳宗元和苏轼文中有涉佛教语而被视为有瑕疵者,故北宋文家多称“韩李”而不称“韩柳”,这恐怕多是受欧阳修的影响。宋人黄震即堪称因人废文之代表,他说:
专辟退之之辟佛、愚谓退之言仁义,而子厚异端;退之行忠直,而子厚邪党。尚不知愧而反操戈焉。子厚自以为智不遂,当矫名曰愚。吾见其真愚耳。[9]卷六十
痛斥柳宗元的异端思想及行事,并以此多责难柳文:
柳以文与韩并称,然韩文论事说理,一一明白透彻,无可指择者,所谓贯道之器非欤?柳之达于上听者,皆谀辞;致于公卿大臣者,皆罪谪后羞缩无聊之语;碑碣等作,亦老笔与俳语相半;间及经旨义理,则是非多谬于圣人。凡皆不根于道故也。惟纪志人物,以寄其嘲骂;模写山水,以舒其抑郁;则峻洁精奇,如明珠夜光,见辄夺目。此盖子厚放浪之久,自写胸臆,不事谀,不求哀,不关经义。又皆晩年之作,所谓大肆其力于文章者也。故愚于韩文无择,于柳不能无择焉。而非徒曰并称,然此犹以文论也。若以人品论,则欧阳子谓 “如夷夏之不同”矣。欧阳子论文,亦不屑称韩、柳,而称韩、李,李指李翱云。[9]卷六十一
黄震赞赏韩愈之文乃“贯道之器”,深蕴儒家之义,而批评柳宗元之奏章书疏之类皆“谀辞”,致公卿大臣之文多“无聊之语”,碑志亦多杂骈语丽辞,涉经旨义理之文却多与儒家先圣义旨不合,并斥责柳宗元这些文章所犯之病,都是“不根于道”,不以儒家之道为作文之根柢所致。黄震最后还引欧阳修之语以证明自己的判断,颇具代表性。
以儒学之异端视柳宗元,进而批评柳文,欧阳修可谓开其风气。欧阳修的这种态度,让今人孙昌武先生也不禁感叹道:“从儒道的大本大原上攻击柳宗元,欧阳修是出言最苛的一个人。”[15]420
二
韩愈、李翱并称,唐代已有,最早出于刘禹锡之文,其《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云:
一旦习之悄然谓蕃曰:“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16]1225
刘禹锡就于此文透露出韩愈与李翱当时为文坛盟主的时誉。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也称:“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称赏韩李二人力图复兴儒学之举。[17]卷一六○
相比而言,韩愈和柳宗元并称,虽未见于二人生前,但在二人逝世之后多为世人所道。晚唐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云:
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18]81
杜牧于此首次把韩愈与柳宗元并称,并同时视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分别为唐代诗歌、文章之典范。唐及五代的“韩柳”并称之例几乎是以韩、柳文作为论文之典范,兹列如下:
外王父左冯翊太守讳敬之,韩吏部、柳柳州皆伏比贾马。文章气高,面诃卿相豪盛之非,盖不得为达官。(《唐乡贡进士孙备夫人于氏墓志铭》)[19]391
杨公(杨敬之)朝廷旧德,为文有凌轹韩柳意。[20]卷上
(柳仲郢)撰《尚书二十四司箴》,韩愈、柳宗元深赏之。[17]卷一六五
来鹄,豫章人也,师韩柳为文。[21]113
刘轲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文章与韩柳齐名。[21]120
这些例子多在论述他人文章时独标韩、柳之文,无疑是把其当成评判的标杆加以比较论述。这也表明韩愈、柳宗元逝世后不久,人们已开始关注二人的文章,且有意识地把韩柳二者加以整合、并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并称,几乎专指文章,这也是韩柳文研究史上最初颇具意义的发明。
北宋初期之文坛多袭五代淫靡衰弱之风,有识之士多起而矫之,积极寻求创作上的典范。而韩柳文由于文与道的完美融合及典范意义,逐渐走进了宋人的视野,如姚铉编著志在“纂唐贤文章之英粹者”[22] 自序的《唐文粹》就鲜明体现了北宋初期人们对于复古文风的追求及实践。该书实际上和宋代诗文革新思潮相互呼应,力图为新思潮提供可资参考、摹仿的经典范本,其中在散文的收录上,韩柳文的数量是最多的。而穆修更是收集韩柳文并加以校订出版。
文学上的典范性使得韩柳在北宋时期多被关注,二者的并称成为了当时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关于宋代的韩柳并称,可参看陈晓芬《宋人以“韩柳”并举所反映的文学思想》,《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第65—72页。不仅如此,宋人还明确把韩柳之文与扶助儒学教义、阐发圣人之道联系起来。田锡在《贻陈季和书》云:
世称韩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词,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故识者观文于韩柳,则警心于邪僻,抑末扶本,跻人于大道可知矣。[23]卷二
王禹偁于《送孙何序》赞孙何之文:
皆师戴六经,排斥百氏,落落然真韩柳之徒也。[24]卷十九
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亦云: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雄歌诗,道未极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寔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徳》《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能崒然耸唐徳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非先生之文则谁与?[25]
由此看来,韩柳文的经典性使二者得以并称,且已广泛获得宋人的肯定赞誉,此在欧阳修之前“盖流俗之相传也”,这一点即使是欧阳修也不得不承认。但在面对佛教思想对儒家学说的冲击越来越强,导致儒学陷入危机的现状,以“专治孔氏,黜异端”以易风俗为务的欧阳修,当然会对柳宗元深习佛学、亲近僧侣乃至欲“统合儒释”的做法表示不满甚至是排斥。面对已定型的韩柳文并称,欧阳修却还要起而矫之,非得以坚决捍卫儒学正统的李翱换掉柳宗元,以“韩李”替代“韩柳”,于此可窥见欧阳修对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坚守与执着。
三
清人平步青《霞外捃屑》云:
《柳亭诗话》卷十六:欧阳永叔欲以卫公文与昌黎并称曰韩、李 。按文忠此语,见《内制集序》,以卫公《一品集》,多代言之作故也 。唐人本称韩、李,不称韩、柳,李谓习之也。《苏氏文集序》云韩、李之徒出,指习之 。苏洵《上欧阳公书》,韩子后亦举习之 。黎洲《明文海序》,则称韩、杜,杜谓牧之。鄙意李文公源出昌黎,卫公、牧之亦仅得一体,皆不若柳州也。储在陆谓千古足当韩豪者,惟柳州一人。信为知言。今人遂无有复理庐陵、明允、黎洲旧说矣。[26]卷七
这段话指出韩愈在文章方面与他人并称的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韩李”并称,此“李”指李德裕。平步青称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云欧阳修以李德裕与韩愈并称“韩李”,并说此语出自欧阳修的《内制集序》:“按文忠此语,见《内制集序》,以卫公《一品集》,多代言之作故也。”韩愈文集与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中相似之处即在于多官府文翰,故平步青认为宋长白说韩愈与李德裕可并称“韩李”应是据此。但考今人李逸安校点的《欧阳修全集》[7]597—598及洪本健的《欧阳修诗文集校笺》[27]1108—1109所收欧阳修之《内制集序》,毫无此意,未见提及“韩李”之称,更不见李德裕之名。不知平步青因何谓此?据目前笔者所查的资料来看,“韩李”之“李”指李德裕,仅《柳亭诗话》一处。
第二种并称亦是“韩李”,但此“李”指的是“李翱”。
第三种是“韩杜”,此“杜”为晚唐杜牧。
对这三种并称之说,平步青并不以为然,其云:“鄙意李文公源出昌黎,卫公、牧之亦仅得一体,皆不若柳州也。储在陆谓千古足当韩豪者,惟柳州一人。信为知言。今人遂无有复理庐陵、明允、黎洲旧说矣。”他认为李翱为文实乃师承韩愈,而李德裕与杜牧之文也仅在某方面似韩愈,此三人并不能与韩愈相抗衡。故平步青十分赞成储欣之说,认同他的千古惟柳宗元“足当韩豪者”的看法,并指明“韩柳”并称广为世人所接受,而欧阳修、苏洵与黄宗羲之说渐为人所弃的事实。
平步青所言极是。韩愈分别与李德裕、杜牧的并称,偶尔见之,可予以忽略。韩愈与李翱之并称,虽在欧阳修的影响下数见于论著,但却并不是普遍现象。延及后世,人们亦多在论儒学时提及,与欧阳修同时的苏舜卿直言:“唐之文章称韩柳,翱文虽辞不迨韩,而理过于柳。”[28] 卷四明确指出文章称“韩柳”,但如以学术而言,称“韩李”则似更为妥帖。宋代王楙在《野客丛书》之“儒人不作释氏语”条说:“韩李二公盖卓然守是见者,元公所言未免狥乎。彼非真能尊吾道者,至当之语,仆于韩李则然。”[29] 卷二十二赞韩李二人对儒家圣人之道的坚守。清人蔡世远编《古文雅正》卷九评李翱《复性书》时云:“韩李并称。韩之外知道者,推李氏。”评李翱《祭韩文公文》云:“观宋儒渊源,亦足见韩李之心各有未虚处。”而在进行文章批评时以“韩李”并提的情况并不普遍。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曾在《题李习之集二则》中指出,正因为李翱文章多“斥异端,崇圣道,词义凛如,在唐人茅靡仙佛中可谓卓然不惑者。他文亦典实明健,一洗浮华”,所以“欧阳永叔至韩李并称而不及子厚,以其识也”。胡应麟在道出欧阳修因李翱之文多崇儒学而斥佛老并使之与韩愈并称“韩李”的事实后,笔锋一转,认为李翱的文章“率人所能至”,集中竟无可与柳宗元《梓人传》及《封建论》等篇相畴者,所以他最终感叹道:“唐惟柳差可配韩,而欧公去若是,盖一时之论道之语,非定评也。”[30] 卷一百五如何评价欧阳修的“韩柳”与“韩李”观,胡应麟之语应可视为一个较为公允的论断。
苏轼云欧阳修“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之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3]316。作为“天下翕然师尊之”的欧阳修,在“韩柳”“韩李”问题上坚持以儒家为本的执着,斥柳而扬李,见出他于北宋儒学遭受危机时欲拯儒学于既倒之坚定信念与魄力,以致“伊洛诸儒未出以前,其能以扶持正道为事,不杂异端者,只推韩李欧三君子”[13]三十六。世人把欧阳修与唐代的“韩李”相比,欧阳修自己也极力推崇“韩李”。但遗憾的是,虽然他以“韩李”替代“韩柳”之举偶获后人支持,但柳宗元于文章的成就非李翱所能比,“韩柳”并称一直都居文学批评之主流,直至今日更是不可撼动。由此可见,韩愈与柳宗元的思想与文章对后世的典范性使得并尊韩柳文的理念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可,“韩柳”并称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经典的文学观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