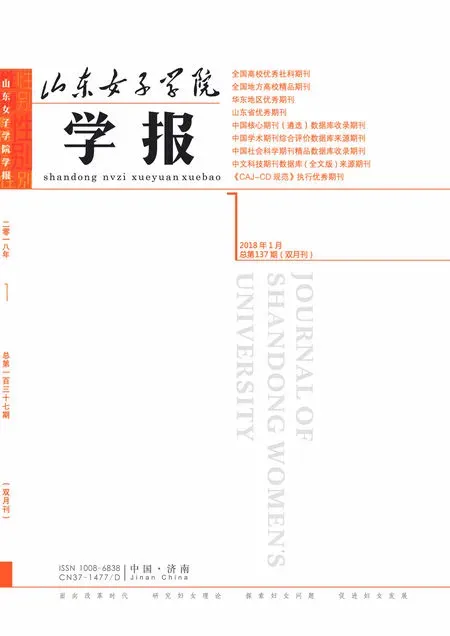元曲女性演员角色发微:以《青楼集》为例
2018-04-03贾名党
贾名党
(安徽农业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6)
·妇女史研究·
元曲女性演员角色发微:以《青楼集》为例
贾名党
(安徽农业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6)
元曲表演的商业性对女性演员的演艺水平提出了一定要求。从接受与传播视阈考察,元曲女性演员非常注重从达官墨客处获熏陶,于家人老师处汲营养;她们大多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湛的表演技能,并能从传播形式、方式与路径等多层面使元曲艺术得以承继和发展。
元曲;女性演员;角色
元代是我国戏曲的大繁荣时期,“曲并非开始于元,而是到了元时臻于极盛”[1]。作为一种包括歌、舞、乐等在内的综合艺术,元曲的发生及实现一般由剧作家、演员及观众等共同完成。演员是元曲表演的实践者,在艺术的生产和消费之间起着媒介的作用。
元代戏曲舞台活跃着大批演员,可谓群星璀璨,耀人眼目。夏庭芝的《青楼集》即是其时一部“记南北诸伶之姓氏”的典籍。该著作涉及女性演员120多人,其中表演杂剧的60余人,歌唱(散曲)的近30人,诸宫调约16人,另有南戏、说书及角技约10人。文本不仅较为客观地记录了她们的生活状况和表演技能,而且还载述着元曲演出及艺术传播的有关情况。然蠡测古代戏曲史,对剧曲作家或剧本的关注远多于对表演形式及演员的研究。本文拟以《青楼集》为例,基于接受和传播层面,探微元曲女性演员的角色特质,以期对元代戏曲研究有所裨益。
一
元曲存在的文字形式是剧本。其内容要想让普通观众接受,一般要搬上舞台进行表演,呈现出较强的商业性质,“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2]。这自然也就对演员的演艺水平提出了要求,因为“屡不中,则不往观焉”。《青楼集》记述的诸位女演员,生活或活跃在元代的不同时期,皆非常注重对前贤时达表演艺术的接受。
(一)达官墨客处获熏陶
元曲前期女演员如珠帘秀、司燕奴、南春宴、天然秀等,或通过在皇庭作表演,或注重与其时达官显宦或文人墨客的交往,而获取艺术及表演等多层面的熏染。
注重从帝王处获熏陶。元曲女演员多把为帝王表演视为难得机遇:“(忽必烈时,宫内团拜)席散后,有音乐家和梨园子弟,演剧以娱众宾。”[3]而元代一些帝王也乐于欣赏和提倡戏曲,如《青楼集》“玉莲儿”条载英宗对剧曲的喜爱:“尝得侍于英庙,由是名冠京师”;被称“郭二姐”的顺时秀在元顺帝时也多次被宣唤入宫表演。不难想象,这些女演员在皇庭的演出中扩大了视野,丰富了知识。
注重从名公士大夫处获启迪。《青楼集》中,元曲女演员与元遗山、鲜于伯机、杨立斋、阿鲁温、张子友、元文苑、李溉之、伯颜、严忠济、贾伯坚、全普庵拨里等名公士大夫皆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如张怡云“诸名公题诗殆遍”;珠帘秀“冯海粟待制亦赠以《鹧鸪天》”;曹娥秀“一日鲜于伯机开宴,座客皆名士,鲜于因事入内”;赵真真、杨玉娥“杨立斋见其讴张五牛、商正叔所编《双渐小卿》”;刘燕歌“齐参议还山东,刘赋《太常引》以饯”;顺时秀“平生与王元鼎密。……阿鲁温参政在中书,欲瞩意于郭”;小娥秀“张子友平章甚加爱赏,中朝名士赠以诗文盈轴焉”;喜春景“张子友平章以侧室置之”;聂檀香“东平严侯甚爱之”;宋六嫂“元遗山有《赠觱栗工张觜儿词》”;王金带“有谮之于伯颜太师,欲取入教坊承应”;周喜歌“鲜于困学、卫山斋、都廉使公及诸名公皆赠以词”;于四姐“名公士夫,皆以诗赠之。”她们或呈妙艺以佐清欢,或寄情词曲,或被赠诗以资赏,从中提升了自己的艺术修养。
注重从文人处获点染。元曲女演员也注重与文人的合作。“元曲的繁荣是由歌妓与文人共同创造的,发源于民间的曲体向文人层面的扩散,无论是在上层文化圈中兴盛,还是在下层文人间流连,都离不开歌妓与文人的社会交往。”[4]这些文人大多是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中有一定声誉的诗人、剧曲作家或理论家,如赵孟頫、姚燧、卢挚、倪瓒、刘时中、胡祗遹、白朴、乔吉、钟嗣成、冯子振、贯云石等。文本中,解语花“廉野云招卢疏斋、赵松雪饮于京城外万柳堂”;赛天香“无锡倪元镇……亦甚爱之”;张怡云“姚牧庵、阎静轩,每于其家小酌”;般般丑“时有刘廷信者……与马氏各相闻而未识”;珠帘秀“胡紫山宣慰尝以《沉醉东风》曲赠”;天然秀“尤为白仁甫、李溉之所爱赏”;李芝仪“乔梦符亦赠以诗词甚富”;王玉梅“钟继先有‘声似磐圆,身如磐槌’之诮”;金兽头“酸斋尝有‘老鹤啄’之诮。”她们通过与各类文人的交流而受其艺术文化的感染,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自己的演出水平。
(二)家人老师处汲营养
元代中后期,有关法律规定:“乐人只娶乐人者,……若娶乐人做媳妇呵,要了罪过,听离了者。”[5]女性演员学习表演知识和提升演出能力渠道狭窄。诸如赛帘秀、燕山秀、李娇儿、张奔儿、荆坚坚等女演员,不仅注意与达官骚客之往来,更注重从家族父母或祖父母、戏曲老师那里学习表演知识,提升自己的演出技艺。
首先,女儿向母亲学习,如天锡秀“女天生秀,稍不逮焉。后有工于是者赐恩深,谓之‘邦老赵家’。又有张心哥,亦驰名淮浙”;李真童“张奔儿之女也。十余岁,即名动江浙。色艺无比”;赵梅哥“其女鸾童,能传母之技”;赵真真“其女西夏秀,嫁江闰甫,亦得名淮浙间”等。其次,儿媳向婆婆学习,如孔千金“儿妇王心奇善花旦,杂剧尤妙”;周人爱“儿妇玉叶儿,文苑尝赠与‘南吕一枝花’曲”等。再次,妻子与丈夫间互相切磋,如帘前秀“末泥任国恩之妻,杂剧甚妙”;张奔儿“李牛子之妻也。姿容丰格,妙于一时,善花旦杂剧”;宋六嫂“与其夫合乐,妙入神品”等。最后,孙辈向祖辈学习,如张玉梅“刘子安母也。刘之妻,曰蛮婆儿,皆擅美当时。其女关关,……七八岁已得名湘湖间”;小玉梅“姓刘氏。独步江浙。其女匾匾,……杂剧能迭生按之……有女宝宝,……艺则不逮其母云”。
贤师出高徒,自古已然。以名师作号召,也是表演等领域相沿成习的艺术传统。除家传外,元曲演员也非常注重师承。如王奔儿“为教师以终”;赵偏惜“旦末双全。江淮间多师事之”;顾山山“后辈且蒙其指教,人多称赏之”;赛帘秀“朱帘秀之高弟”;燕山秀“朱帘秀之高弟。旦末双全,杂剧无比”;喜温柔“回回旦色米里哈,传授其妙”。其他如顺时秀的名弟子有宜时秀、金文石及陈氏等。此外,《青楼集》还有些记述虽未明言,然从字里行间亦可推知似有师承关系,如赐恩深、张心哥等与天锡秀的关连等。
二
由于元曲女性演员注重对显宦骚客及家辈贤师的学习,加之自身的努力学习和反复的艺术实践,她们在多方面表现出较好的素养。
(一)较高的文化水准
元曲女演员大多聪慧不凡,精通经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如刘廷信“天然聪慧,至于词章,信口成句”;般般丑“善词翰,达音律”;赵真真“亲文墨,通史鉴,教坊流辈,咸不逮焉”;张玉莲“文雅彬彬。南北令词,即席成赋”。
具体而言,她们博闻强记,如小春宴“勾栏中作场,常写其名目,贴于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选拣需索”;张玉莲“旧曲其音不传者,皆能寻腔依韵唱之”;李芝秀“赋性聪慧,记杂剧三百余段”;陈婆惜“在弦索中,能弹唱鞑靼曲者,南北一人而已”等。她们同时也能创作曲、词、诗。其中就谱曲言,如梁园秀创作的《小梁州》《红衫儿》《寨儿令》等乐府,“世所共唱之”等。写词方面,如刘婆惜续《清江引》:“青青子儿枝上结,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里滋味别,只为你酸留意儿难弃舍”;一分儿的《沉醉东风》:“‘红叶落火龙褪甲,青松枯怪蟒张牙’。可咏题,堪描画”等。作诗方面,如张怡云“能诗词”;梁园秀“喜亲文墨,作字楷媚,间吟小诗,亦佳”;刘燕歌更是在诗与曲上留有完整的作品。
(二)良好的品行操守
元曲女性演员多具有高尚的品格。一是坚守理想爱情。她们对于真爱的追求执着坚定,很少受到外界环境等干扰。如汪怜怜条:“克尽妇道,人无间言。数言,涅没。汪髡发为尼。公卿士夫多访之。汪汩其形,以绝众之狂念而终身焉。”王巧儿条:“陈云峤与之狎,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辈开喻曰:……王曰:‘巧儿一贱倡,蒙陈公厚眷得侍巾栉,虽死无憾’”。二是洁身自好,看重贞节。樊事真条:“京师名妓也,周仲宏参议嬖之。周归江南,樊饮饯于齐化门外。……樊以酒酬地而誓曰:‘妾若负君,当刳一目以谢君子。’……乃抽金蓖刺左目,血流遍地,周为之骇然,因欢好如初。”三是具有争取人权之抗争精神。元曲女演员中一部分原是妓女,故既要屈从于封建官府的应官身,又要受制于鸨儿,甚至还会面临一些文士的调笑和侮辱,然她们并未颓废沉沦,而是在全力追求本属于自己的幸福,宁为玉碎,显现出豪爽泼辣、放纵多情又富有斗争精神的品格。如刘婆惜“因在赣州宴会即兴作《清江引》曲,得全子仁激赏,纳为侧室。后兵兴,全死节;刘克守妇道,善终于家”;翠荷秀“姓李,石万户置之别馆。石没,李誓不他适,终日却扫,焚香诵经”;李真童“达天山检校浙江,相爱三年。秩满赴京,约明年相会。李遂为女道士,杜门谢客,……节行愈励云”等。她们或甘愿做与己年龄悬殊的侧室,或出家作尼姑道姑,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到做一个大写的“人”的自由,“我的人生我做主”,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三)精湛的表演技艺
元曲女演员大多是“色艺表表”者,有着很高的艺术表演水平。她们多数在演技上较为高超和精妙,有的更是身怀绝技。如米里哈“歌喉清宛,妙入神品”;赵真真“有绕梁之声”;赛帘秀“乃古今绝唱”;李定奴“歌喉宛转,善元曲”等。另有梁园秀为“当代称首”;张怡云“艺绝流辈”;喜春景、秦小莲“艺绝一时”,“后无继者”;时小童“合唱为一时之冠”;魏道道“自国初以来,无能继者”;金文石“其音律调清巧,无毫厘之差”等,实令人叹为观止。
相对而言,元前期女演员多是身兼多艺,表演水平精美。如赵偏惜、朱锦绣等“杂剧旦末双全”;顺时秀“杂剧为闺怨最高,驾头诸旦本亦得体”。其他如天然秀、珠帘秀等,除杂剧为当时“独步”外,花旦、驾头等“亦臻其妙”。元中后期女演员则是艺有专精,独领风骚,少有人能比。如孔千金、王心奇“善花旦”;平阳奴精于“绿林杂剧”;顾山山、荆坚坚等专工“花旦杂剧”;米里哈“专工贴旦杂剧”等。甚至是同工一种脚色而形成了不同的表演风格,如张奔儿和李娇儿同以花旦见称,而“时人目张奔儿为‘温柔旦’,李娇儿为‘风流旦’”。可以说,正是她们的艺超流辈、技压群雄,推动着元戏曲健康蓬勃发展。
三
一般认为,戏曲传播的主要途径有书坊刻印、文人间的相互赠答传阅和艺人们的传唱。而就元曲言,其传播渠道固然有剧本览读等,但由于其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更多的则表现为女演员们的口头传唱及在青楼歌馆、勾栏瓦肆或路歧道场处的表演。
(一)传播形式
元代有许多出类拔萃的优秀女演员活跃在戏曲舞台上。元曲多是通过她们以声乐、器乐、舞蹈及说白等形式,而不断得以传播。
声乐。在元曲传播中,歌唱能烘托气氛,直接塑造形象。很多时候,观众在听戏时,常是陶醉于“声”之感染力和鼓动力。《青楼集》所载的众多技艺如杂剧、院本、散曲、南戏、小唱、说话、诸宫调、慢词等,歌唱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艺术形式。该著作列出了演员们各自擅长演唱的类别,如珠帘秀、南春宴等擅杂剧;赵偏惜、侯耍俏等擅院本;龙楼景、丹墀秀等擅南戏;宋六嫂、杨买奴等擅讴唱;李心心、燕雪梅等擅小唱;赵真真、秦玉莲等擅诸宫调等。
器乐。元曲舞台演出中女演员在歌唱的同时还常需有一些器乐来伴奏。某种程度上,器乐能作为声乐补充,能渲染气氛、宣泄女演员自身或剧中人物内心的丰富情感。元代许多女演员善弹各类乐器。如顺时秀“金簧玉管,凤吟鸾鸣”;金莺儿掐筝“鲜有其比”;张玉莲“丝竹咸精,蒱博尽解”;孔千金“善拨阮”;于四姐“尤长琵琶”;一分儿“答剌苏,频斟入,礼厮麻,不醉呵”等,表现出较高的弹奏技能。
舞蹈。元曲属舞台艺术,女演员们常在舞台上以各种形体动作来隐示表演的内容,坚持听觉与视觉并重;而观众也多能通过这些“肢体语言”加深对戏曲内涵的理解。《青楼集》中记述了其时许多擅长舞蹈而名动四方的演员,如玉巧儿“歌舞颜色,称于京师”;樊香歌“妙歌舞”;赛天香、刘燕歌、赵梅哥“善歌舞”;一分儿“歌舞绝伦,聪慧无比”;玉莲儿“尤善文楸握槊之戏”;事事宜“姿色歌舞悉妙”;解语花“左手持荷花,右手举杯,歌《骤雨打新荷》曲”等。
说白。元曲作为一种抒情写意的艺术形式,宾白关系到戏曲演出的效果如何,在戏曲表演中地位重要。其时亦有许多女演员善谈谐,能隐语。如国玉第、樊香歌善“谈谑”;梁园秀善、玉莲儿善“隐语”;时小童“女童童亦有舌辩”;刘婆惜“滑稽歌舞,迥出其流”等。元曲的演出,就是通过她们中主脚的歌、舞,其他脚色的对白科范、插科打诨而共同构成了成熟的舞台艺术。
(二)传播方式
上文已述,元曲女演员们十分重视艺术继承。但若换个角度看,她们对戏曲艺术的传播亦发挥着积极作用。
元代女性演员社会地位十分卑下。她们深知,自身的色艺固然重要,但仅靠它并不一定就能成名天下,还得要有机缘。一般说来,达官有着显赫的政治地位,文人在曲艺创作及表演理论上有着丰厚的涵养。若能得到他们的青睐与赏识,将直接关涉她们的艺术才能及地位等被社会认可。她们甚至认为,与显宦骚人的交往愈多,那么自身的名气就会愈大,故对与他们的交往趋之若鹜。当时的社会现实也确实成就了许多实例,如曹锦秀、张怡云、珠帘秀和周人爱等,之所以能成为遐迩闻名的名角,与显要墨客们的称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曹锦秀的“欲为效颦,愿乞一言为发越,俾妾姓名得见于当代名公才士题品之末,庶几接大雅之高风,一时增价”。换言之,对于演员们来说,主动出击,与他们攀上关系,是她们声名鹊起的基础,是获得普遍认可的前提,是增高身价的保证。可见,如此交往对元戏曲的传播起着促进效用。
元代出现了诸多师生共同参与演出的“戏班”。在这里,不仅有固定的人员组成,还有各类脚色的具体分工。而一些内行观众在听戏前,也常关注演员的表演是出于何门。
众所周知,戏班以名脚命名,如以赵偏惜组成的戏班,称之为“赵班”;以顾山山组成的戏班,则称为“顾班”等。每一个“戏班”都有自己的形象标识,有自己的拿手剧目,更有自己独树一帜的演艺,即不同于其他“戏班”的“绝活儿”。特别是针对于同一个剧目,不同师承的“戏班”可能就有各不相同的演法,观众自然也可依此而百看不厌。而一些演员更乐于以名师相标榜,如荆坚坚“人呼为‘小顺时秀”’;李娇儿“时人号为‘小天然”’等。如此不仅提升了自身形象,也扩大了本“班”的影响力。
与师承的“戏班”相类,元代还出现有以家族为单位从事戏曲演出的情况。其时有诸多家庭是全家从艺、世代传艺。如上文言及的张玉梅、小玉梅等条目中的祖孙三代等。应该说,家庭式的“戏班”在当时更为常见。“元杂剧是以乐户之间的亲属姻缘关系组成的家庭戏班演出的”,某种程度上,元杂剧就“是以家庭戏班为演出支柱而得以兴盛繁荣的”[6]。也正是有这些精于不同技艺的演员组合,保证了演员的代代相传,也使元曲的演出成为可能。
(三)传播路径
元曲演员不仅担负着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且随着她们的流动演出和异地授徒,同时也在进行着不同地域之间的横向传播。考《青楼集》发现,元曲的演变区域北起大都、南到江浙,东自松江、西至湘湖。它们不仅出现于大城市,而且遍涉广大中小城镇甚至乡村。其时诸如大都、江淮、金陵、江浙、山东、淮浙、江湘、湖广等地区及昆山、松江、沂州、维扬、邓州、赣州等城镇,都能经常见到一些优秀的女性演员。
一般而言,元曲的传播多集中在一些固定的地点,“专业演员以杂剧演出求衣饭,演出有固定的场所及稳定的观众群”[7]。这其中,在勾栏处演出占主体,“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因为有了勾栏这个固定的场所,演出的时间就可不受天气等的影响,观众亦可方便前来观看,当然也便于组织者收费。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演员也常到达官显宦的家庭小院进行演出,如张子友、涅古伯等家的厅堂等。在这里,文人雅士间可交流戏曲新作、演员间可切磋歌舞等技艺、演员与文人雅士间可评品特定戏曲作品或表演的优劣,这些皆有助于元曲艺术的传播。
总之,元曲艺术的发展与繁荣,众女性演员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由于她们精益求精的治艺态度、诲人不倦的艺术传授及一代代的辛勤实践,才使得元曲能绵延不绝地活现于大江南北的舞台,成为一代之文学和艺术。当然,演员在不懈的耕耘中,也有过许多失败的教训,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然而正是这些教训和代价,为元曲表演艺术的完善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最终使元曲发展为一种具有综合性、程式性和表演风格多样性的成熟艺术。后世戏曲也正是以此为基础而迈向新的台阶。从这个层面说,《青楼集》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元曲接受和传播史。
[1] 黎东方.细说元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39.
[2] 夏庭芝.青楼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7.
[3]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记[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55.261.
[4] 陈琳琳.元代文人与歌妓交往述论——以夏庭芝《青楼集》为中心[J].北京社会科学,2017,(2):40-53.
[5] 通制条格[Z].黄时鉴,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44.
[6] 张发颖.中国戏班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08.
[7] 钟涛.元杂剧艺术生产论[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144.
OntheActressesinYuanOpera:ACaseStudyofBiographiesofActorsandActresses
JIA Mingdang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The commercial performance of Yuan Opera developed certain requirements on the performances of female 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ceptance and dissemination, the female performers in Yuan Opera made it a rule to learn from high officials and gain benefits from their teachers. Most of them showed high cultural and moral standards and superb performing skills. They inherited the art of Yuan Opera and developed the forms, methods and channels of its dissemination.
Yuan Opera; actresses; performing
J812.1
A
1008-6838(2018)01-0060-05
2017-11-08
贾名党(1972—),男,安徽农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传统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王 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