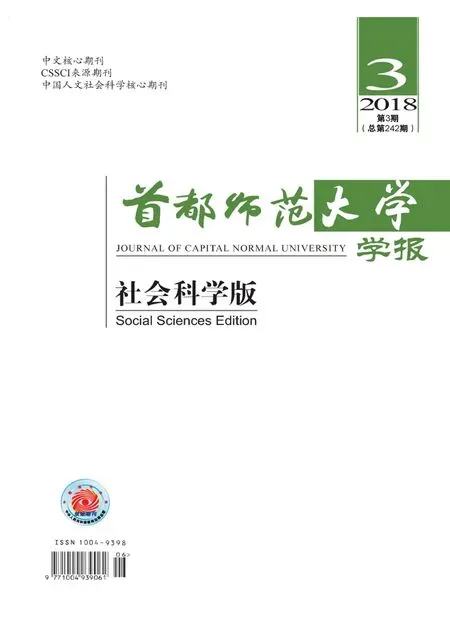陈明远与层累的“郭沫若现象”
2018-04-03李斌
李 斌
在人文学界和大众舆论中,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郭沫若现象”一词频频出现。这个词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解释。有些文章使用这个词时,指的是五四时期那种将个人激情和时代精神融合后产生的“火山爆发”式的创作状态①宋剑华、田文兵:《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中的 “郭沫若现象”》,《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但这个词在更多的文章中指的是像“郭沫若”那样,曾经才华横溢,但新中国成立后,却丧失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尊严,对权力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的知识分子现象。刘再复在使用这个词时,指出郭沫若“埋葬真我”,“把官方语言塞进自己的作品之中”②刘再复:《回归古典,回归我的六经——刘再复讲演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作家安文江使用这个词时认为,随着郭沫若“走向政坛,进入幕僚,当了高官,他否定了真正的自己,成为十分可怜的传声筒”③安文江:《找人说人话》,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散文家何静恒在使用这个词时,认为晚年郭沫若“只有献媚和明哲保身”,“创作生命已经枯萎”,“留下的只是一具逢迎拍马的躯壳”,“说着真诚的假话去左右逢源”④何静恒:《百思不得其解的“郭沫若现象”》,《月亮神》,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版,第195页。。
从上述表述来看,“郭沫若现象”之所以以“郭沫若”冠名,是因为论者认为“郭沫若”有三个特点:第一,作为诗人和历史学家,“郭沫若”曾经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却没有独立的精神,对权力无条件服从;第二,“郭沫若”内心像这些学者一样,能够“辨别是非”,但只能“埋葬真我”,所以他对权力的服从是不真诚的;第三,正因为他不真诚,所以唯唯诺诺、逢场作戏,缺乏知识分子的骨气。这三个特点都指向一个核心形象:“不真诚的郭沫若。”
论者有可靠的材料证明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是不真诚的么?郭沫若对中共领袖和各项建设成就写了很多颂歌,也多次表态承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击右派等运动的合理性,但我们不能从已经披露的可靠的材料中发现他对那个时代的抵触和反省。也就是说,他尽管写了很多颂歌,但如果这些颂歌都表达了他的真实想法;他尽管做出了很多紧跟形势和领袖的行为,但如果这些行为他都认为是正当的,那我们只能说他的认识可能没有一定的“深度”,但我们绝没有理由责备他没有骨气、逢场作戏、屈从权力,更不能得出他不真诚的结论。
我们不能证实“不真诚的郭沫若”为真,在我们接触的史料还不充分不完整的情况下,当然也不能说郭沫若就一定是真诚的。郭沫若是否真诚,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悬置不论,但对于“不真诚的郭沫若”这一形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却有讨论的必要。事实上,“不真诚的郭沫若”和中国古史中的大禹、黄帝形象,民间传说中的孟姜女故事相似,是一个层累式的现代神话。*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与钱玄同论古史书》,正式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并对这一概念做解释,大意是对一些古史提到的人物或现象,我们虽然不能知道其“真确的状况”,但可以通过研究发现它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以及它是如何逐渐丰满起来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在史学界影响很大,本文借鉴“层累”这一概念,意在说明“不真诚的郭沫若”是一个不断生成的神话,有必要讨论它最早出现的状况和逐渐生成的过程。这个神话始于1982年,经过30多年的不断塑造和渲染,今天已经成为很多媒体人和学者笔下的信史。这一神话的主要作者是陈明远。陈明远自1982年起,通过不断虚构回忆录、伪造书信,创造并丰富了这个神话。当他的朋友和一些学者撰文阐发引申他创造的神话后,“郭沫若现象”逐渐成为读书界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高频词,并附带产生了类似于“铮铮铁骨郭沫若”一类的讽刺性话语。
一
1956年8月,当陈明远还是一名中学生时,他给郭沫若写信,就郭沫若的一些作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沫若接信后很重视,给他写了回信。到1963年1月为止,两人有过多次通信。1962年,《中国青年》曾刊发过郭沫若《给青年的几封信》,其中就包括写给陈明远的信,只是陈明远的名字用“XXX同志”代替。在陈明远和郭沫若通信的后期,在上海上学的陈明远不断要求郭沫若帮忙,调他到北京工作。虽然郭沫若欣赏陈明远的才华,但对他露骨的功利欲望却越来越反感。1963年,当郭沫若帮助陈明远进入中国科学院工作后,他决定不再与陈明远联系。
陈明远早在1962年左右,就开始伪造郭沫若信件,虽然他这个时期的伪造,其主要动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但同时也歪曲了郭沫若的本意。
1962-1963年间,叶以群表示要将陈明远和郭沫若通信的事迹写成报告文学,表现郭沫若对青年一代的关心和爱护。陈明远将自己抄写的20多封“郭沫若”书信提供给叶以群。这批抄件一共有三份。记者周尊攘也希望报道此事,陈明远于1963年将剩余的两份抄件提供给了周尊攘一份。叶以群没有写出报告文学,1966年去世后,他手头的抄件由其家属保存。周尊攘当时也没有写出报告文学。直到“文革”结束后,方以他手头的书信抄件为基础,写成《郭沫若与陈明远》一文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上。该文引录“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18封。叶以群的儿子叶新跃看到周文后,发现他家所保存抄件中有9封为周文所未披露,于是在1983年整理好后投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后者以《郭沫若书简九封》为题刊发在1986年第1期上。
这27封信件中,有一多半属于陈明远伪造,其余信件相对于真迹也多有删节篡改之处。陈明远伪造和篡改郭沫若信件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己的形象。下面这封伪信较能说明问题。
在《郭沫若书简九封》中,有一封“郭沫若”1962年7月20日写给陈明远的信,“郭沫若”不同意陈明远作品的发表要求:
你写的关于我的研究文章,译成的我的旧诗,目前是不大好发表的。你就是用了笔名,别人还会知道,要风言风语的。我这是为你着想,你太年轻,太天真无邪,不了解社会的复杂。我也不愿意让你过早地了解到人情世故的复杂性。
这封信是陈明远在郭沫若1962年7月18日写给他的信的基础上伪造的*详见王戎笙:《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129页。。在7月18日的信件中,郭沫若不同意陈明远发表相关作品,原因在于:
你最近寄来的信和文稿,我都看了,你写得相当猛,使我吃惊。但可惜,你写的差不多都是我的陈迹,我觉得你是有点枉费力气的。你为什么不写你自己呢?要写我,恐怕还早得一点,假使我死了,或许你写的东西可能有人看。再则要写我也可以,我替你想个办法,就把我作为“木头儿”(model),写小说、诗、剧、都可以。但如赤裸裸地写我,那就不是创作了。作为研究我的评传,也是一个办法。但目前太早,为生人写评传,有类于标榜,我们中国没有这个风气,特别是目前。因此,不是我替你泼冷水,你是有点像信徒一样了。
这封信在郭沫若纪念馆留有原稿,是真实的。但在陈明远公布的包含大量伪信的69封全部书信中,却并没有这封信。这封信的意见跟1962年6月1日郭沫若致陈明远信的意见是一致的*陈明远将这封信删节收入他的《劫后诗存》,且将落款时间改为1961年6月1日。。在6月1日的信里,郭沫若告诫陈明远:
你费那么多的时间给我写信,翻译我的旧诗,我总有些感觉着不安。我看你是太折磨了你自己,你没有听我的话。
“诗文”,我赞成写,但赞成你写自己的生活,不必悬想别人的生活。你写你自己吧。我的旧生活,我觉得是值不得你那么费力去悬想的。我自己对于它都不感兴趣,我想别人是会更不感兴趣的,因此你的悬想,恐怕有些白吃力。
比照两封真信和陈明远提供的伪信,这件事的原委其实已经相当清楚。对于陈明远研究郭沫若的文稿,及从郭沫若的旧体诗翻译成的白话新诗,郭沫若都不满意。他觉得陈明远在“悬想”、“枉费力气”,在两个月之内写了两封信劝陈明远不要继续下去。1962-1963年,当陈明远面对叶以群和周尊攘时,他要渲染他和郭沫若的交情,宣传经过“郭沫若”多次批阅删改过的他的诗稿。郭沫若既然对陈明远的作品有不同意见,陈明远的个人形象势必受到损害。于是,陈明远隐匿了郭沫若的真实意见,但他又必须解释为什么他的作品没有能够发表,于是就有了杜撰的1962年7月20日信件。在这封伪信中,陈明远将郭沫若对其作品的不满意置换成“郭沫若”对社会环境的不满,这种“假传意旨”式的置换成为后来陈明远塑造“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的重要手段。
二
陈明远进入中国科学院后,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一个左得可爱的先进典型,但是“文革”期间,陈明远因被指控伪造毛主席诗词而被隔离审查,他由此对那个时代带上了伤痕记忆,愤然写下了很多诅咒那个时代的诗篇。
1982年,发表周尊攘文章的同一期《新文学史料》上,还刊出了陈明远的《追念郭老师》。陈明远从此开始了对“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的层累式塑造。
在《追念郭老师》中,陈明远回顾了他“有一年暑假”去西四大院胡同拜访“郭沫若”的情况。据陈明远描述,西四大院胡同的郭沫若住宅“象是一个清朝府邸改建成的,朱漆大门,高墙深院,门口还有警卫站岗”。当陈明远说明来意后,警卫直接将陈明远带到了郭沫若书房。郭沫若向陈明远表示,他对于这样的深宅大院并不喜欢。“其实我内心里也一直不大愿意住在这样王府式的地方,有点跟人们隔绝的味道,我是喜欢象普通人家一样,经常有邻居来往。我特别喜欢小孩子们常到家里来做客的啦。象从前我们在重庆住过的地方,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我回忆起来都觉得满有意思”。“不真诚的郭沫若”在这里现出了他的雏形。他在公开场合对时代大唱赞歌,而在陈明远这样的朋友面前,却表达了他对当时官僚作风的不满。但遗憾的是,这个故事并不真实。长期担任郭沫若秘书的王廷芳曾经指出:“去过郭老大院胡同五号住处的同志很多,大家都会记得,那是一座二层的灰砖小楼,院子前后各有一两排普通的平房。这怎么会给‘经常去玩’的陈明远留下‘清朝府邸’的印象?而且,郭老家门口从来没有警卫站过岗。”*王廷芳:《〈新潮〉的作者到底是谁?》,《郭沫若学刊》,1996年第4期。关于西四大院胡同,现在已经拆除,除王廷芳的记忆外,《北京百科全书》在“郭沫若故居”的辞条中也写道:郭沫若“1949年2月再次来京,携夫人于立群落户在西四大院胡同一座两层小楼(已拆除)”*《北京百科全书·总卷》,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此外,据郭沫若另一位秘书王戎笙称,郭沫若夏天都要去北戴河,而且引导客人拜访郭沫若应该是秘书的职责,作为国家领导人,郭沫若书房可能有机要文件,警卫绝不可能不经允许就进入郭沫若书房。*王戎笙:《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综上所述,西四大院胡同并不是一座清朝的王府,郭府门前也没有警卫站岗,更不可能有警卫将郭沫若的朋友直接带到他的书房,因为这样的事情应该由郭沫若的秘书去做。既然陈明远压根儿没去西四大院胡同见过郭沫若,那位对官僚作风不满的“不真诚的郭沫若”只是在陈明远笔下诞生的神话人物。
在《追念郭老师》中,“不真诚的郭沫若”还展示了他的另一面。就在陈明远杜撰的“有一年暑假”的那次见面中。陈明远对“郭沫若”说:“同学们都讲您有些大白话的‘诗’算不上是诗,只是分行写的散文。”“郭沫若”很诚恳地说:“您们的意见很对,我都接受。我的白话诗有一大半是应时应景的分行散文,我自己都不满意,更难使你们满意了。我很想把那一大半不是诗的东西删掉,免得后人耻笑,你同学有什么意见,不管多么尖锐,请你都如实转告我,好让我以后进行删改!”“郭沫若”不喜欢自己公开发表的赞歌,不喜欢的原因倒并非诗艺不精或思想跟不上时代,而在于诗的内容的“应时应景”(暗示写作态度的“不真诚”),这是陈明远日后不断丰富完善的现代神话。
《追念郭老师》通过编造故事暗示读者:郭沫若表面拥护那个时代,内心对官僚作风充满反感;表面写诗歌颂领袖和各项建设成就,内心对这些诗歌充满鄙夷。陈明远通过这样的编造迈开了塑造“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的第一步。这样的编造不但没有受到学界揭发,反而被研究者重视和引用,陈明远有信心继续丰满完善他的现代神话。
三
1986年,陈明远在《人物》杂志第5-6期上发表了他回顾诗歌创作过程的《诗歌——我生命的翅膀》。1988年,陈明远《劫后诗存》出版,附录收有《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40封)》,这40封信中有13封是新面世的,其中绝大部分是陈明远伪造的。在这两份材料中,陈明远所塑造的“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进一步丰满起来。
陈明远继续描述他到郭府的感受。对于郭沫若在西四大院胡同和前海西街的住宅,陈明远“当时心里并不怎么喜欢。高墙深院,据说从前是清朝的一个王府,门口还有好几个警卫员站岗,叫人觉得挺不自在”*陈明远:《诗歌——我生命的翅膀》,《人物》,1980年第5期,第15页。。 如果说这只是对《追念郭老师》中的细节的有意味的重复,那么《劫后诗存》中新出现的一封伪信则在塑造“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上迈出了更重要的一步。
郭沫若的确在给陈明远的信中说过不满意自己的部分作品的话,这封信就是陈明远在《劫后诗存》中提供的三个影印件的第一件。在这封写于1961年3月13日的信中,郭沫若说:
我的一些未收进集子里面的文章,看来无关紧要。我自己目前还不想再看他们。事实上,我自己对于自己的作品是很少满意的。从前也有过相当大的雄心,结果看来是有点“画虎不成”。光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地已接近七十了。能力和思想长进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时间的速度。自己有点暗暗着急。
郭沫若在这里确实表达了对自己作品的不满意,但他将这种不满意归结为自己“能力和思想长进的速度”的不快,而并非因为这些作品“应时应景”,当然不能指向“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但在《劫后诗存》新提供的13封书信中,有一封陈明远伪造的信件却这样写道:
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的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成为是什么诗!别人处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制应景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这封信落款为“鼎堂 5.5(1963)”,没有手迹或手迹照片为证。陈明远在1963年初如愿以偿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电子所。电子所领导向郭沫若做了汇报,郭沫若于1月8日口述,让秘书以“院长办公室”名义给陈明远写了一封信。在口述信件时,郭沫若对秘书说:“同时告诉他,到电子所后,绝对不要跟别人说他跟郭某人有什么关系。他要是打着我的旗号搞特殊,找电子所的领导提出工作上、生活上的种种要求,使电子所上上下下为难,那就不好了。以后他来信我也不看了,你们处理吧。”*王戎笙:《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2页。也就是说,郭沫若和陈明远的通信时间以1963年1月8日为止。而这封写于“1963年5月5日”的信件,明显出于伪造。伪造此信的目的,是将《追念郭老师》中所伪造的“有一年暑假”他和郭沫若关于郭沫若白话新诗的谈话坐实了,并进一步塑造了“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
为了给“郭沫若”鄙夷自己的新诗作品提供佐证,陈明远在《诗歌——我生命的翅膀》中还提供了如下的“故事”。1957年夏,陈明远和“田汉”讨论说:“郭老解放后的白话诗,越写越像分行的散文、杂文,没有多少诗味;而他的一些旧体诗,倒确实包含着优美的诗意。”“田汉”认同他的看法,但陈明远担心郭沫若不认可。“田汉”说:“你哪里知道!我们现在都老了,怕写新体诗。在这方面,你的话是‘童言无忌’。你敢说皇帝没穿上新衣裳。”果然,“郭沫若”认同了陈明远的看法。但这个“故事”十分可疑,正如王戎笙所说,陈明远有关郭沫若的回忆中出现的事没有明确的地点,出现的人物像田汉、老舍等也都是过世的,这就查无对证,死无对证,于是可能瞒天过海。在历史研究中,孤证不足为凭。陈明远说的都是孤证。所以这个“故事”只能存疑。但这个可疑的“故事”指向的却是“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
四
1992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黄淳浩编辑《郭沫若书信集》时,得到了陈明远提供的29封“郭沫若”书信。据说“这二十九封书信,是陈明远家住上海的哥哥搬家时,从阁楼上翻出来的郭沫若书信手迹抄件中的一部分”。黄淳浩整理为《郭老致陈明远——新发现的郭老书信二十九封》发表在《郭沫若学刊》1992年第2期和1993年3月10日《文汇报·笔会》上,并收入《郭沫若书信集》中。这批书信所署日期多为1956年前和1963年后,由于郭沫若与陈明远通信时期为1956年9月至1963年1月之间,这批书信又没有手迹为证,故被王戎笙等人确认为伪。陈明远在这批伪信中,基本完成了他对“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的塑造。
首先,在这批伪信中,“郭沫若”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中倍感疲倦,对环境十分厌恶,并猛烈地批评了他的时代。
在1982年和1986-1988年,陈明远两次塑造的“郭沫若”对他的住宅所体现出的官僚制度都有所不满,并泛泛批评“社会的复杂”,这在1992年第三次塑造的“郭沫若”的言谈中有了更具体的所指:“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现在我国的新诗那里称得上有什么‘坛’来?别看一些自诩为‘新诗人’者架子十足,也不过是写走江湖的天桥把式而已。”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陈明远第三次塑造“郭沫若”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他将“郭沫若”的不满和批判指向郭沫若自己的身份和五六十年代的具体政策,从而使得“不真诚的郭沫若”更加血肉丰满起来。比如,“郭沫若”对作为政治活动家的自己十分厌倦,觉得这侵蚀了他的“文艺女神”:“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上次谈话时,我说过早已厌于应酬、只求清净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自从建国以来担负了国家行政工作,事务繁忙;文艺女神离开我愈来愈远了。不是她抛弃了我,而是我身不由己,被迫地疏远了她。有时候内心深处感到难言的隐衷”。又如,郭沫若十分尖锐地批判了“大跃进”:“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 ‘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空话、套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
但上引信件显然出于伪造,因其内容明显不符合常识。首先,如果真有这些书信的存在,陈明远又声称这些书信真迹被专案组抄走了,专案组得到这些材料,不可能轻轻放过陈明远,本来地位就岌岌可危的郭沫若也会惹上更大麻烦,但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其次,即便这批书信没有被红卫兵发现,当时的陈明远也不会放过郭沫若。“文革”开始后,中国科学院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正是陈明远“炮打”郭沫若的,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郭沫若”的这些信不正好给陈明远提供口实么?可陈明远却迟至1992年才将其披露出来,这不符合情理。当然断定其为伪信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信的落款时间不在郭陈通信时期之内。
其次,在这批伪信中,陈明远塑造的“郭沫若”十分丧气地承认《新华颂》与《百花齐放》以及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新诗都不是“新诗”。如果说陈明远1982年塑造“郭沫若”只是在谈话中说自己的新诗是“应时应景的分行散文”,1986-1988年塑造的“郭沫若”将“应时应景的分行散文”具体落实为《百花齐放》,那么1992年塑造的“郭沫若”则通过自己的文字将这一批评更加具体化,也更加“实证”化了。“郭沫若”说:“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尽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为憾的”,“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一○一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象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地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天然的情趣就很少很少了!……现在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不仅如此,“郭沫若”还将批评的对象延伸到《新华颂》以及他的很多其它的“诗”:“确实如你所指摘的:《新华颂》里没有多少‘新意’。我自己还要加上一句:甚至没有一首可以称得上是‘新诗’!所有的只是老掉了牙的四言、五言、七言老调,再有就是一些分行印出来的讲演辞”,“近二十多年来我所发表的许多所谓的‘诗’,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文艺作品!这都是我的真心话”。
陈明远1992年出版的《新潮》中收有《新诗与真美的追求》一文,这篇文章引用了1986年《诗歌——我生命的翅膀》中关于《百花齐放》的评论。1986年的原文是:“大跃进中他写的诗集《百花齐放》就是尝试发展新体诗的一种格律:每首八行,每行四—五音步;分前后两片,逢双行押韵,或一、二、四句尾押韵。这是从旧体诗的七律脱胎而来。原先郭老曾用七律形式写过几首咏花的旧体诗,这次都翻译成了新体。但是《百花齐放》的尝试太仓促,突击生产,难免失之于滥。”显然,这是陈明远对郭沫若诗歌的批评,但1992年引用时却篡改了原文,不仅具体表述中字句有变,而且他还在这段引文前面加上了“他当时曾对我说:”,在“难免失之于滥”后面加上“我自己很不满意。我是老而无能了。我的尝试失败了”。*陈明远:《新诗与真美的追求》,《新潮》,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6-17页。这就将陈明远对《百花齐放》的批评置换成郭沫若的自责。这就不是作者所谓的引用时“个别字句有所校正”,而是篡改了文意,这无疑呼应了上述伪信对《百花齐放》的看法,进一步塑造“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但我们正是从这里看出,陈明远有关郭沫若评论《百花齐放》的文字都是杜撰的。难怪明眼人校对两个版本后不禁感叹,“看到这里,你会产生怎样的惊叹?”*雷仲平:《读〈新潮〉之惑》,《文艺报》,1996年5月24日,第2版。
经过1982年、1986-1988年、1992年的三次塑造,陈明远笔下的“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已经成型了,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和科学文化教育战线的旗手,“郭沫若”紧跟党,紧跟政策,但私底下对那个时代强烈不满,进行猛烈批评;第二,“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写了大量新诗,出版了《新华颂》《百花齐放》等诗集,他在这些新诗中赞美领袖毛泽东,赞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和发展,私底下却对这些新诗十分不满,称自己“糊涂”、“赶时髦”。
五
1992年,陈明远已经将他所要塑造的“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基本完成了。这样的“郭沫若”形象符合1980年代以来文史研究领域中的“非郭沫若”认识装置*李斌:《对“非郭沫若”认识装置的反思》,《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5期。,让那些带着伤痕记忆的文史研究者十分兴奋。尽管后来在王戎笙、王廷芳、郭平英等人的考辨下,陈明远伪造信件及回忆录已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但很多学者仍然倾向于相信陈明远塑造的“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郭沫若现象”的说法。
当这些伪信被黄淳浩全部收入1992年出版的《郭沫若书信集》后,很多研究者认为,他们找到了进入晚年郭沫若心灵世界的重要窗口。
有研究者翻遍《郭沫若书信集》,“感到只有写给陈明远的信最为特殊,堪称摘下面具,口吐真言”*丁东:《从五本书看一代学人》,《反思郭沫若》,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234页。。 因为这些信件正符合这位研究者对那个时代的观感:“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知识界的多事之秋,从公开的活动看,郭老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唱的都是红脸,都是拥护紧跟的表态,但他私下里或内心里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在他别的文字中我还没有见到。而当知识界可以公开地反思这段历史时,郭老又已作古。因此,郭老在与陈明远通信中吐露的一点心迹,才格外引起知识界的重视。”*丁东:《郭沫若书信案又有新说法》,《南方周末》,1996年12月27日,第5版。也有研究者从陈明远提供的伪信中找到了他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郭沫若的“难以想象”的“彻底改变”的答案*李辉:《太阳下的蜡烛》,《反思郭沫若》,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222页。。还有研究者感到陈明远提供的伪信“隐隐约约透露出了郭沫若内心世界的另一面”*谢泳:《郭沫若内心有话》,《书城》,1996年第3期。。而陈明远本人,也加入了这样的“合唱”之中,他大力渲染他所提供的伪信的价值:“好在晚年郭沫若还是多少留下了一些发自内心的文字和话语,虽说一鳞半爪,也隐约能够窥见真身。人们从他那‘怆恼的面孔’底下,似乎还能依稀辨认出深深压抑的‘内心的忏悔’,和一声声无可奈何的呻吟。”*陈明远:《湖畔散步谈郭沫若》,《反思郭沫若》,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在这批伪信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将郭沫若形容为“逢场作戏”、“放弃自我,迎合时尚”*丁东:《逢场作戏的悲哀》,《书屋》,1996年第4期。,“戏子的头儿”、“骨子里依然是奴隶”*余杰:《王府花园里的郭沫若》,《反思郭沫若》,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283页。,“当驯服的奴仆丧失自我的道路”*黎焕颐:《一道畸形的文化风景线》,《随笔》,1998年第2期。,“太阳下的蜡烛”*李辉:《太阳下的蜡烛》,《反思郭沫若》,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此外,很多郭沫若研究者在明明知道这批信件和回忆录可疑的情况下,仍然违反学术规范,将其当成信史进入他们的研究成果之中,并对“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进行学理证实。*相关内容参见李斌:《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晚年郭沫若”研究》,《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既然陈明远已经塑造出了一个引起研究界重视的“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现在他需要画龙点睛了。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陈明远说:
郭沫若的文学生涯,可分为前后跨时相等的两半。但这是怎样悬殊的两半啊!前期硕果累累,后期败叶萧萧。一个曾以屈原李白歌德席勒为榜样的天才,一个从来“昂首天外”的诗人,到了后期,居高位、享厚禄,荣华富贵、不可一世,但是,孤独、忧郁、心烦意乱。每逢政治运动的带头“表态”、“紧跟”、说违心话,废套谎盛行、假大空连篇。
据我多年的观察,郭沫若在心理学分类上属于一种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人格型。一方面,外向、情欲旺盛、豪放不羁;另一方面,内藏、阴郁烦闷、城府颇深。一方面热诚仗义,另一方面趋炎附势。*陈明远:《湖畔散步谈郭沫若》,《反思郭沫若》,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255页。
如此,由陈明远等人塑造的“不真诚的郭沫若”很快就成了学界闻名的重要形象。为了概括与“不真诚的郭沫若”相似的那一类知识分子形象,在部分学者的推动下,“郭沫若现象”很自然地就从“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的基础上诞生了。陈明远终于完成了这一现代神话的创造工程。而他却在2013年出版的新书《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中,装着和自己无关的样子呼应了“郭沫若现象”:
客观公正地说,郭沫若的杰出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此后,则基本沦为文化官僚。前期是表现自我的浪漫主义者,后期转化为逢场作戏型的浪漫者。如今评论家们通常认为,郭沫若以1949年为界,分为两大段。不少研究者认为有两个郭沫若。前一个是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个性张扬的才子和革命者;后一个则异化为迷失自我、唯命是听、歌功颂德的文化官僚。这种人格上的断裂形成了“郭沫若现象”的特征。有人认为,郭沫若现象是20世纪几代中国文化人的缩影,是某些精英——知识阶层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时代的悲剧。*陈明远:《透视名人的心理奥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62页。
陈明远此处引证“如今评论家”“不少研究者”“有人”的说法,似乎跟他无关,其实这些人的说法,正是在他经过近30年苦心塑造、宣传、渲染的“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基础上产生的。
通过上文辨析可见,所谓“郭沫若现象”,不过是陈明远等人在30多年的时间里,迎合伤痕记忆者反思新中国的需要,层累地造成的现代神话。“郭沫若现象”中提到的某些现象可能确实存在,但郭沫若本人是否真诚则有待史料证实。既然现有史料不能说明郭沫若不真诚,而部分学者渲染的“郭沫若现象”的内核——即“不真诚的郭沫若”——又是杜撰的,则“郭沫若现象”以“郭沫若”冠名缺乏事实依据,自然也就不能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