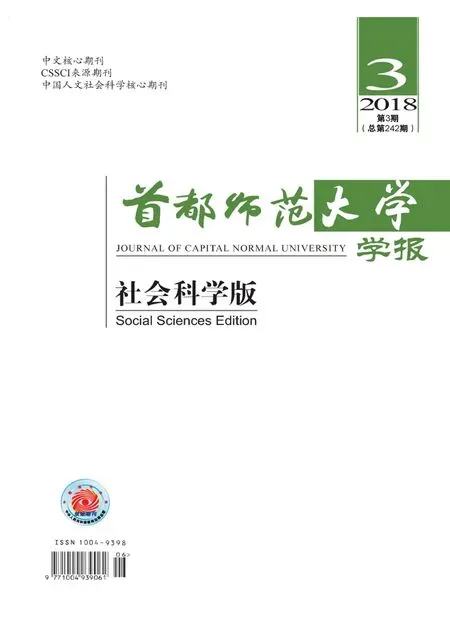“路遥现象”与文学史中的 “农民”问题
2018-04-03卢燕娟
卢燕娟
如何评价路遥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到90年代初的创作,是一个至今未解决的难题。一方面,主流文学史长期对其评价不高甚至避而不谈;①今天比较主流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如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只字未提路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在8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章节中,没有专门介绍路遥,仅在列举80年代归入“乡情、乡土”小说作家名单时将路遥的名字列入其中;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评析了路遥的《人生》,却对其影响更大的《平凡的世界》只字未提。另一方面,这些作品长期拥有人数众多的读者,而且读者对这些作品,不是作为通俗文学接受,而是作为80年代严肃文学经典来推崇。②具体情况可参见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畅销书的生产模式分析》,《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第58-65页。邵燕君文章中,既有诸如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受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委托所作的“1978—1998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这样的专业度比较高、基数比较大的调查结果,也有她本人对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情况的具体调查分析,以及对学生的个别采访讨论等。这些多层次、针对不同人群对象的多个调查结果显示,路遥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平凡的世界》,在广大普通读者和中文系学生中,不仅获得远超其他文学经典的认同,具有同时代和后来经典都难以比肩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受到主流文学史冷淡的作品,并不是作为“通俗作品”获得如此广大的受众,而是作为能够给人以精神力量和严肃审美能量的严肃文学作品在广大读者中受到推崇。因此,批评界提出“路遥现象”问题,用以指“路遥作品的广泛接受性和专家对它的冷淡形成的反差”*吴进:《“路遥现象”探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77页。。正如邵燕君指出:对路遥的这种冷漠态度并不是“精英集团”的一种激进表达,它们“无论是立论还是行文都尽量平衡、客观”,“是对这些年来‘学院派’整体批评观念比较全面、折中的反应”,“正因为如此,《平凡的世界》被‘学院派’整体忽视的状况就表现的更为彻底”。*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畅销书的生产模式分析》,《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第58-65页。而即使近几年来,有文学史试图把路遥纳入其视野,但并未对路遥的创作做出真正超越80年代文学史叙述的解释。如吴进指出的:“这样的转变实际上于事无补,因为如果路遥‘走进文学史’只是一种压力之下无可奈何的平衡之举,并无助于我们对事情真相的认知,也有悖于学术研究的初衷。”*吴进:《“路遥现象”探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77页。
文学史为何冷淡路遥?比较主流的研究是从80年代建构的文学标准内部评价路遥创作,认为其创作方法上恪守现实主义传统,创作姿态上没有完成从“政治美学”向“先锋艺术”的转型,自我意识上则体现出不合时宜的道德主义。*对“路遥现象”的解释分析,著述颇多。在路遥创作的同时期,贺雄飞等人就批评过路遥,当整个文坛都朝着西方先进的艺术形式学习和借鉴的时候,路遥却固守着传统写作方式的“极端保守”态度。参见贺雄飞等编著:《亵渎偶像》,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版;近年来从路遥的“保守性”解释这一现象的代表性论文,可参见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事实上,这些解释随着文学的发展,往往难以自圆其说。80年代以后的文学并不一直排斥现实主义。从早年的改革文学,到后来的新写实,都在理论资源和创作方法上征用现实主义。直至2016年,主流批评家仍然用“现实主义杰作”称道陈忠实的创作。*当路遥因为“现实主义”受到冷淡多年之后,2016年,批评家白烨在陈忠实去世之后,著文称赞陈忠实“坚守了现实主义传统”,以此作为对作家作品的盖棺定论。参见《陈忠实写作〈白鹿原〉的前前后后》,《当代》,2016年第4期。这篇文章在当时广为转载,成为主流文学史对陈忠实的代表性评价。当先锋文学在90年代归于沉寂之后,80年代以“先锋艺术”为方向的文学史叙述本身已经难以为继。路遥早年从创作到理论对这一潮流的批评在这时反而显示出某种先见之明。随着2015年《平凡的世界》改编成电视剧并热播,路遥作品在读者中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再一次质疑了主流文学史对其“保守过时”的判断。因此, 从80年代文学史的先验自足标准出发,描述路遥创作不够经典化的缺陷,是一种缺乏自省意识的研究思路。
“路遥现象”需要立足路遥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意识,越出80年代文学自我建构以自证合法的标准,放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脉络中考察。路遥80年代创作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如何对待土地——或者说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大众的问题”*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2页。。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围绕如何定位和表现农民形象,在文学史中有 “乡土叙事”和 “革命叙事”两个主要传统,其根本差异在于农民与现代历史的关系,前者将其摒弃于外,后者以其为历史主体。具体说,乡土叙事在“传统/现代”的大框架中,将空间上的乡村/都市差异转化为时间上的传统/现代差异,农民被放置在现代文明之外,或从启蒙现代性角度被批判国民性,或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用于抵抗现代性扩张。革命叙事的主题是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有别于启蒙叙事的未来想象,不以现代资本文明为其标准和方向,而以劳动伦理为标准,以劳动者的解放为方向。农民作为中国现实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劳动者,在这一叙事中获得主体性。
伴随着80年代对现代中国历史的重新定位,“现代/传统”与“都市/乡村”的二元结构重新成为文学评价历史、想象未来的主流思维,取代了此前以劳动者为主体创造新世界的叙事。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整体上是“进城”的文学:以现代都市文明为理想,以精英知识分子的视野、经验来评价历史、想象未来。这一时期的农民形象,无论是再启蒙文学中蒙昧麻木的农民、改革文学中被城市现代化克服同化的农民、乡土文学与寻根文学中作为抽象文化标本的农民,整体上离开革命叙事回归乡土叙事。
事实上,路遥在80年代文学创作中,以农民问题为核心问题意识,这本身已经体现出与80年代主流文学的差异。进一步,路遥在创作中重申农民作为劳动者的历史主体性问题,进一步体现出对革命文学话语逻辑的继承。但是,路遥不是革命文学的“遗民”。秉持现实主义精神,他真切地呈现了农民“应该具有主体性”与“正在丧失主体性”的矛盾困境,展示了本应成长为梁生宝的青年农民如何从劳动者变成打工者的问题。无论是提出的问题本身,还是讨论问题的逻辑,路遥都越出了80年代文学的历史视野和问题意识,难以在80年代文学能够容纳的框架内来理解和阐释。但是,这些问题却是“路遥现象”在今天真正的开启性意义:路遥这一时期的创作不是从文学手法等表层难以融入80年代主流文学,而是从文学想象与呈现历史的根本逻辑层面,挑战了80年代主流文学。这一挑战直至今日横亘在主流文学史的自足叙述之外,通过不断在大众中释放出主流文学选定的经典所难以具备的、能持续引发情感共鸣与问题共识的能量,指向对80年代文学史基本叙事逻辑的反思。
一、农民经验与返乡叙事——重申农民主体性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且“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此后近40年的人民文艺,以劳动人民作为历史主体,以他们的情感经验、价值立场为主导。80年代,知识分子取代工农兵成为文学想象历史的主体,这一转型在文学中直接产生了三个后果:其一,以知识分子的经验来评价历史和现实,农民失去主体地位,成为历史的失语者。80年代初数量众多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多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知识分子遭受苦难证明历史的不义,知识分子得到平反、重返社会中心,则证明了“新时期”的合法性。农民的情感、经验不再受到关注和表现。其二,随着知识分子的视角占据文学的中心,知识分子在文学中普遍被塑造为文明、进步的现代历史方向代表。与之相应的,是农民形象在80年代文学中全面溃败。即使不像古华《芙蓉镇》中的流氓无产者王秋赦、王兆军《拂晓前的葬礼》中的野心家田家祥这样,成为历史罪人,最多也就是以陈奂生为代表的“善良愚昧”形象,只能随波逐流、等待启蒙,毫无主体性可言。其三,在城市与乡村再次被从意识形态上区分为文明与蒙昧、先进与落后的叙事中,农民离乡进城的故事普遍存在于文学中,成为现代历史的方向隐喻。在以高晓声《陈奂生上城记》、铁凝《哦!香雪》为代表的一批作品中,乡村不再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现代文明之光照耀不到的场所。 “进城”意味着在物质上受惠于市场福利,更意味着精神都被现代都市文明之光辐射,从麻木沉睡中逐渐苏醒。无论陈奂生和香雪们的肉身如何被排挤在现代城市空间之外,他们的精神却正在进城或已经进城,必须进城也只能进城。进城是不可逆的时间之旅,是农民进入现代历史的唯一通道。返乡意味着失败,意味着被现代历史摒弃。
路遥在这三个问题上与80年代主流文学逆向而行,重申农民的历史主体性问题。
其一,以农民而非知识分子的情感立场与问题视野来写作。路遥说: “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也就能出自真心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痛苦……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634页。农民与农村的问题几乎是路遥全部创作的主题,而且也是他评价历史和现实、想象未来、表现中国甚至世界的基点和载体:“放大一点来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不就是全球的农村吗?”*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虽然他与当时的主流话语一样,也将80年代判断为“拨乱反正”的“新时期”。但是他对这一历史性质的判断,却不基于知识分子的视野,而基于农民的视野,以农民的生活、经验和理想为自己评价现实、想象未来的主要基点。换言之,路遥所要想象和表现的历史与现实,主要是农民的历史与现实;路遥所要观察和再现的中国社会,是以农村为主要建设和改革对象的中国社会。路遥最重视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其创作意图是“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8页。。小说也确实涉及到1975—1985十年间城市乡村中的各种人物,甚至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但是,整个作品中,评价历史、观察社会的核心视野,却始终聚焦于农民孙玉厚一家。在小说视野中,历史的伤痕不来自知识分子曾经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而来自孙玉厚这样的农民辛勤劳动却一无所获的悲剧;现实中改革开放的合法性也不来自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社会地位提升,而来自像孙少安这样的农民,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勤劳,摆脱父辈绝望的贫困,创造新生活的可能性。较之在“拨乱反正新时期”这一模糊结论上的一致性,路遥在历史主体的选择上,对80年代文学的挑战是更为根本的。
其二,路遥笔下的农民普遍具有高度的主体性,体现出自尊自爱的气质,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农民”在乡土叙事中几乎是传统、愚昧、麻木的代名词,到了80年代,陈奂生的精神萎缩到在人群中失语。但是,路遥笔下,即使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玉厚,被生活磨掉了勇气和棱角,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尊严。虽然在人前沉默寡言,可是在是非善恶的信念上,有自己强韧的世界观。《人生》中的德顺爷爷,充满了来自生活与劳动的智慧。而到了中青年一辈农民身上的,虽然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多的差异,但是,基于主体意识的尊严感,仍然一以贯之。路遥以近乎自傲的笔调,讲述了《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平、《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如何在极度的饥饿中也保持着精神的独立与清白。《人生》中的高加林,虽然一度迷失在城市的诱惑中,但是仍然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与尊严感的青年农民,这种尊严感并且成为高加林反抗命运的一个重要动力。同一作品中的理想形象刘巧珍,虽然不识字、没有刷牙的文明习惯,却通过追求爱情时的勇敢无私、面对挫折时的自尊自爱,展现出丰富、独立的精神特征。这些拥有着强烈尊严意识和丰富精神世界的农民,个性生动、形象鲜明,活跃在路遥的作品中,照亮了80年代主流文学中那些浑浑噩噩、晦暗无光的农民形象,提示着农民在现代历史中的另一种形象可能性。
其三,路遥逆进城文学之潮流,将“返乡”作为农民获得主体性的方向。路遥客观再现了80年代城乡物质生活上的巨大差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姐姐》中的男知青、《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都在面对城乡之间物质生活的巨大差异时对进城产生了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真切地显示出他们与陈奂生、香雪在生活经验上的同时代性。但是,当高晓声和铁凝完全站在城市文明的优越立场,将农民的进城欲望表现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提升时,路遥却逆向而行,拒绝将城市较之乡村在物质层面的优越扩展为文明层面的完胜,拒绝将农民定位为现代历史中的落伍者甚至对立者。相反,在他笔下,物质富足的城市,精神往往是匮乏的;外表干净光鲜的城市,道德上却往往是有缺失的。《人生》中,高加林在进城前,用知识分子向往城市的眼光,看到乡下姑娘巧珍没有刷牙的习惯、农村的水井没有净水措施这些表层的“不文明”,却在进城后迅速领略了张克南母亲的腐朽市侩、张克南的庸庸碌碌、黄亚萍的虚荣自私。在这一对照视野中,农村的不文明是物质的、表层的,而城市的不文明才是精神深处的也是更本质的。小说中,黄亚萍与刘巧珍构成了城市与乡村的隐喻,而高加林抛弃灵魂完美的巧珍选择虚荣自私的黄亚萍,象征了路遥一面痛苦地意识到城市对农民产生了难以抵制(甚至是可以理解)的诱惑力,一方面通过德顺爷爷的批评和最后高加林的忏悔,仍然顽强地恪守着“返乡”对农民的正面意义。由此,路遥翻转了80年代主流文学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所建构的历史方向:城市对农民的诱惑不意味着高晓声们的“追求文明”,而意味着背叛与堕落。进城不意味着觉醒而意味着迷失,返乡才意味着农民对自己和乡村主体性的坚守。路遥笔下,几乎所有进城的农民都从返乡中获得升华与净化。如果说,高加林的返乡还具有进城失败之后的不得已,则《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中的刘丽英,则是在经历了城市富足生活中人性的虚伪、丑陋之后主动离开、返回乡村教师丈夫身边;《风雪腊梅》中的冯玉琴,干脆不受城市诱惑,主动逃离返乡。而《你怎么也想不到》中,女大学生抵御城市诱惑的主动返乡行为闪烁着理想主义光彩,返乡的行为在这里不仅仅指向道德层面的坚守,更获得主人公在更正确、更有希望的道路上走向未来的时间价值。
二、劳动价值与劳动者尊严——农民主体性的观念依据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将贾平凹与路遥无差别归入“乡土作家”序列*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这体现出80年代以后主流文学史叙事对革命文学传统的遗忘,模糊了路遥与与乡土文学在话语逻辑上的深层差异。 吴进指出:“不管路遥的乡土情结如何坚定,但他从没有像沈从文或贾平凹那样自信甚至骄傲地自称为‘乡下人’。为什么会这样?他的乡土情结为什么没有导致他做出像沈从文和贾平凹那样自然的身份认同?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路遥仍然十分自觉地停留在革命文化的传统中。沈从文本来就在革命文化的影响之外,他对湘西文化传统的认同很明显是与革命文化传统相悖的——如果不是冲突的话,而深受沈从文影响的贾平凹也抱有一种类似的态度。”*吴进:《城市·农村·中国革命:路遥小说解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19页。
革命叙事区别于乡土叙事之处,不仅仅是以劳动者为主体这一结论,更深层的是这一结论所依据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是:劳动创造世界,劳动者是新世界的主人。换言之,劳动者不是因为贫穷、辛劳受到怜悯,而是因为他们的劳动创造世界,所以他们是历史真正的主人。对这一观念的认同,产生出对劳动者的尊重意识,也产生出劳动者在现代世界中获得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可能性。吴进所说路遥作品停留在“革命文化的传统”,由此具体可以阐释为:置身于80年代语境中,路遥既没有将农民作为 “蒙昧国民”来启蒙,也没有将农民当做逃遁于现代时间之外的“传统乡民”以抵御现代性。他笔下的农民,是现代社会中的劳动者,而且是经历过20世纪革命与建设的新劳动者。他们认同劳动,因而尊重作为劳动者的自己。基于劳动所带来的尊严感与新世界的平等观念,他们对横加于自身的欺凌和歧视具有自觉地反抗意识。由此,农民生活的乡村世界也不是外在于现代时间之外的落后时空,而是现代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革命的现实,甚至是中国进行现代革命与建设的最重要场所。
其一,路遥笔下的农民,普遍从劳动中获得主体尊严感。即使是高加林、孙少平这些青年农民,他们想要摆脱苦重的劳动,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但是路遥仍然要特别为他们声明:他们对劳动与劳动者,绝无半点轻视之心。高加林被取消教师资格,路遥一面坦率地写出了高加林渴望离开农村、摆脱体力劳动的心态,但是仍不忘从高加林的内心活动中替他声明:“农民啊,他们那全部伟大的艰辛他都一清二楚!他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路遥:《人生》,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从来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是不想当农民的高加林虽然受到批评但是尚值得同情理解的道德底线。同样,在《平凡的世界》中,当孙玉亭告诉孙少平为他谋得村办教师一职时,路遥在表现孙少平全家为此兴奋的同时,仍然要为孙少平声明:“他不是庆幸逃避劳动。”*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路遥文集》(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5页。高加林、孙少平,真切地再现了新的历史时期,农民对自己生活现状的不满、对改变自己命运的迫切期待。但是,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仍然坚固地支撑着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在这一观念支撑下,他们为贫穷叹息,也不免在现实中感受到城里人的歧视,甚至高加林会不择手段想要摆脱农民身份。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存在劳动者的主体尊严感。如上一节所述,他们身上普遍具有自尊自爱的气质,而这种自尊自爱的观念根源,正在于作为劳动者,对劳动的尊重与认同。
其二,路遥的小说真实地再现了80年代社会上歧视农民的现象。但是,路遥没有以居高临下的同情视角,将农民作为弱者来表现其卑微与屈辱。他让农民通过重申劳动的合法性来对抗歧视,这种反抗延续了20世纪中国革命赋予劳动者权力与尊严的意识形态,隐含着劳动者通过反抗压迫获得主体解放的叙事逻辑。《人生》中,高加林进城拉粪,面对克南妈的挑衅,不卑不亢地回答:“我身上是不太干净,不过,我闻见你身上也有一股臭味!”*路遥:《人生》,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这句话,直接征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话语资源:劳动者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是却比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干净,重申了劳动者最干净、鄙视劳动的人最肮脏的观念。蔡翔较早注意到挑粪受辱与高加林反抗之间的因果关系,曾经指出: “高加林的自尊在‘挑粪’一节中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屈辱从反面教育了他,催化了他愿望中的出人头地的个人主义因素,并且煽起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蔡翔:《高加林和巧珍——〈人生〉人物谈》,《上海文学》,1983年第1期,第85页。但是需要辨识的是,高加林在心里反抗这一羞辱的语言是:“乡里人就这么受气啊!一年辛辛苦苦,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打下粮食,晒干簸净,拣最好的送到城里,让这些人吃。他们吃了,屁股一撅就屙就尿,又是乡里人来给他们拾掇,给他们打扫卫生,他们还这样欺负乡里人!”*路遥:《人生》,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从这段内心独白可以看出,虽然他曾经一直渴望着城市,甚至以城市的视角嫌弃过农村,但是当在拉粪劳动中受到羞辱的时候,他的愤怒却不指向“无知市侩”对“知识分子”的无礼,而是指向“城里人”对作为用劳动创造了财富、支撑着现代社会运转的“劳动者”的欺凌。在愤怒情绪中,高加林本能地认同了自己劳动者的身份,这就使高加林的反抗同时具有了捍卫劳动者主体尊严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出人头地的野心。
其三,通过将农民的主体性建构在劳动者身份基点上,路遥对乡村、土地的赞美,最终落脚于对劳动创造生活这一叙事的重申,而不是乡土叙事中的“恋土情结”。沈从文与贾平凹对乡村和土地的赞美,基于他们对传统文明的认同,是将乡村与土地作为这一抽象文化符号来抵御现代性。表面上看,路遥对土地的赞美与他们有相似之处:受伤的高加林扑向土地,是乡土文学中常用的情节;而土地对受伤心灵具有治愈功能更是乡土文学的标志性叙事。但是,路遥笔下的土地,不是为现代生活中受挫的年轻人提供一个避世的桃花源,让他们在土地的庇护下逆着现代时间回到过去;而是向年轻人提供一种更积极、更正面进入现代生活的途径,让他们在踏实的劳动中面对现实、创造未来。《姐姐》讲述了农村少女“姐姐”被城市男知情背叛抛弃的故事,在小说的结尾,父亲带着姐姐来到土地上。对于在土地上劳作了一辈子的父亲来说,土地之所以能疗愈女儿的创伤,绝非因为它是静美于时间之外的避世桃源,而是因为:“明年地里要长出好庄稼来的,咱们的光景也就会好过罗……嗷,这土地是不会嫌弃我们的……”*路遥:《姐姐》,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9页。小说结尾,路遥进一步直抒胸臆:“姐姐,你听见了吗?爸爸说,土地是不会嫌弃我们的。是的,我们将在这亲爱的土地上,用劳动和汗水创造我们的幸福。”*路遥:《姐姐》,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9页。——这一叙述清晰地呈现出,路遥对农民的肯定、对土地的赞美,其所依据的都绝非乡土叙事逻辑,而是革命叙事所创造的劳动尊严与劳动者主体性。
三、对柳青传统的继承与背离:农民主体性的困境
路遥与柳青的师承关系曾一度是讨论的热点。80年代,现代主义已经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中国文学主流。路遥却在这一潮流中逆向而行,以柳青为老师,并且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上都尊崇柳青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如上文所述,路遥在文学中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以劳动者为农民主体合法性的依据,确实继承了柳青所代表的文学传统。*实践上,路遥不仅一直坚持在当时被视为落伍的现实主义手法,而且如前文所述,在历史主体的选择、话语立场的认同上,基本继承了柳青所代表的文学传统。在理论上,路遥不仅写作了《病危中的柳青》、《柳青的遗产》两篇文章,表达自己对柳青的个人情感,直言对柳青所代表的文学传统的肯定与推崇,更在自己的多篇创作谈中,反复为现实主义——尤其是柳青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辩护。参见路遥:《路遥文集》(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80年代之初,路遥对80年代文学转型的抗辩姿态使得评论更多看到他对柳青的继承,指责其创作姿态保守、价值观念落伍。但是近年来的研究,从新的历史视野日益关注到路遥对柳青传统的背离。郭春林比较《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发现二者展开的历史主题尖锐对立,认同的历史道路也背道而驰。前者的主题是农民如何从私有制走向公有制、参与到社会主义集体创业的实践中;而后者是对这一主题的否定,是农民从参与社会主义集体创业退回到个体发家道路的历史改道。郭文尤具洞见之处,是作者没有把这一差异简单处理为两个作家的比较,而是放置在现实历史进程的改道中来讨论这一差异。*郭春林:《路遥——柳青的继承人?》,《长安学术》第九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从本质上说,柳青所代表的文学传统,并不完全是文学内部的传统,而是文学呼应、参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结果。所以,以劳动者为历史主体、创造属于劳动者新世界的理想叙事,并不是作家的向壁虚构,而是呼应着20世纪的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建设等一系列开创性的历史实践活动。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历史进程是这一文学传统的现实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入80年代新时期,柳青文学传统在文学史视野内的终结,首先不是文学的转型,而是社会与历史的现实转型。
当路遥从柳青所代表的传统中感受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的时候,他也许并没有特别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有效的创作方法而非一种由革命历史产生的意识形态结果来加以认同。同样,他把柳青作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和伟大的好人来推崇而非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实践者来认同。因此,尽管路遥对柳青及其文学传统的认同与尊崇使他的创作确实与80年代主流文学形成了巨大的分歧,文学史也因此长期冷淡他的写作,但是,路遥绝非柳青文学传统在新时期的“遗民”。尤其是,路遥将作为创作方法而非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当做柳青的主要遗产来继承,这意味着他必然遵循现实主义原则,忠实反映现实历史,在对柳青真实的敬意中呈现柳青文学世界的真实终结。
在本文的问题视野中,路遥在将农民作为文学想象历史的主体、并且重申他们作为劳动者的尊严与权力的基本创作立场上,确实继承了柳青所代表的理想观念和文学传统。但是反讽的是:农民 “应该具有主体性”的理想和“正在丧失主体性”的现实在路遥文本内外的世界中交织并存,呈现出历史转型时期,文学记忆与现实经验之间的博弈交汇。最终,路遥让和梁生宝一样具有丰富精神世界和强烈主体意识的农民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告别了梁生宝的道路,终结了劳动者创造新世界的历史,回归到发家致富、各谋出路的“平凡的世界”,而这正是《创业史》在起点上要超克的道路。
诚然,较之80年代主流文学,路遥通过肯定农民的劳动者身份,援引劳动创造世界的话语资源,避免了把农民、土地抽象化。但是,与此同时,他却把劳动抽象化了。路遥在文本中同样真切地呈现出劳动在现实世界中的无尊严状态。无论高加林个人素质多么优秀,一旦退回农民身份,深爱他的黄亚萍也绝不可能再与之结合。孙少平坐在火车上,想到自己的劳动使得火车能够驶向远方,刚刚生发出作为劳动者的自豪感,马上就遭遇了列车员针对煤矿工人查票的羞辱,使他意识到:他视为光荣的劳动者在列车员眼中,是低贱的下等人。因此,即使在路遥的文本中,劳动也退守到劳动者内心中,成为一种近乎自我安慰和自我坚守的道德理想。这产生了路遥笔下的“知识农民”形象在精神和现实中的分裂:路遥让他们具有阅读能力,从而能通过书本为自己建构一个暂时离开现实的精神世界。于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孙少平可以上天入地、甚至与外星人对话,可是在现实世界中,他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无法将十四岁的少女从包工头的淫威下拯救出来。他与田晓霞的恋爱,本质上也发生在这一虚幻的精神世界中:他们相遇、相爱与相处的场景,都需要大量的阅读场景和书本道具来填充。田晓霞在洪水中的牺牲,是意外情节,却是必然逻辑:作家秉持现实主义的清醒,深知这场精神世界中跨越身份差别、灵魂平等的恋爱在现实中无处容身。
由此,路遥在文本内外均遭遇深刻困境。在文本中,一方面,孙少平和高加林特意声明,他们认同劳动、尊重劳动者;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竭尽所能逃离劳动:即使不能离开农村,能在农村中离开体力劳动当上村办教师也是值得他们全力追求并为之兴奋的。高加林的忏悔是真诚的,可他逃离乡村的愿望更加真切。孙少平为了取得城市身份,哪怕是城市中最底层、最边缘的矿工,也竭尽所能去谋求。从这样的行为来说,所谓“不鄙视劳动”,其实是口是心非、此地无银的无力辩解。在文本之外,路遥在让他笔下的农民选择坚守乡村来获得主体性的同时,却在现实中竭尽所能帮助家人摆脱农民身份。为了给弟弟王乐天解决城市户口,路遥甚至对他在文学世界中所不屑的拉关系、托人情等行为践行不疑。*参见梁向阳:《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3期。在本文的问题视野中,这种言行的严重分裂不指向对路遥个人品格的评价,而在于揭示出路遥的情感立场与价值认同所遭遇的深刻困境:他认同劳动创造世界、劳动者应该受到尊重;可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是城乡的巨大差异下,乡村面对城市的萎缩、农民与城镇居民从现实的物质生活到观念的社会身份之间都存在着难以填平的鸿沟。
真正深刻的问题在于:这一鸿沟,究竟是路遥对柳青的背离,还是历史本身的改道所致?作为现实主义作家,路遥不可能在蛤蟆滩已经瓦解的现实历史中创造一个乌托邦。可是,他真切地记录了从蛤蟆滩退回双水村的历史轨迹中,农民丧失主体性,从劳动者变为打工者的切身经验。正如李晓霞指出:“在乡村转型过程中,劳动及劳动观念正发生着深刻的巨变。劳动的美,或者1980年代所塑造出来的美好的劳动形态首先是个人的,而且这个个人是脱离了具体劳动生产关系……”*李海霞:《从劳动者到打工者》,《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3期。更重要的是,如果路遥的思想背景中没有一个柳青的传统,那么这些农民会毫无违和地以陈奂生的形象出现:他们所遭受的一切不公与歧视将直接归因于他们自身的麻木愚昧。但是在路遥笔下,农民们在贫困中对自己主体尊严的坚守、面对欺凌和羞辱时的自觉反抗,都一直在顽强地提示着读者:他们用劳动创造了历史,他们不是心灵麻木、灵魂晦暗的失语者。今日强加于他们的不公与羞辱,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法性。
“路遥现象”是80年代以后文学史的一个缺口。只要路遥的作品还能继续在读者中释放情感能量、引发新的思考,这个缺口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从不同的角度提示后人对80年代文学所建构的自足标准进行理性审视。本文从路遥创作的核心问题——“农民问题”切入所进行的突破,仅仅是诸多可能视角中的一个。这一思考,指向在社会历史的转型中考察文学的转型。最终,路遥在文本内外所呈现的“农民问题”,同样是80年代真切而重要的社会历史问题。而其在30多年前所提出、讨论的问题,所遭遇的困境,历经三十多年历史发展演进,在今天,仍然在文学世界与社会现实中并未完全隐身匿迹。从这个意义而言,“路遥现象”打开的,不仅是文学史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