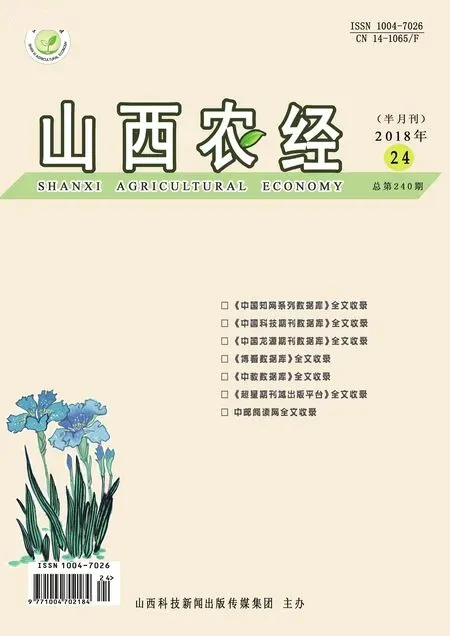参与式治理下的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研究
2018-04-03陈兰芳杨靖伟
□陈兰芳 杨靖伟
(昆明学院经济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1 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及危害
1.1 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
农民工“临时夫妻”,是指在外打工的男女,双方或其中一方已经结婚,又与他人以夫妻的形式组建临时家庭,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男女关系。
近年来,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来自农民工群体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丽指出,农民工长期处于夫妻分居状态,心理、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出现“临时夫妻”,俗称“搭伙夫妻”,引起全国人民的热议。据统计,中国现有2.5亿农民工,其中80%介于21~50岁,选择再婚和露水夫妻的农民工数量有可能已超过10万。由于生活压力大、精神空虚、缺少沟通者等现实生存状态,农民工“临时夫妻”相互之间扮演着合伙人、知心人等多种角色。
1.2 农民工“临时夫妻”的危害
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破坏传统的家庭稳定,冲击社会道德伦理和法制伦理,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
1.2.1 破坏家庭稳定
农民工“临时夫妻”是挑战家庭稳定的利器,损害夫妻感情,冲击家庭关系,影响子女成长。“临时夫妻”的参与者,由于要维系“临时夫妻”关系,导致对原有的家庭观念和亲情观念淡漠。一旦“临时夫妻”问题被发现,必将使夫妻关系产生破裂,甚至会导致婚姻瓦解和家庭解体。同时,“临时夫妻”也影响原有家庭子女的成长。由于“临时夫妻”导致的夫妻离婚案中,孩子都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部分孩子受父母的影响,在耳濡目染中习惯并接受不良性观念,在成长过程中模仿、学习父母亲的不良做法,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1]。
1.2.2 冲击道德底线
一夫一妻制是全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夫妻双方都应自觉忠于婚姻,忠于对方。“临时夫妻”是以一种不规范、不稳定的两性关系形式存在,对社会道德伦理有巨大冲击。“临时夫妻”会极大地破坏人们对婚姻所应持有的尊重态度,会使人们以一种极为随意的态度来处理各自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所应承担的义务,会严重扰乱我国传统的婚恋观,引起农村婚姻和家庭关系失衡等一系列极为严重的问题。
1.2.3 影响法治建设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临时夫妻”违背了一夫一妻制的法律精神,也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各种形式的“临时夫妻”,在性质上都是非法的、不受法律保护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临时夫妻”导致离婚率增高,还会因为复杂的情感纠葛及经济纠纷等问题引发违法犯罪问题。
2 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产生的原因
2.1 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
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是“临时夫妻”问题产生的关键制度性原因,也为“临时夫妻”的滋生提供了空间。农民工身在城市务工,但户口依然在农村,社会地位并没有被承认,生活、精神上都处于边缘,政治上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其劳动权利、社会保障权益、政治参与等合法权益严重受损。迫于生计,农民夫妻一方在家留守,另一方外出打工,部分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割裂情感维系,组建“临时”家庭。
2.2 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
治理理论认为,民主是实现良好治理的实质和核心。随着我国政治制度的完善,让农民工享受均等的政治参与权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从一定程度上说,弱势群体农民工“临时夫妻”的滋生,和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缺失有一定比例关系。在我国现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并受中国农村典型的“臣民型”政治文化的影响,农民工既没有充分参加农村政治生活,也没有融入城市政治生活,同时也限制了农民工权益保护的话语权[2]。
2.3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自2000年以来,国家层面逐渐关注农民工权益问题。但是,随着农民工人数的迅猛增加,社会保障问题依旧严峻。201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比例仅为9.1%、17.6%、28.5%和15.7%。社会保障门槛高、转移难,导致农民工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临时夫妻”成为抱团取暖的无奈方式。在社会保障无法满足需求时,农民工只能就地另觅临时伴侣,共同分担生活的困境。
3 参与式治理下“临时夫妻”问题的解决路径
3.1 “参与式治理”理论要点
“参与式治理理论”伴随着治理理论的出现,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更加突出“参与性”,强调政府与社会、公民等建立良性互动的合作、协同伙伴关系,通过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等民主过程来实现。陈振明在《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中指出,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即为了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
造成农民工“临时夫妻”的原因很多,靠单方的力量是不可能解决的。解决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要形成以农民工自身直接、积极参与为主体,政府主导、企业协同、社会参与的合作网络治理格局。
3.2 解决“临时夫妻”问题的路径
3.2.1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的改革是要实现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的均等化。事实上,城市户籍价值已经在降低,随着地权的确认,农村土地更有吸引力,很多农民工表示不愿意把户口迁入城市。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与户籍制度有关的医疗、入学等配套制度建设。
3.2.2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一方面,要优化产业布局,适当增加男、女工种比例,鼓励开“夫妻店”。如在部分建筑工地,丈夫是技术工,工地可以提供一定的岗位给妻子,以从事简单的协助工作,就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杜绝“临时夫妻”的出现。
另一方面,政府应发挥各项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开展外出务工人员培训。要提供相应的技术能力指导、救助服务,为他们提供基本权益保护,包括身心健康教育、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的培训。驻城镇办事处等组织作为劳务“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桥梁,也要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各种权益保护和支持。
另外,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在资金、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指导,解决就近就业问题[3]。
3.2.3 用工单位重视农民工权益
农民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企业与农民工实现双赢的基础。抑制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企业大有可为。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用工理念,尽可能改善农民工的住宿条件,并提供夫妻探亲房间。如重庆渝安集团,从2010年开始为农民工夫妻提供员工住房,从合伙租房到夫妻房,确实为农民工夫妻做了实事和好事。渝安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表示,“自从推出‘夫妻房’后,员工的干劲更大了,我们的管理也更有效了”。这些举措,为解决农民工“临时夫妻”的问题创造了重要条件。
3.2.4 扩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路径
参与式治理作为一个利害相关者参与的“决策过程”,强调边缘群众、弱势群众的有效参与度,使其参与到政策的制定、执行中来。要努力填补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空白,让他们树立掌握“话语权”的信心,引导其从非官方到官方渠道上来解决问题,以消除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
3.2.5 加强工会组织的作用
工会是为保护劳动者权益而存在的组织,农民工作为一个正处于国家转型重要时期的特殊群体,其工人阶级的身份已经被认可。鉴于农民工群体的庞大性、复杂性,工会工作任重道远。工会工作需要从精神文明、情感关怀等层面更加细微地保护农民工群体,解决农民工“临时夫妻”等问题。如昆明市五华区总工会为农民工会员集中购买2017年元旦春节返乡车票;天津工作组织驻守岗位的农民工欢度津味猴年;首都工会组织关爱农民工活动,为工地上的农民工送慰问品、开设夜校课堂,从维权、技能提升、生活、身心健康等方面增加其获得感。
3.2.6 保障农民工相关社会权益
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是解决农民工“临时夫妻”的一个重要路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从国家层面来看,关系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陆续出台,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实现搭建了政策平台[4]。
(1)实行低门槛准入政策,让更多农民工参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将农民工纳入社区卫生计生服务范围,实现全覆盖。要降低入保门槛,坚持低费率,政府和企业各支付一部分,农民工支付一部分,构建三位一体的保障机制。
(2)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很强的特点,简化参保程序。探索建立全国统一联网的个人社会保障账户,账户号与身份证号一致,账户可累计计算,可跨地区使用。农民工离开参保单位后,只需要身份证就可以转移社会保障账户到新单位。如果暂时没有找到单位,银行要暂时封存账户,为其保留账户。投保数额采用年保制,农民工在1年之内凑足数额即可,收入多时可以多存,没有收入时可以不存,灵活处理。
此外,要建立维权举报热线、应急救助站,对有重大疾病或意外伤害等原因的农民工提供临时帮助,如基本饮食等,完善社会救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