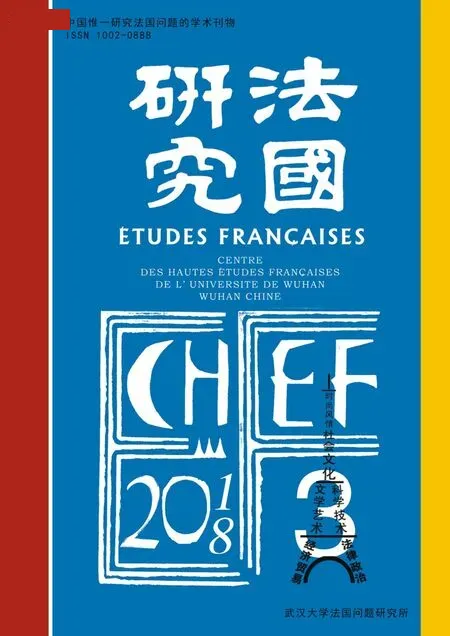亨利与露露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两种生存状态:萨特小说《闺房秘事》解读
2018-04-03李克
李克
《闺房秘事》写了四个人物,亨利和露露是主要人物。
小说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没有感人至深的抒情,没有大时代的宏伟叙事,没有吸引人的悬念故事。小说描写的是一连串的家庭琐事,呈现的是夫妻间的“恩恩怨怨”。存在主义在选材上“躲避”宏大叙事,关注个人,偏重“琐碎”。存在主义在题材开掘的深入与艺术表现的细腻方面见长,“细微琐碎”构成了存在主义小说艺术的表现风格,这一特点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亨利
亨利有一个高大身材,但给人的感觉不是伟岸,而是笨拙。在露露眼中,这个大个子软绵绵的,缺少男子汉的刚毅。
亨利很不幸,年纪轻轻就丧失了男人的功能。睡在露露旁边,一合上眼,“就觉得浑身上下被纤细而结实的绳索绑住,连动一动小指头也不可能。”①郑永慧译《闺房秘事》见《萨特小说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以下引文不再注明。与一般男人不同的是,患上了阳痿的亨利行若无事,一点不着急。晚上露露碰到他的身体,他会脸红,“把头转过一边叹气”。亨利的原则是随遇而安,得了这种让很多男人着急上火的病,可他的心态真好,既不求医,也不问药,没有焦躁,他坦然接受命运安排的一切。
亨利并不一概排斥性事,他喜欢紧贴着露露背后,挨着她的屁股。这样做使露露意识到“有一个屁股而羞愧得要命”,这种“羞愧”会让亨利莫名其妙地兴奋。露露对亨利这一难得的“嗜好”非常厌恶,不喜欢别人接触背后,因为她无法看见背后的人,而背后的人却能够看清楚她,随意上下其手,她却“不能预见它们要到哪里去”。由于看不见也无法预测对方,露露处于被动中,她讨厌这种状态。
亨利爱好虚荣,喜欢装腔作势。露露称其为“格利弗”,他就高兴得不得了。这是《格列佛游记》主人公的名字,亨利并不是对这部小说感兴趣,而是因为这是一个英国名字,露露的发音带一点外国口音,亨利听了舒服,觉得很文雅,显得受过教育。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节上,亨利常常纠缠不休,埋怨露露不够高雅。可在露露眼中,亨利邋遢庸俗,没有情趣,缺乏高贵气质。他们外出逛街,亨利不停地上厕所,露露颇不耐烦,站在橱窗外张望。一会儿亨利出来,样子真让人倒胃口:他“一边拉着裤子一边走出来,两条腿弓成弧形,像个老头子似的。”
亨利为人懒散,不拘小节,但顾及脸面。他与露露弟弟吵架,认为这个小家伙没有教养,教训一下是理所当然。但没想到,这个毛头小子非但不听劝,还顶撞他,竟然骂他“大傻瓜”,这种忤逆天理的行为惹恼了他,气头上打了对方一耳光。露露大怒,但不动声色,使了个诡计,诱骗亨利到阳台,随即把阳台门锁上,把亨利关在阳台上,一关就是一个多小时。亨利愤怒了,他穿的是睡衣,冷得发抖,在阳台外使劲比划,挥舞拳头,不停地咆哮威胁。但是再愤怒,他也不会把阳台玻璃砸了,这一点露露拿捏得很准。在她眼中,亨利是一个吝啬鬼,胆怯得很,行动绝不会越轨。如果换了是她,盛怒之下,早就把阳台玻璃砸个稀巴烂了。
正当夫妻“酣战”之际,来了一对老夫妻,亨利立刻满脸堆笑,在阳台外点头哈腰,向他们鞠躬致敬。看到这一滑稽场面,老夫妻只好隔着玻璃向亨利致意。露露把阳台门打开,亨利笑呵呵地回到屋子,当着他们的面吻露露,称她为“小淘气”。老夫妻前脚走,后脚这出滑稽戏立刻落幕,亨利的笑容烟消云散,一拳打中了露露的耳朵。露露当然不甘示弱,顺手抓起一把刷子,狠狠地朝亨利的脸上打去,把他的两片嘴唇打裂了。亨利的婚姻有名无实,但他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需要一个家,这是生活的常规。大家都有一个家,他既然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就应该与大家一模一样。
后来露露离家出走,大街上被亨利撞到,他抓住露露的胳膊,大声咆哮:“同我回家,我是你的丈夫,我要你跟我回家!”亨利对露露的朋友莉雷特说,“她是我的妻子,她是属于我的,我要她与我一起回家。”在亨利眼中,这个世界有一套规矩,不容侵犯。规矩就是规矩,就是让大家遵守的,不遵守还叫规矩吗?亨利坚定地捍卫生活中的一切规矩,所以他打了露露,依然理直气壮地向她吼叫,“你是属于我的!”
大男子主义给亨利这个孱弱的男人提供了底气,当然,他很识趣,会做出让步。他答应不再管露露弟弟的事情,永远不说露露母亲的坏话。对于亨利的妥协退让,露露没有丝毫感激,她对于在这种状态下承担夫妻责任“并不愉快”。她看得很清楚,亨利需要的不是“她”,而是他的“妻子”,亨利要把她纳入特定的社会角色才称心如意。作为丈夫,亨利没来由地总是认为自己足够聪明,总是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这是露露最反感的。她认为,只要亨利“不那么高傲地对我,她还会同他在一起。”
亨利欣赏瑞士人,尤其是日内瓦人。在小说的表现下,瑞士人的特点是“木头木脑,很有气派”。亨利喜欢这种僵硬得像木头一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守规矩,一成不变,心地善良,忠厚老实。亨利喜欢的一个卖花女人就是瑞士人,无独有偶,他的姐姐嫁给了“高贵”的瑞士人,并且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与姐姐相比,亨利感到不幸,他一个孩子也没有,而且露露不像传统妻子那样循规蹈矩,对他百依百顺。当露露决定摊牌,明确说已经受够他了,准备离开他。亨利怎么办呢?他“恨不得一连睡它八天”,把事情拖下去,把哀伤慢慢冲淡。或者哭泣闹腾,用自杀相威胁。露露对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做法感已经到麻木和厌倦了。
亨利还有一个特点,即纯洁。露露与亨利分手后回到家里,看到亨利“笔直地躺在床上,仿佛有人把一根木桩放在床上。他像他同瑞士人说话那么僵直。”露露两只手抱着他的脑袋,对他说,“你是纯洁的,你非常纯洁。”在存在主义语汇中,“纯洁”并不是一个褒义词,说一个人纯洁,并不是说他特立独行,出污泥而不染。从存在主义观点看,纯洁意味着单一乏味、排斥变化、甚至不能变化,这是人的严重缺陷。纯洁的人是单调和僵硬的,他们固守自己的贫乏天地,缺乏应对挑战的能力。说一个人纯洁,是指他缺少改变和提升自己的能力,他懒惰,得过且过,拘泥不化,满足于“静止”状态,不知不觉地自甘堕落。露露在指出亨利是纯洁的之后,加了一句:“也有点懒惰”。
亨利接受现成的一切,被种种规定充实,其存在已经“死亡”。亨利没有激情、没有欲望、被动无能,这是一个从内到外都被窒息、在禁锢下无法动弹的人。最可悲的是,他对自己的状态完全麻痹,没有反省。亨利在生理上是阳痿的,精神上是木然的,精神和肉体“交相辉映”,展现的是一个典型的“木头人”。在萨特笔下,这个人物有生命,体现的却是衰亡。他哭泣、愤怒,展示的不是力量,而是无奈。他经历了一系列活动,显现的只是麻木和单一。
二、露露
亨利的身体像块木头,露露则相反,她的身体如橡胶一般富有弹性。亨利身材高大,像过期的花朵,蔫头耷脑,已显枯萎。露露则不同,她的身体无论从前面还是侧面看,都表现了“令人惊讶的性感”。她穿上紧贴肉身的裙子,屁股在瘦腰下面圆溜溜的,装满了裙子,“简直可以说是塞进去的,还拼命扭动。”露露的四肢很长,柔软而消瘦,像黑女人的身体。在朋友莉雷特眼中,露露的身体“总有点下流”。
露露的生活总能引发一连串的惊讶,不是她特意谋划、专门制造惊讶给别人看,露露并没有要引起别人关注的意图。对她而言,惊讶是在别人目光里显现出来的,它们仅仅是别人的惊讶,对露露自己,一切都很自然。在人们眼中,露露总是生活在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不合适”中,她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不恰当”,她常常自然而然地越出常规。
露露活力四射,和亨利这样僵硬得如同木头一样的男人能生活在一起吗?奇特的是,尽管亨利年纪轻轻就犯了阳痿,露露却不当回事,她不像一般妻子那样四处奔波,为丈夫治病。让人不解的是,她甚至没有觉得亨利的缺陷会影响婚姻。小说开篇的描写是:露露仰天躺在亨利身边,把左脚拇指伸进被单的一个裂缝,她的脚趾“悠然自得”地“把线扯开一段,以感觉线的断裂。”露露悠闲自在,心无旁骛地营造自己的“安乐窝”,她在被单的一个裂缝中随缘作乐,她的脚在被单的小缝隙里享受着游戏的乐趣。
露露太熟悉亨利软绵绵的身体了,肉体全是灰色,只有肚子是粉红色。她像擦拭一件东西一样,把这具身体揩得干干净净。她把亨利的身子翻转过来,拍打几下屁股。亨利母亲来看望他们,露露找个借口,退下被单,故意把这个大个子的身体露出一截,让她看见亨利的裸体。露露心想,她一定会大吃一惊,“她大概十五年没有看见他这样子了”。露露不是恶作剧,也不是穷开心,她就是想这样做,不知不觉地想这样做,因为生活的常规不允许这样做。哪一个妻子会把丈夫的身体当“玩具”?哪一个妻子会随随便便把丈夫的裸体展示给人看呢?常规不允许这样做,露露偏要“不经意”地这样做,这样做才能得到乐趣,随随便便、不知不觉地违背常规就是露露快乐的秘密源泉。
当然,露露也会用手慢慢地摸着丈夫腰部,“到了鼠蹊处捏了一下”,这时亨利咕噜一声,终于有了一点反应,可是身子却动也没有动一下。遇到这种事,亨利的身体像一块厚实的橡皮,对一切都绝缘了。露露知道,他们不可能有孩子,对于别的夫妻,这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没有孩子,婚姻还能维持吗?不要后代,为什么还要结婚呢?露露对这些在常人眼里是天大的问题没有一丝兴趣,她没有因为不能生孩子而嫌弃亨利,更没有因此抱怨自己的命不好。露露没有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欠缺,与正常人比较,她的生活如此“畸形”,她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严重问题。躺在亨利旁边,与这个柔软而无法动弹的僵硬身体比较,她发现自己的身体和动作都很灵活,这让她高兴。
亨利昏昏睡去,露露没有一丝睡意,她的意识异常活跃,脑子根本停不下来。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是肚子叫,她有点恼火,因为“分不清楚是亨利还是她的肚子发出的声音”。每个人的肚子都一样,里面有一大堆管子,不知疲倦地发出咕嘟声。露露想,亨利爱她,但爱她的一切吗?譬如,亨利也爱她的肠子吗?把她的肠子装在瓶子里拿给亨利看,他一定大眼瞪小眼。对于不认识的东西人们也能够去爱吗?如果像俗话所说的,爱一个人就应该爱他的一切,那么,食道、肠子和肝脏等也应该成为被爱的对象。可是人们很少见到它们,根本不认识它们,怎么去爱呢?人们能够爱他们不了解、不认识的东西吗?要是人们能够经常看见这些东西,就像经常看见胳膊和大腿一样,说不定人们就会爱上它们。这样看来,海星的爱就比人类的爱更彻底。每逢太阳高照,它们躺在海滩上,把内脏拿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海星能够把自己的一切都摊开在眼前,没有什么秘密需要遮掩。人能够像海星那样把内脏拿出来吗?从哪里拿出来呢?从肚脐吗?人的特点是把许多东西包裹起来,只剩下一个外壳,爱人就是爱这个外壳,至少爱要从这个外壳开始。爱人实际上只能爱人的一部分,不可能一下子爱人的全部。爱不能贪婪,不能要求对方一五一十地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陈列在眼前,人无法像海星那样把自己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人有许多东西不可能一眼看透,因为人的存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就像冰山那样,显露在外面的只是一部分,其它部分总是“秘不示人”。由于人的存在无法那么“实在”,不能被“凝固”,所以人必定是千变万化的,永远不会固定在一个点上。
露露闭上眼睛,脑海里出现了莉雷特,“每天晚上她总是在同一时间去想莉雷特”。刚开始出现的是卷曲的头发,接着出现了“一只鲜红而带金黄色的耳朵”,后来听到了莉雷特又尖又清晰的嗓音。露露已经结婚,但仍喜欢与莉雷特在一起。莉雷特身材壮硕,“肩膀肥而光滑”。她爱上了别人,露露理解这一点,她不想也没有办法阻止莉雷特爱上别人。可是一想到莉雷特爱上别人,她就伤心不已。一想到那个男人怎么抚摸莉雷特,莉雷特怎么喘气,她就“心烦意乱”。她想知道莉雷特的一切,但始终保持着界限:即使“给她全世界的黄金,她也不会碰她,因为她不知道拿她怎样办才好。”露露想着许多事物,想着女人,她的手顺着平坦而漂亮的肚皮往下挪,接着就感到快感,这是她给自己的快感。
露露神思畅游,她的想象也会遇到“抵抗”。想象中什么都可能发生,谁也无法预测下一步出现什么。如果出现的是一张脸蛋,不会引起什么不安,但如果是一些肮脏和恐怖的记忆,就会惹来烦恼。露露认为,对男人的一切都熟悉,尤其是连那个都熟悉,是很可怕的。“那个东西如果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倒还好,如果像个畜生似的蠢动起来,坚硬起来,真叫人害怕。”有鉴于此,露露对爱的认识是,“爱,真是肮脏事。”他喜欢亨利,就是因为他不会让她担惊受怕,不会把她弄脏。亨利像一个神甫,穿着长袍,把自己包裹起来,这使露露感到安全。亨利作为一个男人徒有其表,这对于露露反倒是件“好事”,她甚至说,“我爱亨利是因为他阳痿”。从这一点看,亨利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对象。
当亨利独自酣睡,露露心烦意乱,四顾茫然,她也会动怒,骂一味酣睡的亨利是“笨蛋”。夜深人静时露露对亨利也有期望:要是这个笨蛋“搂住我,哀求我,对我说,你是我的一切,露露,我爱你,不要离开我!”那么,她的心会软下来,她会为她做出牺牲,留下来和他在一起,“甚至用一生来讨他的喜欢”。可是,露露听到的只是鼾声,看到的是这个大男人僵尸般顽固的躯体。
露露身上各种特质不是一个一个清楚地呈现出来,而是奇特混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使她的存在始终是模模糊糊的。譬如,露露不满亨利,决定离开他,但又“怜悯”亨利,最后回到他的身边。露露的许多做法无法用一根标尺去衡量,她总是处于反复和矛盾中,她的行为常常前后不一。她刚刚做出一种选择,随后就被推翻、被否定。她的行为让人们惊讶不断,其存在处于不断折腾的“模糊”地带。她不是那种个性鲜明、有棱有角的人物,或者说,她既是个性鲜明、有棱有角的人物,又不是个性鲜明、有棱有角的人物,其存在总是处于对自己的不断否定中。
传统文学塑造的往往是个性鲜明的人物,这类人物之所以个性鲜明,前提是他们受到强力本质的制约,致使人物性格得到统一,显现出主导的一面。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不是某种固定的模块,人应该不断超越、不断更新,始终处于变化的超越中。相应的在文学创作上,存在主义不主张塑造传统意义上个性鲜明的人物,而力倡塑造变化的、模糊的、无法或难以清晰定义的人物,露露的形象就诞生于存在主义这一思想土壤上。
三、莉雷特与彼埃尔
莉雷特和露露交往多年,俩人无话不谈,可谓知心朋友,但她们性情和趣味差别很大,实则为两类不同的人。
莉雷特坚持原则,在她看来,露露早就应该结束这段婚姻。
首先,露露根本不爱亨利,她只是为了体面才同他在一起。如果不爱一个人,还与他待在一起,这就是“罪恶”。莉雷特认为,两个人不合适还要纠缠在一起,就违背了道德,而违背道德就是罪恶。露露与别的男人交往,背后还说亨利的坏话,但只要人家把她称为“夫人”,她就认为这些都不算什么,莉雷特认为露露根本不爱亨利。
其次,亨利不值得爱,露露没有权利为一个阳痿的男人毁掉自己的一生。莉雷特最恨生理有缺陷的男人,因为这关系到幸福。露露可以对其它事情马马虎虎,迁就忍让,但没有权利把自己的幸福当儿戏。
第三,露露在婚姻上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关键是她“根本不知道怎样才算是一个美男子”。如果一个女人脑子里没有一个好男人的清晰概念和恰当标准,婚姻必然一塌糊涂。露露之所以找亨利这样阳痿的男人结婚,犯这种对于婚姻是致命的错误,就是因为糊涂,她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莉雷特建议,露露应该找彼埃尔这样的男人结婚。彼埃尔聪明,会关心人。而且有钱,有能力关心人。彼埃尔懂得说话的艺术,能说一大堆甜言蜜语讨女人的欢心,而且他穿着考究,衬衫、鞋子、领带等都是一尘不染,浑身上下散发着英国烟草和科龙香水味。彼埃尔完全符合一个好男人的标准,露露应该找这样的男人定终身。
莉雷特作为精明的销售员,自诩是一个不错的观察家,但现在她犯难了,因为她发现,露露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露露的许多表现让莉雷特越来越惊讶,越来越把握不住,甚至她到底是喜欢还是讨厌男人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莉雷特越来越吃不准了。本来凭着细致观察,她形成了对露露的一套看法,并且把它归纳到一个“模式”中,她认为这套模式对把握露露非常合适,简直可以说是专门为她量身定做的。然而一回到现实,她发现露露总是轻易地就超越了她辛辛苦苦打造的这一模式。她虽然费尽心思对这套东西修修补补,但显然还是跟不上露露的变化。她发现自己经常陷入不尴不尬的境地:她刚想谴责露露,又发现她很有趣,露露老是处于微妙的模糊中,处于对清晰概念的不断闪躲中,总让人产生不能痛痛快快、直截了当地“抓住”她的烦恼。总之,用固定清晰概念衡量和检验露露非常困难,露露在这些概念面前像一条经验老到的泥鳅,不声不响,自自然然地一下子就滑走了,不留下一点痕迹。应该说这不是露露的深思和筹划,而是她“无为而为”的做事效果。露露永远不走清晰路线,她的生活飘忽不定,总是含含糊糊,模模糊糊,好像是这样,似乎又是那样,究竟是怎样,总是模棱两可,不清不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她与大家确实不一样,她既不同于亨利,也不同于莉雷特。
露露离家出走,马上与彼埃尔取得了联系。彼埃尔朝思暮想得到露露,他把露露安排在一间破旧不堪的旅馆,楼梯和铁床都嘎吱嘎吱作响,还有那个不怀好意的阿尔及利亚门房,老是窥视露露,目光在她的大腿上扫来扫去。彼埃尔一进门就干那种事情,他在房间里待了两个小时,铁床也响了两个小时。彼埃尔强壮,干这种事“充满诗意”。做完之后,“像一只刚挤完奶的母牛那样轻松”。他换上漂亮的衣服,扬长而去,经过窗户还吹着响亮的口哨。露露浑身发冷,想到以后每一个夜晚都要这样度过,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最让露露不满的是,彼埃尔沉重地压在她的身上,她不得不喘粗气。他像发现了一件宝贝似的叫唤起来:“你发出快活的声音了,你有快感了。”彼埃尔认为亨利无能,只能由他来给露露制造快感。露露承认,彼埃尔确实比亨利更懂女人,他把女人当作一架乐器,会因为自己懂得流畅的弹奏而洋洋自得。但露露并不因此对他有一丝感激,相反,她恨彼埃尔,因为她的处世原则就是反对被操纵,哪怕是在做爱中被操纵。
四、露露存在的意义
露露的存在像流动的水,没有固定形状,没有稳定边界,让人难以捉摸把握。她身上随时会涌现一连串的相异性,这个充满活力的女人永远不能“恰到好处”,永远不知道什么叫“恰如其分”。她的存在不是要回答“我是谁?”而是趋于指向“我不是谁?”露露的存在意义是挑战、是冲击、是破坏,萨特塑造的是一个把不要规范作为规范的典型,是一个把永恒的流动性作为理想的范本。这个形象的意义是在昭示,一种模糊性的存在比一种确定性的存在更具生命的力量,一种没有形状、没有边界、无法定型、不断变化的存在,比亨利“僵硬”的木头式的存在更具活力。
从正常世界的视角看,露露没有自己的事业,她的婚姻糟透了,这个女人一事无成,她的存在是一连串的失败。按照传统标准衡量,露露只是一个不幸的失败者,她身上哪有什么值得自豪称道的地方?哪有什么幸福和自由可言?但从存在主义视角看,露露的存在具有特殊魅力。露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正常女人,一个变态女人?一个爱丈夫的女人,一个出轨的女人?一个同性恋者,一个手淫者?一个敢做敢为的女人,一个犹豫不决、患得患失的女人?一个善变的女人,一个随波逐流者?一个缺乏理性的女人,一个过于自信的女人?……这样的界定和疑问可以不断提出来,露露与所有这些定性有关,但又不是其中任何一个定性。露露的存在拒绝合适、恰当、单一的定性和定位,她的存在犹如流动的水,无法在任何一个点被凝固,用存在主义术语讲,就是拒绝本质化。
拒绝本质化是存在主义的自由底线。在一个逻辑和理性的世界中,拒绝本质化意味着拒绝存在的确定性、清晰性和稳定性等,意味着把存在导向流动性和模糊性,它们都是确定性的有力“杀手”。流动性是对规则世界的冲刷和肢解,模糊性是对一个棱角分明世界的悄然解构。波伏娃指出,“存在主义一开始就被定义为一种模糊性的哲学。”①波伏娃:《模糊性的道德》。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2013,6页。存在主义青睐模糊性,认为模糊性才是这个世界的根本性质。传统哲学一开始就力图消除世界的模糊性,用各种方式把世界还原为单一的精神或物质。传统哲学的任务是为建立和展现一个清澈透明的世界奠定基础,在存在主义看来,这种做法是本末倒置,因为模糊性才是世界的真理,是世界的真正本源。从这一立场看,人的存在不仅是变化的,而且变化是模糊的,人的存在永远不会变成“清澈透明”的。
传统哲学与存在主义都讲变化,但它们的分歧更重要、更有意义。传统哲学认为,变化是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变,是从一种规定性向另一种规定性变化。变化是规定性的变化,变化只是在肯定本质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在这种思路下,变化本身并不被看重,看重的是变成了什么、形成了什么样的规定性、最终结局是什么。在存在主义看来,传统哲学所说的变化局限于物,只能用来说明物的变化。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变化,这种变化永远不会与自身一致。变化总是意味着变成什么,对人而言,变成什么不是目的,变化本身才是重要的。对于人,变化永远不会变成一个纯粹的东西,不会变成一个十足的肯定性,不会变成一个僵死的规定性,不会变成一个与自己的存在完全一致的东西,不会变成一个不会变化的东西。或者说,人的变化永远不能消除变化本身,人的变化永远停留在差异上,永远造成差异,永远在差异中运行,人的变化永远不会“死”在本质的规定面前,不会用本质的高墙封死变化的可能性通道。存在主义强调,变化比凝固的本质更为重要,不确定性要先于本质的确定性,变化带来本质,又超越本质,变化才是一切。存在主义对变化的界定必然把模糊性注入存在,这使人的存在必然处于绵绵无尽的永恒变化中。
在传统文学观下,露露这样的人物由于缺少本质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处于缺少理性统驭的幼稚状态,其存在样态很容易被判定为不成熟。这样的人物塑造在艺术上令读者无所适从,很容易被判定为艺术创造的“失败”。但从存在主义艺术表现的视角看,露露这样的人物具有更真实的存在形态。由于模糊性成为生命本身的样态,偶然性成为存在的常态,露露的形象别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