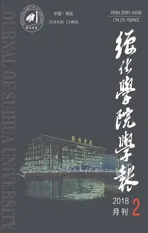“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家认同的导向作用
——以跨界民族为对象的研究
2018-04-03丁洋洋赵志朋
丁洋洋 赵志朋
(1.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大连 116000;2.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吉林长春 130117)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党中央总揽内政外交的全局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出访哈萨克斯坦时着重提出,并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我国主要的外交策略,中心内容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以构建中国与周边相关国家的密切联络为重要目标,以创造适应中国发展的良性国际及周边环境为长远打算。
我国自古至今一直是多民族的国家,并且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56个少数民族中就包含了30多个跨界民族。我国的陆路边境线长达2.2万多公里,与包括朝鲜、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在内的14个国家接壤,分布着包括朝鲜族、蒙古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苗族等跨界民族。沿路地区较为和谐的民族关系和稳定的边疆局势,为“一带一路”等重大政策和措施的出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1]“一带一路”不仅覆盖了新疆、西藏、内蒙古、广西和云南等主要民族省区和大部分民族聚居区,相关各国的边疆地区也都处于“一带一路”范围之内。我国跨界民族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虽然拥有不同的国籍,但是他们不仅语言相通、宗教相近,并且文化习俗及民族归属感也大同小异,交往频繁、彼此关注,较为熟悉当地的历史背景及风土人情。跨界民族的这些属性体现其在“民心相通”方面能够展现出先天优势。
一、跨界民族的内涵及其国家认同特殊性
对于跨界民族的理解,应该从其形成的角度去定义。跨界民族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有特定语言和文化习俗的族类划分,而是拥有共同聚居特征的群类划分,是民族与国家在历史过程中矛盾与融合的结果。民族与国家都是相对独立的范畴,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和活动情况与国家的政治疆界都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发展过程中,致使两者有重合之际也有交错之时,造成了一种民族跨多国而局的现象,从而形成了跨界民族(Trans-nationality)。跨界民族不仅是人类民族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及世界地理分布的特点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中既普遍存在又兼具多重特殊性的群体。跨界民族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同一跨界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同一原生态民族;二是同一跨界民族居住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而且聚居国的边界是连在一起的;三是同一跨界民族成员拥有不同的政治身份或国籍;四是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特殊性。
认同是人类独具的意识活动,是心理和情感上的趋同过程,由于现代人类拥有多重属性,每一个方面都有相应的认同表现,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与国家认同(nationalidentity)。一切群体性的认同都具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归属于这个群体的具有辨识性的标志,二是有不同于这个群体的“其他”的存在。国内学者对于国家认同的理解从各自的学科角度有所差异。沈桂萍认为:“国家认同是将国家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政治认同建设和文化认同建设是其核心内容。”[2]贺金瑞则认为:“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3]美国学者莱恩看到了国家认同是一种运动变化的过程,即“国家没有稳定而自然的认同,相反的,国家认同通过话语而被不断的协商。”[4]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国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对跨界民族的政治文化的塑造结果,这是一个长久的构建、排斥、内化和差异的反复过程。
“国家认同”可以理解为三个层面,分别是意识、追求和赞同,是公民从思考、立志到行动的过程。首先个体的人被赋予了国家公民的身份,会对这个国家的综合构成要素如性质、制度和文化进行评价和接纳,建立了个人的政治心里和政治意识;然后公民在对自己的国家和公民身份有了明确的认知之后,自然地把个人利益从属于国家利益范围以内,共享国家利益和维护国家利益成为政治追求;国家认同还是一种政治赞同,是心理状态与行为实践的统一,公民对所处于的政治体系作出反应,包括政治系统的制度、政策和管理等方面,趋于赞同和支持的意识及采取的相应举动就是国家认同的表现形式。公民从思考、立志到行动的整个过程,就是国家认同赋予国家公民的基本政治生活。
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民族与国家的交错关系在“认同”问题上总是会有碰撞,在特定群体尤其是跨界民族身上体现的更为复杂。[5]跨界民族成员作为国家公民,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多元的价值冲击,感受到了“差异性”的体验,逐渐认识到本族文化、传统及认同的“独特性”,不由地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和产生民族归属感,这既是民族成员的社会化也是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属性与公民身份是跨界民族认同的基础,民族交往与国家生活是跨界民族认同的路径,而认同差异是跨界民族认同的结果。对于跨界民族来说,其民族属性是先天赋予的,国家公民身份虽然也不是自己选择的但是会有更改的可能性,所以民族属性更为稳定,但是跨界民族能够与不同民族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并且共存共荣,说明公民的政治属性要高于民族的自然属性,那么国家认同大于民族认同才是较为合理的。
二、跨界民族的外交优势及其引导
在“一带一路”的宏伟部署中,跨界民族能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首先在民族交往方面,想要得到相关国家切实的认同和接受,必须要对其历史、国情和风俗等人文知识具体掌握,跨界民族与周边国家同族拥有基于族群渊源的共同认同感,可以充分利用与周边国家同宗同族的民族身份,冲破国家之间的交流障碍,为深度合作搭建精神桥梁,扮演和平及友谊使者的角色;其次在经贸交往方面,跨界民族凭借其民族习惯及语言优势,要广泛地参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中去,跨界民族领袖要起到带头的模范作用,让经贸交往更加顺畅和高效;再次在宗教信仰方面,“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不仅民族种类繁多,而且宗教信仰复杂,有些地区还是宗教发源地,每个国家都极其重视宗教,甚至有些国家还是全民信教,我国作为无神论为主流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与其经贸合作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宗教问题,而同一跨界民族往往是信奉同一宗教的,在消除矛盾阻碍和创造更深度更有效的交流合作上,跨界民族是不可或缺的沟通枢纽;最后在地区治理方面,“一带一路”事业少不了中央和地方的双层监督和管理,尤其是边境地区基层政府更是面对极为繁琐和具体的工作,尤其是对跨界民族人口的无序流动经常是手足无措,如果能够使跨界民族成员作为基层的管理者,那么不仅对国内的边境稳定大有裨益,并且对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能够提供更多方便。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跨界民族属于国际性的民族,它具有跨地域性、政治上的割裂性和社会心理的复杂性等特点,跨界民族之间的互动也是一把双刃剑,[6]积极的方面肯定是促进了相关国家的文化和经贸往来,消极的方面就是国家认同与民族向心力在民族利益诉求过程中进行角逐,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我们称之为跨界民族问题。跨界民族问题的负面影响主要在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两方面,这些问题不仅会破坏国内稳定的政治生活环境,还会造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误会及摩擦。
如何能够使中国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走偏路,发挥积极的、有效的及爱国的正能量,那就需要国家认同对跨界民族的正确导向。首先,加强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有助于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跨界民族自觉的国家认同能够保障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树立中国的民族形象,并且能够预防和抵制国外某些不怀好意的民族分裂势力的渗透,和谐的社会环境亦是周边国家能够与我国加强贸易往来的定心丸;其次,加强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有助于经济建设的长远发展,跨界民族自觉的国家认同使他们与所有中华民族成员一样,拥有共同的国家奋斗目标,在“一带一路”事业中自然会主动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再次,加强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有助于我国民族关系的深化和中华民族的崛起,和谐的民族关系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并且缓解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压力,减少后顾之忧,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环境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
三、结语
加强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十分重视的民族工作,在新形势下,基于“一带一路”事业的战略需求,更加彰显了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加强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建设,坚定不移的实行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要充分的发挥和调动中国跨界民族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并且更多地关注于培养跨界民族人才,让跨界民族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够完全地释放民族优势,使“一带一路”战略能够顺利地推进。
当代世界格局在不断的变化和转型,民族交往及相互认知的情况也更加复杂,理解与包容显得格外重要。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发起国,我们还要充分尊重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这不仅包括我国的跨界民族,还有“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中涉及的周边国家的众多民族。我们在加强我国跨界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同时,也要对“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和地区对跨界民族及边疆治理的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包括治理的理念、民族的政策和治理的模式,以真实的经验为借鉴基础,解决好现实问题。我国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下,不仅要带动多边的经济发展,如果能够与周边国家共同治理跨界民族问题,那将是一举多得的成功国际范例。
[1]李梅花.“一带一路”与跨界民族社会文化结构的改造与创新[J].贵州民族研究,2016(1):12-13.
[2]沈桂萍.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国家认同问题[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2):55-56.
[3]贺金瑞.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3):6-7.
[4][美]M.莱恩·布鲁诺.记忆的战略——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修辞维度[M].蓝胤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66-70.
[5]刘永刚.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与公民身份建构[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4(9):65-68.
[6]黎海波.“一带一路”战略下“跨界民族”概念及其逻辑连接[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7(1):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