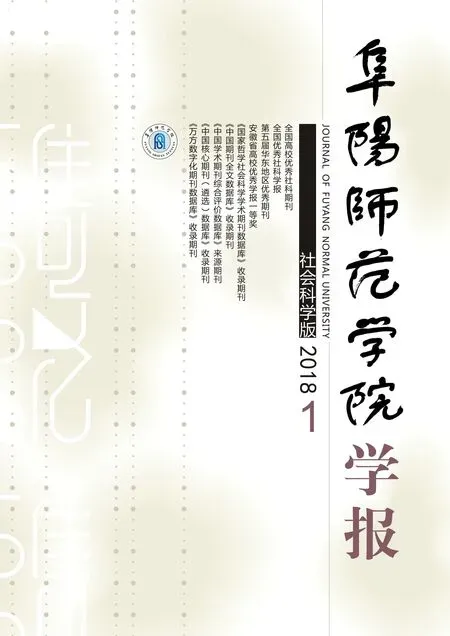行进中的寻找——探析戴厚英“知识分子三部曲”的思想历程
2018-04-03王亚楠
王亚楠
行进中的寻找——探析戴厚英“知识分子三部曲”的思想历程
王亚楠
(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戴厚英在“文革”结束后创作的《诗人之死》《人啊,人!》和《空中的足音》,被称为“知识分子三部曲”。作品审视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走过的道路与精神历程,包含着戴厚英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反思。同时,通过“知识分子三部曲”,可以了解作家在那个时期的思想历程,认识一个更真实的戴厚英。
戴厚英;知识分子三部曲;反思;思想历程
戴厚英(1938-1996),安徽颍上人,是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坛的小说领域里第一个呼吁人道主义的作家。她曾在“文革”期间犯下错误,做了一些那个时代的人独有的疯狂举动。十年“文革”结束后,思想逐渐成熟的戴厚英反思走过的道路,深刻地剖析自己,把自己完全暴露在阳光下让众人检阅。她以人性的自省接连创作了《诗人之死》《人啊,人!》和《空中的足音》,统称为“知识分子三部曲”。这些作品饱含着作家个体生命的遭际、对社会历史的理性思考以及心灵的忏悔,是戴厚英用血泪换来的人生领悟。通过梳理“知识分子三部曲”,不难观测到戴厚英从简单到深刻、从迷茫到清醒、从冲动到理智的思想历程,同时也呈现了一个坚守人性、不断思索的戴厚英。
一、情感的倾诉:《诗人之死》
《诗人之死》是十年“文革”后戴厚英的第一部作品,于1980年完稿,也是她发出的“第一声长哭”。当时的文学界和出版界都刚苏醒,长篇小说创作极少,《诗人之死》应是“文革”后第一部涉及“文革”的长篇小说。故事以戴厚英与诗人闻捷的恋爱故事为原型,讲述了滨海市文协的一批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迫害。小说真实还原了两人从相爱到后来受到“四人帮”的迫害、闻捷被逼自杀的真实经历。女主人公向南是《滨海文艺》的诗歌编辑,凭着自己的闯劲与能言善辩,被任命为“最重要的专案组组长”,负责审查“黑线人物”余子期。一直以来,向南都将“听话”和“服从”作为准则,对“文革”深信不疑。但无休无止的批判运动使她困惑不解,尤其是在专案组审查余子期时,她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一次次拷问自己。她被眼前这个真诚善良的人所打动,“对余子期的深切同情已经在思想上完全占了上风”[1]90。由于向南对余子期的种种袒护,她被定罪为“思想动摇”“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放牛棚与“牛鬼蛇神”一起接受改造。在牛棚里,对余子期进一步的了解让向南更加感受到政治的荒谬,她由一开始对余子期的深切同情,逐渐发展成爱情。最终两人爱情的无果迫使诗人选择了一条极端的道路,以死捍卫了自己高尚的品格,也将任凭政治摆布、思想处于迷惘之中的向南唤醒。
“文革”结束后,绝对化的思想观念逐渐消散。“人们以各种方式来言说他们对革命的理解和想象,表达对革命价值和内涵的反思、调整或修正。修正的主导思想是背离甚至反叛‘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试图为革命话语恢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维度,将‘人’从阶级性话语的覆盖和淹没中剥离出来,恢复真实的人性情感和欲望。”[2]62-70于是,被“文革”压抑得太久的人们终于获得了解救。大批作家纷纷拿起笔,声讨这场浩劫。戴厚英自然也清楚这个时代的规律:“文革”的结束不仅意味着中国历史的转折,也是个人的转折,必须对过往进行彻底清洗[3]198。戴厚英在“文革”中跌宕起伏的经历和闻捷的自杀无疑是她一生无法摆脱的梦魇。但也因这段际遇,给她带来了超于常人一百年的领悟,让她清楚地看到了个人的脆弱、人性的恶毒和政治的残酷。她开始了自我剖析,把人生遭际与领悟融入到艺术创作中,完成了“文革”后对历史和现实的初次反思。《诗人之死》原来的书名取为《代价》,也可见戴厚英的创作意图是表现“个体生命存在为填充历史的某种随意性、荒谬性的骇人深渊所付出的代价”[4]19-23。在作品中,戴厚英将对诗人由憎恶发展到尊敬、由理解而萌生爱情的过程摊开给众人看,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极度彷徨与困惑,长期处于“黑暗之中”的戴厚英。正如贾植芳先生所言:“这其实是一种人性的复苏。”[5]10戴厚英更是以在章节末放上“一封信”的方式,用主人公向南的口吻,抒发心中郁积着的情感,痛斥极权政治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也以此证明了她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考力、有价值的人,而不再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
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最初的几年,对“文革”的反思主要体现在对“四人帮”的批评,大家普遍认为是这几个野心家造成了“文革”的灾难[6]9-13。当时的文学作品大多采用一种“少数坏人害了多数好人”的泛道德模式。如在古华的《芙蓉镇》中,将造成小镇动乱和好人受苦的原因归之于“坏女人”李国香的恶劣品格。《诗人之死》中,余子期的妻子被迫跳楼自杀后,她的女儿晓京从开始的迷茫无助到最后“慢慢想通了”,认为:“我没有害妈妈,是坏人害的。我恨他们。我只想和他们算账,感情上就不那么折磨自己了。”[1]267连向南也表示“总有害群之马”,并自认为:“我向自己的心灵深处挖下去,可是挖不出一丝一毫反革命的因素,却又看见了那一颗可贵的种子。”[1]196戴厚英在她发出的“第一声长哭”中虽然倾诉了真挚的感情,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自我剖析与反省,但也许是受到当时环境的局限,创作时间也较早,且基于自身经历的书写,更偏重于情感倾诉而非理性客观,她的初步反思只停留在社会层面,并不够透彻。时代自然是造就悲剧的原因,但并不是唯一,历史原因造成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丧失也值得探讨。
《诗人之死》创作完成后,戴厚英自己也觉得不尽人意,她在自传中表示这部作品“留有教条束缚的痕迹,流露出的感情也缺少节制”[3]180。可它确是在当时的中国“持否定‘文革’观点创作较早的三部长篇小说之一(另两部是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将军吟》和《春天里的冬天》)”[7]24-29,是作家“灵魂出窍”后自我本真的展示。也是因着这部作品,让戴厚英于不惑之年走上创作之路,才有了后来轰动一时的作品《人啊,人!》。
二、沉重的反思:《人啊,人!》
“文革”结束后,由于戴厚英“文艺哨兵”的特殊身份,她一直身处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不断接受审查。她的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因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迟迟不能出版。也因“身份”问题,戴厚英的原单位,恢复以后的上海作协明确表示不再接收她,其他单位也因受“某种压力”不敢用她。一系列的打击让戴厚英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痛定思痛后,戴厚英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以人道主义为切入点,创作了《人啊,人!》。
故事以C城大学为背景,描述了一批知识分子从“反右运动”到“文革”期间各自坎坷的人生经历,控诉了人为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巨大伤害和人性的扭曲变形。女主人公孙悦和向南一样,经历了十年“文革”,有过痛苦,有过迷惘。但不同的是,在孙悦的身上存在着当时知识分子软弱与犹疑的一面。此时的戴厚英不再塑造单纯完美的角色,而是用心塑造一个个鲜活且具有“人性”特点的形象。主人公孙悦曾受左倾思想影响而否定自我,把精神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文革”期间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以及后来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孙悦曾经的“信仰大厦”发生倾颓。在小说的开始,孙悦就向好友李宜宁诉说了自己的困惑:“人与人之间应该划出怎样的界限?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用与犯了错误的同志的界限分明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呢?我们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继续当官,一个连发表文章的权利也不给呢?这公正吗?”[8]20这一连串的发问也是戴厚英的困惑。在那个人人自危、互相伤害的特殊年代过去后,取而代之的不应该是一个互相尊重、“人”的权利最大化的新时代吗?而实际情况则不然。
“当时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转换的敏感时期,虽然已经有了三中全会和思想解放运动,但长期极左的流毒一时还很难清除,问题多多,积重难返,不少人的思想还很僵锢。”[9]163-171这点在《人啊,人!》中也有所体现。即使“文革”已经结束,根深蒂固的极左思想依然难以清除。如游若水、王胖子等人,他们具有一定的知识修养,洞察一切,却主动放弃原则,争权夺利,甚至不惜损害他人。还有奚流这样曾经“很有价值”,却在恢复职务后利用权势拉帮结派、打击对手的人。面对这些被扭曲了的灵魂和痛苦的呻吟,戴厚英“大声疾呼:‘魂兮归来’!”[10]333她塑造了一个心胸宽广、富有正义感与责任感的人物——何荆夫,在他的身上注入美好的期望。在何荆夫关于革命问题的连续追问中,戴厚英传递了她对人性的思索:
我想是能够的,老师!我们共产主义者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马克思说过:“无神论是通过宗教的扬弃这个中介而使自己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共产主义则是通过私有财产的扬弃这个中介而使自己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直接追求时效的博爱。”马克思划清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界限,并没有否定人道主义和博爱本身啊![8]81
把人放在首位,一切行为以“人”为出发点,这是戴厚英回顾自身遭际时最透彻的领悟。此时作家心中的“人”字已完全彰显。她不再把造成伤痛的原因归于社会,归于几个坏人身上。她深刻认识到“不论是人、是鬼、还是神,都被历史的巨手紧紧地抓住,要他们接受实践的检验。都得交出自己的账本,捧出自己的灵魂”[10]333。正如书中人物何荆夫曾说:“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时代的历史,是由千千万万个人的历史汇集而成的。在这个汇集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历史道路。”[8]237
在自我反省的力度上,《人啊,人!》已经完全超越了《诗人之死》。从寻找“是什么让我犯了错误”,到反思“我为什么会犯错误”,戴厚英的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凝聚在她身上的人性意识促使她真诚又严厉地解剖自我、反省自我。她不再自我倾诉,用感情支配写作,而是理智思考,深思熟虑后再动笔。《人啊,人!》历经坎坷出版后,造成轰动。“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是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对文学产生广远影响的、最深刻的文艺思潮激荡,最直接的是启发文学从人的角度来反思历史,以异化来对人的悲剧进行形象的解释,《人啊,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1]76。《人啊,人!》是戴厚英剖析自己的灵魂的心血之作,也是她在一次次的痛苦中的涅槃重生。
三、 觉醒的回归:《空中的足音》
《空中的足音》是继《诗人之死》《人啊,人!》之后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是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生活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空中的足音》写于1982年,至完稿却用了整整三年时间。三年间,戴厚英及其作品《人啊,人!》先后两次受到大规模批判。人们纷纷指责《人啊,人!》,戴厚英所在学校还罢免了她的职务,甚至取消了她上课的资格。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身心俱疲的戴厚英断断续续完成了《空中的足音》的创作。较之于《诗人之死》和《人啊,人!》,《空中的足音》的调子是比较低沉的。戴厚英不再振臂高呼人道主义,而是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叙述人性。“文革”后不断出现的风波使戴厚英开始追求生活和心灵的平静,也使她有了更清醒的认知。在小说看似平常的叙述下,矛盾重重,暗流涌动。
A省大学中文系的女教师云嘉洛,因不想让自己的精力在纷纭复杂的人事纠纷中白白耗费,遂离开省城,回到故乡的宁城师范学院工作,希望能抚平心灵的创伤。但是,人事纠纷的阴影又再次笼罩了她,宁城师范学院的两大派系之争使她几乎寸步难行。即使云嘉洛“诚心诚意地伸出自己的双手,让所有人来检查”,并“无情地解剖了自己的灵魂”[12]3,却仍然受到排挤倾轧。A省大学中文系主任贺秦仁因私人恩怨非要她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前宁城师范学院院长宁家梁的妻子余萍更是直言不讳地告诉云嘉洛,只有和其中一派团结在一起,才能在这里立足。云嘉洛不禁感慨:“前进的脚步越来越沉重,每走一步都伴随着精神镣铐的叮当响声和心灵的痛苦。”[12]137镣铐的响声自然也敲打在戴厚英的心上。她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新时期想迈出踏实坚定的一步是何其不易。人害人、人整人、人伤人的事情不仅发生在“文革”期间,在当时仍在上演,知识分子身上的暴戾之气与市侩之气依然没有扫除。在《空中的足音》中,不再出现前两部作品里余子期、何荆夫式的精英型知识分子形象,出场的人物身上都有着或大或小的缺陷。如云嘉洛的老师孟跃如,即使有着很高的道德理想,当他面对云嘉洛时,却因惧怕世俗的眼光而压抑自己的情感,不敢接受云嘉洛的表白。女主人公云嘉洛身上也存在着思想保守、太在意别人的眼光等问题。戴厚英把自己切切实实感受到的生活,接触到的人物以及最真实的自己写进书里。尽管所写的生活和社会都平庸腻味,如“一地鸡毛”,但却是戴厚英“不能不看,不能不面对和适应的生活”[3]250。曾经洋溢在《诗人之死》和《人啊,人!》中的激情和理想似乎大大冲淡了。
结合戴厚英在“文革”后的遭遇,并不难理解她渴望寻求精神依靠、脚踏实地的心情。即使如此,依然不妨碍戴厚英对社会及人性的思考。在书中,戴厚英塑造了一批新成长的青年人形象。他们身处经济浪潮中,思想新潮,见解独特,敢于和老师论长短。对于云嘉洛避世的想法,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意识上的变革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有先驱为之奋斗。可是先驱应该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不但清楚自己能够走多远,还应明白客观允许你走到哪里。盲目地乱撞只会造成毫无意义的牺牲。”[12]可见,对当前社会形势的认识,戴厚英是清楚的,只是她不再希望永远生活在理想和现实的激烈冲突中。透过主人公云嘉洛,戴厚英完全倾诉了自己:在人生历程中,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完全清醒地认识自己,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一条理想的道路,甚至有时不自觉地选择了一条非自己意愿想走的路。这里固然有客观的、个人无法掌握的力量使然,但也不乏是性格所至。不断审视自我,明白自身需要选择什么,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更为重要的。“文革”前后的坎坷经历使戴厚英在痛苦中逐渐走向成熟,成熟的思想使她对自己有更清晰的认知。这一时期的戴厚英的反省是冷静的,可也正是这种无声的反思显得最有力量。
在《空中的足音》的结尾,戴厚英这样写道:“生活当然会特别宠爱一些人,使他们无须付出代价就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东西。但是,任何时候,受到宠爱的都只是少数人。多数人则必须在敲打和磨压中挣扎、奋斗,或者自生自灭。所以,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也只有少数人是不累的。累就累点吧!每一步都靠自己的双脚踩地,也许走出来的路子更宽,脚印更正呢!”[12]422至此,戴厚英完成了她的“知识分子三部曲”。尽管磨难重重,身心疲惫,可《空中的足音》终于不再回荡在空中,而是降落于大地,这完全是作者在焦灼的煎熬中奋力突出重围的结果[13]196-202。戴厚英没有停止对自己的审视,“仍然直接向每个人的灵魂发出呼吁”[14]76-78,站在更高的角度冷静思考,进行现实的批判与灵魂的开掘。
结语
戴厚英的“知识分子三部曲”不仅是“文革”前后知识分子生活状态及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也是戴厚英本人思想历程的再现。在这三部作品背后,隐藏着她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总结和历经艰辛之后的思考与感悟。作为一个愿意对时代和历史承担责任的作家,戴厚英“从第一部小说到现在,始终坚持写自己心里要说的话。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心声,对总结中国历史有作用,就把它写出来”[15]21-23。从《诗人之死》到《人啊,人!》,再到《空中的足音》,戴厚英一直把自己带入创作中,人物形象的背后蕴含着她对现有形象的不满和批判。她在自传中谈到:“写《诗人之死》时,我看到一个傻乎乎的女人在哭泣,唯恐人家不知道她受伤了。她希望并相信,一切人都会理解她,安慰她,搀扶她。但是到了写《人啊,人!》,我就不满意这样的形象了,觉得太幼稚,也太浅薄。十年‘文革’,给予人的提示应该更深更多。我喜欢看到自己是一个思想者,内心收敛了更多的情和泪,但却不再哭泣。到了《空中的足音》,我希望看到自己是一个几乎分不清性别的老人。他慢吞吞向我走来,不想看风景,也不想讲故事。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他都看到了,但不惊不咋,不喊不叫,只是自言自语。我喜欢这样新的‘自我’,因为觉得实在不该再那么感情用事、以幻想代替真实的生活了。”[3]250
通过“知识分子三部曲”,我们认识了一个更加真实的戴厚英。她曾经的盲从、蒙昧成就了如今的清醒独立。戴厚英在不断地反思与自省中掏出肝胆嚎哭出的《诗人之死》《人啊,人!》和《空中的足音》,也使她完成了自己的文化品格:“两脚踏开生死路,在另一个世界找到她的星座,翻看尘世一片冰心,虽云汉飘渺而灵魂依旧栩栩如生,并没有因政治的劫灰化为腐草流萤[16]9-12”。在戴厚英这里,文学作品的精髓隐存在对世俗化生活下的个人心灵家园的寻觅,她所依托的是作为“人”的实在。“知识分子三部曲”是戴厚英的生命体验,也是血泪浸染的生命感悟。她这种直面历史、审视自我的姿态,本身就是可贵的。
[1]戴厚英.诗人之死[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90.
[2]白亮.个体经验、创伤倾诉与自省姿态——重读《诗人之死》[J]. 文艺争鸣,2016(8):.
[3]戴厚英.自传·书信[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黄裳裳.人性的自省——戴厚英论[J]. 文艺理论研究,1998(6).
[5]贾植芳.她是一个真实的人[M]//戴厚英啊戴厚英. 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
[6]王彬彬.错开的药方[J]. 文艺争鸣,1996(1).
[7]左泥.我所认识的戴厚英[J].档案春秋,2006(1).
[8]戴厚英.人啊,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9]杜渐坤,白亮.八十年代初期语境下的《人啊,人!》[J]. 长城,2012(1).
[10]戴厚英.《人啊,人!》后记[M]//人啊,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11]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2]戴厚英.空中的足音[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13]杜渐坤.我为戴厚英编辑《人啊,人!》[J].花城,2010(3).
[14]张英.安顿自己的灵魂——访著名女作家戴厚英[J]. 山花,1995(3).
[15]徐泓.留下一个历史的足迹——追忆1988年5月采访戴厚英[J].世纪,1996(6).
[16]黎焕颐.戴厚英和余秋雨[J].书屋,2002(5).
Searching in the Journey: An Analysis of Dai Houying’s Thought of “Intellectuals Trilogies”
WANG Ya-n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Anhui)
Dai Houying wrote the,and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se novels are known as the “intellectuals trilogies”. Her novels examined the road and spiritual journey intellectuals have taken in different period, including Dai Houying’s deep reflection on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Moreover, we can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Dai Houying’s thinking and realize a real person through the “intellectuals trilogies”.
Dai Houying; intellectuals trilogies; rethink; ideological course
2017-04-22
王亚楠(1992- ),女,安徽阜阳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2015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8.01.07
I206.7
A
1004-4310(2018)01-003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