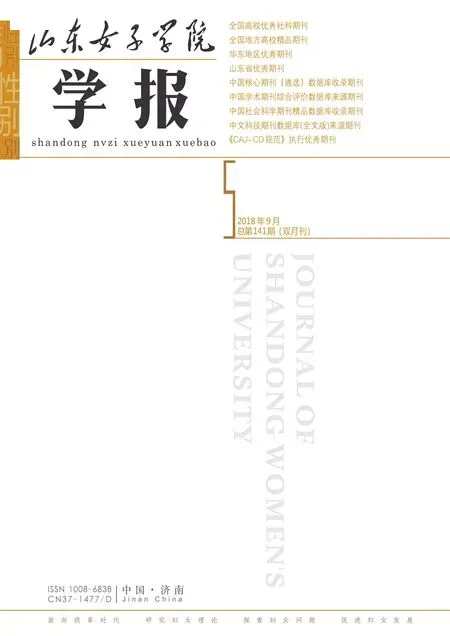《呼兰河传》:“性格即命运”的艺术样本
2018-04-03王澄霞
王澄霞,王 旻
(1.扬州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2; 2.扬州市职业大学, 江苏 扬州 225009)
近年来,“萧红热”持续升温。除了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百十计的研究专著和60多部传记以外,更有影响的是萧红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的两处文字尤其是被命名为《祖父的园子》的千字段落,已被大陆5家出版社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同时选用作为讲读篇目①。2013年3月,霍建起导演的电影《萧红》在全国各大院线全面上映。2014年,香港导演许鞍华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又隆重登场。因此,将与萧红有关的这些现象称之为“萧红热”[1],实在并不为过。
在此先要提及电影《黄金时代》。香港导演许鞍华执导的这部影片追述了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1911~1942)的短暂一生。片名“黄金时代”出自萧红本人1936年11月19日于日本东京写给身处上海的萧军的一封信。萧红一生颠沛流离,能令她满足或快意的人和事都极少极少,她的临终绝笔是“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2](P103)。
《黄金时代》的编导努力摆脱一味渲染男女情爱的窠臼,选择了相对来说易于沉闷乏味的纪录手笔,采用了大量亲友访谈、史料式镜头、信件复述、人物自述等纪录片摄影手法,真实呈现了一个性格偏执、极富个性的现代女作家萧红及其短暂的一生。在学术界几乎一边倒的同情萧红的声浪中,影片编导在史料搜集上下足功夫,以求无限逼近历史真相。尽管近年来国内对萧红的关注持续升温,但是对其文学创作和人生命运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包括电影《黄金时代》到底属于对萧红其人性格的真实呈现,还是“萧军朋友圈对萧红的一次残忍补刀”[3],都引发了论者的不同意见。因此,有必要对萧红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影响亿万读者的《呼兰河传》及其节选进行深入解读,同时联系萧红的人生际遇,探究萧红其人其文的内在联系。
一
笔者认为,《呼兰河传》特别是“祖父的园子”一部分,其中蕴藏着破解萧红一生悲剧命运的“达·芬奇密码”——萧红至死怀念儿时在呼兰县老家祖父园子里的那种为所欲为、绝对自由的生活状态,其实是她借助描写童年生活所创造的一种人生梦境,清晰地折射出萧红任性偏执的性格特点。童年梦幻支配着萧红一生,再一次印证了“性格即命运”这一著名格言。
在1940年完稿于香港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中,萧红以儿童的独到视角表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呼兰县的风土人情和一般民众的生存境况,他们的愚昧残忍、质朴善良与无尽苦难。语文课文《祖父的园子》就选自《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部分。这一千多字的篇幅写的是一个四五岁小女孩的日常生活,她无忧无虑率性而为,慈祥的祖父呵护左右,老家的后园就是她童年的天堂。全文语言清新,基调欢快,充满孩子的天真和灵气,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特别是对纯真童心的由衷赞美。
萧红因反抗包办婚姻于1930年离家出走,此后就一直漂泊无定,感情屡屡遭受挫折,抗战后期又只身远走香港,人近中年还疾病缠身,此时的她十分怀念自己的童年和故乡,“我要回到家乡去”[2](P99)成了萧红那时的强烈愿望。度过她童年时光的美丽后花园,祖父的慈爱宠护,自己儿时的娇憨单纯,越发让如今远离故土孤身度日又疾病缠身的萧红,深感慰藉和温暖。
以上这些观点就是萧红《呼兰河传》问世70余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界、语文教育界基本一致的解读和评价,也是其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主要原因。
但是,这样的解读显然太过肤浅狭窄,因为萧红借助这一段童年生活的描写所要传达的独特的情感和愿望,没能得到深入的解读和深切的体察领会;也未能由此剖析萧红的性格特点,并进而挖掘萧红人生悲剧的内在缘由。其实,只要再参看文中另一段文字,尤其注意其中那十一个“就”字所传达的意愿,或许就能读出儿童视角背后的成年心理: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4](P280)(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上述文字“平易而又隽永、清通而复清新”[5],历来被人称赏不已,这一段落也是全文的核心或曰点睛之笔。但是细细研读就会发现,这段文字传达出萧红一心向往的是那种为所欲为、毫无羁绊、极度自由的生活。结合前文所写的这个女孩在后园中的种菜、拔草、栽花、浇水、填坑等活动,无一不是由着她的性子,没有遭到祖父丝毫的呵斥或管制。萧红借这两段文字表达了一种共同心愿:为所欲为,绝对自由。细加鉴别就可发现,来自萧红记忆中的小女孩和祖父一起在园子里的活动,基本上是真实的,而所表达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种强烈渴慕绝对自由的心理和愿望,则绝非一个四五岁女孩所能拥有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自身行为的状态和性质,在认识上不可能如此自觉和清晰;更不可能有如此明确的愿望。这种理想和渴求只能来自成年的萧红,不过是她假借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来加以倾吐和表达。《呼兰河传》写就于萧红离世前一年,那时的她竟还强支病体,怀着憧憬和追求,倾尽心力描绘昔日“祖父的园子”。由此可见,在她三十多年的人生中,这一童年梦幻给她的印象之深刻、影响之巨大。
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6]。
退一步说,即使那般绝对自由的生活确曾为萧红童年时代所有,那也只能是一度拥有,而非能够时时拥有直至永远,因而不应将它作为理想人生而盲目追求。因为复现当年那等生活情状必须具备三个前提:首先,孩子才四五岁,因此凡事可加宽容;其次,对这个孩子凡事不予计较的长辈是年届七十左右的祖父,相比中年的父亲要宽容慈祥得多;最后,这是在自家的菜园子而非客厅,不会造成多大损害。上述三项条件缺一不可。小说中就曾写到,那时候这个小女孩曾头顶宽大的缸帽子摇摇晃晃想走进里屋去,父亲抬起一脚就将她踢翻在地了[4](P296)。
其实,人们的童年生活哪能全都如此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不往远处说,仅以入选语文教材中的同类篇目为例。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等篇章,都写到了他本人的童年生活。文中所写固然不乏童年生活中种种的有趣情景,表达了作者对那段已逝时光的怀念与向往,不过,百草园中自在快乐的生活未能持续多久,纵使“迅哥儿”万般不愿,他还是被送进了全城最严厉的书塾。书塾中的学习生活虽然也有种种乐趣,但是也有种种不自由,还会时时存在着戒尺的威胁。《社戏》中掘蚯蚓、钓虾、放牛、看戏、吃豆子诸事固然快乐无比,可其间同样也有种种不顺心,想去看戏就差一点看不成。其《五猖会》中所写就是鲁迅童年时期的一段痛苦经历;《父亲的病》一文更反映出鲁迅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艰辛。
至于萧红《呼兰河传》的语言,一般论者都认为充满童真和灵气,特色鲜明。笔者却认为这种说法只是表层之见。譬如下面一段文字就当细加品味推敲: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4](P280)。(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细加推敲这段貌似儿童话语的文字,就会产生如下疑问:才刚四五岁的小孩子,她的观察何以如此认真细致,会觉得太阳特别大,天空特别高,还会有“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这样高度抽象的判断和结论?因为四五岁的孩子还不具备健康与否的知识或概念;不能明确区分何谓事实何谓想象,更不会觉得“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自然也就更不会有“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这样的判断、想象和预见。可见,这些语言是成年萧红的语言,这些感受更应都是成人萧红的感受。这也进一步证明在“祖父园子”中的自由自在、为所欲为的童年生活,带有成年萧红的诸多想象,是她借此传达出的梦幻般的人生理想。
在“祖父园子”里的这段梦幻岁月以及对这种梦幻的念念不忘,充分反映出萧红性格上的执拗任性。《呼兰河传》中的其他多处细节也印证了萧红的这一性格特点。例如,祖父教她背唐诗,她听了喜欢的才背,不喜欢的就不背;她也不愿规规矩矩地念诗,而喜欢扯着嗓子胡乱喊叫,背不背、怎么背,反正全由着她自己的性子来:
但我觉得这乱叫的习惯不能改,若不让我叫,我念它干什么。每当祖父教我一个新诗,一开头我若听了不好听,我就说:
“不学这个。”
祖父于是就换一个。换一个不好,我还是不要[4](P299)。
《呼兰河传》还写到萧红的祖母有“洁癖”,平时窗户纸总是保持洁白平整;而用手指捣穿那些窗户纸,却是幼年萧红惯常的喜好,“若不加阻止,就必得挨着排给捅破,若有人招呼着我,我也得加速的抢着多捅几个才能停止。……破得越多,自己越得意”[4](P282)。祖母气得无计可施,只得躲在窗户后面用针戳她的手。这样一来,祖母对她的诸多好处萧红全都不以为然,唯独祖母用针戳她的手这一细节她刻骨铭心,一直难以释怀。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有一句著名格言“性格即命运”,萧红这种任性而为的性格特点,注定了她的坎坷命运。“她富于理想,耽于幻想,总好像时时沉迷在自己的向往之中,还有些任性。这,大概就是她的弱点吧!”[7](P319)萧红好友李洁吾的这番感慨,应该是知人之论吧!
二
萧红借助童年回忆所表达的这种为所欲为、绝对自由的人生理想,既然只能是一种白日梦幻,那么,将梦幻当成理想并试图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其实现,势必屡屡碰壁,可萧红屡屡受挫却至死靡悟,这就更加令人感慨。萧红与四位男性的情感经历,也充分印证了上述结论。
(一)萧红与汪恩甲
汪恩甲是萧红的未婚夫。18岁的萧红离家出逃至北京女子中学读书,就是为了反抗父亲订下的这桩包办婚姻。其后萧父将其抓回关禁闭,并断绝经济供给。还有资料披露,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对萧红的出走大为不满,遂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任性倔犟的萧红一气之下反把大伯子告上了法院。“为保全哥哥的名声,汪恩甲出庭作证,辩称解约是自己所为,害得萧红输了官司。”[8]
萧红与汪恩甲解除婚约以后,却又私自离家与汪在县城同居。怀孕在身、毫无经济来源的萧红,最终被汪恩甲遗弃在哈尔滨一家旅馆里。因付不起欠下的食宿费用,萧红差一点被旅馆老板卖入妓院抵债。
萧红的率性而为和倔犟任性,在她的第一次情感纠葛中就已表露无遗。在萧汪两人的同居生活中萧红没有体会到那种“童年梦幻”,汪恩甲自然不可能如她祖父般宠护着她,容忍她的执拗任性,以致两人最终不欢而散、恩断义绝。
(二)萧红与萧军
时任哈尔滨《国际协报》记者的萧军,在松花江发大水时救出萧红。正是萧军的仗义相救,才使萧红免遭卖身厄运,两人因此真心相爱。萧红怀着别人的孩子,萧军毫不嫌弃毅然与之结为夫妻。在萧军影响下,初中文化程度的萧红也走上创作一途,随后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并立稳脚跟。两人生活渐趋安定,感情却出现危机。此后萧红独自远赴日本,不久回国,与萧军重归于好,并相约一起奔赴延安。但是不久二人又爆发矛盾,婚姻最终破裂。在1978年萧军回忆萧红的文章中,他赞赏萧红的文学才华和为人的淳厚单纯,同时也认为她既软弱又固执,实在并非一个合格的妻子:
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
……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我也从来没向她要求过这一“妻性”[9](P158-159)。
萧红则对萧军的感情出轨满腹怨愤:“可是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作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10]萧军自有缺点,萧红不满怨责,这都在情理之中。问题是,萧红有时甚至因为萧军没有陪她一起去买花生米而与友人先走了几步,便生气并拂袖而去[11];特别是萧军为了两人生计疲于奔命而疏于对她温存之时,萧红对此的指责和抱怨更加没有多少道理②。萧军的性格和身份自然不像萧红的祖父,两萧在6年多的共同生活中摩擦不断,远非萧红回忆中的祖父园子里那般自由自在、为所欲为,这恐怕是两人最终分手的根源所在。
(三)萧红与鲁迅
萧红来到鲁迅身边,得到鲁迅的无限关怀和帮助,两人既是师生,又情同父女。萧红觉得鲁迅如同她的祖父,鲁迅的家就像她祖父的园子,一段时间里萧红认乎其真地在鲁迅这儿过起她一直怀念的“祖父园子”的童年生活。其实,萧红的任性而为和频频造访已经对鲁迅家庭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可她对此却始终毫无认知。以致后来许广平先生追忆萧红时,仍难掩怨辞:
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顾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12]。
难怪有论者指出:“许广平是在萧红去世后写这篇文章的,仿佛只是为了纪念,但那份怨责是掩饰不住的。”[13]
可见,萧红觉得鲁迅就像她的祖父,鲁迅的家庭仿佛她儿时呼兰家中园子的再现,完全是她本人一厢情愿的幻想,可悲的是萧红对此始终没有清醒的认识。
(四)萧红与端木蕻良
与萧军分手不久,怀着萧军孩子的萧红,又迅速与东北老乡、青年作家端木蕻良走到一起,端木毅然与有孕在身的萧红隆重结婚,足以见证他对萧红的感情以及挑战世俗的勇气。但不久两人又吵闹不休。抗战期间萧红曾要求与好友一起买船票离开武汉赴重庆,可这么重要的事情她居然没跟端木商量,萧红的自我中心和执拗任性可见一斑:“‘我到哪里去不都是一个人呢?’……‘为什么要和T(指端木,笔者注)商量呢!’她睁大了眼睛。”[2](P85)
萧红与端木在矛盾重重之中辗转来到香港。萧红身患重病,端木蕻良弃之不顾只身离去,使得萧红情不自禁地思念起萧军来。在最后这段情感经历中萧红发现,端木蕻良也没有如祖父一样娇宠她,在端木这里萧红同样没能实现儿时祖父园子中的人生梦幻。
现实生活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可是萧红竟然希求现实生活如同梦幻一般万事顺遂,心想事成。对得到的一切她视为理所当然,而对人生常有的挫折或不如意却一直耿耿于怀。萧红生前好友、胡风夫人梅志忆及萧红时,对她“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临终感慨就既有同情也隐含批评:
“不甘”,是的,她还只活到31岁呀!但要说“尽遭白眼冷遇”,那是有点夸大的感伤!其实在旧社会有谁能如她一样幸运,二十出头,挟着一本《生死场》原稿来到上海,就得到鲁迅先生和许多朋友们的赞扬和爱护。在创作方面,在对她个人的接待方面,我想当时谁也没有给她白眼和冷遇。我似乎没有见到过一篇批评她的文章[14](P288)。
萧红四五岁时在“祖父的园子”里的童年生活,因着萧红成年后的想象,成了绝对自由、绝对美好的人生理想。这一人生幻梦影响着她此后的现实人生;而真实生活的磨难坎坷,又令萧红对童年梦幻愈加向往,两者不断互为因果,相互强化。31岁的萧红在疾病缠身、困守香港之际,仍然抱病写下《呼兰河传》,深情怀念、强烈向往祖父园子中的童年生活,这就充分证明,萧红一生都执迷于祖父园子一般的童年梦幻。这当然不能归咎于她祖父对她的娇惯和宠护,不能苛责她童年生活曾经有过的快乐自在,只能说萧红错在不该执于一念,不该将这种有着特定条件、短暂而不可再现、无法复制的童年梦幻,当作现实的人生理想来执着追求。这种认识上的偏误和她性格的任性执拗,两者一旦结合就难以改变,以致萧红至死都未省察。
三
萧红的《呼兰河传》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曾得到茅盾、曹聚仁、司马长风等大家的高度评价,同时这部小说也使我们对文学与人生的认识多了一个视角和参照。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和梦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匮乏或缺失,往往通过文学作品来宣泄和满足,所以,大凡文学作品表达的都是世人的人生愿望乃至人生梦幻。就此而言,萧红与她的“祖父的园子”并非个例。例如古典名作《西厢记》就表现了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历经坎坷终成眷属的人生理想;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将“情”的力量表现得更加离奇夸张,“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15]。情之所至,生者可以因之而死,死者可以因之而生,爱情的这等神力,显然是出于作者汤显祖的主观想象。《窦娥冤》中为给蒙冤而死的窦娥讨回公道,作者关汉卿就设计了“六月飞雪”等感天动地的浪漫主义情节,借此表达普通百姓渴求公平正义的强烈愿望。中国其他流传了千百年的民间故事如《天仙配》《牛郎织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田螺姑娘》等等,都表现了老百姓的生活理想和生活追求。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能遇到一个中意的女子,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是人生最大的愿望。这个愿望是那么强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容易实现,因而这些民间故事或文学作品就应运而生,以对现实的匮乏给予精神补偿,从而让人们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但是,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应该清醒和明白,梦幻终究是梦幻,现实毕竟是现实,误将梦幻当现实,那就会贻害无穷。文学名著《红楼梦》所描写的宝黛爱情,就曾让多少痴男怨女迷得死去活来。有记载说,有位千金小姐酷嗜《红楼梦》,为小说中的“情种”宝哥哥茶饭不思,形容憔悴,百病缠身,家里人气得夺过她手中的《红楼梦》扔到了火盆里。这位痴情女子居然还强支病体,大哭曰“奈何烧杀我宝玉!”[16]无独有偶,某公子哥也为林妹妹相思成疾,百药不灵。后来家人得一妙法,将一位鸡皮鹤发、颤颤巍巍的老妪搀扶到他的病榻前,告知他这位就是当年千娇百媚的林黛玉活到当下的模样,这位多情公子如梦初醒,相思病霍然而愈。这些近乎笑话的故事无非说明,误把梦幻当现实者,远非萧红一人。
当代流行歌曲《涛声依旧》一直广为传唱,特别是其中“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这几句歌词,表达了许多人期望与旧情人再续前缘的愿望。有意思的是萧红的经历倒是印证了《涛声依旧》所表达的心愿并非无端妄言。已与端木蕻良结婚的萧红,在目睹了萧军与现任妻子王德芬的合影后感到无比失落和痛苦,让朋友感慨“想不到她对萧军还有这么深的余情!”[14](P286)就在萧红重病缠身被弃置于战火纷飞的香港医院时,她对萧军还是心存念想:“当时我想到萧军,若是萧军在四川,我打一个电报给他,请他接我出去,他一定会来接我的”③。而听闻此事后的萧军虽无比感慨,也只能徒唤奈何:
尽管她在临终之前,她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萧军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把我拯救出去的……”(大意如此,见骆宾基《萧红小传》)但是,即使我得知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她在香港,我却在延安……[9](P159)
那张旧船票虽然还在萧红手里,可是时过境迁,人事皆非,她再也无法登上萧军的客船了。
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就是如此纷繁复杂,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呼兰河传》中就潜藏着萧红命运的“达·芬奇密码”,揭示了萧红一生悲剧的内在根源。在深入认识文学和生活之关系上,《呼兰河传》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鲜活样本。
“萧红热”这一文化现象并不正常。客观而论,萧红的文学成就本来有限,正如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指出的那样:“过早逝世的萧红,在文学创作上并未真正成熟,其作品虽然有着独特的价值,但总体上的成就也是有限的”[17]。为何与萧红同时代的那么多男性作家包括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在内都没有如萧红这般走红?果真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成就皆在萧红之下么?笔者以为,已逝70多年的萧红在影视圈的走红,从根本上说,是当今这个“娱乐至死”时代对一个文艺女青年尤其是一个私生活复杂的年轻才女的浓厚兴趣,换言之,萧红身上具备了多种吸引当下眼球的商业消费元素,一般读者更感兴趣的是性格叛逆的她与多个男性的情爱纠葛,正如《黄金时代》片中萧红对骆宾基所说的那样:“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
“萧红热”早该到了降温的时候。正是出于对“萧红热”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心态的关注,出于对生活与文学、性格与命运关系的思考,笔者谨作此文。
注释:
① 萧红《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部分入选3种版本小学语文教材和2种版本初中语文教材:人教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简称)小学五年级课文,题名《祖父的园子》;教科版(教育科学出版社简称)小学六年级课文,题名《我和祖父的花园》;苏教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简称)小学五年级课文,题名《我和祖父的园子》;苏教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简称)初中九年级课文,题名《〈呼兰河传〉(节选)》;沪教版(上海教育出版社简称)初中六年级课文,题名《祖父和我》。《呼兰河传》第一章第八部分则入选苏教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简称)小学三年级课文,题为《火烧云》。
② 譬如萧红散文《他的上唇挂霜了》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很忙,早晨起来就跑到南岗去,吃过饭又要给他的小徒弟上国文课。一切完了又要跑出去借钱。晚饭后又是教武术,又是去教中学课本。夜间他睡觉也不醒转来,我感到非常孤独了!”见肖凤编《萧红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③ 见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页。季红真《萧红传》中也写到这一情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