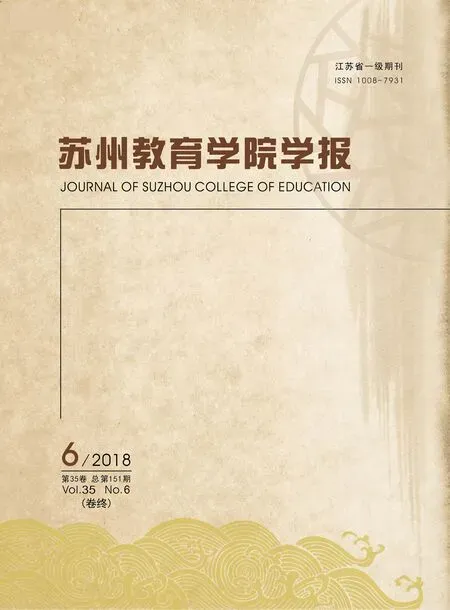印学理论对明清流派篆刻发展的引领
2018-04-03周一红
周一红
(苏州市职业大学 科技处,江苏 苏州 215104)
在早期,印章只作为实用之物,其材质多为金属、牙玉等,由工匠设计制作,其时并无印学理论。自文人亲自参与篆刻,有意识地传承秦汉古印风格,并借鉴书画、金石学等相关领域的成果,在追求印章艺术性上具有了清醒自觉的认识后,开始出现了印学理论著作。印学理论的出现虽远远晚于文论、书论、画论,但此前的文论、书论、画论成为印学理论良好的发展基础,对于刚刚起步的印论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和“惯性牵引效应”[1],为印论在形式、思想和审美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因此,印学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迅速发展,而在随后的创作实践中,篆刻自身发展规律和独特审美取向的发掘也使印学理论摆脱了对文论、书论、画论的依附,具有了独立性。
一、印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学古编》
印学理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印宗秦汉”“印从书出”“印外求印”三个阶段。元代吾丘衍的《学古编》[2]为印学领域最早出现的一部经典著作,阐述篆隶演变及篆刻知识,对后来篆刻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发展,有着上承秦、汉玺印,下启明清流派篆刻的重要作用。故明、清篆刻家,如何震、桂馥、姚晏、黄子高、吴咨等每效三十五举体例而一再续之。《学古编》前十七举多谈篆书的结体与笔法及古今之变,其时已认识到篆书的书写水准直接影响篆刻水平。后十八举则剖析印理,论及汉魏印章铸凿之别,及朱白文印式布局之理。如第十八举:“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2]14元代流行屈曲盘绕的九叠篆,平满闷塞、格调低下,吾丘衍在此对时风提出批判,引导了宗法汉式的复古审美。再如第二十五举:“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又汉器物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2]15明确论及取金石器物文字入印的方法,为“印外求印”思想的萌芽。元人不识古玺,吾丘衍以为“三代无印”[2]16,其时“印宗秦汉”理论尚不完整,“印从书出”与“印外求印”也未被提出,但吾丘衍对汉篆入印质朴之美的推崇及对汉印用篆、布局的总结,奠定了“印宗秦汉”的理论基础;而对于“印从书出”与“印外求印”则具有了敏锐的先知先觉。当时篆刻创作实践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学古编》中所述书、刻技法的系统性和印学思想的前瞻性,使它在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至晚明,篆刻理论研究空前繁盛,除了专门的印学论著,还有印谱序跋、论印诗、印章边款等各种形式,内容涉及印史整理、印人生平、治印技法等。元明印论参照文论、书论、画论而自成体系,引入的复古思想直至今日仍是印学思想的主流,使得篆刻登堂入室,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推动了明清流派篆刻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出新面的繁荣景象。
二、“印宗秦汉”理论的实践
秦汉印是印章史上第一座高峰,“印宗秦汉”理论的提出早于创作实践的成功,“印宗秦汉”是明代和清前期篆刻创作的主流,经一代代印人身体力行,方能深得秦汉精神。
(一)明代篆刻家文彭、何震
明代文彭(1498—1573,字寿承,号三桥,别号渔阳子、三桥居士等)被誉为流派篆刻的开山鼻祖,他发现灯光冻石易于奏刀并取为印材,力矫时弊,打破九叠文俗格,开文人篆刻新风。白文印以秦汉为宗,淳厚平正,雍容自如;朱文以小篆入印,圆劲俊丽,古朴典雅。既承古法,又融入自家个性,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文彭诗、书、画、印皆通,追随效法者众多,大批文人、学者形成了共同的审美追求,由此形成了最早的篆刻流派—“三桥派”。
何震(1522—1604,字主臣、长卿,号雪渔)青年时问业于文彭,艺术主张与文彭相似,主张篆刻风格以秦汉印为宗,用字以“六书”为准则。何震的篆刻追溯秦汉,借鉴秦汉铸印、凿印、玉印等多种风貌,韵味淳厚,且不断出新,化古为今,形成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艺术风格,生前已与文彭并称,在印坛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创“雪渔派”。何震的成功带动了当时很多印人对秦汉印的关注和学习。
文彭、何震作为明代篆刻宗师,他们的艺术主张和审美影响了有明一代大批印人,其中苏宣、朱简、汪关在追摹秦汉的基础上开辟新腔,始于摹拟,终于变化,均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师,领一时一地篆刻新风。
(二)集大成者—丁敬
至清代,“印宗秦汉”理论已经历了长期的实践,学秦汉印者甚众,但唯古是从,绳趋轨步,以至于王稚登有语:“《印薮》未出,坏于俗法;《印薮》既出,坏于古法。”[3]至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钝丁、砚林,别号龙泓山人、孤云、石叟、梅农等)出,其以过人的魄力和远见卓识,力振古法,变形式的模仿为气韵的探求,以钝朴奇崛的切刀法,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具有独特个性又深得秦汉精神的印风。丁敬是“印宗秦汉”理论的集大成者,独创具有个性的汉印,以刀立派,成为浙派篆刻的开山鼻祖。丁敬的篆刻艺术观在他的《论印绝句十二首》中有所阐述:“《说文》篆刻自分驰,嵬琐纷纶衒所知。解得汉人成印处,当知吾语了非私。”[4]自唐以来,《说文解字》被奉为篆刻用字的宝典,丁敬以汉印所用的摹印篆为例,主张篆刻创作用字不必拘泥于《说文解字》,他身体力行,在创作实践中以汉摹印篆为蓝本,根据印面的需要进行简化及美化处理。这一用字原则,对浙派印风的最终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后世印人的入印用字拓展了更大的空间。丁敬在“印宗秦汉”的基础上,熔铸古今,别开新面,在篆刻创作上曾作多方尝试,风格驳杂。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入垂暮之年的丁敬在“王德溥印”边款中道:“秦印奇古,汉印尔雅,后人不能作,由其神流韵闲,不可捉摸也。”[5]715此时丁敬重新回归秦汉印传统。浙派篆刻“西泠八家”中的后起者大多取丁敬一种印式深入研究,或综合几种印式加以发展、变通,各自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更为重要的是,后起诸家直取秦汉古印心法,对秦汉印的审美有更深的领悟,并各自将“印宗秦汉”理论成功地运用到创作中。“钝丁之作,熔铸秦、汉、元、明,古今一人,然无意自别于皖。黄、蒋、奚、陈曼生继起,皆意多于法,始有浙宗之目。”[6]596浙派篆刻影响之巨,声誉之隆,皆是前所未有。
三、“印从书出”理论的发展
“印从书出”理论自吾丘衍《学古编》发端,至明代朱简《印经》中有进一步阐述:“刀法也者,所以传笔法也”,“吾所谓刀法者,如字之有起、有伏、有转折、有轻重,各完笔意,不得孟浪”。[7]朱简不但明确指出篆刻的刀法应当表现篆书的笔意,并且在实践中加以尝试。但由于当时篆书书写水平的局限,“印从书出”并未能在创作实践上有所突破。到清代,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顽伯,号笈游道人、完白山人等)正处于金石学成果叠出的时期,历代彝铭、碑版大量面世,他因此临摹了大量古代金石善本,其书法四体皆备,尤精篆隶,其小篆创造性地融入隶书笔法,使篆书具有了提按、方圆、转折等丰富变化,独具沉雄朴厚之美,使走入僵局的篆书艺术萌发出新的生机。“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写篆。”[8]邓石如之后,整个社会的篆书书写水平大大提高。邓石如突破了以秦汉玺印为唯一取法对象的狭隘见解,最终以“印从书出”的观念与实践重振皖派篆刻代表人物。“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6]596邓石如虽然也列为皖派篆刻,但由于影响深远,被后世吴熙载等人追溯为邓派篆刻始祖。作为一个有创新意识的艺术家,邓石如的印风追求有意识地区别于浙派:浙派阳刚而邓派阴柔;浙派端方而邓派圆转;浙派多用切刀法而邓派多用冲刀;浙派入印文字多用摹印篆,而邓派多取小篆。最重要的是印学思想的变化,浙派禀承“印宗秦汉”思想变革秦汉印成其新貌,邓派则开“印从书出”之先河。
邓石如“以书入印”的探索性实践并未能完全解决篆书印化的问题,印文也未得其篆书之雄浑,其后邓派传人吴让之以切、冲、披并用的刀法,实现了以刀法传笔法,使印文的线条具有了邓氏书法所具有的轻重、方圆、枯润等诸多变化,并使朱、白文风格高度统一,将邓派篆刻推到书印合一、成熟完美的境界,故吴昌硕有“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9]语。自此,追求笔墨情趣成为篆刻创作重要的审美原则,书印合一也成为篆刻家成功的标志。
四、“印外求印”理论的探索
丁敬和邓石如创立了清代影响最大的两大篆刻流派—浙派、邓派,浙、邓两派的兴起也代表着“印宗秦汉”“印从书出”两种思想在实践上的成功。印人对“印外求印”的探索早在明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尝试将商周彝器铭文和传抄古文入印,成为流派篆刻中的新品。[10]虽不甚成功,但可见篆刻家对拓宽印路的渴望。到清代后期,赵之谦将当时所得见的石刻碑版、权量诏版、砖瓦碑刻、帛布镜铭文字均配篆入印,开创了丰富的印风。除了对印面的创新,赵之谦将他对金石学的妙悟用于没有引起前人重视的边款,魏书刻款、朱文边款,以至山水、人物、走兽都引入边款,缩巨碑于寸石,使边款成为袖珍的碑刻。赵之谦在《苦兼室论印》中提出“印外求印”思想:“印以内,为规矩,印以外,为巧。规矩之用熟,则巧出焉。”“刻印以汉为大宗,胸中有数百颗汉印则动手自远凡俗,然后随功力所至,触类旁通,上追钟鼎法物,下及碑碣造像,迄于山川、花鸟,一时一事觉无非印中旨趣,乃为妙悟。”[11]《苦兼室论印》是否为赵之谦所著,因无其他资料印证,学界尚存争议,但赵之谦在多方印的边款中皆道明其篆刻取法:如“星遹手疏”边款:“稚循书来属仿汉印,撝叔刻此,乃类《吴纪功碑》,负负。戊午十一月”[5]756;“魏”边款:“法《三公山碑》为稼孙作。悲庵”[5]760;“沈氏吉金乐石”边款:“摹汉镜铭为均初作。无闷”[5]760;“撝叔”边款:“类小松摹古泉文。悲庵记”[5]761,等等。几乎能见到的金石碑版文字都成了赵之谦取法的对象,他所开发的众多风格启迪后世印人以出新的思路。赵之谦打破浙、邓二派笼罩天下的格局,开启了突破流派局限的篆刻艺术思潮,印坛从此进入一个百花齐放的全新时代。
其后的篆刻大师吴昌硕和黄士陵则借助晚清出土文物甚众的有利条件,从金石学新发现中汲取养分,各取一端深入研究,创造出迥异的风格。吴昌硕汲取封泥、古陶、瓦甓之古意入印,形成一种斑驳浑厚、高古沉雄的意趣。吴昌硕“道在瓦甓”印边款:“旧藏汉、晋砖甚多,性所好也,爰取《庄子》语摹印。”[5]764道出了他对篆刻艺术的审美理想和取法方向。另有多方印作边款为:“古匋器文字得汉银印法”[5]764、“辛巳端阳仿陶拓,刻此得古意否?”[5]765、“拟古封泥”[5]766等。吴昌硕刻印以钝刀硬入,先得雄浑之意,并打破前人重刻不重做的规律,独创做印法,以磨、削、铲、凿、锉等方法营造一种似风化漫漶的雄浑高古之趣,所谓“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篇》)[12]。而黄士陵则与吴昌硕反向而行,取径吉金而得金之魄,他以薄刃小刀竖刀直冲,一气呵成,线条锐利挺劲蕴含笔意,另创一种光洁雅研的印风。他将方圆、曲直、正斜、点线等几何图形组合到印章之中,创造出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篆刻艺术的表现形式。
五、对当代篆刻的启示
自1980年举办第一届全国篆刻展以来,当代篆刻从艺人员数量已远超明清文人篆刻高峰时期,篆刻家们从未停止过在印内印外寻找各种创新元素以融入印章之中,而金石简帛文字的大量出土,使篆刻家具有了更加开阔的艺术视野及更多样的表现手法,篆刻艺术迎来了再次繁荣。当代篆刻对传统最大的改变是刻意打破平正,营造动荡、欹侧、夸张的视觉冲击。徐正濂先生将当代篆刻中“酣畅的线条、猛利的用刀、夸张的文字构型、强烈的对比效果”总结为“痛快”二字。[13]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借写意之名掩盖技法不周的荒率之作,这种粗疏、草率、乖张、跟风现象,迫使印人基于一种反思的立场,回望与追寻篆刻传统中的古意。“印宗秦汉”“印从书出”“印外求印”虽为印学理论的几大分支,但其实质密不可分,不仅推动了明清篆刻成为篆刻史上的第二个高峰,而且对今日印人的创作实践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此三种印学理论皆强调篆刻艺术中的“复古”思想,古意并不是某种固定的程式或风格,而是中华民族积淀千百年的共同审美情感与认同,故能历久弥新。借古出新、熔铸时风,这需要篆刻家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以把握传统及时代精神,最终融于自身心性,创造出具有个性与感染力的作品。当代篆刻又赋予“印外求印”新的内涵,即全面提高印人的修养以提升印章气韵,所谓“功夫在印外”。入古出新、古调新弹是篆刻艺术永葆活力的不二法门,通过书法追求篆刻的个性以及广泛撷取各种审美元素加以印化的思想,将指引篆刻不断出新。对古意的频频回望,既能保证对传统优秀基因的继承,又能获得强大的创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