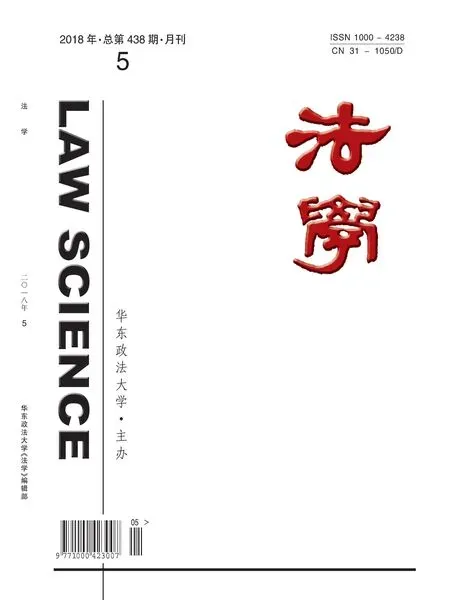“国家资本主义论”下的国企投资者保护
——基于投资协定革新的视角
2018-04-02刘雪红
●刘雪红
一、中国国企投资者海外投资保护的现实困境
在当前逆全球化的寒流中,中国备受来自国际社会“国家资本主义论” 的攻击而深陷生存危机。〔1〕“国家资本主义”本是国际共产主义文献的专门术语,列宁和毛泽东等人对此有专门阐述,但自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媒体和部分学者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使用这一概念,尤其专门用于指称中国等某些新兴国家。2012年1月,英刊《经济学家》 刊发《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 特别报告,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也多次强调“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构成经济和战略挑战。自此,“国家资本主义”成为西方的热门话题,而拥有大量国企的中国则成为受攻击的主要对象。相关研究可参见谢来辉、杨雪冬:《国家资本主义评析》,《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3期;孔庆江:《中美BIT谈判中的国家主导经济议题研究及我国的对策》,《政法论坛》2014年第6期。“国家资本主义论”主要被用以描述经济活动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制度,比如由国有企业组织和运营生产、国有控投公司在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等。依西方主流观点,中国的经济模式由国家主导,中国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操控市场,给全球投资活动带来重大风险并致全球经济发展出现失衡。〔2〕See 2016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One Hundred Fourtee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November 2016), p.122,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 i les/annual reports/2016%20Annual%20 Report%20 to%20Congress.pdf, last visit on April 18, 2018.近年来,国外有学者积极宣扬“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强烈批判中国的经济制度模式和国企身份,〔3〕比如,吴人英(Mark Wu)在《哈佛国际法学刊》上发文称,“世界见证了代表着一种特殊经济模式的中国式企业(China,Inc.)的崛起,它们极复杂地将国家、政党、公有企业和私人企业连接在一起。” See Mark Wu, The ‘China, Inc.’ Challenge to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57, No. 2, 2016, p.323.认为中国国企并非纯粹的“投资者”而是复杂的“公私混合体”或“政府代理人”。2017年5月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3调降至A1时的理由之一即是政策银行与国企的债务会加重政府债务。〔4〕See Moody, Moody’s downgrades China’s rating to A1 from Aa3 and changes outlook to stable from negative, https://www.moodys.com/research/Moodys-downgrades-Chinas-rating-to-A1-from-Aa3-and-changes--PR_366139, last visit on June 22, 2017.基于对中国国企“投资者”身份的怀疑与敌意,西方对参与国际投资活动的中国国企采取了各种抵制措施,长期由西方倡导的国际自由市场正全面对中国国企关闭。
在美国,其主要以国家投资安全审查工具歧视中国国企并阻碍其进入国内市场。〔5〕同前注〔1〕,孔庆江文。2007年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对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之安全效果进行调查,判断要素包括投资项目、技术以及投资者的背景等。但是,当前美国的实践却常将中国国企作为判断跨国收购交易安全的重要指标,频致中国企业并购美企失败。在1990年到2015年间,美国安全审查委员会(CFIUS)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干预和影响的中国企业并购交易主要有 14 起,其中8起属于中国国企的并购交易。〔6〕比如,1990年至2015年间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的安全审查所涉收购主体为国企的数量约占总数的 57%,分别是中航技收购 Mamco、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石油公司、西色国际收购美国优金公司、唐山曹妃甸投资集团收购美国光纤设备制造商 Emcore、鞍山钢铁投资美国钢铁发展公司、中兴通讯参与竞标美国 Sprint 项目、紫光收购西部数据和紫光收购美光科技。除了被收购领域可能具备战略敏感性外,中国收购方的国企背景也成为美国进行安全审查的一个隐形的重要考量因素。参见屠新泉、周金凯:《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中国国有企业在美投资的影响及对策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2016年受CFIUS安全调查而导致中国企业收购美企失败的有4起,其中3起的收购方是中国国企。〔7〕同前注〔2〕,第64~65页。其中,美国生产存储芯片和闪存的美光科技公司因担心不能通过安全审查而拒绝清华紫光的收购要约(2016年1月),清华紫光旗下的Unisplendor收购西部数据公司时对方则在CFIUS调查之初就撤销了收购合作(2016年2月)。〔8〕同上注。据学者分析,CFIUS极有可能认为清华紫光是中国国企,其收购反映了中国意图,从而最终会以“交易受外国政府控制”为由否决中美企业的合作。〔9〕同前注〔6〕,屠新泉、周金凯文。笔者以为,此种推断不无道理,因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一直认为“资本与控制者相结合必产生政治属性”,〔10〕参见王东光:《外资审查的政治维度——以外国政府控制的投资为研究视角》, 载顾功耘主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0页。并建议国会“修改法令以授权CFIUS禁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企业或获得美国企业的控制权。”〔11〕同前注〔2〕,第 5页、第 29页。可以想见,未来中国国企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将会遭遇极为严峻的挑战。
在欧洲,中国国企同样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身份歧视和市场准入障碍。长期以来,除军工、银行或少数的特殊行业外,欧洲一直对外国投资者持开放态度,中国也一度是欧洲市场的主要投资者。〔12〕参见徐萍、姚平、Thomas Harrison:《国家安全审查:警惕中国企业出海的暗礁》,http://www.kwm.com/zh/cn/knowledge/insights/pay-attention-to-the-challenges-of-chinese-enterprises-going-overseas-20161101,2018年1月30日访问。但随“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蔓延,欧洲也开始警惕和排斥中国的国企投资者,从开始尝试利用其域内发达的竞争法到当前积极构建安全审查制度限制国企投资者的进入。目前,欧盟域内仅有12个成员国进行某种形式的外商投资审查,而欧盟层面并无统一的安全审查制度。〔13〕12个成员国分别是奥地利、丹麦、德国、芬兰、法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意大利、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See State of the Union 2017-Trade Package: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es framework for screen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Brussels, 14 September 2017),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7-3183_en.htm, last visit on January 30, 2018.针对欲“买断全球”的中国国企投资者,欧盟一度尝试利用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例如,欧盟委员会(以下简称欧委会)2016年对中国广核集团与法国电力集团的合资进行反垄断审查时,首次将中国国资委下同一行业的所有央企视为单一实体,〔14〕See European Commission DG Competition, Case M.7850 -EDF /CGN /NNB Group of Companies Commission Decision Pursuant to Article 6(1)(b) of Council Regulation No 139/20041 and Article 57 of the Agreement on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p. 11.这一不同于以往的做法被认为是采取了歧视中国国企的“双重标准”。〔15〕See Angela Huyue Zhang, Th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of State Ownership,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50, 2017, p.17.不过,欧盟认为竞争法并不足以规制中国国企投资者,于是进一步效仿美国,史上首次提出要构建欧盟的投资安全和公共政策审查制度。2017年5月欧委会在其“全球化治理意见书”中表达了对“外国投资人尤其是外国国有企业基于战略理由收购欧洲关键技术公司”的担忧。〔16〕See EU, Reflection Paper on Harnessing Globalisatio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reflectionpaper-globalisation_en.pdf, p.15, last visit on January 8, 2018.是年9月公布了《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框架》,在详细分析了流入欧盟的外商投资情况后,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外国投资审查的制度框架,尤其强调要加强审查外国国企对欧盟高科技企业和战略行业的收购。〔17〕See EU Commission, Welcom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hile Protecting Essential Interests (September 13, 2017), https://ec.europa.eu/transparency/regdoc/rep/1/2017/en/com-2017-494-f1-en-main-part-1.pdf, last visit on January 8, 2018.欧委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同时在欧洲议会的国情咨文中声称,“欧盟目前和未来都不会是‘天真的自由贸易者’……如果外国国企要收购欧洲的港口、能源设施或国防科技公司,那么必须要透明,且接受安全审查和讨论。”〔18〕同前注〔13〕。尽管欧盟关于安全审查制度的构建尚在激烈讨论中,但其态度与立场的重大转变已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的海外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对此,有律师指出,中国企业在投资并购中会被要求承担与安全审查挂钩的“分手费”,要为“分手费”提供银行保函或现金保证,使得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19〕同前注〔12〕,徐萍、姚平、Thomas Harrison 文。可见,中国国企在欧洲同样将会因“投资者”身份而面临更为严格的投资审查和准入门槛。
除此之外,西方对中国国企的歧视已从国际市场准入扩展至投资争端解决领域,使国企获取国际性法律救济窒碍难行。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是投资者获取投资保护的重要救济方式,但在近期中国国企投资者向东道国提起的两起投资仲裁案(2010年的“黑龙江三公司诉蒙古案”和2014年“北京城建诉也门案”〔20〕1.China Heilongjia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 Technical Cooperative Corp., 2. Beijing Shougang Mining Investmant Company Ltd., and 3. Qinhuangdaoshi Qinlo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o. Ltd. v. Mongolia (PCA Case No. 2010-20);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v. Republic of Yemen, ICSID Case No. ARB/14/30,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31 May 2017).)中,东道国就以中国国企是“政府代理人”而非“合格的投资者”为由提出管辖异议。可以预见,中国国企投资者日后若因在东道国遭受投资损失而寻求投资仲裁救济,国企身份必然会成为争议的焦点和获取法律救济的障碍,这必对中国海外近12万亿庞大的国有资产〔21〕参见《国资报告:境外国资已超12万亿资产流失涉5宗最》,http://f i nance.sina.com.cn/china/20150616/085522442830.shtml,2017年11月8日访问。的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在此背景下,如何解决中国国企投资者的国际生存危机,如何坚持中国国企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便成为摆在学者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笔者认为,通过革新中国投资协定,引入国企投资者保护机制,应该是在国际投资领域甚至整个国际经济领域全方位地为中国国企身份正位并提供有效保护的可行方法。
二、国企投资者保护的困境归因于制度缺陷
结合国际投资法的理论与实践不难看出,中国国企投资者未能获得充分投资保护的根源在于投资保护制度本身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投资者”定义条款及国企身份判断规则上存在立法漏洞。
(一)模糊的“投资者”条款及法律风险
根据国际投资法中“对人管辖”的要求,国企投资者要获得投资协定下的保护取决于“投资者”定义条款,但定义的模糊可能导致“国企投资者”不是“适格投资者”的法律风险。确实,多数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都只概括规定“投资者”而未专门规定国企投资者,〔22〕OECD调查显示,近84%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定义条款并未明确提及国企、国有投资基金(比如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和政府投资者,没有基于所有权来源的不同而对投资者进行区分。See Y. Shima, The Policy Landscape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by Government-controlled Investors: A Fact Finding Survey, OECD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2015/01, OECD Publishing, p. 5, http://dx.doi.org/10.1787/5js7svp0jkns-en, last visit on January 20, 2018.联合国贸发会一份报告也曾指出,若无除外规定,国企通常就可获得国际投资协定下的保护。〔23〕See UNTAD,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IIAS (UNCTAD Serie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p. 43.尽管如此,模糊性立法显然只适合以私企投资者为主的西方国家,而不利于保护数量庞大且备受“国家资本主义论”攻击的中国国企投资者。
首先,概括性规定使得条约内容不具有确定性,中国传统的“投资者”条款会招致私人投资者可获而国企投资者不能获得投资保护的解读。中国投资协定在界定“投资者”时往往只概括规定“自然人”和“经济实体”,虽然此立法技术可避免突出国企的特殊性,但国企因政府股东的存在表现出不同于私企的“公私混合”特性,在寻求投资保护时极易被认定为不是“私人投资者”。以ICSID为例,其章程明确规定ICSID的管辖范围只限定于“私人投资者与国家”间的投资争端,〔24〕See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Directors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18 March 1965), para. 9.创设之初的目的也是旨在鼓励私人国际投资而非公共的国际投资。〔25〕See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Directors on the Convention of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1965R (1993) 1 ICSID Rep. 23.很显然,国企投资者的诸多特殊性导致其难以归为或等同于“私人投资者”,若投资协定中又不对其投资者地位予以明确界定,实践中就极有可能被解读成非适格的投资者而被排除在投资保护的范围之外。这也是为何西方学者和律师一直质疑国企投资者是否属于私人投资者,是否有资格就其与东道国间的投资争端提起ICSID仲裁的原因之一。〔26〕See Mark Feldma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Claiman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CSID Review, 31(1), 2016,p.25; Paul Blyschak,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When Are State-Owned Entities and Their Investments Protect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 (2), 2011, p.19.
其次,“投资者”概括性条款可能引发非对称立法问题,从而产生外国国企属于“投资者”而中国国企不属于“投资者”的解释。实践中已有缔约一方主张在投资协定中规定其国内的投资者包括国企,但中国仍采模式化的“投资者”概括性条款的做法。例如,中国与卡塔尔《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1999年,以下简称《中国—卡塔尔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条款规定,卡塔尔的“投资者”包括“卡塔尔的公民、法人和政府”,其中“法人”包括“国内的公共组织、公共和半公共实体以及卡塔尔国政府”,而中国的“投资者”只宽泛地规定“自然人和经济实体”,并未专门指明包括国企。〔27〕《中国—卡塔尔投资协定》(1999年)第1条第2款规定:“‘投资者’一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具有其国籍的自然人;(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设立,其住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经济组织。在卡塔尔国方面,系指:(一)具有卡塔尔国国籍的公民;(二)按照卡塔尔国立法组建,其住所在卡塔尔国领土内的法人,包括公司、总公司、公共组织、公共和半公共实体;(三)卡塔尔国政府。”《中国—加纳投资协定》(1990年)第1条也有类似之规定。从法律解释学中的“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规则看,一方明确规定投资者包括国企而另一方却无对称性的规定,这种非对称式立法极有可能导致对中国国企投资者不利的解释。
最后,“投资者”模糊性条款在投资仲裁中不仅会引发国企身份之争,而且会导致国企投资者是否受保护的决策权转移至第三方机构。尽管当前中国投资者提起的投资仲裁案并不多,但只要中国投资者属于国企,其身份问题就会成为被申请方提起管辖权异议的重要理由。〔28〕截至2018年1月,中国投资者提起的投资仲裁案共计6起,其中“北京城建诉也门案”与“黑龙江三公司诉蒙古案”中的中国投资者皆因国企身份被申请方提起管辖权异议。譬如,在“北京城建诉也门案”中,被申请方就以北京城建(国企)属于“政府代理人”为由提起属人管辖权异议,声称“北京城建并不符合《华盛顿公约》第25(1)条项下 ‘缔约另一方国民’的资格要求。”〔29〕同前注〔20〕,“北京城建诉也门案”第29段。尽管仲裁庭最后驳回了被申请方的异议而认定城建具有投资仲裁资格,但是,鉴于当前投资仲裁机制的“碎片化”以及裁决不一致性等问题,〔30〕比如,在“间接征收数额”条款是否包括征收本身的问题上,“黑龙江三公司诉蒙古案”与“北京城建诉也门案”的裁决结果截然相反,前者的仲裁庭作出否定性裁决从而驳回了中国投资者的仲裁申请。尚不能完全排除中国国企被裁定为非“适格投资者”之风险。为避免在投资协定适用中因利益驱动的各种解释之争以及投资仲裁庭不可测的“司法造法”问题,确有必要对中国传统的投资者定义条款作出修改,明确规定国企投资者的法律地位。
(二)身份判断规则的漏洞及滥用
国企投资者的身份判断与法律地位属于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投资协定规定国企属于“投资者”只是其获得投资保护之前提,若想真正获得投资保护,还须以商业身份而非政府身份行事,即要符合“商业判断标准”。国际投资法采用“商业判断规则”来判断国企身份和行为属性,〔31〕参见黄志瑾:《中国国有投资者参与国际投资的规则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该方法源自Broches标准〔32〕该标准最早由ICSID“设计师”Aron Broches提出,即国企投资者若为“政府代理人”或“履行基本政府职能”,则其投资仲裁申请会被拒绝,反之则会被接受。See Victor Essien, Aron Broches, Selected Essays, World Bank, ICSID, and Other Subjec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p. 202.以及反映了国际习惯规则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简称《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5条和第8条内容。〔33〕《国家责任条款草案》 第5条规定,依授权而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个人或实体行为会被视为国家行为,此点类似于“Broches标准”中的“政府代理人”;第8条规定,个人按照国家指示或在国家指挥、控制下的行为会被认定为国家行为,该点则类似于“Broches标准”中的“履行基本政府职能”。不过,与“Broches标准”相比,经过长期编纂和研究而形成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5条和第8条在规则内容上更为明确,也更具有实践指引意义。尽管在如何区分国企“商业性行为”与“政府行为”的问题上被认为已有适用法和国际习惯法的实质性指引,〔34〕同前注〔26〕,Mark Feldman文,第 26页。但事实上“商业判断规则”存在严重的缺陷,难以有效判定国企的真实身份而致对国企投资者不利的保护。
具体而言,一方面,“商业判断规则”提供的国企身份判断的基本规则框架过于抽象,欠缺可操作性。投资仲裁实践在规则适用过程中并不正面判断国企的“商业身份”而是考查其“政府身份”,即主要考察国企是否为“政府代理人”和“政府职能的行使”。“政府代理人”可直接依据是否存在授权等形式作出判断,但如何判断不具备授权等形式要件的“政府职能的行使”(即政府控制问题)却极为困难。作为法律渊源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8条对“个体按照国家指示或在国家指挥、控制下的行为会被认定为国际法上一国的行为”的规定极为抽象,对此,该条的评注曾试图解释称个体与国家间存在真实联系的连接点是“国家指示、指挥和控制”。〔35〕See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with Commentaries 2001, p.47.对国企而言,如果其受到“国家指示、指挥和控制”而与国家存在“真实的联系”,那么相应的行为就会被认定为国家行为,其本身也可能被认定为“政府代理人”而非独立的商业主体。但是,第8条对国有股、人事权、财务权等哪些指标构成国企被政府控制的标准并无进一步的规定和指引或发展出具体的证据规则,由此引发的实践适用困难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法和国际投资法的司法实践在运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8条对国企进行身份判断时都存在严重的分歧或误用,〔36〕See Jaemin Lee, 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Government-Affiliated Entiti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The Danger of Blurring the Chinese Wall Between ‘State Organ’ and ‘Non-State Organ’ as Designed in the ILC Draft Article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49(1), 2015, p. 117.亦未能发展出具体的操作规则。例如,中美在WTO反补贴领域数十年的法律之争与较量,就是因为各方就国企“公共机构”属性分别提出了“政府控制说”“政府功能说”“政府权力说”等学说,〔37〕参见陈卫东:《中美围绕国有企业的补贴提供者身份之争:以 WTO相关案例为重点》,《时代法学》2017年第3期。而WTO对该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过程,例如,在中国诉美国的“双反措施案”(DS379)中,WTO上诉机构在判断中国商业银行是否构成公共机构时抛弃了政府占股比例为主的形式判断标准,发展出重实质的“有意义的控制”标准。〔38〕See 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 Appellate Body Report (WT/DS379/AB), para. 318.但遗憾的是,WTO也未敢进一步界定何谓“有意义的控制”,只是称“政府所有权只是判断国有企业是否为‘公共机构’的证据之一,对国有企业的核心特征、企业与政府关系的认定必须综合所有证据作出。”〔39〕同上注,第317段。
而在“中国城建诉也门案”中,尽管也门政府声称中国城建受国资委和公司内部党委监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政治与社会责任,应是“政府的代理人”,〔40〕同前注〔20〕,“北京城建诉也门案”第37~38段。但仲裁庭认为,这些公司控制机制在中国的国企中并不足为奇,最终以“问题的关键并非国企的公司结构而是其于具体情境下行为的性质”为由,认定中国城建在也门建造航站楼的行为具有商业性质。〔41〕同上注,第39~40段。虽然此案的仲裁庭作出了对中国国企有利之裁决,但是该裁决并不具有先例性,而且仲裁庭避开了对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是否必然会造成对国企的控制等问题的阐述,而这恰是“国家资本主义论”攻击中国国企身份的重要论据。
受意识形态及政治因素的影响,国企身份判断规则在实践中极易因制度缺陷而被滥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常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作为证据直接推定中国国企是政府控制的实体或政府代理人。美国对外资安全审查出现了扩大化倾向,常将中国国企的收购活动视为政府控制的、有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交易。〔42〕同前注〔1〕,孔庆江文。例如,当WTO上诉机构在中国诉美国的“双反措施案”(DS379)中发展出“有意义的控制”标准又尚未明确其内涵时,〔43〕同前注〔38〕,第 318 段。美国趁机通过发布执行DS379的报告,宣称政府绝对控股权、给予政策优惠、受“国家产业政策指导”、管理层由政府和党组织任命、国资委监督体制等事实,是中国政府对国企实施“有意义的控制”和“履行政府职能”的证据。〔44〕See Off i ce of Policy, Import Administration, Section 129 Determination of the Countervailing Duty Investigations of Circular Welded Carbon Quality Steel Pipe; Light-Walled Rectangular Pipe and Tube; Laminated Woven Sacks; and Off-the-Road Tir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Analysis of Public Bo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TO Appellate Body’s Findings in WTO DS379, dated May 18, 2012.这些主张已成为当前欧美在国际上指诟中国为非市场经济体的依据,是“国家资本主义论”向顶峰发展的助推器。但是,美国未经严谨和全面的论证就径直以所罗列要素推导出国企是政府的代理人,不仅欠缺逻辑上的科学性,而且有将法律问题政治化之嫌。不可否认,中国当前并不完善的“政府主导经济”易致国企与政府的关系呈现出模糊化特点,但在个案审理中,仍有必要依据明确和可信的指标进行判断。毕竟,企业政治关联现象在大多数国家都广泛存在。〔45〕在西方国家,私营企业或大财团也会通过商业贿赂、院外游说、支持总统选举、政府非对称管制等方式获得与政府的特殊紧密关系。参见刘凝霜:《政治关系、非正式制度与民营企业发展路径——基于研究脉络与理论逻辑的双视角考察》,《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10期。故此,为了加强对国企投资者的保护,若暂不能发展出“政府控制”判断要素的习惯规则,就需要考虑是否可通过特殊规则来加强对国企身份的确认和保护。
三、国企投资者法律地位的明晰化
(一)以“投资者”条款明确国企投资者的法律地位
传统的国际投资协定较少专门规定国企投资者,中国以往的投资协定也未专门规定国企投资者或其他相关条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国企已成为“贸易投资协定中一个绕不开的议题”〔46〕韩立余:《TPP国有企业规则及其影响》,《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尤其是在西方积极以贸易投资协定规制国企的背景下,中国更需要未雨绸缪,在投资协定中明确国企投资者的法律地位。
通过投资协定的“投资者”条款界定“国企投资者”在国际法上具有可行性。首先,尽管传统的国际投资协定很少专门规定国企投资者,但并不乏将其纳入“投资者”条款并明确对其进行投资保护的实践。1998年OECD在起草《多边投资协定》(MAI)时就曾设置过国企定义条款,规定“除附件另有规定外,国企是指缔约方通过所有权益而拥有或控制的企业。”〔47〕Negotiating Group on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 22 April 1998, p. 39.尽管当时有国家质疑是否有必要专设国企定义条款,但此举表明,在国际投资条约多边化的早期,已经有国家意识到投资条约不应忽视国企投资者问题。此外,OECD的研究也进一步表明,越来越多的投资协定倾向于在双边投资协定(BIT)的投资者定义条款中明确规定政府控制的投资,将国企投资者纳入“投资者”范围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48〕同前注〔22〕,Y. Shima文,第 12页。据称,在被OECD调查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有近16%的投资协定明确规定国企投资者,有6%的投资协定甚至将缔约方或缔约方政府纳入到“投资者”定义范围中(主要是盛产石油的国家)。〔49〕同上注,第5页。其中,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签订的投资协定,有五分之四会在“投资者”定义中明确规定“国企”,日本和阿联酋签订的投资协定有三分之二以上也对其作出明确界定。〔50〕同上注,第13页。尽管西方国家在投资协定中界定国企投资者主要是出于规制之目的,但此类立法举措对中国而言却可起到特殊的保护作用。因此,中国的投资协定若仍固守传统的投资者定义条款、意欲以模糊性立法避免突出国企的特殊性,反倒不利于对庞大的中国国企投资者的保护,亦与国际投资协定的立法实践与发展趋势不符。
其次,明确国企投资者的法律地位符合国际投资实践多元投资者发展的现实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活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经济体性质和形态各异,既有公有企业、私有企业、混合制企业,还有各类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甚至非实体类的投资者。例如,在宣称仅存“公共企业”而无营利性国企的美国,其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排名全球第一。〔51〕See SWFI, SWFI League Table of Largest Public Fund, https://www.swf i nstitute.org/fund-rankings/, last visit on September 3,2017.从本质上看,不能仅从所有制来源划分并歧视不同的投资者,而应平等地对待参与全球经济的各类投资者,或者要对所谓的“私人投资”作出“具有私人投资特征的任何投资”的演化解读。换言之,没必要固守资本来源的二分法,将国际投资划分为私投资与公投资,将投资者划分为“私人投资者”与“国家投资者”。
最后,从《华盛顿公约》〔52〕目前 ICSID已有161名成员,属于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的最重要的多边机制,具有极高的接受度。参见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about/Database-of-Member-States.aspx, 2017年9月2日访问。的规定及投资仲裁实践看,国际投资法认可国企投资者参与国际投资的身份和权利。其一,《华盛顿公约》相关条款具有开放性,为新型投资者享有投资仲裁救济等保护预留了空间。比如,公约第25条规定,提起ICSID仲裁的申请人必须是“另一缔约国国民”,而未采用“私人投资者”的措辞。其二,《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史表明国际社会当时预期投资者会包括国企投资者。据《华盛顿公约》草案评论记载,缔约方当时已注意到“另一缔约国国民”并不限于私有企业,“允许政府所有或政府部分所有的企业以申请方与被申请方身份参与同另一缔约国的投资仲裁。”〔53〕Christoph H.Schreuer, Loretta Malintoppi, August Reinisch, Anthony Sinclair,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61.公约的主要起草人和ICSID“设计师”Aron Broches早年亦提出:“私人投资与公共投资的传统区别即使未过时,也已毫无意义。”〔54〕同前注〔32〕,Victor Essien书,第 202页。其三,ICSID在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银行诉斯洛伐克管辖权异议案”中也确认,“《华盛顿公约》的制定过程确实表明了第25条的‘法人’(投资者)并不限于私有企业,还包括政府所有或政府部分所有的公司。”〔55〕Ceskoslovenska Obchodni Banka, A.S. v. The Slovak Republic, No.ARB/97/4 (decision on objection to jurisdiction), para.16.
可见,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史表明,国企投资者可像私人投资者一样获得投资保护。但是,鉴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论”盲目地排斥中国国企参与国际投资活动的现状,为避免国际投资体制碎片化之下条约解释的不确定性,中国有必要也完全可以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明确规定“国企投资者”的法律地位。否则,诚如学者所言,“不能有效保护我国对外投资者的BIT将很难说是一个成功的BIT。”〔56〕单文华、张生:《美国投资条约新范本及其可授受性问题研究》,《现代法学》2013年第5期。修正后的投资者条款可以使得中国国企投资者能像私人投资者一样平等地获得投资协定的保护,在发生投资争议申请仲裁时,国企投资者表面上可被认为满足“合格投资者”的要求,被诉的东道国如欲提起管辖权异议、质疑中国国企投资者的身份,则需要为此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当然,将国企纳入投资者条款范畴也仅是其获得投资保护的前提或初步条件,若需获得有效保护还要满足身份判断规则。
(二)完善国企投资者的身份判断规则
既然国企身份判断的国际习惯规则尚存在模糊之处,为避免西方国家对模糊规则的滥用或抢先发展出对中国不利的规则,中国不妨可主动在投资协定中对涉及国企行为性质和身份判断等设立特殊规则,以优先于国际习惯规则的适用。
从国际法理论角度看,国家可在投资协定中自设“政府职权的行使”判断标准并优先于国际习惯法的适用。具体而言,一方面,依据条约法原理,国家享有缔约自由,国家之间可自由议定并缔结不违反国际强行法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条约。各国在谈判双边投资协定与自由贸易协定时,完全可自由协商达成解决国企身份判断标准问题的规则;另一方面,《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本身亦规定,国家可另行制定国家责任问题方面的特殊规则并可优先适用。该草案第55条“特殊法”(Lex specialis)规定,“在并且只在一国际不法行为的存在条件或一国国际责任的内容或履行应由国际法特别规则规定的情况下,不得适用本条款。”该草案的评论称,第55条特殊法的规定正是对“特殊法优先”规则的反映,可预见缔约方有可能缔结偏离国际习惯法的与归因有关的问题。〔57〕See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with Commentaries, 2001, p. 140.既然《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4条、第5条和第8条有关于国家行为归因以及国企身份判断问题的规定,国家自然也可另行约定特殊规则。有国际法学者指出,多数国际投资仲裁案之所以依照国际习惯法来解决国企的行为责任归属,是因为相关的投资协定本身对国企投资者的归因问题规定不明。〔58〕See Carlo de Stefano, Attributing to Sovereigns the Conduc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wards Circumvention of the Accountability of States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CSID Review, Vol. 32, No. 2, 2017, p. 272.国企的行为责任归属本身同属于国企行为性质或与身份相关的问题,基于此,中国完全可在投资协定中自设“政府职权的行使”判断标准以及责任归因等特殊规则。
从国际投资仲裁实践看,确实存在未依《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条款而依投资协定“特殊规则”判断国企身份和行为性质的一些案例。最典型的一例为2011年美国投资者“Adel诉阿曼政府投资仲裁案”,〔59〕See Adel A. Hamadi Al Tamimi v. Sultanate of Oman, ICSID Case No. ARB/11/33, Award (3 November 2015).该案仲裁庭依《美国—阿曼自由贸易协定》(FTA)条款而非《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条款来判断国企的行为性质。本案的投资争议因阿曼采矿公司单方终止其与申请方的采石场租赁合同而引发,申请方要求阿曼政府赔偿其投资损失,理由之一即为阿曼采矿公司单方终止租赁合同的行为归属于阿曼政府。〔60〕同上注,第317段。阿曼采矿公司高度类似于中国的央企,其于1981年依据11/81皇家法令成立,最大股东阿曼石油矿业部占股99%,董事成员包括皇家法令指派的政府部长。很显然,如果该案适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5条和第8条规定,阿曼采矿公司极有可能因行使政府职权或受政府控制而被认定为“政府代理人”,其终止租赁合同的行为即为政府的行为。但是,ICSID仲裁庭最终判定阿曼采矿公司终止租赁合同的行为性质属于“私行为”而非“公行为”的关键点在于法律适用上选择了特殊法优先适用的原则,依《美国—阿曼自由贸易协定》第10.1.2条而非《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归因条款进行事实判定。第10.1.2条规定,“如果一缔约方的国企或其他人行使政府授予的任何管理、行政或其他政府权力,那么缔约方在投资章节下的义务将适用于该国企或其他人。”显然,该条对应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5条的授权条款而不包括第8条的“政府控制”条款,被仲裁庭认为是范围狭窄的标准,阿曼采矿公司既未获得政府授权也未受到政府控制。〔61〕同上注,第320段。对于阿曼采矿公司是否因其他国家机关的控制和影响而可被认定为“行使政府职能”这一难题,仲裁庭专门强调,《美国—阿曼自由贸易协定》第10.1.2条“有效排除了控制的归因标准”,并且相关的事实也无法证明阿曼政府对阿曼采矿公司具有真正的控制。〔62〕同上注,第341段。由是可见,若无《美国—阿曼自由贸易协定》第10.1.2条关于政府行使职权的特殊判断规则,该案的国企行为就会依国际习惯规则被认定为政府行为,被申请方阿曼政府很可能就要对申请方承担间接征收的损害赔偿责任。
基于此,中国完全可在双边投资协定中主动为“行使政府职权”“政府控制”以及国企行为或身份性质等问题设立判断标准,并优先于国际习惯规则适用。此举无论在国际法理论还是国际法实践上均可找到支撑依据。但应强调的是,中国在投资协定或自由贸易协定中设置国企行为或身份判断规则,应是对国际习惯法中“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再法典化(re-codif i cation)或具体化,而不能与国际习惯法直接冲突或违背客观实际。正如学者所言,“Adel诉阿曼政府投资仲裁案”所优先适用的《美国—阿曼自由贸易协定》条款,“不过是提供了《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5条中习惯规则之非穷尽性的细化规定,并没有偏离国际习惯规则的基本内容。”〔63〕同前注〔58〕,Carlo de Stefano文,第 273页。故此,中国在主动设置国企身份判断标准的特殊规则时也不能完全背离国际实践,要想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国企身份受歧视的问题,仍须通过国内改革措施让商业类国企发展成为真正独立的商业主体。
四、国企投资者保护制度重构的路径及新立法
(一)制度重构的路径:革新双边投资协定
要修正中国国企的投资保护制度,必定要革新中国现有的投资保护体系,即修改现在的协定条款或在新缔结的投资协定中增设国企条款。但是,条约修改历来是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的难题,WTO、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当前就是因为正式的修正条款难以启动或无望被通过而陷入发展困境。〔64〕参见刘雪红:《论条约演化解释对国家同意原则的冲击》,《法律科学》2017年第3期。革新中国的投资协定同样难度极大,因为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往往属于消极的投资规则更新者,要体系性地修改数量庞大的投资协定或“史无前例”地在新协定中增设国企条款,几无可能。但是,当前国际投资法领域正处于全面革新的时代,欧美国家亦积极重构投资协定,中国可依此契机借助自身的需要和实力推进国企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建立。
首先,国际投资协定正处于全面革新时代,〔65〕See UNCTAD, 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p. 126.中国面临重构投资保护体系的历史机遇,可借机推进国企投资者保护制度。联合国目前正积极呼吁各国在缔结新约的同时修改旧的投资协定,并通过推出各种指南引导国际投资协定条款的更新,理由在于当前生效的约95%的(超过2500个)国际投资协定缔结于2010年之前,其中的相关内容模糊不清、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是当前投资者滥诉以及东道国管制权被侵蚀等问题之根源。国际社会已意识到,要解决这些“有牙齿会咬人”的旧协定,〔66〕同上注,第128页。就需要从根本上重构规则。故此,联合国贸发会近年通过年度投资报告的形式发布了可供借鉴的投资协定新条款,并通过《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框架》(2015年)呼吁新一代的投资政策要加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发展维度,平衡国家和投资者的权利与义务,体系性地管理好复杂的国际投资体制。〔67〕See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5, p. 6.随着中国双重投资国身份的转变,中国的投资保护体系也要依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念进行重构。〔68〕参见王彦志:《中国在国际投资法上的身份转换与立场定位》,《当代法学》2013年第4期;王鹏、郭剑萍:《论中国直接投资法律体系的重构——监管逻辑、历史演进与政策挑战》,《国际经贸探索》2016年第2期。但是,与西方的关注点不同,中国投资者以国企投资者为主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在平衡投资者保护与东道国管制权问题上必然要侧重于强化对国企投资者的保护。
其次,发达国家灵活更新投资协定范本并与时俱进地修改投资协定,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尤其是在立法技术方面可为中国提供借鉴。比如,美国与加拿大(2012年)、挪威(2015年)、印度(2015年)分别根据新形势及时更新了投资协定范本,并积极推进旧的双边投资协定的重新谈判。尽管在新身份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下,欧美最新的投资协定更注重于本国作为东道国的管制权维护,但鉴于其一直重视投资自由化与投资保护,立法技术又甚是娴熟,因而与投资保护相关的条款仍构成极佳的范本。有学者分析认为,美国对投资定义、公平与公正待遇、间接征收等的规定“内容全面充实、严谨、精确”,总体上坚持了高标准的保护原则。〔69〕参见杨丽艳、张霞:《论美国 FTA 投资规则的特点及其启示》,载冯军、陈晶莹主编:《国际贸易法论丛》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3页。事实上,中国与澳大利亚、瑞士、秘鲁、新西兰等国近些年新缔结的贸易协定也已进入了更新谈判,〔70〕中国与澳大利亚、瑞士、秘鲁、新西兰缔结的贸易协定分别于2015年、2013年、2009年、2008年生效。在此背景下,确有必要通过借鉴欧美先进的立法技术,及时修订缔结于上世纪90年代的双边投资协定,消弥对中国投资者(尤其是国企投资者)保护的立法漏洞。
最后,中国完全可以利用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话语权,〔71〕参见王燕:《自由贸易协定下的话语权与法律输出研究》,《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期。选择投资与保护并重的策略,在投资协定中纳入国企投资者保护制度。与西方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相比,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势头迅猛,尤其是2015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是中国实力和话语权的体现。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中国国企积极参与了那些耗资大、风险大、回报周期长的重大基础项目的建设。〔72〕参见《国企领衔一带一路十大项目 大部分对外投资企业都是国企》,http://www.sohu.com/a/133211421_119038,2018年1月31日访问。但是,中国国企在“一带一路”的投资本质上并非“马歇尔计划”,因而中国可率先在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协定中纳入国企投资者保护条款,并作为模板逐步推广。此举不仅有利于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企投资者的保护,也有利于减轻中国与欧美谈判贸易投资协定时就国企问题受到的压力。
(二)制度重构的内容:新型国企投资者保护条款
中国在革新投资协定纳入国企投资者保护条款时,在具体的立法设计上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技术,统筹、审慎地规定国企投资者地位条款。即在投资者定义条款中增加“国企投资者”类别,明确其“投资者”的法律地位。当前明确将国企纳入“投资者”定义条款的投资协定,多数先定义“投资者为缔约一方的自然人或企业”,同时单独界定“企业”为“任何私有、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的实体”。〔73〕采用此种立法方式的有墨西哥—印度BIT (2007)、奥地利—格鲁吉亚BIT (2001)以及美国2012 BIT范本等。同前注〔22〕,Y. Shima文,第12页。此一方式与《中国—卡塔尔投资协定》直接规定国企不同,不仅明确界定了国企是“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的实体”,还明确规定国企与私企一样同属“投资者”,避免了因非对称性立法留下的法律漏洞。
具体而言,可借鉴美国、墨西哥等国家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践,规定“无论私有、由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实体都属于缔约一方的企业”,明确国企与私人投资者同属于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范畴。此外,通过修法或新立法的方式增设国企投资者条款时要统筹考虑对中国其他投资协定的影响,若不能同时对所有协定作出系统性更新,至少要作出可自圆其说的解释或限定性规定。比如,新近的中日韩BIT、中韩FTA、中澳FTA已明确规定“投资者”包括“缔约一方无论私有还是由政府所有或控制的企业”。但是,除此之外的100余个投资协定仍未对国企投资者作出明确规定。这种格局极有可能导致中国国企在依据旧协定主张投资保护时被认定为不属于“投资者”。因为仲裁庭在解释某一投资协定时有可能同时参考中国的其他投资协定的相似规定,会以同一问题的不同条约措辞来作出不利的推导和解读。〔74〕See P. Blyschak,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When Are State-Owned Entities and Their Investments Protect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2011, p. 48.
第二,主动在投资协定中设立国企投资者身份判断标准,可适度借鉴欧美的立法技术,明确规定“行使政府职权”的范围。例如,美国2012年投资协定范本、TPP、TTIP、CETA都对“行使政府职权”或“政府授权”作出了专门界定,〔75〕分别为美国2012年投资协定范本第2条第2款、TPP第17.3条“授予职权”条款、TTIP国企章节条款、CETA 第1.10条“行使政府授权的个人”条款。且多采用明确列举式和兜底条款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这一立法技术其实赋予了欧美在判断他国国企性质方面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是故,中国在设计具体条款时,需推出符合本国发展阶段和需要的改良版条款。一来可学习美国2012年投资协定范本第2条第2款脚注8的做法,规定“被授予政府职权”(government authority)包括以立法授予、政府命令、指令将政府职权转交给国企、个人等情形;〔76〕美国2012年投资协定范本第2条第2款脚注8规定:“为明确起见,被授予政府职权包括立法授予、政府命令、指令以及其他将政府职权转移给国企、个人或授权国企、个人行使政府职权的行为。”为进一步细化,还可借鉴TPP中的条款设计列明“监管、行政或其他政府职权”包括“征收、发放许可、批准商业交易,或实行配额、课以费用和其他规费的权力”;〔77〕TPP第17.3条“授予职权”的脚注条款规定,“监管、行政或其他政府职权的例子包括征收、发放许可、批准商业交易,或实行配额、课以费用和其他规费的权力。”二来应删除与立法授权等形式并列的“其他措施”这一兜底性规定,对于不属于列举范围的“行使政府职权”的行为,规定要依“政府控制标准”条款来进行客观和全面的判断。尽管“行使政府职权”条款往往被用于解决国企哪些行为可归因于政府这一问题,但实质上也具有明确国企投资者身份之功效,此条款的设置可遏制对国企身份过于绝对的、盲目的推断。除此之外,还要明确规定“政府控制标准”要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据规则。学者Mark Feldman曾指出,对公司控制程度的可信指标除了出资来源外还有可影响决策权和控制权的其他各种投票杠杆机制。〔78〕同前注〔26〕,Mark Feldman文,第 28页。可借鉴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相关规定,从证据规则的角度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客观判断指标,亦即要依据股本、投票权、决策人员的任命权等客观要素进行判断,并且在判断这些因素是否达到“实质性”程度时要综合考量和全面论证。
第三,在投资协定中明确国企投资者地位和身份时,要注意设置例外和保留条款以弱化特殊情形下国家的义务负担。因为在主张中国国企与私企拥有同样的投资者身份、享有同等的投资保护时,中国对国企的某些特殊待遇依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条款也应直接扩展至所有的投资者。但是,当前的中国仍处于经济转型期,国企改革仍在进行中,如果贸然将适用于国企的特殊政策普遍化,很可能会影响国家整体的制度安排。国企问题的特殊性在OECD 《多边投资协定》 起草过程中也曾获得认可,当时就有国家指出,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应允许缔约方对国企或政府限制的特定部门的特殊股份安排采取保留措施。〔79〕See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Draft Consolidated Text (DAFFE/MAI(98)7/REV1), 1998, p. 28.故此,中国在明确国企投资者保护地位时,也要注意设置合理的例外规定或过渡期,具体可参照《中加投资促进与保护协定》的规定,该协定第8条的例外条款首次设置了与国企相关的例外性内容,规定对于缔约国销售或处置国企或政府股东权益或资产时的特殊措施,不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国民待遇条款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成员与人员入境条款,该规定被认为可以有效地限制相关国企规则的扩大化适用及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80〕参见王燕:《“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协定话语建构的中国策》,《法学》2017年第2期。
五、结论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大国的角色会越发凸显,而“国家资本主义论”又造就了中国国企在国际社会的生存困境。从国际投资的发展史看,海外投资的自由主义从未离开国家保护,所有投资者的海外探索都离不开母国相关法律机制的支持。故而,中国亟需改变以往片面强调东道国的保护而忽略投资者海外保护的传统立场,积极构建有效的国企投资者保护机制。本文通过对国企问题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研究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结论。
第一,国企正常参与国际经济投资活动应获得与私人投资者同等的法律地位,不应因其“国有出资”身份而受到盲目排斥;依条约解释原理,“国企投资者”属于国际投资协定所保护的“合格的投资者”范围,但为了避免不必要之争议,最佳做法是在“投资者”定义条款中直接规定“国企投资者”,可通过系统性革新投资协定来明确国企投资者的法律地位。
第二,国企投资者只有以“商业身份”才可获得参与国际投资活动的资格,从而获得包括投资仲裁在内的各种投资保护。鉴于当前国际法对国企身份判断标准欠缺明确、可操作性的规定,国企身份判断规则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需要高度警惕西方发展该规则时将法律问题政治化。
第三,国际法理论与投资仲裁实践表明,投资协定中关于国企身份、行为性质以及归因问题的特殊规则可优先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5条和第8条获得适用。中国可在投资协定中主动对“行使政府职权”“政府控制”等问题设立细化的标准,明确国企身份判断标准的特殊规则。
总之,对于“国家资本主义论”的高压,中国有必要改变所谓的“条约建设性模糊”〔81〕“建设性模糊”是一种条约谈判或条约文本设定中常用的外交技巧,也就是说,谈判方为了在谈判过程中尽快达成共识,往往会有意将政治上的妥协或分歧隐藏在含糊的法律文本之中。具体分析可参见韩逸畴:《国际法中的“建设性模糊”研究》,《法商研究》2015年第6期。,尽可能地明确规范国企投资者问题,因为“规范越具体,条款越严谨,对投资者权益保护水平就越高,资本输出国从谈判中所获得的利益就越大。”〔82〕温先涛:《〈中国投资保护协定范本〉(草案)论稿(1):引言和“序言”》,《国际经济法学刊》2011年第4期。当然,从长远看,加强中国国企的市场化改革,确保从事经济活动的国企具有独立的商业主体身份和良治结构才至为关键,只有内外兼修才能在国际上获得有效身份认可和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