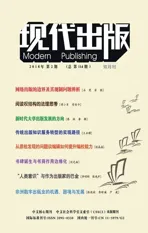大学出版30年:大学为根,学术为魂
2018-04-02蒋东明
◎ 蒋东明

研究中国大学出版的30年历史,离不开探讨“大学”和“出版”两方面的内涵和规律。我以为,众多大学出版社尽管在规模、发展路径和形成特色方面不尽相同,且精彩纷呈,但他们的本质特征却殊途同归,都深深地烙上“大学”的印记,从出版方面为高等学校的发展做出一份贡献;也都遵循“出版”的规律,为浩瀚的书林植入最具文化积累意义的大树。
一、教授办出版:挥之不去的书生意气和优雅气质
20个世纪80年代,为适应高等学校培养人才和教材建设的需求,各重点大学都以申办出版社作为重要任务,一大批大学出版社应运而生,80多家大学出版社就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加上各省人民出版社中的编辑室也纷纷拓展为独立的专业出版社,几乎一夜之间,全国成立了数百家出版社,这是我国出版业大发展的时代。
毛泽东主席曾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大学委派学者办出版社,就是播撒携带大学精神的种子。我曾经询问过当时的学校领导,他们很清楚,我们国家成立出版社是实行“审批制”,要办个出版社很不容易,机不可失。厦门大学出版社是1985年成立的,但早在1981年,根据国家教委的要求,学校就开始了申办出版社的工作。申报材料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学校如何提供办社的条件,特别是班子的人员配备。当时的申报班子名单中,全都是学界的显赫人物。尽管最后成立出版社时,班子的实际配备人员有所变动,但基本上都是学校的著名学者当家,教授办出版已是大学出版的普遍现象。更重要的是,普通编辑也大多是从教师转行或兼职,他们基本上对出版业毫无概念和经验,把出版工作与教学科研工作相融在一起也就顺理成章了。大学出版社的从业人员,特别是编辑,大多是从相关专业的优秀毕业生中招聘,较少选自出版专业,这是对学术出版人才要求所致。
出版本是优雅的事业,大学教授办出版,“书生本色”就构成了大学出版人与生俱来的优雅气质。当年,出版社的许多领导在学术上已经名声赫赫,他们会把自己对大学出版的理解、对学术团队建设的认知带到出版工作中。而奋战在一线的出版人基本上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和知识涵养,绝大多数人没有“象牙塔”外的阅历,他们很好地传承了大学学者的优良传统,在出版的纯真使命与市场竞争的交错中,依然保持难能可贵的学术追求,“书生本色”成为大学出版社的天然潜质。他们一直秉持着“学术为本,进取奉献,与人为善,诚信做事”的企业文化,虽然“书生之气”在市场竞争中有时不适应,但岁月过往,我们看到大学出版人的书生气质却是历久弥新,优雅恒在,体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穿透力。
但说到底,出版工作内在的专业规律和实践技能以及对企业经营、市场竞争意识的要求与一般教学科研工作有很多不同。地方出版社一般有新闻出版局(或后来的出版集团)统一管理,甚至几家出版社都相处同一大楼,来往密切。管理者精通业务,多为职业出版人。而大学出版人的从业知识,大多是从大学出版行业组织的培训交流而来,从走访兄弟出版社学习得来。所以,各大学出版社人员之间的交流特别频繁,对兄弟社的经验会特别重视。
大学出版社在严把出版的导向关问题上,认识有个过程。在初创时期,由于管理经验不足,经营压力较大,出现一些不良倾向。1995年,我参加了由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高校出版工作会议,会议对大学出版社存在的把关不严、“买卖书号”等问题进行认真反思。主办者在会议上反复强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重要性,还将一些出版社出版的有问题的书带到各个小组展示,逐一讲解问题所在,并整顿了多家大学出版社,有的撤销停办,有的停业整顿。这次会议对大学出版社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我社陈社长就说过:“搞科研,你99次失败,第100次成功,你就成功了,是一条好汉;而搞出版,你出了99本好书,出了1本坏书,你就是失败者。”
大学出版社的学者当家,可以作为第一代领导的典范而载入史册。第二代领导,则大多数是有出版经验又具学者风范的出版人。他们充满出版情怀,又比较熟悉出版业务。在他们之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大学出版人,把大学出版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成为大学出版业最为辉煌时代的领跑者。
如果把近几年新登上大学出版的管理者作为第三代领导来看,由于大学自身管理的要求,这一代的领导许多都是从学校其他部门轮岗过来的。出版社作为学校的一个处级单位,任期的限制使得干部的轮岗交流成为常态。但我们也看到这些新的领导,他们大多也是专业的精英,肩负着大学出版的使命,保持着大学学者的风范,在出版业面临挑战的新时代,努力适应,养正出新,做出了不错的佳绩。但也不可否认,大学出版社的主要领导频繁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学出版社的软肋。而各大学出版社自2000年以来,人员基本上不再从学校事业编制内引入,由出版社自行招聘。员工的“校编”和“社编”出现的“双轨制”,也显现出诸多矛盾,呈现出对母体大学归属感的淡化,对大学出版学术使命认同感的弱化。不少大学出版社已经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希望从“社编”人员中选拔部分优秀员工向“校编”转变,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在这个问题上,最好的突破口则是大学在人事制度上的改革,让不同编制的人员都享有同样的权益,进而加深对自己学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二、出版在大学:根植沃土独有优势
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主办单位,他们在考虑让学者办出版时,很显然就已经埋下对这家出版社的期待。我们还可以从当时教育部的批文中解读办大学出版社的初心。虽然无法逐一了解各大学出版社的批文内容,但相信其要求是基本相同。官方对厦门大学出版社成立批复文件的主要内容如下:
同意你校正式成立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社为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独立核算。主要出版高等学校教材、教学参考书、工具书、古籍整理和科学著作,为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出版物除供应校内使用,尚可向社会发行,有的亦可进行国际交流。必须十分注意出版物的质量,发挥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为发展教育事业、繁荣学术和科研工作做出贡献。不要出版思想内容不健康,格调不高的书。必须明确大学出版社不要片面地追求利润,以对教育、科学、文化的贡献来衡量其工作的好坏。
30多年来,对照当时国家对大学出版社的办社要求,可以说大学出版社基本上是不改初心,按照这一要求发展的。
大学出版社是作为服务大学教学科研重要支撑条件而拥有一席之地。但对于大学的领导来说,面对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压力,要想多支持出版社分身乏术。所以,对于出版社,学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政治上把好关,不要出问题,要出好书,多出学术精品,有能力就再为学校多上缴一些利润。因此,许多大学出版社都自认为是学校的边缘部门。但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大学出版社是处在主流与边缘之间。有时成绩斐然,为学校争得荣誉,跻身主流,有时又潜居在边缘,这符合出版工作的作用和坐冷板凳的特征。
大学出版社作为企业,在管理上,在改制问题上,学校对此有自己的理解。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教委分管出版的副主任韦钰就曾在一次大学出版社工作会议上说:“大学出版社是学术性较强的事业单位,实现企业化管理。”这一定性延续多年,也使大学出版社发展方向比较明确。21世纪初,大学出版社开始转企改制,其初衷是要大学出版社明确自己的市场主体地位,更好地利用市场资源发展自己。但从实践过程看,大学出版社虽然形式上转企改制,成立董事会、监事会,划入学校资产公司管理,但学校对出版社的管理和要求却没有变化,对出版社的干部任免还是按照学校处级干部管理办法执行,董事会、监事会也并未真正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有效工作,资产公司也很难深入指导出版业务。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客观上说明大学对出版社的功能要求,并不是希望他成为一般的企业,而是如何从出版方面为宣扬学校学术成果发挥作用。鉴于出版社工作的特殊性,学校都会安排一位校级领导专门分管出版社,对出版物的意识形态倾向、学术含量倍加关注。而出版社则应多争取学校的支持,让领导多了解出版社的工作,因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对出版社的支持力度。
大学出版社的生存土壤,最可贵的是拥有丰富的出版资源。大学的学者需要出版社,而出版社的编辑也最了解学者的研究动态。大学出版社的口碑,就是学校教师对出版社的口碑;大学出版社的成果,就是看是否把学校的学科优势转化成出版优势。但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大学出版社分布全国各地,其母体大学的学科特点不尽相同,所在的地域也不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处地域较偏远,学校的优势不明显,但他们却独辟蹊径,面向全国(甚至是全球)走出一条精彩之路。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地处徐州,又依托专业度很高的母体大学,也在自己的领域做得风生水起。在不同的土壤,只要因地制宜,精心耕耘,一定能有好收成。
三、学术主导出版: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大学出版社依托母体大学,以学术出版为根本,以服务教学科研为目的,这已经是大学出版人的基本共识。不管今后外部条件如何变化,这一定是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曾总结大学出版社对于大学的功能,即“挖掘学术资源,整合学术力量,培养学术新人,传播学术成果”。30年来,大学出版社在出版物的数量、大型出版项目、出版奖项、对外版权贸易和出版文化建设人才培养方面,尤其是在教育出版、学术出版领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中国出版的中坚力量。我校校长就曾经说过:“厦门大学有诸多闪光的名片,出版社就是其中亮丽的名片。”
30年过去了,大学出版社怎么走、往哪里走,这是许多大学出版人的焦虑所在。大学里普遍存在的“有高原、无高峰”的现象在大学出版社也是存在的。不可否认,一些可出可不出的书占用了大量的编辑出版力量,重复出版低水平的教材也屡见不鲜。而对滚滚而来的数字出版浪潮,出版社也显得手足无措。借用当前时髦的“融合出版”一词,大学出版社最主要的“融合方式”是要利用自己的优势,与科研人员进行“融合”。我们要瞄准一流的科研团队,寻找一流的作者(不一定是已经成名的作者),和他们真正融合在一起。要改变大学出版社为大学教学科研服务比较被动的局面,更深入地研究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哪些一流的研究,如何帮他们将这些成果出版。甚至可以利用出版社的平台,整合研究力量,寻找出版资金支持。我们要充分了解学校的一流学科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研究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选题规划,在高原中寻找高峰,迈向高峰。
大学出版社依托母体大学,又要跳出母体大学。大学出版社的真正理想,就是要出版人类对客观世界最前沿、最高水平的认知成果。在迈向一流学术高峰的过程中,只要发现是在某一领域的高水平成果,或是以当今人类知识结构还无法判断其价值,但他的探索是值得尝试的,我们都应积极去了解、去扶持、去争取出版,无论作者的国籍、地域、语种。我们无法要求作者的每项研究都尽善尽美,甚至还心存对这一研究科学性的疑惑,但我们要用科学的精神、探索的勇气,出版更多具有人类探索认知意义,具有文化积累价值的传世之作。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从利用信息技术和物联网改变图书发行方式开始,进而将知识的影响途径以最快速、最吸引人的方式牵动读者、吸引读者。对于大学出版社,其专业出版的使命没有改变,但吸引读者的方式却不可落伍。做好知识传播和服务,是我们在互联网时代面对的巨大挑战。
“蕴大学精神,铸学术精品”,这是厦门大学出版社在对“大学”和“出版”两方面的内涵和规律做出多年探索所凝练出的出版理念。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大学,其“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的大学精神将赋予更加崭新的内容;其充满出版情怀,潜心铸造学术精品的出版价值观也将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