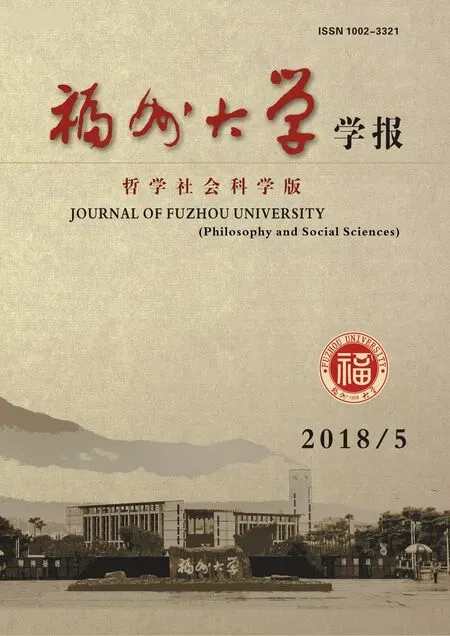韩国古代诗话中的宋诗论
2018-04-01徐安琪
徐安琪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 湖北武汉 430074)
宋诗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然历来论者好尚不同,品评各异;尊唐崇宋,议论纷纭。韩国与中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文脉相通。韩国古代汉诗源于《诗经》,新罗以来则有唐诗东渡,高丽中叶又有宋诗风靡。自高丽中叶韩国诗话诞生以来,宋诗论亦成为韩国诗话的重要论题。本文所说的“韩国古代诗话”,指的是从高丽中叶迄近世朝鲜(13世纪-19世纪)的诗话。检阅这七百年间流传下来的一百多种诗话,我以为韩国诗话宋诗论的主要内容是自得论、用事论与批评论,它们既体现出韩国诗人接受宋诗的历史轨迹,也揭示了中韩两国古代诗论所呈现出的和而不同、相通与共存的状态。
一、宋诗自得论
韩国诗话自诞生之日起,就认为宋代诗歌具有自是一家的特色。这种崇宋的诗论是韩国诗话的重要内容,借朝鲜正祖李算之语以言之,可称之为宋诗自得论。李算(1752-1800)编有中国诗歌总集,其《诗观·义例》论及宋诗时,借康熙间吴之振《宋诗钞序》之语云:“宋诗盖能变化于唐,而以其所自得者出之,所谓毛皮落尽,精神独存者是也。”[1]宋诗自得虽不是李算的创见,却道出了韩国诗话的崇宋意识。“自得”者,自得其体性也,即谓宋代诗歌具备了自成一家的体貌。兹依韩国诗话发展的自然阶段分而论之。[2]
(一)高丽中后期(13-14世纪),约当中国南宋金元时期。“宋诗自得论”的意识萌生于高丽中期。[3]北宋末季,中国诗坛一方面是苏(轼)黄(庭坚)诗风的崇尚与风靡;另一方面是对苏黄诗风、尤其是江西诗派的反思与诘难。批评宋诗言辞最为激烈的是南北宋之际的张戒,其《岁寒堂诗话》卷上有云:
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4]
张戒完全抹煞苏黄对宋诗的贡献,持论自有偏颇之嫌。然张氏之责,开启了中国诗史上的唐宋之争。南宋后期的严羽秉承张戒之说,论诗“以盛唐为法”,其《沧浪诗话》针砭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5]并说诗至苏黄,“唐人之风变矣”。后来的“分唐界宋之说,无不受沧浪之启发。”[6]
高丽诗话对宋诗却表现出极度的推崇,这种现象与高丽科举制度的推行、宋学东渐密切相关。光宗九年(958),高丽朝在后周文士双翼的建议下,设置科举,通过考诗、赋、颂和时务策来选拔儒生,儒士由此前专习经文,转而专尚词章与文艺。于是以经学为核心的儒学,逐渐被以词章文艺为核心的儒学所代替。文士们也因为轻明经习制述(文艺),而把精力集中于研习苏轼等人的书籍上,从而形成了“高丽文士,专尚东坡”的文化现象,以至“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上)此时诗坛虽有唐诗的影响,蔚然成风者却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宋诗。韩国诗话的开创者李仁老为诗即学苏黄,崔滋《补闲集》卷中载云:“李学士眉叟曰:‘吾杜门读黄、苏两集,然后语遒然韵锵然,得作诗三昧。’”对于宋徽宗禁毁苏黄文集的行径,学士权适有诗赠宋朝使者曰:“苏子文章海外闻,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为灰烬,落落雄名安可焚。”(李仁老《破闲集》卷下)这些议论,在中国诗坛力诋苏黄、批评宋诗的背景下,有砥柱中流,扬清抑浊的意义。
“宋诗自得论”萌生于“专尚东坡”的文化氛围,是高丽士人的自然认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韩国诗论家在评论本土诗歌时,往往以唐宋诗作为衡量的标尺。如李仁老《破闲集》卷上自称其有诗云:“红叶题诗出凤城,泪痕和墨尚分明。御沟流水浑无赖,漏泄宫娥一片情”,“座客皆聚首而观之,以谓唐宋时人笔。”卷中又称无名氏之“秋阳融暖若春阳,竹叶巴蕉映粉墙。莫向此君夸叶大,此君应笑近经霜”诗,“语法与唐宋人无异”。“以谓唐宋时人笔”与“语法与唐宋人无异”,可见唐宋诗在李氏心目中没有优劣之分。不过,这时期论诗的主要倾向是推崇宋诗。“宋诗自得论”从内容来看,则包蕴着对宋诗新意、用事与风貌等方面的肯定。
“新意”是韩国文士学习宋诗过程中,针对本土诗歌创作中剽窃现象提出的要求,它基于诗歌以意为主的认识,即《补闲集》卷中所说的“诗文以气为主,气发于性,意凭于气,言出于情,情即意也。”诗人各有性情,诗则各具精神,从而自得新意也。李仁老称为诗当“出新意于古人所不到者。”(《破闲集》卷下)李奎报则称:“吾不袭古人语,创出新意。”(《补闲集》卷中)在他们看来,宋诗就是具有“新意”的。李奎报《白云小说》称:
余昔读梅圣俞诗,私心窃薄之,未识古人所以号诗翁者。及今阅之,外若苶弱,中含骨鲠,真诗中之精隽也。知梅诗然后可谓知诗者也。
李奎报赞赏梅尧臣的诗“外若苶弱,中含骨鲠”。而梅尧臣自道作诗甘苦时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7];欧阳修《六一诗话》则称:“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8]从“造平淡难”可知,梅诗所追求的“平淡”,貌似率意为之,然“覃思精微”,极尽琢刻之工。可见“平淡”的诗歌既是“意新语工”[9]的,又是“深远闲淡”的,而且“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10]。李奎报的“苶弱”是对梅诗“平淡”特征精辟而形象的阐释;“骨鲠”则是对梅诗“深远闲淡”的气质与构意设文上“意新语工”的推崇;“精隽”则是对梅诗总体风貌的评价。崔滋也推崇新意,《补闲集》卷中云:
予尝谒文安公,有一僧持东坡集质疑于公。读至“碧潭如见试,白塔若相招”一联,公吟味再三曰:‘古今诗集中,罕见有如此新意。’”
近世尚东坡盖爱其气韵豪迈,意深言富,用事恢博,庶几效得其体也。今之后进读东坡集,非欲仿效以得其风骨,但欲证据以为用事之具,剽窃不足道也。
崔滋推崇苏诗的新意,并以“风骨”称之。他所说的风骨,即“气韵豪迈,意深言富,用事恢博。”“气韵豪迈”显然是指诗歌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意深言富,用事恢博”则是构意设文的要求了。李齐贤在《栎翁稗说》后编中则说:
古人多有咏史之作,若易晓而易厌,则直述其事,而无新意者也……刘贡父《塞上》云:“自古边功缘底事……”王介甫《张良》诗云:“汉业存亡俯仰中……”禅家所谓活弄语也。
李氏以“新意”为标准论咏史诗,主要强调咏史诗应有独特的历史见解。
对宋诗体貌的认同也是这时期宋诗自得论的内容,议论得最多的是苏轼与黄庭坚的诗歌。北宋元祐后期就有“苏黄”并称,高丽诗人亦多言“苏黄”,这种称谓是对苏黄诗歌体貌与诗史地位的肯定。如李仁老就说自苏黄崛起于诗坛,“则使事益精,逸气横出”(《破闲集》卷上)。苏诗更是“气韵豪迈”(《补闲集》卷中)、“豪宕可人”(《栎翁稗说》)。李齐贤又注意到宋诗“典丽”的风格,如《栎翁稗说》称王珪《上元应制》诗“‘双凤云间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最为典丽。”所谓“典丽”即如《王直方诗话》所称之“至宝丹”,王珪为诗虽用金玉锦绣字,但掞藻敷华,细润熨贴,精思鍜炼,故多炉锤名贵之篇。[11]以上评说,显露了宋诗风格论的端倪,个中隐含着对宋诗体貌多样化的赞赏,可见韩人对宋诗的特色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综观以上论述,可知高丽中后期的宋诗自得论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没有分唐界宋的意识。二是往往就宋诗而论宋诗,这与中国诗学家评价宋诗多以唐诗为参照迥然不同,宋诗在韩国诗学家这里,显然已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三是对宋诗的评论没有系统的理论表述,而是涵蕴于只言片语的议论之中。
(二)朝鲜初期(15-16世纪),约当明朝初中期。明代中期的文坛,复古之风日炽。前后七子力倡“诗必盛唐”之说,造成了有明一代唐诗流行,从俗而变的盛况。但朝鲜初期的诗坛,仍承袭高丽传统,以宋诗为尚,诗人多出入苏黄。“本朝诗学,以苏黄为主。”(许筠《鹤山樵谈》)、“我东诗人多尚苏黄。”(李晬光《芝峰类说》卷九)诗话也仍然以崇宋为中心。与此同时,诗坛亦开始濡染晚唐习气,以至格卑气弱,俯咏低吟。因此,朝鲜初期的宋诗自得论不同于高丽朝的以宋论宋,而是通过批评晚唐诗的“格卑气弱”,表现出对宋诗的推崇。如郑湖阴(士龙)与李退溪(滉)皆有斥责晚唐诗的议论,据权应仁(生卒年不详)《松溪漫录》所载:
今世诗学专尚晚唐,阁束苏诗,湖阴闻之笑曰:“非卑之也,不能也。”退溪亦曰:“苏诗果不逮晚唐邪,愚亦以为坡诗所谓‘岂意青州六从事……’不知晚唐诗中有敌此奇绝者乎。”……丽代文章优于我朝,而举世词宗则坡诗,不可谓之卑也。
“非卑之也,不能也”,是才情不逮也。退溪激赏坡诗的“奇绝”,以为与晚唐诗相比,自有霄壤之别。综观这个时期的宋诗自得论,主要附丽于宋诗用事的叙说之中,并无新的发明。
(三)朝鲜中后期(17-19世纪),时当明末暨有清一代。朝鲜中后期诗话繁盛,宋诗自得论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明末与有清一代诗坛,唐宋之争方兴未艾,公安三袁针对前后七子尊唐黜宋的弊端,推崇苏轼,在中国诗坛开启了宗宋的风气。朝鲜诗坛自初期以来,一味效法宋诗,以至堕入剽窃的泥潭。针对这种现象,有识之士力倡盛唐,以救步趋宋诗之弊。
此时期的宋诗自得论在尊唐黜宋的背景中展开,许筠(1569-1618)是导夫先路者,他将朝鲜诗坛之弊归咎于苏黄,《鹤山樵谈》曰:“本朝人文则三苏,诗学黄陈,故卑野无取。”因此,许筠论诗以盛唐为圭臬,在《鹤山樵谈》中,诸如“似盛唐人作”“有盛唐风格”“可肩盛唐”之语,不胜枚举。他甚至说“诗至于宋,可谓亡矣”[12]思革剽窃之习,发矫枉过正之语,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全面否定宋诗,则又堕入偏执一途。至于任璟(生卒年不详)《玄湖琐谈》批评宋诗滞于理,如“委巷腐儒擎跪曲拳”,亦是以偏概全之论。李睟光(1563-1628)的《芝峰类说》论宋诗虽多肯綮之言,却批评宋诗专尚用事,意兴甚少,这当是对本土诗人学宋诗之弊的感慨之言。
在尊唐黜宋论泛滥之际,亦有持宋诗自得论者。申钦(1566-1628)《晴窗软谈》论中国历代诗歌云:
风者,词而理者也;雅颂者,理而词者也;六朝以后,词而词者也;赵宋以降,理而理者也。世之言唐者斥宋,治宋者亦不必尊唐,兹皆偏已。唐之衰也,岂无俚谱;宋之盛也,岂无雅音?此正钩金舆薪之类也。
“理”当是指作品内容,“词”则指艺术表现技巧,词理之辨,实乃文质之争。申钦认为,唐宋诗各有特色,唐诗是词而词者,宋诗是理而理者。《晴窗软谈》又以禅喻诗,谓“唐诗如南宗一顿,即本来面目。宋诗如北宗,由渐而进,尚持声闻辟支尔。”“南顿北渐”是南北禅宗悟道的两种不同途径,顿者,是自然本色;渐者,是刻苦锻炼,二者并无高下之分。针对尊唐黜宋论,申钦力挺苏轼,《晴窗软谈》云:
东坡诗文,俱神境也,世之学唐者常訾之。若简摘其艳丽,略为数卷书行于世,何渠不若唐家时世妆耶?只以家数甚大,掏井之见,有望洋之叹尔。
分析细致严密,品评严正,持论可谓公允。
南龙翼(1628-1692)的《壶谷诗评》论宋诗则云:
宋承衰季之余,杨大年首唱西昆体,其诗萎弱,虽无可观,尔时犹有山林之秀,馆阁之英。山林则魏仲先野,林和靖逋、潘逍遥阆,而石曼卿最胜。馆阁则宋景文祁、陈文惠尧佐、欧阳文忠修,而王歧公庭珪为优。至王半山安石、梅都官圣俞、苏东坡轼出,而诗道颇大。及至黄庭坚、陈师道诗格一变。南渡以后靡然从之,号称学杜而反不及于楚相之优孟,譬如草木芳华尽谢,叶成阴而子满枝,所见索然矣。王弇州曰:“宋无诗”,此言诚过矣。若比于唐,则有同璧珷。学者当取其义,而勿学调格可也。
南氏在此描述了北宋诗的嬗变轨迹,所谓“诗道颇大”,是说宋诗至王、梅、苏,形成了自是宋诗的风貌。至黄陈“诗格一变”,自然是指江西诗派。“号称学杜反不及于楚相之优孟”一语,显然是对南宋人师法江西的批评。并明确指出“宋无诗”的说法,是言过其实之论,在他看来,“半山之‘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东坡之‘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都官之‘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看花无丑枝’、山谷之‘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后山之‘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放翁之‘雨声已断时闻滴,云气将归别起峰’之句,可谓清新警拔,居然自是宋诗。”持论平和,颇有见地。
金昌协(1561-1708)的宋诗自得论以性情为标尺。他认为宋诗是有弊病的,如“黄之横拗生硬,陈之瘦劲严苦,既乖温厚之旨,又乏逸宕之致”“欧公太流畅,荆公太精切,又有议论故实之累耳。”(《农岩杂识》)但他并没有因此否定宋诗,《农岩杂识》谈到明人攻击宋诗时说:
宋人之诗,以故实议论为主,此诗家大病也,明人攻之是矣。然其自为也,未必胜之,而或反不及焉,何也?宋人虽主故实议论,然其问学之所蓄积,志意之所蕴结,感激触发,喷薄输写,不为格调所拘,不为途辙所窘,故其气象豪荡淋漓,时有近于天机之发,而读之犹可见其性情之真也。明人太拘绳墨,动涉模拟,效颦学步,无复天真,此其所以反出宋人下也欤!
在他看来,宋人以故实议论为主,自是诗家大病,然宋诗的性情之真,明人则不可企及。如此议论,堪称振聋发聩之言。李宜显论诗亦主性情,其《陶谷杂著》曰:“宋人虽自出机轴,亦各不失其性情,犹有真意之洋溢者。”[13]以性情论宋诗,揭示了诗歌的本质特征。朝鲜正祖李算则以宋诗是“以其自得者出之”的论断,为历代宋诗自得论作了一个圆满的总结。
朝鲜中后期的宋诗自得论具有以下特色:一是在尊唐黜宋的背景中发展深化,呈现出尊唐崇宋纠结互动的态势;二是对宋诗的论说往往运用比较的方法,以唐诗为参照,而不再是独立的存在;三是超越了高丽、朝鲜初期对个别作家作品评论的局囿,在对宋诗的整体评价中来凸显宋诗自得论;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有思辨的色彩和充实的内容。
“宋诗自得论”贯穿于韩国历代诗话,韩国诗学家们的期望是:在推崇宋诗、在唐宋之争中建立起“非唐非宋,而自成一家”(洪万宗《小华诗评》)的汉诗诗风。
二、宋诗用事论
用事论也是韩国诗话宋诗论的重要内容。在韩国诗话评论宋诗的文字中,常常可见“用事”“使事”“引事”“故实”等词语。需要说明的是,提倡用事的诗学家主要是“宋诗自得论”者,因此,用事论又是宋诗自得论不可或缺的部分。鉴于韩人对宋诗的用事形成了系统的认识,故置专节讨论之。
所谓用事,是指诗歌创作中引用典故与化用典籍中成语的一种艺术方法。中国诗歌的用事滥觞于汉代末年的文人五言诗,较早注意用事的诗论家是提倡“自然英旨”的钟嵘,其《诗品》说诗“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14]。由是“用事”成为诗歌批评的一个议题。
然而,任何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法度,用事作为诗法之一,肇始之后,群起效之。经历代诗人的探索,它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艺术方法。迨至宋朝,用事之风日盛,从而引起了诗学家的特别关注。首先肯定用事的当是欧阳修,他曾说西昆诗人刘筠、杨亿之作,“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15]批评用事的则以严羽影响最著,《沧浪诗话》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16]因此,为诗“不必太著题,不必多使事。”[17]宋诗的用事一直是诗学界关注的话题,并影响着历代诗人的创作。
高丽、朝鲜两朝,崇宋的韩国诗人以宋人为师、以苏黄为尚,他们深知学诗要合乎法度,用事则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与方法。通过研阅宋诗、创作汉诗,韩国诗学家一方面注意到用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用事不当而导致的流弊。他们从揭示用事之弊切入,对用事论形成了系统的认识,即用事的理想、用事的方法和用事对创作主体的要求。
(一)用事的理想
韩人用事的理想是针对本土诗歌存在的剽窃现象提出来的。如林椿自谓句法往往与东坡相似,但崔滋《补闲集》卷中却批评说:“观其文,皆攘取古人语,或至连数十字缀之,以为己辞。此非得其体,夺其语。”以诗闻名于高丽的林椿尚且如此,他人则可想而知。李仁老对用事已有辩证的认识,即作为创作方法的“用事”,不能以优劣论之;然多用事、不辨用事就成文章一病了。其《破闲集》卷下论用事之病云:
诗家作诗多使事,谓之点鬼簿;李商隐用事险僻,号西昆体,此皆文章一病。
这段话指出用事之病有二:一是多使事而成“点鬼簿”。此语出自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卷六:杨炯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时人因号为“点鬼簿”。[18]李仁老以“诗家作诗多使事”与“李商隐用事险僻”相对,显见李仁老的“点鬼簿”之说,是指以唐人杨炯为代表的好用古人姓名者。用古人姓名作诗,向来被视为下乘小道,仅作应酬的救急之法而已。虽然杜甫也有类似的作品,仍不能以此为法。二是用事险僻,号“西昆体”。宋人对此多有议论,刘攽《中山诗话》即称:“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尚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多窃义山语句。”[19]李仁老本宋人之说,认为李商隐与西昆体诗人有多用故事,语僻难晓之弊。李奎报不太赞成用事,他在《白云小说》中提出诗有九不宜体:“一篇内多用古人之名,是载鬼盈车体”,即李仁老所说的“点鬼簿”;“好犯丘轲,是凌犯尊贵体。”“丘轲”在这里是经史的代名词,“好犯丘轲”,指以经史之语入诗,所谓以文为诗也。韩人对于用事之病的认识在二李这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李仁老等通过对诗歌的具体分析总结出宋诗用事的理想:“用事精切”。“用事精切”以及“使事益精”“用事奇特”“引事奇妙”“用事亲切”等语,皆指用事的精当妥贴,即所用典故、成句与诗歌表达的情志事理要作到契合无垠。韩人也注意到用事是语言艺术的问题,他们认为宋诗“用事精切”主要表现在琢句之妙,造化生成。用事而“莫知用何事”(《破闲集》卷下)、“不觉用前人语”(《鹤山樵谈》),这方是用事精切的审美旨归。
韩人对宋诗用事精切的考察,主要着眼于琢句之妙。从句切入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句是诗章最重要的部分,字在句中,而章以句成。中韩诗人皆重句法,如宋人范温《潜溪诗眼》即说:“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20]惠洪《冷斋夜话》卷四指出:“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21]“言其用,不言其名”包含着实现琢句之妙的两种方法:一是比物以意而不言其物;二是用事而不言其名。李仁老承惠洪之言,盛赞苏黄用事的琢句之妙,《破闲集》卷下云:
诗家作诗多使事……近者苏、黄崛起,虽追尚其法,而造语益工,了无斧凿之痕,可谓青于蓝矣。如东坡“见说骑鲸游汗漫,忆曾扪虱话悲辛”“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尔远来情”,句法如造化生成,读之者莫知用何事。山谷云:“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只此君”“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类多如此。
从李仁老所举诗句来看,东坡是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则是比物以意而不言其物。基于对具体诗句的分析,李仁老指出苏黄追尚唐代使事的艺术方法,但“造语益工”,此即琢句之妙的意思。其句法“了无斧凿之痕”“如造化生成”,具有融化无迹的自然之美。所以李仁老认为唐人唯杜甫“独尽其妙”,宋代则以苏黄为佳。苏黄诗歌的“使事益精,逸气横出,琢句之妙,可以与少陵并驾。”这在诗论史上应是最高的褒奖了。徐居正则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用事作为评论东国诗歌的标尺,《东人诗话》卷下云:
古之诗人托物取况语多精切,如东坡咏海棠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以妇人譬花也。山谷咏荼蘼云:“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以丈夫譬花也。崔文靖恒咏黑豆云:“白眼似嫌憎客意,添身还有报仇心”,以文人烈士譬黑豆,用事奇特,殆不让二老。
徐居正将韩人崔文靖的诗句与东坡、山谷相比较,指出以文人烈士譬黑豆,用事奇特精当,不输苏黄。对用事精当的推崇在韩国汉诗的创作中常常体现为化用唐宋诗句入诗,如梁庆遇(1568-?)《霁湖诗话》论郑士龙诗:
“山木俱鸣风乍起,江声忽厉月孤悬。”举世称之。盖“木叶俱鸣夜雨来”,简斋之诗也;“滩声忽高何处雨”者,吴融之句也。湖阴上下句取此两诗之语,陶铸之圆转无欠。
李氏指出湖阴诗化用陈与义及吴融的诗句,如造化生成,达到了“陶铸之圆转无欠”的境界。《晴窗软谈》称韩国金质冲的“三年药里人犹病,一夜雨声花尽开”,与陈与义“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诗语相似”。又《补闲集》卷中论高丽诗人俞升旦“语劲意淳,用事精简”、李仁老“言皆格胜,使事如神,虽有蹑古人畦畛处,琢炼之巧,青于蓝也。” 类似的评说在诗话中随处可见,可以说是对用事理想的诠释。
(二)用事的方法
用事是语言艺术的问题,在创作实践中,“用事精切”自然需要与之相应的方法。韩国诗学家选择了黄庭坚的用事理论来指导诗歌创作,因此,我们有必要陈述黄氏的用事之说,其《答洪驹父书》云: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22]
又惠洪《冷斋夜话》称山谷有脱胎换骨之说:
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23]
韩国诗学家从《答洪驹父书》和《冷斋夜话》中抽绎出两种用事方法:
一是“无一句无来处”。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上将黄氏的“无一字无来处”演绎为:“古人作诗,无一句无来处”,并进而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凡诗用事,当有来处,苟出己意,语虽工,未免贬者之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之说的偏颇。徐居正指出用事要有来历,有根据,个中包含着向古人学习,多读书的要求。他也注意到一味强调“无一字无来处”,便会导致蹈袭,如《东人诗话》卷上云:
诗忌蹈袭,古人曰:“文章当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生活耶?”唐宋人多有此病。
“用事”不是蹈袭前人诗句,而应自出机杼,点化前人诗句,从而实现“意新而语奇”(《东人诗话》卷上)的理想。朝鲜后期的洪万宗(1643-1725),在《小华诗评》卷之下指出:“诗家最忌剽窃,而古人亦多犯之……夫自出机杼,务去陈言,不果戛戛其难哉?”因此,为诗“无一句无来处”应与夺胎换骨互为补充。
二是“夺胎换骨”。韩国诗学家注意到的是黄庭坚的夺胎换骨说,而不是点铁成金说。最先首肯夺胎换骨说的是李仁老,《破闲集》卷下云:
昔山谷论诗,以谓不易古人之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规模古人之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
这段话本于惠洪的《冷斋夜话》。“不易其意而造其语”的换骨法,指化用前人诗句,在立意上借鉴前人,但在语言上要另有创造;“规模古人之意而形容之”的夺胎法,是就前人诗意而加倍形容,从而翻出新意。李仁老已认识到,用事不是“活剥生吞”“剽掠潜窃”,而是要借前人的诗语与境界点化出新,即“出新意于古人所不到者”(《破闲集》卷下)。《东人诗话》卷上则指出,化用前人诗句,要“妆点自妙,格律自然森严”,在强调立意与造语外,又提出格律的要求。格律自然是中国格律诗的重要因素,徐居正注意到格律的重要性,应该说是颇有创见的论说。
(三)用事对创作主体的要求
从理论上看实现用事精切应把握句句有来处与夺胎换骨的方法,然而对于方法的把握,决定于创作主体的才情。《晴窗软谈》论东坡云:“病东坡者,以其用古事太多,比之饤饾,此论亦宜矣?东坡之用古事,只患才之太多,出语天成而不自觉尔,奚可以此而尤之耶!”申钦充分肯定苏轼的才情,指出苏轼用事达“出语天成而不自觉”的境界,乃因其多才也。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才情是有限的,李仁老在论“琢句之法”时就提出:“人之才如器皿,方圆不可以该备,而天下奇观异赏可以悦心目者甚夥。”(《破闲集》卷上)此即惠洪所引山谷语:“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用事既是引用典故与化用典籍中的成语,那么,才情是可以通过读书来培养的,黄庭坚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24]。类似的论说在韩人诗话中也有不少,如《东人诗话》卷上论康日用诗云:
高丽睿王朝,御楼前木芍药盛开,命禁署诸儒赋诗,康先生日用只得“头白老翁看殿后,眼明儒老倚栏边”一句,先辈以谓用事精切。予初咀嚼,不识其味,后阅昌黎咏木芍药,有“今日栏边觉眼明”,欧阳公咏牡丹有‘自笑今为白发翁’之句,然后始知出处。用事精切,但恨词语深僻,韵高才短。如先生者岂非古人所谓有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者乎。
徐居正认为用事精切,要有材料,否则就像康先生一样,韵高才短,以至词语深僻。可见徐氏强调用事精切与诗人读书学问的根底密切相关。又如李植(1584-1647)《学诗准的》告诫诗人:“宋诗虽多大家,非学富不易学,非诗正宗不必学。”“学富”自然是提倡饱读诗书,讲究学问了。从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论用事,细致周密,已具有些微的理性色彩了。
韩国诗学家论宋诗,注意到用事的意义,也总结出学习和运用的方法,从而使学习古诗、创作汉诗具有了可操作性。如《鹤山樵谈》论荪谷用事时说:“东坡诗:‘惆怅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楼依旧斜阳里,不见当时垂手人。’荪谷悼亡诗亦袭坡语,诗曰:‘罗帷香尽镜生尘,门掩桃花寂寞春。依旧小楼明月在,不知谁是卷帘人。’秾丽称情,不觉用前人语。”运用用事的方法创作汉诗,这应是韩人宋诗用事论的意义。
三、宋诗批评论
韩国诗话对于诗人、诗作批评的形式,主要受欧阳修《六一诗话》那种随笔式评点的影响。宋诗作者有九千余人,但是韩国诗话涉及的只有六十多名,对他们的评点大多随意而为。然而,将这些诗人排列起来,从宋太祖到文天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竟然是两宋三百多年诗歌的发展轨迹。从作者身份来看,有帝王,如宋太祖、宋徽宗等;有台阁大臣,如王珪、晏殊、欧阳修等;有山林隐逸,如陈抟、林逋等;有理学家,如邵雍、朱熹等;有爱国志士,如岳飞、文天祥等。从各时期的代表性诗人来看,北宋初期有王禹偁、杨亿与寇准等;中后期有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与义等;南宋有中兴诗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与尤袤等;后期有刘克庄、赵师秀等。这些诗人分属于宋代的各个诗派,如白体、西昆体、晚唐体、江西诗派、江湖诗派与永嘉四灵,体现了两宋诗歌风貌的流变。韩人议论最多的是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其次是欧阳修、梅尧臣及陈与义,他们无疑是“宋诗中可以模楷者”[25]。由此可知,韩国诗话已把握了宋诗流变的基本走向和发展逻辑。
韩人对宋诗的评说,虽然着眼于诗歌篇章、诗句与字眼,然而在零散的议论中,不乏精到之思,一得之见。关于宋诗的批评论,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知诗为尤难”“诗可以达事情通讽喻”与诗要“细味之”。
(一)“知诗为尤难”
评品诗歌是宋诗论的基础,韩人认为评诗当臻宋人《诗话总龟》《诗人玉屑》《苕溪渔隐丛话》那种“议论精严”[26]的境界,然而要想达到这种评诗之境又谈何容易。徐居正有言:“作诗非难,而知诗为尤难”(《东人诗话》卷上);洪万宗说:“诗固未易作,诗评亦未易也”(《诗评补遗》)。韩人认识到评诗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首先是说诗者的审美趣味不同。金万重(1637-1692)在《西浦漫笔》中指出,宋人对唐诗的审美兴趣就很不相同:“范希文于唐诗,喜‘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之句;欧阳永叔喜‘晓日都门道,微凉草树秋’;朱文公喜‘寒雨晴深更,流萤度高阁’。”至于本土诗人李奎报论诗亦从自己的爱好出发:“李奎报不喜梅圣俞,盖以其见深清省与己之饱满豪宕正相反;而亟称徐凝《瀑布》诗,以东坡为失评者,亦以凝诗只取新意,不拘雅俗,有相契合故也。”只从自己的爱好出发说诗,难免导致审美判断的错误。李奎报后来在《白云小说》中谈及梅尧臣的诗歌:“及今阅之,外若苶弱,中含骨鲠,真诗中之精隽也。”表现了昔非今是的变化。其次是说诗者的才识有差,则识见有异。诚如《西浦漫笔》所言:“诗人于古人之诗,所尚各不同,亦可见其才识。”以上论述说明韩人已认识到说诗者的趣味不同,才识有异,是造成诗无达诂的重要因素。
尽管说诗者的审美趣味、才识对感受作品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说诗者必须从作家作品的实际出发。因此,韩人意识到说诗虽难,但也是有规则可循的。具体说来,一是以意逆志。《东人诗话》卷上举出一些具有夸张意味的诗句说:“太白诗:‘燕山雪片大如席。’又曰‘白发三千丈’。苏子瞻诗:‘大茧如瓮盎。’是不可以辞害意,但当意会尔。”即评说作品不能拘泥于文辞的表层意义,而是要根据文辞去“意会”它的涵蕴与审美意义。二是知人论世。《东人诗话》卷下称:
文丞相天祥《重九》诗:“老来忧患易凄凉,说道悲秋更断肠。世事不堪逢九九,休言今日是重阳。”高丽毅宗朝,金尚书莘尹,重九有诗云:“辇下风尘起,杀人如乱麻。良辰不可复,白酒泛黄花。”盖庚癸之乱,无可奈何。然白酒黄花,聊复自宽,则金老忧世之情,犹或可言。丞相值宋室阳九之厄,又逢九九,世事已去,虽有白酒,又何暇自慰哉?其言休说重阳,慷慨忧愤之辞甚于金老,惜哉。
徐居正从文天祥与金莘尹的身份、各自所处的时代环境来说诗,这就是知人论世。三是论诗要出以“公”心。审美趣味与才识虽有不同,但论诗不能本于个人的好尚;文人之间虽有不相能者,但不可因人废文。韩人论诗提倡一个“公”字。如《东人诗话》卷上赞赏王安石“不废公论”:“半山与东坡不相能,然读东坡雪后叉韵诗,追次至六七篇,终曰:‘不可及。’时人服其自知甚明。”四是说诗者须是知诗者。如《芝峰类说》卷九称:“大抵诗道难以言语相喻,必自知然后可也。”又如《谿谷漫笔》所说:“文章美恶,自有定质,然其物也,精微多变,必能之而后知之,不造其境而能解其妙者,未之有也……若荆公之于东坡,年位尊卑邈然悬绝,又素不相悦也。然一见《表忠观碑》,以为可与子长上下,相如子云皆不及也,唯其知之明,故所论不期公而自公耳。”可见,他们既重视诗人的艺术修养,还强调必须伴以“公心”,不能因人废文,这是论诗能否能达到“议论精严”之境的关键。
(二)“诗可以达事情通讽喻”
韩人重视文学,认为文学是垂名后世的事业,如李仁老即说:“天下之事,不以贵贱贫富为之高下者、惟文章耳。盖文章之作,如日月之丽天也,云烟聚散于大虚也。有目者无不得睹,不可以掩蔽。”(《破闲集》卷下)在他看来,文章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不朽盛事。徐居正亦持此论,其《东人诗话》卷上说:“诗虽细事,然古人作诗必期传后。故少陵有‘老去新诗谁与传’……之句。韩子苍亦云:‘诗文当得文人印’。”徐居正在此引述杜甫、韩子苍语以说明诗歌的价值。“诗文当得文人印”则指出诗文是文人品行、学识的表征,所谓“文如其人也”。诗学家又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洪万宗《小华诗评》卷下即谓:“诗可以达事情通讽喻也。若言不关于世教,义不存于比兴,亦徒劳而已。”将诗歌功能提高到“关于世教”的高度,诗在韩人这里,俨然成为道德的事业了。因此,他们重视诗人的品性,如李睟光虽钦慕李清照“才高学博”,但又深憾其“年老失节,其才不足称也。”(《芝峰类说》卷十四)“失节”之责,毋庸置评,但论诗以道德为重的倾向是不言而喻的。徐居正谈到夏竦的《廷试》(殿上衮衣明日月)诗时说:“天下评者,讥其自负”,因告诫诗人:“诗当先气节而后文藻”(《东人诗话》卷上),亦是重德轻文之论。由此可见,韩国诗话对宋诗的评说带有社会学批评的特点,具有浓郁的功利色彩。
社会学批评首先表现为对诗针砭时弊,有裨“世教”功能的认识。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上指出诗歌当有“世教”的功能,他以古人咏明皇贵妃诗为例说:“尝爱韩子苍诗:‘尚觅君王一回顾,金鞍欲上故迟迟。’张祜诗:‘桃花院静无人见,闲把宁王玉笛吹。’”又称李文顺《开元天宝四十二韵》,“随事讽咏,抑扬顿挫,沉深痛快。”徐氏在此以韩人李文顺与宋人韩子苍、唐人张祜的诗歌相比,认为其咏明皇贵妃事“虽置之唐宋作者亦无愧焉。”李睟光则指出苏轼以诗讽咏时政,《芝峰类说》卷十二云:“东坡诗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盖言青苗之法,使民不得休息,故村童久在城中,学得官话而语音好耳。”矛头直指王安石的新法。李睟光在《芝峰类说》还多次提到“乌台诗案”,可见韩人对诗歌功能的认识已具有相当的深度。
其次,是对诗歌抒情言志功能的认识。李睟光《芝峰类说》于此论述颇多,其论邵雍诗云:“邵康节诗曰:‘平生不做皱眉事,举世应无切齿人。’又‘风花雪月千金子,水竹云山万户侯。’又‘唐虞揖逊三杯酒,汤武交争一局棋。’想其胸怀乐易跌荡,千载之下,诵其诗如见其人。”(卷十二)朱熹有诗云“葱汤麦饭两相宜,葱养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犹有未炊时。”李睟光评之曰:“余谓当食而先念未炊之人,可见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卷十二)“诵其诗如见其人”“可见仁人君子之用心”,充分肯定了诗歌抒情言志的功能。
再次,以为诗可以验人之穷达,此论则误入诗谶之歧途。金万重《西浦漫笔》论寇准诗云:“古人以诗验人之穷达,如寇莱公‘野水孤舟’之语,预占后来相业,然此亦适然。”这种说法一般称为诗谶说,即认为诗作中寓含着人事的吉凶福祸、自然的邪正灾祥。《芝峰类说》卷十云:“宋徽宗赋一联曰:‘日射晚霞金世界,月临天宇玉乾坤。’翌年金兵犯阙,乃诗谶云。”又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下载:“宋王沂公会微时,以所业执吕文穆公,有《早梅》诗:‘雪中未知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吕曰:‘此生次第安排,当作大魁登岩廊’后果然。”这种现象,徐居正认为是“读其诗,可以知其人。”(《东人诗话》卷下)不过,“读其诗,可以知其人”,是说诗是个人思想感情与人生际遇的反映,徐居正把它理解为诗谶现象则是错误的。与之相应的是,他们注意到诗歌与人生际遇的关系,诗能使人飞黄腾达,亦能使人穷困潦倒。《芝峰类说》卷十四载:“宋徽宗见陈与义所赋墨梅诗,善之,亟命召对,仍进用,高宗时参知政事。”此乃因诗而达。苏轼的乌台诗案,则是因诗而获罪。
(三)诗要“细味之”
韩人说诗主张“细味之”(《芝峰类说》卷九),此语源自唐代司空图的论诗之语,其《与李生论诗书》云:“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27]“味”指的是诗的情趣韵味,“辨于味”“当是指辨别诗中的情趣韵味,司空图认为能够辨别诗中的情趣韵味,才可以谈论诗。”[28]“细味之”与司空图的“辨于味”说遥相契合,与传统的诗主政教说大相径庭,显然是对诗歌的审美把握。
韩人在细味宋诗的审美活动中,感受到的是宋诗“奇趣”与“有意味”的美。韩人对宋诗的评点,各家的重点虽有所不同,但“奇趣”与“有意味”却是他们对宋诗美的共同体验。苏轼为诗崇尚奇趣,《芝峰类说》卷十一引《冷斋夜话》语云:苏轼评柳宗元《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说:“此诗有奇趣,然尾两句不为亦可”;李睟光称“此言是”。苏轼欣赏此诗有“奇趣”,认为若将末二句“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删去,即以“欸乃一声山水绿”作结,不仅余情不尽,余味无穷,而且“奇趣”倍增。苏轼的评论之所以引起李睟光的共鸣,就在于此诗有“奇趣”;“尾两句不为亦可。”宋诗的“奇趣”,或指奇绝的想象,如李退溪称苏轼诗:“‘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风花误入长春院,云气长临不夜城。’不知晚唐诗中,有敌此奇绝者乎。”(《松溪漫录》)“冻合”二句,出自苏轼的《雪后书北壁堂二首》。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目为“银海”。苏轼化用道家语,极言雪后之寒冷,可谓是想象奇绝,超然物外之思。奇趣又指蕴含于诗歌中独特的情趣与气质,如徐居正论帝王诗云:“宋太祖微时,醉卧田间,觉日出有句云:‘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我太祖潜邸诗:‘引手攀萝上碧峰,一庵高卧白云中……’其弘量大度,不可以言语形容。”(《东人诗话》卷上)徐氏指出这两位帝王的诗具有独特的情趣气质,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
宋诗的“有意味”应该是对唐诗美学特质的继承。尊唐的李睟光论诗推崇王安石,《芝峰类说》卷九有云:
前辈评王荆公诗曰:“祖渊明而宗灵运,体子美而用太白。其曰:‘樵松煮涧水,既食取琴弹。’清淡也;‘月映林塘淡,风涵笑语凉。’华妙也;‘地留孤屿小,天入五湖深。’高雅也;‘势合便疑包地尽,功成终欲放春回。’豪逸而从容也。法度森严,无一点可校”云。余谓王诗在宋最精巧,有意味。
对于前辈“清淡”等评语,李睟光一言蔽之曰“最精巧,有意味”。李氏所说的精巧是指法度森严,有意味则指情趣韵味了。韩人注意辨别诗歌的情趣韵味,如金昌协《农岩杂识》将苏轼的诗句:“山人若问今何似,犹向灯前作细字”,与陆游的“自知赋得穷儒分,五十灯前见细书”进行比较,以为“放翁诗犹觉有味”,因为他写出了五十衰翁的真实感受,读之令人回味。苏轼平生谪宦,多坐其诗语,文与可及苏辙因有诗戒之。文诗云:“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子由则云:“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申靖夏(1680-1715)《恕庵诗评》以为“两诗皆为坡药石,而子由为尤有味。”[29]韩人还十分注意辨别诗中蕴含的无穷之味。如《栎翁稗说》称陈与义的“开门知有雨,老树半身湿”,是“目前写景,意在言外,言可尽而味不尽”,也就是有味外之味;有味外之味的诗,才是诗的极致。又李奎景(1788-?)论范成大《东宫寿诗》说:“范石湖,宋诗中可以模楷者。王考尝教人曰:‘文则学魏叔子,诗当效范石湖。其诗与文,不入刻琢,淳淡中有至味故也。’”[30]“淳淡中有至味”,这意味着韩人已注意到审美情趣的多层次性。
在韩人看来,“奇趣”美虽然不同于“有意味”的美,但是具有共同的美学理想,那就是金得臣(1604-1684)《终南丛志》所说的“得于天机,自运造化之功。”这也是历代诗人所追求的美学理想。
检阅千余年的韩国古代诗话,我们发现其宋诗论虽本于中国的诗论,但常常有与中国诗论家迥然不同的见解,表现出较强的独立精神,个中也包含着一些有意义的命题。立足于宏观的角度而观之,韩国诗话注意到了宋诗的某些特色,利弊之所在,同时也展现了韩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文脉由来泯国界,拓展宋诗的研究领域,促进中韩文化的交流,这应是我们今天研究韩国古代诗话宋诗论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
[1] 李 算:《日得录》,赵锺业:《韩国诗话丛编》第十二卷,东西文化院,1989年,第578页。本文所引韩国诗话凡出自十二卷本《韩国诗话丛编》者,不再另行出注。
[2] 关于韩国诗话的发展轨迹,本文参考了赵锺业《韩国诗话研究·农岩诗论研究》一文的意见:韩国诗论有三期,“高丽时代(13-14世纪)为第一期,是为古代也。近世朝鲜初期,即自国初至宣祖(15-16世纪)为一期,是韩国诗论史的中世也。自光海至高宗朝(17-19世纪)又为一期,是为近世也。且中世与近世又各有前后期。”见《韩国诗话研究》,太学社,1991年,第392页。韩国历代诗话主要见于赵锺业编辑的《韩国诗话丛编》,有东西文化院1989年版,十二卷本;太学社1996年版,十七卷本。本文依据的是十二卷本。
[3] 韩国诗话起源于高丽中叶,高丽流传至今的诗话仅有四种,即李仁老(1152-1220)的《破闲集》、李奎报(1168-1241)的《白云小说》、崔滋(1188-1260)的《补闲集》、李齐贤(1287-1367)的《栎翁稗说》。
[4]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55页。
[5][16][17]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6,26,114页。
[6] 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27页。
[7]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45页。
[8][9][10][15] 《六一诗话》,郑 文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0,9,9,13页。
[11] 《四库全书总目·华阳集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14页。
[12] 许 筠:《宋五家诗钞序》,《惺叟覆瓿稿》卷四,《韩国文集丛刊》第74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81年,第175页。
[13] 李宜显:《陶谷集》卷二十七,《韩国文集丛刊》第18册,民族文化推进会,1981年,第429页。
[14] 陈延杰:《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4页。
[18] 《朝野佥载》,赵守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1页。
[19] 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7页。
[20] 胡 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81页。
[21][23] 《冷斋夜话》,《笔记小说大观》第八册,第43,38页。
[22] 《山谷集》卷十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 胡 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20页。
[25] 李奎景:《诗家点灯》,韩国学文献研究所:《韩国汉诗选集》,亚细亚文化社,1981年,第623页。
[26] 姜希孟:《东人诗话序》,《韩国诗话丛编》第一卷,东西文化院,1989年,第157页。
[27] 《司空表圣文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73页。
[29] 《恕庵诗评》,赵锺业:《韩国诗话丛编》第五卷,太学社,1996年,第705页。
[30] 李奎景:《诗家点灯》,韩国学文献研究所:《韩国汉诗选集》,亚细亚文化社,1981年,第6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