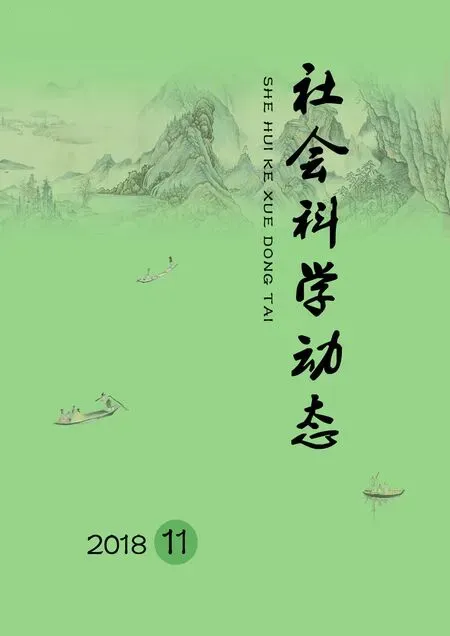传记考论与诗学研究的双重建构
2018-03-31姬志海
姬志海
一、京派文学家传记热的凸显及写作概貌
何谓 “传记”?关于此一概念的阐述首次出现在 《四库全书总目》中,其 “史部”有 “传记类”案云: “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①与先秦两汉时期的 “文学”概念相类似 (其时的“文学”在内涵上基本上相当于 “文化”之范畴),“传记”一词在更大程度上被国人认为是隶属于历史学的一种表述方式。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 “首先将传记脱离于史纳入文学的范畴、最早提出 ‘传记文学’名称的应是胡适……此后,传记文学一词被广泛应用,成为当代最具权威的传记术语。”②
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古典传记文学的写作在中国一直有着优秀的传统。先秦 《战国策》中有关苏秦、张仪和冯谖等的若干篇章即可以视其为最早范本,而两汉的 《史记》 《汉书》中的 “列传”系列更是树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古典文学传记写作之高标,这以后汉魏别传、唐宋墓志铭及宋以后的年谱均可以看作是贯穿于不同时代的、若隐若现的 “传记文学”写作的红线。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传记文学产生于近代的 “五四”,随着思想启蒙运动和人的解放,经过多位学人的共同努力,传统的传记文学一改以往传记写作谀墓、颂扬之弊病,迅速完成了向现代传记的转变,摆脱了历史附庸地位,在20世纪初至1949年间取得不菲实绩,出现了一批以梁启超、胡适、郁达夫、茅盾、朱东润等为代表的传记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卓有成就的理论大家。
在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广泛存在的各种制约,关乎传记类文学作品的写作微乎其微,彼时只有像鲁迅那样的极少数人才配享有传主的资格。新时期以来,此一格局被渐次打破,各类传记作品大量涌现,进而形成了一个井喷的势头。这其中,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传记的主体地位逐渐凸显出来。
80年代以后,京派文学开始名声鹊起,受到名家追捧。与此相呼应,80年代末,在30年代曾被左翼批判继而在1949年以后又长期被冷落、被压制一些京派作家也接踵进入了传记作家的视野。1988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发行的凌宇著述的《沈从文传》一书可以视为京派文人传记创作的先声。这以后,这种以 “京派”作家为传主的传记文学经历了一个集束式、规模化的创作高涨期,除了若干影响颇大的单部著述外,更有关乎京派文学家评传的丛书系列陆续问世:1990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钱理群的 《周作人传》;199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郭济访的《梦的真实与美——废名》;1993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姜建的 《大地足印——朱自清传记》;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吴立昌的 《沈从文传》和雷启立的 《周作人传》;1997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陆建华的 《汪曾祺传》;1998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坚、陈抗的 《周作人传》 《朱自清传》 《沈从文传》;1999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傅光明的 《人生采访者·萧乾》;2005年2月杭州出版社出版了箫悄的《古槐树下的学者——俞平伯传》,同年5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由金介甫著、符家钦译的 《沈从文传》;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湜华的《红学才子俞平伯》;200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清平的 《林徽因传》;2008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孝全的 《朱自清传》;201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钱理群的 《周作人正传》和凌宇的 《沈从文正传》,同年,吉林大学以系列形式出版了 “京派文人系列丛书”;201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欣编著的 《师陀论》;2012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朱映晓的 《凌叔华传》;201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吴立昌的 《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截至2018年5月,关于京派文学家的传记几乎覆盖了目前学界认定的所有京派文人,个别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朱自清等更是被多次立传述评。足见新世纪前后这一阶段关于京派文学家传记著述的分量之重和繁荣局面。
关于京派作家的传记写作,经过了2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应该说其形式已日益多样,其水平亦不断提高,然大凡在涉及到传主深层次的思想和学术成果的堂奥时,大部分传记作者往往因无力对之进行深刻剀切的理论阐述而选择避重就轻,乃至知难而退。 “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两句郑板桥的诗,是鲁迅先生借以讲给日本学者增田涉的 (当时后者正拟写作鲁迅先生的传记),这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鲁迅先生对传记作者的严格要求,即 “希望听到 ‘入木三分’的深刻批评,反对 ‘搔痒不着’的浮浅赞谀。”③无独有偶,作为现代传记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复旦大学的朱东润先生亦极不赞成那种将传主的学术著述从其生平轨迹中人为割裂开来的、所谓纯粹的 “评传式、考论式”的传记写作方法,他在批评梁启超的《王荆公评传》时称: “评传是传记文学的支流,不但国内,在国外也是有的,例如 《托尔斯泰评传》 《契科夫评传》,大都就其生平及其著作综合叙述,使人一目了然……可是这本 《王荆公评传》却是大切八块,使人无法理解王安石和他在学术和政治上发展的必然联系。”④由此可见,传记文学应是对一个人的生平、事业各个方面的展示,如果传主是位文学家、文艺家等,那么传主的文学创作、学术成就也势必应成为传记文学需要着力表现的两个主要方面。
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目前付梓出版的关乎京派文学家 (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家)的传记创作,大多采用的是偏重于文学研究外部因素的知人论世法,在以俄国形式主义等为代表的新批评家看来,这种以作者的时代背景、具体环境、社会状况和作者其人的生平、为人等诸多因素作为文学研究主要对象的 (传记式)文学理论,与丹纳倚重 “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说都属于失之偏颇的 “文学外部研究”之范畴,因而他们大力提倡聚焦于文学作品文本自身的文学内部研究。当然,对文学与生活联系的观点进行绝对排斥势必导致文学研究的同样偏颇,诚如英美新批评、一度风靡全球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之所以长期被学界诟病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它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那么,能否在传记文学写作中突破固有研究范式的窠臼而努力采取一种 “兼顾内外、综合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李生滨教授等的《远去的背影——朱自清及其诗学研究》一书为学界提供了有益的尝试。该著是李生滨继《雕虫问学集》、 《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之后的第三部学术著作,既往研究中沉淀下来的关于京派文学研究的学养积累、立足于 “性情说”的独特批评视角使得他无疑成为对朱自清进行总体研究和传记写作的合适人选之一。在对既有京派作家传记诸多文本的宏观观照和博采众长的基础之上,该书在 “传” “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上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兹将该著的整体框架略作介绍,然后分别评析该书在 “传” “论”两个方面所具有的特色。
该书分为上下两编,编前各有一篇引文。上编名为 “朱自清与 ‘京派’文人”;后面依次为少年书生、扬州才俊;北大学子、五四诗人;重返江南、桃李春晖;清华学者、出入京派;西南联大、学术高峰;背影远去、文脉长存。下编名为 “朱自清与中西诗学”,后面依次为:五四新文学研究的初步实践和学术视野;中国新诗批评的理论建树:《新诗杂话》;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先声: 《中国歌谣》;中国古典诗学的正本清源: 《诗言志辨》;国学典籍的雅俗共赏: 《经典常谈》;朱自清诗学批评的现代建构。上编六章勾勒了在20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特定时代里朱自清这样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一生的经历和师承交往;下编的六章则集中对朱自清近十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和杂论文集进行批评解读,历史地考察了其诗学批评的影响和诗学研究的成果。
二、“京派”视角下朱自清传记写作的新景观
在《远去的背影——朱自清及其诗学研究》之前,大陆和台湾已出版了五部有关朱自清先生的传记,多是从时代背景、具体环境、社会状况和朱自清先生的生平、为人、诗歌、散文成就以及毛泽东在 《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钦定的民主斗士身份等着眼进行描述和评价,大都有意无意忽略了朱自清丰富的个人情感、生活,忽略了其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现场中的京派作家和京派文艺家的双重身份。从这一角度来看,李生滨先生等的这部论著没有以往朱自清传记写作中的诸多条框和先验的演绎,而是十分精确地捕捉到了朱自清作为出入京派的现代诗人、散文家、文艺理论家的精神世界的独异性和其在创作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两个领域内的独特贡献——诚如作者在上编引言中所说:“出入于 ‘京派’的诗学批评家朱自清,这样的研究视角和定位,会让我们重新认识朱自清。”
上编六章针对朱自清传记的写作中,主要体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是对朱自清生活方面内容的重点关注。既往的朱自清传记大都着眼于朱自清民主斗士和诗歌、散文作家的身份定位,而对于朱自清和京派文学的师承渊源关系注意不够,更谈不上将此作为重点进行叙述。《远去的背影——朱自清及其诗学研究》一书中,显然作者对朱自清 “京派”身份的定位极为看重,专用近一节的篇幅以爬梳朱自清在师承关系,文学、学术渊源上与京派的密不可分的事实 (该书在62—64页专设 “回望北大师友”一节。通过梳理传主与胡适、周作人、俞平伯、杨振声等人的关系,讨论了朱自清成为 “京派”文人的精神与思想渊源)。除此而外,该书还增补了大量朱自清与兄弟、朋友、夫妇、师生等交往关系的丰富资料,为我们刻画出一个完整的、历史的、具有复杂的思想发展和鲜明个性的传主形象。如在弟弟朱国华的眼中,大哥朱自清从少年时期就读书非常用功:“(他常常)登上梅花岭,坐在史公墓旁阅读书籍,不经家人催促,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忘了。”⑤而在朋友眼中他是最实在、最诚恳、最谨慎和低调的一个人。朱光潜很是敬重朱自清的学问和为人,他在《敬悼朱佩弦先生》一文中写道: “我对于佩弦先生始终当作一个良师益友信赖。这不是偶然底。在我的文艺朋友中,他是和我相知最深的一位,我的研究范围和他的也很接近,而且他是那样可信赖的朋友,请他看稿子他必仔细看,请他批评他必切切实实地批评。”挚友孙伏园在回忆 “新潮社”时期的朱自清时也说, “他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虽然那时我们都在二十左右的年龄。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在 “文学新人”冯雪峰眼中,朱自清则是一位甘做泥土、不错过任何机会推举文坛后起之秀的良师,他回忆说: “提到 ‘晨光社’,我也就想起朱自清和叶圣陶先生在1921和1922年之间正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书的事情来,因为他们——尤其是朱先生是我们从事文学习作的热烈鼓舞者,同时也是 ‘晨光社’的领导者。”应该说,在这种历史考证中,作者没有将传主肢解成残缺的碎片来研究,而是将朱自清的全部丰富性、深刻性、复杂性置于其事业、交友、日常生活、婚姻等方面来作详实考察,让朱自清的本色形象呼之欲出地活脱在我们眼前。
第二是重视从文化源流和乡俗本根上入手,对濡养朱自清精神气质的故乡文化、风俗、乡习等背景材料予以深度开掘。在第一章 “少年书生、扬州才俊”里,有两处描写非常细致:其一是第22—24页中关于朱自清故乡扬州的叙述,无疑是旨在让读者理解在历史的扬州和现实的扬州生活着的少年朱自清,他既 “感染着江南的烟雨”,也 “感染着前辈文人的个性精神和艺术情怀”,于是也就 “在最不经意的纯朴和敏感中沐浴着自然的情趣和人文的光华”;其二是第25—26页中对于朱自清少年时经常流连于梅花岭上的史公祠的表述,亦旨在说明正是这种让少年朱自清无限敬仰的史可法的忠贞精神和民族气节,哺育了他特有的气质,也让读者看到了日后在日寇入侵、民族存亡的关头朱自清毅然南下至西南联大的决心,及其在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害的危急时刻怒目金刚般指斥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莫大勇气。李生滨教授等以独特的学术眼光,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悠久厚重的扬州文化传统给予童年、少年朱自清先天优秀的文化 “基因”。
第三是注重对朱自清诗歌、散文作品内涵的分析。朱自清首先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散文和新诗作家,作家的实践以及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在于他的作品,所以对朱自清的传记写作应着重作品内涵方面的分析。该书上编三到四章对朱自清各个时期的经典诗歌和散文作品,依照时间和逻辑双重次序分别进行了切中肯綮的精辟概括。这些名篇分析有很多地方让人有醍醐灌顶的新感触:如对 《背影》的解读,作者从文本47—48页就开始埋下伏笔,在102页才重点展开,让读者在两种不同视角的对比解读中,真正深入地领悟文本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元素。其中既有传统解读 “弥散在质朴的字里行间的文字的温暖和亲情的深厚”,亦有朱自清自己身为人父之后对 “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的传统父子亲情的感悟,更有对当年父亲因纳妾事件导致家境衰落而怏怏不乐的最终冰释和宽容。再比如,对《给亡妇》的解读,也同样昭示了朱自清在纪念前妻的追思中隐含的对新婚的陈竹隐女士琢磨不透的自怨自艾。最出彩的解读,要数对 《荷塘月色》主题情感之 “别样幽深”,结合家国不幸、豺狼横行的时代背景,作者对文本中 “心里颇不宁静”的内涵作出了眼光独到的解读:苟安于乱世保持清白正直的无人理解、文坛重心南移之后的落寞、企图流连于清风明月中江南采莲意境以遗世独立而不能的种种心绪……全都化作了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的流水一般无言的月光。
第四是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作者在考察朱自清思想倾向、性格特征、家庭背景和人文环境、文学风格、学术论著等方面时,善于借助对举比较的批评方法,这种示例在全书中俯拾皆是。如在该书第30页这样写道: “朱自清在扬州八中的级任老师回忆说: ‘……他个子不高,不苟言笑,不曾缺过课,他在那时喜看说部书,便自命为文学家。毕业时校中给予品学兼优奖,其时另有一位同学表示不满,怨校方将奖给朱不及己也。这位同学各科成绩均好,惟英华外发,与朱之浑厚不同耳’”。上编六章中最重要的比较,应是作者将俞平伯、闻一多及白马湖作家群中的其他成员作为他者的存在来与朱自清进行比照 (下编中主要以胡适、周作人、王国维、郭绍虞等作为比照对象,特别是将朱自清与俞平伯、闻一多这两位挚友之间的细致比照尤为精彩)。通过比较研究,作者更加清晰地把朱自清的人生历史、心理历程、情感流变等演变发展的具体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五是图文并茂的形式。在该书编纂过程中,无疑对画传传记类型的优点进行了借鉴。画传传记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的传记体裁,它兼具画册和传记两方面特色,是以图片、照片等为主,辅以简短精炼的文字、资料,综合反映传主的生活历史、生平状况、精神面貌、主要贡献等的纸质书籍或者电子文本读物。在《远去的背影——朱自清及其诗学研究》中,作者搜集了朱自清大量珍贵的原始照片、书影、画页,在此基础上配以生动的文字说明,以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让读者感到既熟悉又亲切,给予读者以鲜活的形象感、立体感、直观感。
如上所述,在该书上编六章中,作者使用历史考证的基本方法,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研究入手考证朱自清一生近30年的文艺活动,考证其生平、师承与交往,制定创作与活动年表,在考证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其历史考辩的研究方法和批评眼光。这样做显然有两个好处:小者,从“晚清——五四”的文化演变,可以讨论朱自清诗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的历史背景及学术价值;大者,可以较好地处理 “历史”与 “人”的关系,利于从中国文化的原初形态和诗学传承来进一步梳理和辨析朱自清的全部人性内涵、情感蕴藏、精神风貌及性格特征,从而作出切中肯綮的评价。
三、“宏观诗学”意义上的朱自清学术著作透视
在下编六章中,作者带着中西诗学比较视域下的美学批判视野,对朱自清的诗学研究著述进行了文本分析。
在中国诗论中,不少学者将朱自清与朱光潜并列,誉为实力相当的 “二朱”⑥,足见作为诗学批评家身份的朱自清影响的巨大与深远。但以往的朱自清传记似乎很少从这一维度来对其诸多学术著作进行剖析。《远去的背影——朱自清及其诗学研究》的面世弥补了这一不足,令我们转遗憾为欣喜,因为从这一层面上来说,这部论著为读者描摹与勾勒了一个更加丰满完整的朱自清形象。又及,作者在此论著中使用的广义诗学概念 (即完全等同于整个文艺理论),因而其眼界更加开阔,其针对朱自清诗论批评的内涵亦更加丰富,其批评的视野不仅涵盖了朱自清有关中国白话新诗、古典诗学的学术论著,还进一步扩大到 “狭义”诗歌范畴之外的朱自清所有学术著作领域。在对朱自清不同时期所写的诗歌评论文本及其他重要的文学批评论著的阐述评析中,李生滨教授从京派文学批评的视角出发,在学界既有的批评成果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不少颇为新颖的宝贵见解。概述如下:
首先,在体例结构上,《远去的背影——朱自清及其诗学研究》不像许多对朱自清诗学研究的既有范式那样,先把朱自清所有诗学批评 (狭义的诗学批评)文本视作一个整体,然后从中逐项提炼朱自清诗学批评的特色与成就建树,而是采取了 “冰糖葫芦式”或曰 “线串珍珠法”的体例。这种结构的优点在于,它同时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时间性和逻辑性各个方面。下编细读的主要诗学文本包括《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新诗杂话》 《中国歌谣》 《诗言志辨》《经典常谈》等。虽是单篇文本分析,但在针对各个诗学概念进行分析时有效地辐射到其它相关文本,从而强化了章节之间的内在关联。例如在第九章分析 《中国歌谣》时同时分析了 《古歌谣笺释三种》 《十四家诗抄》 《宋五家诗钞》等著作,在第十一章研究 《经典常谈》之后,又解读了 《语文拾零》 《标准与尺度》 《论雅俗共赏》等文本。如此归类,除了照顾到研究对象创作时间的相近或诗学研究内容的相关,也兼顾了全书体例大体一致和叙述的便捷。
其次,该书以具体详实的调查考证和鞭辟入里的独到分析,充分肯定了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学科建设方面的巨大开拓之功。中国现代文学从1917年胡适发表 《文学改良刍议》和鲁迅创作 《狂人日记》发端,到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国文系开设 “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时,已经历了13个春秋。从最初 《新青年》编辑们的尝试倡导,到20年代伊始以来各种新文学社团的风起云涌,新文学在创作和批评方面都已经出现活跃的局面,并取得了初步的实绩,但这股充满知识增长点的、蓄势待发的学术发展性与突破力彼时尚未启动,独立地肯定五四新文学的学术主张和文学史意识尚不明确。尽管这一阶段,也有学者对中国文学的新变与发展予以关注,一些关乎此专题的论著也开始出现,如胡适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赵景深 《中国文学小史》和陈子展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但基本上都是将这段新近兴起的文学史作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史的尾声予以处理的。在当时的情境下,朱自清于1929年上半年首先在清华大学,接着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开设、讲授的 “中国新文学研究”这门课,无疑具有巨大的开创意义。李生滨等首先将朱自清的 《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成书上溯到五四时期以来,朱自清从新诗入手、对新文学的各种体裁进行的批评实践作为其《纲要》的深厚学养和学理支撑,并在与胡适、周作人、赵景深、陈子展等人著述的多方对比中,肯定其 “大大超过了以上著作而具有了开创性价值”。而后,再沿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被学界逐渐认同、接受和最终得以确立的轨迹,以穿透性的视界论证了朱自清这种 “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地研究现代文学”的示范性努力对王瑶的传承和辐射的事实,认为 “王瑶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他对新文学的研究深受了朱自清 《纲要》的影响。他沿着朱自清的方向对1917—1949年的文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新文学的学术价值在朱自清的 《纲要》中得以确立,这为后来新文学的研究发展树立了一座丰碑。”
第三,该书在评价朱自清的 (狭义)诗学评论时,注重从知史通变 (以史的观念汇通古今中西)、钩稽考辨 (现代立场的考据释义理论)、雅俗共赏(学术精神与人文情怀的融合)、披沙拣金 (古典与现代之间的诗学批评)、借鉴西方 (比较视域下的诗学阐释)等多元、综合的视野进行审慎、整体的关照,高屋建瓴地概括了朱自清诗学批评的主要特质。通过对朱自清诸多学术著作尤其是对朱自清的现代、古典诗论的解读,基本上厘清朱自清诗学批评在中国诗学现代建构历程中的独特风格和不朽价值,让读者可以真正近距离观照这位 “眼界开阔、将历史感与现实感高度统一的” “京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并在与历史现场的其他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的纵深对比中,感悟到朱自清那份不偏狭、不苛求,具有多维的视野,容得下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诗歌流派的兼容并包的气度和胸怀。
在充分肯定该书下编六章所体现的体系之严整完备、学术洞见之深刻独到等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一些不够圆满之缺憾。如对于个别目前学界尚存争议的观点和史料,该书有时存在有失谨慎地直接引用,这可能会对读者产生误导。如该书第302页的 “‘诗言志’这一诗歌理论,最早见于 《尚书·尧典》: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以及在该书306页中的 “由于五四广泛接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因而当时盛行以表达感情为主的文学观念。受此影响,中国古代的 ‘诗言志’说也被阐释为表达个人感情的诗歌理论,从而与西方文论接上了轨”这一段表述,笔者认为,这样处理均不太妥当。事实上,对于前者涉及到的 “‘诗言志’是否最早见于 《尧典》”一说, “许多学者承续顾颉刚的考证和罗根泽的论述,怀疑 《尚书·尧典》的成书年代,进而怀疑 ‘诗言志’产生于尧舜时代。”⑦而对于后者所涉及到的 “言”与 “志”二者的具体内涵和关系问题,朱光潜早在 《周论》1948年8月第二卷第7期上就曾撰写 《朱佩弦先生的 〈诗言志辨〉》一文对之进行了质疑。著名学者吴小如1984年也在 《北京大学学报》上发文与之呼应: “我的看法是:‘言志’一词的涵义,是统摄 ‘载道’和‘缘情’的。 ‘言志’所以在先秦时偏于指政教,到两汉以后乃接近于 ‘缘情’,稍后更别出 ‘明道’一名以代替 ‘言志’的说法,这同各个时代受教育者的背景环境有关。”⑧
放眼学界,具体到对 “志”自身内涵发展演变的认知,可以说直至今日学界还对此聚讼不已。“有的认为 ‘志’是包含志意、思想、怀抱,排斥个人的情感因素。闻一多、朱自清、叶朗、李泽厚等持这种观点。有的认为 ‘志’指人们的思想感情,是意和情的结合。主张这种看法的有罗根泽、郭绍虞、周振甫、王运熙、陈良运、张少康等”。⑨——这些学术争议也许作者基于论证的需要而无法作淡化处理或直接规避,但无疑可以作为页下注或者文后注加以说明,不妨罗列各种主要研究者所提出的各自观点,让读者自己做出判断,而不是不假思索地直接采用朱自清先生一家之说作为唯一的权威进行论述。作为一名后学,在坦陈以上意见时确有顾虑和僭妄之感, 因为与其大著中诸多异彩纷呈的创新之处相比,上述个别地方的偏颇只是枝节末流,实在是瑕不掩瑜。
《远去的背影——朱自清及其诗学研究》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些事物注定要终其一生地渴望和坚持,比如我一直思考的晚清五四人物、京派文人、知识分子的精神之魂,还有我极其看重的作为知识者对生命自由自在的选择,等等。那些我们像仰望星空一样仰望着的人们也终归淡出了时空的舞台,但他们留下的精神光辉将会和我所恪守的道德情感一样在我心中长明不息。”整体言之,该著展示了作者扎实的考证功底和鞭辟入里的独特见解,彰显了材料与观点并重、考证与理论结合的学术风格。作者在该书中兼顾了文学研究的内、外部两重视角,从而使得该书较之于同类的其他评传式、考论式的传记写作而言,无疑提供了更加丰富与多元的 “批评景观”。这种引 “论”入 “传”式的传记研究方法,虽然算不上有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但亦不失为一个佳惠学林的极好创意。可以预见,该书不仅对京派文学研究会有推动,而且对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和传记写作都会大有裨益。
注释:
① 转引自朱东润: 《朱东润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83页。
② 许菁频: 《百年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综述》, 《学术界》2006年第5期。
③ 张梦阳: 《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 (一)》,《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3期。
④ 朱东润: 《论传记文学》, 《复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⑤李生滨、田燕:《远去的背影——朱自清及其诗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本文后面所有该书引文均出自此著,不再标注。
⑥ 常文昌: 《朱自清的诗论》, 《浙江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⑦⑨ 周朔: 《先秦 “诗言志”观念的孕育与完型》,《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⑧ 吴小如: 《读朱自清先生 〈诗言志辨〉》,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