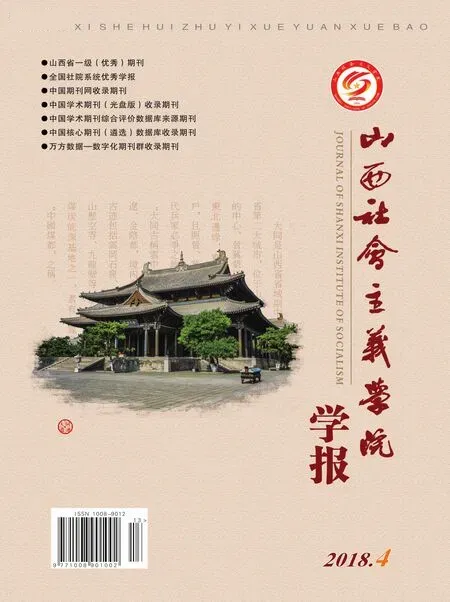先秦儒学视阈下的荀子经济思想浅述
2018-03-31高专诚
高专诚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中国上古以来的政治发展特别是周朝的政治过程,到战国末期基本结束,客观上面临着大转折,这就使得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荀子有条件在思想领域有所总结、有所发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说到底还是各家各派都想使自己的思想学说参与甚至左右现实政治。荀子思想既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又不乏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这种双重性集中体现在荀子关于霸道和王道的政治思想以及表现在此思想之中的荀子经济思想中。
一、先秦儒家王、霸政治思想中经济因素的作用
先秦儒家的王道和霸道之说,分别专指以仁义道德和强力手段主宰天下,认为天下政治非王即霸,王道与霸道不可调和。孔子政治思想的总体倾向是肯定王道的,而霸道充其量只是对王道的补充。可是,到了孟子那里,却独称王道,力排霸道。从终极意义上讲,荀子是王道论者,认为仁义道德具有更强大持久的力量,要想实现天下统一并长久保持下去,必须以王道为根本。
荀子的成长经历和思想历程既不同于孔子,也不同于孟子。孔、孟生活在鲁国,受传统周礼影响很深,理想主义倾向严重,都强调王道唯一性,主张以王道一统天下。荀子生长在三晋地区,深受三晋法家思想和战争文化影响。中年之后,荀子又在齐、楚、秦之间游历,而秦国对外不断取胜和国内井然有序,使荀子深深感受到霸道的现实有效性。所以,荀子不仅没有从根本上反对霸道,而且还关注霸道之术,比如研究兵法战策,形成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这与孔子“未学军旅之事”[1]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不过,荀子在肯定霸道现实有效性的同时,也强调以王政思想对霸道加以约束和修正。比如说,荀子的王政思想主张发展经济,以国力的全面提升作为实行霸道的基础。这种发展经济的思想,既是对现实需求的有效回应,更有利于改善普通人的处境。荀子王政思想对于经济的重视、对于普通人利益的重视,使儒家的王政思想具有更加明确的现实性。
在荀子王政思想中,经济问题得到了多方面关注,并被视为王政的重要基础之一。荀子思想这一特色与其整体思想是一致的。之所以说这是荀子思想的特色,是因为在先秦儒学中,没有其他思想家能像荀子这样,不仅重视一国的经济问题,而且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学理上进行了全面探讨。荀子思想总是能够理性地对待一切问题,能够结合社会现实提出政治社会或思想文化方面的主张。
孔子虽然不认为发展经济是儒家学者的首要关注,但也非常看重经济和民生问题。孔子虽然认为过度注重经济利益有碍良好社会风气的养成,但并没有从学理上排斥经济利益。总之,孔子并不轻视经济问题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作用。
相对来讲,孟子对“利”的反感甚至排斥更为强烈和明显一些。孟子的思路是沿着孔子思想下来的,但他由于深感道德问题在他的时代更为突出,就对经济问题特别是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诉求更为敏感。他虽然有“有恒产者有恒心”[2]之类的论断,但这个论断更多地是针对普通民众而言的,而他心目中的君子是要超越利益诉求的。
荀子主张人性为恶,强调人们总是把个人利益摆在首位,并且多半时候是自然而然的,下意识的。即使是有修养的社会中上层人物,绝大多数也无法超越私利。所以,与其漠视其存在,还不如直面现实,加以引导和疏导,更重要的是加以合理限制和管理。理性地来看,荀子的主张更具现实合理性。但是,在古代专制政治时代,这种思想的负面作用却胜过孔子和孟子的主张。在个人权力可以无限膨胀的条件下,荀子的主张更容易滑向助纣为虐的境地。
二、“王者富民”是发展经济的政治导向
先秦儒家大师们确实注意到了经济问题对于国家安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甚至是基础性作用。但是,他们同时也意识到经济利益的负面作用更是巨大,所以宁肯把思想重点放在道德教化上,这也就使他们有意无意地尽量避免谈及经济问题。但是,在这方面,荀子是个例外。他的理性主义精神让他有勇气面对现实。从其思想大方向上讲,荀子甚至可以说是明确和强调了经济利益对于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
荀子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划分出了各种类型的君主、各种类型的政治模式。荀子把当政者分为四类,即聚敛者、取民者、为政者和修礼者即王者。具体说来,最恶劣的是聚敛之君,只是想方设法从民众手中聚敛财富,而并不在意民心向背,荀子认为这种君主迟早是要亡国灭身的。其次是取民者,注意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很得民心,但却没有在政治方向上多做文章,荀子认为也只能做到使民心安定,社会不出现大的动荡,国家保证平安无大事罢了。再好一些的是为政者,能够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但政治改革力度有限,方向也不明确,并没有走上儒家礼治道路。荀子认为,最高明的政治是修礼之政,也就是王者之政。
那么,以上对从政者的分类,如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看,荀子认为,“王者富民”,让老百姓富裕,霸者是保证士卒的经济收入,那些勉强生存的国家则是富了当权者,而走向灭亡的国家则是富了君主一人。[3]所以说,“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即一个国家到底是走向贫困还是走向富裕,从一些现象当中是能够看出来的。荀子说:“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4]致使国贫民困的原因有很多,但荀子认为君主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君主好大喜功、贪财贪利是首要原因。其他则是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吃政府财政的官员太多,再其次则是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太多,减少了农业劳动力,最后则是政府的税赋没有一定之规,随意收取。所谓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员太多,是就当时的农耕社会而言的。这也是在强调,国家的强与弱,最基础的部分还是贫与富。不能打好经济基础,就很难造就真正的强国。
荀子进一步指出,在下者贫困,在上者也会贫困;在下者富足,在上者就会富足。所谓小河有源,大河才会有流。由此看来,能够生长庄稼的田野,才是天下财富的源泉。百姓劳动积极性高,把必要劳力投入到田地之中,国家收入才会有保障,国家仓库充实只是庄稼丰收的结果。所以,英明的君主,有远见的君主,必定要想方设法激励百姓的劳动积极性,开源节流,增加劳动者收入。当劳动者收入有余之时,在上者自然就不会发愁收入问题了。结果就是,在下者与在上者都富足,相互不用算计得失,到了这个时候,治国大计就到了极致之处了。[5]荀子说,在他的时代之前,曾经存在过的诸侯国有千千万万,但却只剩下十几个。这没有其他更复杂的原因,原因就是共同的一个,即没有把百姓利益作为立国的基础去对待。讲到此,荀子不无感慨地说:“君人者,亦可以觉矣!”[6]那些做人君的,应该可以觉醒了吧!
很显然,荀子这一思想既不是单纯的经济考虑,也不是完全的政治考虑,而是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的有机结合。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但只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才能付诸实施。
三、“以政裕民”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保证
在荀子礼、法治国的政治思想中,礼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但是,荀子讲礼法之治意义上的礼,并没有轻率地认为礼是自然而然的无须证明的先验之物,而是源之于经济利益的。这样一来,荀子不仅把礼和法统一了起来,而且也把礼的产生和发挥作用置于一个合理而坚实的基础之上。既然经济利益是礼的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基础,那么,注重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经济利益也就成为必然之事,至少在逻辑上讲更是社会的首要问题了。
与传统儒家的理念相一致,荀子认为对社会管理者应该用礼乐加以节制,对普通劳动者则以法规加以制约。那么,这样的礼乐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呢?制定它们的必要性在哪里呢?荀子指出,从上到下,先根据土地的大小设立诸侯国;在诸侯国之内,要根据耕地的多少、肥瘠和分布情况来决定人口的多少;对于具体的劳动者,则根据其能力的大小决定他耕种多少土地。这样一来,荀子就把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相联系,并取得了一致性。
在政治理念和经济理念取得一致之后,荀子具体讲述了他的经济措施。他认为,只有让劳动者的能力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相适应,才能保证完成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不管是农耕之事,还是百工之事。只有让劳动者顺利完成了他们应当做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才能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因而也才能保证劳动者的衣食所需,进而还能有一定的盈余。荀子把这个合理的过程称为“称数”[7],即人的客观活动与客观需求相一致。
既然是客观需求,荀子就自然推导出,上自天子,下至庶民,人们所从事的工作不管是体量大小,还是重要性如何,都应该遵循“称数”的规则。一个社会,以“称数”为准则,那么,无论是社会管理者,还是劳动者,就都不会有侥幸之心,也不会有侥幸之事,更不会有侥幸之行。这就是说,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行为一旦走上了合理之途,政治的合理性、道德的有效性自然就不在话下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称数”也就是法治之途。政治意义上的法治,源之于经济意义上的规则。
荀子坚持“以政裕民”,本质是强调政治的作用就是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合理的政治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保证。只要政治合理,就可以使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循环轨道。甚至可以说,没有合理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荀子的这一主张,在传统儒学中是不明确的。在与荀子思想紧密相关的法家思想中,这一思想虽然很明确,但其动机和最终目的又严重脱离荀子最初的设想。荀子思想站在儒家和法家之间,本意是要弥补双方思想的不足之处,但其合理的真意却未能得到当时任何一国的真正贯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历史遗憾。
四、“节用裕民”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荀子的经济思想虽然非常重视创造财富和生活消费,但同时也不断强调传统儒家“节用”的重要性,即所谓“节用裕民”。
荀子指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8]要想使国家富足,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必须节用裕民,只有在实现了节用裕民之后,国家的经济收入才会有富余。荀子顺便强调指出,要妥善积藏好富余下来的资财。
根据先秦儒家的一贯主张,“节用”的主体,通常是指在位者。比如孔子就有“节用而爱人”[9]的主张,要求在位者节约开支,节省民力。荀子“节用裕民”思想的重点在“裕民”,即不是为节用而节用,而是为了使百姓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节用。所谓“裕民”,就是让民众富裕,有富裕的收入,过上富裕的生活。在这个问题上,荀子有着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主张。
荀子主张,“节用以礼,裕民以政”[10]。节用和裕民,都要根据一定之规来进行。因为节用是针对在上者,所以要依礼而行;裕民针对在下者,所以要依照政令行事。荀子认识到,“裕民”的实质不是单单地让民众得到实惠,而更重要的是让国家有多余的收入,这样一来,社会便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国家政策对头,把民众利益放在前面,民众收入就会增加,民众收入增加的结果,必然是国家税收有保障,甚至会有多余的收入。国家利益有了保障,就有条件更加坚定执行既定政策,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也会更加提高,结果就会使国家的经济进程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荀子“裕民”思想中的民众,就是粮食的生产者农户或农民,而在荀子时代,这些人或者是至少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拥有自己的土地的,所以才会在土地中进行投入。荀子解释说,一旦实现了“裕民”,民众就会富有。民众富有了,就会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田地之中,使田地更方便耕种,更有可能实现高产,获得百倍于投入的产出。
收入的问题解决了,在上者依据一定之规收取税赋,在下者则加以理性的节用,结果就是,富余下的粮食或其他财物就会堆积如山,荀子更为形象地说,即使是不时地进行焚烧,这些东西也会多得无处堆放收藏。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在上者实施“节用裕民”政策,还会得到“仁义圣良”的好名声,更不用说富厚如丘山一般的实际收入了。所以,“节用裕民”才会成为王政之经济政策的不二选择。
五、“以利导民”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原则
着眼于现实,既然利益是基础,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是当政者回避不了的,那么,与其避而不谈,还不如直面加以讨论,更不如合理地加以利用和引导。特别是对于当政者来说,充分重视和利用实际利益的作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为此,荀子分若干层次讲述他的“以利导民”的原则。
在普通层次上,当政者如果要想从民众身上得利,可取的办法是让民众也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利,而不应该限制甚至阻止他们有所得。此所谓从民众身上获利,既包括税赋之类的直接从民众的劳作中获利,也应该包括社会的安定,即民众奉公守法,当政者安享国运。为此,荀子主张,当政者必须让民众也从这个过程中得利,即至少要保证他们的温饱和心情舒畅。这也就是荀子接下来解释的,当政者与其以不爱民众的心态去役用民众,不如怀着慈爱之心去役用他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建功立业。
在高层次上,荀子的主张也是非常明确的。当政者与其让民众得利之后再利用他们,还不如让民众得利之后,根本不要从民众身上获利,这样的利益才是当政者最应该得到的利益。同样,以慈爱之心役用民众,还不如既有慈爱之心,又不去役用民众所获建的功业更为宏大。其实,一个国家要保证其正常运转,不取利于民,不役用民众,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当荀子倡导“利而不利”“爱而不用”[11]的时候,主要是强调当政者对待民众的指导思想,以及尽可能在合理的范围内低额度取民用民政策。
从获利的角度出发,荀子还是把当政者分为三个档次,这与荀子对天下政治的层次划分也是一致的。
那些最高层次的,是能够以王道一统天下的统治者,荀子称之为“取天下者”,他们对待民众的态度是“利而不利,爱而不用”,只为民众谋利,不从民众身上获利,以爱临民,不过度役使百姓。
中等层次的统治者,荀子称之为“保社稷者”,即维持自己的国家不被灭亡。他们对待民众是“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就是上述普通层次上的当政者。
下等层次的统治者,是“危国家者”,让国家处在危亡之中的当政者,因为他们对待百姓是“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不为百姓谋利,反而一味地从百姓身上取利,对百姓不仅没有慈爱之心,反而无度地役用百姓。[12]
很显然,在荀子思想中,治国临民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经济利益。如果解决了民众的经济利益,如果当政者如同对待自己的利益一样对待民众的利益,就能使国家走向兴盛。这样的观点,在其他儒家大师的思想中是不明确的,甚至是难以推导出来的。正是有着这样的理性思维,荀子思想才能在务实的汉唐时代受到普遍重视,产生广泛社会影响。
六、“王者之法”是发展经济的有力促进
为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荀子还讲到了“王者之法”。此“法”并不完全是法律之法,而是“师法”之法,荀子的说法是“人师”,即王者给人做榜样,让人们效法。荀子甚至强调,英明的君主是发展经济的有力促进,这一思想是那个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不敢设想的,也是不可能提出的。
荀子强调说,身为人民之主,一定要喜欢美饰自己、追求富厚生活,以此来统一民心,让人们满足物质欲求。君主过着优渥的物质生活,耳、目、口都得到了最大满足,就会使人民知道,追求物质享受是合理的。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在守法的前提下,去努力劳作,以求得到最大物质利益。在个人物质利益得到满足的同时,社会财富也会不断增加,以至于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物产,不得不烧掉。[13]荀子使用这种夸张的说法是要告诉人们,统治者不可以用限制人们物质消费的方法统一思想和安定社会,而是要用必要的物欲去刺激人们的行为,让人们明白物欲是可以通过必要的劳作而得到满足的,这就在客观上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找到一个合理的根据或发展动力。
我们注意到,在荀子的“王者之法”中,重点是经济原则,强调了王者之民并不是生活在纯粹的道德原则之下,而是必须在必要的和优渥的物质条件下生活,这个方面,如前所述,是孔子、孟子的思想中相对薄弱的一面。这就说明,当荀子考察各国状况时,特别是考察秦国的发展进程时,明显注意到了生产和生活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在韩非子的思想中,特别强调奖励耕、战之士,其中的“耕”,就是农业生产,也包括人民生活。农业生产有进步,人民生活有保障,是“战”的根本保证。秦国士兵的战斗力超强,根本原因是秦国士兵不仅纪律严明,而且体格好,兵器好,而这些都有赖于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和有保障的物质生活。在山东六国都在力保上层社会享受的同时,秦国却非常在意所谓“耕战之士”的生活。这样一来,最终的胜负其实早就有结果了。荀子根据现实考察和理性思考,认识到了发展经济的必要性,所以才明确主张“王者之法”的核心是经济,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可贵的思想。
七、“导民”“教民”是发展经济的必然结果
当然,在主张富民,让民众生活富足的同时,荀子也没有忘记他的政治思想家的使命,即以儒家的道德思想教化民众,以期造就一个理想的社会。荀子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
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导之也。[14]
根据荀子的人性之论,人性是人的本质,人情是人性的表现。荀子提出,人的思想本质需要通过道德教化加以调理,而人的实际表现则需要通过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加以调养。如果只有道德说教,而缺乏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办法,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性之恶、节制人情之放纵。当然,如果只强调物质生活,不进行教化,也无法实现民性、民情的改变和提高。从逻辑上讲,富民与教民应该同时进行,二者同等重要,但从实际操作层面讲,荀子还是主张富民放在前。
因为必须富民在先,荀子主张,普通人家应该有五亩宅院,百亩耕地,还必须保证其劳动时间,当政者不能用太多的劳役影响农时,这才是富民的正确路径。做到了这一点,才能设立各种层次的学校,用礼乐教化导引人们由富走向善。值得强调的是,荀子真意并不是说富了之后再去教化,而是说必须在民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教化才能发挥其真正作用。荀子关于“五亩、百亩”以及“大学、庠序”的观点,在《孟子》书中被孟子多次提及[15],看起来并不是荀子的创见。但是,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是在多方位强调民众经济利益的大背景下讨论富民与教民的问题,这就显得比孟子的观点更加实在。
总之,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论是理想中的王政,还是现实中的霸政,必须注重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这其实是法家的基本主张。但是,法家人物,比如荀子的弟子韩非子,认为只要解决了民众的物质生活问题,并不需要刻意进行道德教化。在儒家思想传统中,孔子早就提出了“先富后教”[16]的思想。不过,孔子以及其他儒家人物主张的“先富后教”是将富作为教的手段和过程,教才是最崇高的目的。而荀子的高明之处是把富也作为不可或缺的目的。也就是说,其他儒家大师们有意无意地认为只有教才是天经地义的,而荀子则认为既富且教才是合理的现实选择。
注释
[1]《论语·卫灵公十五》。
[2]《孟子·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3]《荀子·王制》。
[4]《荀子·富国》。
[5]《荀子·富国》:“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
[6]《荀子·富国》。
[7]《荀子·富国》。
[8]《荀子·富国》。
[9]《论语·学而第一》。
[10]《荀子·富国》。
[11]《荀子·富国》。
[12]以上均见《荀子·富国》。
[13]《荀子·富国》:“财货浑浑如泉源,滂滂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藏之。”
[14]《荀子·大略》。
[15]《孟子·梁惠王上、滕文公上、尽心上》等。
[16]《论语·子路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