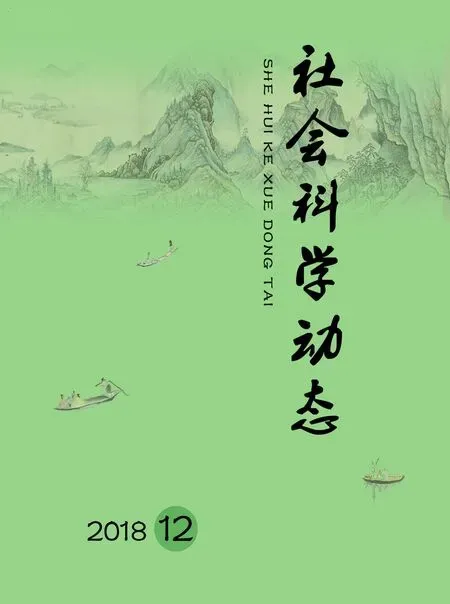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资源综论之儒家篇(二)
2018-03-31胡静
胡 静
(接上期)
二、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重点方向
(二)各时代诸子学说
从知网的学术文章及相关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来看,目前对于儒家诸子的生态思想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先秦的孔孟荀、汉代的董仲舒、宋明张载、二程、朱熹、王夫之、王阳明等。这些人物往往具有划时代的思想史意义或者其思想对儒家生态思想观念的形成、体系的建构等具有特殊贡献。从学者们研究的情况可以发现,越往近代,诸子生态思想的线索越清晰、内容越丰富、体系越完整。具体归纳如下:
1.孔子
学者们对孔子生态思想的考察主要切入的角度在其“仁”学思想,主要引用《论语》、《孔子家语》、《礼记》等文献中孔子(或者借孔子名义发表)的有关言论来说明。如《论语·学而》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述而》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弟子行》的“启螫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等等。主要突出的是孔子对自然生命的尊重与爱护的态度及其由此对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统治者提出的为政要求。对天人关系问题的生态意义的理解,孔子代表性的观点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能“言”、有“言”是人类的特点①,而“天”却无声无臭,不喜不悲,所以“四时”之“行”、“百物”之“生”都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其背后并不是由某种人格意义的主观意志主宰的,而是由其自然本身内在规律决定和推动的。这种天道的自然运行是一种不由人的意志改变的力量,而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的范围、方式、内容、成果等也要受到这种力量的制约。因此,一旦人类的行为违背了自然天理,就必然会受到惩罚,所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很明显这其中蕴含着值得思考的生态意义。
2.孟子
孟子对人与自然关系已经有比较明确的表达,如学者们经常引用的《孟子·尽心上》中的句子:“君子之于万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这段话中,孟子清楚地指明了在爱、仁、亲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层次差异与逻辑关系,不仅突出了人及其社会生活在天人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彰显了生生才是仁道的起点和根本。因为亲亲就是基于由“生生”之道而产生的自然情感和自然现象。没有对亲亲中生生之道的深刻领悟,则难以行忠恕于他人,做到仁民。而如果连自己的同类都无法推恩,那么就更不可能产生护生万物的意愿和行动。反过来,如果先爱物而不仁民,或先仁民而不亲亲,则是将爱与仁的行动直接建基于人的个性化的感性或理性,而抽掉了作为人性之普遍性来源的自然基础。这就与儒家仁道本于天道的逻辑相违背了。这是孟子生态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孟子生态思想的第二个层次是探讨了人如何才能够完成天赋的养护万物从而维系人类的生生责任。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这里的逻辑前提是确定人来自于自然,因此只要人运用自身的认知和反思能力,由认知人性始,则能够达到对自然本质和万物之性的认知。而发展这种认知和反思能力,使人性得以涵养、保全、充盈,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处理好天人关系了。孟子生态思想的第三个层次是法度的保障:“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洧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梁惠王上》)在这个政令性的观点当中包涵了对万物生长有“时”的自然规律的认知,强调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确保自然的生机勃勃,从而才能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由以上三个层次的分析可见,孟子的生态思想已经具有比较清晰的理论逻辑和比较完整的理论结构。
3.荀子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强调万物生长有“时”,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必须以时禁发。此观点在《荀子·王制》的“圣王之制”中有清楚的论述。但是,荀子最重要的生态思想贡献在于他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更加细致,论述更为明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本体论层面强调天是万物生命的源头,是万物生长变化的根本原因,指出“天地者,生之始也”(《王制》),“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礼论》)“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论》);二是既具有天人感应的观念倾向,指出“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荀子·宥坐》)②,又认为天没有主观意志,不会主动干预人事:“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荀子·天论》)。两种观念结合起来看,说明荀子认为天道无私,真正对人事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乃是人本身③。人的行为能够与天道相符合,就是为善,不符合则是为恶。为善或为恶所得到的福祸不过是自然进程在人为的顺应或干扰下产生的必然结果,也就是福祸自招的意思。所以人类的活动才应当特别谨慎;三是认为天人职责相分。荀子指出:“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论》)但是,“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礼论》)也就是说自然对于万物包括人虽然有生育之功,且万物之间存在互养共生、相须相资之实,但是真正能够使自然万物的存在价值得到体现和实现的却是人。这就确立起了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的主体地位与责任根据。四是强调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认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性恶》),强调知天的目的在于致用于人事,这表明其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坚持人本主义的生态观。在他看来,尽管自然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人却可以通过主动作为参赞天地。所谓主动作为就是顺天时尽地利,使万物达到“治”的状态。这种以人及其活动为中介而获得的“治”的状态,简单来说就是使进入到人类视域中的自然世界,或者说人化自然界及其中的万物,仍然如同在自然条件下一样,能够各安其位、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各正性命。这就要求人的活动必须建立在对天道具有正确认知的前提下,以正确的认知为指导而进行的参赞天地的人为之“治”,才能做到成物之性、尽物之利,而人类自身也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和空间。所以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原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五是高扬人性的力量。荀子认为人与万物一样都是禀赋了天道而产生的,“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人性就是人所禀赋的天道,它内在地蕴含了人类活动的合理、正当的倾向。因此,人只要涵养人性,就自然能够感受到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正当的,从而在人类活动中将这种合理性与正当性实现出来,达到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效果,使万物各正性命、各得其宜、生生不息:“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也,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天论》)
4.董仲舒
董仲舒的生态思想资源最为学者们称道的就是正式提出了“天人合一”理念:“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 尽管他对天人关系进行了神秘化解释,但细究起来,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自然其实已经摆脱了纯粹自然意,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化自然,换句话说,人与自然是在人文意义上合而为一的。他说:“事物各顺赞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深察名号》)“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立元神》)可以看到“名”这一人文化的事物,具备了作为万物与天之间的媒介的作用,也正是因天道而正“名”④,天人合一的关系才能够得到理解和表达。所以在这样一个人文世界(包括人化自然)中,人与天地一样成为万物之所以是其所是的根本。万物离开天地固然无法孕育成长,但是离开人,离开建立在礼乐基础上的“名”,万物就不是其所实然的存在状态。可以说,董仲舒的这一思想是极其深刻的,从生态意义上讲,我们所讲的自然与人的关系确实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加以理解的。从根本上讲,人是无法脱离人的立场去界定万物的存在的,当然也就不可能脱离人的存在去讨论生态保护的问题。这是董仲舒生态思想的重要贡献,也是我们认知自然与人的关系时必须客观地面对的现实情境。此外,董仲舒将以近取譬的语言传统发挥到极致,其对天人关系的描述极其经验化,其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人副天数”,就是将人与天进行非常直接的对应比附,使人变成了天的异形复制品,就好像神仙化成凡人模样,形态上虽不同,但本质上没有变。这样的天与人在本质上当然是合一的,而且是必然能够感通的。既然人性即是天性,仁道即是天道,人动与天动两相应和,那么人就必须随时修养自己的天性,反思自己的行为,使之不背离天性、天道,从而实现与天之间积极正向的互动。董仲舒还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 的思想,将仁道推及自然万物,为儒家仁学赋予了明确的生态意义。他说:“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离合根》)“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义法》)
5.张载
虽然前有董仲舒首提“天人合一”的理念,但是作为一个范畴提出并作出更为深刻论证的是张载。因此张载及其思想在儒学乃至中国哲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张载的生态哲学思想包括以下逻辑层次:其一,解释宇宙(自然)生成及其运动机制。与儒学的“天”观一脉相承,张载认为自然界本身有其内在价值。所谓内在价值不仅是指自然界为万物包括人提供了存在和活动的场域及其条件,而且其天然地具有使万物包括人生生不息的本质力量或运行机制。这种内在价值并非由人赋予而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成为人类一切价值的根据,构成人类一切活动最根本的价值原则。其二,通过“性”与“能”范畴构建了天与人之间的基本格局与动态关联。所谓基本格局就是指确定了自然(物)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性”之一源的基础上的。在中国文化中,性生相通,生性不离。也就是说自然(物)与人之间从存在性上讲是平等的,这就等于确定了自然(物)与人共生格局的合法性。所谓动态关联就是指天人合一不是既成性的,而是生成性的。张载提出:“天能谓性,人谋谓能。大人尽性,不以天能为能而以人谋为能,故曰‘天地设位,圣人成能’。”⑤这就是说物是性能一体的,所以天物合一可谓是既成性的,但人之性与能却有天人之分,而天人合一就是“尽性”,就是“成能”,是人发挥主体能动性实现自身天性或本质的过程。这种尽性成能的状态可以借用马克思所谓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得到很好的理解。这种对天人合一关系的生成性的理解意味着,人如果不能朝向成就自性⑥的方向作积极的努力,天人关系就可能面临相背离的危机。其三,揭示了自然对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的规定性。张载的生态思想将《周易》的自然必然性与儒家的仁学伦理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论证万物之间同根不同质的客观实在,确立了尊重多样性的民胞物与的和合关系原则;通过揭示自然的内在生机,及由其所决定的万物之间的相生关系,确立了人对自然万物护生成全的责任担当与道德使命,正所谓“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不难发现,在这样一种生态思想下,人的存在方式就只可能是关系式的而不是原子式的,其存在价值也必须表现为手段与目的的统一。由此可以说,正是通过张载的生态思想的逻辑展开,使《易传》以降儒家参赞天地的思想获得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表达。
6.二程
二程(程颢、程颐)作为理学的创始人,其生态思想是与其天理观相贯通的。二程的“天理”观是其原创的范畴,正如程颢所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其所谓“天理”是贯通自然万物包括人类及其社会的,是整个世界得以存在和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儒家的“仁”则与此天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是天理通过人所显现的价值形态。所以天理流行处,仁道亦当流行。由此逻辑,仁道必然也会从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的处理中体现出来。二程以天理观为基础的生态思想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万物一体”,二是生生为仁,三是自然审美,四是存理制欲。
与张载对天人关系生成性合一的认识不同,二程更加强调天人在本体上的绝对同一,认为“天人本无二,不必有合”(《二程遗书》卷六)。既然无二,那么就意味着人的社会存在实际上是自然生态存在和运动变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与自然关系的应然状态就是共生共振的,其所作所为与自然生态息息相关。自然生则人生,自然长久则人长久。如果人能体认到与自然的一体相通性,爱自然万物如同爱己之四肢百体,则天人长久就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而如果局限于一己之私就无法体认到这种同体共生关系,使物我相互隔绝对立,将满足私欲建立在伤害自然万物的基础上,其最终结果必然是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以这种天人关系认知为基础,天理与人理、天道与人道当然也就是一致的。所以程颢进一步指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如果失去这种浑然一体的贯通性,就是不仁。人道之仁与天道之理由此达成了统一——由于“天以生为道”,所以“继此生理者”的仁的本质就是“生生”,即仁者或者说儒家对于人的存在价值的理想规定就在于将这种天地自然的生生之理推行于人类社会生活当中。也是在天理仁道相统一的意义上,程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学者们已经论证,程颐此言当中的“灭人欲”并不是否定人的正当合理的需要,而是指克制或摒除超出正当合理需要之上的刻意需要或过度欲求。原因就在于与天理的中正平和相一致,人道也应该是中正平和的,所以人就应当坚持“理”所当然的存在方式,而摒除非“理”的、与“理”相违背的倾向。以此原则关照自然与人的关系,当然就要求用之有节,取之以时,存物之性,涵养生意。
此外,程颢生态美学思想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生态美学的核心就是人与自然互动而产生的美感。这种美感既源于自然的客观呈现,又依托人的心理加工,从根本上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合关系。因此生态美学是生态哲学重要的理论形态。儒家自孔子就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的生态审美观,董仲舒则有“仁之美者在于天”(《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的美学本体论。而程颢则将《易传》所描绘的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宇宙和谐而生机蓬勃的状态作为美的最高境界,并由此产生了以“生意”为核心的自然审美观念⑦。这是程颢生态思想独具特色的内容。
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北宋时期,由于人为活动引起自然灾害频发使生态危机成为儒家学者强烈关注的社会问题。对此,程颢曾有措词严峻的论述:“圣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于五官;山虞泽衡,各有常禁,故万物阜丰,而财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无节,取之不时。岂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资,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荡,尚且侵寻不禁,而川泽渔猎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则将若之何!此乃穷弊之极矣。惟修虞衡之职,使将养之,则有变通长久之势,此亦非有古今之异者也。”(《河南程氏文集》卷一,《论十事劄子》)这段话程颢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去谈的,但是从中可以发现其所坚持的生态思想。首先是“圣人奉天理物”,使“各有常禁”而“财用不乏”,这是与儒家一贯的尊重自然规律、参赞天地的思想相一致的;其次是人“用之无节,取之不时”导致“物失其性”,这种行为违背了儒家节用、以时、成物成己的生态实践原则;再次是只有“将养之”才能“有变通长久之势”,提出了生态修复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7.朱熹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对前人,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等皆有继承与发展。朱熹通过对理、气、仁、心、性、命、情等范畴体用性质和相互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天人关系的本质及其表现,此亦成为其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理”是朱熹思想的核心范畴。朱熹认为万物虽然众相殊异,但是归到理上却是一,而这个“一”从事实来说就是“生”,从价值来说就是“仁”,所以他说“仁是个生理”(《语类》卷二十)。这种“生理”,不仅是指创生(新陈代谢、生生不息)是一种自然而必然的运动趋势,也是指驱动创生趋势形成的内在机理,所谓生之“心”。而后者更为重要。前者可以理解为具体的规律,比如四季的转换带来的生态变化,生命的繁衍与生老病死等现象,都是由这种意义上的“生理”所规定或决定的。而后者则强调在具象层面的“生理”之上还存在一种使这种“生理”产生的驱动力,类似于物理学上的第一推动力。也就是说,后一种“生”理是前一种“生”理得以产生的根据,或者可以称之为“生欲”。正是因为从这两个层面去讲“理”,所以朱熹既说“天地以生物为心”,又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天地生物就是前一种“生理”的流行,而“以生物为心”或者说“生物之心”则是强调此“生理”的流行源出于其背后的自然“目的性”⑧。由此朱熹的生态思想便可以展开来说了。首先,从理一的层面来说,“天地之间,万物之众,其理本一”⑨,所以“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⑩。即自然万物包括人虽然形态各异,但是其得以存在和生生不息之“理”据都是一样的,这种生存本质上的共性决定了其相互之间本不应有隔阂与对立,而应该能够感通移情、惺惺相惜。其次,从分殊的层面来看,“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⑪。此即是说,万物包括人都是由天理流行而产生的造物,并且因此成为涵容天地之“生理”与“生欲”的载体,即具有“生”性。这种“生”性并无“偏全”之分,而是在万物身上表现为对生或生生的共性追求(欲望)和本能维护。由此则可以得出:万物与人在存在上具有平等性,或者说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再次,从物与人的差异性上说,朱熹认为,虽然万物与人皆具“生”性,但是其他生物往往为“形体所拘”,不仅难以实现或只能部分实现与外界其他生命之间“生”性上的感通交流,而且无法体认其内在的天理⑫。人则独具灵性,不仅能够在生存实践中体认到“天地怏然生物之心”,而且能够自觉地“合内外之理”,使己、人、物之共性的“生理”得以贯通,在追求成己之性的同时,成人之性、成物之性。正所谓“此心爱物,是我之仁;此心要爱物,是我之义”⑬,“此心何心也?……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⑭。正如蒙培元先生所说,“实现理性自觉,实现‘天理流行’的境界,是朱子哲学的根本使命。所谓‘天理流行’,就是人与自然的完全统一,生生不息,万物的生命因而得以畅遂,人则尽到人的责任,完成人的使命,从而体验到生命的意义,感受到人生的快乐”⑮。
总之,朱熹的生态思想是通过其所构建的完整的“理—仁”学体系得以阐发的。基于理与仁的内在统一,朱熹构造了天理生物与人仁爱物两条相向而行的逻辑线索,一方面,人物皆因生而得其理,理在人即为仁,理在物则为理,仁理本一,物与人因此具有了相通互爱的自然根据;另一方面,物不能自通通人,而人能自通通物,人的特殊资质使人自任了参赞天地“生理”的责任,这种参赞责任不仅表现为对每个人的生生与整个人类社会的生生负有责任,而且表现为对自然万物之生生负有责任。所以人需要格物致知,正确认知物理人仁之本然,既要成物之性尽物之利以为人,又要成人之性尽人之能以爱物,此即《易·泰·象》所谓“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8.王阳明
王阳明的生态思想是与其心学立场紧密联系起来的。首先,“心”是王阳明探讨一切问题的基本视域。所谓“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⑯。这就是说,一切存在性都由心出发,由心的照应而显现。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如此。在“心”的照应空场的情况下,自然的存在只是“寂”,也就是不显、不动的状态,因而其存在与否、如何存在等都脱离于人的意识之外,对人而言,这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毫无意义的,当然也就无法与人构成关系。反之,凡与人之间构成关系者,都意味着受到了“心”的照应,即是已经显现其存在意义的存在者。与《周易》揭示的天地之一阴一阳生成自然世界的机理不同,“心”的照应是意义世界的生成机理。但是在王阳明,这两个世界又并非是各自独立的,因为“人者,天地之心”,也就是说,以人的存在为前提,我们对自然世界生成机理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描述本身已经是一种为“心”所照应而赋予了意义性的结论。这实际上就取消了纯粹自然世界存在的现实性。从这个视角来看,自然与人的关系本质就是意义的,即是以人为坐标来界定的,一方面,人以自身为立场,则需要在自然与人之间划出分界,体现人的独特存在性;另一方面,人以超越自身的立场,则可以认识到自然与人之间的同质性⑰。这两种性质不仅是“心”所照应到的自然与人关系的全面本质,也是人自身的存在本质。因此人的活动的完整意义就在于同时满足或实现这两种性质。在王阳明看来,这不能理解为某一个体刻意的道德行为,而是所有人的“心”之明德。所以王阳明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⑱
其次,心是天理良知呈现的介质。王阳明认为“良知即天理”、“良知即道”,而由上文可知,天理是通过“心”来显现其意义的,而良知可以理解为是天理在人心的全面映射。因此要使天理良知在每个人的“心”上光明地呈现出来,成为指导人的活动的依据,就必须保持“心”的干净和敏锐,所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朱熹的“格物”是不同的。王阳明将天地万物包括人均纳入到“心”的范畴,认为人们只需要将“心”打扫干净,去除私蔽蒙昧,保持其照应天理、映射良知的功能能够完全地发挥出来,那么天理良知就会自然地呈现在人之“心”幕上,而无须刻意追求。这样人的首要活动就是对自身“灵明”之心的照顾保养。王阳明指出:“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⑲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人的良知就是人心对天理的全面把握,在这一基础上,当天理化入具体物象当中而成为物象自身的物理时,良知也就随之成为其物理之意义化的表达——即理而命名,这样,万物的意义投射才得以完成,万物才成其为它在这个意义世界中的自身,并与人发生关系。由此,人“心”只要能够完全地呈现天理良知,在天理良知的引导下,便无需刻意算计思考就能够遇事而化事、遇物而待物,无所不至,无不合理,“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⑳。既然如此,人与自然在相处过程中如果存在矛盾,就说明“心”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以致于天理不彰、良知蒙蔽,而要解决矛盾,就必须修养人“心”,恢复“心”应有的功能,当此时,则“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㉑。此所谓“必”说明的就是人在“心”如明镜的情况下,必然能够天理昭彰,从而循顺良知、参赞天地,使万物化育、成性存存、和谐共生。
由于王阳明将人“心”作为介质,使天理经由人“心”而照应为良知,人继以良知为“明镜”照应现实,在社会活动中实现体用合一。因此王阳明心学生态思想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突出了人在自然与人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使自然的现实性存在成为一种人为性的存在。这种人为性,不仅是说现实的自然是一种意义性的存在,而且说明人的活动对于自然的现实存在状态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人成为解决一切关系,包括自然与人关系问题的关键,人心明则关系顺,人心昧则矛盾生。这样,在万物一体的认知前提下,人就不得不担负起对己、对人、对物的全部责任。反过来,人履行对人、对物的生态责任——维护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之和谐共生关系的过程,在本质上也就是修心养性、使自身明德昭彰的过程,“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由此,人与自然各正性命、各得其所。
9.王夫之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大家,其研究通贯儒学各个方面,不仅集前人思想之大成,而且自成一严密体系。与中国古代哲学家一样,天人关系问题也是其思想的逻辑起点。从生态视角看王夫之的天人关系思想及其整个思想体系,可以发现其基本的理论逻辑与构架。其一,气本论。王夫之的思想基础是气本论,其与张载的气本论有非常明显的承继关系。通过确立气本,不仅解决了万物之源与万物之生的问题,也解决了世界应然的存在状态(动态、均衡、和谐)的问题。“天下之物,皆天命所流行,太和所屈伸之化,既有形而又各成其阴阳刚柔之体,故一而异。惟其本一,故能合;惟其异,故必相须以成而有合。然则感而合者,所以化物之异而适于太和者也。”㉒其二,天人之间本和质异、由分致合的逻辑关系。王夫之由气本论论证了天人关系在本质上的同源性与和谐性,又通过对质、气、理等范畴及其关系的阐释说明具体人物性命的差异,突出人的理性之可贵与责任之必然,指出要解决天人关系因质异而造成的失和,必须经由相天、竭天、以人造天㉓的过程,将被拘蔽的“天人合一”㉔解放出来,实现由分致合。
具体来说,王夫之的生态思想有几个重要的方面值得注意。其一,王夫之天人论域中的“天”彻底摆脱了传统天人之学中的人格神意,成为无意向性、目的性、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具有普遍性的客观存在。由此天人关系真正落实为自然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二者之间具体而现实的因应关系。“天不可以体求也,理气浑沦,运动于地上,时于焉行,物于焉生,则天之行者尔。天体不可以人能效,所可效者,其行之健也。”㉕其二,天人之间的因应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意味着天人是相分的,所以才会有互动性;另一方面说明天人具有相合的可能性,所以因应互动才能实现。天人通过因应互动,人以其气质禀赋天理而成性,通过尽人之性而发展、发挥认识与实践之能,以其能而从天之治,尽人道以成参赞自然化育之功,从而合于天道,成己成物。“因天之能,尽地之利,以人能合而成之。凡圣人所以用天地之神而化其已成之质,使充实光辉者,皆若此。”㉖其三,人的活动之自为性。王夫之对自然与人的认识较之前的学者更为深刻。他不仅认识到自然造物的无意向性,而且认识到人的认知与实践的有限性。王夫之认为,“天无为也,无为而缺,则终缺矣”,而“人有为也,有为而求盈,盈而与天争胜”。也就是说,自然万物并非按照人的需要形成的,因此从人的视角来看其各有缺陷,且容易导致“吉凶常变”。在这种情形下,人类活动就不会止于一般意义上的因应互动,而会通过主动改造自然,追求实现更加圆满的生存状态。但是受到“血气心知之所限”,改造自然、与天争胜的结果往往是成败相乘,所以“固盈”是不可求的。可见王夫之认识到,虽然人的主体自觉自为是人的可贵之处,但是这种自觉自为最终会受到“自然之秩叙”的限制。这种“自然之秩叙”的限制,一方面表现为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先天地具有有限性,只能对于那些切近自身需要的事物加以认识和追求,“不切于吾身之天地万物,非徒孔、孟,即尧、舜亦无容越位而相求”㉗,所以“人心不可以测天道”㉘;另一方面表现为人作为气聚而化成的具体物,其质各不相同,对天道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拘蔽”。因此即便只是因应互动,人的活动也无法做到完全地合乎天道,更不用说自觉自为的与天争胜的活动更会受认识上的“拘蔽”影响而导致实践结果的偏差。在王夫之看来,严格意义上,只有圣人才能够“退藏于密,上合天载”,真正实现天人合一㉙。对于大多数人,包括君子贤人来说,都只能通过穷理尽性,使人与物的先天缺陷通过人的合乎物理人性的自觉有为而实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故缉裘以代毛,铸兵以代角,固有之体则已处乎其缺,合而有得,而后用乃不诎。”㉚也只有这样,人才能不断纠正、减少和避免不合乎天道的行为偏差,使自己的活动臻于天人合一之至善,接近圣人所达到的天人境界,从而担负起参赞天地之化育的责任。其四,处理天人关系的基本原则或精神。王夫之基于其自然观与人为观,提出尽性、尽人道的关键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继天之道:“天人相绍之际,存乎天者莫妙于继。”㉛这一“尽”一“继”的基本精神或原则就是“发己自尽”与“循物无违”。所谓“发己自尽”,就是“凡己学之所得,知之所及,思之所通,心之所信,遇其所当发,沛然出之而无所吝”。而“循物无违”,则是指“依物之实,缘物之理,率由其固然,而不平白地画一个葫芦与他安上”。说到底,“发己自尽”、“循物无违”就是要求人要效法自然“不复吝留而以自私于己”,“不恣己意以生杀而变动无恒”,“顺其道而无陵驾倒逆之心”,使“物之备于我,己之行于物者,无一不从天理流行、血脉贯通来”,那么就能够实现天人和合的美好图景:“物之可以成质而有功者,皆足以验吾所以行于彼上之不可爽”,“方春而生,方秋而落,遇老而安,遇少而怀,在桃成桃,在李成李”,“道以此而大,矩以此而立,絜以此而均,众以此而得,命以此而永”。反之,“内不尽发其己,而使私欲据之;外不顺循乎物,而以私意违之。私欲据乎己,则与物约而取物泰;私意达乎物,则刍狗视物而自处骄。其极,乃至好佞人之谀己,而违人之性以宠用之;利聚财之用,而不顾悖入之多畜以厚亡。失物之矩,安所失絜,而失国失命,皆天理之必然矣”㉜。此段文字中,王夫之对于人在处理自然与人关系时应坚持的原则与精神给予了清晰的表达。
三 儒家生态思想的逻辑构架与基本观点
在中国古代,生态问题并不只是一个现实层面的社会治理问题,它还包涵着对人类自身何来何往的根本价值追问和对生命的美感体验,因此在梳理古代生态思想资源,理解和把握古代生态思想的内在意蕴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些方面。整体来看,儒学是围绕“人”来展开的。向上,强调知命与乐道,关注人之所从来与所将往的问题;中间,强调修身养性,关注个体现实的安身立命问题;向下,强调治事以礼法,关注社会生活的秩序性与和谐性问题。如上文分析所见,儒家讨论自然与人关系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儒学的立论基础与终极追求问题。也就是说,在儒学中,天人关系是作为对“人”的存在从以上三个层面展开思考的必要条件纳入其中的。通过对天人关系的界定,并根据这种界定,儒学得以完成对人的存在性质、存在价值、存在境界等的解释。由此决定了我们对儒家生态思想的把握及其基本观念的归纳也必须遵循这样一种逻辑构架。简要陈述如下。
首先,在第一个层面上,儒家生态思想回答了人之所从来与所将往的问题。儒家的基本观点是,第一,自然是人类生命的起点与终点,自然与人本源于一。关于自然与人的生成问题或者说本源问题,最早是由《周易》的《易传》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即阴阳(乾坤、天地)的相互作用是万物生成的根本原因。先秦时期,已经有将阴阳作气解的思想,气本论逐渐成为解释万物生成、变化的基本范型。到宋明以后,儒学的本体论更加精致化,以张载为代表,对自然万物包括人的生成及变化作出了系统的解说。由气本论立场,万物之生乃气之聚,万物之灭乃气之散;气之聚散的差异形成了万物之差异,万物之差异不仅表现在各自具体的存在形态、存在方式、存在机制等方面,更表现在天性的差异上。但是就根源来说,这种具体的差异终将消失,回归到气的原初状态。由此可以证得,自然与人在本源上是同一的,其根本质性也是一致的。进一步来说,自然与人在均气同体的意义上一定是和谐统一的。第二,自然性是万物包括人类的基本性质,自然的天性是纯朴合理的。在中国古代各思想流派中,自然具有天然的正当合理性是一个基本的共识。而在儒家,关于人性的解释虽然有精粗之别,但是都肯定人性当中自然而然的那一部分具有客观的合理性。比如人自然而然的生理欲求都是得到肯定的㉝。反过来,超出人的自然天性规定的欲求则是不合理的。儒家认为人的天性是自然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即明德。明德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能够选择正确行为的内在根据。不合理的欲求,包括生理层面与心理层面的,都是明德不明造成的,而不合理的欲求则是导致自然与人、人与人关系失序恶化的根源。同时,就其他生命来说,其天性欲求也都具有合理性,都应当被尊重和保护,因此人在自身的生存活动中不仅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求对自然予取予夺,而且还要能够成全万物的天性欲求。即所谓成物成己。第三,自然为人类美好价值的衍生提供了依据,天人合一包涵着自然与人的情感交融。自然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先在的、强大的、丰富的、神奇的存在。尽管人类早期在自然力量面前过于弱小,但同时人类也发掘到了自身的生存优势——认识与实践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恰又是自然赋予的。特别是对农耕民族来说,人们对自然是既敬畏又赞美的。自然也是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对象,人类从自然获得生存的必要知识,领悟建构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几乎一切美好价值的源头都在自然那里或者与自然有关。所以自然以及自然而然的状态也成为中国古代先哲欣赏、体悟的对象。而在欣赏体悟自然美的过程中,人的明德之性也得以涵养、保全、充盈。此外,自然与人本源上的同一,使得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相亲关系,如同亲子同胞之间的血缘关系一样。所以自然能够成为人类寄情之所。而也正是这种情感的皈依使得自然与人的关系充满互动的生趣。
其次,在第二个层面上,儒家生态思想指明了人类安身立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儒家的基本观点是,第一,自然是人类生存活动展开的空间场域,自然条件是影响人类活动及其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在《周易》中已经传达了这样一种基本思想。《易经》的卦象体现了阴阳运动所构成的环境条件的变化,从万物包括人皆出于阴阳来看,这就实际上指向了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的变化。《易传》则以文字的方式解说了卦象的意蕴:上天下地的立体空间、动态的自然条件构成了人类安身立命、上下求索必须充分考虑的前提条件。人类活动只能在这个前提下开展,并且受到这个大前提的制约。人类对这个空间场域及其自然条件的认识越充分,互动越良性化,其展开的活动成功的机率越大,反之则越小。第二,自然与人是相生相成的关系,从长远来看,自然的存在质量与人的生存质量成正比。儒家以人为贵,强调人的自觉自为性。这一观念在《周易》已经得到申发。《周易》经传不仅揭示出自然与人的统一关系,而且揭示出二者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不同意义。自然作为先在的客观条件,对人类活动的开展既具有支撑性也具有制约性。而人类则需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将顺应与改造有机结合起来,使自然以人化的面目转换到人类社会这一场域中来,实现天人在这个场域的再和谐。所以事实上,在儒家,自然归根到底是作为人类存在的条件而存在的,具有为人性。而儒家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差异则在于,它是从一种伦理的视域去认识这个问题的。儒家将自然的这种为人性理解为一种仁的品质,将自然与人的本源关系理解为亲子性的生生关系,从而使仁也成为人性的一种规定性。人类仿效自然之道即天道开展活动,就形成了人道。天道生生,人道亦生生;天道生人,人道生天。人道之生,就是所谓的参赞天地之化育,成性存存。由此,自然与人之间形成物质与能量交换的封闭循环,天人在更高层面实现了合一,获得了生生不息发展的内在动力。反过来,人类如果为了自身利益的满足而违背天道、践踏人道,就是斩断了生生链条,破坏了循环的封闭性,使天人相隔绝,物质与能量相互对抗、相互抵消、难以为继,则天灾人祸必然接踵而来。
再次,在第三个层面上,儒家生态思想强调对自然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并将其作为执政者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必须对自然资源进行有效管理。自然资源的管理是执政活动的重中之重。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对于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视犹为突出。在《易传》中就有古代圣王如何通过卦象利用和改造自然事物,教化民众从事生产生活的例证。同时《周易》非常关注“时”,强调人类活动必须在合“时”的情况下开展,这其中就包涵了对自然资源取之以时的思想。而如前所述,在《周礼》中更详细地记载了我国古代对于管理自然资源的职官设置及其职责的要求。后来程颢也指出北宋朝廷因为忽略了自然资源的管理而导致生态恶化。自然生态的状况关乎人类个体与社会发展的质量。因此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不仅有各种政策保障,而且从礼法上也对民众和政府的资源使用予以规范,形成了“以时禁发”等重要的生态治理观念。第二,仁政的基础就是使百姓能够占有和享用维持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在中国古代,土地资源及其上的产物是维持个人和家庭生活所必需的条件。儒家认为,只有那些能够使百姓拥有这些条件,安居乐业的人主才有可能得民心而王天下。也就是说,占有和享用维持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民生问题、政治问题,社会管理者应当以保障并实现这一民生基本权利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孟子甚至将此作为衡量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标准,人主王或不王,国家亡或不亡,首要就是看执政者能否解决好百姓的自然资源分配问题,因为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解决得不好,使百姓流离失所,缺衣少食,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足以供养妻子,那么就会带来社会矛盾,威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总之,在儒家生态思想中,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具有“合—分—合”的过程性。第一个“合”是指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分”是指二者在表象上是有区别、有矛盾的。这种区别不仅是存在形态上的,而且是个性功能上的。自然大美无为,却决定了人类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规定了人类活动的可能空间,提供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人类则自觉有为,通过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不断突破局限,确证自身的优越性,并将自然纳入到人类世界,赋予其人文意义。二者之间的矛盾则表现为人类活动对自然规律的背离,这同时意味着背离人自身的天性、明德和良知,其结果是导致自然、人类两个世界产生危机。第二个“合”是指二者在人为的基础上实现再统一。现实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具有动态生成性,是自然规律与人类意志的结合体。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不断接近自然的本质,也就会同时接近人类自身的本质,反过来,人类对自身本质的不断探索也会带来对自然规律更全面深入的理解。当此时,人类活动就趋向合理化发展,而这种合理化发展必然是与自然规律相一致的。这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再统一。由此,自然与人类进入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完)
注释:
① 如果从广义而言,可以将生物之间“主动”的信息交流均称为“语言”,甚至将人机之间的信息交流也称之为“语言”。比如我们已知的计算机语言。但是在此我们仅仅只特指人类语言。
② 这与《易传》中“天佑之”之说具有相同的意思。
③ 这同样与《周易》的三才观念是一致的。
④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董仲舒这里可以说与孔子的正名思想保持了一致,并且进一步将“名”之正的根据归于天。
⑤ 《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1页。
⑥ “自性”在此是指源于自然、天道充盈的完整人性。
⑦ 《宋元学案》记载:“明道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草之与鱼,人所共见,唯明道见草则知生意,见鱼则自得意,此岂流俗人所共见。”[明]黄宗羲撰,[清]全祖望补:《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78页。
⑧ 通常来说,目的性仅仅用来说明人类意识的倾向性,所以自然应当是无目的性的。但是在这里采取一种拟人的方式说明在自然创生万物的背后,还有一种类似目的性的“意识倾向”。正如人类的意识倾向是有力量的,自然的“意识倾向”也是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推动着创生之天理的流行。
⑨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8,《四书集注》,中国书社1994年版,第271页。
⑩ [宋]黎靖德:《朱子语录》第2册卷17,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7页。
⑪⑭ 《杂著·仁说》,《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卷第67,《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9、3280页。
⑫ 参见《朱子语类》相关论述。
⑬《大学二·经下》,《朱子语类》卷15,《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
⑮ 蒙培元:《朱熹哲学生态观(上)》,《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⑯《答季明德》,《王阳明全集(上)》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页。
⑰ 同样,从自身立场或超越立场,人也在人与人之间划出分界或者认识到人与人的同质性。
⑱ 《续编一·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下)》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页。
⑲⑳ 《语录三·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下)》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106页。
㉑ 《续编一·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下)》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页。
㉒ 《张子正蒙注卷九》,《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65页。
㉓ 参见邓红蕾:《王夫之“纟因缊—太和”和谐观及其现代启示》,《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
㉔ 参见张云江:《论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
㉕ 《周易大象解·乾》,《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98页。
㉖ 《张子正蒙注卷八》,《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17页。
㉗《读四书大全说卷二·中庸》,《船山全书》第6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75页。
㉘《思问录内篇》,《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23页。
㉙ 参见张云江:《论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
㉚ 《尚书引义卷四》,《船山全书》第2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41页。
㉛ 《周易外传卷五》,《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007页。
㉜ 参见《读四书大全说卷一·大学》,《船山全书》第6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45—446页。
㉝ 宋儒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对人的欲望的全面否定,而是否定那种超出自然而然的合理性的过分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