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再出发
2018-03-30许倬云
许倬云
讨论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个使命的框架不应局限于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而应涉及长久的发展。因而,我想讨论中国今天和未来文化发展应有的方向,这个话题涵盖的时间跨度就不只是十年而已了,而应是一个超越世代的重大重建工作。
作为居住在美国的华人,我既已将他乡做故乡,国人或认为我已没有资格、也没有立场讨论中国事务。可是,作为一名远离家乡的游子,虽然在别处已成家立业,但午夜梦回,仍是故国山水、亲友故旧。游子之于旧日家园的兴衰祸福,常有切肤之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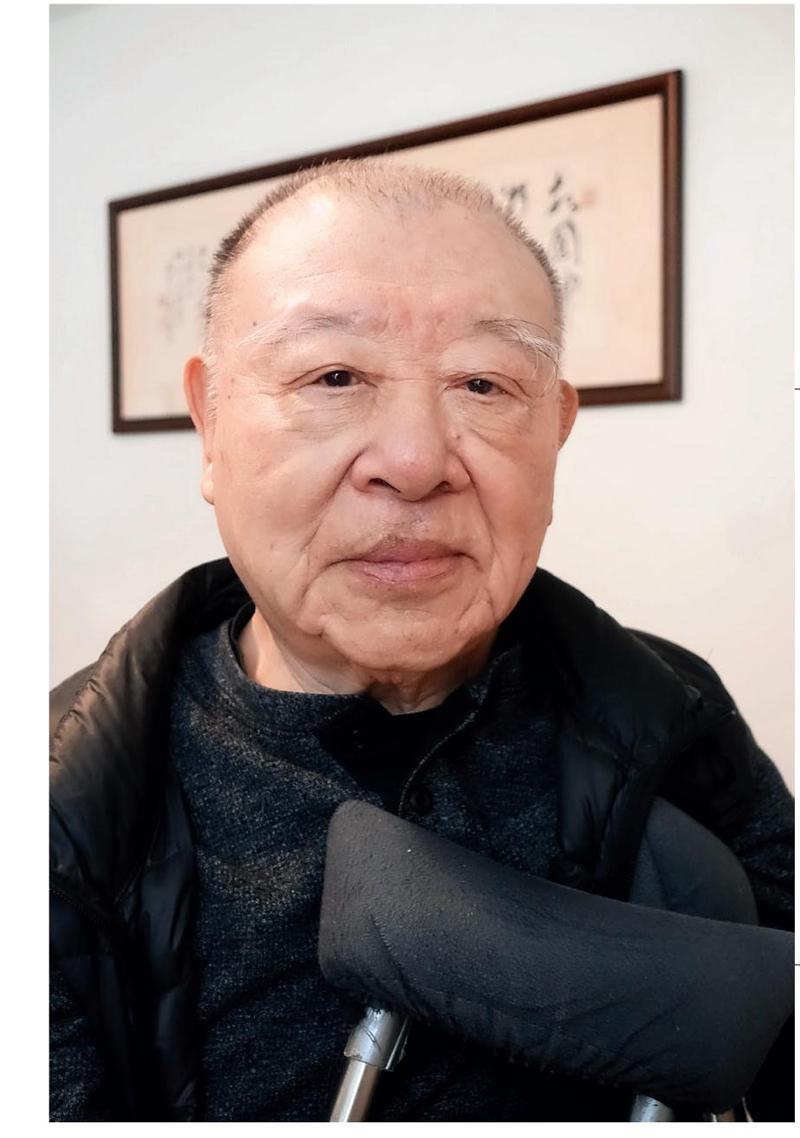
我的专业是历史,兼跨人文和社会两个学科的范围。我所关心的事物,也因此既有每个“人”内心的安身立命,也有“人”与群体的关系。在我心目中,复杂群体例如国家,相当于躯干;族群归属,相当于肌肤;经济流通,相当于血液;社会脉络,相当于神经;而文化,对群体而言,则相当于人的思想和精神。
这几个方面互相依托,不能分离,而人之精神所在与行为准则,以及思考方式,都是在文化范畴之内——这也是我挑选文化发展方向作为谈论未来十年这个话题的原因。
今日的中国,硬件建设发展之迅速众所周知;而且这一领域的问题,我也没有置喙的资格。今天重建中国的事业,亟需补足的部分却应在文化建设,亦即如何充实硬件躯壳当中的灵魂——前述中的思想和精神。
中国文化的发展,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经过数百年诸家融合,在西汉已组成了中国文化的体系,具有自己的特色。董仲舒规划的“天人感应”, 和《易经》所表现的“变化的原则是不变”,结合为一。这个体系,乃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其中有各种元素互动的趋衡状态,也有二元互动的辩证关系。这个网络有很多层次,最外层是宇宙,最内层是个人以及身体内部各器官之间的关系。网络之间经常变化,不会固定,也不应固定。如此动态的网络结构,在古代以至于中世代是中国特有的宇宙论。最近,拙著《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之问世,就是论述仍淀集于中国人生活中的文化与行为模式,也许可与此处所论互相参考。
在古代印度多神信仰中人神之间的混杂,以及在印度发展的佛教,对于变化的认识倾向于接受宿命,悲观而消极。而在欧洲发展成主流的独神信仰中,神是一切的主宰,人并不能参与独一真神之下的大系统,而只能服从。由于独一真神主宰一切的特点,固定的秩序或变化的趋衡都由神的意志决定,人是被动的。古代中亚近东的波斯信仰系统,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二元之间永远进行着“正、反、合”的辩证变化,其第三个时期乃是斗争之后的解脱。
以当时这三大系统与中国对比,中国的系统是以人为主体的、多层次而多元的大网络,一层一层都是从个人向外辐射。在这个结构下,“人”具有非常尊贵的地位,也正因为每个人都处于轴心位置,“个人”负担了无穷的责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也对群体因此而发生的变化负责任。人为贵,但是人不能妄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固然是很重要的社会网络,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息息相关。
如此文化网络应是开放的,可不断接受外来的刺激,加以修正、容纳以至于消化。外来因素只是在多元之中增加更多的选择而已。“海纳百川”,由各方河川带来的不同土壤和养分,大海不会深闭固拒。对内而言,吸收了外来因素之后,这一庞大的多元互动系统内涵更丰富,变动的选择也更有弹性。因此,中国特殊的文化体系,可以不断因为外来刺激而自我调整。
汉代以后、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是中国吸纳许多外来因素予以综合的阶段。外来的佛教、祆教、基督教等都进入中国,分别被中国所吸收。在印度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佛教,在中国却是开花结果,直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佛教信眾群还是中国人。北方草原的胡人甲士曾经占领大片中国土地。北方农村中的汉人则以坞堡自卫,保留中国的文化;南方的汉族也带着中原文化,与中国南方的土著融合。佛教的内修和波斯系统的救赎观念,都被中国文化系统接纳,成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隋唐帝国的扩张本身就是一个胡汉融合的过程,发展为多姿多彩的盛唐。中国文化随之辐射于东亚,也使这个文化体系的特色,传布于亚太地区。
宋代的中国,过去隋唐帝国的大片领土都已不属汉人政权管辖,宋代的国家组织有了新的设计:建立在胡人后裔(亦即五代的沙陀军团)武力基础上的皇权,和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儒生官僚彼此合作。官僚体系屈服于皇权之下,而掌握文化发言权的儒生们则致力于重建一个文化秩序。
宋代的道学与理学,实际上将前述具有强大弹性的民间系统重组为纲常伦理结构:在这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内,分为尊卑两级:君臣、父子、男女、阳和阴、上和下等等。每一种伦理之内都有确定的相对关系。于是,这一社会关系结构网,竟将古代中国具有弹性的网络转变为固化的结构。一个固化的网络犹如钻石,坚固却难以调节。因此,宋代的政治永远是在僵固的结构中纠纷不断。
倒是在经济部分,宋代的工艺水平有很大的进展。由于外贸的发达,生产能力颇有因应。在宋代,民间力量也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具有相当的自主性。中国固有的多元弹性系统却存在于民间,始终保持活力,以适应宋以后蒙古的征服,和明代继承胡风而建立的专制皇权。
明代的心学则将坚固的理学结构彻底予以修正。个人的自主权和自尊心,在心学理论中重新具有重要位置。这一转变对于中国的传统儒家网络,本可注入新的力量,足以抗拒专制的皇权;再加上明代晚期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也将“宗教革命”前西方的自然科学带入中国。这两个条件如果配合得当,也许中国的整个文化面貌会出现重大变化。可惜,明代的专制皇权,承袭了蒙古时代的暴力传统,不断地摧残儒生士大夫的努力。
满清入主中原,更加剧了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强化了对中国文化的压制。于是,宋代以来皇权和科举出身的官僚之间彼此合作,掌握了中国的命脉,也剥夺了中国人调整自己文化的机会。这一僵化的老大帝国,对于外来刺激懵然不知,深闭固拒,迄于 1840年大败,遂屈服于西方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此后百年之内,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终于二度激发了革命。
不论是五四群贤领导的文化革命,或是相应于两次政治大革命引起的改变,都犯了匆忙草率的毛病:诟病中国文化传统,颂扬西潮带来的现代文明,可是在中国学术圈内却罕见对中国过去持平的检讨;对于西方文明,无论是政治、哲学、经济等方面,也缺少认真的研究和讨论。于是,百年来,中国的命运动荡于对西方的或迎或拒。对于中国过去具有弹性的文化系统,却一次又一次地毁弃。
过去近七十年来,中国大陆有一半时期笼罩在“破四旧”的口号之下,直到今天才有重新恢复中国传统的提议。在台湾,于威权政治体系下,“传统”曾经是政权的护身符;最近三十年来,又因为外来与本土的冲突,“中国文化”四字居然成为禁忌。时至今日,中国文化体系又有复兴的契机,我们必须认真寻找自己文化的安身立命之基础,而不能仅仅邯郸学步,一味模仿西方模式。
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在欧洲和北美,由于科技的長足进步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劲,三百年来占尽世界各地的资源,竟成全球主流。可是,经过了几次重大战争以后,西方文化本身因应着国家组织和社会形势的改变,原有的文化系统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基督教的影响力日趋式微;随着工艺与科技发达,工具性的理性改变了文化价值的选择。生产力强大导致了生活的高度物质化,也削减了人间精神的发展余地。人权观念的自由和平等,在争夺权利的场合中逐渐转变为保卫自己利益的个人主义,自制的纪律也沦为放任和懒散。一次又一次产业结构的改变,给教育的内容和居住的形态引来新的形式。例如,大部分人口都集中于都市,都市的居民不断变动,不遑宁居,社群离散,人情淡薄,遂使“寂寞的人群”只有孤独。又如,民主政治是西方现代文化的骄傲,但在个人主义代替了公民精神后,民主制度的实践也就打了极大的折扣。
最近两三年,欧洲不少国家的政局都有向右转的趋向,美国的特朗普政权也远远背离了民主的传统精神。文化领域的活动一天天地远离心灵的滋润,而趋于庸俗的欲望满足。剩下的一些不甘于粗俗和低劣的文化产品则转而走向消极和悲观。
以上这些趋向,到了今天已积重难返,很难在枝节上加以修正。尤其在可见的未来十年,以走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发展方向,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精神,在精神物化海啸的巨浪下,将不再有发展的余地。原本在人类历史纪录中具有傲人成就的西方现代文明,可谓已到日薄西山的黄昏。西方模式有值得参考及学习之处,却也应当作前车之鉴,让我们避免覆辙。
从当下展望未来十年,尤其是从更长远的历史跨度考虑,我呼吁中国的俊彦之士,在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居住的中国,并正在国人望治心切的今天,多花费精力,也多得到一些空间,努力进行推陈出新,在中国传统的多元而又辩证性变化的文化基础上,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东”和“西”的新世界文化。这一文化眼光所注视者,也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天下;不再是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个地区或是一些人,而是普世众民。
建构如此文化系统,不应当以中国的儒冠、儒服,或者读经、祭孔等外表的东西当作提倡的方式。知识界应当严肃地面对这一重大任务,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让每个人认识自己的尊严,同时也提醒每个人的责任感;目标应落实在儒家理想,“修己而后济众”“安百姓”;这一“济”与“安”的对象,却是从自己身边开始,一直推广到这个世界的人类。
人类可以从自然取得资源,以利用厚生;但也应有所约制,不可过度。要完成如此任务,不应仅仅寄望于领导者,而应是全民的投入。我们也盼望整个社会开放讨论空间,为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共同努力——对这个严肃的议题不应设置禁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