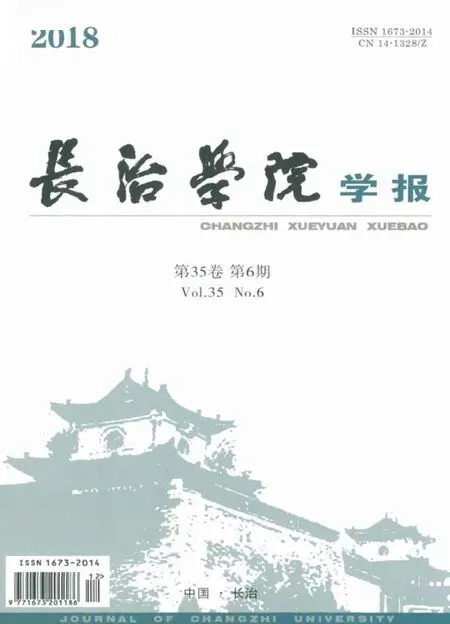土耳其军事政变的成因新探
2018-03-30史永强
史永强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土耳其已先后发生过四次成功的军事政变。①昝涛在《浅析土耳其的民主危机与军事政变,1960-2008》一文中认为土耳其历史上成功的军事政变有三次;无独有偶,哈全安在其论著中也多次用“军方的温柔介入”定义1997年军人干政,以区别于前三次军事政变。分别是1960年的“五·二七”革命[1]4131971年的“备忘录政变”[2]1980年的“九·一二行动”[3]21以及1997年的“软政变”(或称之为“后现代政变”或“军方的温柔介入”)[4]240。除以上四次成功的军事政变外,土耳其历史上亦不乏蓄意的、失败的军事政变。[5];[6]293最近发生的“七·一五”未遂政变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国内学界对于土耳其军政关系及军事政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②王铁铮的《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哈全安的《土耳其共和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与《土耳其通史》,黄维民的《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刘云的《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杨兆钧的《土耳其现代史》,李秉忠的《军人干政与土耳其民主政治》,姜明新的《军人政治传统与土耳其现代社会变革》,范若兰的《试论土耳其军队干预政治的原因》,周术情的《试论军人政治与民主化进程——以土耳其1980年政变为例》,昝涛的《浅析土耳其的民主危机与军事政变,1960-2008》,张立梁的《1960年以来的土耳其军人干政与政治现代化》,孙亮的《土耳其军人政治研究(1980-2013)》等。不过,从政治体制、军队属性等方面探讨军事政变的原因仍是主流方向,相反,对经济困境、社会问题、民族矛盾与外部环境等方面与军事政变的关系则缺乏关注。因此,拙文试图从这些新的视角对土耳其军事政变的原因进行进一步探讨。
一、历史与政治军事根源
历史传统是土耳其军事政变频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有历史成因,土耳其素有军人民族之称,军队成为土耳其的国中之国。”[7]土耳其军人干政的历史不仅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甚至能追溯到哈里发国家时代,而这种历史传统,正是阿拉伯-伊斯兰因素与突厥因素两种不同传统的结合。共和国建立后,这一传统在土耳其得到了保留。可以说,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以及传统的一脉相承导致了“土耳其现代军人干政现象的复活”。[8]
归根结底,军人干政是土耳其政治结构性问题的必然结果。自共和国成立至1945年是土耳其的一党制时代,二战以后,随着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政府开始允许反对党的出现。[9]随后,民主党成立并在1950年的议会大选中大获全胜,土耳其进入了所谓的多党制民主时期。然而,土耳其的政治体制依然存在诸多弊端,哈全安认为,民主党的独裁倾向无疑是导致军方发动政变的重要原因。[4]1991961年宪法包含了一个“分权制衡、防止专政”的多元化体制,开启了土耳其的新时代。[1]416但这一原则存在漏洞,而且,宽松的政治环境又滋生出一些新的问题。第一,权力破碎化,政党林立,政党之间分化组合紊乱,政局更迭频繁;第二,军方的政治参与度过高,影响文官政府的正常运作,军人-文官政府未能同心协力,而是相互掣肘,这主要表现为“国家精英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10]第三,以军方所代表的传统精英主义与新进崛起的以农民为砥柱、以宗教为旗帜的民粹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
在土耳其,“军方一直被看作是受尊敬的国家机构,并被看作是凯末尔世俗共和国加之精神的化身。”[11]这赋予了军方维护共和国世俗、民主的天然使命。同时,军队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有维护其利益的本能驱动。二者相结合,为军方干预政治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凯末尔奠定的土耳其共和国实行军政分离的原则,军人只有脱离军界才能跻身政界,因此,军人最初是处于政治之外的。[12]这种隔离可以避免军人卷入党派争端,但也存在问题。一方面,军队作为国家的守护者要对土耳其的社会稳定、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负责,但由于缺乏合法的政治解决途径,因此当国家遭遇危机时,军方就只能采取政变的方式。另一方面,军政界的隔离事实上引起权力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军人被排除于政治运作机制之外,这就为其发动政变并进行政治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动力。而既经政变后的土耳其,军方虽还政于文官,但权力运作机制已然改变,待危机再现或军方地位受到挑战时,军方就会发动另一次政变。据此,土耳其基本形成了“文官执政、军人监国”的模式。当然,军队在共和国的地位,以及军人-文官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本身也对军队参与政治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二、经济困境、社会问题、民族问题与军事政变
经济困境、社会问题与民族矛盾虽不能决定土耳其军事政变的必然发生,但当政治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军人-文官政府之间矛盾不可调和时,这些问题就会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直接原因。
经济困境与政变的关系主要通过两方面表现出来,其一是发展道路的困境,其二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其发展道路在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大幅摇摆,缺乏稳定的经济政策与健全的经济体制,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也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口实。凯末尔六原则中的国家主义就是经济理论,他从理论上论证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性。[13]112在国家主义经济原则的指导下,土耳其实行五年计划,使得经济在三、四十年代得到快速增长。[6]224-232到民主党执政时期,土耳其放弃国家主义的原则,改行自由经济,盲目的引进与发展造成整个国民经济失控与经济形势的恶化。1963年开始,土耳其经济再次转向,政府连续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70年代后期再次遭遇发展瓶颈。[14]80年代以后,厄扎尔政府又采用自由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今天的土耳其已成为中东地区堪称样板的经济大国,但在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仍需进一步坚定和巩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于诱发军事政变同样发挥了重大作用,50年代中期以后土耳其经济形势的逐渐恶化就是1960年军事政变的一个直接原因。[15]同样,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70年代后期,土耳其再次面临经济困境,到1980年,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直接导致了1980年军事政变的发生。
社会问题与政变的关系也通过两方面表现出来,其一是伊斯兰复兴与世俗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其二是暴力恐怖活动的盛行。世俗主义作为凯末尔六原则之一,是土耳其共和国精神的内核。[16]在社会与宗教层面,凯末尔进行了世俗化改革并一再申明“土耳其是一个世俗国家”,[13]103但土耳其98%的穆斯林人口以及几百年的伊斯兰文化积淀为伊斯兰复兴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17]在政教关系层面,凯末尔立致力于“把伊斯兰信仰从数世纪以来惯于充任政治工具的地位中拯救出来,使其得到纯洁与提高”,[18]政治伊斯兰却长期存在,正义党、秩序党、繁荣党虽已先后淡出历史舞台,但自2002年以来,“以宗教精神定位的”正发党已维持了连续16年单独组阁、一党执政的局面,对凯末尔的世俗主义提出了挑战。事实上,宗教并非与现代社会相悖,世俗化也并非与现代民主对等,只是土耳其的社会演进与军方所秉持的凯末尔主义分道扬镳,造成了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模式之间的悖论。当然,凯末尔的道路并非土耳其现代化的唯一、必然、正确的选择。[8]但就目前来看,以守护凯末尔主义为己任的土耳其军方将不会轻易放弃与伊斯兰复兴势力的斗争。暴力恐怖活动的盛行是土耳其的又一社会问题,也是军人干政的重要诱因。六、七十年代,左翼力量、右翼组织和狭隘民族主义者是土耳其暴力恐怖活动的主要参与者。[15]到70年代末,随着土耳其真主党、伊斯兰运动组织等极端组织的死灰复燃,暴力恐怖活动便与伊斯兰教密切相关。[6]217-219一方面,暴恐活动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造成威胁,1980年中期,每天有20-30人被夺去生命;[19]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对政治的渗透以及政治暗杀的盛行使得土耳其民主政治更加脆弱。
民族矛盾与政变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库尔德问题、土耳其犹太人问题、塞浦路斯问题对政变的影响。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库尔德问题一直是困扰土耳其的难题之一。库尔德人为实现其政治诉求,自70年代后期开始了暴力活动,并力图通过武装斗争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成为1980年军事政变的重要起因,因此有学者认为,此次政变源于“对库尔德问题的偏见”。[20]塞浦路斯问题的长期存在为军方的重要性添了一注筹码,而两国的特殊关系又使得塞浦路斯的民族矛盾成为影响土耳其政局非常重要的因素。此外,土耳其的犹太人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是研究土耳其军事政变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21]
三、周边环境、大国政治与军事政变
除历史与政治军事根源、经济困境、社会问题与民族矛盾等国内因素外,地区与国际环境对土耳其军人干政的频发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周边阿拉伯邻国军人统治与军事政变的外溢效应,其二是大国政治的影响。
亨廷顿认为在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军队干预政治是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并且“成为政治现代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2]这一论断在中东国家可以得到很好的验证,二战后中东诸国,如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均经历了军人政治的发展阶段,有的国家军事政变频发。1949年,叙利亚军人集团连续发生了三次政变,成为战后中东军事政变潮的敲门砖。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二三”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统治,进入纳赛尔军人政权时期。1958年,卡塞姆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月革命”,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此后直到70年代萨达姆掌握政权,伊拉克政局动荡,政变频发。叙利亚、伊拉克都是土耳其的邻国,两国频繁的军事政变无疑会对土耳其的政局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巴勒斯坦法塔赫对1971年土耳其军事政变的发生起了很大作用。从1969年开始,随着法塔赫志愿者的回流,土耳其的社会和政治开始受其影响,受过游击队训练和法塔赫教育的青年学生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的校园鼓吹革命;另外,法塔赫还卷入了直接诱发1971年政变的银行抢劫案。[23]
土耳其的政治、安全与经济诉求使其经常受制于大国的态度,这对土耳其的军事政变也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例如,与美交恶就是1971年政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战后,美国成为土耳其的亲密盟友,但60年代,两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出现分歧,关系开始交恶,因此,中情局怂恿土耳其军方推翻意欲亲苏的德雷米尔政府,这对1971年政变的发生产生了潜在影响,因为对军方来说,美土关系恶化是不可想象的。[3]17-18土耳其争取入欧也是影响其政局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入欧进程的漫长使得这种影响深刻而持久。入欧进程对土耳其军方势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因为军人干政有悖于西方民主的形式。因此,土耳其自1987正式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之后,军方变得相对温和。但与此同时,欧盟对伊斯兰因素的芥蒂也使得军方更加坚定地维护世俗主义,1997年的“后现代政变”以及2007年军方对参选的正发党的警告都反映了其反伊斯兰的决心。
四、结语
自共和国建立以来,土耳其军事政变频发,其成因是纷繁复杂的。首先,从哈里发国家到奥斯曼帝国再到共和国早期,军事政变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这是其历史根源;同时,土耳其的政治体制存在结构性问题,无论是一党制统治时代还是多党制民主时期,土耳其的现代民主都不够成熟,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而军队的特殊身份与使命,以及自身的利益考量,为其发动政变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其次,土耳其发展道路的困境与周期性经济危机,世俗化与伊斯兰复兴之间的较量,暴力恐怖活动的盛行,库尔德问题等民族矛盾的存在等构成了军事政变的经济动因、社会动因与民族动因。再次,战后中东国家的政变潮及其外溢效应,大国政治对土耳其神经的牵动构成了土耳其军事政变的外部动因。
军事政变对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观上来说,军方或出于维护国家的民主、稳定,或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的目的而干预政治,但客观地讲,军事政变不仅没有造成军事独裁的政治现象,也没有中断土耳其政治现代化进程,反而为土耳其民主政治保驾护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军事政变或许有悖于现代民主的形式,但其作为土耳其特殊的成长方式,是历史的选择,也将由历史作出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