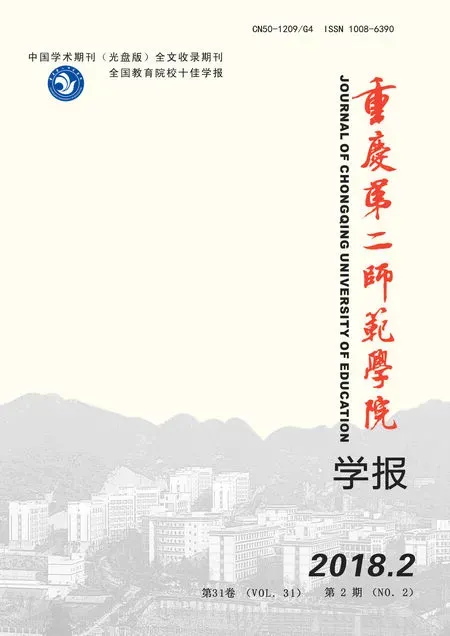论《金瓶梅》中的葡萄架意象
2018-03-29张国培
张国培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 河南 平顶山 467000)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而言,葡萄架意象并不罕见。葡萄架、葡萄酒都是由葡萄这种植物派生而出的文学意象。相对而言,抒情文学青睐于葡萄酒,而葡萄架因其自身所具有的空间性可以为人物行动提供场所,因此,多出现于叙事文学之中。如《水浒传》第二十八回,张青、孙二娘与武松不打不相识,杯盘整顿端正后,“张青教摆在后面葡萄架下”[1]366;《红楼梦》第六十七回老祝妈在葡萄架下与袭人叙谈[2]536。在这类描写中,葡萄架的意义就在于空间背景,但这一空间背景并无深意可言。在古典文化的积淀过程中,葡萄架的确有了特别的内涵,即妒妇。此意起于元代,《全元散曲》收一小令《朝天子·从嫁媵婢》①:“鬓鸦。脸霞。屈杀了将陪嫁。规模全是大人家。不在红娘下。巧笑迎人。文谈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他。倒了葡萄架。”[3]157自此,以葡萄架代指妒妇一直延续至清。这一含义也常出现于叙事文学之中,如明代小说《醋葫芦》多次用葡萄架形容妒妇都氏;再如《长生殿》第十九出“絮阁”亦以葡萄架比喻杨玉环:“哎,万岁爷,万岁爷,笑黄金屋恁样藏娇,怕葡萄架霎时推倒。”[4]68除此之外,葡萄架还有一内涵,它代表着性欲和淫行,而赋予葡萄架此种内涵的正是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葡萄架这一意象在《金瓶梅》中出现得并不多,但是经过《金瓶梅》的渲染,它与性爱之间的关系已经挥之不去,并被之后的小说所沿用,本文将对此作出阐释。从有关葡萄架的文字来看,《金瓶梅》的诸多版本并没有显著出入,本文所用《金瓶梅》文本资料皆出自1991年齐鲁书社出版的《金瓶梅》评点本,此本属于绣像本系统。
一、《金瓶梅》中的葡萄架
《金瓶梅》中的葡萄架意象分别出现在第二十七回、二十八回和五十二回中,并与性描写紧密相连,其中又以第二十七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为主体。“潘金莲醉闹葡萄架”是《金瓶梅》性描写中的著名段落,葡萄架被描写得最为详尽,其意义于第二部分详述。在第二十七回的一番淫行后,潘金莲的大红睡鞋不见了,因此,第二十八回再次提到葡萄架。秋菊到葡萄架下寻鞋,而小铁棍儿告知陈敬济昨日于花架之下见到了葡萄架下的“玩耍”,并捡到了一只鞋子,由此引出潘金莲与陈敬济的偷情,第二十八回的葡萄架可视为第二十七回的余绪。余绪并非毫无意义,在第二十七回西门庆与潘金莲都非常担心葡萄架下的行为被人发现,而第二十八回则告知读者,的确有另外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他们,小铁棍儿固然不解人事,然而他的模糊描述足以让陈敬济清楚明白,并充满想象。因此,这一余绪中的葡萄架不但让读者又在回忆中重温了二十七回的故事,而且在为潘金莲与陈敬济的偷情埋下伏笔的同时,预示了二人更为伦理所不容的情欲关系,因为葡萄架下潘金莲的淫行毕竟是二人所共知的私密话题,而这一话题已经为陈敬济创造了对潘金莲的性期待。
第五十二回,在一次小型的宴席之上,西门庆和李桂姐相继离席,久久不归,应伯爵预料二人必行苟且之事,便存心起身去寻,终于发现了二人在藏春坞中的淫行。文中写道:“不想应伯爵到各亭儿上寻了一遭,寻不着。打滴翠岩小洞儿里穿过去,到了木香棚,抹过葡萄架,到松竹深处藏春坞边,隐隐听见有人笑声,又不知在何处。”[5]781追随着应伯爵的脚步,经过一段曲折的路径,读者被带到了一处不堪入目的淫乱场面。于此路径中提到葡萄架并非无意,而是特意,提到葡萄架必将令人联想到之前“潘金莲醉闹葡萄架”的情景。因而,此处的葡萄架一方面是对即将亮相的藏春坞情景的一个短暂铺垫,另一方面也是对它的正面衬托。这一次藏春坞的偷情,即使西门庆也担心为人所知,其原因在于李桂姐已拜西门庆为干爹,若从伦理角度而言,藏春坞比葡萄架更为不堪,故此藏春坞比葡萄架更为隐秘,也只有葡萄架可以与之比肩并加以衬托。
很明显,《金瓶梅》中的葡萄架意象就是围绕着“潘金莲醉闹葡萄架”而展开的,此处的性描写字数之多、文笔之直露、场景之秽乱在《金瓶梅》所有的性描写中堪称第一。作者对于这次性行为表现出的“津津乐道”还在于展开性描写之前,作者以韵语的形式对葡萄架大加赞美,为西门庆与潘金莲乃至庞春梅的性活动做了充分的铺垫,让读者感觉到这次性行为的与众不同,其独特之处在于这是唯一一次西门庆的室外性活动。这次性活动的地点葡萄架非常突然地出现在读者眼前,它坐落在西门庆的新花园中,是一处十分惊艳的庭院景色。此园落成之时,吴月娘等游览花园,将园中亭台楼阁、水池花架描写殆尽,并未提及葡萄架,由此至第二十七回之前皆未提及只字。第二十七回方由潘金莲说出:“咱们到葡萄架下投壶耍子儿去。”至此,葡萄架不但与性联系到一起,而且与潘金莲也扯上了关系,在葡萄架下的是潘金莲而不是别人,而潘金莲与西门庆选择在葡萄架下而不是园中其他地方“醉闹”,这其中是否有深意是值得探讨的。
对“潘金莲醉闹葡萄架”的阐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陈诏先生在其《金瓶梅小考》中提出:葡萄架是代指妒妇,作者将“潘金莲的丑剧”安排在葡萄架下演出有特别用意,即“暗示她奇妒无比也”[6]288。二是孙秋克先生认为葡萄架带有佛家神异色彩,在庭院中种植葡萄、搭建葡萄架是为了得到神灵护持,“在‘私语翡翠轩’后兜了一圈儿,《词话》接着把西门庆和潘金莲安排在葡萄架下‘醉闹’,深刻地讽刺了二人对因果报应虽然持有不同心态,但在行事上都同样不惮亵渎神灵”[7]。
以上两种解读都显牵强。首先,潘金莲强烈的嫉妒心理无须葡萄架暗示。古典文学中常有以葡萄架代指妒妇者,如李渔《无声戏》第十回卷首词中云“齑菜瓶翻莫救,葡萄架倒难支”,引言所举《长生殿》杨玉环之例,在使用葡萄架的妒妇含义时,葡萄架往往是一种代指,并不是暗示,而《金瓶梅》并未以葡萄架代指过任何女性。另外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潘金莲的嫉妒在第二十七回之前就已有充分展示。如第十八回,潘金莲在西门庆跟前挑拨其与吴月娘的关系,第二十一回,吴月娘与西门庆和好,潘金莲私下里出语讽刺,这其中无疑是嫉妒之心在作祟,且潘金莲之嫉妒于小说中随处可见,如此何须再以葡萄架“暗示”?第二,潘金莲固然嫉妒,但距离“奇妒无比”尚有距离。潘金莲的嫉妒与用葡萄架来形容的妒妇们是不同的,致使葡萄架倒的妒妇的确是“奇妒无比”,如《醋葫芦》之都氏,无所不妒,且这一妒妇群体在身份上皆为正室,因此,她们在心理上具有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丈夫爱慕其他女子的自信,她们认为这是合理的,但潘金莲不同。潘金莲还未进西门庆家的大门就已经有过被冷落的经历,她猜想西门庆贪恋着其他女人,内心嫉妒,但却只能对着迎儿发泄;进入西门家之后,她的嫉妒心时常挑起与吴月娘、李瓶儿、孙雪娥乃至诸多下人的不快。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面:比如春梅,她对春梅一直另眼相看,默许西门庆与春梅的关系,在与陈敬济偷情时也要拉上春梅;比如未嫁入西门家时的李瓶儿,她第一个发现西门庆与李瓶儿偷情,但是保持沉默,几乎在每一次西门庆与李瓶儿偷情后,潘金莲都得到了好处;再比如宋惠莲,潘金莲即使在脚的问题上受到了宋惠莲的奚落和挑衅,即宋惠莲将潘金莲的鞋套在自己的鞋外面穿,但她依然为西门庆保守与宋惠莲偷情的秘密,直到这已经不是秘密为止。这些情节都表明,嫉妒并非潘金莲性格的主旋律,既然如此,葡萄架对于潘金莲的个性就更不具备暗示意义了。
其次,这座葡萄架是突然出现在第二十七回的,如果于新花园中搭建葡萄架含有祈求神灵保护之意,那么在建造园林之初就应当有所暗示,或者于吴月娘等初游花园之时作一交代,以示其重要,但这些情节都没有出现在小说中。而葡萄架在古典文化中是否真的具有神的力量也是值得怀疑的,笔记中的确有关于明代时期葡萄架显灵保护家人的记载,见于《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作者记杭州城多火,并特别谈到辛酉之火时的一桩异事:
辛酉之火,烈焰满城,而吴山上一老翁家独存。翁平日诵经乐施,火起之夕,以老惫不能跬步,遣儿与妇令亟走,儿妇竟不忍相舍,同处烈焰中,举家昏睡,庭有葡萄架,亦不焚灼,明为神物护持也。其时杭人称积善而免祸者,必曰葡萄架云。[8]442
这个故事具有明显的佛教意味,因为老翁是虔诚的佛教徒,故得到葡萄架的护持,而葡萄架被看作佛法神异的代表或者象征。然而除此之外,于明清笔记中并未发现与此类似的记载。此一孤立的事件不足以说明于庭院种植葡萄架以求神灵保护是明代的风俗,而葡萄架是佛教的象征也并非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如此葡萄架突然出现在小说第二十七回就不奇怪了。既然如此,葡萄架下的性行为就更不能看作对神灵的亵渎,更非作者有意安排。
这两种解释的不妥之处在于偏离叙事重心,而理解《金瓶梅》中葡萄架意象的重点在于“性”。此处的葡萄架并没有借用前代已经积淀在此意象上的内涵,而是单纯地用了它作为植物的基本含义,它自身所带有的空间性使其成为这次室外性活动的天然背景和衬托。然而,恰恰是因为这次特殊的性描写,葡萄架反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二、潘金莲“醉闹”之“葡萄架”
上文已明确《金瓶梅》中的葡萄架意象是围绕着第二十七回展开的,而葡萄架的新内涵正是第二十七回中“潘金莲醉闹”一节所赋予的。书中写潘金莲与西门庆本在太湖石边饮酒玩乐,渐至亲嘴咂舌,于是潘金莲建议离开太湖石而到葡萄架下去,此时她已经想好将在葡萄架下与西门庆淫乱一番。葡萄架相较于他们所在的太湖石要隐蔽一些,从两次行程可以大致推断葡萄架在花园中的位置,一是潘金莲与西门庆走到葡萄架的行程:
两人并肩而行,须臾,转过碧池,抹过木香亭,从翡翠轩前穿过来,到葡萄架下观看,端的好一座葡萄架。[5]416
二是第五十二回应伯爵寻找西门庆的行程:
打滴翠岩小洞儿里穿过去,到了木香棚,抹过葡萄架,到松竹深处藏春坞边,隐隐听见有人笑声,又不知在何处。[5]781
这说明此座葡萄架在花园大卷棚后面,离假山很近,从园门或者角门进入后都不会一眼望见葡萄架。其间李瓶儿曾敲开过角门,回到自己小院,而她也并没有看到葡萄架下的情形,这足以说明葡萄架的位置比较隐秘。从整部小说来看,作者的空间概念并不是很强,因此,西门府的具体布局并不是十分明确,根据书中内容所可以得之也仅仅是葡萄架位置并不显眼而已。即使如此,潘金莲与西门庆仍然不能无所顾忌,二人皆曾强调要关闭花园门、角门,潘金莲吩咐秋菊:“放下铺盖,拽上花园门,往房里去,我叫你便来”。中途西门庆也问春梅:“角门子关上了不曾?”二人的顾忌有所不同,潘金莲关心园门,说明她担心被人看到,而西门庆关心角门,正如张竹坡所评:“防月娘也”。性行为的私密性和葡萄架的露天性形成了矛盾,然而也构成了刺激,最终强烈的欲望使得这二人在这一天然屏障之下肆意所为。
在性行为描写之前,作者从主观视角对这座葡萄架大加赞赏:“端的好一座葡萄架”。但见:
四面雕栏石甃,周围翠叶深稠。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弹坠流苏;喷鼻秋香,似万架绿云垂绣带。缒缒马乳,水晶丸里浥琼浆;滚滚绿珠,金屑架中含翠渥。乃西域移来之种,隐甘泉珍玩之芳。端的四时花木衬幽葩,明月清风无价买。[5]416
在叙事文学中以欣赏的态度对葡萄架做如此详尽的摹写非常罕见。在这里,葡萄架首先是作为一个行为活动的空间而存在的,但它又不是普通的空间,在这段韵语中作者所描写的葡萄架最大的特点在于浓郁,这是一架生命力非常旺盛的植物,它能够让人感觉到生命的冲动。这为接下来的性描写做了正面的衬托。接下来的性描写文字则洋溢出强烈的性欲气息,葡萄架的生命力正是对人物性欲的有力渲染。作者越是赞美它的浓密茂盛,越能增强画面的性欲色彩。
张竹坡在第二十七回回首评道:“至于瓶儿、金莲,固为同类,又分深浅,故翡翠轩尚有温柔浓艳之雅,而葡萄架则极妖淫污辱之怨。”[5]407翡翠轩与葡萄架分属室内与室外,李瓶儿与潘金莲又个性不同,两处描写自然形成对比,但其中是否寄寓了作者的某种态度很难确定。作者对这座葡萄架是何等的赞誉,对葡萄架下性爱活动的描写不遗余力,无论是葡萄架还是性活动都足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即使怀着讽喻的目的,也不过是劝百讽一的效果。
将性行为移至室外实际上不足为奇,小说中的这种描写很少有,但是在春宫图中却常见。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春宫画应兴盛于明代,后期尤其普及。高罗佩就曾说:“我本人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比明代更早的摹本,尽管有些画自称是仿自唐宋原画,但却具有明代色情艺术的所有特点。”[9]298《金瓶梅》第十三回写西门庆从李瓶儿那里拿来一本内府画出来的春宫图与潘金莲分享,二人视作珍宝,这说明二人也深受春宫图的影响。春宫图中室外之景常常作为背景出现,如树旁、花下、石边等。而作者让潘金莲与西门庆创造性地实践了一次室外春宫,这幅图景已经超越了春宫图,他以文字的形式让画面鲜活、生动,足可以补明代春宫图之不足。在这幅图景中葡萄架已经成了标志性的景物。
三、《金瓶梅》对“葡萄架”内涵之影响
自《金瓶梅》之后,葡萄架作为意象具有了新的内涵,它可以指代性爱、淫欲。葡萄架与性发生关系并不始于《金瓶梅》,葡萄架常常是男女幽期密会之所。如《国色天香》之“刘生觅莲记”:“生归,莲父醉寝,莲出立于葡萄架下。生望之,奇葩逸丽,景耀光起,比常愈美。”[10]71《淞隐漫录》卷七《秦倩娘》:“生视其容,美秀罕俦,丰韵独绝,明眸善睐,顾盼生姿。时生已设座于紫葡萄架下,邀女入座。”[11]312明清俗曲小调中亦有此类描写,且更为露骨,如《霓裳续谱·轻轻来到葡萄架》:
[隶津调]轻轻来到葡萄架,葡萄架下有一棵桂花。那棵桂花青枝绿叶开满杈,那葡萄一嘟噜一嘟噜头朝下。酸的溜儿的葡萄,香喷喷的桂花。左手掐葡萄,咳哟右手掐桂花。吃了葡萄,带上桂花,见情人说些风流话。你与我同解香罗帕。[12]下册312
只是这些情节不足以赋予葡萄架意象新的内涵,只有《金瓶梅》具有赋予葡萄架特别内涵的力量。在《金瓶梅》中葡萄架虽然同样是性爱活动的空间,但作者对此倾注的笔墨使得它与性爱活动成为一个整体,加之“醉闹葡萄架”笔墨淫靡、画面触动人心,成为《金瓶梅》乃至明清文学性描写中的登峰造极之作。因此,葡萄架被赋予了淫乱的色彩,并在后代小说中得以展现。
清代钱泳的《履园丛话》卷十七:
(某太守)慕《金瓶梅》葡萄架之名,以金丝作藤,穿碧玉、翡翠为叶,取紫晶、绿晶琢为葡萄,搭成一架。其下铺设宋锦为褥,褥上置大红呢绣花坐垫,旁列古铜尊彝,白玉鸳鸯洗,官、哥、定窑瓶碗,及图书玩好之属,与诸美人弹琴弈棋,赋诗饮酒,或并观唐六如、仇十洲所画春册,调笑百端,以此为乐。[13]3595
文中交代得很清楚,此太守受了《金瓶梅》极深的影响,但人为制作葡萄架的做法却未得《金瓶梅》之壸奥。这也是封建士大夫家庭与商人家庭的不同,不能视礼教如无物,此太守固然倾慕葡萄架下的恣意淫乐,但终不敢如法炮制。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第七回,金凤等人看半个胡桃壳里塑着的一出春宫,汤啸庵问金凤看得懂否,金凤道:“葡萄架啘,阿有啥勿懂”[14]53。晚清小说《海上尘天影》第二十四回,借着《金瓶梅》葡萄架的段子来打趣:“知三又笑道:‘霁月,我问你,你们园子里景致通通有了,就少了葡萄架’”[15]374。由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金瓶梅》传播之广,影响之大,葡萄架因此而闻名于知识分子乃至闺阁之中,即使一再禁毁,也无法抹去读者对此的记忆。
葡萄架所带来的影响在《金瓶梅》续书中也可以看到。首先,《隔帘花影》就抓住“葡萄架”这一细节,并有拨乱反正之意。第八回写到:“如今一个寡妇,领着五六岁孩子,怎么住着?又到了玳瑁轩、山洞、石山子前,见那太湖石牡丹台,花都枯干了,葡萄架久倒了,满地都是破瓦,长的蓬蒿乱草半尺深,那些隔扇、圆窗,俱被人拆去烧了。前后走了一遍,放声大哭。”[16]72上文已经交代,葡萄架并不是《金瓶梅》多次提及的景色,而是仅仅在特殊的性活动场面才会出现。《隔帘花影》写花园景色已不同往年,却强调“葡萄架久倒了”,这不仅仅是在写繁华不在的冷落感,更令人想到纵欲无度的西门庆终归命丧黄泉,就像这葡萄架一样失去了生命力。第十八回,作者另写一座葡萄架,吴月娘被邀请到高家居住,在这里她也见到了葡萄架,“东屋后一个独院子,三间正房、一个葡萄架,好不清雅”[16]171。这才是一座正常的葡萄架,它的特点不是茂盛,而是清雅。从这两处描写来看,作者无疑还是借着葡萄架所代表的纵欲之意表达了否定的态度,只有摆脱淫乱才能归于常态,不至于死亡。《金瓶梅》的三续《金屋梦》对“葡萄架”的处理也大致若此,在因果轮回之中,那葡萄架的淫根最终被彻底断去。两本续书都是借葡萄架来表达对淫欲的否定,然而葡萄架被《金瓶梅》所赋予的淫乱色彩却挥之不去。
葡萄架作为古典文学中的意象之一,具有两种内涵:一是指代妒妇,二是象征着性爱与淫欲。《金瓶梅》中仅有的葡萄架描写都与性欲联系到了一起,尤其是“潘金莲醉闹葡萄架”,这里的葡萄架意象没有因袭前代,反而创造了新的内涵。然而这两种内涵又略有不同,以葡萄架指代妒妇的使用范围更广,古代笑话集《笑林广记》就收了一则“葡萄架倒”,这证明葡萄架的这层含义已经扩展到民俗层面。但《金瓶梅》所赋予的新内涵更多是在小说中流传,也就是说这一内涵的接受并不普及,它的接受者往往是具有阅读能力且具有小说阅读经历的人,毕竟对这一内涵的接受是建立在对《金瓶梅》的接受之上的。
注释:
①《太平乐府》《词林摘艳》俱谓此曲为周德清作,《词品》《尧山堂外纪》属关汉卿,可见此小令作者尚待考定,与此小令相关的关汉卿轶事的真实性当然更需考证。本文姑且取其“葡萄架”之说,作者与真实性问题对此不构成影响,因此本文不加辨析。
参考文献:
[1]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长沙:岳麓书社,1987.
[3]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64.
[4]洪昇.长生殿[M].吴仪一,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5]兰陵笑笑生.金瓶梅[M].张道深,评.济南:齐鲁书社,1991.
[6]陈诏.金瓶梅小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7]孙秋克.《金瓶梅词话》二考[J].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42-44.
[8]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M].李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0]吴敬所.国色天香(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本)[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
[11]王韬.淞隐漫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2]冯梦龙,王廷绍,华广生.明清民歌时调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3]钱泳.履园丛话(清代笔记小说大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4]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5]梁溪司香旧尉.海上尘天影[M/OL].中华艳情文库.
[16]丁耀亢.金瓶梅续书三种·隔帘花影[M].济南:齐鲁书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