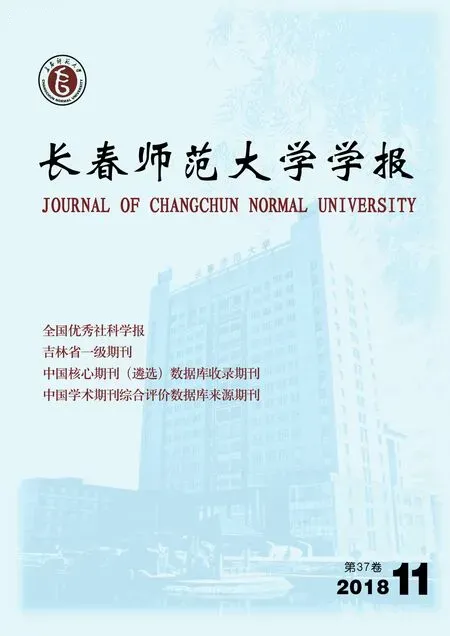论晚明文坛“性情”风潮与佛教之关联
2018-03-29柳旭
柳 旭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是古来士大夫秉承儒家文化的人生理想和价值体现,然而在明万历以后,却形成了“士夫无不谈禅”[1]119的局面。许多士大夫甚至背离了“以道自任”的入世传统,因不堪忍受污浊吏治而冲破名累,为官请辞,不屑仕进,又在佛禅和心学的双重助力下,愈发关注本然之心,以心统摄性情,随缘自适,任情而为,终在晚明文坛掀起了有活泼泼生命气息的性情风潮。
一、求真
禅宗五祖弘忍在向慧能传授衣钵前曾为其说法。提及《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2]36时,慧能言下大悟,对弘忍说:“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2]134弘忍知其已悟本性,又对他讲:“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2]134王阳明援佛入儒,引入禅宗心性论论断己说,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这样解读此心:“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如今死的人那一团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3]36又道:“夫吾之所谓真吾者,良知之谓也。”[3]250王阳明将“心”视为“真己”,将“真己”解读为“良知”,而其“良知”与禅家不假外求的本来面目等同,即内在本有的真诚恻怛之心。基于此,在文学思想上,唐顺之、徐渭倡导“本色”,罗汝芳主张“赤子之心”,李贽高呼“童心”,公安派钟情“性灵”,实际上都是心学“真己”“真吾”的映现。
唐顺之所谓“本色”是洗涤心源后的清净本源之心,即原初之心性。为文即使文章文采斐然、承转跌宕、技法高超,也无法替代本色精髓。徐渭强调为文本色必是释放真我的结果。真我是文章成败的关键,它无法靠外在把握,只能于本源心性中获得。罗汝芳论述的赤子之心亦是不虑不学、本体自足的初心。李贽受罗汝芳赤子之心的启发,提出童心说。童心即真心,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4]172李贽认为只有保有童心,才能做真人,才能写出天下之至文。公安派性灵说以禅宗心性为理论基础,强调为文应是心的抒发,自心本有,自出胸臆。袁宏道赞其弟袁中道作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5]187袁宏道本人作诗亦是“信心而出,信口而谈”[5]501,往往意会所至便随章直书,以真性情的流淌为贵。
二、贵适
禅宗四祖道信在论及明净心性时说:“亦不念佛,亦不捉心,亦不看心,亦不计心,亦不思维,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6]12六祖慧能谈见性亦云:“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2]258禅宗的明心见性在于回归本原的自然心性,因自性本来具足,故应随心而动,但莫使之造作、污染。任运时,自是“春来草自青”[7]351,如同“双眉本来自横,鼻孔本来自直”[7]1126。王阳明受佛学影响,提出的良知说指的也是本体之心,认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便是良知不假外求。”[3]6王龙溪以“无念”为宗,强调乐是心之本体。颜山农“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8]703晚明时,士人吸收佛禅及王学思想,信奉的不是看一切烦恼尽皆虚空而入悟境的如来禅,而是顺从自然性情、应机悟入的祖师禅,是一种“大活动”之禅。在行为上,他们遵从自心,坦然地追求心体的“乐”与“适”,崇尚心灵的自由自在,将“触类是道而任心”[9]175发挥到极致。
心之所安,适之所在。李贽为人务求其真,他作文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4]169-170直泻内心真情实性,发之成文,以吐胸臆,追求内心本真之适。
晚明文人中,袁宏道对自在的适世者最为推崇。“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5]205,做一个“自适之极”的适世者,是他最大的人生理想。袁宗道亦云:“口于味,四肢于安逸,性也”,认为爱享口腹之欲和身体之适均属人的正常本性,并以此解读陶渊明的出仕与辞官。袁宗道没有将陶渊明视为符合道德礼教的高古孤洁之士,而是从自然人性的角度对他的行为进行解读。陶渊明“一为州祭酒,再参建威军,三令彭泽”,乃缘于其“口”。他不能因贪图身的安逸而盎中不储斗米,但终因“疏粗之骨,不堪拜起;慵惰之性,不惯簿书”而无法自在游走于官场。与其口体交累,不如“解印而归,尚可执杖耘丘,持钵乞食,不至有性命之忧”[10]292-293,于是陶渊明选择放弃仕途。他因口而折腰,因体而弃官,袁宗道赞他是见事透彻之人,对人性充分肯定和张扬。袁中道在《赠东奥李封公序》中说:“处穷处达,无往而不适,是之谓乐得其道”[11]609,也体现了对乐与适生活的渴望。
率真适意地生活,做无拘自在之人,是追求真我、彰显人性独立自由的体现。明中叶以后,士人们纷纷摆脱强加在身上的梦魇桎梏,对迫人的传统礼教产生了强烈反抗。他们追求自由、平等,呼唤符合人性的理想生活,《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塑造即传达出这种情感。孙悟空是绝对自由的化身,他被众猴拥戴为王,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拘束”的自在生活。为挣脱一切束缚,他学了一身本领,向龙宫索得如意棒,去地府勾掉生死簿上猴类的名字,“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第三回),获得了晚明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至境。他眼中不存半点权威敬畏,公然树起了“齐天大圣”的旗幡,欲与玉帝平起平坐。受到天庭讨伐后,他强势反击,直“打得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踪”(第七回)。他对前来救驾的如来佛祖说:“‘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第七回)孙悟空的反抗不是为推翻现存政权和改变自身地位,而是一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肯定与倡导。
三、厚情
《大乘起信论》设“一心二门”之说。“二门”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二者不一又不异,总摄一切法,体现了“不二”思维。这一切法自然包括“色法”,从而有“色空不二”的论断,“烦恼即是菩提,无二分别”[2]272“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2]272皆从此处而来。故而了悟本心无所定法,“无门为法门”[12]375。又因“法身无穷,体无增减,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应物现形,如水中月”[12]2253,所以“一心二门”的思维模式既有可能导致复性论,亦可能导致率性主张。王阳明心学认为,“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3]46,此“心”便包含人的情感因素。到王畿处与随缘自任的禅学思想结合,发用为“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虚心应物,使人人各得尽其情”[13]105-106,肯定了人之情。焦竑将性、情联系在一起,“性之静,非离情以为静也,而不知性者常倚于情”[14]28,“不捐事以为空,事即空,不灭情以求性,情即性”[15]82。江右王门聂双江亦云:“圣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疾痛疴痒皆切于身,一随乎感应自然之机而顺应之。其曰‘无情’,特言其所过者化,无所凝滞留碍云尔。若枯忍无情,斯逆矣,谓顺应,可乎!”[8]379认为人应该顺乎自然之情,不可与之相逆。王琦更进一步道:“人,情种也。人而无情,不至于人矣。”情成为人之所为人的根基所在。在佛学及心学的牵引中,晚明士夫在思辨个体生命的体悟中观照自心,从而引起对感性生命的重视。他们重性厚情,文坛性情之风随之狂吹不断。
晚明士人所厚之情并非单纯的爱、恶、贪、嗔、痴等个人情感,情须是一往而深的真情、至情,与士夫崇尚本真、贵适是一脉相承的。情成为一种恒在的本体、生命的象征,让人们不失自我、以更高深的心灵境界看待宇宙人生,坦诚自我情怀。徐渭说:“人生堕地,便为情使”[16]1296,屠隆云:“夫生者,情也。有生则有情,有情则有结”[17]1294,道出情是本体生命的价值体认。情之于文学,更是其核心源流。焦竑将情与性灵结合起来,认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动魄,垂世而行远。”[15]155汤显祖称:“世总为情,情生诗歌”[18]1110;谭元春云:“夫作诗者,一情独往,万象俱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即手口原听我,胸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测;即胸中原听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可强”[19]408;孟称舜讲:“盖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同本于作者之情。”[20]3他们都强调情即是真,有情之人方为真人,用情所写之文才是真文学。汤显祖高举至情之旗,“因情成梦,因梦成戏”[18]1464。《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情而与柳梦梅在梦中一见钟情,一觉梦醒,求情而不得,于是丽娘相思成疾,终致芳魂幽逝,后又因可与柳生再续前缘而得以复生。杜丽娘因情而死,又由情而生,将情的力量发挥到极致。故而汤显祖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8]1153在汤显祖“至情”的召唤下,晚明传奇几呈“十部传奇九相思”的盛况,王玉峰《焚香记》、周朝俊《红梅记》、吴炳《画中人》、孟称舜《娇红记》等都直言不讳地言情、写情,崇尚至情。
冯梦龙更是提出“情教”说,认为四大皆空,惟情是真,将情视为万物产生的源动力,其在《情史序》所撰的《情偈》云:“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21]1情成为宇宙最高的存在,统摄一切世间万物,于是情统三教、以情摄儒成为冯梦龙理所当然的认知。他认为,“六经皆以情教。《易》尊夫妇,《诗》有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非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21]3忠孝节义皆由情出,忠孝之人也必是有十分真情之人,情的地位在晚明达到巅峰状态。
四、纵欲
唐代禅师马祖道一认为,“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12]2252提倡随缘放旷、“平常心是道”的任运禅。此禅不执著于任何事物,一任本心,即《金刚经》中“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禅法。“无所住而生其心之说,若善用之,即是情顺万事而无情。情顺万事而无情之说,若不善用,即流于猖狂自恣。”[22]26晚明士大夫禅学在商品经济繁荣带来享乐风尚的影响下,并没有走向以“普度众生”为弘愿的宗门禅学,而是沦降为以世俗化入世情怀为目的的禅学旨归。因为无所执著,凡事顺应自心,于是不自制,导致人们进入纵情的圈子,由此文坛上反映任情纵欲的作品比比皆是,蔚为大观。
明人对本然之心的参悟,导致将欲望公开置于合理的地位。王畿曾说:“其行有不掩,虽是受病处,然其心事光明超脱,不作些子盖藏回护,亦便是得力处。”[23]4心成为人们行为的直接指挥棒,而无需受世俗礼教的桎梏。李贽坦言:“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4]225他甚至认为只要出于性情,“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24]125。晚明社会进入“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为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25]123的人欲横流阶段。袁宏道愿“贪荣竞利,作世间酒色场中大快活人”[5]1225。袁中道更是花丛中的浪荡子,“予少年时,烟霞粉黛,互战而不相降。迩烟霞,则入烟霞;近粉黛,亦趋粉黛。”[26]584他挥金如土,酒醉时长达数日不醒;呼朋结友,每到酒市热闹人声仿若千百人,等他离去时,市肆顿时如落日般冷清。屠隆曾穿着官袍而狎妓,终日“朝出左掖,暮过隆中。醉蹋侠斜,回盼娼家,酒支千日,门有万里”,放浪无边。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回忆自己的早年风习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27]157笙歌艳舞、锦衣美眷、珍馐百味、华灯广厦,这些声色追求成为晚明士人追求的风尚。朝野之上也竞谈房中术,一些方士因献方药而飞黄腾达,于是人们“渐不以纵谈闱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起,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28]113在此情形下,《金瓶梅》《浪史》《绣榻野史》《龙阳逸史》《僧尼孽海》《宜春香质》《痴婆子传》《春梦琐言》等艳情小说有见于世。它们无不连篇累牍地铺叙床帏之事,尽可能地追求新奇和刺激以哗众取宠,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虐恋、物恋等不一而足,大量有关性爱淫滥的描写令人不能卒读,持志守节的烈妇受到嘲弄,大胆追求人欲得到肯定,并在金钱的刺激下愈发放纵。如西门庆言:“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金瓶梅》第五十七回)这些书虽一再遭禁毁,但在当时流传相当广泛,可称风流之事。
五、结语
晚明是一个矛盾的时代:一方面,朝不虑夕的政治环境令人心惊胆战、如履薄冰,节妇烈女人数亦以明代为最[29]132;另一方面,社会氛围异常开放,人们关注自心,任性纵情,追求自由,张扬个性。这种矛盾是传统礼教与个性解放思潮的博弈,是繁荣富庶的商品经济与晚明佛教和心学为这个时代注入的新契机。士人彻底挣脱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桎梏,使得晚明文坛涌现出求真、贵适、厚情、纵欲为主旨的性情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