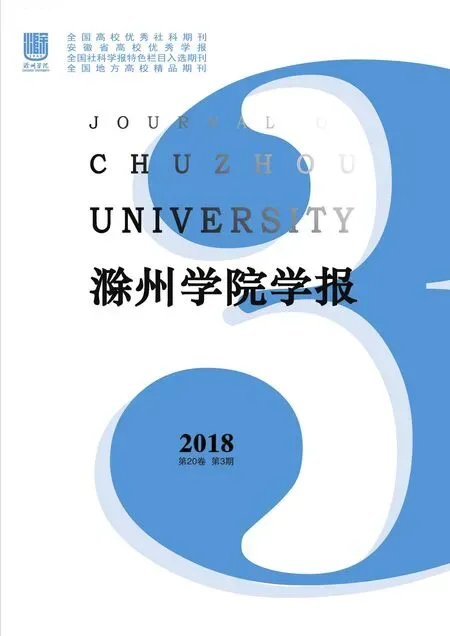伦理学视角下的伍光建翻译初探
2018-03-29刘孝梅
刘孝梅
清末民初翻译家伍光建首开白话翻译之风,译作等身,与严复、林纾齐名,被誉为“翻译圣手”。但因其埋首翻译而著述极少,后世对其研究较少。学界对伍光建的研究主要始于上世纪90年代,相关专题论文仅30余篇可见,主要是从语言学、文化学和译介学角度出发,大多数侧重于伍译的译介特色及其贡献影响;[1]极少数比较了伍光建与严复等其它翻译家的异同;[2]其余分别评论了伍光建的文学译本,如《孤女飘零记》、《浮华世界》、《狭路冤家》等[3],而对于其翻译的大量的其它文学作品及体裁的作品,尚缺乏研究。可见,学界对伍光建的相关研究非常薄弱,缺乏对伍光建翻译实践作全面深入的探讨。
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从单纯文学和语言的角度转换到宏观文化语境的分析,对翻译与伦理关系的研究已经在西方和中国形成了一股新的潮流,自从1984年贝尔曼首次提出翻译伦理的概念,[4]翻译伦理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但中西方对其理解还存在很大差异。综合起来,西方在谈及翻译伦理时,主要是指译者的责任问题如忠实原文还是迎合读者以及译者本身的职业伦理,还有是指人际交流和文化交流的道德认知问题如宗教伦理和丰富目的语的伦理,很少涉及翻译活动本身的伦理问题。而中国学者彭萍指出,翻译伦理学是研究伦理与翻译之间的理论体系,是从伦理的视角来审视翻译的方方面面,所以这里的“翻译”是广义的,涉及社会、译者、译文读者和中间人(如出版商、赞助人等)等诸多要素。[5]本文将从这些伦理要素的视角探讨伍光建的翻译实践,如他的翻译动机、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风格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等,以期比较全面准确的厘清相关问题。
一、社会伦理的影响
社会伦理是指翻译活动应该实现促进文化交流引领时代进步等社会目的和学习异域文明开启民智等教化目的。伍光建1866年出生,1943年去世,一生经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日本侵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可谓国家积弱积贫,民族屡次处于危亡之中。随着列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也同时传入中国,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转型时代,关注民族、国家和自身命运的读书人受冲击最大,感受亦最深,为此掀起了种种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正是痛感于国家濒临灭亡的危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得伍光建和其老师严复一样,“致力于译述以警世”, 开始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立国之道”、“盛衰之理”、“名儒之言论,英雄伟人之行为,……”,[6]以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潮来促进中国的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他的译作目的很明确,即通过向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的文化成果来启迪民智改造社会。
伍光建译作选材严格、内容广泛, 主要有三类:一是自然科学、英文等教科书。所译九种物理学教材成为当时最为完善、系统的教材,《帝国英文读本》(五卷) (后改名《中国英文读本》) 、《英汉双解英文成语辞典》、《英文范纲要》等是当时国人学习外语的必读书目。二是哲学、科学、历史等经典学术之作,对介绍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有筚路蓝缕之功。如哲学家休谟《人之悟性论》和英国哲学家梅尔兹《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是中国最早对西方思想史的译介;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该书系统阐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和伦理学。马基雅维利代表作《霸术》(现译《君主论》),西方评论界将其与《圣经》、《资本论》等相提并论的影响人类历史的十大著作之一;还有英国历史学家马尔文的《泰西进步概论》,帮助国人了解西方的社会政治。[7]三是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以欧美小说为主。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1907年翻译出版的法国大仲马作品《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 与《续侠隐记》(今译《二十年后》)。此外他还陆续翻译出版了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代表作《狭路冤家》(现译《呼啸山庄》)、夏洛蒂·勃朗特的《孤女飘零记》(现译《简·爱》)、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和英国萨克雷的《浮华世界》(现译《名利场》)。1934年至1936年,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了伍光建所译的《英汉对照名家小说选》第一集和第二集,采用节译形式,涵盖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瑞典、丹麦、挪威、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名家名作,影响深远。
此外,伍光建由于身跨政、学两界的丰富阅历和贯通中西的高深学识,具有洞察社会发展趋向的远见卓识,他顺应社会伦理的发展和时代精神的变革,开创了用白话文翻译西方著作的先河,是近代历史上用白话文翻译外国作品的第一人,引领了文学革命的白话文方向。以白话文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和文学、哲学、史学名著,将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思潮、最优秀的文化著作介绍给中国青年,这对当时知识界和社会大众开拓眼界、增长知识,具有启蒙作用,对于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二、译者伦理的影响
译者伦理既包括传统意义上译者自身的道义和使命感,也强调加强译者自身的修养来提升翻译水平从而对原作和译文读者负责。正如傅雷所说,翻译“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能深切领悟”。[8]这实际上是对译者修养和伦理责任的概括。
作为有良知的传统爱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存亡之际、历史剧变关头, 伍光建忧国忧民,力图用翻译促进先进文化之传播,达到警醒同胞发愤图强的目的。在谈到自己译书的选题时,他曾说要选择“自己喜爱的,例如:把世故人情摸得很透,写来逼真:描摹真情至性,肝胆照人,倒不一定情节曲折,甚至离奇;笔墨细致,刻画入微,却不是大人物、大问题。”[9]5-6伍光建以白话文首译的很多作品如《侠隐记》、《孤女飘零记》等都体现了这一标准,并且他所选译的作品大多成为后世经典,足可见其在选材方面的洞察力。此外他还提醒译者:“了解西洋,介绍西洋,不等于盲目崇拜,也要让读者看到西方社会那些肮脏东西。”[10]伍光建对西方社会的这些远见卓识,对今天社会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为学贯中西的优秀翻译家,伍光建十分注重译者对自身修养的培养。他认为,要翻译出好的作品,译者首先要提升自己在文化背景、写作能力、语言表达等各个方面的修养。在文化背景方面,伍光建主张译者不仅要对作品仔细研究,而且还要不断丰富自身的文化知识、社会经验、历史知识等内在素养。在写作能力方面,伍光建认为:“写好散文是锻炼译笔的基本功”、“写文章先从叙事入手,不急于描绘、抒情,久而久之自然干净利落而又有神采”,[9]4并且良好的叙事能力也能使译作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更有风格神韵。此外,他还提倡多读书,尤其是古人的书,认为这对文章和译笔都有好处,至少不会使行文拖沓呆板。在语言表达方面,虽然伍光建坚持用白话文翻译,但他十分重视古文研究, 他认为白话文写作虽以自然流畅为标准, 但也可以追求韵致,多读多背古诗文章就会写得流畅且富有韵致。伍光建认为“信、达、雅”原则不能等量齐观,他认为翻译的核心是“信”,为了译文准确,先得正确理解原文。只有正确理解原作的内在精神,才能避免仅得其貌而失其神。他还强调译者不能只满足于字面的通顺,还要追求“传神之笔”,这才是译本的文学价值和译者的思想修养、文化境界之所在。以伍光建所译《孤女飘零记》为例,第一章开头部分描述了在冬季阴冷的午后简·爱与里德太太一家散步时的感受,茅盾曾举此处说明两种译本的不同。伍译的“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比李霁野译本“在湿冷的黄昏回家”,读起来就“多些韵味”。[11]5而这“韵味”正来自译者的文学修养、敏锐的感受力和对文字的精心锤炼。伍光建所提出的这一系列主张深刻影响了其翻译风格的形成,即便对现今的译者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读者伦理的影响
翻译作品既要忠于原文原作,又要对译文读者负责,必须在价值观、道德观、文化习俗、社会风俗乃至语言表达形式等诸方面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在根本上来说,后者甚至更为重要,因为任何翻译作品最终都是指向读者的。
考虑到当时读者的文化背景、阅读习惯、审美兴趣等因素,伍光建在翻译实践中有意识地尽全力适应读者的需求,采用通俗化的翻译策略,将原作改译成适应国人欣赏习惯和审美判断的文笔和体例。比如在译作的书名上,他更多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兴趣,将《三个火枪手》译为《侠隐记》,将《简爱》译为《孤女飘零记》。节译是伍光建译作的显著特色,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主要译出故事情节,原作中的自然环境描写、人物心理描写多被删去,甚至大刀阔斧地改动原文的叙事结构,同时又加了很多的注释,以此来弥补大量删节所带来的译作整体理解上的不完整。如在翻译《孤女飘零记》)和《狭路冤家》时,他一方面保持原作精华,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的修饰、合并、删减等,减少了原作中的宗教因素和暴君形象,突出了女性形象和爱情悲剧,使作品更适应中国读者的价值判断和“一般读者”的阅读体验。在译文上他以直译为主,但又避免逐字逐句地翻译,而是把长句子分解成很多小句子,甚至在翻译《侠隐记》时针对原著里面三个主人公的不同性格翻译了不同的说话风格,使得译文别具一格,读者读起来也颇具趣味。如《侠隐记》译文简洁明了、句式匀称。如描写动作:“妇女们往大街上跑,小孩子们在门口叫喊,男子披了甲,拿了枪赶到弥罗店来……”;[12]1如描写外貌:“这位奥国的公主,年约二十六岁,正在盛年;十分艳丽,举止名贵;眼光射人,神情极流丽,而又带端庄;……”。[12]123-124可见,他的译文是雅俗共赏的略带文言韵味的白话文,通俗易懂,信达晓畅,因此受到各层次读者极大欢迎。正如茅盾所说:“伍先生的译作,我几乎全部读过;我常常觉得伍译在人物个性方面总是好的,又在紧张的动作方面也总是好的。而对话方面,尤其常有传神之笔。主张直译的我,对于伍先生那样的节译,也是十分钦佩的”。[11]12。
伍光建用白话文翻译的法国大仲马的名著《侠隐记》、《续侠隐记》、《法官秘史》先后出版于1907、1908 年, 早于1917年文学界开展白话文运动10年,均受到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茅盾专文评论《侠隐记》的译文“实在有它的特点, 实在迷人”,说伍译广受欢迎最大的原因是“译文的漂亮”使人人爱读。[13]胡适1918年在北大演讲时说:“我以为近年译西洋小说当以君朔(伍光建笔名) 所译为第一。君朔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别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作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抒百倍”。[14]后在致曾朴信中又说:“近几十年中译小说的人,我以为昭扆先生的白话最流畅明白,于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气力炼字炼句,严谨而不失为好文章,故我最佩他”。[15]伍光建顺应当时普通读者的理解需要,首开白话文翻译,这在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由此译界在翻译过程中开始注重读者体验。
四、中间人伦理的影响
中间人是指不直接参与翻译,而是通过自己的特定活动使文本与译者、译本与读者发生联系的组织或个人。[16]正如吕俊曾经指出:“翻译活动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一种被话语权力所操作和控制的活动。”[17]翻译出版社作为赞助商和中间人,它的喜好和决策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译者译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伍光建曾为新月书店、华通书局、启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供稿,其中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时间最长、关系最密切。作为近代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从一开始就怀着引进西方学术以开启民智,传播文化知识以促进中西文化融合与国民进步,从而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1902年,张元济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与总经理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18]240,还曾说:“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民之民质、俗尚、教化、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耳”。[18]171凭借着文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商务印书馆广招人才,使商务印书馆与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一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广招人才,注重市场与读者的需求,为有价值的原本,寻找合适的译者,保证了所出版译本的高质量。
伍光建与张元济私交甚笃,两人常书信往来,讨论翻译事宜。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拟推出“英汉对照名家小说选”丛书,因张元济对伍光建的白话翻译小说甚为欣赏,伍光建就成为这套丛书译者的最佳人选。在译本选择方面,从1933年5月2日伍光建写给张元济的信中,“敬悉所托译书事已蒙转询……容日内选商”,[19]可见译本虽由伍光建甄选,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商务印书馆编者手中。1934年商务印书馆曾委托伍光建续译它们提供的20种英文著作,伍光建回信表示这20种书“惟范围较窄,不容如愿挑选到”,[20]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译本的选择权偏重于编者一方。一般而言,出版社首先会根据自身战略和社会需求提出大的方向或选题,在确定具体译本方面,会考虑到译者特别是长期合作者的意愿,编者再权衡经济利益、社会影响和文学价值等各方面因素,最终确定翻译书目反馈给译者。有时,编者也会自拟一个范围交给译者由其再做选择。总的来说,虽然译者和编者都拥有一定的选择自由,但是编者显然拥有更大的决策权。从伍光建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的时间跨度和交往深度来看,他都可以算是商务印书馆认可的重要译者,商务印书馆的伦理考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伍光建对译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五、结语
以翻译伦理学为新的切入点,从社会、译者、读者和中间人的伦理要素出发,本文重点探讨了这些伦理要素对伍光建的翻译实践的影响,如他对翻译作品、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风格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等。概言之,从伦理学角度分析,伍光建译著范围之广,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实属翘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饱学之士,加之多年在英、美留学和访问对西方文化传统、艺术理念及社会习俗的深入研究,使他得以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顺应读者的阅读体验,首先以白话文翻译西方文学、哲学、历史等方面的名著,把西方先进的文史哲思想和文化成果从典雅、晦涩的古文翻译中解脱出来, 通过白话文译介而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开启了白话翻译西方名著的先河,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虽然近年来对伍光建的翻译研究范围有所拓宽,但大量伍译作品仍未得以探讨,角度也非常有限。只有拓展伍译的研究视角,才能促进对伍光建翻译实践的完整认识。
AProbeintoWuGuangjian’sTransl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Ethics
Liu Xiaomei
Abstract: As a translator at the late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of Republic of China, Wu Guangjian enjoyed the equal popularity with Yanfu and Linshu, but for a long time the researches carried out on Wu have been extremely poor, because he put his heart and soul into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failed to write any theoretical works on translation. Approaching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ethics, i.e. from the ethical elements such as society, translators, readers and intermediaries, we can penetrate into Wu’s translation practice more deeply and systematically.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thics, the eth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era determines his motivations in translation and his choices of works to translate.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s’ ethics, we find out that Wu’s own morality and literary accomplishment have greatly influenced his choices of translation vers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style of his translation. Besi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ders’ ethics, readers’ experiences in reading determine the practic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he use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mediary ethics, the ethical evaluation of Business Press has great impact in th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his translation versions.
Keywords:translation ethics; social ethics; translators’ ethics; readers’ ethics; intermediary eth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