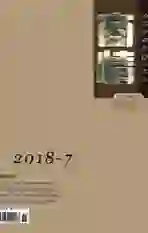论临时起意取财行为的性质
2018-03-28许雅璐
许雅璐
[摘要]行为人在实施暴力犯罪后,利用被害人被压制反抗的状态,临时起意取财的,主要存在“抢劫罪说”和“盗窃罪说”两种争议。在被害人不敢反抗的状态下,应采“抢劫罪说”,不敢反抗是基于前行为对被害人形成的胁迫并没有消失,行为人对此胁迫的积极利用能够被评价为抢劫罪的实行行为。在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情况下,应采“盗窃罪说”,此时不存在需要压制反抗的客观条件,也不存在对于胁迫状态的积极利用,应当构成盗窃罪。
[关键词]临时起意 取财 抢劫 盗窃
实践中存在着行为人出于其他暴力犯罪的目的,在实施暴力、胁迫等行为压制被害人反抗后,利用被害人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状态,临时起意以平和的手段当场取走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对于该行为的性质在理论界存在着各种观点的聚讼,其中主要有“抢劫罪说”和“盗窃罪说”。最高人民法院曾针对以上问题,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认为行为人在实施伤害、强奸等犯罪后,在被害人未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临时起意取财的,前行为与抢劫罪数罪并罚;在被害人失去知觉或没有发觉的情况下临时起意取财的,前行为与盗窃罪数罪并罚。但理论界对此问题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针对该司法解释也存在着质疑,因此,对临时起意取财行为的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一、“盗窃罪说”的理论基础及存在的问题
(一)“盗窃罪”说的理论基础
盗窃罪说认为,临时起意取财行为应当构成盗窃罪,针对临时起意的取财目的,行为人并没有基于此实施新的暴力、胁迫等行为,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主要理论基础在于:
第一,将前暴力、胁迫行为再次评价为抢劫罪中的构成要件违反了刑法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是行为人实施伤害、强奸等暴力行为所致,如果认定为抢劫罪,则暴力行为既作为伤害、强奸等犯罪的构成要件,又作为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同一情节被重复使用了,这是不容许的。
第二,临时起意取财行为符合盗窃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盗窃罪不以采取和平非暴力手段为前提,盗窃罪、抢夺罪、抢劫罪的区别,仅仅在于暴力程度不同。那么在实施取财行为时,即使实施了程度不高的暴力时都可能属于盗窃行为而非抢夺行为,那么,以平和方式临时起意取财的行为就应认定为盗窃行为。
(二)“盗窃罪说”存在的问题
1.对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理解误区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在定罪量刑时,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予以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法律评价。此原则禁止的是一个犯罪构成内的事实在刑法上被予以双重评价,而不是单指一个事实不能重复评价,它实际上强调的是犯罪构成内的事实是有法益侵害性的,不能重复评价的是一个事实对一个法益的侵害。就犯罪构成要件个体来说,并不完全排斥重复评价,如果完全禁止重复评价势必导致刑法的不公正及动摇犯罪构成制度的基础,相应地影响一罪与数罪的区分,以及引发其他一系列问题。抢劫罪属于复行为犯,其实行行为由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构成,行为人利用自己先前暴力行为所造成的被害人不能反抗状态作为抢劫的手段行为与临时起意取财行为组合成抢劫的犯罪构成事实作为侵犯财产法益的抢劫罪去评价并不属于重复评价。
2.认为临时起意取财行为均为盗窃罪具有片面性
前暴力行为与后取财行为是相对独立的,前暴力行为并非后取财行为的手段行为,取财的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意也是在暴力行为实施后产生,确实存在构成盗窃罪的情形,比如,将被害人打昏之后,产生夺取财物的意思,趁其处于昏迷状态而拿走财物;殴打被害人之后,趁其不备窃取其财物,等等。
但是,也不排除存在构成抢劫罪的可能性。盗窃罪不以采取和平非暴力手段为前提,但并不意味着以平和方式临时起意取财的行为就都构成盗窃罪。抢劫罪的实行行为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其他方法”,例如,强奸妇女后,趁被害人仍处于极度恐惧状态,当面拿走其财物。表面上看取得财物时似乎沒有进一步的暴力、胁迫行为,但实质上是利用强奸行为对被害人产生的胁迫效果而取得财物的,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利用胁迫手段劫取被害人财物,无疑应当定抢劫罪,而不能定盗窃罪。
二、“抢劫罪说”的理论基础及存在的问题
(一)“抢劫罪”说的理论基础
抢劫罪说认为,虽然取财行为是出于暴力犯罪后的临时起意,但结合整个过程来看,应当认为行为人存在抢劫罪的主观故意,因而构成抢劫罪。主要理论基础有:
第一,“不作为构成说”,主要是认为在行为人起意取财前,被害人存在的被压制反抗的状态也是由行为人的暴力犯罪行为导致的,行为人如果不对此状态予以排出,而是利用该状态进而实施了取财行为的,其不作为的行为与以作为方式实施的暴力、胁迫等行为并无区别。
第二,“留在现场说”,主要是认为只要行为人在实施暴力犯罪后仍留在现场,对于被害人来说威胁就是持续存在的,行为人正是基于这种威胁的持续存在而取得财物的,因此应当构成抢劫罪。
第三,“持续说”,主要是认为在行为人取财时,前暴力行为导致的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状态仍是在持续中。
第四,“拟制说”,主要是从量刑上来考虑,认为在此状况下的取财行为的可罚性远比一般的盗窃罪来得高,如果仅仅以行为人后续并无暴力、胁迫等行为而否定行为人构成抢劫罪的可能性,必然会导致处罚过轻。
(二)“抢劫罪说”的存在的问题
抢劫罪说的理由存在不合理的部分,主要在于:
1.“不作为构成说”及“拟制说”缺乏理论依据
在临时起意取财的情况下,要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作为义务,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如果行为人不实施一定的作为,被害人的财产是否有被侵害的现实危险。显然,先前的伤害、强奸行为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行为对象并非被害人的财产。在先前的伤害、强奸等行为实施完毕以后,只要不存在新的侵犯财产行为,被害人的财产就不会有损失。因此,在临时起意取财的场合,并不存在不作为犯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先前的犯罪行为不能作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虽然行为人实施了伤害、强奸等行为,也压制了被害人的反抗,但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并不存在保护被害人财产的义务。“拟制说”为了避免按盗窃定罪可能出现的处罚上的不均衡,而把本来没有抢劫的故意和行为的情形,假设或拟制为有,这本身就违反定罪应该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责任原则。
2.“留在现场说”及“持续说”在特殊情况下存在不合理之处
在一定情况下,例如行为人将被害人打昏,或者被害人虽未昏迷但完全不具有反抗能力,或者行为人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取财物的情况下,即在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时,暴力、胁迫已完全结束,客观上已不存在压制被害人反抗的作用,把在这种场合取得被害人财物的行为,也认定为抢劫罪,有不当扩大抢劫罪处罚范围之嫌。
三、司法解释对于临时起意取财行为的定性存在问题
(一)是否失去知觉不能作为定性标准
对于临时起意取财行为,如果被害人未失去知觉,利用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处境的,认定为抢劫罪;如果在被害人失去知觉或者没有发觉的情形下,则认定为盗窃罪。这样的规定从表面上看似乎没什么问题,在被害人失去知觉时拿走其财物,认定为盗窃罪,对此刑法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然而,司法解释对于临时起意取财行为的定性取决于被害人的状态,是否失去知觉成了认定行为人行为性质的重要要素,这一点是存在问题的。
(二)不知反抗和不能反抗两种情况不存在区别
司法解释认为,对于临时起意取财行为,如果被害人未失去知觉,但不能反抗的,认定为抢劫罪;如果被害人失去知觉的,认定为盗窃罪。但是在客观上,被害人虽未失去知觉但不能反抗的状态与失去知觉的状态并无不同,均已不存在需要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条件,已不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司法解释之所以作如此区分,主要在于传统理论将盗窃罪中的“盗窃”理解为秘密窃取,因此,在被害人未失去知觉当面取财的行为就定性为抢劫罪,这是存在问题的。
目前通说把秘密窃取作为盗窃罪的本质特征,认为盗窃必须是秘密窃取,但只强调行为人主观上自认为不为人所知,不要求秘密必须是指不为被害人所知,例如王作富教授就认为:“取财物之秘密性的含义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秘密是指行为人自认为没有被所有者、管理者所发觉。”但是这一通说不能解释实践中存在的行为人当面取财的情况,即行为人明知被害人已发觉,仍取走财物的情形。因此,仅凭行为人“自认为”秘密或公开来决定犯罪性质,属于主观主义的观点,必然导致盗窃罪与抢夺罪的区分不具有客观标准。当面取财的行为当然也不能认定为抢夺罪,首先,抢夺罪客观上必须具有暴力行为,当面以平和的方式取财不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其次,也有学者认为,盗窃罪与抢夺罪是相互包容的关系,盗窃与抢夺的区别,仅仅在于暴力程度不同,盗窃行为也可以包含程度上达不到构成抢夺罪的轻微暴力行为。
因此,在被害人不知反抗和不能反抗的情况下,是否失去知觉只存在当面取财与秘密取财的不同,而秘密性并不能作为盗窃罪与抢夺罪、抢劫罪的区分。如上所述,在不知反抗和不能反抗的情况下不能构成抢劫罪,以和平方式取财的行为也不能构成抢夺罪,在此情况下只能以盗窃罪论处,不知反抗和不能反抗即不存在区分,是否失去知觉并不具有区分这两种情况的作用。
四、对于临时起意取财行为性质的认定
对于先出于其他犯意而压制被害人反抗后临时起意取财的行为在实践中可能存在两种情形:一是被害人尚未丧失知觉处于不敢反抗的状态,二是被害人失去知觉处于不知反抗的状态,或被害人尚未丧失知觉但已丧失反抗能力而处于不能反抗的状态。被害人死亡的情形在此不做讨论。
(一)临时起意取财行为应当分情况讨论的理论依据
前行为不能直接评价为抢劫罪的手段行为。客观上,取财行为与前行为是相互独立的,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临时起意取财的场合,行为人在实施暴力、胁迫或其他压制被害人反抗的行为时并没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意思,行为人实施的暴力、胁迫等行为属于其他暴力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并未侵犯财产法益,不能被评价为抢劫罪的实行行为;被害人不知反抗、不敢反抗、不能反抗的状态也是前暴力、胁迫等行为的延续。取财行为是在前行为结束后实施的,且前行为不是取财的手段行为,不是为取财行为压制反抗而存在的,前行为侵犯人身法益、取财行为侵犯财产法益,两个行为是相互独立的。主观上,取财行为犯意的产生既不是在压制被害人反抗行为实施之前,也不是在压制被害人反抗行为实施过程中,而是在压制被害人反抗行为结束后,取财行为的犯意产生是属于另起犯意,是前一犯罪停止状态下产生新的犯意。
(二)在被害人不敢反抗的场合,应当认定为抢劫罪
在上述两种情形中,第一种是行为人在实施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后,利用被害人不敢反抗的状态,临时起意取财的情形,应认定为抢劫罪。在此情形下,前行为已经实施结束,但对于为失去知觉且有反抗能力的被害人来说胁迫仍是持续存在的。即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被害人仍存在反抗的可能性,前行为对被害人形成的胁迫仍然起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作用;主观上,行为人在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目的支配下积极地利用了这种胁迫。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并积极利用持续存在的胁迫而取得了他人的财物的,因此应当构成抢劫罪。
(三)在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场合,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在上述两种情形中,第二种是行为人在实施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后,利用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状态,临时起意取财的情形,应认定为盗窃罪。在此情形下,在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时,暴力、胁迫等行为已完全结束,前行为对被害人也不存在胁迫,因为客观上已不存在需要继续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条件,前行为结束后也失去了压制被害人反抗的作用;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也只是后行为新产生的犯意,与前行为无关,这种情况实质是行为人利用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状态而取得财物,构成盗窃罪。
五、结论
综上所述,因临时起意取财行为与先前的暴力、胁迫行为相互独立,不能简单地认为前行为是后行为的手段行为而构成抢劫罪,应当分为两种情况讨论。在被害人不敢反抗的情况下,客观上,前行为对被害人形成的胁迫仍然起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作用;主观上,行为人有积极利用这种胁迫的意思,因而这种情形能认定抢劫罪成立。在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情况下,已不存在需要继续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条件,前行为结束后也失去了压制被害人反抗的作用,不构成抢劫罪而构成盗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