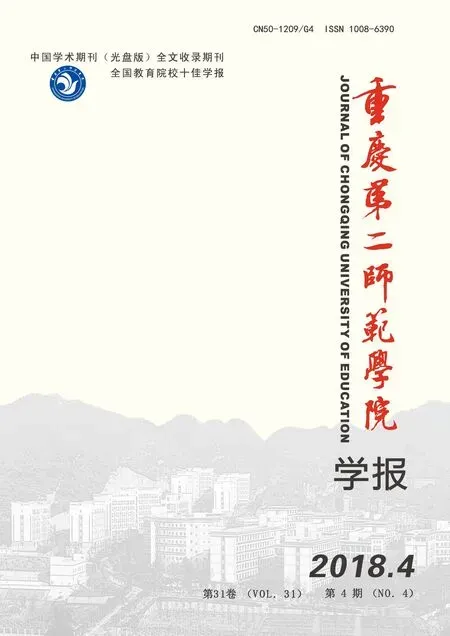张居正讲评《诗经》的思想渊源探析
2018-03-28熊焱
熊 焱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张居正对《诗经》之评注见于《新镌张阁老进呈经筵诗经直解》,是其为万历皇帝开设经筵的讲义。经筵作为汉唐以来为帝王讲史论经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其讲义具有独特的形式和内涵。张居正为皇帝讲学所呈的《诗经》讲义,兼具经学特征与政治目的,具有深刻的思想成因,呈现出通经致用的诗学特色。
一、张居正诗学对《毛序》与《诗集传》的融合
明代以前,尊毛与尊朱是诗学的两股主流,至南宋后,两者之争论喧嚣不已。张居正的诗评呈现毛、朱相杂的状况,他一方面沿袭《毛序》之评注美学,多处“以诗说史”并强调教化作用,另一方面亦兼采朱熹对《毛序》反叛之处。具体表现在:一是认同“淫诗说”;二是多处保留“以诗说诗”的阐释方法;三是在诗教的阐发上,受“修养论”影响,由单一的政治美刺转向兼顾道德修养。
(一)对《毛序》的态度:基本美学思想的承袭
1. 以诗附史的沿袭
《诗经》经过郑玄作笺,孔颖达作疏,形成了传、序、笺、疏一体的汉学体系,巩固了儒家诗学的地位,其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力图为每篇诗冠以明确的史实背景,再作美刺之评。近人傅斯年在说到研究《诗经》的三种态度时,曾明确指出“拿它当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去整理”[1]是要义之一。然《诗经》并非尽然如此,《毛序》很多时候不免牵强附会,“以诗附史”的诠释方式引来后世的两极评价:从之者认为“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2];废之者认为“《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3]。无论《毛序》的解说是否合理,后人是否赞同,不可否认的是,《毛序》为后代诗学研究规定了大致的方向,且成为儒家诗教观的经典文本。附史构筑起了《毛序》诗教观的基本框架,张居正为帝王讲学而注《诗经》,注重政教和儒家道统,当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毛序》附史的影响。
张居正对《毛序》的态度,从其《诗经》评注与《毛序》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大体沿袭了“附史”的基本框架,并以之作为其阐述政教观的基石,并在此基础上认同美刺之说。从篇幅上来看,《颂》本就作为宴飨赞颂之篇,其史实性相对明晰,因此张评基本都从《毛序》,明确了背景史实。《国风》和《雅》由于内容多义性较《颂》强,因而张评在附史问题上就与《毛序》有同有异。如在评《邶风》《鄘风》《卫风》共计38篇中,与《毛序》之附史类同者27篇,相异者7篇,其中对《鄘风》9篇的总体评注基本都从《毛序》。在《周南》《召南》中,张居正注解与《毛序》更是达到了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原因在于,这部分诗被汉儒认定为“正史之道,王化之基”[4],多为赞后妃、美文王的温柔敦厚之言,张居正需要此类注解来达到其目的,这就涉及第二个方面——教化作用。
2. 道统教化功能的延续
诗教概念的源头在孔子。孔子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5]孔子将《诗经》的基本社会功能概括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6]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传统。到了汉代,《毛序》的出现将这一特点标志性地确定了下来。此后,《毛序》在政治教化和伦理道德方面的作用被发掘引申,成为对全民精神教导的重要工具和武器。温柔敦厚的审美风格和平和中庸的审美取向也被后世诗学甚至文学和美学广泛采用。后世说《诗经》者,均没有能够回避或是完全背离这个范畴,张居正也不例外。
在张居正的评本中,那些“正风正雅”不必多论,是“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结果。对于那些“变风变雅”,张居正亦作儒家“思无邪”之辨,如被《毛序》认为是“七世至顷侯,当周夷王时,卫国政衰,变风始作”[4]的《柏舟》篇,将自伤控诉的女子评为“不得于夫,大变也,妇人唯知反躬自咎,而无怨愆之词,可谓贤矣”[7]。再如,《简兮》中评失意贤人“此处衰世之下国,而思盛世之显王……故虽经世伟志或近于不恭,而犹不失为贤人欤”[7] 56。此类评注变风之法,不可谓不多见。对“变风”“变雅”亦秉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标准,即使那些表达哀怨或愆怒的诗,也被认为是“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便使情感的发泄囿于“礼”之规范。
张居正以儒家诗学为基本框架,构建了自己的评注思想。然纵观张居正的整个评注可以发现,其中多处与《毛序》有所出入,甚至大相径庭。在这部分评注中,张居正吸收了朱熹的经学思想,这既是诗学流变融汇的反映,也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由此,张居正诗学在儒家基础上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二)沿袭朱子经学思想对《毛序》之背离
朱熹是南宋经学疑古的代表,他构筑起了与《毛序》相对立的宋代诗学体系,开启了“尊毛”与“尊朱”之辩。他认为《毛序》是村野妄人所作,其论实不足信,且通过《诗集传》突破汉儒解诗之窠臼,“不直言和辨析具体问题,而是从理论根基对《毛序》进行颠覆和瓦解”[8]。张居正继承和发展了朱熹“感悟道情”“以史说诗”以及“修养论”,将其融于对《诗经》的评注中。
1.沿袭感物道情的诗学内涵
“感物道情”是针对《毛序》的“以诗附史”提出来的。朱熹在《诗集传》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则不能无思。”通过人心感物而引起的“欲”来肯定人的情思。同时,他将《诗经》定义为“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9],侧重主体的情感思想,意志理念,将“情”提高到了较史更独立的地位。“感物道情”理论的重大成果体现为“淫诗说”的提出。
自古以来,“郑声淫”一直是世人争论不休的公案。孔子云:“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且云:“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10] 232然其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6] 2461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实际上涉及“诗与乐”,即声类和义类的问题。孔子从郑卫之音不合礼乐的角度出发,认为轻柔曼丽的靡靡之音是败国僭礼之声,因而加以挞伐。从义类来说,诗不似声乐那样不可更改,而可赋予不同的意义。总之,孔子认为的“淫”指的是“淫声”,并非诗义。然而,后世学者却歪曲了孔子的本意,将表达个体“情性”尤其是男女爱情之诗定为不符合仁学精神和温柔敦厚原则的“淫奔者之诗”,朱熹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将“淫诗”说作为攻击《毛序》的一大武器。
张居正将这一理论引进其对《诗经》的评注中。张居正认为,“淫诗”说体现在变风中,尤其是《郑风》和《卫风》中,这些诗大多是男女爱恋的情诗,不是关于美刺和政治历史的作品。因此,张居正在《郑风》21篇评注中,凡涉及男女爱情之诗皆被定为“淫奔者歌也”,共计13篇。此外,尚有《东方之日》《将仲子》《桑中》《匏有苦叶》等多篇被定为刺“淫女”之作。张居正“淫诗”说承袭了朱熹的理论,体现出对道统的维护,是对温柔敦厚诗教观念的表达。张居正的评注部分冲破了《毛序》以诗附史的窠臼,而注目于诗本身所缘之“情”,进一步回归《诗经》本文之中。相较于《毛序》将这类诗一概附于史实,这种理论给予后来者以启发,使其反向探求《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真正价值。因此,作为“以诗说诗”的另类附属物,“淫诗说”是有一定意义的。
2.继承“以诗说诗”的解诗原则
朱熹批评前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3] 2077张居正传承其说,在评注《诗经》时除了以“淫诗”背离“证史”之外,尚有不少地方与《毛序》不同。
其一,《毛序》言明美刺对象,而张居正据诗本义而论,不涉美刺之说。如对《邶风·雄雉》的评析中,《毛序》谓之“刺卫宣公也”,而张评“妇人以君子从役在外”[7]47;《卫风·木瓜》以“男女赠答”“人际交往之礼”[7]94区别于《毛序》的“美齐桓公也”[4]446;《豳风·东山》毛序评其目的为“美周公”[4]518,而张评认为“周人劳东征之归士”[7]205;《晨风》“以夫不在而言”[7]173反《毛序》解之“刺康公”[4]429。值得注意的是,张评《唐风》12篇皆背离《毛序》言,独出机杼,缘诗生义。类似篇目还有《国风》中的《考槃》《芄兰》《伯兮》《有狐》《山有枢》《扬之水》《鸤鸠》《权舆》,《雅》中的《四牡》《常棣》《采薇》等多篇。这类评述,是最能反映张居正评注背离《毛序》而探寻诗之本意的部分,还原了诗人作诗的原始之情,如评《扬之水》发“戍申者怨思”[7]98,《鸨羽》还原“民从征役,不得养父母”[7]157的哀思等。
其二,沿袭《毛序》美刺之说,但不具体指明美刺对象或美刺侧重点不同。在张居正的诗评中,尽管认同部分诗具有明确的美化和讽刺主题,但并不似《毛序》硬性附于史实或政治,而是就文意臧否诗中人物。例如,张居正评《采苓》为“刺听说之诗”[7] 161,但不附于“刺晋献公”之上;《毛诗正义》释《相鼠》为“卫文公能正其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无礼仪”,最终归结为“美文公”[4]73,这里便将“史”“刺”和“美”三者结合起来,体现出“附史”特点和儒家经学温柔敦厚的传统,而张居正却简要地评注为“恶人无礼作也”[7] 73。
3.汲取“修养论”之理学养分
关于《诗经》的教化功能,《毛序》云:“《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4] 56。将《诗经》作为圣人施教于民的载体,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目的,这就直接指出了《诗经》的政治教化功能是其核心宗旨。至于朱熹,对《诗经》教化功能的发展在于,强调了《诗经》对人心性建构的重大意义。朱熹说:“圣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恶,此则炳如日星耳。”[10]朱熹强调《诗经》对于人心灵的熏陶和内在人格的建构,正契合张居正对幼年皇帝进行基础教育的需要。在为皇帝讲学这一现实因素驱动下,张居正注重对年幼皇帝修养之道的传授,道统思想的灌输,潜移默化的人格塑造,从而为其治国为政打好基础。在张居正的经筵讲义中,这种内在教化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人生道理的阐发。如《蟋蟀》篇,张居正评“夫必岁晚而后取为乐,方乐而遂切于相戒”[7]148,这是倡导一种人生苦乐观,即人生必须先克己弃乐,至老成才能得到真乐趣;借《甫田》告诫其勿“厌小而恶大,而大终不成”[7] 133;评《蒹葭》“曰天下之人,有颓然于流俗之中,则见之恒易也,惟超然于尘寰之表者,则见之恒难也”,强调“诗人思欲见之,深慨其不可得焉,其亦秉彝好德之心”[7]169。这就将仁德修养的追求自然融入诗歌的阐释中。二是将《诗经》作为经世治国之用,从政教得失中吸取经验,劝诫皇帝。例如,评《硕鼠》说“诗人之意,盖欲在位者无贪残以竭民之财……为上人者可以惕然思矣”[7]146,教导上位者引以为戒;借《汾沮洳》告诫“贵人者自当恹乎雅量”[7] 49;借《扬之水》劝诫“为人君者,诚当有自强为志哉”[7]87;借《采苓》警示“天下最不可信者,惟谗言,而人每为其所惑者,凡以听之轻耳”[7]161;评《羔裘》说“可见国以政史为先,衣服乃末节也。君以逸豫为戒”[7]74;评《鸡鸣》说“天下理乱之原,本于君心,而君子勤怠之原,关于内助耶”[7]127等。
在对孔子诗学、《毛序》、朱子经学思想的取舍中,张居正明确了自己的诗学特质,即各有扬弃,通经致用。在明代中后期,经学研究由前代遵毛与遵朱之辩开始走向两者皆取,成为清学背离毛朱,独开风气的过渡,张居正无疑受到了这种时代风潮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张居正评注《诗经》强调“通用”,其目的是为教化服务,此种思想特征由其阐释结构表征出来。
二、张居正诗学的阐释结构
张居正的《诗经》评注形成了两个层次的结构,一是评论的外部体例结构,二是经学思想的呈现结构。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受动机驱使,外在体例的设定受其诗评动机所规定。张居正诗评在体例上所体现出的异于传统经学著作的特点,是其诗学思想贯穿于内容的宏观体现,更是其作为《诗经》皇家读本,为皇帝讲学的直接目的所驱动。外在体例和内在评注思路组成了张居正诗学的呈现结构。
(一)体例结构
首先,从整体结构上来看,张居正的诗评中并没有一篇总的序言来阐释其美学思想。《毛诗》和朱熹的《诗集传》都有序总括各自的评注思想,明确提出其对“诗言志”、变风变雅、政教功能等基本问题的看法,而张居正评注《诗经》,却没有这样一篇“序”。
其次,在《国风》《雅》《颂》之前,张居正只作简短的介绍和评注。例如《郑风》总评曰“郑伯爵姬姓,周厉王之后,凡二十篇”[7]106;《齐风》总评曰“姜姓侯爵,太公之后,凡十一篇”[7] 127;《雅》《颂》干脆没有总评。这也有别于《毛序》以较长的总论来介绍各地域方位,风土人情,以及阐释政治和地域的关系,并引大量文献典籍来进行佐证的特点。
第三,在具体文本的阐释中,张居正不重名物训诂,只对诗句作较为通俗的文言译解,不似《毛诗正义》对诗中的每一字句进行详细甚至烦琐的注解。其注解结构是:篇头冠以简短的总括,多为介绍作诗者,作诗背景,可以将其视为小序(只是这个小序相对于《毛诗》更加简明);正文注解以第一人称对每句诗的含义作细化,很少名物详训;而在篇末,张居正作相对较长的讲评,一是总结该诗的主旨内涵,二是由此生发开来,观民风以见政治得失,或是作道德评价,以体现教化作用。由于张居正没有其他思想阐述的论文,这是最能体现其诗学思想的部分。
从上述体例可以看出,张居正诗评详略分明,重点突出:不拘泥于历史背景的追溯和字词章句的考释,而是缘诗生义,提炼出修身经世的道理,体现思想教化功能。通过对诗句本身含义的解读,以及由此生发的评价,达到“所美者皆可以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为戒”的教化目的。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张居正构建了其诗学思想。
(二)思想结构
总的来说,张居正《诗经》评注的思路遵循了一条链式结构,即“政治-民风-道统仁德-政治”。其中,第一重关系“政治-民风”是可逆的,即二者互见:以在位者行为得失观其政教对民风的影响,解释民风形成的上层建筑原因;民风之形成,必有其政教原因,以此反向体察政教得失。《毛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亦指出了诗乐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张评中,这种基本功效更是随处可见,如评《桑中》“淫奔者歌此”“卫之淫乱至此,所谓其政敝,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者也,皆要宣公,宣姜诲淫于上,则其俗之不美有自来矣”[7]68;评《葛屡》刺“无宽宏之度”“魏俗之美,一至此哉”[7]139;《北风》言贤者去国,评其“人之云亡,邦国殄悴,卫之贤者相率避乱,则康叔之祀,自此而衰矣”[7]61等。这种外部可观的作用并不是张居正诗评的宗旨,其独有的特色是将各种诗的题材上升至修身立命、道统仁德的层面。张居正在章句注释中以第一人称嗟叹吟咏,在篇首和篇末评论中又以评论者的立场进行观照。张居正在“观民风”或知政治得失后阐发仁德道统,可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所美者顺向体现出的美德。这体现在《周南》《召南》及正风正雅中,对那些受到“文王”“武王”等圣人之化的对象,皆深层发掘其身上的品德,并提炼出天下应当遵守的儒家礼义标准。例如,张居正评注《周南》前四首诗皆为美“后妃之德”,此外还有很多诗作被其释为美“贤者”。对于这些贤者,张居正逐一加以评述。如评《考槃》“居人所不堪之地,而适己所独乐之情,非贤者见大心泰而能若是乎”[7]132,这就与“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重视自身修养而摒弃外部条件的儒士风范相一致。二是从其刺者身上汲取经验教训,用以告诫帝王及世人。这种情况多体现在变风变雅之中,张居正沿袭孔子“温柔敦厚”“思无邪”的诗教观念,在评注变风变雅时体现出性情中和的审美取向。对于所刺对象,张居正从儒家道统出发作评判,其后总结出仁义道理,为尊者谏。如《甫田》,张居正评说“天下之事小之可大也,迩之可远也,人能循其序而至其极者……又何为欲速不达之敝哉”[7]169,此为对治国施政经验的总结。
那么,修身养性的要求和道统的宣扬就是张居正诗评的最终目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归根结底,从政史与民风的相互观照,到仁德道统的阐发,都是为政治服务。对掌握国家至高权力的统治者的教育与教化,关乎整个国家的兴废存亡。因此,作为皇家读本的《诗经》评注所具有的浓厚政治性,最终制约其评价方式和内涵。
三、张居正诗学的成因
首先,为帝讲学是张居正诗学形成的直接动机。隆庆皇帝过世后,年仅10岁的万历帝即位。对辅政大臣张居正来说,扶持万历帝便成为其首要任务,教育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史载,万历皇帝的学习分为两部分,一是日讲,二是经筵。经筵是每月固定为万历讲经的仪式。为此张居正多次组织大臣撰写讲义,呈上多部对儒家经典的评注。《新镌张阁老进呈经筵诗经直解》便是其中之一。《明神宗显皇帝实录》载:“丁亥,大学士张居正等奏,二月十二日经筵开讲。除《孟子》照常进讲外,其《书经》去年讲完,今岁应讲《诗经》。”且评:“此书本人情该物理,近之可以修身齐家,远之可以治国平天下,于君德治道禆益不浅。上允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儒家教化层次的构建,君德治道则强调对心性道德的培养。张居正诗学的建构特点,是以培养优秀君王为核心理念,对皇帝心性人格的塑造和仁德道统灌输为首要任务,构建一个教化体系。在文本上重缘诗生义,阐发引申,而不是名物训诂,钩沉古意,以便集中体现思想上的目的性。虽然在具体的文本中,张居正并没有直接以老师的身份和口吻对幼帝进行劝导教育,但为帝讲学是张居正诗学的根本意义所在,这从那些充满教化色彩,上升到至圣至德的阐发,以及吟咏吁叹的口吻中能得以观照。
其次,为矫正不良学风提出实用学术观是张居正诗学形成的社会成因。明代是一个理学蔚然成风、心学亦崭露头角的时代,世人多空谈心性,“一切务为姑息弛纵,贾誉于众,以致仕习骄侈,风俗日坏。间有一二力欲挽之,则又崇饰虚谈,自开邪径,所谓如肉驱蝇,负薪救火也”[11]。针对当时政界和学术界的这种“空虚”学风,张居正要“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12],因此其学术特点之一就是学术致用,学见于用,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张居正诗学本就是为皇帝教育所创立,在此学术思想的指导下,张居正更是将《诗经》的实用性发挥到极致。
第三,兼取诸家思想熔于一炉是张居正诗学的思想取向。张居正“援用儒家教义但根据己意加以诠释和引申,借儒为己用”[13]。从其解经文本内部来看,张居正确实以儒家诗学为其基本构架,大体沿袭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注重政治教化。同时亦兼采朱熹思想,对《毛序》进行部分扬弃,秉承朱熹学术中的“道心”说,注重个人修养及人格完善。张居正提出了求本寻真的学术思想,他曾在反驳世儒讥议时阐述其见解:“言不宜不喜道学之为学,不若离是非、绝取舍,而直认本真之为学也。”[12] 437他不赞成受制于先儒设下的藩篱,而主张探求“本真”,其实质在于打破诸家壁垒,搁置孰是孰非,以己之见探求本真,从而达到通经致用的目的。
四、结语
张居正的《诗经》评注作为明代经筵讲义,对《毛序》与朱子诗学各有取舍,且融入“本真”之见。这种特点的出现,一是明代经学直面汉、宋二学所持之态度,二是在为幼帝讲经这一目的驱动下所做之选择。为最大限度发挥诗教功能,张居正的诗学结构区别于传统经学,呈现出精炼集中、层层深入的特征。凡此种种,皆潜含着张居正经筵讲义通经致用、教化幼帝的目的。尽管张居正这位官至首辅的政治家一生颇具争议,但在其经筵讲义中,我们却可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看见其作为真儒者、帝王师对幼帝之耳提面命,春风化雨。那些对《诗经》道统仁德、修养教化的解说实际上包含着张居正对皇帝、对政治、对国家的担当和责任感,这也使得《新镌张阁老进呈经筵诗经直解》在经学和政治之外,还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