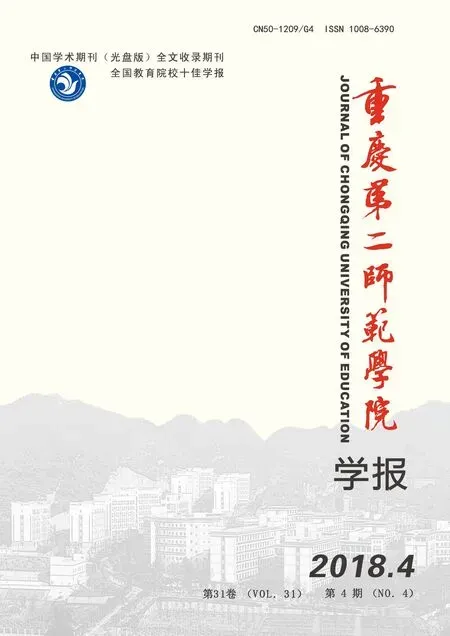传统与反传统: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建构
2018-03-28阮丹丹
阮丹丹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马泰·卡林内斯库提出:“现代性总是意味着一种‘反传统的传统’,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现代主义否定其自身(它的各种历史‘传统’)而又不丧失其同一性的更新能力。”[1]现代性的这一特征,对于理解儿童文学在现代的建构和发展过程,有理论上的帮助。本文试图在理解“现代性”这一特征的基础上,探析现代儿童文学中的传统与反传统的对抗,进而对儿童文学在现代的建构做出学理性分析。厘清儿童文学发生期中传统与反传统的发展悖论,可以加深对儿童文学内部发展张力的认识,并对儿童文学中的一些矛盾命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
一、“儿童”和“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反叛
儿童文学领域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变革,涉及观念、内容两个方面。观念的变革是内部根源,内容的变革则是外在表现形式。从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到“五四”全面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在进行着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社会、思想、文化的大变革,要求儿童文学领域也要做出相应的革新。
现代儿童文学反传统的表现之一,在于现代儿童的发现以及儿童形象的建构。以晚清作为儿童文学的萌芽期,晚清以前的儿童文学尚处于蒙昧状态,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概念。现代语境中的儿童身份和形象的建构,与晚清以降的社会危机催生的思想变革关系密切。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和《新中国未来记》中,将少年的品质与国家的未来相联系,赋予少年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2]这对于儿童的身份和形象无疑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提升,引起社会各界对于少年儿童的关注,并且开始将儿童与未来中国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西方进步学说的传入和影响,警醒一代中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文化观念。1896年,严复翻译了英国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较大的轰动和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民权思想让沉睡的中国人认识到生存的危机和进化的准则。这些为后来对儿童作为“民族的未来”的身份发现埋下了伏笔。对于儿童群体的关注、儿童身份的确立与中国的现代性危机紧密相关,儿童作为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无限可能的象征开始被启蒙者关注。
近代启蒙思潮为儿童的发现和儿童身份的重新确定提供了适当的时代契机。“近代以来的启蒙者试图通过离弃旧伦理传统来建构一种新伦理,这种新伦理符合进化的精神,符合现代的传统。”[3]在传统的社会家庭伦理道德中,儿童只能作为成人的附庸而存在。“父为子纲”和传统孝道的驯化,已经完全抹杀了儿童的独立价值和个性尊严。传统思维观念主宰下的人们,对于儿童大多不能正确理解。他们多将儿童当作“缩小的成人”或“不完全的小人”,一味地灌输圣经贤传,从未将他们当作完全的个人来看待。周作人正式提出应将儿童当作独立的个体看待,注重他们的内面生活。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指出:“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4]
“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不仅仅是儿童领域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更是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重大变革。它不仅仅是对儿童个体价值的发现,更是对传统社会家庭伦理观念的革命。这无疑是现代观念对传统纲常伦理的反抗。同时,儿童的发现作为一个文学事件,构成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反抗。将儿童群体纳入文学的框架中去塑造和思考,是在文学领域做出的对儿童社会关注热潮的回应。
儿童文学这一文学类型的确立与形成是儿童文学反传统的又一表征所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晚清社会启蒙思潮的传入和发展,中国儿童文学也从传统的自然状态,开始走向自觉时期。茅盾在《关于“儿童文学”》一文中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大概是‘五四’运动的上一年罢,《新青年》杂志有一条启事,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5]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发起了一场“儿童文学运动”,开始重视儿童文学的原创生产,并且展开了全面而深刻的儿童文学创作和译介活动,如创办儿童杂志、开展儿童读物的编写、译介安徒生童话等西方儿童文学作品。在儿童文学的兴起之势下,一批儿童文学作家正式产生。茅盾、叶圣陶、郑振铎、冰心、张天翼等开始走上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五四”儿童文学的出现,打破了中国古代没有专门为儿童写作的文学历史。
儿童文学观念的变革,构成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儿童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变革正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一种反叛。在儿童文学的确立上,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是一篇纲领性的文献,提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儿童文学”概念。周作人提出,要建设专为儿童创作的儿童文学,将适当的“儿童的”文学给予儿童。文中虽没有提到“儿童本位”的概念,但其关于儿童文学的理念已经可以称之为“儿童本位”了。他提出应该承认并尊重儿童有独立的内面的不同于成人的生活,儿童的生活是转变和生长的,所以“可以放胆供给儿童需要的歌谣故事,不必愁他有什么坏的影响”[6]。这对于认为“猫狗说话”的故事毒害儿童思想的言论显然是一个有力的打击。继周作人之后,茅盾、郭沫若、严既澄、郑振铎、赵景深等纷纷对现代儿童文学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言论。
现代儿童文学对于传统的反抗,主要是它的现代性创造。它创造了儿童文学这一专门满足儿童的文学需求、促进儿童成长的文学类型;它打破了儿童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学作品的历史传统,打破了儿童不需要文学的传统观念。儿童文学正式从一般文学的类别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自立门户的文学类别,为文学大家庭输入了一股新鲜的血脉。
“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兴起与确立,构成儿童领域的两大现代性创造。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创造。真正的现代性都是同创造性相联系的,它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发明和想象。这些现代性创造,彰显着对传统伦理、传统文学观念、传统文学形式的反叛和破除,并在反叛传统的同时逐渐建构起儿童、儿童文学以及儿童读物的现代性框架。
二、传统在反传统中的延续
发生期的儿童文学,经历了一场现代化的变革。一批作家通过启蒙思潮和反传统的形式对儿童形象进行了重新建构,将儿童从传统的封建束缚中解救出来,并且发展和建构起了新型的儿童文学创作。不得不说,是反传统的力量给儿童身份、儿童文学带来了新生。但是,这一反传统的过程,一方面完成了对传统的反叛,另一面却是对传统的延续和继承。儿童刚刚走出传统的藩篱,立即就被纳入了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理论家组织的现代话语的框架中。作家和知识分子阶层成为儿童身份的新的“立法者”。他们在给儿童带去文明和理性的同时,实际上并未脱去传统的霸权性质,他们如同传统的控制力量一样参与对儿童的监视和建构。
现代儿童的发现以及儿童身份的重新确立最终并未跳出“成人-儿童”的框架。儿童形象的建构,是以成人对儿童的想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儿童由于其生理上的先天不足,无法作为自己的发言人,成人掌控着他们的话语权。成人视角下塑造出来的儿童形象难免附着成人对于儿童的期望,以及儿童作为社会人的责任与使命。作为现代社会的儿童仍然摆脱不了成人世界灌输的伦理和理性。成人框架下的儿童解放,并未实现真正的自由与个性解放。在现代儿童形象的建构过程中,一股追随传统的暗流一直在涌动。
在成人与儿童的对立关系上,儿童一直处于弱者的地位,而成人则是控制和支配儿童的强者形象。“在儿童与成人的对峙话语中,成人往往充当秩序的统治者,儿童成为被这些‘正常人’排斥在外的异类。”[7]197“儿童”这一命名也是成人所赋予的。成人在看待儿童时,往往有一种固定不变的认识,觉得他们是“幼稚的”,是“黄毛小子”,从而很少会与儿童有真正的沟通,也不会真正地去理解和触及儿童的内心世界。赵景深在与周作人讨论童话问题时,也提到过成人对于儿童的控制和霸权地位:“我觉得世界上的领地,差不多成了成人的,没有一种设备不是成人的设备,几曾见成人为儿童谋一些幸福?”[8]在成人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则会经常利用儿童的角色、借用儿童的声音去言说自己。成人对于儿童的控制和霸权,主要体现在他们延续了传统的儿童观念。在对儿童的教育和形象塑造上,成人总是将儿童往“乖孩子”的道路上引导。这对儿童的自然性和叛逆本性无疑是一种现代化的规训。
“五四”启蒙思潮在“发现”儿童的同时,也“遮蔽”了儿童。它发现了儿童独立的生命价值,但是却没有将这种主体自由发挥到极致。现代启蒙赋予儿童新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关乎国家民族未来的想象、成人对于儿童的期望,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儿童观念对儿童个体精神带来的新的“遮蔽”。在现代启蒙话语之下,现代儿童文学在实现了对传统儿童观念的反叛之后,在获得反传统的胜利之后,它自身又重新构成对儿童的传统束缚。
在儿童文学中,儿童视角和儿童本位的文学在获得现代性的反叛之后,经常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的成人视角或成人思想影响的印记。“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常常以反现代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表现现代性的方式深化了儿童文学,也使儿童文学带上较多的成人化倾向。”[9]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却往往难以去除“文以载道”的教育和言志特征。成人作者往往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加入自己对于儿童的启蒙期待和教育引导成分,以实现自己对于儿童、文学和社会的文学想象与介入。郑振铎在评论叶圣陶的童话写作时指出,叶圣陶最初“努力想把自己沉浸在孩提的梦境里,又想把这美丽的梦境表现在纸上。然而,渐渐地,他的著作情调不自觉地改变了方向……而同时却又不自禁地融凝了许多‘成人的悲哀’在里面”[10]。
现代儿童文学以反抗传统的方式将自己从一般文学的类别中独立出来,试图建立以儿童为创作对象、为儿童而写作的文学。但是,儿童文学的成人本位总是暗藏在儿童文学的各个角落中,不自觉地对儿童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如叶圣陶在后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中,逐渐偏离了儿童本位的创作思想,其笔下的儿童文学创作越来越带有浓厚的成人色彩。再如冰心的儿童文学创作,主要是借儿童的口吻、儿童的回忆故事来抒发成人的忧思。她的作品创作的初衷都不是专为儿童读者所写的,而是写给成年读者的关于童年的回忆。现代儿童文学创作中包含了很多非儿童本位的作品,它们有的不是为儿童而写,有的借儿童的视角抒发成人的情绪,或引起成人读者对于童年的回忆。但是,成人读者对于童年的回忆,与正在发生和体验的儿童经验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同时,由于儿童生理上的弱势地位,他们无法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文学需求,也不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创作文学作品。“儿童同成人一样需要文艺,而不能自己创作,不得不要求成人的供给。”[11]儿童对于文学的需求,儿童对于文学趣味的追求与儿童文学作品产生的阅读效果之间往往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此外,儿童文学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写作形式,“而是在国家与社会改革的宏观背景之下对儿童的未来国民身份提出要求并进行精巧设计的文学—政治实践”[12]。从知识和权力的公共角度看,儿童文学在现代的发生和发展,确实包含着知识阶级对于儿童文学的一种权力争夺和文学设计。综观儿童文学的发展脉络,儿童形象的确定、儿童文学在现代的发生,以及各种儿童文学的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各种儿童文学形象,都与时代的需要和社会的思潮发展密切相关。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现代性的反叛都是社会权利文化建构的结果,是各种时代话语博弈的产物。
齐格蒙·鲍曼说:“现代性的展开就是一个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构建园艺文化过程当中的一步,它重新评价了过去,并且,那些在新的藩篱背后延伸开去的土地,以及在自己的园地中,阻碍农人耕作并无法逾越的那些块地,都成为‘荒野’。”[13]从儿童文学的视角来看这句话,“儿童”就相当于“农民”,“儿童文学”就相当于“荒野”,成人掌控下的儿童文学领域就是那块被称为园地的“荒野”,是儿童无法逾越的。儿童文学在现代的发展,就如同将一片荒野变成园地,但在园丁的监护之下,最后又变成荒野的过程。
三、传统和反传统的张力建构起儿童文学的发展
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将儿童文学推向尽头,反而成为儿童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现代儿童文学中传统与反传统的共存共生,成为儿童文学发展的特质。关于现代性与古代性的关系,伊夫·瓦岱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不要把现代性和古代性视为对立面来看待,“现代文学与过去文化的彻底决裂只能是幻想”[14]。传统与现代之间难以决裂的关系,同样证明了儿童文学领域的传统与反传统共存的合理性。
儿童文学领域中传统与反传统形成的张力,主要可从儿童与成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的对立关系中加以考察。儿童与成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在构成矛盾对立的同时,又可以通过一定的介质找到两者之间的契合点。
由于儿童经历了从“成人”中分离出来,儿童文学经历了从一般文学类别中独立出来的过程,所以,儿童文学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儿童—成人”这一对立关系的悖论。对于这一关系,不可片面地将其看成儿童文学的“灾区”。儿童与成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可以找到彼此关联发展的契合点。承认成人对于儿童的操控和教化,但也不可否认成人对于儿童的引导教育产生的积极意义。儿童作为一个心智不全的群体,他们需要有成人的适当引导。同时,成人对于儿童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故,对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矛盾,需要秉持一种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关于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之间的关系,刘晓东提出:“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可以在互补与互哺中相得益彰:一方面,儿童的成长是依赖于成人的;另一方面,儿童清纯朴素的天性又对成人的心灵和文化具有反哺的功能。”[15]
同时,从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来看,儿童世界对于成人世界并非一味地排斥和否定。儿童群体的独特性,儿童作为成长中的成人,他们的情感、思想有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他们自身有着对于成人世界未知的探索欲望。从这一意义上看,成人给予儿童的社会化影响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它从侧面满足了儿童对于社会的认知需求,儿童可以在社会化和成人化的文学世界里,逐渐认清社会现实,对现实世界构成自己的独立认知。尤其是从现代儿童的心理发展来看,他们对于成人世界的事物,往往有着一套独特的认知。成人不必想着将儿童完全隔绝在成人世界之外。再者,在儿童与成人群体之间实际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儿童在自然性之外也有成人社会性的一面,而成人的社会属性之外也有源自童年的自然性。关于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融通,日本作家柳泽健在《儿童的世界》里提出了一个“第三之世界”[16]的概念。柳泽健指出,儿童与成人世界并非完全对立,成人也不必变成儿童,而可以在两者之间找出一个“第三世界”来。
成人所赋予儿童文学的教育特性,在可能引起儿童的接受反感的同时,不否认其对于儿童的正确引导效果。如班马所提出的“干预”理论。“教育与儿童文学,教育与文学性,两者相容而不产生排斥作用,必定存在着深深的‘功能’上的亲缘力。”[17]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在发挥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正确引导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儿童文学强加了一定的说教成分。这一教育性质,可能会导致儿童的反感。但是,儿童文学的教育性质是指向儿童未来的认知和能力发展的,这种教育性质是可以被恰当接受并发挥作用的。
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相对立的同时,可以找到互为关联的逻辑关系。基于儿童与成人的“人”的通性,“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建立关联的逻辑起点是文化的同一性命题和文化的时代性命题”[7]195。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虽说是不同的文学类型,但它们可以统一于文化和文学的共同命题,在两者之间可以找到对话的契合点。此外,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处于文学的共同生长领域之中,两者之间的博弈与对话,丰富了文学的内涵,促进了文学的整体发展。
在儿童与成人组成的关系链上,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矛盾,从另一个侧面又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互为参照的张力结构。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可构成彼此的参照物,以对方的发展作为自己发展的可供借鉴的资源。
厘清儿童与成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的矛盾关系,对于看清成人对于儿童的话语操控,成人文学对于儿童文学的压制,作家知识分子对于儿童文学的权力话语争夺等,都有前理解上的帮助。现代儿童的发现以及儿童文学的确立,一方面是儿童文学领域发生的对传统的儿童观念、文学观念以及文学类别的现代性反叛,实现了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胜利;另一方面,在儿童文学领域,却仍然残存着成人对于儿童、成人文学对于儿童文学的话语操控,即表现出传统在现代的延续。从辩证的眼光来看,儿童文学领域发生的反传统与传统的延续,是儿童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生发的悖论关系,也是儿童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同时,正是这些矛盾体的存在,构成儿童文学寻求自身发展、推进自我更新变革的内外部动力。
对于传统的反抗,以及在反抗的过程中延续传统,都是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特征所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传统与反传统的共生关系,在整体上形成了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建构。另一方面,恰恰是这些矛盾和悖论之处,构成了儿童文学无限的生长点和可能性。通过对传统儿童观、文学观的反叛,启蒙者实现了儿童的发现和儿童文学的确定,这是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创造,是它的现代性胜利成果。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传统的延续,则是儿童文学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产生的异质。反传统与传统在互相克服的过程中,又找到了彼此共存的契合点。儿童文学在传统与反传统的矛盾共存中,实现了自身的现代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