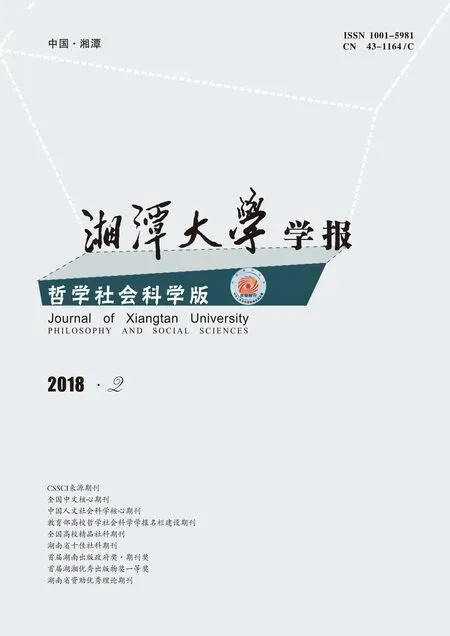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确定与长征前的准备工作*
2018-03-28罗玉明
李 勇,罗玉明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湖南 湘潭 411105)
学术界在研究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时,大体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后,“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进行。”“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又变得惊惶失措,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政治动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0.持此观点的还有叶心瑜,他认为,1934年10月,敌人继续向中央根据地腹地推进。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等惊慌失措,在战争指导上由单纯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逃跑主义,既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又没有在广大干部和战士中进行政治动员和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即匆忙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仓促实行战略大转移。(参见叶心瑜.遵义会议前后[J].党史通讯,1985[1])郑德荣也认为,长征开始时,党中央领导人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当作大规模搬家式的行动。出发前既不做长征的准备工作,又不在指战员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参见郑德荣.中国革命史教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347.)也就是说,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是在毫无准备、惊惶失措之中进行的。但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央红军在长征前是做了一定准备工作的,尽管并不充分,存在一些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袁征.试论长征的准备[J].江西社会科学,1986(5);王健英.中央红军长征前的酝酿和准备[J].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8);硕大全.试论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准备工作及其失误[J].贵州社会科学,1989(10);章克昌.略论红军长征前的准备工作[J].争鸣,1986(4);兴宇.红军长征历史研究若干问题之我见[J].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10);张天荣.关于长征准备问题述评[J].党史通讯,1986(9);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编.长征新探[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1—3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红军长征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本文在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中共中央确立战略转移的过程及在红军长征前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做一梳理。
一、中共中央关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提出与决定
中共中央何时提出战略转移?何时决定向湘西转移?据伍修权回忆:“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75在这里,伍修权似乎认为是李德首先提出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建议,而且当时就决定了向湘鄂西根据地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种说法很显然存在问题,因为,那时红六军团还没有向湖南进发,何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之说?
综观史料,最早提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是毛泽东。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认为打破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时机已来到,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好处,一则可以“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二则可以“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否则“第五次 ‘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2]236但“左”倾中央领导人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失去了打破国民党军事“围剿”的良机。
福建人民政府倒台后,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根据地。1934年4月上旬,蒋介石集中11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广昌进逼,企图首先占领广昌,打开中央苏区的北面门户,进而攻占瑞金。对此,中共中央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的兵力,全力保卫广昌,与国民党军“决战”。红军集中主力,苦战十数日,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尽管予敌重创,但自己亦遭受很大伤亡。28日,红军被迫撤离广昌,转移到贯桥、高虎垴一线进行防御,根据地形势骤然紧张,中共中央不得不考虑应对之策。
1934年5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紧急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会后,一方面委托李德制定计划*李德回忆说:“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一九三四年五至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李德.中国纪事[M].现代史料编刊社,1990:97.),另一方面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3]266但是向何处转移,中共中央并未明确,战略转移的决定既没有向党内高层传达,又没有向广大红军指战员传达,只是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
6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毛泽东在会议上再次提出建议:“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毛泽东认为,“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4]327毛泽东的建议为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指明了方向,但是向西转移至何处,毛泽东并未明确。
7月初,国民党军为巩固“围剿”根据地的成果,集中31个师的优势兵力,从6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发动全面进攻。“左”倾中央采取“六路分兵” “全线抵御”战法,指挥各路红军节节抵御,同敌人拼消耗,企图在各条战线上同时阻挡敌人,结果反而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湘赣根据地处境更是危如累卵。为了寻找应敌之方,特别是寻求红六军团打破敌人“围剿”的策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央红军往西边去,“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5]431毛泽东指出,如果不这样做,“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2]236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战略转移方向,既不是与红二军团会合建立革命根据地,也不是西入贵州寻求新的落脚点,更不是丢弃中央革命根据地。但是毛泽东已经十分明确将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和目标定在湖南中部地区。
对于毛泽东的建议,学术界历来认为“当时的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4]327,但种种迹象表明,“左”倾中央领导人虽然没有完全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将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地区转移,但也没有完全拒绝毛泽东的建议,并且一定程度上受到毛泽东建议的影响。这个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共中央采取了两个重大举措:一是组织抗日先遣队北上,二是红六军西征湖南,试图在湖南中部地区建立起根据地。派出这两支部队的目的,周恩来曾在1943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说得很明白,“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4]327很显然,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是毛泽东在福建事变发生后提出的建议的反映,红六军团西征则是此次建议的结果。
8月31日,在国民党军队的猛攻下,广昌的驿前失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线和北线完全失守,西线因为红六军团西征,更为困难,只有南线自4月筠门岭被粤军陈济棠部占领后,由于展开了对陈济棠的统战工作,两军对峙于筠门岭一线,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9月初,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3]268
二、“调敌”与“探路”
自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战略转移后,中共中央开始进行秘密准备工作。9月之前,“左”倾中央领导人对于战略转移目标并不明确,而且心存侥幸,对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不舍,准备工作不积极;9月后,随着战事紧张,根据地日益缩小,战略转移的工作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战略转移首先进行的准备工作,就是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六军团西征,“调敌”“探路”。
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红七军团6000余人组成,1934年7月6日由瑞金秘密出发。中共中央赋予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有四项,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其他三项任务是:“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在福建及浙赣边境上的单个部队。”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关于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1934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G].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34.。按周恩来的话说是“调敌”,通过“调敌”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为中共中央和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创造条件。从这个角度讲,北上抗日先遣队达到了这一目的。
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后,“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震惊。敌人匆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十七师王敬久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我军。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6]114当红七军团与红九军团攻占大田县后,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即派第52师罗景星旅、第56师汤邦桢旅、第85师谢彬部、第87师王敬久部第517团分别向大田县扑来,企图堵截红军。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又先后调集第49师、补充1旅、新编7旅、第21旅、独立43旅、第11路独立旅和浙保、赣保各一个团,第57师、第55师李松山部、第7师第21旅李文彬部,补充1旅、阮勋旅、刘惠心旅,浙保纵队及安徽保安团等部队进行“追剿”,总兵力逾10万人。北上抗日先遣队牢牢牵制住了这10余万国民党军队,这不仅完成了“调敌”的任务,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条件,而且有力地配合了红军顺利突围,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对于西征的红六军团,中共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中央指出,红六军在湖南的行动分三步走:第一步由黄坳、上下七地域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四团行动的桂东地域。六军团在桂东不应久停,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第三步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联络。[7]12很显然,红六军团西征是受到毛泽东建议的影响,虽然提出要与红二军团联系,并没有提出与红二军团会合建立根据地的任务。这表明,在7月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将战略转移的目的地放在与红二军团会合、在湘鄂西建立根据地的意图。但9月8日,中共中央对红六军团发出补充训令,认为“七月训令中关于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在目前是不利的”。要求红六军团在9月20日前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以后则转移到湘西北地域,并与红二军团在川贵湘边境行动的部队取得联络。9月20日后,沿绥宁、通道到贵州之锦屏、天柱、玉屏、铜仁,转向湘西之凤凰地区前进。然后“协同二军团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于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7]30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确定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就是到湘鄂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红六军团的西征就是探路,寻求与红二军团会合的最佳路线。而红二、六军团的会合,可以说是圆满完成了“探路”任务,从而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做好准备,创造了条件。
三、选择突围方向与加强对陈济棠的统战工作
要实行战略转移,必须确定转移的方向和突破口。毛泽东认为,红军战略转移只能从赣南走,于是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视察,得到中央同意。9月中旬,毛泽东到于都后,“调查于都、赣县等地区的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调查情况。同时,密切注视前线战况的变化,只要有从敌占区和敌人刚攻陷地区来到于都的人,都要找他们询问战事。”[5]432
这时,中共中央加紧了战略转移准备工作,也意识到选择突围方向的重要性。周恩来委托毛泽东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9月20日,毛泽东将自己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以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 〔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5]43210月初,毛泽东又奉中央之命,骑马赶回瑞金,向周恩来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毛泽东复周恩来电及其汇报,坚定了中央从于都突围的决心。尔后,中革军委派部队到于都河搭浮桥,为战略转移做准备。
要从南线突围,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与粤军陈济棠的关系。为此,毛泽东、朱德及中共中央加强了对陈济棠的统战工作。
1934年4月,毛泽东前往中央根据地南线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在了解南线军民反“围剿”情况的基础上,指示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 “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也要提高警惕,要“听其言,观其行”。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并且对当时的形势进行分析:总的是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毛泽东主张,现在应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以小部队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另一方面要向陈济棠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5]425
为了加强对陈济棠的统战工作,1934年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等五点建议。得到陈济棠的应允,双方约定派代表在寻乌会谈。10月5日,中共代表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初谈判,双方达成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往来;(三)互通情报;(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借道路,各从现在战线后退二十里。[3]269这个谈判为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条件。
四、部队的整理整编、补充与集中
为了充实部队战斗力,中央军委从1934年8月底起,开始对部队进行整编与补充。
8月25日,中革军委下令成立红二十一师,由六十一团、六十二团及六十三团(原江西军区赣江团)组成。第二教导团全部(有军政干部64名,战士1307名,工作员187名,步马枪286枝,重机枪2挺,及其他军用品)补入红二十一师。[7]269月21日,红二十一师及红二十三师合编为红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军团政委。[7]30
8月26日,中革军委下令成立教导师,将第4教导团1171名指战员编入红二十二师、二十三师、二十四师。9月15日,第一、第三、第五教导团及一个机枪连、一个警卫连编为教导师,由张经武任师长,并要求“査清全教导师所缺的干部,到九月十五日则由公略步校第二批毕业生中全部补齐。”[7]30—31
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等通知全苏区在9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要求各县9月27日前完成任务。[7]32
10月13日,朱德下令将各补充团补充至各军团,江西补充第二团、于都补充第八团拨给一军团,补充第三、第四团拨给三军团,补充第五团拨给五军团,于都补充第六团拨给八军团,于都补充第一团拨九军团,第七补充团补充红二十四师及军委直属部队。[7]66第一、三军团最后分别拟补充2600人,五军团和九军团最后拟各补充1300人,八军团最后拟补充1900人,共补充9700人。
在补充兵员的同时,对各军团的粮食弹药也进行了补充,经补充后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军委纵队及罗迈纵队马匹达338匹,步马枪达29153支,短枪3141支,重机枪357挺,轻机枪294挺,迫炮38门,刺刀17552把,步马弹达1418200发,手榴弹76526枚,迫炮弹2473枚,此外短枪弹、手榴弹、重机弹、冬衣、盐、药、通信材料等都得到了补充[7]82—83。
由上可见,截至10月8日,各军团战斗人员、武器弹药、冬衣、食盐、钱、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这就为战略转移做好了人员物资武器装备上的准备。
为了顺利实施战略突围与转移,从 1934年10月7日起,中共中央开始电令各军团逐步向集结地域集中整训。10月7日,朱德电令三军团于12日完成对人员、干部、弹药的补充和整理,集中于于都东北之水头圩、石溪坝、车头圩、禾田及仙露观地域。于15日晚,全部应准备备战前进。[7]49同日,令九军团于9日集中于古城、瑞金之间的地域。集中留下红二十四师开展游击活动,拆毁汀州河上的桥梁,掩护部队转移。并要求,“九军团的移动应在二十四师掩护下,保守绝对的秘密,除二十四师首长可知道外,不得使其部属知道。”[7]50令一军团于7日晚集中于兴国东南竹坝、黄门地区,11日晨应集结于以下分界的地区:在北面及西面则以宁都河为分界线,在东面则以下坝、宽田为分界线,[在]南面则以宽田、梓山市及向西到会昌、宁都河会合处为分界线,各分界线均不包含在一军团集中地域内。[7]5110月9日,令八军团9日晚由现地出动,于12日拂晓前到达杰村、澄龙、社富地域,并要求严守秘密,“这一命令不得下达,而仅以单个的每日的命令实施之。严防落伍和逃亡。只应于夜间移动部队,日间休息配置时,则严密注意防空。”[7]5710月16日,令五军团于17日晚转移到社富地域。[7]69各军团遵令迅速集结,到达指定位置,为战略突围做好了准备。
五、战略转移指令逐级下达,并进行长征前的政治动员
过去在研究红军长征时,有人认为“左”倾中央决定战略转移后秘而不宣,没有向广大红军指战员传达,只有中央高层才知道。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战略转移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和军事行动,不可能弄得路人皆知,必须严格保密,否则敌人预先知道红军的行动,半路设伏,其结果可想而知。中央红军能顺利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与中央的前期保密工作是分不开的。相反,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红军西征湖南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因而湖南省政府调集大军,并通令全省各县组织民众“节节防堵,节节兜围,张网设阱,层层密布”。[8]218因而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遭受重大损失。
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各项准备工作的开展,从9月起,红军战略转移的指令开始逐级传达,虽然并没有传达到每一个战士。
在中共中央,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等签署并发出《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关于军团后方勤务组织的命令》《采取具体步骤减少和消灭减员现象》《关于巩固和扩大地方部队及自给问题的训令》等,强调“目前部队管理与指挥的首要原则为最高限度的保全有生力量,特别是干部及现有物质资材”。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7]41这一社论,就成了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而向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民众发出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在苏维埃政府方面,10月初,毛泽东从赣南回瑞金后,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了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 (即青山会议)。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和说明了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大家要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4]330—33110月15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由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上指出: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他对将留在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说: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5]434—435
在部队,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中央红军在阻止敌军推进时,一方面应以“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为基本原则,在战斗的间隙,除1/3的值班部队外,主力应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并加强部队政治团结,另一方面明确提出部队在对敌运动防御的同时,“应准备全部撤退”。[9]5410月9日,李富春签发了《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指令要求各部队“进行整理补充与解释工作,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与巩固部队”,“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各兵团政治机关应根据上列的政治指令,分别定出‘整顿补充工作’‘行军工作’‘居民工作’的具体计划,并采取有效的实施步骤”,并规定“此训令只限于发到军团和师政治部止,根据此训令分别定出适时的工作与口号,迅速传达到连队中去”[10] 396—401。
这一指令,不仅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下达到各连,而且实际上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政治动员令。正是由于有了战略转移意图的逐级下达,因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战士几乎都知道红军要“走”了。李富春回忆:“9月时,当我和蔡畅同志离开江西省委时,许多的同志知道我们要走,并且也隐约知道要离开中央根据地了。”[11]126也就有了瞿秋白知道自己留下来,希望叶剑英“说情”跟着中央红军走,也就有了何叔衡准备了长途行军的两双草鞋。[11]124
六、制定红军各军团战略转移详细日程表
1934年10月9日,中革军委颁布各军团行军日程安排,对10月10日至20日11天里各支队伍每天的日程进行了详细安排,现仅选取其中10月10日、20日两天的行程进行分析,见表1:[7]84-87

表1 野战军由10月10日、20日行动日程表(1934年10月9日)
从上表可知,中革军委对各军团的行军路线做了非常详细的安排,各军团布防、移动、出击、目的等都有详细的安排,而要做到这一点,很显然非一日之功,而是要经过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充分而周密的调查研究和长期的准备才有可能。
除此之外,10月初还制订了第一野战纵队集中计划、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等。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由提出到最终确定,经过了一个过程,1934年5月中央即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到10月10日实施,经历了大约半年时间。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1934年5月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虽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但是尚未到达不可挽救的地步,不甘心放弃根据地,但到了9月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队已经进入根据地中心区域,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已无可能;另一方面是因为战略转移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工作,而由于有第一方面的因素存在,中共中央在9月以前没有做好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
第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经历了由向湖南中部转移到向湘鄂西转移的转变。中共中央在7月给红六军团的训令中明确要求红六军团到湖南中部地区建立根据地,红六军团也试图建立以阳明山为中心的根据地,但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站不住脚。9月8日,中共中央电令红六军团放弃在湖南中部建立根据地,转而继续西进,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这意味着,中共中央战略转移目标的最终确立,长征初期即是以此为目标。
第三,毛泽东在党内最先提出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以图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左”倾中央领导人虽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也没有完全拒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组建和红六军团西征湖南,可以说是这种影响的表现,特别是红六军团西征湖南,起到了“探路”作用,后来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的行军路线西进。
第四,中央红军在进行战略转移前,中共中央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虽然在9月前比较薄弱,但在9月后是比较积极的,并不是如以往所说毫无准备,且这些准备工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对中央红军成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条封锁线起了积极作用。
第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是在保密状态下有序进行的,但并不是如过去所说只限于中央高层领导人知道,而是经历了由中央高层向中下层逐渐传达的过程,并且一直传达到连队。这种保密是当时尖锐激烈的斗争环境所决定的,无可厚非。试想,如果中共中央一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就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让每一个士兵都知晓,毫无秘密可言,那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第六,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包括中央颁布的各种指示训令、各领导人召开部门会议等,特别是张闻天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和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是政治动员的纲领性文件,对于长征初期战略转移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七,当然,中共中央的准备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对那些身体不太好而又有所谓“问题”的老干部如瞿秋白、何叔衡等,缺乏事先的安置和转移,而是将他们留在根据地,以致这些同志后来大多在残酷的斗争中牺牲;又如中共中央虽然决定西出湘鄂西根据地与红二、六军会合,且将长途行军的动员令在长征之前下发到连队,但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却始终秘而不宣。又如,军事行动计划中的主观主义,行军日程制定得过细,将部队每天行军的路程、驻扎地点都事先予以规定,限制了部队的主动性、灵活性,结果“总是按照纸上画好的直线笔直前进,结果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于是我们自己不能取得主动地位,去袭击敌人,反而变成了敌人袭击的对象”。[11]52—53再如,保密工作做得不好。中共中央虽反复强调要保密,但是中共中央一决定西出湖南,国民党方面即得到了中共战略转移的消息,电令湖南省长何键严密防守,何键随即调集大军在湖南省境内构筑了封锁线,张网以待,并电令各县“建筑碉堡,修筑机场,以及组织民众”,“预防流寇,靖乱殄凶”[8]218,给红军的战略转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与危害。再如,由于保密工作的需要,对根据地群众和红军战士没有做细致的解释工作,“中央红军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12]344,以致“西征的准备工作感受很大的困难”,也“使一部分不明了西征目的和前途的青年兵士以及某些个别分子,在行军时不十分坚忍”[12]52。正如遵义会议的决议所指出的,它“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忱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13]61
[1]伍修权.我的历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周恩来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金冲及.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5]毛泽东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6]粟裕.战争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7]红军长征文献[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湖南部分)[G].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1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11]刘统.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13]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G].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