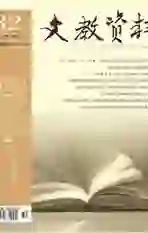论“看理想”系列文化类视频节目的突围
2018-03-27罗朗
罗朗
摘 要: “看理想”系列节目依托互联网为平台,以精准的节目定位与内容生产、垂直的创收模式与商业变现,突破过去文化类电视节目定位不清晰、曲高和寡的困境,坚持内容专业化、分众化,利用高粘性的受众,将文化内容转化为商业价值。
关键词: “看理想” 文化类节目 垂直创收
一、“看理想”系列节目概况
“看理想”是由优质出版品牌“理想国”推出的一个影像计划,该计划力图用简单准确的镜头语言来实践“影像出版”,将主创认为有意义的知识、价值和观念展示给观众,并希望通过文学和各种艺术来触碰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2015年6月15日,“看理想”系列视频节目正式上线,它的网络播放平台是中国最早的视频网站“土豆”和最大型的视频网站“优酷”(双平台播放),这是一场传统出版行业与新兴视频网站之间的跨界合作。
“看理想”系列第一季共播出了三档节目:梁文道的深夜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该节目于每周一三五播出(后听取观众意见改为一周两次);陈丹青解读艺术史经典作品的节目《局部》,于每周二播出;马世芳讲解台湾音乐与文化的节目《听说》,于每周四播出。2016年7月28日,“看理想”系列节目的第一季完结。截至完结当日,该系列节目在优酷土豆双平台的网络总播放量达2.8亿,微博阅读量超1170万次,节目收获了大量受众,并形成了播放量与口碑双赢的局面。得益于第一季的完美收官,“看理想”第二季在节目内容和形式上继续拓展,变得更为多元。除延续第一季的三档节目外,“看理想”第二季推出了两档收费会员专属节目:陈丹青的《号外》是《局部》节目的番外篇,带领观众了解木心美术馆;由作家杨照与其钢琴家女儿李其叡讲解的古典音乐节目《呼吸》。此外,“看理想”第二季还推出了由窦文涛主持的谈话类节目《圆桌派》及其番外节目《圆桌女生派》,该节目引发了范围更广的关注和讨论,将更多受众引向“看理想”的其他节目。
二、背景:文化类电视节目陷入困境
过去,在互联网时代未到来之前,文化类视频节目的播放平台只有电视媒体。电视作为一种典型的大众艺术形式,和其他大众艺术形式共享一些相同的特质。由于大众艺术处于工业化大众社会的大环境,它利用这个环境特有的批量生产和批量传播技术,进行作品的制作与推广。电视这种大众艺术的设计从理想状态来看,就是希望作品能够迅速被最广大的普通观众理解和接受。因此,它是一种“显白的”艺术——它要求最快的传播速度、最广泛的覆盖率,为了让数量如此庞大的观众迅速参与进来,必然会对作品进行一些特别的设计,使它们具备“非常高的用户友好特性”[1],让观众们轻松地进行消费。事实上,大部分电视文本的内容取向、节目形式与理解的容易程度可见一斑。由于电视这一媒介本身的传播特点,加之长期以来电视台的创收制度和盈利模式,高收视率和高收益率早已成为电视节目不可避免的追求,因而,文化类视频节目向來不是荧幕的主流。
大陆最早的文化类视频节目可以追溯到1996年5月12日由中央电视台推出的读书节目《读书时间》,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多省市电视台掀起创办电视读书节目的热潮,并且节目形态也颇为多样。可以说,尽管文化类视频节目在电视台众多节目类型中处于非主流地位,其中却也不乏话题之作。中央电视台推出的一批文化类节目,如《百家讲坛》、《走进科学》、《探索发现》、《人文地理》等都曾收获较高的收视率和关注度。其中,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于2001年7月9日开播的讲座式节目《百家讲坛》,在本世纪初掀起了大众学史热潮,也造就了一批“电视学者”、“学术超男超女”。大陆之外,香港凤凰卫视也制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化类节目,如《文化大观园》、《开卷8分钟》、《世纪大讲堂》、《文明启示录》等。其中,《开卷8分钟》于2007年1月1日开播,这是一个在工作日日播的读书节目,由梁文道在每期节目中主讲八分钟的书评,该节目致力于帮助和引导观众读书,让他们以最便利的方式了解一本书的精髓。
尽管少数文化类视频节目收获了良好的口碑,成为风头一时无两的话题性甚至现象级作品,但是,以电视为播放平台的此类节目最终难免陷入文化价值与商业利益相冲突的窘境。例如,《百家讲坛》的知识生产方式就被指责为将知识流行化、浮躁化。另一方面,电视平台播出的文化类视频节目难以清晰地定位目标受众,常常陷入曲高和寡、难以为继的困境。例如,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就在2014年宣布停播,一项针对其节目内容的调查结果表明:“74.42%的人认为该节目推荐的书太高深,看不懂;41.86%的人认为节目的形式单调,总是主持人一个人说,没有什么新意;20.93%觉得节目时间太短,还未尽兴就结束了。”[2]实际上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文化类视频节目在政策上也曾拥有过天时地利之便。2011年,广电总局发布“限娱令”,开启了音乐类真人秀独领风骚的时期。2013年,为了抑制过度泛滥、同质化的音乐选秀节目,“限唱令”、“限歌令”出现,各大卫视不得不另谋出路,寻找新的节目类型。2014年,中国大陆的电视荧屏是喜剧节目的天下,与此同时,文化类节目也成为荧屏上的新风景,仅全国卫视开播的文化类电视节目就达数十档。但是,电视这一媒介有其根深蒂固的属性和特点,“限娱”、“限唱”并未使文化类节目恢复它本应有的内涵与价值,恰恰相反,对利润的追逐使得文化类节目也披上了娱乐、奇观、竞技、明星的外衣。
三、策略:“看理想”系列节目的突围路径
文化类节目在电视平台的处境是尴尬的,一方面,长期以来它并非电视荧幕的主流节目形态;另一方面,它的确不时引发观众的观看热情,却缺乏持续性。事实上,在如今这个媒介融合的时代,文化类节目早就从电视渗透到了互联网。依托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平台,各种各样的文化类视频节目相继出现。这些形态各异的网生内容,以更轻盈的模式生长,迎来了文化类节目的互联网之春。“看理想”系列就是其中一支异军突起的劲旅。
(一)精准的节目定位与内容生产
“看理想”系列投入资金逾千万元,节目的主创们专业背景雄厚,对节目的定位也十分清晰。这一系列节目坚持内容专业化、分众化,同时对目标受众把握精准,专注于分享文学艺术领域的优质内容,对观众的态度不是迎合,而是呼唤理性思考与参与。它背后依托的是大陆出版业的标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品牌,该品牌经过历年积累,本身就拥有众多来自各界的作者资源和忠实的、不断增长的读者群体。
从节目主讲人的专业程度和内容生产能力来看,“看理想”系列节目由梁文道担任策划人,第一季邀请梁文道、陈丹青、马世芳作为主讲,这三位主讲嘉宾都是各自行业领域的资深从业者——他们具有一定知名度,且非常熟悉自己所属领域的知识和话题。第一季收官后,“看理想”继续邀请谈话节目主持人窦文涛、作家杨照、钢琴家李其叡加入该影像计划。在“看理想”系列节目中,主讲人是节目的核心,他们是内容的主要生产者。例如,《一千零一夜》的主講人梁文道就是资深的电视读书节目主持人,过去他长期服务于香港凤凰卫视,有非常丰富的介绍和推广书籍的经验。《一千零一夜》第一季介绍了数十部文学作品,第二季大致保持一周一部书的播出节奏。从节目所推介的书籍来看,内容涵盖知名小说、经典剧本、历史研究著作等,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严肃且专业的文艺作品,如《玫瑰的名字》、《亨利四世》、《国史大纲》、《乡土中国》、《想象的共同体》等,主讲人梁文道对这些书籍做了深入浅出的扫描式推介。
从定位和目标受众来看,该节目划分、投放得十分精准。“看理想”系列节目大致可划分为四大板块:文学、美术、音乐、谈话。在节目立项之前,“理想国”曾经做过一次针对读者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47%的读者和粉丝年龄集中在25岁—35岁之间,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大学以上学历。知识、学术,或者是历史、理论研究的书籍,买得最多的都是在25岁—35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3]由此可见,“看理想”把目标锚定在“文艺青年”身上,这些受众对内容有较强的兴趣和忠诚度,也有理解比较复杂的文化的基础和意愿,且热衷于文艺话题的互动和分享。《听说》的主讲人马世芳是台湾资深的广播人和作家,其母陶晓清是1970年代台湾校园民歌的重要推手,马世芳自小对流行音乐耳濡目染,对流行音乐的历史和实践均有所了解,他本人也被听众和读者视为真正的“文艺青年”。《听说》的节目大都从经典的台湾音乐作品出发,又不止于作品本身,由点到面介绍创作者的故事、词曲的故事,马世芳用一首首歌曲和他本人的描述将音乐背后所反映的背景串联起来,辐射时代和文化的变迁。例如,在《旅行的意义》这期节目中,马世芳以陈绮贞的经典同名歌曲为引,从1970年代漫谈至21世纪,用极具时代象征性的几首歌曲来解释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热爱旅行,以及在各个时代青年人旅行的不同意义。再如,在《给我一张铿铿的吉他(上)》这期节目中,介绍了木吉他这种乐器在中文歌曲中应用的历史。追溯广为传唱的歌曲《恭喜恭喜》最早的演唱者是当时上海流行乐坛著名的兄妹姚敏、姚莉,作者陈歌辛是为庆祝抗战胜利而写,到李建复的名曲《渔樵问答》,来展现了乐器的多样的功能性。可以说,“看理想”系列节目的专业性和针对性极强,意图掌握小众市场,这一系列互联网视频节目填补了市场空白,正是为电视节目所不能为。
从节目的视听语言来看,“看理想”系列节目针对互联网的观看习惯在时长上做出调整,每期节目20-30分钟,其镜头语言和表现形式相对简单质朴,同时也力图与节目气质相匹配。“看理想”系列节目由张亚东出任音乐总监,创作了一支支与节目气质十分吻合的曲子。在节目摄制人员的选择上也很讲究,这批工作人员此前大多有过拍摄纪录片的经验,例如,陈丹青的节目《局部》的拍摄团队中,工作人员对美术史有一定的了解;马世芳的节目《听说》导演团队曾经拍摄过台湾金马奖获奖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这一系列节目在摄影机调度、录制场景的设置方面也力图与主题相符。陈丹青主讲的《局部》是一档精读美术作品的节目,节目里陈丹青的座位与背景的搭配、陈丹青在画面中的比例,都是精心按照美术作品的比例来设置的,可见主创在场景设计上也力图符合绘画之美。再如,梁文道的节目《一千零一夜》把拍摄场景搬到了室外,为了符合“读书在人间”的节目设定,录制场景基本锁定在深夜的马路、天桥、公交车站、地铁站等日常化场所。
(二)垂直的创收模式与商业变现
“看理想”实行垂直式的商业模式,不横向跨到其他行业,做与该系列项目相关的上下游产业,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同时,它采用分众内容消费的思路,“看理想”的受众对内容的黏性高,能够直接将精准定位的用户转化为相对高端的广告客户资源。2015年3月26日,在《看理想》看片会现场,优酷土豆集团高级副总裁杨伟东在回答为什么要参与制作类似读书、美术、音乐这类相对小众的深度文化内容时指出,与电视台迫于收视率压力而放弃很多类型的节目不同,互联网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其中可能会有数百万的用户对这些深度内容感兴趣。这些垂直的内容消费用户极具商业价值,制作精准分众的文化类节目必定会吸引粘度更大的、消费意愿极强的用户。
数据显示,“看理想”系列的观众群体中,有相当比例的高收入、高学历人群,这批观众有很强的消费意愿和能力。除了传统的知名广告商赞助,“看理想”的收入方式也很多样。例如,节目开发生产了各种自有品牌的限量商品,如手机套、笔记本等。此外,“看理想”与电商平台合作,让观众可以一边欣赏节目一边购物,播放结束后页面就会跳转出相关音乐专辑或书籍的购买链接,甚至主讲人身上的服饰、周边产品都能购买。进入第二季,“看理想”开始探索付费会员制。2016年8月25日,“看理想”视频系列的会员业务上线,节目为观众准备了两档会员,分别对应不同的会员福利。例如陈丹青的节目《号外》、杨照与李其叡的节目《呼吸》就只有拥有会员资格的观众才能观看,从免费到“内容付费”,也从侧面显现了在互联网时代从事知识经济产业的一种尝试。同时“看理想”系列节目还做成自频道,利用互联网将视频、出版物、活动和自有品牌商品整合在一起,使其成为摆脱了传统电视节目困境的互联网视频节目。另外,“看理想”节目视频有在线弹幕和留言功能,主讲人、主创团队和观众可以零距离甚至零时差直接沟通,也改变了过去电视节目单向传播的形态。
四、结语
当然,除了上述行之有效的突围路径,“看理想”系列节目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首先,在内容的表现形式上,不同节目之间存在差异,部分观众质疑某些节目是否有视频化的必要,以及没有体现视频和互联网的优势。近期,“看理想”与豆瓣合作推出的音频节目——《白先勇细说红楼梦》、《杨照史记百讲》,就没有采用视频的方式。其次,某些类型的节目基于有时效性消息的二次加工,可以持续很久,但是文化类节目不像脱口秀,以生产内容为核心需要警惕内容的枯竭。最后,制作文化类节目必定要重视内容的真实和精准,例如梁文道的《一千零一夜》就数次被观众指出纰漏,节目在信息准确度上仍存在待改进的空间。
参考文献:
[1]诺埃尔·卡洛尔.大众艺术哲学论纲[M].商务印书馆,2010:268.
[2]陈欣.我国电视读书节目传播策略研究[D].山西大学,2013.
[3]孙冰.当传统出版遇上互联网:押宝文艺青年?[J].中国经济周刊,2015(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