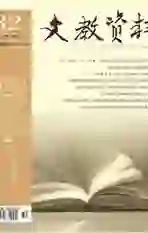浅论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的饥饿叙事
2018-03-27陈悦
陈悦
摘 要: 饥饿并不仅仅是一种普遍性的生理现象,还是一种富有深刻性的政治文化现象。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现实社会的饥饿现象再次回归文学之中,这在反思文学、新写实文学中皆有所体现。根据饥饿的含义及产生原因,饥饿叙事的种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强调饥饿的生物属性,另一种则强调饥饿的精神属性,这种精神属性可以是一种欲望的言说。从饥饿叙事的主体上来看,饥饿的主体可谓多種多样:按照性别划分,有男人,也有女人;按照年纪划分,下到小孩,上至老人;按照社会群体分,有农民,也有知识分子。从饥饿叙事建构的视角上来看,可以分为两种:精英视角与平民视角。高晓生的《漏斗户主》、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莫言的《忘不了吃》《吃的耻辱》《吃相凶猛》皆为代表。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中也出现了诸多有关饥饿叙事的经典作品。
关键词: 中国电影 饥饿叙事 原因 表现 建构
食物是一切生物存在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食物的缺失会影响到生物体的不适,即为饥饿。梅洛-庞蒂曾说:“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可见,饥饿是人类最常见的一种苦难。然而,饥饿并不仅仅是一种普遍性的生理现象,还是一种富有深刻性的政治文化现象。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现实社会的饥饿现象再次回归文学之中,这在反思文学、新写实文学中皆有所体现。高晓生的《漏斗户主》、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莫言的《忘不了吃》《吃的耻辱》《吃相凶猛》皆为代表。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中也出现了诸多有关饥饿叙事的经典作品。
一、饥饿叙事的原因
身体是饥饿的第一感知主体,相比于西方人对于人类身体纯粹的科学主义兴趣,中国人对于身体从来都是用文化与政治的角度进行审视的。葛红兵在《身体政治》一书中对“饥饿”“饥饿感”“永恒饥饿”三者作出了一个概念上的区分。饥饿指的是一种身体的匮乏,饥饿感指的是一种对于身体匮乏感的体验,而永恒饥饿则指的是身体在不饥饿状态下对于饥饿的记忆与领受。“从饥饿到饥饿感再到永恒饥饿,是饥饿的去生理化的过程,也是饥饿由单纯生理现象而文化政治化的过程。”①可见,饥饿使得身体与世界的关系变得复杂化了,饥饿感的实质来源于文化政治对于人的操控,来源于一种深刻的人类集体性记忆。对人类饥饿及饥饿感的书写,彰显出艺术家对于人的生存与精神联系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人类本质的深度探寻。
饥饿作为一种单纯的生理现象,其成因只能是两种情况:体内缺乏营养或者外界食物供应不足;然而饥饿作为一种超越生理的政治文化现象,它是可以由多种因素导致的,例如贫困、天灾、战争、政治运动、特定宗教活动以及社会动荡等等。饥饿根源于集体性的饥饿记忆,而这种集体性的饥饿记忆反映出人对于生存最基本的渴求与信念。历史不仅仅是英雄人物展现自我的舞台,更是一个个平凡躯体与生命不断抗争并最终消亡的悲剧性过程。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生存”二字。影片《活着》(张艺谋,1994)中的主人公福贵从一开始的纸醉金迷,到五颗子弹的恐惧,再到儿子夭亡时的悲愤,女儿大出血的无助,其中经历的辛酸苦楚让人痛心。即使这样,福贵与家珍始终没有放弃活下去的信念。影片结尾他们盼望着馒头可以过上好日子的镜头让每一个观众动容。可见,在饥饿面前,在苦难面前,人是卑小而无助的,唯有顽强地与饥饿抗争,才能赢得一丝生存的气力和一线翻身的希望。这里的“活着”二字,已经不再是一个生物概念,甚至不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是上升到一个关于生存的哲学命题,是回归生命这一原始意象最本初的理性确认。
“权利方法所重视的是每个人控制包括食物在内的商品组合的权力,并把饥饿看作是未被赋予取得一个包含有足够食物消费组合权利的结果。”②可见,饥饿永远都不可能是所有人的饥饿而只能是一部分人的饥饿,是弱者的饥饿。《夹边沟》(王兵,2010)中,绝望的右派们打老鼠、挖尸体充饥,而一旁的管教干部们却在一碗一碗地喋着臊子面;《芙蓉镇》(谢晋,1986)里,国营饮食店经理李国香关起门来自己吃香喝辣却对“豆腐西施”百般记恨……饥饿虽然是一种匮乏,但这种匮乏是不平等的。这种匮乏的不平等根源于权力分配的不公正以及集权统治对主体意志的专制性压制。
二、饥饿叙事的表现
根据饥饿的含义及产生原因,饥饿叙事的种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强调饥饿的生物属性,就是使饥饿场景完全以原初实在的唯物性状态呈现,例如吴天明导演的影片《老井》(1987)中,由于村里无井,干旱异常,竟然上演羊和人争相抢水的荒诞场景;《甲方乙方》(冯小刚,1997)中的刘老板因为追求一种极致的饥饿体验,在穷乡僻壤活生生饿成了一匹“黄鼠狼”……另一种则强调饥饿的精神属性,这种精神属性可以是一种欲望的言说。例如影片《大鸿米店》(黄健中,2003)根据苏童小说《米》改编,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一个农民五龙在大鸿米店的复仇故事。“米”让他获得重生的希望,满足他的食欲,带给他对性的渴望,并最终化成复仇的怒火将他燃烧殆尽。此外,这种精神属性同样也可以侧重于反映人因物质匮乏而导致的精神崩溃、尊严沦丧、人性泯灭的全过程。例如影片《一九四二》(冯小刚,2011)中展现给观众的处于饥饿和死亡边缘残忍丑恶的众生相……
从饥饿叙事的主体上来看,饥饿的主体可谓多种多样:按照性别划分,有男人,也有女人;按照年纪划分,下到小孩,上至老人;按照社会群体分,有农民,也有知识分子。
艺术来源于生活,更依靠于人类的日常经验。席勒说,饥饿与爱统治全世界。可见,饥饿这一主题可以说是最具普适性的主题之一,因为它贯穿于人类的潜在记忆。农民的饥饿也就是最广大劳苦百姓的饥饿,在电影作品中有较多呈现。管虎导演的《斗牛》(2009)为我们生动展露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极端环境下广大农民的饥饿困境,也展现出人在一系列的求生本能中生命原本的能量与意义。1941年的中国,战火弥漫,大地哀鸣。奶牛作为生产牛奶、犒劳伤病员的宝贝,地位显贵。寡妇九儿想接一口奶被十三叔当场拒绝,牛二趁乱去牛棚偷吃的,只因奶牛吃的比他好。饥饿感的本质是一种匮乏感,而消灭这种匮乏感的重要途径就是占有。于是一瞬间,奶牛成为众矢之的:难民牛二门前苦苦哀求分一杯羹;土匪流民妄图宰牛果腹费尽心机;日本鬼子活捉奶牛日夜看守……在以生存为目标的极端环境下,人畜的生命同等的低贱,每个人都被迫在忍受饥饿的煎熬与苟活之间做出抉择。
知识分子在电影及文学饥饿叙事作品中,常常扮演的是无辜的受难者形象,物质与精神的激烈斗争使他们比普通老百姓经受更多的内心挣扎。身体上的饥饿感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无助与绝望,“饥饿”二字使他们不得不在苦难中自我的异化,成为某种性质上背负原罪的忏悔者。王兵导演的影片《夹边沟》(2010)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影片讲述的是3000多个被当局认定的右派分子在一个叫做夹边沟的沙漠边缘地带接受劳动改造,经历意想不到的饥饿与无休无止的批斗,最后只有将近500个人活着逃离苦海的故事。这些知识分子忍受着非人非畜的苦难生活,有人喝下明知会肚胀而死的菜籽粥;有人去抢别人刚刚呕吐出来还可以消化的食物;有人设计捕捉老鼠开水烫烫就咽下肚;有人半夜偷偷去坟场挖死人身上的肉吃从而“看上去红光满面”……同样,李大为导演的影片《走着瞧》(2009)也将知识分子的饥饿描摹地淋漓尽致。影片中的黑六不仅可以不用耕田不用拉车,吃香喝辣妻妾成群,是全村人的掌中宝,这让知青马杰的嫉妒心日益加重,最终对黑六施刑,使其永远丧失生育能力并走向死亡。马杰的嫉妒心本质上是知识分子自身尊严的摧残、颜面的丧失而导致的愤怒与不甘。由此可见,饥饿体验成为中国现实政治对知识分子肉体改造的一种表征,迫使他们丧失作为人的尊严,而这种尊严的沦丧、独立精神的倒塌,也迫使他們进行着由“士”到“民”的退化。
三、饥饿叙事的建构
从饥饿叙事建构的视角上来看,可以分为两种:精英视角与平民视角。精英视角顾名思义指的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视界与空间,因而精英视角下的饥饿书写立足于展现宏观的民族历史。知识分子对饥饿主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不仅有对于人性的批判讽刺,更有对于生命个体的人文聚焦。冯小刚导演的影片《一九四二》(2011)根据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该片以1942年河南大旱为背景,讲述了千百万民众背井离乡、外出逃荒的历史故事,日本鬼子的入侵、国民政府的无能使民众落入更加悲惨的境地,灾民们为了活命,不惜一切代价强取豪夺、杀人分赃、卖儿卖女、贱卖自我……由此可见,饥饿是最大的现实,它不仅吞噬生命、残害伦理秩序,甚至阉割人性、催生丑恶。正如影片主题曲所唱:“当灵魂的寄所,千疮百孔之后,人性的泯灭,只是因为生命还残留。”饥饿是所有苦难的根源,它使得人性之光的沉沦与变异像传染病一样播撒在每个灾民的灵魂深处。
平民视角下的饥饿书写则立足于展现微观普通人的生活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分子群体对于政治的疏远态度与地位边缘化,电影创作者们对于饥饿的关注点也逐渐由宏观转向微观,由群体转向个体,由民族大义转向生命个体的人文诉说。影片《活着》里的妇产科老教授戴高帽、关牛棚,几天没吃饭,一口气吃了七个大馒头差点噎死;《一个都不能少》(张艺谋,1999)里的张慧科在弃学出走后来到城镇,多次在馒头铺前垂涎三尺、左右徘徊。正如他所说:“城里可以白吃白拿,比这里好多了。”其中的无奈与辛酸,将贫瘠农村难掩的隐痛揭示得具体形象……
饥饿叙事的视角决定了饥饿叙事建构的两种常见的主题表达,一种是侧重于饥饿的政治文化诗学属性,此类电影创作者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将饥饿表达作为重要的文学内容和社会人生问题,“以此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现实政治文化的关切,建构从政治文化专制压抑中刚刚觉醒的主体意识。”③影片《活着》虽然说的是福贵一家的故事,却折射出一代甚至好几代人的饥饿困境与苦难人生。饥饿是中华民族贫困落后的直接性表现,他们的饥饿书写是对民族隐痛的聚焦。
另一类电影创作者则认为,身体不是自然物,而是社会建构的必然产物。“它同时也是建构者,它总是与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消费政治中身体话语拥有极高的表述权。”④这种观点受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影响,认为饥饿是社会权力分配不公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一类的电影创作者在进行饥饿书写时总带着鲜明的社会讽刺意识与批判色彩。影片《大鸿米店》一开始,五龙在码头一霸阿保的百般羞辱下和畜生争抢剩肉,最底层的阶级身份使得他不得不用尊严换取食物活命。面对冯老板和其大女儿绮云的刁难,六爷的凌辱,五龙只能在“米雨”中找寻饥饿感被满足的短暂性快感,并最终走向扭曲、走向毁灭。在影片中,缺失的人权酿造缺失的人格,在一个集权社会中,饥饿感的满足方式必然是扭曲而癫狂的。
结语
马斯洛曾说:“如果一个人极度饥饿,那么,除了食物外,他对其他东西会毫无兴趣。他梦见的是食物,记忆的是食物,想到的是食物,他只对食物发生感情,只感觉到食物,而且也只需要食物。”⑤由此可见,饥饿不属于某一个体,更作为一种潜藏的集体性记忆烙印在人们的内心深处。饥饿叙事类电影作品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加深这种创伤性记忆,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正视历史,正视民族隐痛。从这个意义上说,饥饿叙事作品研究更显必要,饥饿叙事类电影创作也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承担起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111.
②[印度]阿玛蒂亚·森,著.王宇,王文玉,译.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5.
③刘传霞.饥饿的政治文化诗学——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饥饿叙事[J].扬子江评论,2009(3).
④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94.
⑤[美]马斯洛,著.成明,编译.马斯洛人本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