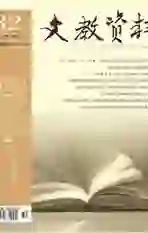成长创伤与自我救赎
2018-03-27荣蓉
荣蓉
摘 要: 张悦然在长篇新作《茧》中塑造了两位主人公形象,作家透过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家庭结构剖析了李佳栖、程恭两位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揭示出病态的家庭环境对儿童性格造成的影响之深、之痛,以及成年后主人公自我认知困难,无法真正完成自我救赎的迷茫。张悦然在书中利用两位主人公分别讲述历史的叙事方式巧妙的将小说人物病态的心理与人格抽丝剥茧般展现给读者。本文试图从家庭环境、家庭结构与儿童成长之间的关系来解析两位主人公的病态人格与自我救赎的有效性。
关键词: 家庭环境 病态人格 自我救赎 叙事方式
张悦然作为“80后”作家的代表之一,曾获“最富才情才智的当代女作家”称号,其作品受到广大青年人的喜爱与追捧。张悦然总是用敏感唯美的情怀、飘逸瑰丽的想象、绮丽凄婉的文笔完成其对人生的感悟与思考。无论是《樱桃之远》中小沐和小桌发现人们对李婆婆葬礼前后情绪的反差,体现了作者尊重生命、珍视自然的道德立场;《水仙已乘鲤鱼去》中讲述了女孩璟对性爱的抗拒到被纯真爱情所感动,显示了作者对纯洁爱情的向往;还是《这些那些》《霓路》中主人公放弃了虚荣肤浅的爱情,做出了守卫理想的选择,透露出作者在浪漫浮华的俗世生活中仍选择对现实作冷峻理智的思考,这些作品彰显出作家并没有被商业利益冲昏头脑,一味的迎合市场“耽于幻想、卖弄残酷”,正体现了张悦然对“纯文学“的追求。她并不止步在“青春文学”的盛宴中尽情飨食,而是进一步挖掘人类生存困境的原因,开启自我救赎之路。
《茧》注定是一本引起轰动的作品,张悦然用她惯用的浪漫风格将人生的残酷赤裸裸的揭示出来,尤其是两位主人公在病态的家庭环境下形成的病态人格常令读者心中一紧,久久不能释怀。《茧》分别用李佳栖与程恭的口述,用两个平行又互相交叉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发生在文革后一家三代人的恩怨纠葛。由于文革的发生,两个家庭的机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文革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减弱,家族的隐秘、丑恶、欺骗、盲从与反抗到了第三代发生了爆炸与裂变。李佳栖和程恭作为受文革影响的第三代家庭成员,都属于单亲家庭,都经历过父母离异的打击,他们身上有相似的病态症候。他们的童年是在父母争吵、家暴、冷暴力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下度过的,从小便对外部世界产生怀疑与不满,性格自卑敏感,被动抑或主动地疏离人群。小说的很多章节都在写他们在得不到亲密关系下童年的经历与心理状态,因此本文试图从家庭环境、家庭结构与儿童成长之间的关系中解析两位主人公病态人格与自我救赎的有效性。
一、“恋父情结”患者-李佳栖
家庭社会学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系统,由家庭成员构成。在家庭系统中,每个家庭成员都有特定的角色和功能,他們彼此依赖、互相影响。在《茧》这本书中,作者主要介绍了两个单亲家庭,李佳栖和程恭的家庭成员、家庭结构。恶劣的家庭环境、扭曲的家庭教育方式和冷漠的家庭成员关系最终影响李佳栖和程恭的个性和心理素质成长,从而形成阴冷扭曲的人格。
李佳栖,是小说首先出场的叙述者。她敏感脆弱、冷漠自私,身上具有浓重的“恋父情结”。正如西蒙·德·波伏瓦曾站在女性的立场这样分析了弗洛伊德的恋父情结:“弗洛伊德的所谓恋父情结,并非像她猜想的那样,是一种性的欲望,而是对主体的彻底放弃,在顺从和崇拜中,心甘情愿地变成客体。如果父亲对女儿表示喜爱,她会觉得她的生存得到了极雄辩的证明;她会具有其他女孩子难以具有的所有种种优点;她可能一生都在努力寻求那失去的充实与宁静状态。”这些话正可以为李佳栖一生下一个注脚。李佳栖从小就过渡迷恋父亲、轻视母亲,在她身上表现出的“恋父情结”正是我国离异单亲家庭孩子非常典型的特点。小说的很大篇幅都在表现李佳栖如何崇拜自己的父亲、寻找父亲生活的痕迹,力图印证这是一个伟大的令她神往的男性形象。为了取悦父亲,李佳栖苛责母亲粗陋的习惯,纠正她讲话时用错的词,嘲讽她土气的审美,对母亲孤立无援的处境竟没有一丝怜悯与同情。书中也解释了父亲对李佳栖冷漠的原因是因为爷爷也是从不和孩子亲密的,父亲从原生家庭获得的信息影响了下一代的父女关系。当李的父亲和母亲离婚,她从没有怨恨父亲的出走与抛弃,而是更为痴恋父亲,如她对父亲学生许亚琛的无意识的眷恋,竟然使她献出身体换取父亲当年教书时的记忆。这种心理和行为上出现的偏差源自李佳栖家庭破裂以后,在处理情感问题时缺乏自制力、易依赖别人、好走极端,因而这严重影响了李佳栖的心理健康与健全人格的形成。与跟父亲有关的男性产生暧昧的关系,是她寻找父爱、自我救赎的方式。虽然这种救赎方式欠缺理性,但也是李佳栖解除心灵创伤最有效的方式。但是在这场追忆似的男女游戏里,李佳栖依然无法客观的评价父亲、审视父亲,而是固执的蒙蔽自己,陷入自己为自己编织的茧中,自我救赎宣告失败。李佳栖的心灵创伤最终也没有被治愈,正如小说题目茧的寓意一样,我们自认为在生活中找到了事情的真相,其实不过是在茫茫大雾中被一层层的茧束缚住。
不止张悦然,新时期女性作家很多人都塑造过父亲的形象,其中不乏赞美父亲,认为父亲是完美男性的化身。这些作品中女主人公都具有“恋父情结”,并大多是单恋父亲,没有得到身为男性的父亲爱的互动,[1]如迟子建的《岸上的美奴》中美奴热烈的爱恋自己的父亲却得不到父亲的关注,以致杀了母亲,将“恋父憎母”发展到了极致。虽然《茧》中李佳栖“恋父憎母”的心理并没有走向罪恶的深渊,却用冷暴力与言语攻击推开母爱,用迷狂的信仰抓住父亲的影子。另外,李佳栖在对待朋友与亲人的态度上也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看似骄傲却敏感脆弱。但是李佳栖并不算坏人,她的心理能唤起很多读者的共鸣。从她与程恭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发现她身上的善良、童真、柔弱……她与程恭在病房里悠闲的看书听录音、她因为程恭没有回信而感到失落、后来去挽留程恭的种种行为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女孩成长道路上明快单纯的一面。至此小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既让人生气又让人怜惜,既固执又脆弱的李佳栖,只强调一点都是不完整的。李佳栖的童年时期因为家庭中父爱缺失,心灵受到了创伤;对父爱的过渡迷恋锈蚀了她的性格与人格。
二、“心里有脏东西”的程恭
《茧》这部小说的主要线索是程恭的爷爷在文革中如何遇害。小说中另一位叙述者程恭,他的性格变化跟小说的主要线索紧密相联。程恭从小就对家里的这个“废人”爷爷抱有很强的好奇心,他通过幻想做梦建立了与爷爷亲密的情感关系。程恭对植物人爷爷如此关注,在病人身上寻找情感慰藉,原因是程恭的家庭也是不幸的家庭。程恭的父亲酗酒、嗜赌,除此之外就是打妻子,后来他欠债闹事后被关进了监狱里,因此程恭从小得不到父爱,十分厌恶父亲并且怀疑自己心里有脏东西,在小说第一章程恭想到:“我怀疑这种毫无由来的恶,可能是基因里就有的。”[2]程恭的母亲是个具有浪漫幻想的女性,这影响了程恭的性格,让他具备爱幻想、善良的浪漫品质。然而母親后期跟人私奔,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导致程恭的心理开始扭曲,病态人格症候逐渐显露。
程恭的人格是病态的,他的心里到底有没有脏东西是整篇小说想要探讨的主要疑团,而这个问题是被李佳栖的奶奶点出来的。在小说的第二章中,李佳栖奶奶告诫她不要和程恭玩,说他心里有脏东西。杜赫提出了家庭系统理论的假设:家庭关系是影响人们心理健康与个人是否病态的主要因素。程恭从小家庭生活贫苦,不像李佳栖家庭条件优越,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充满了紧张冲突,所以这对他的性格产生了一些影响,天真的童心日益衍生出嫉妒与愤怒,使他对整个外部世界持有强烈的怀疑心与自我防御感,无法正常的表达感情。但是程恭一开始并没有对人性的爱与感恩丧失知觉,他是感激对他施与恩惠的人的。对外部世界美好幻想的崩塌源于教堂事件,也正是这一事件让他触摸到文革中爷爷被害的真相,掀起了小说的叙事高潮,复仇的情绪化刺激了程恭的暴力倾向与冷漠心理。然而笔者在前期阅读的过程中,感性上是不愿意承认程恭心里有脏东西,或许程恭是缺乏正常的家庭教育与良好的家庭环境,他到了叛逆的青春期时,欲望与暴动无限膨胀,这个时期尤为需要有人引导,但他的父亲在坐牢,他的母亲跟人跑了,奶奶只知道为生活算计着,姑姑单纯愚昧,没人来关心他的心理状况。所以他心理变的扭曲,后来竟然虐杀了之前喜欢的小狗、强奸精神有问题的陈莎莎、恶作剧李沛萱导致人家毁容、背叛好友大斌的信任。到这里,他变了,曾经受伤的小孩变成了“心理有脏东西”的罪犯。张悦然在描写程恭的心理变化时,多用心理独白的手法,细腻的揭示出程恭矛盾又紧张的心情,体现了作者对人情观察的深刻。程恭的救赎之路是友好地外部世界首先为他伸出了援手,当李沛萱、陈莎莎和大斌都无一例外地包容、原谅了他,程恭才顿悟:“我感觉这个世界好像和原来有点不一样了。它似乎对我抱有极大的善意。”[3]最后,当程恭可以冷静地面对将死的李冀生,与李佳栖站在雪地里从容地说起从前,并开始想象炸酱面盛入碗中的日常画面时,我们知道程恭已渐渐缓和了自我与社会的紧张对峙,尽管这还只是和解的第一步,也是自我救赎的第一步。可以看到,与之前一样,张悦然再一次有意延宕了成长的完成,对于程恭而言,与被埋在雪地里的硬币的正反面一样未可知的,还有他暧昧不明的将来。[4]
三、新奇的叙事手法
张悦然表示:“我没有呈现社会全景的野心。我会努力让自己的小说的视野更宽广,但我不会放弃个人化的表达。”[5]因而,除以个人命运透视宏观历史外,《茧》通篇以李佳栖和程恭两人之间的互动式讲述结构而成,而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择取不仅让文本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私语性,也使得作者对历史的介入并非是冷眼旁观式的,便于将自我的觉知和感悟融入其中。应该看到,作为讲述与回忆双重主体的李佳栖和程恭都不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与他们的祖辈相比,他们基本可说是隔绝在外的;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也离得更远。然而,这样一种带有隔离感的叙述视角显然是作者有意选取的,一方面它在作者与叙述者上使得作者无需在历史细节、场面的刻画上倾注过多精力(这与《誓鸟》所选取的南洋空间有相近的作用)。[6]因而与亲历者的回忆录不同,《茧》透过记忆对历史的追索并不旨归于厘清淹没于雾障之中的历史真相,也无意以严谨的态度重现历史现场,而更多地是为了修复历史与个人,尤其是与80后的关系,[7]即个人绝不会是完全自由独立的存在,那些渺远与隐秘的历史无时无刻不在捆绑着个人,左右着个人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施害者的一方还是受害者的一方都被牢牢地拴在历史的藤蔓上:李牧原、汪露寒、徐绘云、秦婆婆等承受着亲人过继给他们的罪愆,终其一生活在赎罪的痛苦煎熬里;程恭的姑姑、爸爸和奶奶,或跌进失衡不幸的圈套,或以各种非常态的方式宣泄愤恨。而在看似离“风暴眼”最远的第三代那里,历史反而释放出更大的能量,它不仅预先设定了李佳栖、程恭、李沛萱的人生轨迹,甚至还以他们为原点更大范围地辐射开去,包括唐晖、大斌、陈莎莎,甚至许亚琛、殷正等非直接人物都被裹挟进来。历史最终扩散成一张遮天蔽日的巨网,任何人似乎都无所遁逃。
尤其是小说中李佳栖的爷爷李冀生,他是推动全书情节的关键线索。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工作职位上还是家庭结构中都处于绝对的权威位置,他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是传统的专制教育,古板严厉。跨代影响也是如此,在这种教育方式下产生了两个极端方向,一是绝对的服从一是彻底的反抗,也造就了不同的性格特点,制造了全书的矛盾和高潮,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如李佳栖的父亲对她爷爷的反抗,才有了一段敷衍了事的婚姻,懦弱的母亲与冷傲的父亲,这种不平衡的父母关系,让李佳栖形成了厌恶母亲与盲目崇拜父亲的扭曲心理。家庭中父爱的缺失导致了李佳栖在与异性相处时的迷茫,“恋父情结”贯穿了她的一生,这种情结也让别人觉得不可理喻,固执的令人害怕。而李佳栖的表姐则是完全顺从与认可爷爷对家庭的管理与教育方式,她与李佳栖不同的性格特点与人生追求也是《茧》这本小说中引人深思的地方。
主人公李佳栖、程恭的性格变化与通常的成长小说类似,小说主人公的成长历程经历了“天真-诱惑-出走-迷惘-考验-失去天真-顿悟-认识人生和自我”的基本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变异形式[8]。与通常的成长小说类似,程恭和李佳栖的“顿悟”(虽然他们实际上并未跨入成熟之门)也是透过一个契机事件表现出来的,这既构成了一个具有戏剧性的叙事单元,又带出了故讲述的转捩点。对于程恭而言,是曾被他伤害过的陈莎莎、大斌甚至陌生人的原谅帮助他开始改变对自我与世界之关系的认知;对于李佳栖而言,则是恋人唐晖的离去直接促使她基本结束了对父亲的追寻。而实际上,这看似相异的两种“救赎”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即重新相爱(尤其是爱情)的力量。在张悦然早期编织的那些青春故事中,爱是纯洁的、高于一切的,更是值得人为之粉身碎骨的。对那些大喊着“让我们相爱,否则死”(《毁》)的少年们来说,“爱是生命的引擎”。然而许多年后,当张悦然开始小心翼翼地刻写人与人之间的微妙情感,“不肯让主人公轻易地说出一个‘爱字”泛滥于文本间的自由、解放的性关系实际上已部分地宣告了爱在成人世界中的衰败。[9]
张悦然的《茧》真正触动读者阅读情绪的不仅是小说典型的故事情节、双人叙事方式,也有作家充满个人特点语言风格,冷静深邃,富有寓意。笔者认为张悦然的小说没有当代青春文学的那股甜腻感、造作感,没有过分铺张与伪饰感情。她的小说不像郭敬明那样悲伤的逆流成河,不像安妮宝贝笔下充斥着都市的眩晕迷醉。张悦然将当代中国单亲家庭病态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显示了作家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引起人们对社会病态现象的注意。虽然作家并没有在书中给出如何拯救病态人格,实现自我救赎的建议与方法,但读者依然能通过作者饶富笔力的描写中,看到主人公性格的变化与跌宕的成长之路,这也正是张悦然《茧》成功的地方。正如李佳栖,虽然不是我自己,但是她就像我身边的群像。我认识她,做过旁观者,也做过她的朋友。
参考文献:
[1][4]杨有楠.“破茧”的艰难——从长篇新作《茧》看张悦然的创作转型[J].当代文坛,2017(1).
[2][3]张悦然.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69,350.
[5]张悦然,霍艳.“80后”的文学对话——霍艳访谈张悦然[J].中国图书评论,2013(7).
[6]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8.
[7]王琨,张悦然.:“我们这一代作家是由特写展开的”——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3(6).
[8]张悦然.动物纪年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17。
[9]祁春风.爱欲的衰败与“八后”的成长——张悦然论[J].当代作家评论,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