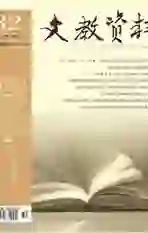叙事学视域下的《革命时期的爱情》解读
2018-03-27王雨柔
王雨柔
摘 要: 以叙事学理论观照《革命时期的爱情》,叙事声音的多重替换,叙述语言的反讽荒诞,呈现隐喻意味浓厚的叙事文本,这种三位一体的叙事学理论是解读王小波对小说形式的把握,以及探索人文精神其中的重要线索。采取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解读囿于“革命”时代困境中的个人与整体的对立和碰撞,通过叙事策略揭示了人性被压制走向异化,在个体的人生轨迹中体现出时代悲剧的张力,呈现出内蕴丰富的文本。
关键词: 革命时期的爱情 叙事声音 叙述语言 叙事文本
王小波是荒谬年代中特立独行的个体,他的小说中存在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在对传统叙事的反叛之中建构了全新的小说叙事形式。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通过多重叙事声音展现其内在自我的复杂,通过叙述语言的反讽荒诞彰显社会的压抑与荒诞,在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之中建构隐喻意味浓厚的叙事文本,以叙事学理论观照《革命时期的爱情》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从而挖掘文革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戕害。
一、叙事声音
布斯指出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他不是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他自己的一个隐含的替身”[1]。在创作文本的过程中,文本中的人物形象会带有作者自身思想观念的映射。《革命时期的爱情》则更进一步,文本建构了双重叙事声音,作者和叙述者不断交替来完成整个故事的讲述。《革命时期的爱情》全文分为八章,章节之间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交替出现,呈现出明显的双重叙事声音。一重为作者的声音,力图证实经历虚构的故事的人为真实的“我”:“这件事显然也是我的故事”[2],“这个被追逐的故事就发生在我身上”,“小时候我想当画家但是没当成,因为我有色盲”,从这些自我意识极强的第一人称讲述方式来看,有理由将故事中的我基本等同于现实中的作者。“这件事我也可以用第三人称叙述,直到我划破了胳膊为止。这是因为第三人称含有虚拟成分…讲到了划破胳膊,虚拟就结束了。”同时强调“我”的真实与故事的“虚构”。第二重叙事声音为叙述者声音,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来建构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王二,“王二年轻的时候在一家豆腐厂做工人”,“王二打毡巴的事是这样的”……力图从客观的角度来重现当时的事件。一重声音叙述“我”的个人化经历,描摹宏观时代下“我”的心理和行为,在增强故事真实性的前提下与读者建立起亲密的联系。一重声音叙述文本,从限知视角合全知视角勾勒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两条线索并行,以全景敞开的的角度展现文革时期的个体的生命體验。
双重声音可以更为完善地叙述故事情节,推动文本发展,同时,文本中对叙事主体的模糊化处理更具深意。文本在真实的“我”和虚拟的“王二”之间频繁转换,文本中的“我”是作者本人旨意的传达者,亦或是“作者已死”之后的纯粹独立的形象“王二”。“王二”作为王小波小说中多次出场的人物,实际上无论从相貌亦或是精神都赋予了作者的某些特征,“作者本人年轻时也常被人叫作王二,所以他也是作者的同名兄弟。”[3]同时,作者又点出了这个“王二”和其他“王二”的区别:“他从来没有插过队我,是个身材矮小,身体结实,发很重的人”。作者在赋予其标志性名字的同时强调其个性,在作者和叙述者声音的转换之中,小说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不断被打破重组,引发对“王二”身份更深层次的思考:如果故事中的人物带有自传色彩,是否文本中建构的的荒诞不经的事件可以作为真实历史的参照?在多重的叙事声音之中,又体现出何种叙事意图?
在作者与叙述者的转换之间,在叙述人称的反复之中,是对个体独立的存疑。在“王二”和“我”的摇摆之间,“某种程度上,叙述人无法整合我和王二双重视角的冲突”[3]这种叙述者不断将自身陌生化的局外人视角,有力的证实了文革中的人物处境:人物分裂成两重叙述声音的主体,而这种分裂究其根本原因为缺乏自我身份认同感,在文本呈现平静的表面之下是“对峙与冲突”。作者在叙述中,没有按照传统的固定的叙述视角,而是借用蒙太奇的技巧,按照作者主体构思的角度来安排哪一种声音的出场。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充斥着作者自我情感的抒发,从生理上对“磨屁股”的疼痛到精神上不断的“交代”的无奈与调侃,文本作为小说的虚构性质被弱化,从而突破了传统叙事中历史与虚构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引发对文本中看似荒诞的事件的深度思考。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革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个体成为集体的附庸,革命时期下的自我认同感被时代加之于人身上的压迫所摧残,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被取消,取而代之是集体的共性。《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双重叙事声音体现了王小波对叙事策略的自觉把握,在九十年代的文坛上完成了一次小说叙事形式的先锋实验,展现了对人性的思考,对个体存在的焦虑,同时,在叙述声音的转换之中,展示人物对自身身份的迷惘与矛盾,解构文革的严肃性,完成了对历史的独特表述。
二.叙事语言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语言看做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而语言的的表达受制于这个系统本身的一套规范。《革命时期的爱情》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常规,在颠覆与拆解之中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戏谑与调侃是王小波在小说中常用的叙事技巧,借用“充满趣味”的语言剥下历史严肃的外壳,露出内里荒诞的原貌。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一文中,王小波将这种戏谑的笔调用到极致,“在我看来,既然生存的主要方式是比赛磨屁股,那么我们这些生来屁股窄的人就处于极不利的地位,”[2]“我患的就是革命时期的痔疮,在革命时期我陷入了困境,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王小波将传统的形而上哲学问题具化到生活中的细节,将崇高的革命与低俗的痔疮放在一起,并且以严密的逻辑用加以论证,形成了崇高与低俗,美与丑的强烈对比,在对比中显示出极强的文本张力,同时过程越是看似严谨,所谓的事实真相就愈加荒诞。王二在回答x战鹰漂亮不漂亮的问题时,将主观判断直接升华到复杂的伦理问题层面,并经过层层推导得出在文革时期称赞一个人漂亮的重重困难。将这种论述放置于宏观的时代语境中,透视个人话语权的微弱。艾晓明认为王小波的作品中“罗列出的逻辑脱离及事实演绎过程,常常把革命时期里常见的生活场景概念表述的荒谬性推向极致”[4],“对某个荒谬情境的的反复分析,使其荒谬性穷形尽相,无所逃遁”,而戏谑与调侃的语言是王小波有力的叙事工具,在极尽荒诞的叙述语言之中,对历史的本质发问。
反讽也是《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常见的表达方式,克尔凯郭尔在《论反讽概念》中提出“反讽最严肃的形式说严肃的话但并不把它当真,另一种形式是,说着开玩笑的话,但把它当真”[5],王小波的反讽属于另外一种形式,在形容X海鹰的外貌时“我就把她画成埃及墓葬里壁画上的模样,岔开脚,岔开手,像个绘图用的两脚规。”对于X海鹰的感情是“对于不能恨的人,我只能用爱来化解仇恨。我爱上她了。”语言的反讽背后是时代的荒诞,王小波“以反讽的思辨从容,冷静演绎着生活中荒谬的一面”,[2]文本中的王二是身世平凡的豆腐工厂的工人,在被“确认”为创作淫画的作者之后被老鲁追打,这种判断的过程充满讽刺,因为“他的右手的手指总是黑黑的”,从而判断其经常拿炭条,而“那几根线条显得极为老练”所以“足以证明是他画了那些画”,这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只是王二恰巧是你,一切都不一样了”。而“王二”的选择并没有硬性条件,而更像是“中彩票”,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王二”。寥寥几笔,勾勒出文革年代的荒诞性。“王二被老鲁追得不胜其烦之后”,就决定“她要是敢咬我,我就揍她。”然而“打定了这种决心以后,老鲁就再也不来追王二”,在荒诞的开始是荒诞的结束,事件合理的因果关系被解构,而对王二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文中只有一句解释——“因为是在革命年代”,后来,老鲁成为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这时候的老鲁已经变得心平气和,她甚至还和我解释年轻时的行为,“有一阵子火气特别大,压也压不住,有些事干得不对头,让我别往心里去。”老鲁的话再次被解构了事件的因果关系,将原因指向为个人性格,而这种性格又与“有一阵子”緊密相连,特殊年代,人们成为主流思想的奴隶,个体对生存环境的困惑衍生出一系列荒诞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时代成为大众走向荒诞状态的指引者。正如“所有的荒谬背后都有一整本革命时期的逻辑推理。”[4]时代早已形成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足以解释理性无法寻求答案的问题,在语言的的颠覆与拆解中,还原历史的本来相貌。
王小波的语言一向以智性的幽默取胜,即使触及到文革此类沉重的话题以依然也能做到戏谑与超脱,正如孙郁所说“以往文字在控诉恶势力的时候,要么怆然泣下,要么义愤填膺,情感都是单线条的,王小波以快慰,戏谑的笔法,轻松的掠过那段历史”[6]这种写法在重塑文革历史毫无疑问是具有原创性的,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小波对普通语言进行变形和解构,从而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常规和逻辑,在反讽和戏谑之中对历史真伪的进行发问和质疑,展现了在特定的历史年代个体荒诞生存体验。
三、叙事文本
双重叙事声音与反讽式的语言建构出复杂立体的小说世界,同时呈现出一种隐喻意味浓厚的文本,罗钢指出有一些作家在创作时“并不企图制造逼真感,对与客观经验的相对性也不感兴趣,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某些精警独特的意象,调动读者的想象和参与,促使读者去猜测、探寻、思索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意。”[7]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隐喻俯拾皆是,丰富的隐喻不断引起读者的困惑和思考,其中最为表现出来的是虐恋模式下的革命隐喻。
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也时常表现着十分顽强的固执现象,有时甚至宁可退化,宁可变态,而不情愿受阻”[8]《革命时期的爱情》书写“非性的年代”里个体心理的扭曲和变态,在正常的性本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走向异化。在这里,人的正常本能在走向变态的过程中存在多重隐喻。一重以“我”和x战鹰被异化的情欲描写来展现权力对人的禁锢,“权力是一种暴力,一种发生在实施者和承受者之间的强权”[9],一方面x战鹰对王二的训导成为权利禁锢的外在表现模式,而社会的全景式规训场所在潜移默化中禁锢了x战鹰作为人的正常欲望和思想。在文中,x战鹰以帮教者的身份出现,王二则是受教育者。x战鹰对王二在精神和肉体上实行了双重戕害,精神上是和无休止的冗长的在“王二”看来毫无意义的“交代”,肉体上是长期的“磨屁股”以致于长了痔疮。在这个过程中,×海鹰占据主导地位,是权力的代表和执行者。然而这种权力关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帮教的过程中,X战鹰爱上了王二,X战鹰无法理解自己的心理,她只能通过受虐的方式来将自己对王二的爱与性合法化,以求心理安慰。文本中,x战鹰只能接受以受虐和受虐的方式进行性交,在与王二做爱的过程中,她总是“闭着眼睛,就如睡着了一样,但是不停地吸着气,仿佛在做忍疼的准备”[2],“她在等我打她,蹂躏她”,在这场“恋爱”关系中,×海鹰在受虐中发现自己的欲望,而只有在受虐中,才能找到性爱存在的意义,才能展示自己坚持革命的坚韧的意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海鹰拥有一定的自觉意识,但是这种自觉并没有转化为对权力体制的抗争,而是在自己的无意识中被压制,再被社会主流话语同构,×海鹰无法理解本能的合法性,将任何性交都认定为强奸,她不是主动的去“享受”性爱,而是被动的接受“蹂躏”,由此王二说“她的心属于黑夜和狠心的鬼子”。×海鹰的性格被社会异化,她的观念为规则和权力左右,成为主流话语体系下的人物典型。她的精神和行为都是非自由的。再虐恋模式中,揭露的是权力机制对个体精神的束缚和奴役。一方面“x战鹰被摆放在队列的时候,看到对面那些狠心的鬼子就怦然心动,但她没有想到是自己被摆布成阵,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出于别人的摆布”[2],×海鹰在这里一种非自由的状态,而最为可悲的在于,这种非自由的状态不仅来自于社会的控制和奴役,更在于自发去拥护和迎合这种奴役,从这个角度来说,×海鹰已经被文革打磨成典型的时代女性,失去了身体和精神额度双重自由,实际上,正是在虐恋的表达之中,文本彰显出权力与自由,遵守与反抗两组对立关系。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之中,具体阐述了全景敞式主义的规训机制对人的控制,权力无处不在,它渗透入生活的微小层面,发挥作用。而虐恋成为反对权力压制的突破口,对性爱的大胆的露骨的描写,更是人物对非性年代无声的反抗,以虐恋展现当时的社会现实,再多写实的描写之中极具隐喻意味。
隐喻一方面赋予文本深度,同时“丰富、扩大、深化文本的内涵,从某种意义来说,作品是作者从时间中赢取的空间,可以激发读者的联想,无形之中丰富了作品的意蕴”[7]。关于文本中王二的色盲设定,也存在很大的想象空间,一方面我“热爱画画”,“想当画家”,通常来说,画家具有极为敏锐的观察力,拥有对美和真的向往,然而色盲的生理缺陷却导致我“没当成”,色盲实际上隐喻着社会的黑暗,而“我”的愿望成为一个画家,实际上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此类精巧的隐喻在王小波笔下屡见不鲜,在已有的深意中大大丰富了文本的内蕴。
《革命时期的爱情》直面描写文革中革命话语压倒个体声音下的众生百态,另一方面,也使用了众多精巧的隐喻来深化文本,在虐恋中深化人物形象,进一步勾勒出集体无意识下的典型时代产物——×海鹰,讲述在时代对人的同化中,作为个体的沉沦和反抗。
结语
以往对评论家对《革命时期的爱情》的阐释多从其具体文本进行分析,而忽略了《革命时期的爱情》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和创造性,以叙事学理论观照《革命时期的爱情》文本,从叙事声音,叙事语言,叙事文本层层展开,注意到了双重叙事声音下缺乏独立性的个体,以及戏谑反讽的叙事语言之下对历史的真伪的严肃思考,而多处精巧的隐喻进一步的丰富了文章的内蕴。《革命时期的爱情》呈现出的文本复杂性值得当代文坛的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1]布斯.小说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3]黄平.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J].文艺争鸣,2014(09):6-19.
[4]艾晓明.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N].华侨日报,1994-09-25.
[5]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M].汤晨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孙郁.王小波遗墨[J].收获,2010(6):43-49.
[7]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8]方刚.21世纪的两性关系的预测[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9]马汉广.论福柯的启蒙批判[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