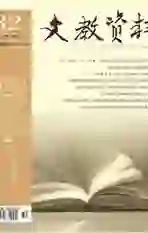论《时与光》中的佛耶思想
2018-03-27李亦岚
李亦岚
摘 要: 《时与光》是徐訏晚年的重要作品。其延续绮丽浪漫的风格,并融合佛耶思想文化意蕴。以佛理来阐发人生的奥义;以基督教作为生命的最终归宿;以书写爱的倏生倏灭,人生偶然与必然的错综复杂,来揭示生命的终极意义,表达对宗教式的永恒极境的神往追寻,传达出徐訏“宇宙和谐”的哲学理念,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价值。
关键词: 徐訏 《时与光》 佛耶融合
《时与光》是徐訏构思二十年,跨越大陆与香港进行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对比他在大陆时期的奇情小说,如《鬼恋》、《风萧萧》等,《时与光》更加强现实人生的关照,哲学的感思,尤其是糅合佛耶思想,使其文化意蕴更为深远博大。《时与光》以跌宕曲折的爱情悲剧为主线,以主人公向宗教的回归为暗线,是徐訏饱经人生沧桑、生死离别后的人生沉淀,是他求解生命真谛,追寻人生理想的思想升华,亦是他作为异乡者,在面对文化隔阂,遭遇精神打击后,转向神性彼岸世界的典型见证。小说主人公郑乃顿在死后升入天国,获得上帝的拯救。而徐訏曾作为宗教怀疑论者,在死前一星期选择皈依天主教,文学与现实互相映照,可见宗教对徐訏的救赎意义与超越现实的价值。
一、“时”是空幻人生的刹那之时
缘起法是佛教的根本教义,“诸法因缘生”,世间诸相都是由因缘和合而起的假相,没有自主性。“它强调宇宙间万物生长都是由各种条件(缘)和合而成的,互相依持,互为因果,因而也都无自体,空无所相”[1]。一通意外打错的电话,使异乡漂泊者郑乃顿卷入陆美娜和尤旁都的爱情游戏中,随后在陆美娜的带领下,步入光怪陆离的香港社会,住进了萨第美娜太太的公寓,结识形形色色的人,引出一系列人生与爱情的际遇。郑乃顿、林明默、罗素娜的感情纠葛在命运的错位安排中起起落落,“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缘起缘灭,万法皆无恒常性,一切事物都在迁流变动。否定爱情、想出家为僧的郑乃顿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初次见面的林明默;天真坦率的罗素娜与郑乃顿心意相通,却因郑对林明默的炙热感情,两人不得不分离;当郑乃顿逐渐正视对罗素娜的感情时,却又在“然偶”室向林明默求婚;当林明默抛却旧情,爱上他时,他却沉浸在对罗素娜的思念中不可自拔。爱情中相好与厌倦如海上泡沫骤生骤灭,让人难以捉摸。佛教缘起论启示世间万法的是无常观。对于执着于情爱,执著于人世的人来说,因无常体会到沮丧无措折射的正是个体生命在因果探寻时对存在的迷茫,“我觉得我爱的竟不是她。时间真是一件无法解说的魔障,它改变了一切色泽与光彩,人间没有永久的爱情,没有纯粹的爱情,没有不变的爱情,人间的爱情一定要在谐和的天时地利人和中存在,其中有因素与机缘,一错一折中,就完全不是我们理想的内容”[2]“生灭”二字包含着生、住、异、灭的含义,即显示着事物的生起、存在、变异和消散。《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露亦如电,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郑乃顿以为剖明心迹,经历种种波折后,便能和罗素娜白头偕老,可暗恋罗素娜的鲁地毫无预兆地出现,用一声短促的枪响直接粉碎了文末的爱情喜剧。一切因缘合和而生的事物都在刹那间生灭,佛教的无常观和宿命观在郑乃顿的人生遭遇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一切看似偶然的表象下潜在着命运的必然:郑乃顿违背不带任何人去看巫女水晶棺的誓言因而不得善终;罗素娜忘记了十八岁以前必须结婚,否则难以长寿的预言,在水晶棺中看不到自己老去的容颜。同样还有林明娜与尤庞都的命运竟与剧本《舞蹈家的拐杖》重合,预述的结构意在揭示人生的空幻如梦。前因后果早已明了,必然与偶然本是一体,诸生法相皆为空虚,只是当局者勘不破谜底。
“由缘起而看到无常,由无常而体认苦难,由体验苦难而求证无我的解说之道,这是佛家教义的一种结构逻辑”[3]。“一切皆苦”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苦”也是佛经提及最多的字眼,而人之所以痛苦在于他的不觉悟,看不透无常,过于“我执”即处于“无明”的状态。“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时与光》分为三部,分别是“传记里的青春”、“舞蹈家的拐杖”以及“巫女的晶櫬”,代表着三个性格各异,年龄不同的女子幻灭的人生之苦。鹤发鸡皮的萨第美娜太太妄想用传记留住青春,她嫉妒自己女儿,叨念着被战火毁掉的照片,时刻计算着过去生活中遗漏的东西,却空置了现在的生命,将后半生白白浪费。陆美娜拥有让人目眩的魅力,执著于眼前的光鲜,相信凭此自己能掌握命运,能自由玩弄爱情,却怎料《舞蹈家的拐杖》一语成谶,一场三角恋引发的车祸使她失去了身为舞蹈家最宝贵的左腿。而在巫女的水晶棺上闪现的是罗素娜葬身海浪、化为烟尘的景象,可当事人见此却仍茫然不解,耽于情爱,怎料情爱一朝如云散,青春之花还未完全绽放便过早凋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目之所见,耳之所听,身之所感都只是暂时的因缘和合。看不透这一点,任妄念扰乱清净心性,贪嗔痴慢疑这五毒也随之而来,陷自身于苦海中,不能自拔。除这三人之外,郑乃顿、林明默、尤旁都、鲁地、方逸傲等众人莫不是在红尘中苦苦挣扎。他们伪称怀疑爱情、厌倦人生,可偏偏正是对此最为执着的人,因而动辄产生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反复咀嚼人生苦味。
而佛法说苦却并不消极悲观,反而珍视人生,肯定人生的价值。关于如何消除苦痛,“大乘佛教认为苦谛当知而不当断,也就是说世人应该知道人生的苦恼与烦忧性,以时时提醒自己,警惕自己,获得人生的无上智慧,不再被生命的假相所遮蔽。”[4]同时积极入世修行,以慈悲之心教化众生,解救他人于苦海之中,“利益众生乃是佛教菩萨行观念的核心所在。”[5]与这群痴男怨女形成对比,《时与光》写到真正快乐自足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帕亭西教授,他将身心奉献给艺术和教育;另一个则是多赛雷,他是个英国人,却皈依了佛门。他曾见证过战争的血腥残酷,看到无数难民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他也参观过剥削童工的纱厂,孩子们悲惨的遭遇同样让他难以释怀。世人的苦海浇灌进他的心胸,他则回之以慈悲宽广的情怀。“只有体验到别人的痛苦,才能忘去自己的痛苦,想到大我的惨遇才会轻视自己小我的惨遇——而人间竟有那么多痛苦值得你想及”[6]。他无私地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孤苦的舞女苏雅;他率先洞察郑乃顿对林明默虚幻的爱,鼓励他放下执念,多写作,踏实地面对生活;他也将饱受失恋折磨的林明默带到Little Food,让她明白在那些落寞无依的人群中,她的痛苦只是沧海一粟。他在印度寺庙里过着简朴的生活,潜心研习佛经,当得知苏雅因他的离开而抑郁,他便回信鼓励苏雅努力寻找新的寄托,如果三个月后,苏雅仍放不下他,他愿放弃修行。多赛雷对苏雅毫无爱恋,此举所凭的仅是佛陀的济世之心。在他看来入不入寺,为不为僧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的淡泊宁静、安详满足。在《时与光》现世的芸芸众生中,也只有多赛雷一人,真正放下烦恼,达到了澄明无染的圆融境界。
二、“光”是照亮迷途的天国圣光
《时与光》采用倒叙的手法,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个幽灵。这个幽魂经过一段波折的人生,跨过情涛爱海,在奇妙的音乐、瑰丽的光和色中重获新生,回归到神的怀抱。在神慈爱、庄严的声音的启示下,他在神面前毫无保留地忏悔哭泣,坦白生命的卑屑污秽,最后在神的恩典下,他的灵魂获得救赎,与宇宙融为一体。原罪说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创造之初,一切都是好的,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却经不住诱惑,偷食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堕落到苦难的人间。他们的子孙后代不仅不能返回伊甸园,而且世世代代都要背负先祖的罪孽,其被污染的本性永远都无法达到原初完善的状态。“原罪说提醒人类最无奈的一面:人的知识、意志与能力之间的无限距离,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应该,我愿意,我却不能够……这是一种向善的无力。”[7]当这个幽魂面对上帝时,他所忏悔的罪不是在俗世中所造的恶业,而是基于对沉沦人生的负罪感,对生命本体残缺的发现,对完备人格、理想精神家园的渴求。定罪并不是上帝的最终意图,赦罪才是定罪的目的。基督教是爱的宗教,上帝是出于爱创造的人类。在《时与光》中上帝的爱是救赎的爱,“上帝对人的看顾与护佑是极其‘个人化的,上帝向一个父亲对子女一样与世上的每一个人建立‘位格式的关系。”[8]在《时与光》中,人与神之间全然是自由对话的关系。神以如父般的爱填补郑乃顿生命的空虚,抚平孤独的创伤,让他的灵魂得到净化、安息。而他也以谦卑的姿态,以彻底的悔悟心来回应上帝的爱。这是“完全的忏悔”,充满对上帝的感恩和灵魂重获新生的释然,而不是出于恐惧上帝的惩罚。
郑乃顿是繁华都市中一只“迷途的羔羊”。他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是彻底的偶然主义者。在三角爱情的漩涡中,他始终纠结在追寻与犹疑、偶然与必然、爱与不爱的人生矛盾的困境中,而爱情并不能为他解疑答惑,反而使他陷于烦愁,死于情杀,直到死后,沐浴在神的光辉下,才使他不安迷茫的灵魂得到平息。郑乃顿的人生经历参照了《圣经》中受难—皈依的叙事模式,《圣经》中约瑟、约拿等使徒都是经过一番人生的打磨,最终经受住了神的考验,得到神的庇佑。在《时与光》中迷途的灵魂渴望得到救赎,回归伊甸园的潜意识一直与他如影随行。人不能直接认识上帝,而上帝可以通过自我启示在任何时间与地域,通过种种方式向人类揭示自己。在《圣经》中托梦及预言是神传达指令的重要方式,如雅格梦见天梯;约瑟梦见众星辰向他下拜等等。书中多次描写郑乃顿的梦境,在梦中,有时他疲乏地倒在路途中,想挣扎着起来却一动也不能动,想极力呼喊却发不出声音。有时是与神通灵的梦境,他听见远处传来教堂的合唱声。那声音呼唤着他,使他不禁加入合唱的声潮,不知疲倦地沿着灿烂星光铺就的大道向天庭走去,感到无法抑制的兴奋与骄傲。他内心对基督教的归属感也体现在与林明默初次见面的场景中。在布置得像教堂一样的音乐厅里,在神圣庄严的基督教乐曲的感染下,闭目冥思的林明默在他眼中被纯化为崇高的女神塑像。他不敢跟名花有主的林明默表白,却对着圣母像诉说“我爱她”。郑乃顿对林明默的爱是宗教式的。与其说他对林明默一见钟情,不如说在那一刻,他被那和谐宁静的宗教氛围所打动,被林明默那对爱情如对宗教般虔诚信仰的姿态所吸引,于是将自己的宗教情感寄托在了林明默身上。因而,当林明默因爱情的背叛失去对爱的虔诚性,展现出她精明世故的真实性格时,她对郑乃顿的吸引力也就日益消退,最终使他意识到自己爱过的不过是幻影而已。与郑乃顿形成对比的是苏雅,她是个孤儿,为了生计沦落为歌女,在多赛雷、林明默等人的帮助下得以离开夜总会,进入电影公司。她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多赛雷。随着多赛雷的离开,她日益消瘦,精神萎靡。可面对无果的爱情,她并未就此沉沦,她抛弃初露星光的锦绣前程,远离庸庸扰扰的都市,选择进入修道院,把整个自己奉献给天主。皈依上帝使她精神焕发,重获新生,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平和与满足。
《圣经》意象也多次出现在《时与光》中。“光”是《圣经》的核心意象之一。神创造万物的第一日便说“要有光”,光破除混沌,区分白昼与黑夜,为生命的出现带来希望。上帝用光给予人力量,启迪人的智慧,驱除内心的黑暗。在《时与光》中神的圣光就展现巨大的威力,以绝对的光耀照进灵魂里污浊的沟渠。在凡间,大量光的意象如:“灯光”、“月光”、“烛光”总是在主人公孤独忧郁的时候出现,安抚他寂寥的心灵。郑乃顿也将不同个性的女子比作不同的光,如陆眉娜热情得像太阳,尤美达娴雅似月光,而神圣的星光,他将其作为理想爱情的信仰,每当他仰望星空时就会想到心中至爱。那一颗星起初代表林明默时总被其他紊乱的星辉遮蔽,当变成罗素娜的象征物后,则明晰地揮洒着光辉。同时,梦中排列成行的星光也让郑乃顿感受到上帝的存在,那是超自然的力量,显示着上帝的临现,其爱情的苦乐总是伴随着神的注视。在变故发生之前,他与罗素娜相拥在甲板上,孕育新生的喜悦与对死亡预言的恐惧交织在一起。百感交集中,郑乃顿回头看到岸边耀目的灯光。这灯光既是船靠岸的信号,也是来自彼岸的光,是神的召唤,是他们生命之光即将熄灭的预兆。可这灯光并不让人害怕,必然的死亡被理解为诗意的回归。另外,《圣经》中水与蛇的象征在《时与光》中也有深刻的诠释。处在两难境地的郑乃顿来到悬崖边,看到石子被湍急的漩涡无声无息地吞没,这让他忽感自身存在的多余,使他忍不住想纵身跳海,结束渺小的生命,可正在此时,他的身后出现了一条大蛇,舞动着从身边游走,这使他顿时惊醒,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可笑。圣经中的启示或意象通常都有两面性,水在《圣经》中是生命之源,象征着新生与净化,而承载着上帝愤怒的洪水则成了惩戒、毁灭人类的工具。而蛇在《圣经》中一般是作为堕落、罪恶的象征,可在《民数记》中,以色列人因路途艰难,埋怨上帝,神便放出火蛇咬死很多人。而当他们开始悔悟了,神便命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使被咬的人见此便能复活。蛇化身警戒者和救赎者,意在点醒世人:违背上帝者必遭重罪,而只要愿意回转,必蒙上帝的拯救。当郑乃顿怀着踌躇的心情走到大海边,汹涌的大海恶魔性地引诱使他欲自我毁灭,而巨蛇的及时出现无疑具有双重启示,一方面警醒他已濒临罪孽的边缘;另一方面又使他从茫然的空虚中挣脱出来,正视自己的人生。
三、泛宗教观:融合在宇宙的爱与和谐
徐訏的《江湖行》中的一段话可作为《时与光》的注解:“假如你爱过,你就会知道爱情在某一刹那就是纯净清澈的。这是一个天堂的境界,但人间不是天堂。天堂有永久的纯净与清澈,人间所能的只是这一刹那而已。”[9]从此岸到达彼岸即是刹那与永恒的距离。纵观徐訏漫漫创作长途,亦是对人生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孜孜追问、反思之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将此岸的爱视为创作的唯一源泉,认为爱情才是青年人的上帝,才是人应皈依的宗教,虽然其间夹杂佛耶思想的灵光,但只是借宗教的外壳书写俗世的爱情。而自南下以来,在现实与精神的双重忧患下,在他晚年的创作中爱情已失去了原初的意义,代替爱的是泛宗教化的对超验的彼岸世界的探求,对绝对理想境界的追寻。《江湖行》、《彼岸》、《时与光》这三部长篇小说中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在经历爱情与人生的幻灭后,从宗教中找到最终的归宿。徐訏对佛经与基督教思想资源的汲取,并不是随意取摘、拼贴,而是糅合在他自身的生命体验中。佛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本身就具有兼容性和互补性。佛教为人生的种种困境与矛盾作出了解释,使徐訏彻悟人生的真谛。而基督教以其宽大慈爱使他漂泊疲乏的灵魂有了可停靠的港湾。
郑乃顿的灵魂最终消逝与宇宙融为一体、了无痕迹,善于哲学思辨的徐訏追求的更是超越宗教的更高境界。徐訏认为佛法是能容纳万物的極境,是超宗教的,任何理论都是佛的理论,佛教华严宗“一中多”、“多中一”的万物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思想与徐訏开放的宇宙观是极为契合的。“宗教不过是一种境界,这无法解说也无法理明,使空净的心灵与整个的宇宙吻合,这就是神的境界,神使万多,神是独一,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全人类无数的灵魂,在神的境界中就融为一体。”[10],在这种贯通融合的境界中,上帝的形象也不仅仅只是宗教意义上的神本身,而是成为了代表整个宇宙圆满和谐的终极理想。“人世融合在宇宙里面,爱者融合在被爱者里面,整个的谐和就是爱的融合;人与人间没有分隔,上帝与人世完全吻合。这就是整个宇宙浑成一片的境界,这就是自然也是上帝。”[11]基督教教义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凌驾于自然与宇宙之上。而在此,上帝与自然、宇宙合而为一,徐訏显然还受到了泛神论的思想,显示神秘主义倾向,提出了“宇宙和谐”的新信仰。坚持纯文学的创作态度,坚持对人生终极价值、对形而上超越意义的执着探寻,并融入佛耶深刻的文化精神,其思想与艺术上的异质性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别开生路,创造出瑰丽的文学之花。
参考文献:
[1][4][5]谭桂林.百年宗教与文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141,153.
[2][6]徐訏.时与光.徐訏全集第3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25,87.
[3]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13.
[7]林季杉.论基督教“原罪说”的圣经起源及现代意义[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5(3)..
[8]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8.
[9]徐訏.江湖行.徐訏全集第2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24.
[10]徐訏.幻觉.徐訏全集第6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71.
[11]徐訏.彼岸.徐訏全集第5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