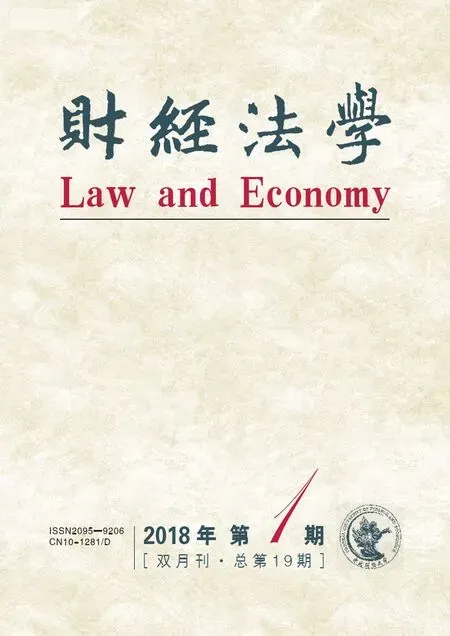解释论视角下保险标的转让规范的检讨与完善
——以《保险法》第49条为分析对象
2018-03-26蔡大顺
蔡大顺
一、问题的提出
保险合同属长期性合同,在其有效存续期间内,保险标的难免会发生变动,造成法律关系的不稳定。两大法系的保险法皆对此一议题有所规定[注]See Edwin W.Patterson,The Transfer of Insured Property in German and in American Law,Columbia Law Review,1929,Vol.29,No.6.,我国《保险法》第49条亦对保险标的转让做了专门规定,以保障保险法律关系的稳定。但囿于我国《保险法》系大陆法与英美法的融合物,而两大法系在保险法理上存有差异,因此我国《保险法》规范中存在诸多相互矛盾之处。《保险法》第49条所规定的保险标的转让制度亦存有龉龃之处。然学界却欠缺对此法规范文本的深度阐述,尤其是基础理论部分的阐述,实属遗憾。
第49条第1、2款系围绕保险标的转让制度的具体构成要素展开,但现行法规定得不够清晰,实务争议较多。主要存在的焦点有:首先,保险标的是指保险利益还是保险标的物?其与相关概念间有何关联?两大法系对保险标的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然我国《保险法》之规定融合了两大法系,因而在解释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时会产生概念界定上的矛盾与冲突。其次,我国《保险法》所规定的保险标的转让时的通知义务,其性质为何?此外,还有些细小问题,如保险标的转让的主体为谁;如何界定保险标的转让之时点,是否即时生效;我国《保险法》并未明确规定保险标的转让后,受让人享有何种权利,承担何种义务,保险人的权益如何保障,保费如何缴付。发达国家的保险立法多对此问题明确规定以杜绝争议。未来修法时,《保险法》应对这些问题做清晰规范,以便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第49条第3、4款之规定旨在阐明保险标的转让后之法律责任,但该规定仍存在较大问题。其一为保险标的转让,保险人无须行使同意权,保险合同自动变更。有学者认为此系风险控制模式已从事前模式转向事后模式,但结合保险法制发达国家的保险立法来看,我国《保险法》所规定的事后控制模式并不完整,保险人终止保险契约的权利系以危险增加为前提。如此规定是否合理?此外,第3款所规定的通知义务与第52条危险增加后的通知义务功能相同,学者认为可以合并研究。[注]参见王静:“保险合同中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人民司法》2015年15期,第90页。因此,违反转让后的通知义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可套用危险增加时通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如此是否意味着此处通知义务的规定属多余立法,可予以删除?如有法院认为,投保人未履行转让后通知义务的,被告保险公司拒赔是附有严格条件的,即只有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才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注]参见“杨彬诉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坡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九法民初字第03740号。如此,对保险人而言似乎过于苛刻,保险人利益保护机制有所欠缺,如何完善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保险标的转让的构成要件分析:第49条第1、2款之规定为中心
(一)保险标的的内涵厘清:兼议保险标的物、保险契约标的与保险利益
我国《保险法》第49条调整的对象是“保险标的”。然反观英美保险法学者在论及保险领域内的转让时,多认为保险司法实践中因转让(Assignment)滋生的问题,总的来说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一为保险标的物(the insured of the subject matter)的转让导致保险合同效力问题;二为保险合同利益(the benefit of a contract of insurance)的转移;三为保单自身的转让(the assignment of a contract of insurance itself)。[注]See John Birds,Birds’ Modern Insurance Law (10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2016,p.195.上述三种转让问题,相互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我国法语境下的保险标的是否属于上述之一,抑或是上述类型之外的其他类型,针对此问题,我国学者对保险标的的内涵做了些零散的研究,存有较大分歧。有鉴于学术分歧,本文尝试对保险标的与相近之概念做比较分析,以期获得保险标的内涵的正确认知。
1.保险标的为保险标的物说
保险标的为保险标的物说,即认为保险标的系保险利益所依存之物或人身。此观点多为英美法学术背景学者所采。如郑玉波教授认为,保险标的就是保险对象的经济上的财货(财产保险)或自然人(人身保险),也就是保险事故发生所在的本体。其中,财产保险系以经济上的财货为标的,而所谓经济上的财货,指具有经济价值的财货而言。若以有体物为保险标的时,法律上特称之为“保险标的物”。[注]参见郑玉波:《保险法论》(第8版),刘宗荣修订,三民书局2010年版,第20页。我国保险法学界[注]参见樊启荣:《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韩长印、韩永强:《保险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陈欣:《保险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马宁主编:《保险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与实务界[注]参见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325页。亦是多采此观点。
一般而言,我国《合同法》及司法解释中所说的合同标的,时常需要按照标的物理解。[注]参见崔建远:《合同法学》,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54页。就《保险法》之具体规定而言,我国《保险法》上关于保险标的转让的规定系源自于1983年《财产保险合同条例》,该条例第11条使用了诸如“过户”、“转让”或者“出售”等词语,从中可以得知我国《保险法》系将保险标的的内涵等同于保险标的物。我国立法机关对此条文的解读,系将此处的保险标的解释为保险标的物(保险标的的财产)。[注]参见“保险法法律释义与问答”,载http://www.npc.gov.cn/npc/flsyywd/jingji/2004-10/21/content_337769.htm,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4月8日。
此外,就我国现行法之规定而言,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亦属不同。《保险法》第12条对保险利益做了立法解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从该立法解释可知,保险利益系依附于保险标的之上。两者应该系属不同之物。此外,我国《保险法》第48条将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规定于同一规范之内,再次表明了我国法上的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并非同一。
2.保险标的为保险利益说
德国法认为保险标的系保险利益。如江朝国教授认为,保险标的系指保险制度之标的,而非保险契约所指向的标的。前者系就制度本身而言,后者则系指具体的法律关系。[注]参见温世扬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页。保险制度所欲保护者应为被保险人对某特定客体之利害关系。此利害关系之连接对象为保险标的物。因此,保险标的实为保险利益。[注]参见江朝国:《保险法逐条释义》(第三卷 财产保险),台湾元照出版社2015年版,第562页;上注,温世扬书,第65页。学界应该严格区分保险契约标的与保险标的,有关保险契约标的,下文将做进一步论述。
3.保险标的与保险契约标的
有学者认为,保险利益则为保险契约之对象。[注]参见袁宗蔚:《保险学——危险与保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因此,有学者认为保险契约标的系保险利益。[注]参见前注〔5〕,郑玉波书,第47页。一般而言,合同标的系指合同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多认为系指给付行为。因此,保险契约标的系指保险人的给付(保险金给付)与要保人的给付行为(保费交付),主要是指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而保险标的如前所述,乃保险这一法律制度之标的。故两者间存有较大差异,不应混淆。
因此,转让保险契约标的多系指转让保险金请求权(给付行为),被保险人在不转让保险标的的情形之下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受让人不需要对保险标的物拥有保险标的,保险合同本身也不会因保险合同利益的转让而有所改变。[注]参见〔英〕克拉克:《保险合同法》,何美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4.本文小结
保险标的物,不限于有体物,还包括无形之权利、利益,其为保险利益存在之本体,在概念上类似于德国法上之“关系连接物”,至于保险标的,则为保险制度之标的,即保险所欲保护之对象,为被保险人与特定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保险利益乃特定人对某一客体所具有经济上之利害关系,因有此种关系之存在而保有利益,亦因此关系遭毁损而遭受损害。保险法这一制度之根本目的旨在保护上述这种利益关系不受破坏。
(二)保险标的转让之性质界定
保险标的转让,有法官认为可依据《合同法》第80条“债权让与”的规定进行裁断。[注]参见贾林青主编:《法院审理保险案件观点集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270页。学界亦有对此持肯定见解,其认为《保险法》第49条之规定属保险合同的让与。[注]参见马宁主编:《保险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根据合同主体变更的法理,可知合同主体变更的类型细分为三种,债权让与、债务承担与债权债务的概括转移。债权让与应与合同承担相区别。在合同承担中,原债权人不仅将孤立的债权让与给了新债权人,而且让与其整个合同的地位。也就是说,它导致合同当事人的完全变换。此一情形之下,新债权人承担的不仅是债权,还包括了原债权人的给付义务,因此在债权人更换外同时还发生了债务人的更换。
然本文保险法上标的转让是保险合同当事人的一方,依法将其所享有的合同权利和负担的合同义务,全部或部分地让与给第三人的行为。[注]参见前注〔10〕,温世扬书,第140页。详言之,保险标的的受让人在取代原来的被保险人之后,应当承担的义务有: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德国法称之为风险维持义务)、危险增加时的通知义务、事故发生后的减损义务。其所享有的权利主要为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金即付请求权。[注]参见刘建勋:《新保险法经典、疑难案例精解》,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17页。有关于此,德国法亦是采此说。该国《保险合同法》第95(1)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受让人取得投保人在保险合同项下所享有的权利及应承担之义务。[注]§95(1)Wird die versicherte Sache vom Versicherungsnehmer veräußert,tritt an dessen Stelle der Erwerber in die während der Dauer seines Eigentums aus dem Versicherungsverhältnis sich ergebenden Rechte und Pflichtendes Versicherungsnehmers ein.因此,采债法上之合同概括承受说相对较为合理。
然而英美法学者认为,任何变更合同的努力实际上都是在创设另一个合同。[注]参见〔美〕杰弗里·费里尔、迈克尔·纳文:《美国合同法精解》,陈彦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0页。当保险标的转让时,保险标的所指向的标的物的转让导致保险财产合同的转让,保险契约的双方主体“自然转换”。受让人成为被保险人,而转让人是退出人,这种变化被描述为债务的更新。[注]参见前注〔14〕,克拉克书,第172页。详言之,保险人一方并未转换,只有被保险人的身份发生了转换,由受让人继受了被保险人的身份。这种保险契约当事人的更换为保险契约的变更,此将一切保单之利益及权利,完全归另一人所享有,在法律立场上无异于另订一新的保险契约。[注]参见王卫耻:《实用保险法》,文笙书局1991年版,第142页。此一认识即为英美法所采之认识,英美合同法上系认为其属合同更新(Novation)。英美法学者的“合同更新说”实则进一步证明了保险标的之转让系属合同的概括承受而非权利转让。
然亦有部分英美合同法学者认为,合同更新与合同转让系有区别,合同更新获得了债权人、债务人与第三人的一致同意。在普通法(common law)不承认转让效力的时代,合同更新制度发挥了转让的部分功能。合同更新系指债务人所负之债(the debt)自此以后移转于第三人。[注]See G.H.Treitel,Treitel on the Law of Contract (11th Ed),Sweet & Maxwell,2003. pp.672~673.而英美合同法上转让的对象是合同权利(contractual rights),其生效无须获得债权人的同意。[注]See Anson,Anson’s law of contract (29th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661.因此,转让仅仅系指我国法上的债权让与,而非概括承受。而英美法上的合同更新制度,则包括了合同的债权(the benefit)让与,亦含有债务(burden)承担。[注]同上,第676页;何宝玉:《英国法研究三部曲:合同法原理与判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因此,可以说合同更新与我国法上合同的概括承受更为相近。
综上,保险契约中,被保险人实则系集权利与义务于一身之人。被保险人在移转保险金请求权时,天然地将风险维持义务转移于受让人。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其移转的不仅仅是权利,还包含义务。故保险标的转让,在性质上应为合同的概括承受而非仅仅为债权让与。
(三)保险标的转让之主体辩明
我国《保险法》第49条并未清楚地点明保险标的转让系由何一主体实施,法律规定得语焉不详。我国保险法制主要系承袭德国法之体制,保险契约系由三方主体构成,即要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而非如英美法系之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两方主体。因此,我国法上保险标的转让究竟系由要保人为之抑或是被保险人为之,存有疑问,殊值探讨。
我国法承袭德国法之规定,要保人与保险人为保险契约之当事人。要保人以自己名义缔结保险契约成为契约当事人,然其仅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被保险人则依据保险人和要保人所订立之保险契约,成为保险利益依附的主体。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受有损害,有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
1.德国与日本法之规定
德国《保险合同法》第95条规定,投保人转让保险标的,受让人取得投保人在拥有所有权期间内基于保险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因此,德国法系认为保险标的转让的主体为投保人。
日本在保险单独立法之前,其《商法典》第650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系保险标的让与之主体。2008年《保险法》专门制定,保险法典并未对此问题有明确约定。因此,可以认为2008年《保险法》对此并未有所改变。在原为自己利益保险之情况下,保险标的之转让使得保险契约变成他人利益契约,此时,受让人仅系取代了原被保险人之地位。韩国法亦采被保险人为转让主体,韩国《商法典》第679条第1款规定,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时,推定受让人承继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
2.本文观点
“利之所在,损之所归”。保险标的与被保险人紧密相连。要保人在保险契约关系中,其仅仅为一负有缴纳保费义务之人,而被保险人才是保险利益依存的权利主体。因此,只有被保险人有权利转让保险标的。
实践中要保人常与被保险人不一致,此时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时,要保人之地位如何变化,则存有争议。要保人可以为他人为被保险人投保,其只是保险契约的当事人,被保险人的变更,并不影响要保人在原保险契约中的地位,而对保险人而言,其仅能向要保人主张权利义务,对象十分确定。至于要保人与受让人或被保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则与保险契约无关。对要保人而言,其对保险标的物既无利害关系,却课其以义务,未免太过于苛刻,更为重要的是若因要保人之行为导致危险增加或未为约定义务,保险人得终止或解除保险契约,此对受让人亦属不公。
若要保人与被保险人一致时,保险标的转让,受让人会成为被保险人,亦会成为要保人。然原保险契约,要保人系为他人(被保险人)利益保险,在订约时要保人与被保险人间必定会具有某种利害关系,要保人方会自愿负担一定的义务而由他人享有权利。然若此被保险人发生变更,受让人(新被保险人)与要保人间是否仍有某种利害关系,则实属不确定。此时就要保人之内心真意而言,其极有可能不愿再负担义务,而由受让人享有权利。因此,这种情形之下,要保人之地位理应有所变化。
德国《保险合同法》明文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受让人与要保人负连带义务,其已间接赋予了要保人脱离保险契约关系的潜在可能,即让受让人取代要保人之地位,变为为自己利益投保之保险契约。未来我国《保险法》修改时,亦应做如此完善,方能维护要保人的权益。
(四)保险标的转让之时点辨析
由于动产买卖一般都是即时性的交易,所有权移转与危险负担转移之时点多属一致,现实争议较少。保险标的转让时点认定困难多出现在不动产交易之中。依据物权法之规定,不动产所有权之转让需履行登记程序。由于不动产买卖合同之签订与不动产登记之间存在着时间差,假如在这时间差之内发生了保险事故,保险赔偿是应给付于买受人还是出卖人(所有权人),存在学理上的争议。
1.英美法系之观点
(1)美国法之观点
早期美国保险实务界遵守着“布劳内尔规则”(Brownell Rule)[注]See Jeffrey W.Stempel,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 (Fourth Edition),LexisNexis,2011,p.642.。该规则系由1925年纽约州Brownell v.Board of Education[注]See N.Y.369,146N.E.630 (1925).案衍生而来,其核心观点为买受人不能从出卖人个人属性的保险契约中获得任何法律利益。近些年来,有些法院采取了不同见解,如Acree案中,法官认为买受人对转让财产享有衡平法上的利益,买受人对保险财产享有保险利益,故保险事故发生时,买受人可以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金赔偿。即使如此,时至今日,布劳内尔规则仍在美国部分州的司法实践中获得支持。如Whitley案中,法官认为,买受人若能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赔偿可能构成不当得利(unjust enrichment)。亦有部分法官采折中做法,如Berlier案,出卖人为保险财产投保支付了保费,事后发生保险事故,买受人可以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赔偿,但应扣除部分买受人的保险金以抵消(offset)出卖人所支付的保费。
(2)英国法之区别说:责任保险例外
早期英国司法实务界认为,对于转让财产,买受人支付完价金,并且成功转让才享有保险利益,否则不得主张保险赔偿。[注]See Collingridge v Corporation of Royal Exchange Assurance Association,(1877) 37 LT 525.随着学界认识的不断演进,此一严苛观点已逐渐得到缓和,如今学界多认为不动产的买受人基于买卖合同,对转让的财产享有保险利益。[注]See Lowry,Rawlings and Merkin,Insurance Law: Doctrines and Principles,Hart Publications,2011,p.297.保险标的物的转让并不必然导致保险合同的转让。出卖人对不动产保有法律上权利,而买受人享有衡平法上的利益(equitable interest),因此,双方都是被保险人。[注]See John Birds,Birds’ Modern Insurance Law (10th Edition),Sweet & Maxwell,2016,p.195.
1881年Rayner v.Preston案中,出卖人P将不动产卖于买受人R,P所购买的保险并未随之转移,自买卖合同签订时,不动产的风险即归于买受人R,P从R处获得全部的转让价金。在这期间,发生保险事故,P依据其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获得了保险赔偿,后R起诉至法院,认为随着保险财产的转让,保险合同利益亦应随之转让。上诉法院否决了R的主张。法院认为,不动产上的保险契约只是不动产转让的附属(collateral),当事人之间并无明确的保险契约转让之约定,不可剥夺P的保险金请求权。尽管P获得了两次价金(转让价与保险金),但其仍负有返还保险金的义务(保险代位)。
为缓和此案的严苛后果,1989年后英国的法律委员会倡导对保险转让制度进行改革完善。在某些特殊的物之转让情形中,保单明确约定一旦出卖人转让标的物,保单则自动失效。但该制度适用范围较小,仅限于保单对保险标的物做了明确约定。英美学者认为最佳的制度安排应该是,出卖人与买受人皆为被保险人,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应赔付出卖人应获转让价金的剩余部分,应赔付买受人已支付之价金部分。
一般来说,买卖不动产时,出卖人随着交易的完成,保险标的上的保险利益随之消失,即失去了保险保障。即使出卖人主张依据1979年《货物买卖法》第39条之规定主张其仍享有留置权(lien),但上诉法院仍坚持认为出卖人之保险已自动消失(lapse automatically)。[注]同上,第197页。但这一规则似并不适用于责任保险领域。如早期Boss案中,被保险人就指定的摩托车投保了责任保险,并于保单中明确约定了所保摩托车的属性。后将该摩托车转让。某天被保险人驾驶他人的摩托车,被治安官控诉其无车辆责任险,属危险驾驶行为。地方法院认为,第三人责任险并不依附于任何财产本身,其并不会随着保险标的的转让而自动消失。然即使如此,保险人仍可主张依据保单中的条件(conditions)约款主张免于给付保险金。
最新的Dodson案中,法院认为三责险中,保险标的物转让,但被保险人的保险并不随之自动消失,因为责任保险保障的对象系被保险人的不利状态,此不利关系独立于保险标的物。这一认识已形成学界共识,并为大部分条款保单所确认。英国法所采之区别说,亦可参见我国澳门地区“商法典”第1012条之规定。
2.本文见解:风险负担说
依据《物权法》第9条之规定,不动产买卖需践行多个程序方能完全实现,如价金的交付、不动产的交付以及所有权移转的登记。仅有当事人意思尚不足以产生物权取得和设立效力,只有经过登记才产生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与废止效力。[注]参见高富平:《物权法原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87页。这些手续可能分散于不同时间点完成,假如此时不动产之所有权虽未完成登记,但不动产已交付于买受人。此时,不动产(保险标的物)的实质危险已移转由买受人负担,若发生保险事故,将会出现买受人需承担损失,而出卖人仍为被保险人的不合理现象。因此,若坚持以物权法之所有权移转规定界定保险标的移转之风险,恐造成实质受有损害之人将会无法得到保险保障而形式上所有权人却可获得双重利益(转让之价金与保险金)之吊诡现象。
利益之所在即危险之所在,当标的物进入一个人的事实管领下时,他才可能去使用收益。接着,谁来用益就由谁来负担风险,如此才能公平。[注]参见余延满:《货物所有权的移转与风险负担的比较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页。若买受人已实际占有保险标的物,交由其实际控制风险具有优势,其应该是危险的最佳分担者。学理称之为交付主义原则,即以货物的交付为转移风险的时间标准,而不论所有权是否已经转移。[注]同上,第316页。依据《合同法》第142条之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依标的物交付而转移,即在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关于不动产的风险规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第11条第2款之规定,房屋毁损灭失的风险,在交付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后由买受人承担。此外,在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的买卖中,风险也自标的物交付时转移给买受人。因此,“所有权转移说”只注重物权法形式上之所有权存在问题,而忽略了经济上直接之受害者,有违保险损失补偿之本质,实属不可采。
简言之,无论是动产抑或是不动产,若保险标的物已交付,保险利益即发生移转,随之风险业已发生移转。此时,保险应补偿实际受有损失之人,即危险实际承担之人——受让人。
三、保险标的转让后的法律效力:第49条第3、4款之规定为中心
(一)保险人的权利与义务
1.立法演变:保险人同意权的废弃
2009年《保险法》第49条第1款废除1995年《保险法》第34条所规定的保险人同意权,在保险标的转让时,保险人并无同意权规则的限制,保险合同因保险标的的转让自动转让。为何我国《保险法》废除了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人的同意权?立法机关解释为系出于如此规定并不违背保险精算原则,且最大限度维护受让人之权利,避免空窗期的出现。[注]参见前注〔7〕,奚晓明书,第326页。多数学者认为,立法的转变系从属人主义转向从物主义,乃立法进步。
然本文认为,立法的转变有失偏颇。保险契约是一种属人契约,一般保险契约不得任意转让,除非获得保险人的同意。尤其是财产保险契约通常不能转让,因为被保财物之安危容易受被保人之特质而影响。[注]参见陈彩稚:《保险学》(增订二版),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67页。故保险契约中多约定,保险标的物除被保险人死亡以外之原因移转时,除经保险公司以批单载明同意继续承保外,本保险契约于保险标的物移转时失其效力。此项规定,旨在使保险人得以重新评估危险,并选择是否继续承保或变更承保条件。[注]参见陈云中:《保险学要义》(修订9版),三民书局2011年版,第197页。我国保险法之规定对保险人过于苛刻,是对保险契约属人性的完全背离,未来修法仍应做出相应的补救与完善,应赋予保险人无条件终止权。
2.应赋予保险人对保险契约的无条件终止权
(1)现行法以危险增加作为前置要件:与第52条之规定重复,叠床架屋
现在的《保险法》规定保险人的契约解除权系以危险增加为前置条件,如此规定是否合理?现行《保险法》第49条之规定,主要系考量保险标的之转让可能造成保险标的风险之变动,因此规定保险标的转让时,保险人或受让人应及时通知保险人,而保险人亦得据此评估是否调整保费或解除保险契约。[注]参见林勋发:“2009年保险法修正评析”,《铭传大学法学论丛》2012年第18卷,第57页。但若确实因保险标的之受让人造成保险人承担危险之成本增加,保险人可依据《保险法》第52条有关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规定增加保费或解除保险契约。故此处保险人的解除权之行使以危险增加作为前置要件,实无必要,且与《保险法》第52条之规定构成重复立法。
若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显著增加,此时,保险契约关系即进入《保险法》第52条的“统摄”范畴,保险人可援引该条之规定主张合法权益。《保险法》第49条的立法宗旨系规制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人与受让人的权利义务,平衡保险人的危险控制需求与被保险人的权益维护需求,而危险增加显然非属其规制重点。因此,以危险增加作为其前置性要件,与第52条之规定重复,显非合理,理应修正。
(2)肯定保险人的契约无条件终止权:属人性与被保险人权益保护的再平衡
早期保险法学说认为因为保险契约的属人性,即特别注重当事人间的关系,其权利义务不得任意移转。盖个人之道德水准不一,甚有可能因要保人之转换而提高主观危险,或产生保费给付能力之变动。因此,保险人对保险标的转让之事实,实有正当之利益。[注]参见江朝国:《保险法逐条释义》(第一卷 总则),台湾元照出版社2012年版,第583页。
然而随着现实市场交易的频繁,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实务上,货物运送过程中可能不断发生保险标的让与以及保险契约效力移转之需求,因此保险契约的属人性逐渐淡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保险契约的属人性已被废弃,究其根本而言,保险契约的属人性旨在实现保险人对危险的合理评估,维持对价平衡原则,进而保证保险业的正常运营。因此,时至今日,我们的保险法仍应重视保险人对危险的科学管控。
就债务转让视角而言,保险标的转让时,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亦随着移转。依据合同法上债务转让规则,债务转让应该获得债权人的同意。保险法为避免空窗期的出现,强制规定了当然生效规则,但保险法还是应赋予保险人权利以调整保险契约。义务转让的,作为相对人的保险人还是应该有一定的权利以做应对,若有违对价平衡原则或受让人个人危险性因素较高的,保险人可以行使终止权,终止危险已变更的保险合同,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权益。
在当然继受模式之下,保险人并不能左右保险契约转让之效力。保险契约变动之效力全由转让人与受让人决定,且由于保险标的转让,使得原契约主体发生变动,让与人脱离了契约关系。因契约主体变动,依据契约自由原则,若保险人不希望原契约继续存在,应赋予保险人及受让人终止契约之权利。但若考虑受让人之利益,于保险人行使终止权时,应给付受让人一定的“缓冲期”,即应提前一段期间告知,让其有机会重新签订契约。此外,为避免法律关系不稳定,对于保险人的终止权,应规定一定的行使期间,即应有除斥期间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人的契约终止权系保险人实现危险控制,维持对价平衡原则的有效手段。事后终止权取代事前同意,有效避免了“空窗期”的出现,符合保险消费者保护的时代潮流。但我国《保险法》以危险增加作为终止权的前提要件,如此立法不甚合理,一方面,对保险人而言过于苛刻,完全背离了保险契约的属人性特征,无法实现有效的危险控制;另一方面,如此立法与《保险法》第52条危险增加条款构成重复立法,造成体系上的紊乱。因此,本文建议,废除危险增加的前置性要件,肯认保险人的无条件契约终止权,确保与《保险法》第52条的体系协调,实现受让人(被保险人)权益与保险人利益的再平衡。
(二)受让人的义务
1.通知义务
《保险法》第49条第2款规定了转让人的通知义务,并未明确受让人是否负有该通知义务。本文认为,受让人与转让人负有通知义务。通知义务,其所强调的是该义务的履行是相对人行使某种权利的前提,这使得通知义务更为强调义务履行的程序性。《保险法》第49条所涉之通知义务,其履行与否并非保险标的转让行为有效的构成要件。在学理上可参照债权让与时通知义务的界定,其与危险增加时通知义务有所区别。危险增加时通知义务系以危险增加为其前提要件,而此处的通知义务系由于保险标的变动所引发,保险标的转让并非一定导致危险增加,其更多的属于程序性规定,并无实质性(危险增加)要素的前提要求。
(1)“通知”行为的准法律行为属性
在法律交往中,存在着各种类型的通知,其都属于法律效果的事实构成。这些通知,均有一定的外在表示行为,且基于其表现而发生法律效果。因此,学理上称为准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通常有三种表现形式,即意思通知、观念通知与感情表示。若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以通知的方法请求另一方在某一期限内进行作为或不作为,并且对违反要求的行为以不利相威胁,或某人宣告自己将采取某种行动,这就是意思通知。然若当事人针对某一事实,特别是针对过去或未来发生的时间发出告知,人们将这一告知称为观念通知。[注]参见〔德〕弗卢梅:《法律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保险标的转让的通知行为属于上述何种类型的通知?
我国《保险法》第49条所规定的通知行为,其效果应准用意思表示的发出、到达规则。就通知行为的方式而言,英国法要求转让人以书面形式(written notice)告知债务人。[注]See M.P.Furmston,Cheshire,Fifoot and Furmston’s Law of Contract (16th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646.但就我国法制规定而言,《合同法》第80条并未对此做出要求,《保险法》第51条亦未做强制性要求。但就该通知的内容应该予以明确,即通知必须是清楚的,使债务人理解债权人已将债权转让给了第三人。通知中所包含的信息足以使承保人很明确地知道自己应该向谁支付根据保险合同应支付的保险金。[注]参见前注〔14〕,克拉克书,第176页。
结合上述学理认知,保险标的转让后的通知系告知债务人该债权已自原债权人让与给受让人之事实,而非使债权让与发生效力之意思表示。[注]参见常鹏翱:《事实行为的基础理论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因此,本文认为保险法上的通知行为属于准法律行为项下的观念通知(事实通知)。
(2)通知义务之性质:附随义务抑或是不真正义务
附随义务是随着债务关系的发展,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于个别情况下要求一方当事人作为的义务,以维护相对人的利益的义务。如债权让与之通知义务、买卖时通知义务,这些义务与主给付义务密切相关,故其本质上均应为从义务。[注]参见姚志明:《诚信原则与附随义务之研究》,台湾元照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我国《合同法》第60条第2款对附随义务做了规定,并具体规定了诸如保护义务、照顾义务、通知义务等义务类型。此外,司法实践中多认为《合同法》第80条所规定的债权让与时应履行通知义务,债权转让通知义务未及时履行只是使债务人享有对抗受让人的抗辩权,它并不影响债权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12期(总110期);“佛山市顺德区太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广东中鼎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民二终字第212号。因此,有学者认为《保险法》第49条之通知义务应系属该附随义务中的通知义务。
本文认为,义务内容与义务性质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合同法将通知义务界定为附随义务的典型形态之一,其强调的是附随义务的内容典型地表现为这些形式的作为或不作为,然并不能推导出以这些形式作为或不作为内容的义务,在性质上就一定是附随义务。[注]参见王文胜:“附随义务研究——以债务关系上义务群之合理化为目标”,清华大学2013年法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15页。如何正确界定通知义务的性质,还应结合具体的场景讨论。
我国《保险法》第49条第4款规定,被保险人若未履行通知义务,其法律后果是保险人就危险增加部分导致的损失不予赔偿。换言之,违反该通知义务系让受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受到部分减损而非全部消失。然若将此处的通知义务界定为附随义务,则依据附随义务的相关原理,其法律责任形式可以为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注]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0页。此时,被保险人自身不仅遭受财产损失,还应担负损害赔偿之责,如此规定显然与保险之本质相违背。
当被保险人违反此处的通知义务,后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的行为实际上对保险事故的发生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过错,如因怠于通知,保险人错失有效事前管控后发生损失,被保险人之行为应属于民法之与有过失。依据德国学者的见解,与有过失的阶层结构有三:事实构成、不真正义务之违反以及过错。[注]参见〔德〕埃尔温·多伊奇、汉斯·于尔根·阿伦斯:《德国侵权法——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及痛苦抚慰金》(第5版),叶名怡、温大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因此,可以说与有过失的构成要件之一为不真正义务的违反。此处所谓的不真正义务,具有同义务一样的结构,但法律赋予不真正义务人自由,是否注意行为要求,根据共同过失规则,受害人是否采取保护其法益或利益的必要措施,是其自己的事,违反该不真正义务,其需要承担减少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不利益。[注]参见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9页。
因此,保险法上的通知义务应为不真正义务。违反通知义务构成与有过失,其法律后果为权利人的权益遭到相应程度的减损。
2.保险契约的终止权
受让人取代转让人成为保险契约的新被保险人,依据契约自由原则,是否应该赋予其契约相对人选择的自由?本文认为,应赋予新被保险人以终止权,让其自由决定由谁承保其风险。每个被保险人的具体情况不尽一致,其有权选择最为适合自己的保险公司。保险交易属于长期交易,(被保险人)基于承保人的履历和明显的偿债能力谨慎地选择承保人。[注]参见前注〔14〕,克拉克书,第174页。保险合同是否“存续”应取决于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因此,赋予受让人以契约终止权,是契约自由原则的内在要求。当事人有权决定选择何人作为交易伙伴,决定与何人缔结合同。基于此,受让人有权终止转让人与保险人的原保险契约,选择适合自己的新的保险人,缔结一份适合自己的新保险合同。
依据《保险法》第15条之规定,要保人可任意解除保险合同。保险标的转让后,受让人称为要保人,其可任意行使契约解除权。关于受让人的任意终止权,德国《保险合同法》第96条做了明确规定,保险标的受让人有权终止保险合同。因此,无论是基于契约自由抑或是保险法上的要保人任意解除权,保险标的的受让人都享有转让后的契约终止权,赋予受让人重新选择保险人的权利。
另就民法原理而言,终止权属形成权,是可依照权利人单方意思表示即可生效从而改变相应法律关系的权利。为维持法律关系的稳定,应要求受让人在一定期间内行使,即法律上应规定除斥期间。
3.保费缴付的连带义务
我国《保险法》第49条并未明确规定保险标的转让后保费如何缴付,然此一问题实则攸关保险契约能否继续存续。随着保险标的转让,受让人成为被保险人,然此时要保人因其与新被保险人间欠缺相关的利益联系,主张脱离保险契约关系,基于情势变更原则,法律应准许其从保险契约中脱离,不再作为保险契约的要保人。但基于保费不可分原则,在保险契约的有效存续期间,让与人亦应与受让人负连带的保费缴付义务。
如前文所述,保险标的转让,不仅转让债权(保险金请求权等权利),亦是债务(风险维持义务等义务)的转让。因此,当要保人脱离保险契约时,受让人即一体承受要保人与被保险人之权利义务,理应承担交付保费的义务。然若允许要保人脱离保险契约,在其未脱离契约之前,其为保险契约的当事人,应承担给付保险费的义务。此时,受让人是否需要承担缴付保费的义务,则有待进一步研究。因为依据保险法学理的见解,要保人为交付保费的义务人,受让人称为保险契约的新的被保险人,其并非为交付保费的义务人。然如此规定,则势必会影响保险人的权益,进而破坏保险制度的团体性,不利于整个保险体系的有效运作。对此,德国《保险合同法》第95条第2项规定,在投保人将保险标的转让给受让人的过程中,对于应支付之保险费,投保人与受让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注]§95(2)Der Veräußerer und der Erwerber haften für die Prämie,die auf die zur Zeit des Eintrittes des Erwerbers laufende Versicherungsperiode entfällt,als Gesamtschuldner.如此未来修法之时,可借鉴德国法之经验。
四、结论
保险标的转让制度,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皆为保险法领域一重要议题,实务争议频发。我国《保险法》第49条立法的滞后与不完善无法为保险标的转让所引发的问题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亟待修订与完善。详言之,首先,就其内部构成的学理而言,保险标的转让的对象为保险利益而非保险标的物,保险标的转让的性质应为债法上的概括承受而非仅仅为债权让与,转让的主体为被保险人,转让的时点应以风险负担说作为判断依据;其次,就其法律责任而言,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对保险人过于苛刻,有违保险的属人性,未来修法时应赋予保险人转让后的无条件终止权以做补充完善,应规定转让人与受让人缴付保费的连带义务,被保险人应负担通知义务,此义务性质为不真正义务,法律责任应围绕不真正义务之违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