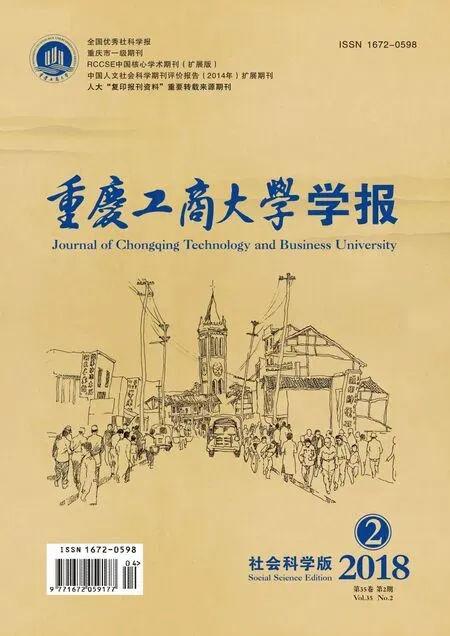童年家庭经验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小说创作
2018-03-23宋雯
宋 雯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州 510275)
在儿童的生活里,家庭环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存在,它深刻影响着儿童个性、气质、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心理结构的形成。具体来说,“家庭环境是指家庭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社会地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家庭成员的语言、行为及感情的总和。”[1]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家庭和20世纪初期的很多中国家庭不同。20世纪初期的很多中国家庭通常以家族为核心,家庭成员众多,关系复杂,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任何一位家庭成员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儿童的重要分子。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家庭主要以核心家庭为主,即以父母和孩子为主要成员,那么家庭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家庭氛围、父母的关爱和言传身教方面了,因为在核心家庭中,与父母的关系和交往构成了儿童早期生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在儿童的生活里,父亲、母亲对其的影响,特别是对其情感的影响特别大,而这些一旦成为定势,就要极大地影响人的情感体验。”[2]
一般来说,父亲是孩子理性世界的引路人,主要影响孩子社会人格的形成,母亲则是孩子感性世界的导师,主要影响孩子自我人格的形成。“鉴于实际的父母和父母职能的矛盾情况,不妨称作父亲意象和母亲意象。”[3]
一、“母亲意象”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
所谓“母亲意象”中的“母亲”,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生育者,而是指给予爱、温暖及照顾的养育者的形象。这个人可能是亲生母亲,也可能是其他监护人或养育者。与之相对的则是让儿童感到敬畏的“父亲意象”,这个人可能是亲生父亲,也可能是与他建立了监护关系的其他人。“母亲意象”和“父亲意象”从不同方面塑造儿童的心灵,“母亲”主要是从情感上塑造作家的个性和气质,而“父亲”则从才能上、社会规范上培养他们。这对于作家日后创作的影响,特别是对作品情感类型的影响极大。
“母亲意象”对儿童的心灵成长至关重要。因为充满着温柔、包容、理解和慈爱的“母亲意象”能使儿童的天性得到自由发挥,“儿童的天真的幻想、好奇心、神秘感等一切与诗心密切相关的东西,似乎都获得了鼓励而有一个永久的居所,这对儿童日后走上创作的道路至为重要”[4]。“母亲意象”的强大与发达使他们发展了“情感移入”能力。依罗杰斯(Rogers)的观点,儿童得到亲人无条件的爱时,他对一切新鲜的经验也是灵活的和敞开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自己“情感移入”的能力。所谓情感移入能力,指的是儿童理解他人心情的能力。情感移入能力的高度发展对艺术家的人格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情感移入能力的高度发展可以促成艺术家道德良心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使得艺术家能够充满感情地对待他人、社会及万事万物。“这种情感态度正源于艺术家对爱的体验。”[5]因此对于作家而言,“母亲意象”比“父亲意象”更为重要。因为创作需要才能,但更需要有一颗诗心、爱心。所以往往是“母亲意象”占据了作家心灵的中心地带,一个作家的情感倾向和对美的热爱与渴望往往与“母亲意象”密切相关。虽然很多“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父母们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忙于大生产和各种政治活动,忽略了对家里孩子的照顾,可还是有不少作家在童年时期得到了充分的母爱,“母亲意象”呈现出温暖和美好的色调,所以他们的情感倾向也较为温暖和明丽,与那种压抑型的情感不同。他们的创作,即使选取了比较沉重的题材,或者在作品中写的是一种痛苦的感情,也总是带着一种温暖的色调。
迟子建童年经验中的“母亲意象”就是非常强大的,她出生在一个温馨和谐、健康向上的家庭环境中,父亲慈祥幽默,母亲温柔娴淑,他们奉行“爱的教育”,对子女们都非常疼爱。“爱”温暖了孩子的心灵,所以兄弟姐妹间从小就互谦互让,家庭氛围非常的和谐融洽。迟子建童年时有段时间曾因某些缘由被送至北极村的外婆家暂住,也受到了众多亲人的呵护与疼爱,在这种暖意融融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成人,迟子建内心深处被涂抹上了一层温暖的底色。从迟子建的童年回忆录《会唱歌的小火炉》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最难忘、叙述得最多的都是和家人在一起的平淡温暖的幸福时光:在白雪皑皑的山上和父亲及兄弟姐妹一起拉柴火、烤土豆;在夏日凉爽的黄昏和家人一起其乐融融共进晚餐;在过年的时候为贴哪张年画展开愉快的争论,或者拎着父亲做的灯得意地走东家串西家;再加上迟子建故乡地处偏远,受“文革”冲击很小,所以她的童年记忆并不像其他的六十年代作家如余华、苏童那样充满了狂热、喧嚣、血腥、暴力,而是透着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温暖。因此,迟子建的作品有别于大多数“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风格,她幸福的童年使得她在看待事物的时候,都会蒙上一层温情的面纱。在她的笔下,我们看不到太多的残酷、暴力、冷漠和阴暗,虽然她大力书写的都是一些社会底层艰难生存着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承受着生活带给他们的辛酸和磨难,悲剧也常常在他们身上发生,可是小说的基调并不残酷和黑暗,而总是在淡淡忧伤中透着一股浓浓的温情和诗意,透着一丝人性的光亮。
童年时期来自母亲的关爱必然在作家的心理形成某种“机制”,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各种暗示或指引。尤其在成人之后面对现实的种种残酷和黑暗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向往并依恋慈柔的母性,这在深层心理上正是对外界危险的一种本能逃避。这种逃避恰恰暗合了弗洛伊德所谓的“涅槃原则”,即回归母体,重归静寂的无机状态的冲动。所以在深受母爱浸润的作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母亲的热爱、讴歌和依恋。“母亲意象”有时甚至会被神化为无处不在、无所不容的伟大力量,是随时等待着孩子来休憩的港湾。
东西生长在广西一个偏远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家庭非常贫困。东西是那个执着地一定要生一个儿子的母亲在46岁时生下的孩子,虽然他已有了两个姐姐。东西可以说是他母亲强加给未来生活的全部意义,再加上他母亲之前曾痛失过一个孩子,所以,不管是干农活还是去工地做工,他母亲都会带着他。挖沟的时候东西被母亲背在背上,背石头的时候东西被母亲抱在怀里。直到六岁时上小学,他的母亲才依依不舍地让他离开她的视线。为了挣钱供东西读书,每到雨天,他母亲就背着背篓半夜出门,赶在别人之前进入山林摘木耳,家里养的鸡全都拿来卖钱,一只也舍不得杀。凡是能换钱的农产品她都卖过,一分一分地挣,十元十元地给东西寄[6],这使得东西童年时虽然充分领略了生活的艰辛,饱受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带来的歧视,却并没因此变得颓废,强烈的母爱使他对着“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他选择写作即是因为“它使我能在虚构中看到一些渴望的美好,比如信任、公平、善良、原则等等”。由于母爱给他的影响过于深刻,所以在他的乡村小说和记忆小说中,“女性始终处于一种非常重要的母性位置上。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诗性场景和人性的闪光点都落在女性的身上”[7],东西自己也坦承,他小说中女性所有的善良、勤劳和坚忍都是来自于他的母亲。
如果一个作家的母亲在其成长过程中处于缺席的状态,或者连“母亲意象”都是缺失的,那么作家的个性就会变得较为内向敏感,其作品的情感倾向也会趋向黯淡和忧郁。如林白就属于这种情况。林白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已去世,母亲又因为工作忙碌常年在外奔波,她很小就独自一人住在空阔的大房子里过着孤独而寂寞的生活。在林白的童年体验中,爱恋本能是处于被压抑的状态的,安全感是极度缺失的。正是有着这样的童年经验,林白习惯于深深地封闭自己,用充满着戒备的眼光探视着眼前纷乱多变的世界。林白曾回忆道:“小时候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女孩,我怕狗怕猫也怕人,既怕生人也怕熟人,甚至害怕自己的亲人。”[8]长时间的,强烈的孤独和恐惧体验深深沉淀在林白的先在意向结构中,并影响到她成人之后的行为方式。林白自述:“长大之后我怕上班,怕开会,怕打电话,怕组稿,怕采访。”[9]因为爱恋本能和安全感没能得到满足,所以在林白的小说中就出现了“强大的破坏本能——死亡与性,以及由这种边缘本能伴随着的那些群体话语中被剔除掉和伦理道德所不容的阴暗心理,如自恋、自虐、同性恋倾向、恋父情结、仇母情绪。”[10]此外,由于童年时期“母亲意象”的平淡,爱和关心的缺乏,致使林白在成长阶段没能发展好“爱的能力”,自恋也就出现在其生命的稍后阶段。“对自恋的人说来,只有一样东西是实在的,那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所拥有的东西,他的感觉与需要。外部世界不可能被客观地体验到或知觉到,也就是说,外部世界是以它自己的关系、条件与需要而存在着的。”[11]这种自恋投射在作品中,就是封闭压抑的环境,孤僻自恋的主人公,大量的内心独白以及细腻的个人感受和情绪体验,可以说,“母亲意象”的平淡,正是林白的作品普遍呈现出黯淡忧郁的情感基调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父亲意象”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
“父亲意象”对作家的影响也极为深远。美国心理学家埃·弗洛姆(Fromm Erich,1900—1980)说:“父亲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支柱,代表思想的世界,人民自然的世界,法律和秩序的世界,原则的世界,游历和冒险的世界。父亲是教育孩子并指导他步入世界之路的人。”[12]如果说“母亲意象”以感情赋予他们爱心和诗心的话,那么“父亲意象”往往是以理智启迪了他们对人生、社会的深刻思考,从而使其作品带有更多的对社会和人生的冷峻的透视。“父爱体现的‘父亲意象’主要表现在引导儿童实现社会化、获得适应外界的才能上面,而且父亲对儿童倾向感性世界的举动视为幼稚,不能容忍而进行干预。”[13]
我们从许多作家的传记、回忆录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普遍的情形:父亲对作家少年时期的文学兴趣的压制和文学志向的否定,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司汤达、卡夫卡等著名作家都曾因选择了文学道路而遭到父亲的反对,父亲强迫他们去当医生、律师、牧师、商人等。在很多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自述中,我们也能发现许多这样的情况,如毕飞宇的父亲希望毕飞宇成为理工科方面的人才;余华也曾说他父亲当年想把他设计成一个牙医,结果没有成功。虽然这些作家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违抗了父亲的意志,但是“父亲意象”的影响都在他们个性的发展、创作情感的倾向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比如毕飞宇在很多小说中写到了“父子关系”,这些文本中的“父亲”都试图支配子辈的命运,让他们的人生按照自己规定的道路前行,这就注定和逐渐具备独立意识的子辈发生矛盾。对这些“父子关系”的反复书写,正是因为“父亲意象”的专制和强势留给他极为深刻的印象。荆歌的父亲也是个非常固执而专制的人,喜欢在家里发号施令,使得家庭氛围压抑而沉闷。十岁那年,荆歌因被怀疑写了“反标”而遭拘禁。一年后,他得到释放,代价是父亲作为“幕后黑手”被关了起来。从此之后父亲的性格更为暴躁、专横,成了一个“仇恨子女的人”。荆歌在《创作自述》里这样回忆了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我与父亲的关系一直紧张,……他对我的打骂,一直延续到我当上了教师。”因此荆歌很喜欢描绘那些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以及亲人之间紧张的关系,他笔下的父亲都是暴烈专断甚至乖张变态的,如在《画皮》里,父亲居然用刀在“我”的背上活生生地刻下了一副毛主席画像。荆歌自己也说,他的许多小说里都有着他家庭生活的阴影,“对于父辈,领导和权威,我都把他们放在了扭曲的、神经质的、可笑的位置上。童年生活的压抑终于在写作这种形式上找到了喷发点”[14]。
没有父亲参与的成长是不完整的,父爱的缺失会促使作家们“缺父情结”的形成。体现在作家的创作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缺父情结”转换为“憎父情结”,将父爱缺失带来的心灵创伤直接表露在作品中。如陈染在《空心人诞生》中塑造了一个脾气暴躁乖戾,行为变态的父亲形象,母亲因受不了他无休止的暴力与蹂躏逃出家门,最后还是因父亲的变态折磨和无法承受的压力而自杀。而在她的《巫女和她的梦之门》中,父亲是个专断狂躁的“暴君”,他凶狠地抽“我”的耳光,把“我”连根拔起,跌落到两、三米之外的高台阶下边去。《纸片儿》中的外祖父和自己的女儿乱伦生下“纸片”,在得知“纸片”与单腿人乌克相恋之后,竟带领其豢养的几十只猫咬断了乌克身上所有的血管。在虹影的笔下,则有大量丧父或丧失父爱的主人公,他们是一群被抛到世界上的“孤儿”或“半孤儿”,他们的父亲要么在他们还未出生时就已死去,要么是对家庭完全不负责任的浪荡子,在《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你一直对温柔妥协》《阿难》等作品中,主人公都因为父爱的缺失而经历了从物质到精神的种种磨难。还有一种是父爱的缺失激起了作家对父爱的极度渴望,“缺父情结”转换为“恋父情结”,父爱的缺失会影响女儿心灵的成长,影响她们对男性最初的感知。她们希望能够把缺失的父爱补偿回来,于是,陈染、虹影、林白在她们的作品中构建了一系列她们所期望的男性形象,表达对父亲的呼唤和依恋。她们笔下那些缺失父爱的主人公对爱情的追寻也成了寻找父爱的代偿。这些在童年时期缺失父爱的女子力图通过爱情满足自己的精神渴求,抹去“无父”带给他们的恐惧感,所以她们爱上的,往往都是比他们年长很多的,沉稳的老师或大男人。比如在《饥饿的女儿》(虹影)中,六六爱上历史老师的原因是:“我是在寻找我生命中缺失的父亲,一个情人般的父亲,年龄大到足以安慰我,睿智到能启示我,又亲密得能与我平等交流感情”[15]。在《致命的飞翔》(林白)中,李莴的情人,是一名掌有实权的官员,他“虽然年过五十,但仍不失为一个美男子”,李莴毫不掩饰地说:“我需要情人就像需要父亲,登陆正是一个切合了我的各种需要的人。”[16]在《私人生活》(陈染)中,父亲般的男人对倪拗拗总是有着深深的吸引力,她从他们那里寻求保护寻求依恋,因此她和四十多岁的男邻居发生了性关系,靠在跟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男人怀里,“我心里想到了许多词:温情、依赖、大海、沙滩、沉睡、死亡、融化、伴侣、秘密……但惟独没有想到情欲这个词,在我那个年龄的词汇里,这个词还不存在。”[17]这充分说明倪拗拗并没有把男邻居视作一个真正的情爱对象,而是将其作为父爱的代偿。不过更多的时候,这两种形式,“憎父情结”和“恋父情结”是交织在一起的,如在《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陈染)中,“我”的父亲冷酷、残暴、无情,而正值花季年龄的“我”却被邻居家那个“半裸着脊背有着我父亲一般年龄的男子”所吸引,并主动要求与其发生性关系。这反映了作家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们对父爱的缺失表现出不满和痛恨,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度渴望这份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的关爱。就像陈染在一篇日记中所说:“宽容度世的时候,‘父亲’是一个与我的血脉情感毫无关联的字词,……但是,当我在悲观、忧戚的时候,当我处世中常常感到自己心理上的严重缺憾的时候,或者当我作为一个成年女子回首遥望自己的成长历程并运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进行剖解的时候,‘父亲’这个字词就使我内心不平静起来,甚至一股该死的恨意便从顶至踵注满我的身体,”但是,陈染也承认,多年来,她无法抑制一种说不清的“父亲情结”。“一个男人走进我、吸引我的也往往首先是他的父性的一面。我始终无法把一个男人的位置摆放在一个通常的女子所需要的位置上。”[18]
此外,父爱的缺失还会使得女性对男人产生恐惧心理,反映在作品中,就是对男人的排斥和对同性的亲密认同。如在陈染的作品中,很少有阳光健康、讨人喜欢的男性人物形象,他们要么粗暴、专制,如《私人生活》《空心人诞生》中的“父亲”;他们要么平庸、乏味,如《潜性逸事》《时光与牢笼》中的“丈夫”;他们要么猥琐、下流,如《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的男邻居和《私人生活》中的“T老师”,他们在两性关系中常常不过是女性性欲发泄的工具而已;如《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沉默的左乳》中的年轻男人,这些男性大多在作品中是没有名字的,显得模糊化和符号化。虽然《私人生活》中的“尹楠”和《与往事干杯》中的“老巴”是陈染作品中少见的较为美好的男性形象,是倪拗拗和肖濛“生活中一抹温暖、明亮、美好的亮色”,但从小说中陈染对他们的描摹可以看出,除了美好、帅气等词汇之外,他们的形象始终是空洞、模糊的。我们根本无法从人格特征、思想、性格等角度对他们作出具体的分析。总的说来,陈染对男性缺乏信任和安全感,在《破开》中,她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了对男性的看法:“有的男人总是把我们的性别挡在我们本人的前面,做出一种对女性貌似恭敬不违的样子,实际这后面潜藏着把我们女人束之高阁、一边去凉快、不与之一般见识的险恶用心,一种掩埋得格外精心的性别敌视。”[19]与陈染作品中的男性形象截然不同的是女性形象,她们都是陈染作品的主角,是陈染的重点刻画对象,她们才华横溢、特立独行,她们的心理和情绪体验被陈染描写得细致入微、纤毫毕现。在《与往事干杯》中,陈染借人物之口说:“我对于男人所产生的病态的恐惧心理,一直使我天性中的亲密之感倾投于女人。”[20]所以我们不难发现,陈染作品中的女性普遍对男性呈排斥态度,喜欢在同性身上寻找安慰和归宿感,无论是《破开》中的“黛二”和“陨楠”,《饥饿的口袋》中的“麦戈”和“薏馨”,《麦穗女和守寡人》中的“我”和“英子”,《潜性逸事》中的“雨子”和“李眉”,还是《世纪病》《人与星空》《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我”和“母亲”,都体现了心有灵犀、惺惺相惜的同性情谊。
不过,“父爱的严厉性对艺术家的审美心灵和对世界的感性态度是一种灾难,因而父爱的丧失,使儿童的社会化不能顺利完成,这对其心灵自由状态的保持、童心的保持反而变得有利。”[21]虹影、陈染、林白等作家文学创作上的成功,部分原因就是自幼缺失父爱,社会化未完成,使他们得以长久保持一颗童心,而童心和诗心是相通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诚。具有这种真诚之心的作家,才能在文学史上争到一席之地。
如果作家在童年时期同时拥有较强大的“父亲意象”和“母亲意象”,那么他既会获得一个丰富的,充满诗情的感性世界,又能对现实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冷静的审视。“这类作家的心理历程是,他先得到爱、诗情、丰富的感性,然后再得到能力、智慧、深刻的理性,在其成熟阶段则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样其作品就会表现出诗情和智慧、感性和理性、直接性和规律性的完整统一。”[22]如毕飞宇就属于这种情况。毕飞宇虽然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而跟着下放到苏北农村,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但父母的关系是非常和睦的,每天晚上都会用聊天来打发漫长的夜晚。毕飞宇认为他的想象力就是在这些夜晚开始生动起来的。虽然不富裕,可是毕飞宇总是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还可以穿着当时很多小朋友都没有的袜子。父亲虽然对他比较严厉,可也都是处于关爱的目的。总体来说,毕飞宇的家庭环境是很开明的,这样的家庭环境培养了毕飞宇豁达乐观,幽默开朗的性格,使得他在面对沉重的苦难的时候,也能够用一个良好的心态去面对,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都呈现出轻盈而凝重的风格,体现了卡尔维诺所说的“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父亲意象”的强大也对毕飞宇意志的培养、智力的发展、思想的成熟等起了非常积极重要的作用,养成了毕飞宇热爱思索的习惯,他坦承在小说中对语词和事物进行细致分析的习惯则主要来自于他的父亲:“父亲曾告诉我,要小心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是一个‘仓库’, 从一个字出发,每个字都能把我们生活完整地联系起来。”[23]毕飞宇在创作中喜欢运用感性和智性的双重叙述话语,被吴义勤称为“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这与毕飞宇童年经验中“父亲意象”和“母亲意象”的完整与强大是分不开的。
三、家庭出身:不可选择的政治身份
不过,与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不同的是,“六十年代出生作家”除了受“母亲意象”和“父亲意象”的影响外,他们还会受到家庭出身带来的深刻影响。因为在这个“血统论”盛行的时代里,人的家庭出身决定了其政治身份,当时的政治身份主要分为两类:“黑五类”和“红五类”。不同的家庭出身代表着不同的政治身份,不同的政治身份意味着不同的政治地位、政治待遇、物质生活。“黑五类”是接受批判的主要对象,他们的家被抄,人被揪斗,财产被查封,他们的子女、亲属受到株连,“连不懂事的孩子也都定为‘黑帮子女’‘黑线人物子女’‘叛徒子女’‘狗崽子’,受到歧视和虐待。相反的情况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24]在当时,家庭出身好的孩子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欢迎,可以加入“红小兵”,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小学生加入红小兵却受到限制,此外,他们还承受着家庭氛围压抑和外界歧视带来的痛苦,过早体会到的炎凉世态对他们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先在意向结构的形成都有很大影响。如东西的性格胆怯,胆怯到没有胆量去责怪别人,而总是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这是与他不好的家庭成分有很大关系的,他曾在一篇自述中说,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只要是长有鼻子眼睛的都可以骑到他的头上。于是,大多数时间里,他都躲在紧闭的家门内,谛听着父母无奈的咒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东西喜欢卡夫卡,当他看到卡夫卡的《地洞》时,他才找到了真正的知己。他坦承:“他喜欢卡夫卡的小说不是为了做秀,而是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怯懦的人。”[25]他甚至认为他写作成功的因素正是他不好的家庭出身造就的他的“不怨天尤人,自卑和恐惧,相信别人吹牛皮”的性格特质。麦家的祖父是地主,叔公是基督徒,父亲被划为“右派”,连累幼小的麦家也跟着受歧视,他没有朋友,在学校不仅受到同学的欺负,还受到老师的歧视和言语讽刺,这使得麦家不爱跟人说话,而是喜欢跟自己和静物交流,养成了忍受孤独和寂寞的本领以及多思的习惯,他写日记,对着镜子说话,跟夜空中的星星许愿,稻草人也成了他经常说话的对象。[26]这样的行为培养了他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感受力,这使得他更善于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事物的不平凡的表现性,这对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是非常有利的。
总的说来,“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童年家庭经验中的“母亲意象”、“父亲意象”、家庭氛围、家庭出身等因素都影响到了他们个性、气质、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及先在意向结构的形成,他们的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叙事、人物形象塑造、风格基调等因素也因此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八十年代出生的大部分作家相比,“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们大都有兄弟姐妹的陪伴带来的快乐,由政局的动荡和父母的繁忙形成的“权力的真空”也使得他们的童年生活更加的自由自在。据六十年代生人回忆,那时的他们都没有家庭作业,每天放学之后就是玩,所以“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不会像八十年代出生作家那样从出生起就受到来自学校和家庭的过度保护。有人指出,“当今中国的80生人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他们生长的时期正是独生子女政策实施阶段,因此他们的生长从一开始,就有着严重的社会化不足。”[27]所以在面对成长之痛和残酷现实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迎难而上,而是逃避。他们最主要的逃避方式就是拒绝长大。这使得八十年代出生作家在整个群体的心理上呈现出后退的特点,因而也就缺乏作为一个作家应当具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他们的创作多徘徊在个人情感的抒发上,而“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相对自由的成长经历使得他们能成熟得更快,使他们面对问题时勇于怀疑,勇于反叛,在创作的时候也更加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1] 翟瑞青.童年经验对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及其呈现[D].济南:山东大学,2013.
[2] 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197.
[3] 崔志远.论中国地缘文化诗学[J].文艺争鸣,2011(8).
[4] 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198.
[5] 童庆炳.现代心理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35).
[6] 东西.故乡,您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N].河池日报,2008-1-11.
[7] 洪治纲,东西.伤痛的另一种书写[J].青年文学,2000(11).
[8] 林白.生命热情何在[M]//前世的黄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5.
[9] 林白.内心的故乡[M]//前世的黄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63.
[10] 肖莉娇.执着的“边缘”探索——论林白的新世纪小说创作[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
[11] 埃里希·弗洛姆.黄颂杰,编.弗洛姆著作精选 ——人性·社会·拯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283-284.
[12] 埃里希·弗洛姆.康革尔,译.爱的艺术[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7.
[13] 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198.
[14] 荆歌.创作自述[M]//口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2.
[15] 虹影.饥饿的女儿[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286.
[16] 林白.致命的飞翔[M]//林白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81.
[17] 陈染.私人生活[M]//孟繁华,主编.青春小说精品读本:艰难时世的感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208.
[18] 陈染.关于父亲的梦[M]//声声断断,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0:148-150.
[19] 陈染.破开[M]//危险的去处,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415-427.
[20] 陈染.与往事干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10.
[21] 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200-201.
[22] 童庆炳.文学审美论的自觉——文学特征问题新探索[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233.
[23] 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M].济南:明天出版社, 2013:148.
[24] 金春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M].北京:求实出版社, 1989:204.
[25] 东西.时代的孤儿 [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5.
[26] 韦志刚.分裂的守望者[A].文艺报社主编,《文学生长的力量[C].合肥: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261.
[27] 王涛.代际定位与文学越位——[80后]写作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