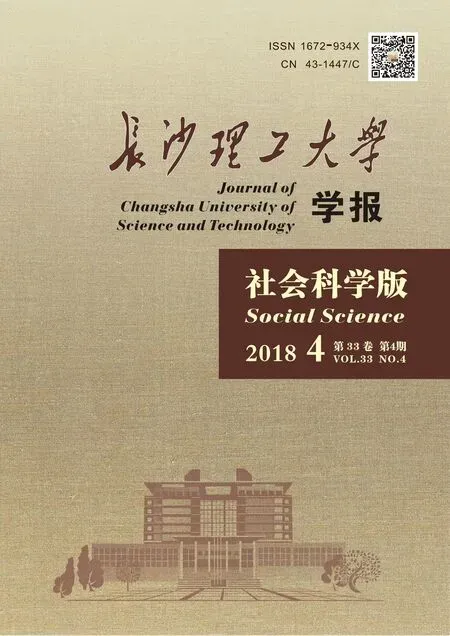军事技术伦理价值的三重形态
2018-03-20陈多闻何祖龄
陈多闻, 何祖龄
(1.成都理工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2.国防科技大学 哲学博士后流动站,湖南 长沙 410073)
军事技术价值蕴含着人类的原始需求和解悖方式,既属于技术哲学的基本论域,也是我们国家实现“强军梦”进而实现“强国梦”所必须要面对的实践问题。“军事技术不仅是研制武器,还包括一切与满足军事需要相关的科学技术。”[1]军事技术价值是多元的,20世纪初哲学领域的伦理学转向,凸显了伦理价值在军事技术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性。“伦理价值属于技术的内在价值,技术从诞生开始,就内在地具有伦理属性。”[2]所谓军事技术的伦理价值,指的就是军事技术客体本身所具有的能够满足军事技术主体伦理道德和伦理精神需求的属性,这是一种伦理属性,区别于政治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等其他属性,它反映了军事技术主体在进行军事技术的设计、发明、生产和使用等有关活动时所持有的价值理念、伦理取向以及道德规范。军事技术的伦理价值肇始于远古人类的生存诉求,异化于近代工业的侵占特质,回归于现代人文的反思浪潮,在历史演变中呈现出生命伦理-生存伦理-生态伦理的逻辑层次。
一、生命伦理:军事技术伦理价值微观形态
拥有生命是人能够开展活动书写历史的最基本前提。所谓生命伦理,就是人类以生命为中心所建构起来的一系列伦理关系,涉及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尊严、生命的质量等,其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生与死的问题。军事技术的生命伦理价值就源自于人类维持生命、保护生命的天然需求,是军事技术伦理价值的微观支撑。
首先,从关注自己人的生命到关注他人的生命。武器的诞生之初,人类就已经表现出对生命的敬畏。早在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原始人类就约定俗成“绝不能用武器来‘伤害’自己人”[3](P23),所谓“自己人”就是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内部人员,他们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就应该相互照顾和扶持。在母系氏族社会,惊奇于女性如同大地一样能够孕育生命,原始人类给予了母亲以至高的地位,相约“不可杀母”,并界定“杀母是不可赎的大罪”[4](P6),而当时杀死一个男人则是可以赎罪的。还有当时的“血族复仇”习惯,当有外族人杀害了“自己人”,整个氏族部落都要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寻出行凶者,把他杀死”[4](P83)。
现代社会的到来,使得战争的恐怖性和残酷度与日俱增。战争本来是作战双方或者多方解决恩怨的局部行为,但是往往由于现实战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是会涉及到无辜的他人,比如平民。根据历史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830万平民和857万军人丧生。仅仅过了一百年的时间,在二战中丧生的生命数量翻倍增长,特别是无辜平民的死亡人数竟然创历史新高,包括德国纳粹党大肆屠杀的犹太民族和日本军国主义无情残害的中国平民和朝鲜平民在内,竟然达到了近2 500万!远远大于一战中平民和军人死亡人数之总和。在这期间,还有两件事情深度炙烤着人类的道德良心,质问着人类的伦理底线,其一是日本军国主义的731部队所进行的人体实验,另一是二战末期的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包括科学家在内的人类开始整体上注意到他者生命的神圣性,并很快就体现在军事技术实践活动中,出现了“不杀害俘虏”“禁止对战俘使用武力”的规定。《圣彼得堡宣言》强调,在战争中不应使用“无益地加剧失去战斗力的人的痛苦或使其死亡不可避免”的军事技术,而应“满足于使最大限度数量的敌人失去战斗力”。
其次,从专注于肉体上消灭敌人到青睐于意志上摧毁敌人。20世纪中叶之前的战争虽然已经出现了要求区别对待平民和敌人、敌人中的战斗员和非战斗员、有作战能力的战斗员和丧失作战能力的战斗员等的作战原则,但是在战事中为了省事总免不了一通狂轰滥炸,宁可错杀不可错过。20世纪末以来,军事技术主体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开始有了伦理共识,在精神上打败敌人远胜于在肉体上消灭敌人,所以“从千方百计追求增加杀伤力到考虑武器‘慈化’,即设法研制‘非致命武器’”[3](P3)。非致命武器是指为达到使敌方人员或装备失去正常功能而专门设计的武器系统,按作用对象的不同,非致命武器可分为反装备和反人员两大类。目前,国外发展的用于反装备的非致命武器主要有超级润滑剂、金属致脆剂、致痒弹、超级腐蚀剂、超级粘胶以及动力系统熄火弹等。非致命武器虽然目前还处于概念阶段,但已经成为各军事大国的新宠儿。这些军事大国特别是美国在新型武器的开发和研制中,不再一如既往地仅仅青睐于杀伤性能,也开始关注不致命的致盲性能、致聋性能、致瘫性能等等,企图瘫痪敌方的通信、管理、指挥系统,或在一定程度上损伤敌方人员的器官功能,使其丧失部分甚至全部战斗能力,但控制在不致死亡的程度之内,比如高能微波武器、光学武器、脉冲化学激光器、声束武器等,它们的杀伤功能弱化,威慑功能凸显。
除了非致命武器的研制开发,军事技术主体也注意利用经济、文化、信息等手段进行没有硝烟的和平演变。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发动的海湾战争,不仅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伤亡不大,被无辜牵连的平民数量也创同等规模战争之低。在这场现代战争开动之前,美方率先就派出大批EA—6B、EF—11lA和EC—130H电子飞机不断发出错误信号制造信息干扰,误导甚至破坏了伊拉克的通信系统和防空雷达,致使还没有开始战争,伊军意志就已经崩溃,失败已经不可避免。“信息武器的杀伤作用更具选择性,同时可以避免大规模毁灭性的可怕后果,因而代表着未来军事斗争的发展方向”[5](P5)。
二、生存伦理:军事技术伦理价值中观形态
生存是地球上所有生命最为基本的诉求,自从人类在其演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阶级,当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生存伦理也就突破生命个体和氏族部落跃进到国家层面,“军队是用来保卫国土的”[6],军事技术活动开始围绕着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武装对抗而进行。所谓军事技术的生存伦理,就是国家或阶级以生存为目的所发生和建构起来的各种伦理关系,关系到国家的尊严、自由和独立,是军事技术伦理价值的中观体现。
首先,从着眼于物质生存到致力于精神生存。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子说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7],这其实已经孕育着朴素的军事技术生存伦理价值思想。军事技术最核心的部分是武器,根据甲骨文的记载,武字,由“止”和“戈”组成,这里就包含了使用武器发动战争的原初目的,是为了“禁止暴虐、消除战争、保卫江山、巩固功业、安定民众、协和万邦、丰裕财富”[8]。“战争是一种生存的斗争、权利的斗争、弱肉强食的竞争,它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生存、消灭或扩张。”[3](P112)
先是为了物质生存,人类需要军事技术。“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9],人类早在遥远的蒙昧时代就已经开启了技术化生存模式,一部人类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技术进化史,革命导师恩格斯不仅承认“古代部落的战争”[10],并且进一步指出这种战争,“是由来已久的”[11](P219)。虽然远古时代的战争和现代社会的战争不管是在概念上、规模上还是程度上,都不可能同日而语,但就其实质来说却都表现为不同利益团体的暴力冲突。当时,人类的生活模式是一种游牧状态,靠天靠地来提供生产资料,自然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这个时候就要移民,而“要实行移民就必须进行征服战争”[12],以获取新的资源或更多的生产资料。
国家满足了其在物质上的生存需求之后,必然要追求精神生存——安全感,因为人“生来就是一种要行动的动物,是要改造外在世界的各种事实的动物”[13](P14)。人的这种改造本性使得他迫切需要帮手,因为人赤裸裸地来到世上,手无寸铁,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里没有任何优势:论速度,跑不过猎豹;论体力,抗不过大象;论视力,远不过老鹰;论听力,辨不过蝙蝠;论耐力,敌不过骆驼;论嗅觉,灵不过狼狗……在强烈的改造意愿支撑下,“人类就发明了一种工具,他既可以用这种工具来改善他的日常生活,又可以用它来作为杀死他的同类的武器——削尖了的石头”[14]。人类最初的工具就是石头,石头是力量的象征,代表着拳头,既可以帮助人类获取生存所需的食物,又可以帮助人类与虎视眈眈的野兽搏斗,击退敌人。所以说,石头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工具,更是人类捍卫自己生命安全、领地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武器。之后,人类又发明了弓箭,“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4](P19)。军事技术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成为了人类的好帮手,帮助人类改造,帮助人类征服。国家在满足了其基本的物质生存和精神生存需求后,不断努力地“扩大他驾驭自然的力量,因为这就是他生存的规律”[13](P23)。
其次,从满足于基本生存到努力实现“更好地”生存。不管是哪个时代的战争都与生存有关,其真实目的无非两个,或是为了生存,或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之所以双引号于“更好地”,因为这只是某些国家的强盗生存逻辑。军事技术本来就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侵占气质,在科学知识的装饰和辅助下,这种侵占气质一点一点被挖掘出来,也给兴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绝好的武器,不仅把本属于自然的,而且把本属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领地慢慢据为己有,耀武扬威。
18世纪蒸汽机技术革命在英国率先爆发,蒸汽机可以将蒸汽能直接转化为机械能,使得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结为一体紧密协作,开创了机器生产机器的工业系统,不仅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繁荣的物质文明,也为军事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直接导致了“以火炮、战舰为代表的武器装备的变革”[5](P118)。当人类拥有了坚船利炮之后,征服、抢夺的欲望则空前膨胀,战争于是频频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是彼此之间为了抢夺霸权而发动战争,比如英国和法国、英国和西班牙、法国和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美国和西班牙等等之间都进行过激烈的战争,后又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以坚船利炮为武器,占领和剥削弱小的国家、民族和落后地区,将其变为附属于自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妄想一劳永逸地加以控制和奴役,比如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鸦片战争,1840年英国以我国民族英雄林则徐销毁了英国出口到中国的两万箱鸦片为由,派出舰船47艘、陆军4 000人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公然封锁海口,发动了鸦片战争,之后通过不平等条约无耻地将我国香港据为己有。以此为契机,法国、俄国、日本、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美国纷沓而至,意图瓜分中国。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如此猖獗,一方面,是因为有了威力巨大的军事技术作为工具,他们有恃无恐;另一方面,继新教伦理之后,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理念给予了这些侵占者进一步的精神支撑,使他们认为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合理的战争,有利于人类整体的进步。“文明制度下,战争往往意味着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强化”[5](P12),而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和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即使敌我力量非常悬殊,也不惜浴血奋战要誓死捍卫自己的领土和尊严。
三、生态伦理:军事技术伦理价值宏观形态
不管是生命伦理还是生存伦理,都是基于人和国家民族的立场而言的,人类的欲求轻而易举地掩盖了人的本质需要,那就是人作为大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要素,最终要作为种的形式、作为类的存在物延续下去的需要。军事技术的生态伦理即军事技术主体基于自身与周围的人、动物和大自然等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所持有的一系列道德观念,它倡导整体价值优于部分价值,并将伦理的范围扩到了非人的对象,它是军事技术伦理价值的宏观存在。
首先,从追求生存率到关注生存环境。近代以前的人类主要是为了满足生命需要和生存诉求而使用军事技术,此时的军事技术停留在冷兵器时代,不涉及能量之间的转化,对自然环境的伤害是极其有限的。到了16世纪,“发明的精神已经被唤起,到处都有一批热心的人,他们向往着把新的思想用于军事领域”[15],军事技术迅速进入到火器时代,富含铅元素的火药跃身成为常规武器,军事大国们打起仗来,满脑子都是击败敌人保存自己,子弹枪炮满天飞,不仅给战场制造了难以估量的环境破坏和生态污染,也制造了数量惊人的太空垃圾。有统计称,每发子弹含铅量大致介于2-3克之间,铅虽属于非放射性元素,却毒性极强及无法降解,一旦排入环境中或进入人体内会不断积累,已成为强污染性的世界公害物质之一。“具有毒性或酸性的有害物质,因战争而释放到空气中,对大气环境造成破坏;由于大气环流的作用,生态环境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类将深受其害。”[3](P340)
二战期间,人类成功研制了原子弹,但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爆炸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多少快感,因为,这不仅仅是日本人的劫难,更是全人类的劫难。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的爆炸不仅促逼着人类伦理的生命底线和生存道德,也打破了人类伦理的生态界限。原子弹爆炸当时就摧毁了广岛67%的建筑和长崎40%的建筑,更是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长期的核放射性污染。20世纪中叶接踵而来的八大环境公害事件,进一步震惊全球,随后,卡逊《寂静的春天》使人类幡然醒悟,意识到生态环境的恶化将会毫不留情地葬送掉人类整体,毕竟地球只有一个,如果不想同归于尽,就必须有所改变。到时候任你是何等强盛,谁也无法生存,更别奢谈更好地生存了。一种全新的自然观也就是生态自然观正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孕育并取得了军事技术主体的共识,“只有通过使用现代技术,才能构建一个自我循环的生态栖居地”[16],人类开始赋予军事技术以生态伦理的考量。
其次,从无视环境破坏到重视环境保护。对生存环境的关注推动着军事技术主体积极研制能够对生态的破坏降到最低限度的武器,比如着眼于软杀伤的软武器,这个概念相对于硬武器来言,它并不借助于导弹、兵器等杀伤性武器,而是利用光、声、电、磁等高技术手段进攻,其目的是使敌军暂时性失去作战能力、罪犯暂时失去活动能力、枪械车辆等武器装备失去正常功能,所以属于一种非杀伤性武器。2003年以美国为首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抛开其争议和伤亡不谈,从软杀伤运用的角度来是看是一次极好的展示。这场战争,从软杀伤运用领域来看,涉及到多个领域,比如宗教、政治、经济、外交、金融、贸易、资源等等,从软杀伤的手段看,关系到各个方面,有情报、公约、媒体、网络、心理、技术、法规等等。战争从酝酿到结束,在世人面前构筑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完整现代软杀伤系统。软杀伤武器的推行还直接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新军种——网军的建立,“它的使命是保卫网络主权和进行网络战,还可以用能发射电磁射频流的电磁枪,远距离摧毁敌方计算机网络的物理设备”[3](P132)。网军经常使用的武器就是计算机病毒,比如特洛伊木马病毒、蠕虫病毒、逻辑炸弹病毒、熊猫烧香病毒、比特币病毒等等,这些网络战士使用着键盘、鼠标在互联网中植入或输入病毒,一旦被激活就可以大量繁殖并以惊人速度传播开来,可以瞬间删除或随意篡改敌方的数据和程序,最终摧毁其电脑系统,在网络时代这可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可以称之为没有硝烟的战争。
针对之前以弹药为代表传统武器的深度污染,绿色武器的概念也应运而生,绿色武器,又称之为环保武器,它融入了当代绿色环保、可持续性等生态哲学理念,指的是在使用中较少污染甚至不污染生态环境、不破坏生态平衡的武器,比如不含铅的子弹、可以自动减排的装甲车、可制肥料的炸药以及其他低毒素无毒素的武器等等。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开始重视弹药武器的绿色化,据悉,美国和英国都在积极研制绿色武器,以便在清洁能源的战略竞赛中拔得头筹。1976年第3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止为军事或任何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公约》,直接将保护环境写进军事条约里,借以约束破坏生态环境的武器研制行为。《禁用集束炸弹公约》也于2010年正式生效,缔约国现在已经突破了100个国家,禁止了对集束炸弹制造及使用,对于已经拥有的集束炸弹,持有国必须在八年之内予以销毁。20世纪末,人类除了制定一系列的法律公约来制约甚至禁止地雷、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使用,也开始积极设计和研制内含生态约束的军事技术。
四、结语:不可忽略的军事技术伦理价值
人类作为宇宙间唯一具有德性的物种,从诞生之初就对美好生活充满着向往。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人类不得不借助于技术手段时,古代的圣贤们就注意赋予技术以伦理属性。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技术的词源形态techné与伦理内涵关联在一起,指出技术与伦理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17],并借以呼吁一切科学技术都应当“以善为目标”[18]。古代中国的老子直接把技术分为君子之器和非君子之器,鼓励人们使用君子之器,对于非君子之器,则主张“有而不用”。在马克思看来,伦理价值总是蕴含在人类的技术实践中,每天的生产实践都在不断产生着“人”的正面思想和“非人”的负面思想。人们的技术实践活动不断生产着或善的或恶的或好的或坏的伦理思想,技术生产活动也就成为了伦理的寓身之所,而判断伦理是否合理,最终也是根据它在技术生产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由技术和伦理价值两种因素构成的异质性实践,两种因素的良性互动,对于实现其实践目标——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显得尤为重要。”[19](P158)
军事技术的诞生最初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命需求和生存诉求。人类刚从动物形态脱胎换骨,就既要与大自然竞争以获取食物,也要与其他人其他动物竞争以保护自己。老子提倡道的思想,强调道法自然,认为万物都有其与生俱来的天性,也都按照其天性来运转,是太阳就应该在白天普照大地,是星星就应该在夜晚熠熠生辉……压抑天性,道法不容,除了天道和地道,还有人道。人道首先就表现为人生存的本能,为了不至于饿死冻死,人必须与其他人其他动物竞争,抢夺赖以生存的食物和资源。先是要寻求可以充饥的食物以维持物理生命,“桂可食,故伐之”[20];然后是要寻求遮风挡雨的地方以供身体休息,故“凿户牖以为室”[21](P72),这样就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在满足了最基本的低层次物质需求之后,人类便开始寻求高层次的精神生存,也就是安全感,这就需要“舟舆”和“甲兵”,虽然这些都是“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但是一定要“有之”[21](P261)。孔子虽然以人伦为其思想核心,但也注意到了工具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2],我们想要做好一件事情,必须借助于合适的工具。就这样,为了维持生命并生存下去,人类在发明了生产工具的同时,也发明了军事技术,最古老的工具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11] (P513)。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社会,军事技术虽处于“退隐”状态,却一直引领着民用技术的发展,“不管人们愿意与不愿意,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技术创造的最高成果总是首先用在军事上。被称之为现代技术三大标志的原子能技术、电脑技术、火箭与空间技术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诞生并开始应用的,直至今天它们也首先是为满足军事需要才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然后才逐渐转化为民用”[23]。只是,因为军事技术先天的攻击特质,有人就直接将军事技术界定为恶的技术,并将其彻底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认为即使是非致命武器、软武器、绿色武器等也不可能有伦理属性可言,只不过是一种“人道迷雾”,在其背后依旧充斥着暴力、伤害、破坏和污染。这显然有悖于人类的历史和现实,从人类历史来看,军事技术不管是在诞生之初还是在退隐之今,都闪耀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德性的渴望;从现实角度来看,只要有人类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6](P42),在战斗中,正义的一方如果不想坐以待毙,那就必须要用军事技术来保家卫国、惩恶扬善、消灭侵略、遏制奴役,当然,军事技术使用者也同时是道德主体,对当代“有其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24],使用军事技术要保持在一定的度中,如果只是满足一己私欲,必然会遭受世人的唾弃和伦理的拷问。
而与此同时,军事技术并不只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客体,在使用中其“固有的伦理价值会不断地随着其发展型塑我们的价值观和实践观”[25]。籍于此,军事技术主体除了要规范自己的使用行为,也要设计和采用有“伦理意向”的产品来引导甚至改变人类的军事道德行为,比如当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智能机器人替代军人上战场就体现了对己方军人生命的伦理保护,有尊重生命保护生命的伦理意蕴;非致命武器的采用则体现了对敌方生命的伦理保护,提醒着军事技术主体生命的可贵性和平等性,越是在敌对分子和平民混杂的场地,非致命武器的采用就越加必要。在军事技术设计阶段开始就纳入伦理因子,“将伦理因素作为一种直接的重要影响因子加以考量”[19](P158),伦理制约应该内化于军事技术之中,时时提醒主体履行作为人的伦理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军事技术的伦理价值更符合人类整体的福祉,进而使道德伦理制约真正成为军事技术的内在维度之一,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和书面上。“我们必须维持着一种随时警惕的状态,不断检测着我们的局势,在伦理上不断为我们的行为重新定向,不断明确地表明并修改我们的基本承诺”[13](P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