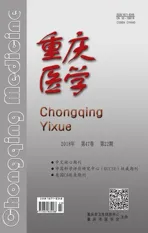13例医源性肾血管损伤性出血的介入治疗
2018-03-20刘灵军崔天蕾
于 洋,刘灵军,崔天蕾△,李 肖,付 平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脏内科,成都 610041;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介入诊疗中心,成都 610041;3.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放射科,成都 610041;4.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北京 100021)
近年来随着泌尿系统微创技术的发展和肾脏活检技术的普及,医源性肾血管损伤的发生亦随之增加;其中以术后出血最为常见,且一旦发生往往难以自止,若处理不当易导致严重后果,甚至引起医疗纠纷。现总结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008-2015年急诊介入治疗的医源性肾血管损伤患者资料,探讨急诊介入治疗在医源性肾血管损伤出血的疗效与诊疗策略。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收集2008年1月至2015年6月间采用血管内介入治疗医源性肾脏术后出血患者13 例,男 8例,女5例;年龄 26~73 岁(平均47.3岁)。7例为经皮肾镜取石术(PCNL)后,其原发疾病包括5例肾脏多发结石、1例肾铸型结石、1例输尿管上段结石;5例为肾活检术后,原发疾病包括3例肾病综合征、2例肾功能不全;1例为部分肾脏切除术后。患者术后出血时间1~9 d(平均3.4 d)。主要临床表现:9例腰部胀痛,5例持续性或间断肉眼血尿、9例持续性镜下血尿,4例引流管持续或间断引流出鲜红色血液,6例早期休克表现(血压下降、心率增快、少尿)。10例患者行腹部超声或CT检查,其中6例发现肾周血肿,2例肾脏血肿合并假性动脉瘤,2例腹腔内或腹膜后积血。13例患者血红蛋白下降程度均大于3 g/L,2例患者合并急性肾损伤,给予止血、补充血容量后生命体征仍然不稳定,予以急诊造影并进行介入治疗。
1.2治疗方法 采用seldinger技术穿刺股动脉交换血管鞘并送入导管,使用5F猪尾导管在第1腰椎水平行腹主动脉造影,明确肾血管及其出血情况;采用5F或4F超滑Cobra导管行选择性肾动脉造影进一步明确肾动脉破裂的部位、程度、大小以及是否有动静脉瘘及假性动脉瘤形成等血管损伤,酌情采用多角度投照显示靶血管走行。使用3F同轴微导管(Cook公司,美国)超选择至靶向血管造影确认病变,选用匹配病变管径的弹簧钢圈、PVA颗粒等栓塞材料进行血管内栓塞治疗,尽可能避免误塞栓正常血管分支;若血管损伤为肾动脉主干或因血管解剖原因无法进行超选择性肾动脉栓塞的患者则行肾动脉覆膜支架置入术(Bard公司,美国);复查造影时未见造影剂外溢、动静脉瘘或假性动脉瘤等血管损伤和活动性出血等表现提示治疗成功。术后常规给予补液、利尿等对症治疗,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出院后每3个月定期随访。
2 结 果
13例医源性肾血管损伤性出血患者中,有12例经选择性肾动脉造影明确诊断,1例未发现明显异常。肾动脉血管造影表现:肾实质内局限性动静脉瘘1例(静脉早期显影);假性动脉瘤9例(肾实质内囊状血管结构与肾动脉分支交通,无静脉早期显影),其中合并对比剂外溢2例,动静脉瘘1例;对比剂外溢2例(造影剂滞留于肾实质或包膜破裂渗入腹腔)。病变血管分布于叶间动脉7例,下段动脉4例,副肾动脉1例,1例无明显血管病变。11例患者使用弹簧钢圈或PVA颗粒行超选择栓塞治疗;2例患者皆因肾动脉下段动脉分支解剖变异大,无法超选择栓塞治疗行肾动脉覆膜支架置入术,分别置入5 mm×2 cm和5×3 cm的覆膜支架。
所有患者均治疗成功,术后未再出血活动性出血且生命体征稳定,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停止下降并逐渐上升。1例患者术后3 d再次行介入治疗,造影显示原栓塞血管部位的小分支未见造影剂外溢,且发现与其共干的另1支小分支活动性出血,随后进行栓塞。3例患者术后出现腰部胀痛加重、低热等表现,考虑与局部肾梗死相关,经对症治疗后缓解;术后复查肾功能较术前无变化。随访5~71个月(平均27.9个月)未再发肾出血,随访期间患者血压与治疗前未见明显变化。
3 讨 论
医源性肾出血是指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因针刺、切割、撕裂等各种原因损伤肾脏血管导致急性或迟发性出血,是医源性肾损伤中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处理不当或处理不及时都可能危及患者生命并引起医疗纠纷。经皮肾镜取石或肾活检术的肾穿刺通道造成的血管损伤最为常见,肾移植术后、部分肾切除术后吻合口出血或血管内介入治疗中导丝或导管损伤肾动脉分支亦为常见原因[1]。医源性损伤造成肾动静瘘和假性动脉瘤的形成,高动脉压使血液经针刺通道向肾静脉、肾盂或包膜下渗漏[2]。文献报道,肾穿刺活检后肾脏周围血肿发生率为34.1%~60.0%,多数患者临床症状轻微或无症状,数日内血肿可自行消退;较大血肿的发生率为0.5%~1.5%,为肾脏撕裂或损伤较大的动脉所致,需介入干预避免迟发性出血[1,3]。FURNESS等[4]报道在肾移植患者中肾活检血管损伤的主要诱因有高血压、肾髓质疾病等。硬化性肾脏、较大的动脉分支损伤、多穿刺针数和存在感染、肾血管壁高纤溶活性、尿毒症、动脉周围支持组织缺乏等将延长血管穿刺处的愈合[2]。PCNL术后出血可能与反复穿刺、筋膜扩张器边缘损伤肾段或叶间动脉,随呼吸运动切割肾实质或因进入过深损伤肾盂对侧或肾黏膜下血管、术后过度剧烈活动致血痂脱落等原因相关;血管损伤可发生在操作的任何时候,尤其是穿刺方向过于居中或指向肾盂[5]。TURNA等[6]报道PCNL术中采用多个通道的患者出血的机会成倍增加,出血还与穿刺通道位置是否恰当、是否伴有高血压、肾功能损害程度、感染、糖尿病、结石位置、形态和成分以及手术时间等有关。部分性肾切除术等外科手术术中可能因低温小动脉痉挛等原因未及时发现小血管损伤导致术后出血。静脉性出血因肾内静脉系统弹性较大往往可以自行停止。迟发性出血多因假性动脉瘤破裂或小动脉血痂脱落复发出血导致;保守治疗无效的严重出血往往因动脉分支损伤所致。
肾动脉通常在分出肾上腺下动脉、肾包膜动脉、肾盂输尿管动脉后,分为2条终末支,分别经肾门在肾盂的前方和后方进入肾脏,称为腹侧支和背侧支。腹侧支和背侧支在肾内再逐级分支,分出段、叶间、弓状及小叶间动脉。肾动脉变异较常见,主要有肾动脉提前分支和副肾动脉供血两种,不经肾门而在肾上端或下端直接入肾的上段或下段动脉分别称为上极动脉和下极动脉,也统称为副肾动脉,约在三分之一的人群中出现;其来源可起自肾动脉(63%)、腹主动脉(30.6%)或腹主动脉与肾动脉起始部的交角处[7-8]。下段动脉或下极副肾动脉供应的是肾盂和输尿管上段的血供,肾段之间无吻合支,每一支均为某一区域血供的终末动脉,所以变异分支的误扎、误切将导致相应供血区的肾实质发生坏死;需重视医源性操作前肾脏血管解剖变异的识别,在肾移植和腹腔镜手术等微创治疗中尤为重要,CT增强血管造影可以提供准确的评价[9-10]。
肾动脉造影检查能立即对病变部位、范围、血管解剖、形态作出准确判断,是肾脏血管损伤的诊断的金标准;其可同时经导管迅速闭塞肾动脉分支以控制出血,并最大限度保留正常肾组织,操作简便,避免开放性手术给患者带来更大的损伤;微型导管、微型钢圈及高分辨率数字化影像导向技术的运用大大提高了血管内栓塞治疗的精准度和安全性[11-12]。医源性肾血管损伤以肾实质内型多见,应以彻底止血、最大限度的保留肾组织为原则。既往外科剖腹探查术为主要的治疗手段,但因肾周血肿、组织粘连重、解剖结构不清等原因,结扎损伤血管等手术难度和手术创伤均较大;如果只做肾修补或肾脏部分切除术,手术复杂且止血成功率不高,术后仍可发生迟发性出血,出血严重者需作患侧肾脏全切术;目前外科手术多作为介入治疗无效的补救治疗手段。
医源性肾出血的损伤血管多与穿刺部位一致,多见于穿刺侧肾脏下极。DSA造影检查最常见表现是造影剂外溢呈团状、片状造影聚集;其次为单独或合并肾动静脉瘘,表现为动脉期肾静脉显影;再次是出血沿肾造瘘管边缘流入肾盂。造影时应低压、低速注射,避免高压、高速注射引起细小血管内压剧增、使血管破裂或已形成血栓的破损血管再次破裂、加重肾损伤。血管造影应该全面,避免遗漏副肾动脉、肾脏包膜动脉等;肾段动脉的分支叶间动脉或弓形动脉近端出血以及副肾动脉出血易漏诊,应根据临床穿刺部位超选择至肾段动脉行DSA造影,以便显示出肾段动脉末梢的出血点。在肾动脉主干造影未发现活动性出血及可疑病变者,可根据穿刺损伤位置进行超选择血管造影,以提高血管造影检查的阳性率。栓塞前要确认异常血管,肾动脉常因自身的扭曲和多支肾动脉以及分支的重叠需多角度投照。部分患者可能因血肿或造瘘管压迫未显示明显出血征象,需仔细观察是否有出血沿肾瘘管边缘流入肾盂。对于血管造影未能明确出血部位的患者,尤其是再次出血的患者,可根据穿刺部位的解剖走行进行预防性超选择栓塞治疗,造影明确出血病变后,血管内栓塞治疗因快速、微创、安全、有效已成为首选的治疗手段[13-15]。假性动脉瘤形成是由于穿刺、扩张通道时损伤动脉壁后造成搏动性血肿,血肿周围纤维包裹与动脉腔相通所致,栓塞治疗时只需栓塞其载瘤动脉而并不需瘤内填塞治疗;动静脉瘘形成是由于术中同时损伤相邻动静脉,动脉血直接进入静脉内所致,医源性肾损伤中多为肾实质局部AVF,使用弹簧钢圈或PVA颗粒等永久性栓塞剂闭塞瘘口和供血动脉。可选用的栓塞材料包括明胶海绵、弹簧圈、PVA颗粒和NBCA胶等;弹簧圈依然是最常用、最安全的栓塞材料。术中推注栓塞剂,只有在使用微导管插管至肾段动脉小分支时才用PVA,宜少量多次间隙栓塞,防止过度栓塞。对于血管造影未能明确出血且伴有肾脏反复出血或迟发性出血的高危患者,笔者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使用PVA颗粒超选择栓塞穿刺部位的叶间动脉分支,为避免影响可能的二期治疗,未使用弹簧钢圈。
覆膜支架已在肾动脉瘤、肾动脉主干假性动脉瘤出血等肾血管损伤中成功应用,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16-17]。笔者所行的2例支架置入术患者,皆为下段动脉小分支出血,因血管解剖变异与肾动脉主干成锐角,暂无合适头端导管进行超选择栓塞;因出血部位为肾实质内,外科治疗风险、损伤大;于肾动脉主干非选择栓塞治疗可使全肾梗死代价极大;笔者测量肾动脉主干的长度和直径,选取恰当长度和直径的支架以保证可完全覆盖瘘口或闭塞血管,又尽量不影响正常分支血供;2例患者分别选取5 mm×2 cm和5 mm×3 cm直径的覆膜支架,支架置入后复查造影示未见造影剂外溢,闭塞血管范围均小于40%,其中1例患者术前造影示另有一副肾动脉供应肾下极血供。患者术后随访3个月和9个月均未出现狭窄和再出血。此类患者内膜增生导致的远期支架再狭窄发生的风险尚不明了,有待于进一步的长期随访。
目前本中心医源性肾出血的介入治疗指征主要为:术后血红蛋白进行性下降伴有生命体征不平稳、药物保守治疗好转后再次发生出血、需要输注红细胞悬液超过2 U和影像学检查提示肾周或腹膜后积血或伴有动静脉瘘、假性动脉瘤者。在急诊介入治疗前需与主管医师和患者同时进行充分沟通,最大程度保证医疗安全。介入治疗的并发症较为少见,如栓塞后综合征、造影剂急性肾损伤、肾功能不全、高血压等,多出现在造影剂大量使用或栓塞肾动脉主干等情况下。本研究中并未出现上述症状,且在治疗前持续给予充分补液及水化治疗,尽可能减少肾脏低灌注的风险。1例患者在肾活检合并出血后出现肾功能恶化,在栓塞治疗术后复查肾功能未发现血肌酐进行性加重,且在出院后肾功能降至活检前基线水平。1例患者置入支架时遮挡了部分肾下段动脉分支血供,但其尚有副肾下极动脉供血,患者下段肾脏未出现缺血表现。笔者认为超选择栓塞治疗是预防介入并发症发生最基本的要求;对于确实病情紧急又难以行超选择栓塞治疗的患者,在置入支架移植物前,一定要根据肾动脉分支的距离、直径来选择合适的支架,以最大限度的保护肾血供。
总之,医源性肾血管损伤性出血经保守治疗效果不明显者应积极实施急诊介入治疗,以尽早控制出血,保护肾功能。经皮选择性肾动脉造影能对医源性术后出血病变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可与急诊超声或CT相互结合,明确病变部位与性质。超选择肾动脉栓塞治疗具有止血快、疗效确切、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等优点,可作为保守治疗无效的医源性肾血管损伤性出血的首选治疗手段;而肾动脉覆膜支架植入术可作为难以行超选择栓塞治疗的急诊替代治疗手段。在血管造影阴性的高危出血患者,可考虑预防性超选择栓塞治疗,以降低患者再出血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