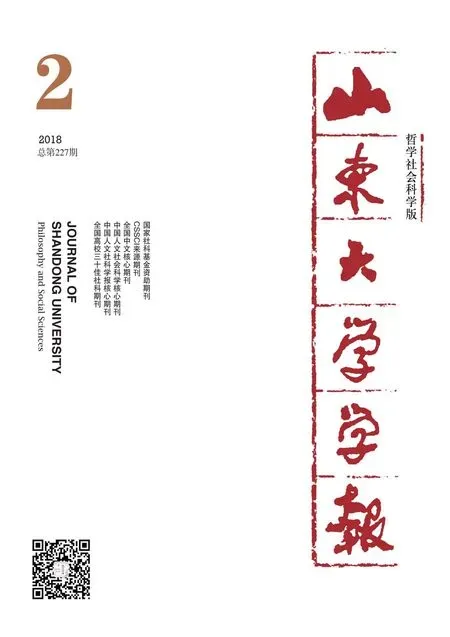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中的三个理论问题
2018-03-19黄俊杰
黄俊杰
一、引言
儒学传统是东亚文明的公分母,源起于中国山东半岛的儒家精神,数千年来呵护着东亚各国子民,抚慰东亚人民的创伤,与东亚人民共呼吸、同甘苦。记录先秦孔门师生对话的《论语》,是对东亚各国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儒家经典,《论语》中的核心价值就是“仁”,环绕着“仁”学的相关概念(如“礼”“义”等)与命题(如“克己复礼为仁”“仁者,心之德、爱之理”等),数千年来历经中、韩、日各国思想家的解释*黄俊杰:《东亚儒家仁学史论》,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第1-6页。,胜义迭出,赋予东亚儒学传统以新生命,也对诸多思想交流中的理论问题有所启示。
本文以东亚儒者对“仁”及相关概念或命题之解释为中心,并以儒者对《论语》与《孟子》的诠释为例证,探讨儒家经典解释学中的三个具有理论意趣的问题:(1)思想原创者的所有权问题;(2)思想交流中的“脉络性转换”与解释者的自由度问题;(3)诠释的无政府主义问题。
二、思想原创者的所有权问题
(一)思想的自主性
从东亚地区儒家学者透过经典解释而进行的思想交流经验中,所显示的第一个理论问题是:相对于后代的诠释者而言,思想的原创者对他自己的思想是否拥有所有权以及对他人诠释之正确与否的“终审权”?
从东亚儒家经典解释史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任何思想概念或命题,一经原创者如孔子(公元前551-479)或朱子(1130-1200)提出之后,就取得自主性,恍似具有独立的生命,翱翔于天地之间,等待经典阅读者提出“心解”*张载(1020-1077)云:“心解则求义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万物纷错于前,不足为害;……。”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第276页。,并与异代异域经典“知音”*刘勰(约464-522)就曾大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刘勰著,黄淑琳注:《文心雕龙注》卷10《知音》,台北:开明书局,1975年,第13页左。亲切对话。在经典与读者的对话之中,读者从经典中开发新的问题,也提出新的解释。
我想以东亚儒家“仁”学发展史为例,说明思想命题一经原创者提出之后,就取得自主性这个事实。东亚儒家“仁”学发展史波涛壮阔,孔子与朱子双峰并峙。孔子所揭橥的“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是儒家“仁”学史第一个高峰。当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说之后,“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就脱离了孔子,而取得了独立自主的生命,中国古代儒家学者各自怀抱着自己的思想立场与时代背景,面对“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进行解释。我在新刊拙著中,曾归纳两千年来中国儒者在解释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时,读入了三大问题:(1)“克己复礼”如何可能?其理论基础何在?(2)何以“一日克己复礼”就可以“天下归仁”?(3)“克己复礼为仁”与“为仁由己”两说是否冲突?何以故?第一个问题涉及自我观与人性论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人我关系,亦即“自我”与“世界”关系之问题;第三个问题则涉及修养工夫论中之逆袭或顺取工夫之问题,也涉及“自我”是被决定之客体或是可以自作主宰的“道德主体”这个问题*黄俊杰:《东亚儒家仁学史论》,第180-181页。。
这三个问题在孔子精简而素朴的表述之中,原处于潜藏之状态,三者皆郁而不发,必待后代《论语》的解释者之阐释,才能全幅舒展。这三个问题之所以可以从潜藏迈向发露,固然牵涉多方,例如解释者所身处的时空情境、解释者个人的原创性等因素,都产生相当的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是:当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时,这项命题就脱离原创者而成为天壤之间独立自主的存在,成为后人可以印可、推衍、争论或质疑的命题,等待后人赋予新生命。也因为思想命题一旦提出之后,就取得自主性,所以记载这项命题的《论语》这部经典,也就取得了开放性,对异代异域的解读者完全敞开,接纳他们,与他们亲切对话,使他们可以出新解于陈编。
(二)思想的“自主性”之表现
正是从“克己复礼为仁”这项思想命题的自主性,我们看到东亚儒家“仁”学解释史所呈现的两个现象:
1.解释即是创造。儒家经典解释者每一次所提出的新解释,都是一次的再创造,而且这种再创造是通过解释者个人的思想系统或生命体验而完成的。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说:“所有的再现首先都是解释(Auslegung),而且要作为这样的解释,再现才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再现也就是‘理解’。”*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补充和索引》,洪汉鼎等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第487-488页。伽达默尔所说的完全可以在儒家“仁”学诠释史上获得证实。东亚各国儒者每一次对“克己复礼为仁”说的“再现”,都是一次再创造与再解释,而且常常是从最重要的关键词切入。
从后代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说的解释来看,最核心的是对于“克”与“己”这两个关键词的涵义之解释。“克”字有二训,一是以“胜”训“克”,自东汉马融(79-166)*何晏集解,皇侃义疏,鲍廷博校:《论语集解义疏》卷6,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知不足斋丛书本),1966年,第23-24页。、隋代刘炫(约546-613)*刘炫:《春秋左氏传述义》(丛书集成续编)第13函65册,台北:艺文印书馆(据清嘉庆王辑刊本影印),1970年,第27页。,以至朱子均循这条思路;二是以“能”训“克”,宋代心学一系儒者杨简(1141-1225)*杨简:《慈湖遗书》卷11,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年,第35-36页。发皇此说。这两种解释进路虽然仅一字之差,但相去甚远。以“胜”训“克”的解释者,都采取“道德的二元论”(moral dualism)立场,将“自我”视为应予矫治的对象;采取以“能”训“克”的解释者,均采取“心”即“理”的立场,认为充分展现“自我”即可臻于“仁”之境界。但这两种解释者,都是通过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或生命体验而对“克己复礼为仁”说提出解释,也可以说,他们都是通过自我理解而理解孔子。
2.解释者比文本更重要。东亚儒家“仁”学之所以能够经两千年而绵延不绝,繁衍壮大,固然是因为孔子与朱子所提出的命题本身具有自主性与开放性,穿越时空而召唤异时异地的儒者,起而向他们叩问,与他们对话。但是,就儒学诠释史观之,比“文本的开放性”*里克尔(Paul Ricoeur, 1913-2005)特别强调诠释过程中文本(例如一部经典或一幅画作)的自主性与开放性。Paul Ricoeur, ed. and tr. by John B. Thompson,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39.更重要的是文本的解读者的角色。在东亚儒家传统中,经典研读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在于经典文义的解明,而是在于经典阅读者受到经典的感召,而将经典中的价值理念含纳入自己的身心之中,并使自己的精神与生命境界获得提升。因此,几千年来东亚各国儒者阅读经典所采取的是一种所谓“入乎其内”(emic)的读经方法,他们不只是经典中的命题或价值的观察者,他们更是介入者与参与者。北宋程颐(1033-1107)说:“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3页。伊藤仁斋(1627-1705)在《语孟字义·序》中强调研读《论语》要掌握《论语》的“血脉”,而不是“意味”*这是仁斋自己的用语。仁斋说:“学问之法,予歧为二:曰血脉,曰意味。‘血脉’者,谓圣贤道统之旨,若孟子所谓仁义之说是也。‘意味’者,即圣贤书中意味是也。盖意味本自血脉中来,故学者当先理会血脉;若不理会血脉,则犹船之无柁,宵之无烛,茫乎不知其所底止。”伊藤仁斋:《语孟字义》,见井上哲次郎、蟹江义丸编:《日本伦理从编》卷之五《古学派の部(中)》卷下,东京:育成会,1901-1903年,第50页。。伊川与仁斋都强调诠释者必须以参与者的角色,与具有独立自主性的经典及其命题进行深刻的对话。
以上这两种儒家经典诠释史常见的现象,都印证了:思想的原创者一旦提出某一个命题(如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之后,这项命题就取得独立自主的生命,可以与后代的解释者互相对话,从而使孔子的“仁”学繁衍发展。思想的原创者不能独占思想命题的所有权,更不能对后人的解释拥有“终审权”。但是,我们却不能说“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换取”*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因为思想的原创者虽然已经远逝,沉魄浮魂难以召唤,但是,原创者所留下的文本,对于后人的诠释,也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因为任何创新的解释,都必须在文本可以印证的范围之内,才能获得其他读者的认可。
三、思想交流中的“脉络性转换”与解释者的自由度问题
(一)“脉络性转换”中的制约因素
儒家经典解释史所触及的第二个问题是:解释者的自由度问题。更精确地说,在何种程度之内,在什么意义之下,解释者是自由的?这个问题与思想交流中所见的“脉络性转换”(contextual turn)*关于“脉络性转换”的讨论,参看:Chun-chieh Huang, 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Texts in Contexts, Göttingen and Taipei: V&R unipress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5, chap.2, pp.41-56.有其深刻之关系。我在拙著中,曾以“脉络性转换”为主轴分析儒家仁学的发展与创新。简言之,所谓“脉络性转换”指将思想或命题从其原生的脉络逸脱而出(“去脉络化”),再流入新的脉络(“再脉络化”)之后,必然产生的转变。这种所谓“脉络性转换”,又可区分为两种类型:(1)思想脉络的转化;(2)空间(locality)脉络的转换。我在《东亚儒家仁学史论》第5章探讨中日韩各国佛门人士采取“由佛显儒”与“在佛摄儒”之解释策略,对儒家仁学所提出的新诠。佛门中人以“慈”“戒定慧”“此心之性真”等佛教思想重新解释儒家“仁”学之涵义,达到移花接木、偷龙转凤之诠释效应*黄俊杰:《东亚儒家仁学史论》,第211-298页。,这是在不同的思想脉络中的转换。另外,朱子《仁说》东传日韩之后,深深浸润在实学精神的日韩异域儒者,解构朱子学的形上学与宇宙论之基础,而在日用常行或政经措施中赋朱子仁学以新义*黄俊杰:《东亚儒家仁学史论》,第299-329页。。日韩儒者也在“功效伦理学”脉络中重新解释中国儒家“仁政”之意涵*黄俊杰:《东亚儒家仁学史论》,第377-453页。。这是在不同的空间脉络中的转换。
那么,异时异地解释者的自由度有多大呢?从东亚儒学史的经验来看,解释的自由度恐怕仍是很有限的,因为他们的解释至少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制约:
1.时代氛围的浸润。解释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时代思想氛围的产物,他们对经典中的核心价值(如“仁”)或命题(如“克己复礼为仁”)提出新解时,他们都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都不免时时受到他们身处的时代思想氛围的影响,诚如青年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所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页。
是的,思想家在他们所身处的时代氛围以及先行思想中进行创新。南宋孝宗干道九(1173)年,朱子撰《仁说》一文,是孔子以后儒家“仁”学发展之另一高峰,但《仁说》起首就引程颢(1032-1085)“天地以生物为心”*《河南程氏遗书》卷3,《二程集》上册,第366页。陈荣捷先生从明人沈桂之说,认为此语出自程明道,今从其说。见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下册,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第766页。一语,接着申论“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朱熹:《仁说》,陈俊民校订:《朱子文集》卷67,台北:财团法人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3390页。,并以“爱之理”释“仁”*朱熹:《仁说》,陈俊民校订:《朱子文集》卷67,第3391页。。相对于先秦孔门之以“爱人”言“仁”(《论语·颜渊·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9页。以及孟子说“仁者爱人”(《孟子·尽心上·4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63页。而言,朱子将“仁”解释成“爱之所以然之理”*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3册,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第244页。,可谓石破天惊,将“仁”学论述提升到本体论的层次,也提升了中国人生命感的高度。但是,朱子“仁”学的创新确有所承,而且深深地浸润在北宋以降“理”学的思想氛围之中。
2.原典文本之印可。后代的解释者虽然可以“自由”地对孔子或朱子的命题提出新解释,但是,这种“自由”是在原典文本所印可的前提之下的“自由”。诠释如果背离了原典文本,就成为个人哲学之表述,而不是对原典文本之诠释。这种情况很像篮球比赛中的每一个球员,固然都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球技与才华,但是,球员的“自由”确是建立在所有球员都服从篮球比赛规则的前提之上。
在以上两项因素的制约之下,多数解释者都是在继承之中有所创新,是“既述且作”,或是“寓作于述”,而不是“述而不作”。他们的解经事业,必须在“述”与“作”之间,力求获得创造性的动态平衡。
(二)在“诠释的权威”下的抉择
我曾归纳东亚儒家学者在诠释经典中的核心概念或命题时,必须面对三种“诠释的权威”:第一是孔孟的权威,第二是朱子的权威,第三是中日韩各国前辈学者的权威,如退溪学之于朝鲜儒者,仁斋学之于德川儒者*黄俊杰:《东亚儒家仁学史论》,第73-74页。。东亚儒者的新诠,必须力求在这三种权威之间获得平衡或同意。
但问题是:如果以上所说的三种不同层次的“诠释的权威”互相抵牾时,则解释者当如之何?从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来看,诠释者常采取的是以下两种抉择:
1.以解释者自己所认同的“权威”为最终判准。这种现象最常见于诠释多歧的关键命题,如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孟子的“知言养气说”,或者《孟子·告子上》各章,后代儒者的解释常常必须在诸多异说之中,抉择他们所认同的权威。我以朱子对孟子的解释为例加以说明。
《孟子·告子上·6》在孟子人性论中,特居首出之地位。孟子在与公都子讨论人性问题时,正式提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28页。的主张,并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28页。。孟子这种看法与朱子的理气二元论下的人性论,显然差距甚大,所以,朱子在诠释孟子时,先引一大段程颐与张载(1020-1077)的说法,再以“愚按”提出他自己的判断: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则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学而知之,则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性之本,汤、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则自暴自弃之人也。”又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愚按:程子此说才字,与孟子本文小异。盖孟子专以其发于性者言之,故以为才无不善;程子兼指其禀于气者言之,则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张子所谓气质之性是也。二说虽殊,各有所当,然以事理考之,程子为密。盖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学者所当深玩也。*朱熹:《孟子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卷11,第400页。
朱子面对孟子与程子说法的冲突,他认为“然以事理考之,程子为密”,决定采取程子“性即理”的立场。朱子以他自己所认同的“诠释的权威”作为抉择的判准。
2.诠释者经过抉择后,决定以自己的思想立场批驳“诠释的权威”。从孔子以后,东亚儒学史上最大的“诠释的权威”就是朱子。朱子毕生理会《四书》,将汉注唐疏与北宋诸老先生诸说融于一炉而冶之,勒成体系,14世纪以降中日韩等东亚地区儒者,皆必须面对朱子学的“诠释的权威”。东亚儒者可以赞同朱子,可以与朱子争辩,可以反驳朱子,但无法绕过朱子。元仁宗(在位于1311-1319)皇庆二年(1313)之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中国科举考试的定本*宋濂:《元史》卷81《选举志》,四库备要本,第3a页。,对中国、韩鲜、日本知识阶层思想之形成影响更是深远。德川日本儒者如林罗山(1583-1657)、中江藤树(1608-1648)等日本朱子学的开山大师固然都是浸润在朱子学之中,伊藤仁斋(1627-1705)中年时代所撰《仁说》,基本上依循朱子《仁说》之思路;16世纪朝鲜的李退溪(1502-1571)更穷数十年编成《朱子书节要》*李滉:《朱子书节要序》,《陶山全书》3,首尔:退溪学书院,1988年。。我们可以说,朱子学正是近七百年来东亚儒学家最重大的思想典范。
正因为朱子学是东亚近世最重要的“诠释的权威”,所以东亚近世儒者一旦决定告别朱子,就必须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王阳明(1472-1529)的思想自剖最能将这种精神压力与心路历程和盘托出。王阳明说:
……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陈荣捷:《传习录》第176条,第253页。参考陈荣捷:《从朱子晚年定论看阳明之于朱子》,陈荣捷:《朱学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353-383页。
东亚近世许多儒者都经过类似王阳明的学思历程,他们对朱子“诠释的权威”之扬弃,从东亚儒者解释先秦儒家的一些重要概念时,最能透漏其消息,而这种“诠释的转折”均以解释者个人的思想立场为其理据。
我们再以“克己复礼为仁”说解释之变化为例说明。朱子为“克己复礼为仁”说提出了以“理气二元论”作为基础的解释典范,在“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的“道德二元论”架构中,以“胜”训“克”,并将“己”解为“己身之私欲”。朱子的解释作为“诠释的权威”的地位,从明末开始就受到阳明后学如邹守益(1491-1562)、王龙溪(1498-1583)、罗近溪(1515-1588)等人的批判,阳明后学本于“致良知”之教,主张人性本善,以“能”训“克”。他们的诠释与南宋杨简(1141-1225)之说*杨简:《慈湖遗书》卷11,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3年,第35-36页。互相呼应。到了18世纪戴震(1724-1777)论“克己复礼”,又经历另一个转折。戴震主张“礼”的精神在其“秩序性”,“能克己以还其至当不易之则……”“求其至当,即先务于知也”*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6-57页。。如果说朱子的“诠释的权威”是建立在“理”学的基础之上,那么,阳明后学批判并告别朱子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他们采取以“心”学为基础的新典范,而戴东原则更将“仁”与“礼”加以“知识化”,建构新的诠释典范。
东亚儒家经典解释者,对于先前的“诠释的权威”的批判或挑战,常常是通过自己思想体系的网络的筛选而完成的。在这种筛选过程中,自己的意见常自成段落,朱子就常以“愚按”*朱熹:《孟子集注》,《朱子全书》第6册卷11,第396页。起首表述己见。18世纪朝鲜丁茶山(1762-1836)在《论语古今注》中对朱注提出批判。我过去的研究曾指出:丁茶山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的解释,对朱子学既因袭而又创新。在“己”与“心”之二分以及“道心”之优位性,以及“克己”即为“复礼”这两项命题之上,完全循朱子之思路。但是,丁茶山在社会脉络与伦理脉络中掌握朱子的仁学,则与朱子特重“仁”之本体论意涵极不相同*黄俊杰:《从东亚儒学视域论朝鲜儒者丁茶山对〈论语〉“克己复礼”章的诠释》,黄俊杰:《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第207页。。
丁茶山对朱子“诠释的权威”的挑战,常另撰以(质疑)起首的文字,以下是一个例子:
(质疑)集注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案,仁者,人也,二人为仁,父子而尽其分则仁也,君臣而尽其分则仁也,夫妇而尽其分则仁也,仁之名必生于二人之间,近而五教,远而至于天下万姓,凡人与人尽其分,斯谓之仁,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仁字训诂,本宜如是……。*丁若镛:《论语古今注》,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编:《韩国经学资料集成》第27册,首尔: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88年,第453页。
在以上这一段(质疑)文字中,丁茶山批判朱子以“爱之理”解“仁”的旧说,主张“仁”必须在人与人之间各自完成其理分之后才能成立。
总之,东亚儒家经典的解释,固然享有相当程度的“既述且作”或“寓作于述”的“自由”,但是他们的“自由”诠释也必须能获得以上三种“诠释的权威”的印可。他们一旦发现自己的解释与既有的“权威”(尤其是朱子学的权威)有所背离,内心就不能免于拉扯的紧张,朱子《四书集注》中的“愚按”,或丁茶山的“质疑”等文字,正是他们纾解紧张的一种方式。
四、诠释的无政府主义问题
现在,我们讨论第三个问题:儒家经典超越时空而召唤东亚各国读者的心灵,起而与经典对话,说解纷纷,家自为书,人各为说,是否会出现经典诠释的无政府主义?
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从“诠释的无政府主义”的涵义开始。所谓“诠释的无政府主义”一词,常常在两个相对脉络中使用:
1.“一”与“多”的脉络。如果经典文本中的命题(如“克己复礼为仁”或“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也”)是“一”,那么,异代异域的解释者所提出的众说纷纭的解释就可被当作“多”。因为“多”是“一”的变异,所以“多”就被视为“诠释的无政府主义”。
这个意义下的“诠释的无政府主义”,乃是出于对经典诠释的误解,所以是不能成立的。就东亚儒家经典诠释的历史经验来看,经典诠释就是经典中的普世价值与时间/空间特性互动、对话、争辩、协商的过程。儒家经典及其价值理念原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深具中国文化之特质,一旦传播到异域,异时异地的解读者,必须“读入”具有“时间特色”(time-specific)与“空间特色”(site-specific)的社会文化因素,才能使经典中的价值理念融入并“风土化”于传入地。例如朱子的《仁说》将先秦孔门所揭橥的以“爱人”的“仁”之义,提升到作为“爱之存在的存在性”(用牟宗三先生之语)*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3册,第244页。的“爱之理”,从而将“仁”提升到宇宙论与本体论的高度。但是,朱子将伦理学建立在宇宙论与形上学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套以“理”学为基础的“仁”学大论述,与日本实学思想风土格格不入,所以,德川时代日本儒者莫不致力于解构朱子学中的形上学基础,并将“仁”学论述从天下拉回人间,将朱子“仁”学论述中的形上学与宇宙论转化为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提出各种多元多样的以实学思想为基础的“仁”学论述。
这种意义下的“多”,不但不减损“一”,反而使“一”的内涵更加丰富,而“多”的流注使“一”的生命更加绵延壮大。试以黄河为喻,源起于青海巴颜喀拉山的黄河源,原是潺潺小溪,但流经各省,不辞细流,终能源泉滚滚,汇成巨流,以奔腾之姿堂堂入海。但就异时异地的“多”的立场来看,正因为汇入“一”的大传统,而使“多”取得了新意义。正如作为“部分”的一根木材,如果弃之于荒野,终究只成为无用之木。但木材如果被放置在殿堂的正中央,就成为栋梁,使“部分”在“整体”之中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并被赋与新的意义。
所以,对经典及其价值理念的多元解释,绝不能被视为“诠释的无政府主义”。在东亚思想史中,日韩等地异域儒者对“仁”学的新诠,因为融入儒家“仁”学的大论述传统之中而获得新的定位,使其意义为之豁然开显,也使儒家“仁”学的主流论述,更加波涛壮阔,更加扣人心弦!
2.“同”与“异”的脉络。所谓“诠释的无政府主义”之说,也常常在“同一”与“歧异”相对的脉络之中提出,认为与“正统”(orthodoxy)不同的就是“异端”(heterodoxy),诸多“异端”遂构成“诠释的无政府主义”之乱象。
这种意义下的“诠释的无政府主义”之说,其实是建立在未经明言的一种主张之上:认为思考的原创者拥有思想或命题的所有权,也因此对后人的解释拥有“终审权”。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在经典解释史中,任何命题或概念,一旦由原创者提出之后就脱离原创者的掌握而取得了独立自主的生命,可以与异时异域的诠释者对话。
在经典与诠释者对话的过程中,经典的解读者居于主动之地位。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说,解释者比文本更重要。孟子说解读《诗经》应“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06页。,朱子解释“以意逆志”的“逆”字说:“逆者,等待之谓也”*黎靖德编:《朱子语类(1)》,《朱子全书》第14册卷11,上海与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6页。,或不免稍嫌消极。19世纪日本儒者西岛兰溪(1780-1852)说:“心无古今,志在作者,而意在后人,由百世下,迎溯百世曰逆,非谓听彼自至也”*西岛兰溪:《读孟丛钞》,关仪一郎编:《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第十三卷,卷9,东京:凤出版,1973年,第354页。,其说较贴近孟子“以意逆志”之原意。
正因为解释者与经典的对话中,解释者恒居于主动之地位,才能“以意逆志”,而且,儒家读经不仅读之以口耳,更读之以身心,他们将个人的生命体验读入经典之中,并取经典中的价值理念与命题而与自己的生命历程相印证。因为每一位解读者的学思历程与生命体验各不相同,所以,他们所开发的经典新诠亦多元多样,但我们并不能说他们就是“异端”,是“诠释的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在形式上诠释的多样性之下,他们都分享儒家的共同价值。因此,在表面的“歧异”之下,潜藏着深厚的“同一”,我们不能率尔以“诠释的无政府主义”称之。
总结本部分所说,解释者面对经典既不能完全强人以从己,又不能完全屈己以从人。经典的生命正是在“一”与“多”以及“同”与“异”的辩证之中绵延发展。
五、结论
本文以东亚儒家“仁”学诠释史为主轴,探讨三个具有理论意趣的问题。本文第二部分首先指出:思想命题一经原创者提出之后,就取得自主性,原创者无法拥有思想命题的所有权,也因此对于后人的诠释并不能拥有“终审权”。本文第三部分指出:虽然原创者并不能独霸思想命题的所有权,但是异代异域的解释者,在从事经典解释时也不能拥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浸润在自己的时代思想氛围之中,而且他们的“自由”解释也必须获得经典文本的印可。尤有甚者,经典诠释者的解经事业,也必须面对孔孟、朱子以及他们各自国家前辈的“诠释的权威”的印证,也在“述”与“作”之间求其平衡。本文第四部分接着指出:因为经典诠释活动是经典中的普世价值与时间/空间特性的互动之过程,更是一种作为主体的解释者与作为客体的经典文本的对话过程,所以,双方互为创造,此其间并无所谓“诠释的无政府主义”之问题。
综合本文论述,我想提出以下两项结论性的看法:
第一,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读者的身心如何受经典精神之感召而自我转化?所以,中日韩各国儒者都以个人生命之体验与经典相印证。我们可以说,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学,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一种“实践诠释学”(praxis hermeneutics),读经的目的在于行经,读经不是“概念的游戏”,也不是纯粹理论的推衍。简言之,东亚儒家在经典诠释中读入个人生命之体验、体会与体知,所以,他们对同一个命题常常能提出多元的诠释,也从中赋与经典以崭新的生命力。
第二,东亚儒家在诉诸个人生命体验的“自由”,必须在与“诠释的权威”相印证的“秩序”之中,进行创造性的诠释。他们也在经典中的普遍命题与地域特性的互动之中,完成经典意义的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