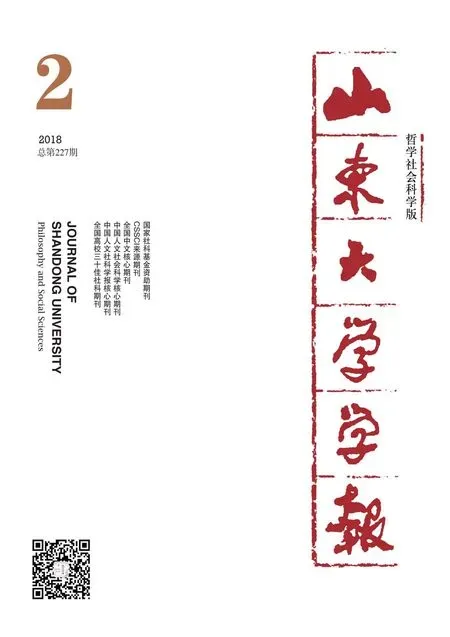从互惠性到宽容性:法律责任构造逻辑的嬗变
2018-03-19郑智航
郑智航
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来看,早期资本主义主要奉行的是一种主体性的观念。它要求法律全面地贯彻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以及人道主义基本理念,并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这种主体性的观念在法律责任领域体现为对过错、互惠以及泄愤的强调。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来看,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或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奉行的是一种主体性的观念,因此,本文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或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定义为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法律责任奉行的这套逻辑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人们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这种艰难发展中愈来愈意识到主体性观念和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的缺陷与不足,从而导致人们对以主体性为支撑的现代社会愈来愈多批判与反思。这种反思与批判在事实上推动了法律责任构造逻辑的嬗变。
一、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法律责任的互惠性逻辑
(一)从结果责任到过错责任
从前现代社会*本文所说的“前现代社会”主要是指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欧社会。到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法律责任经历了一个从结果责任到过错责任的转变。在前现代社会,由于认识能力受到神学钳制,人们往往在法律责任认定方面主张结果责任,即有加害就有责任,并且责任的承担形式主要是一套野蛮、粗陋和严酷的刑罚。公元9世纪法兰克王国制定了《撒利克法典》,该法典共有489个条文,其中有343个条文是禁止犯罪的。从立法技术上讲,该法规定得特别具体,而法律条文的抽象性严重不足。这主要是由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所决定的。在关于人身侵害的规定中,该法典第41条规定:杀死一个法兰克自由人或一个归属撒利克法律管辖的蛮人,应罚付8000银币;杀死一个为国王服务的男人或同样的自由人妇女应罚付24000银币等。另外,该法还对伤害一只手臂、一只脚、一只眼、一条腿、一个指头等应当支付多少罚金做出了具体规定*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61-62页。。这种结果责任原则是不考虑当事人是否有过错的,因为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蛮族王国自给自足的世袭领主庄园在社会结构中愈来愈发挥重要作用*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第59页。。然而,当时罗马人开办的公共学校被关闭,教育主要掌握在教会手里,这些世袭领主接受的教育很少,甚至很多人都不认识字。他们更多地是从形象思维的角度,而不是也不会从抽象思维的角度来认识事物。他们也不能够充分地认识人的心理活动,甚至还没有意识到人的心理活动的存在*“心理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关于“灵魂”的学问。但是直到19世纪初叶,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才首次提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参见鲁忠义:《心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发展推断出中世纪前期,人们很难有意识地去总结人的思维活动的规律。。而以“有加害就有责任”为核心的结果责任原则具有直接性,在具体的实践中也具有更强的操作性。从当时纠纷解决的角度来看,这种严格责任具有合理性。前现代社会主要以神明裁判和决斗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假如采取过错责任原则就会与神明裁判和决斗相违背,因为人的内心世界是由神来控制的,也只有神才能够理解。
随着神学的衰落与科学的发展,人的认识能力逐步增强,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人的行为是由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两个方面来决定的。因此,法律对于行为进行评价时,也会考虑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两个方面。“(特别是)在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功利的口号下,资产阶级民法把所谓‘个人人格的绝对尊重’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因而它的整个民事规范都以‘私法自治’相标榜”*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第76页。。这种“私法自治”表现为在所有的私法制度中都强调意思自治原则,它强调的是个人意志处于自由状态。所谓自由,也就是个人能够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与限制。在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人只能在自由的状态下承担相应的责任,人在不自由的状态下所从事的行为是不承担责任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9页。,因为这种不自由状态违背了以人的意思自治为核心的私法自治原则。这也就慢慢地演变成了过错责任原则,并且在民法中逐步取得了支配性地位。例如为《法国民法典》的制定进行理论奠基工作的法国学者多马特和波西尔,在当时都倾向于只有有过错的人才应承担责任。德国法学家耶林也提出了“不是损害而是过错造成了责任”*引自王军:《侵权法上严格责任的原理和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的著名论断。在这种责任观的认识下,过错责任原则在19世纪晚期的侵权法中取得了支配性地位*例如1869年《阿根廷民法典》规定:“任何因故意或过错而致人损害的行为人,均应对此损失作出赔偿。”1889年《西班牙民法典》规定:“凡致他人以不法损害的故意或过失行为,均应对所致损害负赔偿责任。” 1896年《日本民法典》规定:“故意或因过失侵犯他人权利者,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另一方面,过错责任也是刑事责任归责的基本原则。法官在判定一个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首先要看其是否具有犯罪意图,而这种犯罪意图就是该人是否有故意或过失,假如没有犯罪意图即使有危害行为的发生,也不构成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相反,假如有犯罪意图,并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即使危害结果没有发生,也构成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对此,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首次规定了犯罪未遂的概念和处罚原则,这一规定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它纠正了以前刑法所奉行的“客观归罪原则”。
(二)过错责任、互惠与法律责任的泄愤性
从结果责任到过错责任的发展受到了源自于前现代社会法律中的互惠性观念的影响,并且在民事责任领域和刑事责任领域逐步形成了一种以过错为核心的互惠性责任范式(the paradigm of reciprocity)*王立峰在《惩罚的哲理》一书中考察了刑事责任与互惠性的关系。参见王立峰:《惩罚的哲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乔治·弗莱彻在1972年发表了《侵权法理论中的公平与效用》一文,阐述了两种可以用来理解侵权法不同作用的责任范式(paradigm),即以基于过错的道德标准而产生的互惠性范式(reciprocity paradigm),以及以功利主义的计算为基础的合理性范式(reasonableness paradigm),并认为前者更能对个人的权利提供更加周全的保护。See George P. Fletcher,Fairness and Utility in Tort Theory, Harvard Law Review,1972.3.。在互惠性法律责任范式看来, 法律所要实现的正义主要是一种矫正正义。这种正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正义是一种自愿遵守规范的行为,但是这种自愿态度是有条件的,即社会其他成员也做有利于他人的事,而不做不利于他人的事。第二,正义侧重于不损人利己,正义的人是根据他人是否回报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人遵守正义规则的目的在于实现自己的欲望。第三,正义以相互间承诺遵守非个人性规范为前提。在承诺遵守这种规范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对他人做出承诺,保证不伤害他们的合法利益,而他人对我们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参见慈继伟:《正义的两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8-20页。。人们将这种正义称为互惠性正义或等利害交换正义。用赵汀阳先生的话说,“无论对于人际关系还是事际关系公正的对等性首先表现为‘等价交换原则’,即某人以某种方式对待他人,所以他人也以这种方式对他,或者某人以某种东西与他人交换与之等值的东西”*赵汀阳:《论可能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40页。。
在这种互惠性正义的指引下,启蒙哲学家也从互惠性或等利害交换的角度来看待法律责任问题。
一方面,这种互惠性强调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对等关系,这种对等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当事人之间在权利或利益的总量上具有对等性,例如你有生命权,我也有生命权;又比如人与人之间签订一个买卖合同,也就意味着,一方具有获得货物的权利,另一方具有获得价款的权利。二是当事人在相处的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以及认识风险的能力是对等的。这种对等性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平衡。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也就意味着有一个别的因素进入了这种关系中并起到了破坏作用,而这个因素就是一方因为过错而背信弃义。对此,弗莱彻解释到:互惠首先意味着风险的对等性,既然风险对彼此而言是对等的,那么发生纠纷的原因就在于一方存在过错,从而在既有平衡关系中引入了不平衡因素。例如原告驾车沿着公路行驶,别的驾驶者给原告造成的风险,大致上相当于原告给其他驾驶者造成的风险。因此,他们的风险是对等的。这种风险存在的对等性要求有过错的一方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既然发生损害的概率对每个人而言是对等的,那么一方当事人侵害另一方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侵害人的过错在损害发生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ee George P. Fletcher,Fairness and Utility in Tort Theory, Harvard Law Review,1972.3.。
另一方面,这种互惠性强调责任与损害之间的对等性。所谓法律责任,主要是指损害发生以后,当事人之间如何进行损害分担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法律设定责任制度主要是为了通过矫正正义的实现来保障分配正义的实现。在以过错责任为核心的互惠性责任范式中,损害与责任之间是一种等利害交换的关系。“等(利)害交换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损害社会和别人,那么他也受到同等的损害。这样,他便不会轻易损害社会和别人了。所以等(利)害交换能够使人们避免相互损害,赋予社会和人们以安全,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际交往,因而是道德的”*王立峰:《惩罚的哲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8页。。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互惠性的法律责任观是建立在人的“反应性态度”上的,亦即我们把别人对我们的态度和意向联系起来,并且这种个人感受和反应程度,依赖于或包含着我们对这些态度和意向的信念*约翰·马丁·费舍和马克·拉维扎认为,当我们承认某人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时,这里所包含的意思常常不仅仅是对他抱有某种特殊的信念,还包含着愿意对那个人采纳某种态度,以及以某些方式对他作出某种行为。例如,假设有一天晚上你回到家里,发现你的贵重的花瓶被摔碎了。当你发现该花瓶是被家里的一个有预谋的来客蓄意毁坏的,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反应就和你发现它是被你家的小猫不小心从架子上碰下来摔碎时那种反应大不相同。参见约翰·马丁·费舍、马克·拉维扎:《责任与控制——一种道德责任理论》,杨绍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6页。。因此,在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民法往往强调按照实际损失来进行赔偿。而就刑法而言,犯罪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破坏人与人之间互惠性或等利害关系原则的行为,“惩罚意味着让罪犯偿还他迄今为止所享有的所有好处”*慈继伟:《正义的两面》,第182页。。因此,法律责任的大小往往是以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为真正的衡量标尺*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67页。。“罪刑相适应原则”成为刑罚的一条基本原则。
在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法律责任在本质上体现了人具有一种算计的色彩。在霍布斯看来,理性就是一种计算,也就是对公认为标示和指代思想的那些普通名词所构成的序列进行加减*徐向东:《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政治辩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这种“算计”的理性,在法律责任方面是通过“反应性态度”体现出来的。彼得·斯特劳森认为人无法长期避免人际交往而丧失人性,但是只要与人交往,人们就会产生一种反应性态度(reactive attitudes)*Peter Strawson,Freedom and Resentment,London:Methuen,1974,p.24.。交往双方之所以发生生活上的关联,原因在于彼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对方的现实生活要求。彼此之间所作所为能够得到对方的回应,并且这种回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其付出等值的。因此,正义具有一种交换的性质。当一方因过错而违背了等(利)害原则,给另一方造成了伤害,受害人就会对此产生愤恨(resentment),其他社会成员会对此产生义愤(indignation),加害人则会由此产生负罪感(guilt)*斯特劳森的“反应性态度”理论在西方学术界获得了共识。见慈继伟:《正义的两面》,第12页。。在此基础上,受害人和其他社会成员就会产生泄愤的要求。所谓“泄愤”,“是指不是仅仅不喜欢他,而是对他持有一种否定性情感,这种否定性情感的根据是他所做枉行,这种情感带有不友好或侵犯性特征”*转引自王立峰:《惩罚的哲理》,第162页。。法律责任就是要保障这种泄愤要求能够顺利实现,因为“在社会纠纷中将愤恨情绪减少到最低限度,其重要意义并不表示愤恨是毫无价值或全然是邪恶的。……完全没有愤恨只表明缺乏社会智性和道德活力”*转引自王立峰:《惩罚的哲理》,第166-167页。。换句话说,法律责任使泄愤制度化、规范化,避免泄愤的非理性化而致使社会生活的失序。因此,过错责任具有了一种否定评价、教育和惩戒的功能。
与这种泄愤直接相关的是人们对于过错的理解。人们往往把过错责任与道德因素结合在一起。“当一个人被判定故意伤害了另一个人,这种伤害行为展示的是侵害人对受害人的蔑视,把自己的道德地位凌驾于受害人之上。受害人会因此激发出愤怒情感,产生惩罚动机并试图借此重新建立心理平衡,恢复受害人的道德地位”*对此问题的论述,参见王立峰:《惩罚的哲理》第160页;Vidmar,N.and Miller,Social Phychological Processes Underlying Attitudes Toward Legal Punishment, Law and Society,1980, 3. pp.565-602;Peter Strawson,Freedom and Resentment,London:Methuen,1974.。而这种道德最为主要的内容是对相互服从互惠性承诺的背信弃义。当一个人违背了这条承诺时,也就意味着他或她在道德上是成问题的,应当受到谴责,并承担相应的损失。因此,在具体的侵权认定过程中,倘若被告的行为动机以及其心理状态在道德上有罪过,他或她的行为就构成过错侵权行为,就应当对其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倘若被告在行为时的动机以及其心理状态在道德上无罪过,他或她的行为就不能被认定为过错侵权行为,也就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张民安:《过失侵权责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3页。。
二、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法律责任的困境
法律责任在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以互惠为出发点,以过错原则为基本归责原则,它所遵循的是一套强调泄愤的逻辑。这种强调泄愤的法律责任制度的确对于捍卫人的主体性、自由与尊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在具体的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
过错责任强调过错与法律责任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这种以因果律把握事物的方式强调法律上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对这种关系在事先就能够进行把握,即行为人对行为结果应当有一定合理的预见。并且,这种因果律必须通过一定的外在客体加予“对象化”。一如邱聪智先生所言:“在法律规范原理上使遭受损害之权益,与促使损害发出原因者结合,将损害因而转嫁由原因者承担之法律价值判断因素,即为‘归责’意义之核心”*转引自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但是,人们要想通过因果关系的方式来把握法律责任,就必须具有充足的理性。这种理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行为人在从事一定行为之前,必须具有充分认识该行为可能造成的一系列后果的理性能力;其二,在进行具体的责任设置和归责时,能够在具体的结果与诸多的相关原因行为之间确立一种最近因果关系;其三,在损害结果与赔偿数额、犯罪与惩罚之间确立精准的数量对等关系。这在实践中遇到诸多麻烦:第一,证据上的麻烦。法律上的事实是由一系列的证据重构起来的。然而,证人的不可信性已被无数的经验所证实。这种不可信性随着事件的发生时间与作证回忆的时间间隔而不断增加。第二,被告过错与原告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建立的问题。第三,过错程序认定的困难*胡雪梅:《“过错”的死亡》,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64页。。在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由于受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不够,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表现出一种唯理主义倾向:随着后工业社会来临,各种高科技在促进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风险,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个人预期其行为将要带来结果的难度以及在过错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认定的难度愈来愈大。
另一方面,这种过错责任是以强调泄愤为内在逻辑的,因此,过错责任极为强调对行为人的否定评价、教育和惩戒功能。从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法律的目的来看,“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旨在教育、惩戒有过错行为的人,从而指导人们正确行为,并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对过错行为的制裁,意味着法律要求行为人应该尽到合理的注意,应该像一个谨慎的、勤勉的、细心的人那样,努力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损害,努力避免可能发生的损害”*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1页。。但是,这种过分强调侵权行为的道德性与人们的实际心理状态具有不一致性。英国法学家阿提和彼德·卡尼就针对英国具体法律实践指出,由于我们过于强调对侵权行为的道德校正,而忽视了侵权行为人的具体生活处境,例如,行为人或许是个笨手笨脚的人、或许是个愚蠢的人,甚至当事人也确实赞成“无过错即无责任”原则。但是,法院对这些是不会过多关注的。因为在法院看来,侵权责任最为重要的功能在于防止当事人再犯同样的错误*Peter Cane and Atiyah’Accidents,Compensation and the Law,London:Butterworths,1999,pp.145-161.。从这个意义上讲,过错责任是将侵权行为人、被害人以及社会三方主体都孤立起来看待。既然侵权行为人有过错,他或她就得为这种过错承担责任,也只有通过承担这种责任,被害人、社会的泄愤才能实现,而对于侵权行为人因侵权承担赔偿责任后的生存状况则漠不关心。特别是对那些贫困者仅仅因为极小的过失而极有可能被剥夺全部财产,甚至是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物质条件。尽管我们要保护被害者的利益,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考虑这些侵权行为人一无所有之后的生活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See Peter Cane and Atiyah’Accidents,Compensation and the Law, London:Butterworths,1999.在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侵权行为人的赔偿标准是按实际损失来进行赔偿的,因此,侵权行为人因过失而承担的赔偿费用往往非常高。例如,一个学生在一次事故中受到伤害而致残,他所获的赔偿主要由医药费、看护费、精神损害赔偿、未来收入等部分组成。面对这样高昂的赔偿费,侵权行为人极有可能破产。而这种破产又极有可能滋生新的社会问题。。
三、主体性重建时期法律责任的构造逻辑
人们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愈来愈意识到主体性观念和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的缺陷与不足。“主体性的黄昏”、“主体性的终结”、“主体性的退隐”等愈来愈成为较为刺耳的话语。“后工业社会”、“风险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社会”等也逐步成为流行词汇。人们对以主体性为支撑的现代社会愈来愈持批判与反思的态度。尽管人们有关“主体性破产”的论述流露出一种悲观主义的色彩,在具体观点上也存在夸大其词之嫌疑,但是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理论缺陷与现实困境,在事实上值得人们认真加予对待。捍卫主体性、重建主体性与批判主体性、否定主体性相伴而生,并成为二战以后的一个主旋律。在捍卫主体性与重建主体性的过程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人们试图改变过去那种“独白”的主体性、形式理性意义上的主体性,而强调从交往与沟通的角度来看待主体性。人们愈来愈倾向于用主体间性来丰富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主体性重建对主体性的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主体性重建以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为主导价值,并在此基础上突出了社会公正、合作、宽容等价值;主体性重建强调从独语的主体性向对话的主体性发展;主体性重建突出了程序以及程序性权利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主体性重建强调“优胜劣存”的基本理念等。对此问题笔者曾有专门论述,参见郑智航:《论法律内在逻辑的基调演变》,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93-95页。。这种主体性重建的努力带来了法律责任内在逻辑的演变,即法律责任愈来愈体现出对被告人的关注,愈来愈改变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所留下来的“他者态度”。
(一)法律责任对主观过错的宽容
在主体性重建中,法律责任对被告人的主观过错愈来愈表现出宽容的态度。“当我们转换一个视角即从社会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观察该归责原则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时,就会发现人犯错误原来是一种常态、不可避免。”因此,“对于具体一个人来说,过错或许有些偶然,但相对整个社会来说,过错却是必然,因为人犯错误是一种客观存在”*彭诚信:《民事责任现代归责原则的确立》,《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2期。。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事法律责任在主体性重建中呈现出对过错的一种宽容态度。法律责任之所以要对主观过错表现出宽容态度,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受主体间性哲学对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主体性进行批判的影响,人们愈来愈对理性,特别是认知理性本身抱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过去,受启蒙哲学的影响,法律将人的理性强调到极致。就民法而言,它强调人能够进行自由抉择是因为人具有独立思考的理性能力。这构成了民法意思自治的核心。既然人具有独立思考的理性能力,也就意味着人知道什么对自己而言是好的、有利的以及应当去追寻的;与此同时,他或她也知道什么对自己而言是不好的、不利的以及不应当去追寻的。倘若对于明知对自己而言是不好的、不利的以及不应当去追寻的还要进行追寻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或她有过错。在主体性重建中,人们尽管也强调理性,但是理性中增强了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这些因素深深地影响着人们对法律责任的认识。这正如考夫曼所说:“在高度复杂的社会中,没有人可以负责任地行事,而又不会遭遇错估行动情况的危险”*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470页。。因此,法律责任,特别是民事法律责任要允许当事人犯错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合同法广泛采用严格责任制度就是明证。在侵权责任中,也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侵权赔偿的根据是补偿,而不是过失’”*彭诚信:《民事责任现代归责原则的确立》,《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2期。。另一方面,随着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的发展,法律责任的社会化愈来愈受到重视,而这种社会化的前提是人们对于侵权行为以及侵权责任本身的认识,倘若法律责任中还过于强调泄愤的话,法律责任的社会化是难以为人所接受的,因为在过于强调泄愤的逻辑支配下,侵权责任所要实现的首要目标是侵权人能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具有可责斥性,法律责任的社会化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目标。
(二)法律责任泄愤性的隐退
在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法律责任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归责原则。而这种过错往往具有道德的属性,往往强调一种心理状态。但是在主体性重建过程中,尽管过错责任还是在归责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它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过错的实质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过错主要取决于一个理性的人是否满足于一个特定行为标准。例如,假如判断一个生意人出售一种掺假的食品是否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就必须得判断其是否符合特定的行为标准;或者证明他满足了所有的相关行动标准,该损害就不会发生*Peter Cane and John Gardner,Relating to Responsibility,Oxford:Hart Publishing,2001,p.100.。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英国这样来认定“暴力侵犯的故意”,它“并非指要求被告有伤害原告的故意,仅要求被告有使用暴力的故意”*Harpwood,Principles of Tort Law,London:Cavendish Publishing,2000,p.294.。对于什么是侵犯他人土地,英国在实践中是这样认定的:只要是没有正当理由,无论是进入原告土地,还是停留在原告土地上,抑或是在原告土地上摆放物品或建筑项目都构成侵权,而无须证明实际损害,并且误解并不构成免责的理由*Margaret Braxier and John Murphy,Street on Torts,London:Butterworth,1999,p.220.。对此,帕罗舍说:“过错意味着对应当由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而非由个人道德因素来决定的行为标准的偏离。在20世纪,被告可能对其善意的、完全符合道德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个人或许在道德上根本不具有可责难性,但是,法律仍然要他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在于他没有达到社会所要求的行为标准”*William L.Prosser,Law of Torts,St,Paul,MN:West publishing,1998,p.18.。
基于此,笔者认为主体性重建时的法律责任中泄愤的成分逐步隐退,其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这种法律责任具有典型的结果主义色彩。被告的行为之所以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主要是因为该行为给对方造成了损失,而被告的主观心理状态到底是什么,法律不会过度关注。而泄愤性是极为关注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这种源于“反应性态度”的泄愤性强调人在主观上具有过错。但是,这种责任与严格的结果责任的不同之处在于赔偿的标准:严格的结果责任往往坚持一种实际损害的标准,而这种责任强调有最高限度的赔偿责任。这就事实上改变了过错责任中过错与责任对等的原则,而将被告人的一些实际情况纳入了责任确定的范围内。第二,法律责任的教育、惩戒功能弱化,而恢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功能得到加强。从侵权法的原始功能来看,它主要是通过金钱的方式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在主体性支撑的现代社会,由于法律的实证化倾向,即法律是一种主权者的命令,对法律的违背也就意味着对统治秩序的破坏。因此,法律除了要确保个人权利的实现,还要对统治秩序进行维护。教育、惩戒功能自然是法律责任的应有之义。然而,在主体性重建过程中,法律更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系,法律所具有的统治功能被淡化。相应地,以法律责任的确立与承担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更为重要的功能,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评价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教育和惩戒功能则退居二线。第三,强调泄愤逻辑支配的法律责任更多的是一种“历史责任”,而这种逻辑并不适用于“未来责任”*彼德·卡尼提出了“历史责任(historic responsibility)”与“未来责任(prospective responsibilities)”的区分。他认为历史责任强调对过去所发生的行为和事件进行向后看(backward-looking),而未来责任则更为强调通过人的行为产生一种好结果或防止坏结果发生。但是,人们往往过于关注历史责任,而忽视了未来责任。参见 Peter Cane,Responsibility in Law and Morality,Oxford:Hart Publishing,2002,pp.30-31.。历史责任往往强调对侵权人的一种教育与惩戒,而未来责任则更为强调通过对行为人规定责任的方式去促进好结果的产生或防止一种坏结果的发生。
(三)法律责任中合作的社会化
由于法律责任对过错的宽容以及法律责任泄愤色彩的淡化,法律责任愈来愈强调补偿的功能,而教育和惩戒的功能则是次要的。这样的一种责任观念的确在道德上有利于宽恕当事人,但是,侵权人毕竟还是要承担一定的经济负担。侵权责任一旦发生就会给当事人产生巨大的经济压力、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并且单凭个人的能力难以应对这种风险。例如,被告人可能在一场车祸中倾家荡产。这也在事实上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法律愈来愈强调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来分化侵权人破产的风险,即“人们蒙受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的风险被分散给了社会的一部分成员甚至是广大成员。以工伤责任为例,雇工就工人在工业事故中蒙受的人身伤害的风险向保险机构投保,保险金被打入生产成本,从而使风险分摊给所有的使用或消费产品的人”*王军:《侵权法上严格责任的原理和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尽管社会保险制度并不是起源于主体性重建过程中,但是它的确在主体性重建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就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质而言,它主要强调责任风险的承担并不是孤立的个人的事,而是强调每个人承担社会风险和责任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社会保险制度通过这种责任的社会转嫁来防止因单个人在责任承担过程中破产而滋生不利于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因素。所以,社会保障制度以强调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合作为前提来进行制度设计。因此,它要求社会公众共同来承担因这种风险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因为,它极为强调风险发生的概率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同等的。这也就意味着,侵权行为的发生是社会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可能随时成为一个侵权者。今天你可能是被侵权者,但是明天你可能就成为侵权者。尽管法律责任中合作社会化的实现以支付保险金为条件,但是保险金的支付并不以当事人是否有过错为前提,并且支付的数额也不与所获的保险赔偿金的数额具有数量上的等值关系。因此,社会保险制度充分体现了“集小力、办大事”的社会合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