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猫的父亲
2018-03-18龚曙光
☉龚曙光
父亲属猫,这是祖父说的。老家人相信,猫有九条命。祖父认定,父亲也有九条命。
一生下来,父亲就是棵病秧子。父亲窝在祖母怀里,瘦小得就是只刚出生的猫崽,两片薄薄的嘴唇,喵呀喵呀地哭泣,声音细得像一根游丝,听上去随时都会绷断。
父亲之前,祖母生过一个男孩,生下来不吃不喝,月子里便夭折了。祖父见父亲又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急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远远近近地找郎中。郎中找来三四个,都是望上一眼便摇摇头,没一个提笔开药方。最后一个老郎中,总算开了口:“取个贱点的名字试试吧!”好孬算是开了个方子。
给刚出生的孩子取个贱名,以求日后好养好带,这在老家是旧俗。家中孩子看得愈金贵,名字便取得愈贱性。好些大户人家少爷小姐一大帮,不是叫猫便是叫狗,走进去像是进了一家牲畜馆。老家人都信奉,阎王爷拿本簿册到人间,走村串巷地索拿人命,就是照着名字贵贱取舍的,猫儿狗儿之类的贱名字,入不了阎王爷的法眼。
祖父照了老郎中的吩附,把父亲的小名往贱里想,想来想去想到了“捡狗”二字,意即父亲不仅命贱如狗,而且是一条野地里捡回来的丧家之犬。命贱至此,也算到了极限。说来也怪,祖父“捡狗”“捡狗”叫上一阵,父亲竟断了游丝般的哭声,眯缝着两只小眼破涕为笑,钻进祖母怀里找奶吃。
父亲身坯子太单薄,即使取了贱名字,还是难养难带。一年二十四节气,至少有十八九个节气,父亲在病里滚。天热了上火,天冷了伤风,不冷不热吹一点风照样感冒。父亲一病便发烧,一发烧便痉挛,一痉挛便两眼翻白、手脚僵硬,一口气憋住便只有进气没了出气。
有一回,父亲高烧痉挛,身体抽搐几下便没了呼吸和脉搏。祖父从祖母手中接过僵硬的父亲,装进箢箕提上了山。依照老家的习俗,没有长大的孩子死了,必须当晚由家人送上山。祖父正用锄头挖着坑,父亲突然“哇”的一声大哭,几乎将黑漆漆的夜空撕破了一道口。祖父把父亲抱下山,对着躺在床上哭哑了声音的祖母说:“捡狗不是一条狗呢,他是一只猫!一生九条命,死了都会活过来。”
祖父一语成谶。没人说得清,父亲这一生究竟死过多少回,反正他已病病歪歪活到了85岁。好些熟悉父亲的医生,看着父亲住进病房,常常一两天不上药,弟弟妹妺急了催问,医生总是笑嘻嘻地说:“他老人家的病,不是靠药治的,是靠命。”
一个农民的儿子,下田使不了牛,上坎担不得禾,日后靠什么活命,靠什么养家?祖父看着病病恹恹的父亲,一直在心里犯愁。祖父认定父亲吃不了凭力气种田这碗饭,便想让父亲学门手艺,靠技艺去吃百家饭。但木匠瓦匠都是使力气的活,父亲看上去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没一个师傅想收他。祖父提上烟酒找郎中,说看病行医不拼力气,捡狗干这行能行。郎中一看以为父亲是来看病的,心里暗忖:谁知道这孩子熬不熬得到学徒出师。思来想去,只剩了上学读书一条路,祖父一咬牙,将父亲送进私塾发了蒙。
父亲属于那种长心不长肉的人,虽然三天两头生病,背着一副药罐子上学,书倒是读得一路顺畅,进私塾,上完小,后来考取九澧联中,一点没让祖父的钱白花。父亲在学校不劳动也不运动,同学在操场上动腿子,父亲在教室里动脑子;别人信奉生命在于运动,父亲信奉生命在于不动。偶有同学讪笑,父亲反唇相讥:兔子撒腿天天跑,最多能活十几年,乌龟缩在売里一动不动,却能活上千百岁。
父亲平素不爱站,也不爱坐,爱两臂抱胸,蜷缩着身子,蹲在地上,即使是吃饭喝酒,也是杯碗一端,自己蹲在一边。如今八十多岁了,父亲依然有蹲在地上歇息的习惯。父亲将瘦弱的身体缩紧成一团,尽可能躲避外力的伤害。同学们在操场上奔跑跳跃,父亲抱胸蹲在操场边上,一动不动,就像一只孤零零的灰鹳,将头颈埋在翅膀里,似睡似醒地缩在自己的世界。
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弱者对弱肉强食的本能防御,而且是一个社会弱者对弱肉强食的本能防御。一个命定要当农民,靠使气力流汗水挣饭吃的人,却命定当不了农民,这种难以言说的悲哀,一直山一样压在父亲心里。靠不了体力,父亲只能靠心力吃饭。父亲缩着身子蹲在地上,那不仅仅是在体能上示弱,而且是对心力的蓄养。父亲将身体的能耗降到最低,让一切意志和力量向内去供养深藏不露的心智和心性,用绵密的算计和坚韧的意志蓄聚出自己的力量。

祖父把父亲抱下山,对着躺在床上哭哑了声音的祖母说:“捡狗不是一条狗呢,他是一只猫!一生九条命,死了都会活过来。”
父亲初中一毕业便参加了土改工作队,跟着一帮官兵到乡下帮农民分田分地,挎了一支枪清匪反霸。我印象中,父亲下乡的地方,在太青界岭那片山区,也就是母亲老家那一带,外祖父当年率兵攻打的乡公所,也都在那片山里。父亲所在的工作队,是否与外祖父的队伍交过火,没人可以确考。父亲说,他们的工作队打过仗,只是他参加的好像是打土匪,一颗子弹擦左耳呼啸而过,偏一点便把脑袋钻一个洞。祖父说父亲命大,这是又一次证明。
从工作队归来,父亲直接留在了澧县二中,就是父亲之前就读的九澧联中。一个初中毕业生,被留在一所县里最好的完全中学做学生工作,即使在人才奇缺的1950年前后,也算是一种破例的安排。毕竟,父亲不是南征北战的革命战士,也没有在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据说,组织上曾征求父亲的工作意向,在留在乡区政府和回到学校之间选择。父亲之所以选择回学校,还是出于对身体的考虑,虽然那时父亲青春年少,还是应付不了乡区政府对体能的要求。留在乡区政府的政治前途是摆在眼前的,换了其他人,即使身体差一点,也会先去搏一搏,不行日后再换,但父亲信奉的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万事先算清楚,不博意外之喜。

父亲抱胸蹲在操场边上,一动不动,就像一只孤零零的灰鹳,将头颈埋在翅膀里,似睡似醒地缩在自己的世界。
父亲不是那种追求快意人生的人,在父亲的理念中,活着便是过日子。过日子就靠两样东西,一是健康,一是钱财,而恰恰这两样东西父亲都匮乏,这便注定了他一辈子要比别人过得艰难。因为缺乏健康,父亲信仰好死不如赖活着,留着性命多过几天日子;因为缺乏钱财,父亲信仰吃不穷、穿不穷,没有盘算一世穷。这样的人生信念,不高贵,不伟大,然而世上所有卑微的生命,不都是如此活着的吗?是他们用自己的平庸衬托了另一类人的伟大和高贵,没有理由逼迫他们去为这种伟大和高贵牺牲!每一条生命都只能活过一次,如果他们只能选择活着,只想选择活着,任何人也没有权利来指责和嘲笑。
20世纪50年代初期,民众对学校和教师,沿袭了民国时代那种由衷的尊重,那时的先生对学生,亦沿袭了民国时代那份真诚的呵护和绝不苟且的责任心。父亲作为学生干事,虽然年纪比好多学生还小,但关照学生却无微不至。清晨叫早,晚上查铺,几乎和学生朝夕相处。学生生了病,父亲会上医院陪护。有一位赵姓的学生需要输血,父亲挽起袖子便让护士抽,护士看着父亲瘦骨伶仃的样子,针头怎么都不忍扎进脉管,父亲板脸催促,硬是让护士抽了四百毫升。后来这个学生当了兵,每次回家探亲都要来我家探望,见面就说一句话:“我这条命是龚老师救下来的。”
父亲和母亲的恋情,就发生在那个时间。母亲从桃江二中调来,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些人关注母亲的年轻美丽和能歌善舞,一些人关注母亲的小姐出身和母亲的父亲作为国民党将军被处决。对于好些未曾媒娶的男老师,母亲是一朵名副其实的带刺攻瑰,见了想伸手,伸手怕被刺。
直到父亲和母亲的恋情正式公开,这种欲摘不敢欲罢不甘的纠缠才算了结,一部分人转为懊恼不已,责怪自己怎么就没有这么一份胆气;一部分人转为幸灾乐祸,庆幸自己又少了一个政治进取的竞争对手。这桩无论是从长相,还是从政治上,怎么看都不般配的婚姻,究竟是如何缔结的,我至今都没有弄清。我曾亦庄亦谐地问过母亲,当年怎么会爱上父亲,母亲的回答出奇的简单:“他追求进步。”我相信,母亲当年选择父亲的理由,真的如此简单。从旧式大家庭里冲出家门的母亲,进步是她唯一的追求。“文革”前的那几年,父亲身体依然很糟,胃上的毛病让父亲吃不了东西,勉强塞一点下去,立马吐得昏天黑地,直到连胆汁都吐出来。好几次还大口大口地吐血,送到医院说是呕吐得太厉害,把咽喉吐裂了口子,血是从咽喉流出来的。父亲还有头晕的毛病,两眼一黑,身子一歪,便倒在了讲台上,好几次把学生吓个半死。镇上的医生査不出原因,便诊断是进食太少造成的低血糖。躺在医院里,吊两天葡萄糖,然后又站回讲台上。老家有句话,“人又生得丑,病又来得陡”,仿佛说的就是父亲。一口饭菜吃进嘴里,气味稍有不对,哇的一口吐出来,不管席上多少人,捂都捂不住。医生说,父亲患的是胃神经官能症,到今天我都没闹明白这是个什么病。低血糖更是说倒便倒,父亲在课堂上抬出去,谁都不觉得新鲜。镇上隔年半载,便传说父亲死了,甚至有两次朋友把花圈扛到了家里。
对于我们兄妹四人,父亲似乎从未生过成龙成凤的妄念,他寄望于我们的,就是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人。我和弟弟妹妹们要打藕煤、种菜园、担水,还要洗衣裳、打毛衣、缝针线。兄妹四人都是六七岁便开始学做饭,先从学习炒饭开始,直到每人都能单独做出一桌可口的饭菜。父亲自己厨艺不错,无奈他一呛油烟便咳嗽不止;母亲忙于工作,没空待在家里,因而家里如果不在学校伙房打饭菜,便是我们兄妹轮着做。父亲坐在躺椅上,时不时指点一下,即使我们把饭烧焦、汤炖咸了,父亲都会点头说好吃。生活中一向严厉的父亲,在学做家务上却从来没有责骂过我们。长大后,我慢慢体会到,父亲不仅是在培训我们手艺,而且在培养我们的兴趣。如今,周末闲了,我会围上围裙自己动手烧菜,不是为了显摆厨艺,而是为了调剂生活,享一份居家过日子的情趣。
除了大妹妹,我们兄妹三个身体都不好,我瘦得一把捏得住,活像父亲脱的一个壳。弟弟寄养在保姆家,又患了肾盂肾炎,一年到头身上浮肿。小妹则动不动便拉肚子,土方洋方都止不了泻。父亲一方面筹钱给我们治病,一方面逼迫我们锻炼身体和意志。父亲对我说:“真有病的人,再好的药也治不了。能让你战胜病痛的,只有你的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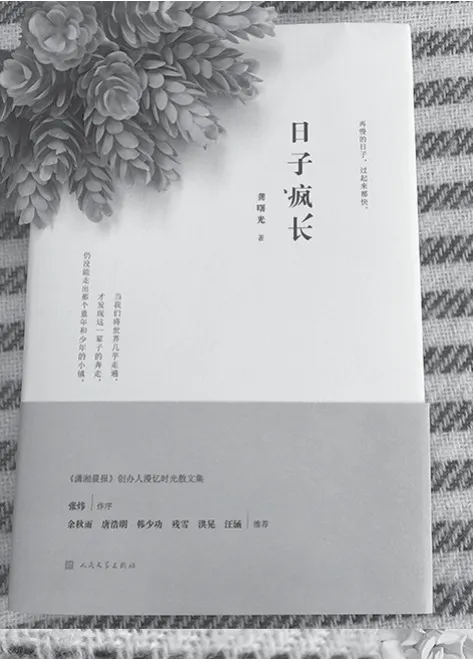
父亲教了一辈子书,说得上桃李满园,但说不上有什么独特思想,倒是在四个孩子的养育上,父亲践行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我们兄妹,都被培养成了有意志应对艰难时局、有能力应付琐碎生活、自食其力的普通人。
上个月,大妹妹打电话,说父亲病重,得转院治疗。父亲转到长沙湘雅医院,咳喘得整夜睡不着,医生做完检查,说找不到病源,担心肺大泡破裂。我怕病重得花钱,带了些现金交给父亲,让他别惜药费,来了就治好。父亲说他有钱,硬是没收下。
平常我们回家,悄悄给父母留点钱在枕头下,等下次见面父亲又原封不动地退回来,而且振振有词地说:“你是你的家,我是我的家,我这个家有钱。再说我是一家之主,用你的钱我没脸面!”为了证明他的家里有钱,父亲躺在病床上一五一十地给我报了个账,存款多少,每月退休金多少,利息还有多少;每月保姆费多少,菜米油盐多少,电费水费气费多少,应当自付的药费是多少,人情往来还有多少……一个八十五岁的人,不仅凭记忆把数字报得清清楚楚,还把收入支出算得明明白白!
父亲说,他怎么都会走在母亲之前,留下的钱给母亲度晚年。我说,这事您不用担心,母亲是我们的亲娘,我们会为她养老送终。父亲听了两眼一瞪:“她是你娘,但她是我老婆。老婆娶进屋,一辈子都归我管。管吃管穿归我,管生管死也归我!”
我不能再说什么。转过脸去,望着窗外的冬日,咬紧牙齿,努力不让泪水流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