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权利,死的自由
2018-03-18黄蘅玉
☉黄蘅玉
死亡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人一出生就向着死亡迈进,这是客观规律。死亡像一个终点站的醒目标志,愿意或不愿意,或快或慢,人们只能朝着这个目标行进。
人生的最后一道考题就是如何面对死神的召唤。
林语堂曾经说过,“我们都相信人总是要死的,相信生命像一支烛光,总有一日要熄灭的。我认为这种感觉是好的,它使我们清醒,使我们悲哀,它也使某些人感到一种诗意。此外还有一层最为重要:它使我们能够坚定意志,去想法儿过一种合理的、真实的生活。”
生死抉择
一个人的生死抉择应该由谁决定?有时看到一些长辈、亲友或医院里的病人,身上插满管子,瘦骨嶙峋,面无血色,意识不清,日复一日地躺在病床上消耗着自己的或公家的钱财,承受着永不康复的磨难,直至生命耗竭。
这是当事人所希望的吗?尤其是当一个人面临生死攸关的手术和痛苦不堪的垂危抢救时,当事人有无抉择的权利?
电影《姐姐的守护者》讲的就是一个有关生死权利的悲伤故事。
安娜是凯特的妹妹。让安娜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患有白血病的姐姐凯特提供配对合适的维系生命的器官:骨髓、肾脏或其他。
待安娜长到11岁时,她将一张状纸交到了律师的手里,她要起诉她母亲违背她的个人意愿而将她身体的某个部分捐给她姐姐。她表明她有权利拥有自己的身体。
身为律师的母亲,为了拯救和照顾病重的凯特,她早已辞去工作,远离了律师行业。但是,当她要为自己心爱的大女儿凯特争取存活的权利,争取急需的肾脏时,她决定重操旧业,自己为自己辩护。她深信她一定会赢,凯特一定能活下去。
与疾病抗争多年的15岁凯特,心身疲惫。当她的同病相怜、心心相印的男友去世之后,她已经没有了生存的愿望,没有能力再与疾病相争。她想死,她不愿意接受妹妹的捐赠。但是,她妈妈不同意,她妈妈要竭尽一切方法来挽救凯特的生命。
凯特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吗?
美国哈佛医学院的外科医生、作家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提到了他与他父亲的一次艰难而极有意义的谈话,此次谈话涉及了他父亲的生死抉择。他父亲因癌症将进行一次十分危险的手术,病人的生命很可能就消失在手术台上。
葛文德医生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最艰难的谈话,是他问过的最最棘手的问题。当他问父亲是否要做手术时,心里极度不安,非常害怕。如果不做手术,他父亲将会四肢瘫痪,靠呼吸机和饲管存活,24小时都需要他人护理。
当他父亲明白了自己所面临的选择后,毫不犹豫地回答:“绝不,”他说,“如果瘫痪地活着,那还不如让我死。”父亲愿意手术。结果手术很成功,他父亲又活了过来。
这位病人有幸是阿图·葛文德医生的父亲,他有机会在自己的生死难题上做出符合自己意愿的抉择。然而,当今社会,究竟有多少病人有自己的生死决定权?有时,仅仅因为亲属或医疗专家善意的期望而延误了与病人进行“生死抉择”的探讨,贻误了病人的自主决定权,导致病人承受其不愿承受的死前痛苦。

这是一个告别派对。美国加州正式设立《结束生命选择权法》后,身患绝症的Betsy成为新法案下第一个通过安乐死向世界说“再见”的人。
病人丧失了“死的自由”。
葛文德医生还提到另一个案例,曾经有个病人在脊髓肿瘤切除的手术中发生意外出血,医生给家属三分钟的时间作出是否继续进行另一个手术的决定。若不做另一手术,那么病人随时可能丧命,如果做另一手术,病人可以存活,但是他可能会瘫痪几个月或更久,有可能永远瘫痪。
这也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
这位病人的女儿是位医生,她非常清楚当今时代病人可能会遇到的难题:什么时候应该努力医治,什么时候应该放弃治疗?所以在她父亲做脊髓肿瘤切除术前,她曾问过她父亲:“为了博取一个活命的机会,你愿意承受多少?”她父亲回答道:“如果我能够吃巧克力冰淇淋,看足球电视转播,那我就愿意活着。如果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愿意吃很多苦。”
听到父亲这样回答,他女儿极其震惊。因为她所了解的父亲是位专注于研究,静静地做学问的教授。在女儿的记忆里父亲从来不看足球比赛,也很少吃冰淇淋。但这确实是她父亲非常理性的回答。
在三分钟的时间内,那女儿问医生:如果她父亲手术后活下来是否还能吃巧克力冰淇淋、看电视足球比赛?医生说:“可以。”于是,她同意让他们再给她父亲做一次手术。
那女儿庆幸自己曾与父亲进行过艰难的生死探讨,否则单凭自己的想象,那很可能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她深切地体会到,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视生死问题为谈话禁忌。她真诚地建议:“我们要坦诚地询问,而且不要拖得太晚。”当她看到父亲术后恢复良好,躺在床上,吃着巧克力冰淇淋,看着电视里的足球比赛,她为自己在那三分钟内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高兴。
安乐死
生的快乐与死的安详,是人类对于生命的理想追求。
曾有过“幸福晚年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的讨论,尚未步入老年的人们和耄耋老人的回答迥然不同。青年人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幸福要素,然而长者们只能叹息道:暮年的幸福要素是“自己还能上厕所”。
确实,医学再怎么发愤图强,依然无法摆脱一个很确定的结局,那就是永远无法战胜死神,生命的最后一课必定是衰老与死亡。救治失败也不是医学的无能,而是对生命进程的尊重。
2015年2月6日,星期五。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全体一致通过并做出了重要裁决:那些已被证实患有不治之症的人,如果不想继续忍受剧烈病痛的折磨,他们有权要求医生协助他们死亡。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被认为是历史上最重要的裁决之一,因为它改变了既往加拿大人被法律和政府所认可的死亡方式。
2016年6月,加拿大颁布了医生可以协助病人死亡的法律。
联邦政府正式公布极具争议的《医生协助安乐死法案》,该法案对申请安乐死的病人设有具体的限制:病人必须是精神状况健全的18岁或以上的加国公民;患有严重的不治之症、残障及身体状况正处于不能逆转地变坏;病人正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病痛和正走向死亡的阶段。法律规定,除医生以外,法案容许执业护士协助病人安乐死。这些寻求安乐死的病人,需要在申请时提供精神状态良好的评估。新法案明确规定,凡有精神疾病和精神失常状况的人,不得申请安乐死。
病人要求医生协助死亡时,必须在神志清醒状态下做出书面请求。如果无法亲自撰写时,可由一位指定人士代笔,并须附上两个独立见证人签署的见证文件。为了确保申请人的这个决定是神志清醒的理智的个人要求,法庭设定了“15日的冷静思考期”,也就是说,在提出申请后,寻求安乐死的病人将通过15天的冷静期,让他们有时间重新考虑并确认有关自己生死的重大决定。
在加拿大,安乐死被分为两种。第一种为被动安乐死,即医生放弃对病人进行延续其生命的治疗,由他们自然死亡。这些放弃治疗的措施包括移除维持生命体征的仪器,移除喂食管,取消延长生命的操作,取消给予延长生命的药物等;第二种为主动安乐死,则是医护工作者或他人采取故意的行为协助病人死亡。
既往的加拿大法律规定:“任何人辅导一个人自杀,协助或教唆人自杀,无论自杀是否真实发生,都是犯罪行为,将被判刑,刑期不超过14年。”当时的联邦总检察长对此的解释为:“法律绝对禁止协助自杀。所有的生命都是珍贵的、值得保护的,也都应该受到保护,任何人都不能潜移默化地鼓励弱势群体终止他们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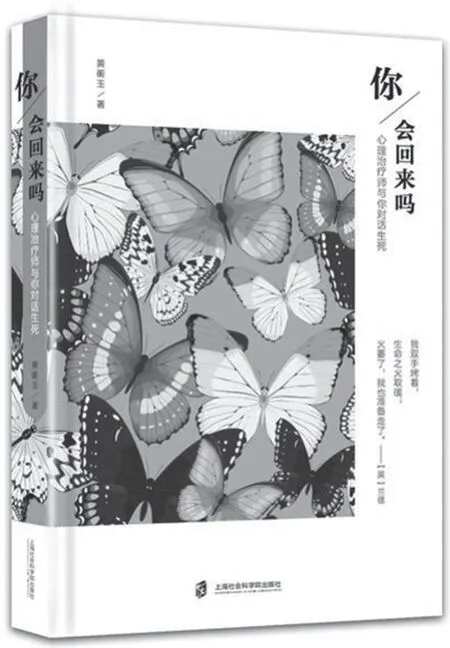
一些反对安乐死的人士表示,当病人在清醒时做出安乐死决定,家人无从反对,医生也没有权利拒绝。不过,他们认为,政府更应该在善终服务上增拨资源,即使病人无法痊愈,仍能获得持续优质的医疗护理,让他们有尊严地活下去。
医疗界对安乐死也有异议。一些医生认为,他们在医学领域所学习的都是治病救人,他们曾认真学习过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医生职业道德的警诫圣典,正式宣誓过:“……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也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
那么,为什么现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致同意将“安乐死”合法化呢?因为现在在司法管辖妥善的地区,弱势群体面临的“被迫死亡风险已大幅度减小”。如果法律继续禁止协助死亡,不仅会延长终极患者的痛苦,还会导致一些人更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有人批评加拿大安乐死的新法案过于狭窄和严厉,包括把病人年龄限制在18岁以上,一些深受病痛折磨的孩子将继续承受痛苦。
不管怎样,人们都期盼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而有尊严。
在加拿大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聚集在一家气氛温馨的咖啡馆里喝着冒热气的咖啡,吃着美味的蛋糕,讨论着关于生与死的话题。“死亡咖啡馆”帮助人们为死亡做准备,当有人死亡或死神将至时,他们可以从容地为自己或垂死的人,做一些事先规划和行动。“死亡咖啡馆”将打开人类关于死亡和垂死的文化融合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