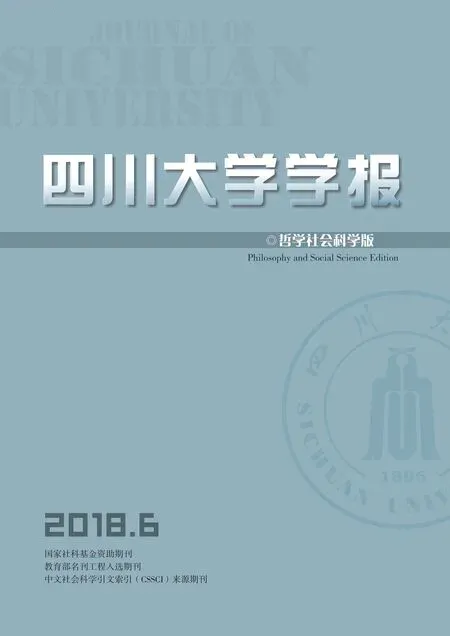当代美德伦理
——古代儒家的贡献
2018-03-17
随着美德伦理学最近几十年在西方世界的重大复兴,大家开始看到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道义论和功用论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同时也看到被这两种伦理学看作是属于古人伦理学的美德伦理学在当代人类生活中实际上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许多研究非西方哲学传统的学者也纷纷试图在他们所熟悉的哲学传统中发现美德伦理的踪迹。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儒学研究。与以前港台新儒家往往用康德主义伦理学解释儒家伦理不同,现在有更多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本质上是一种美德伦理。无论是在中文世界还是在英文世界,这方面的研究文章甚至著作都不胜枚举。笔者在最近十几年中的一个主要研究也是儒家和美德伦理的问题。但与大多数学者试图论证儒家具有西方美德伦理的主要特征因此是一种美德伦理不同,笔者一直关心的问题是,不管古代儒家思想是不是一种美德伦理,它对当代美德伦理的发展能够作出什么样的独特贡献,这包括如何帮助美德伦理回应来自各方面、特别是康德主义伦理学的批评,如何帮助美德伦理处理其自身存在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如何帮助美德伦理对当代的伦理学及其相邻学科做出贡献。在这方面,笔者写了大量文章。本文的目的是将笔者在这些文章中所讨论的古代儒家思想对当代美德伦理在上述三个方面所能作出的贡献做一总结。*本文根据笔者为其将出的《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一书所撰的序言之一部分改写而成,因此在本文中所讨论的古代儒家思想对当代美德伦理的贡献限于收入该书的若干文章所阐发的观点。实际上,笔者在其他一些地方,特别是在其已出的 Why Be Moral: Learning from the Neo-Confucian Cheng Brother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 和将出的Knowing-To: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Wang Yangming's Moral Philosophy两书中,还讨论了古代儒家思想对当代美德伦理所能作出的其他一些贡献。
一、儒家如何帮助美德伦理回应外来的批评
在美德伦理刚开始复兴时,我们看到的主要是美德伦理对当时盛行的道义论和功用论伦理学的批评,而后者,正如当代美德伦理学的佼佼者霍斯特豪斯(Rosalind Hurthouse)所说的,将刚刚开始复兴的美德伦理轻蔑地看成是邻里出现的一个外来的淘气小孩,懒得理睬。但在美德伦理学得到长足发展并开始挑战他们在伦理学中的垄断地位时,他们就开始找美德伦理的毛病,并加以批评。在此过程中,当代的美德伦理学家也对这样的批评作出了一些回应,其中有些回应很成功。例如关于美德伦理无法为人提供行动指南的指责,霍斯特豪斯就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但在还有一些问题上,当代美德伦理学家的回应就不仅并不成功,而且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局限于西方的美德伦理资源,可能根本无法作出成功的回应。因此笔者试图利用古代儒家的资源,对其中的某些批评,为当代美德伦理作出辩护。
第一是关于具有美德的人是否只关心他人的外在福祉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将他心目中的有美德的人看成是一个真正的自爱者,以与他所谓的庸俗的自爱者相区分。庸俗的自爱者只关心自己的外在福祉,如健康、财富、名声等等,而真正的自爱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美德,即是比其外在福祉更为重要的内在福祉。当然,亚里士多德称这样的人是真正的自爱者,不只是因为他们所爱的是自己身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也是因为这些东西之所以有价值,至少部分地是由于这些东西、特别是那些涉及他人(other-regarding)的美德,要求他们关心他人的福祉。例如,正义这种美德就要求其拥有者对他人公正,诚实这种美德就要求其拥有者对他人诚实,慷慨这种美德就要求其拥有者对有需要的人乐善好施。但这些真正的自爱者所关心的只是他人的外在福祉,而没有同时关心在他们看来更重要的他人的内在福祉。这种观点就遭到了当代哲学中康德主义哲学家的批评,说这样的具有美德的人是自我中心的。如果他们真的认为内在的美德比外在的福祉更重要,那么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也应该关心他人的美德。例如,一个真正慷慨的人应该设法让他人也有慷慨这种美德,一个真正诚实的人应该设法让他人也有诚实这种美德,一个真正正义的人应该设法让他人也获得正义这种美德。
虽然笔者曾撰专文,以朱熹为例,说明儒家的美德伦理可以对这样的批评作出很好的回应,[注]黄勇:《关于美德伦理之为自我中心的批评及朱熹的回应》,吴震编:《宋代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也是贯穿笔者其他一些文章的一个重要论点。例如在讨论孔子的以直报冤时,笔者强调,这里的“直”应当理解为“正曲为直”之“直”。假如有人打了我的左脸,孔子的立场不是像耶稣所教导的那样转过右脸让他打(以德报怨),也不是去打他的左脸以作出报复(以怨报怨)。相反,孔子的看法是,在这里,我所面对的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一个枉者、一个曲者、一个不直者、一个具有恶德的人,那么我作为一个具有“直”这种美德的人就应该设法让这个人从枉者、曲者,变成一个跟我一样的直者。这就是孔子以直报怨的意思。[注]黄勇:《为什么你不应该转过你的左脸:孔子论如何对待作恶者》,《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1-12页。这样一种理解也贯穿于我关于孔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讨论中。这里的直也是正曲为直的“直”。偷了羊的父之所以要被隐,是因为他做了不道德的事情,是个曲者、枉者,那么子作为有道德的人、作为直者,就应该设法让其不道德之父变成直者。儒家认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微谏,而如果子在这里对父亲的不道德行为不是隐之而是证之,那么微谏的环境或气氛就不存在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认为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注]黄勇:《正曲为直:〈论语〉“亲亲相隐章”新解》,《南国学术》2016年第3期,第366-377页。在另外一个地方,笔者指出杨国荣在其《成己与成物》一书中忽略了成人这一点,也与这个问题有关。[注]黄勇:《成人:在成己与成物之间》,《哲学分析》2011年第2期,第19-30页。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成人与成己不同,后者是一个人的自我修养,也即大学中的明明德,而前者则是帮助他人进行自我修养,也即大学中的新民。另一方面,成人与成物也不同。尽管这里的“人”和“物”相对于要成就之的、具有美德的人来说都是他者,但对于后者,具有美德的人只能辅其自然,而对于前者,具有美德的人不仅要帮助其明明德,而且要在此过程中帮助他去帮助他人明明德,而这也是基于儒家对于具有美德的人的理解。
第二个是与上述问题有关的关于具有美德的人是否本质上是利己主义者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上,美德伦理与后果论和规则论差别不大。假如有人需要帮助而且我可以帮助这个人,我该不该帮助他?笔者认为所有这些伦理学都会作出肯定的回答。但如果问为什么我要帮助这个人,则这三种伦理学会提供很不相同的回答。规则论也许会说,每个人都有遵循道德原则的义务;后果论也许会说,这样做会最大限度地增加这个宇宙中的幸福总量;而美德论的典型回答是,只有这样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人。比较这三种回答,似乎美德论的回答具有明显的利己主义倾向:一个人之所以要帮助人是因为他自己想成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卡(Thomas Hurka)认为具有美德的人是根本上的利己主义者。这里他承认,与我们上面讨论的第一点有关,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不只关心他人的外在福祉,而且还关心他人的内在福祉,即也想让他人成为具有美德的人;他也可以承认,一个具有美德的人确实是为帮助他人而帮助他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才帮助他人,因为不然他就不是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但这个人之所以作这些,还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人。换言之,他是为了自己(成为具有美德的人)的缘故,才去为他人的缘故去帮助他人(help others for their sake for one's own sake)。
在上述那篇关于朱熹如何帮助我们回应美德伦理的自我中心问题的英文原文中,笔者对这个问题也有详细的讨论,但由于原文较长,在翻译成中文时,这一部分删除了。这也是笔者另外一篇文章所聚焦的一个问题。[注]黄勇:《好德如好色:孔子对当代美德伦理的贡献》,《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2017年第4期,第1-12页。由于儒家伦理是一种美德伦理,因此它似乎也存在霍卡所谓的根本的利己主义问题,这特别体现在孔子强调的为己之学。今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实际上就体现了儒家的这个思想:我们从事道德修养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为健全的、没有缺陷的人。笔者认为儒家对这个问题可以做出本质上相同的两个回答。一方面,可以说儒家的具有美德的人就其努力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了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人而言,他确实在根本上是个利己主义者;但另一方面,他所要获得的主要美德,仁义礼智,又都是涉及他人的,因而要成为这样一个具有美德的人就需要成为一个关心他人(既包括他人的外在福祉也包括他人的内在美德)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又在根本上是一个利他主义者。在这里利己主义者和利他主义者就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就必须成为一个彻底的利他主义者,反之亦然。这是儒家对这个问题可以做出的第一个回应。儒家可以做出的第二个回应是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和程颢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出发,从而从根本上否定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来描述一个具有美德的人的恰当性。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都假定自己和他人的分离,但这里提到的孟子和程颢的观点表明,一个具有美德的人把他人看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因而把他人的痛苦(无论是外在的身体上的还是内在的人性上的)看作是自己的痛苦。你可以说这样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但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不包含在他这个自己中,也就是没有任何“他”这个人还可以利,说他是一个利己主义同说他是一个利他主义就一样失去了意义。
第三是美德与社会正义的问题。在美德伦理学所讲的诸美德中也包括正义这种美德,但美德伦理学中的正义是作为个人美德的正义,而不是作为社会政治制度之美德的正义,而政治哲学中讲的正义恰恰是关于社会政治制度包括法律和政策的正义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较之规则论伦理学和功用论伦理学,美德论伦理学似乎存在着一个天生的缺陷。功用论伦理学可以很容易地提出一种社会正义的理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是能够产生最大幸福总量的社会制度。规则论也不难提出一种社会正义理论,事实上今天比较有影响的社会正义理论,包括罗尔斯的理论,都是规则论的,毕竟我们可以根据制定有关个人行为的规则的同样理论去制定有关社会运作的规则。而美德伦理讲的是个人的美德,那怎么从作为个人美德的正义推出作为社会美德的正义呢?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途径是,先看具有正义这种美德的人是如何维持与他人的关系的,然后再看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能够维持这些关系。这样一种途径的一个缺陷是,它把社会正义的主体(agent)看作是具有美德的个体,而社会的功能就是保证这些个体能够维持其与他人的正义关系。如果这种模式在小规模的古希腊城邦还有可行性的话,在当今规模大得多的民族国家中,它很显然已经不能适合了。
笔者认为,儒家的美德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作出贡献。[注]黄勇:《关于美德的正义:儒家对桑德尔正义观的修正》,《南国学术》2017年第4期,特别是第二节。简单来说,儒家的看法是,一个社会的正义观念源于作为个人的正义这种美德。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 离娄上》)《大学》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这是说,政府及其政策法规之所以是正义的,只是因为治理它的人是正义的。孟子还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这里他强调,领导人有仁心,政府也就有仁政,即仁政来自仁心。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要确定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否公正,关键是看这样的制度是不是一个具有正义这种美德的人制定出来的。这一点与美德伦理关于个人行为的讨论一致。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是正义的行为就是看其是不是一个具有正义这种美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做出的行为;如果正义的人会作这样的事,那么这件事就是正义的事,即使在这个特定场合下作这件事的人还不具有正义这种美德,因为美德伦理学可以承认,缺乏某种美德的人可以做相关的德行。同样的道理,判定一个(例如)法律是否公正,就是看一个具有公正这种美德的人是否会制定这样的法律,尽管实际上制定这个法律的人还没有公正这种美德。总之,儒家把法律与个人的行为看成类似的东西,其公正与否取决于一个公正的人是否会制定这样的法律和做这样的事。
二、儒家如何帮助美德伦理克服其内在的困境
在对外来的批评作出尽可能有力的回应的同时,当代美德伦理学家也开始认识到其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和困境,并努力加以弥补和解决。但笔者认为,其中的一些弥补和解决方案并不令人满意,而儒家在这些方面也具有其长处。
第一是关于所谓的美德两难的问题。这是由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福特(Philippa Foot)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福特认为美德对于人的自然倾向起一种矫正的作用:美德要求我们去做的事往往是我们缺乏自然倾向去作的事,而美德要求我们不要去做的事往往是我们的自然倾向让我们去做的事。例如,勤劳之所以是一个美德是因为我们有懒惰的自然倾向(如果我们的自然倾向就是勤劳,那么我们也就不会将勤劳作为一种美德去提倡了)。由此,福特注意到,美德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往往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即需要我们通过克服自身具有的相反的自然倾向才能完成的事情,但具有美德的人在做这些美德的事情时却感觉很轻松、甚至很愉快。这里就产生了她所谓的美德的两难:当一个没有美德的人成功地但艰难地(因为他要与自己所具有的相反的自然倾向作斗争)从事了德行时,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个行为比具有美德的人做的同样的行为更值得表扬,因为他成功地作了一件艰难的事情;而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觉得这个人之所以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做这一德行恰恰是因为他在德性上不完满,因而不像那个具有美德的人那么值得表扬。福特自己解决这个两难的办法是在作为总体的人类与具有美德的特殊的人之间做一区分:具有美德的人在做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困难的事情,因而还是值得表扬,尽管他在做这件事情时轻而易举。
笔者在两个地方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福特的这个解决方案是有问题的。[注]黄勇:《好德如好色:孔子对当代美德伦理的贡献》,《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第五节;黄勇:《美德伦理与道德责任:儒家论道德赞扬与责备》, 景海峰编:《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二节。具有美德的人在做德行时之所以值得表扬(如果值得表扬的话)不仅仅是因为他做了一件对他轻而易举而对一般人十分艰难的事情。假如一个身高二米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碰到很高的屋顶,我们不会说这个人的行动值得表扬,因为这个人做了一般人或者根本不能做到或者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做到的事。笔者认为儒家对这个所谓的美德两难会提出一个不同的解决办法,而其不同之处在于它采取了一种历史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换言之,它不是只看当下两个人在做同一件德行时谁做得轻而易举而谁需要克服很大困难;相反它会问,为什么一个人做这个德行时这么容易,而另一个人在做这个德行时却这么困难?经过这样一问,我们就会很容易发现,具有美德的人之所以能这么轻而易举地从事德性,恰恰是因为他以前花了非常大的力气从事道德修养,而最终成了一个具有美德的人;而没有美德的这个人之所以在做德行时要作这么大的努力才能成功,恰恰是因为这个人以前没有下力气进行道德修养,从而没有成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人。如果他以前花了大力气从事道德修养并成了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他今天在做这个德行时就不会感到这么吃力了。这样,在一个没有美德的人花了很大力气才成功地从事的德行与一个具有美德的人轻而易举地完成的德行之间,到底哪个人的行为更值得赞扬的问题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是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大家知道,这是苏格拉底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是知识,而知识是可教的,但苏格拉底又明确地说,美德不可教。这里我们应该清楚,当苏格拉底说美德是知识时,他说的知识也就是我们下文将提到的动力之知或者信欲。这一点可以从他在《普罗塔格拉》中关于意志软弱问题的看法来说明。他在那里说,没有人在做一件事时知道或者相信他在做的这件事不是他在这种情况该做和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即他可以做别的更好的事情)而还继续做这件事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儒家的知而必行的观点,因此他否认有意志软弱这种现象,因为意志软弱恰恰就是指知道自己不应该做某件事而且可以不做这件事却还是去做这件事,或者知道自己应该做某件事而且可以去做这件事而不去做这件事。但在同一对话中,苏格拉底却认为这种作为知识的美德却是不可教的,不是可以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为了说明他的这个观点,苏格拉底做了一个类比。一方面,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造船,我们可以请造船专家来教我们,这就表明造船技艺是可教的。但另一方面,伯里克利(Pericles)为他的孩子提供了最好的教育,教了他们所能教的一切,但在美德方面,他不仅自己没有教他们,而且也没有请别人教他们,因为美德不可教。
对这个问题,笔者也曾撰专文,以孔子的思想为出发点加以讨论。表面看起来,孔子似乎也认为美德不可教。他曾经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根据宋儒程颐对这句话的解释,这里孔子既不是说老百姓愚不可及,也不是说圣贤不是好的老师,更不是说君王应该让老白姓处于愚昧状态。关键是这里的知乃是道德知识,即动力之知和信欲。这种知识按其本性需要靠人通过默识心通而自得。如果这样,似乎孔子就跟苏格拉底一样认为美德不可教了。但事实上,孔子作为一个老师教给学生的又恰恰正是这样的作为美德的知识,因为孔子的目的并不是想让他的学生成为学问家,而是成为具有美德的人。这里的关键不是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教的问题。理论知识(理智之知)可以通过书本或者演讲从一个人传递到另外一个人,能力知识可以通过手把手的方式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由于作为美德的知识即动力之知不能通过这两种方式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苏格拉底便认为美德不可教。但在孔子看来,美德是可教的,但需要有上述方式之外的方式。由于缺乏美德的人所缺乏的往往不是对美德的理解,也不是从事德行的能力,而是相应的情感和欲望,美德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乃是情感主义教育。孔子说的道德教育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中的第一步,“兴于诗”,就属于这样一种情感主义的教育方式。但孔子最为注重的是身教。这里所谓的身教主要不是用来传递技艺知识的手把手的教育方式,而是指以身作则的模范方式,因此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古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第三是美德与道德责任的问题。道德知识的一个特征就是具有这种知识的人一定会有动力去从事相应的行动,知而不行,非真知。这就引出了一个美德伦理必须面对的道德责任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要求一个人为其没有行善或者甚至作恶而负责。这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要人为其行为(或者其行为的缺失)负责,即使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这人的行动是其自由选择决定的。如果一个人被他所无法抵抗的外力强制地作了一件伤人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不能要这个人为他给他人造成的伤害负责。第二,这个人对他所做的事要有相关的知识。假如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时并不知道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我们也就不能要求这个人为其行为负责,换言之,我们不能为一个人因无知而做错的事情负责。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这第二个条件给美德伦理带来的难题。我们前面提到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观点,具有美德的人是具有知识的,而这种知识是能使人有动力从事相应行动的知识,而不能使人有动力行动的知识实际上不是知识,或者只是宋明儒所谓的常知、浅知、闻见之知,而不是真知、深知、德性之知。如果是这样,一个人没有做他应该做的德行或者做了他不该做的恶行,一定是因为他缺乏相应的知识,是因为他的无知。如果是这样,我们似乎就不能让他为其行为(或者其缺失)负责,而这很显然是很严重的问题。
笔者也曾讨论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注]黄勇:《美德伦理与道德责任:儒家论道德赞扬与责备》,第三节。儒家的这个看法与我们在上面谈论的看法有关:它所采取的是一种历史的而不是截面的看法。如果采取截面的看法,那么这个人在作恶时,根据美德伦理的看法,一定是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因而我们不能让这个人为其行为负责。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就要看这个人该不该为其无知负责。我们知道有些无知是情有可原的。 假如我无法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么我想很少有人要我为自己的这种无知负责。但有些无知是不可原谅的。假如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超速被警察抓,是因为我不知道高速公路有限速,那么假如我真的不知道,很显然我要为我的这种无知直接负责,而同时也要为我自己因这种无知而造成的超速间接负责。现在的问题是,缺乏有关的道德知识,道德的无知,是情有可原的还是不可饶恕的。儒家的回答是后者。这是因为在儒家看来,这种道德知识,即所谓的良知良能,是我们每个人生而俱有的。之所以我们许多人现在好像缺乏这样的知识,是因为我们的私欲将这样的知识泯灭了。我们现在要重新获得这样的知识,就要将这样的私欲去除,而要去除这样的私欲,我们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即使“愚夫愚妇”,只要努力用功,不自暴自弃,都可以获得为道德行动所必要的知识。因此,儒家认为每个人都要为其因无知而做出的不道德的事情负责,是因为这个人要为自己的道德的无知负直接的责任,因而要为其因这种无知而做的不道德的事情负间接的责任。
第四是美德的客观性与规范性问题。瓦特森(Gary Watson)认为美德伦理面临一个两难:如果想对美德做一说明,美德就失去了其在伦理学体系中的首要性;而如果想保持美德的首要性,你就无法解释什么是美德。笔者曾经用朱熹的例子说明,儒家如何可以既提供一种对美德的说明,而又保持美德的首要性,从而避免这个两难。但瓦特森认为在我们去说明什么是美德时,不管我们是否避免了第一个两难,我们往往会陷入又一个两难。我们在说明美德时往往借助人性概念,将美德与人性相联系。如果我们强调人性的客观性,那么这样的人性观念就会缺乏美德所需要的那种规范性;而如果我们要想强调人性之为美德所必需的规范性,我们的人性概念就往往缺乏客观性。亚里士多德用来说明美德的人性概念似乎就陷入了这个两难的第一翼。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即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是理性。一般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一点,因此这样一种人性观具有足够的客观性。但是正如很多当代有名的哲学家如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和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都指出的,从理性里面是推不出规范性的美德概念的,也就是说一个具有充分理性的人不一定就是一个具有充分美德的人。麦克道尔还用了其有名的理性的狼来说明这一点。狼跟人一样是社会性的动物,其跟人不一样的一点即是缺乏理性。但麦克道尔说,假如一个狼群中的一只狼获得了理性,它不见得会变得道德起来;它反而有可能利用自己新获得的理性来算计其他狼,使自己不劳而获。这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说明是强调了人性的客观性而缺乏为美德所需的规范性。
笔者曾用朱熹为例子说明儒家对美德伦理的贡献,强调了其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在儒家看来,真正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不是人有理性而动物没有,而是人有仁义礼智而动物没有。仁义礼智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同时又是儒家最重要的德目。因此在另一个地方,[注]黄勇:《理学的本体论美德伦理学:二程的德性合一论》,杨国荣编:《思想与文化》第四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笔者强调,在儒家那里德(美德)和性(人性)是同一的。由于构成人性的仁义礼智本身就是规范性的美德,那么这种对人性的说明就避免了亚里士多德对人性的说明所具有的问题,而保持了人性这个概念为美德所必要的规范性。但现在的问题是,儒家在强调人性概念的规范性的同时是否失去了这个概念应有的客观性呢?也就是说儒家有没有什么客观的根据来证明人性中确实有仁义礼智呢?如果没有,那就表明儒家根据人性对美德的说明陷入了瓦特森所提到的这个两难的另一翼:保持了规范性却失去了客观性。笔者曾试图以朱熹为例回答这个问题。[注]黄勇:《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而非基础主义的》,《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118-128页;黄勇:《规则与德性:评童世骏〈论规则〉》,《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5期,第76-82页。虽然在朱熹看来,人性本是形而上者,对之我们不好说什么。但是人性是通过人情体现出来的。我们看到人有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之情,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必有其根,因此从这样的人情里面我们就可以推知人性里一定有仁义礼智。在朱熹看来,虽然人性看不见摸不着,但四端之情却是我们都可以看见的,而为了解释为什么会有这四端之情,我们不能不假定有仁义礼智之性,这就好像我们看到一棵健康的苗,为了解释其存在,我们就不能不假定下面一定有一健康的根,尽管我们看不见根,更无法直接断定其健康与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朱熹关于人性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解释性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仁义礼智概念是用来解释我们都感觉到的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这些经验现象的。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具有规范性的人性概念同时也具有客观性,从而避免了瓦特森所说的美德伦理的第二个两难。
三、儒家如何帮助美德伦理对当代哲学作出贡献
发展美德伦理学的目的当然主要不是要与近代以来在伦理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道义论和功用论争第一把交椅的问题,而是要看美德伦理学能够为当代伦理学甚至当代哲学作出什么重要贡献的问题。在这方面笔者认为,挖掘儒家的资源同样重要。
第一是关于动力之知的问题。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儒家作为美德伦理学对道德认识论所可能做出的一个独特贡献。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不能仅因为一个人有德行就称他为具有美德的人。具有美德的人当然会从事德行,但除此之外,这个人还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才可以算是一个有美德的人。第一是这个人对于自己的德行有认识,即不是懵懵懂懂地去做的;第二是这个人自己选择去从事这样的德行并且是因为这个德行本身而不是别的理由才从事这样的德行;第三是这个德行来自其坚定而又稳定的性格。这里讲的第一个条件是知识,而且正是这样的知识使人有动力从事德行。但知识怎么能使人有动力去从事德行呢?这就涉及了认识的本质问题。传统的认识论,包括道德认识论,主要关注的是理智性的认识,即赖尔(Gilbert Ryle)所谓的命题性知识(knowing-that),如我知道我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这样的知识很显然与道德动力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有这样的知识而缺乏动力去帮助他人的大有人在。赖尔认为传统的认识论过于狭隘,忽略了一种与理智之知很不相同的能力之知(knowing-how)。他所谓的能力之知主要是指像知道怎样开玩笑和欣赏玩笑,怎样弹钢琴,怎样骑自行车等。它跟理智之知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前者是通过看书或者听讲座就可以获得的,而后者则必须通过自己的反复实践才能获得。由于这样的知识具有实践性,而道德知识乃是实践的知识,很多人认为道德知识就是这样的能力之知。但是能力之知,同理智之知一样,跟一个人去做有关事情的动力没有必然联系。知道怎样帮助人即有能力帮助人而缺乏动力去帮助人的情况也是司空见惯的。
所以笔者认为美德伦理中谈论的能够使人有动力去行动的知识一定既不是理智之知,也不是能力之知,而是与此都不同的第三种知识,即笔者所谓的动力之知(knowng-to)。这是笔者在两篇相关的文章中已阐述的一个看法。[注]黄勇:《论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抑或动力之知?》,《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第49-63页;黄勇:《再论动力之知:回应郁振华教授》,《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第24-30页。笔者认为虽然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观点,但把道德知识与道德动力的关系真正说清楚的要算王阳明。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就是笔者所谓的动力之知的范例。所谓的动力之知也就是人有动力去做相应的事情的知识。例如,我关于孝的动力之知就既不是我应该孝顺父母的知识(理智之知),也不是我关于如何去孝顺父母的知识(能力之知),而是会(不是表示能力的“会”而是表示倾向的“会”)去孝顺父母的知识,而这正是王阳明所要强调的。王阳明的良知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所谓的知行合一。所谓的知行合一,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知而必行;知而不行的“知”并不是真正的知。但这不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独特的方面。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主要是用来批评程颐和朱熹的知行观的。程朱也非常强调知而必行,但他们同时却又认为知先行后,这就是说,知和行在他们那里是两回事。而在王阳明看来,知行的本来状态即他所谓的知行本体就是同一的,说知,行已经包含在里面,而说行,知已经包含在里面。说行只是要强调知所含有的使人行动的动力,而说知只是要说明行动之明觉精察。
第二是所谓信欲(besire)即信念和欲望的综合体的问题。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儒家作为美德伦理学对当代行动哲学、心灵哲学和道德心理学所能作出的一个贡献。在行动问题上,当代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休谟主义。休谟主义认为行动与信念(belief)和欲望(desire)这两种心灵状态有关。例如我去帮助一个人,作为一种理性的行动,一定是因为我相信我应该去帮助这个人,同时我又有欲望去帮助这个人,两者缺一不可。当然,这种立场也遭到了不同的批评。理性主义者认为信念本身已经可以说明行动,因此无需用欲望来解释行动,而情绪主义者(emotivist)则认为只有欲望可以解释行动,信念要么不过是一种伪装了的欲望,要么与行动根本没有关系。最近也有一些反休谟主义者,他们同意休谟主义,认为需要同时用信念和欲望才能解释行动,但他们与休谟主义又有不同,认为信念和欲望不是两个不同的心理状态,而是同一个心理状态的两个不同方面。这个心理状态一方面像信念,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另一方面又像欲望,促使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由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同时包含了信念与欲望,有人造了一个字,称之为信欲(besire)。很显然,笔者上面用动力之知来描述的王阳明的良知也就是这样一种信欲。例如,我关于孝的动力之知,一方面是关于我应该孝顺父母的信念,而另一方面又是我想去孝顺父母的欲望,而王阳明反复强调,这两者按其本体是一回事,他们是同一个心灵状态的两个方面。
但是这样一种观点遭到了休谟主义的批评,认为信欲( besire)非常怪异(bizarre),因此不可能存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信念和欲望与世界的关系正好相反。如果我的信念与世界不一致,我就必须改变我的信念以与世界一致;但如果我的欲望与世界不一致,我往往会去改变这个世界以使它与我的欲望一致。所以信念这种心灵状态与世界一致的方向(让心灵状态去与世界适合)和欲望这种心灵状态与世界一致的方向(让世界去与心灵状态适合)正好相反。如果信念和欲望是两种不同的心灵状态,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它们属于同一个心灵状态,问题就出现了:假如这个心灵状态与世界不一致,我们是改变这个心灵状态、使之与世界适合呢(好像我们应该这么做,因为这个心灵状态是信念),还是改变世界、使之与这个心灵状态适合呢(好像我们应该这么做,因为这同一个心灵状态也是欲望)?作为信欲,我们要同时做这两件相互矛盾的事情。由此可见,信欲这种怪异的心灵状态压根就不可能存在。但笔者认为休谟主义者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信念做了过于狭隘的理解,以为信念只包括像“今天在下雨”这样的描述性的信念。但事实上也存在规范性的信念。假如我相信所有子女应该孝顺父母,而在世界上并不是所有子女都孝顺父母,甚至世界上没有人孝顺父母,这也并不表明我应该放弃我的信念,而开始接受一个与世界相符合的信念。相反,我会认为,这个世界不是其应该是的样子,因此需要加以改变,使之与我的信念一致。这就表明,规范性的信念与描述性的信念不同,它与世界符合的方向是让世界与它这种心灵状态相适合,而不是相反,而这种适合方向同欲望与世界的适合方向是一样的。因此当儒家肯定有一个既是信念又是欲望的心灵状态即信欲时,他们并不是在讲一个非常怪异的心灵状态。笔者曾撰专文讨论过这个问题。[注]黄勇:《为何信欲不是怪胎:儒家与印度教中的道德知识》,泰奥多、姚治华编:《梵与道:印中哲学和宗教比较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
第三是关于政府有没有从事道德教育的功能的问题。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关于政府是否有引导公民过好生活的功能问题上,存在着国家完善论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政治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保持中立,而国家完善论则认为政府有责任引导公民过好的生活而避免不好的生活。但笔者认为,他们所争论的都是那些涉及自我的(self-regarding)方面。例如,国家完善论认为国家有责任引导其公民过的好生活就包括欣赏艺术、音乐、自然之美等,而国家应该设法让其公民避免的不好的生活就包括酗酒、抽烟、赌博等。而自由主义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到底什么是好生活应该由个人自己去决定。由于个性的极大差异,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好的生活,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则不一定是好的生活。在笔者看来,这场争论忽略了在其公民之涉及他人的(other-regarding)行为方面政府所应有的功能。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可以强制地推行与涉及他人的行为相关的那部分道德,而在这方面国家完善论没有加以质疑。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儒家可以做出其独特的贡献。[注]黄勇:《公共权力应如何劝教生活方式》,《学术前沿》2013年第2期,第12-33页。
孔子有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就说明,在儒家看来,在推行涉及他人行为的道德方面,政府所依靠的主要不是政和刑,而是德和礼。在这一点上,如笔者曾指出的,儒家的主张甚至也与亚里士多德很不相同。[注]黄勇:《关于美德的正义:儒家对桑德尔正义观的修正》,《南国学术》2017年第4期,第568-583页。亚里士多德与儒家一样,也认为国家有让其公民成为具有美德的人的功能。但怎样才能让其公民具有美德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多数人之所以不去做坏事,不是因为他们会为自己所做的坏事感到羞耻,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惩罚,因此国家只有通过立法的手段才能使人获得美德。这与孔子上面讲的以德和礼使老百姓获得美德的看法大异其趣。这里所谓的德是政治统治者应该有的美德。孔子认为统治者是老百姓的样板。如果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他对问政于他的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些都说明,统治者要想让老百姓成为有德之人,首先他自己得成为一个有德之人,成为一个表率,让老百姓模仿。除了德教以外,孔子也很注重礼教。我们前面提到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我们说这里的“兴于诗”,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教育。但是通过诗歌等手段所激发起来的道德情感往往短暂而不稳定。为了维持由诗引起的道德情感,使之稳定化,孔子强调了礼的重要性。礼仪规则与惩罚性的法律不同。刑法偏重消极的禁止,而礼仪注重积极的规矩;违法的有刑罚的处分,而违礼的会受到君子和社会的批评;刑罚利用的是人们害怕惩罚的心理,而礼仪利用的是人们的羞耻心,因而可以使人“有耻且格”。当然在做出由礼仪规范所限制的道德行为时,人们可能还会感到某种拘束、不自然,因此孔子认为道德教育最后还需要通过乐教来完成,使人能够自然地、轻松地、快乐地从事德行。
第四点则与法律哲学中的惩罚理论有关。在一个人犯了罪以后,大家都认为这个人需要受到惩罚。在西方的法律哲学中,主要有两种惩罚理论。一种是报应(retributive)论。这种理论认为,在有任何人犯罪之前,大家都是平等的(不管这个平等是如何定义的),而罪犯通过其犯罪行为打破了这种平等,因为他通过让他人受损而使自己得益。社会就是要通过惩罚来恢复这个犯罪行为之前的平等状态。因此公正的惩罚应该不多不少地剥夺这个罪犯通过犯罪而获得的益处,或者应该不多不少地让这个罪犯接受他加给受害者的伤害。另一种是功用论(utilitarian)。这种理论认为,惩罚的目的是使这个罪犯甚至其他潜在的罪犯以后不再去犯罪。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通过惩罚使罪犯得到的伤害必须大于他通过犯罪得到的好处。在功用论看来,报应论的主要问题是,由于报应论反对让罪犯通过惩罚受到的伤害大于他通过犯罪得到的好处(或者他通过犯罪给他人带来的伤害),惩罚就起不到威慑的作用,这个罪犯以后还可能犯罪,而别的潜在的罪犯也会因此去犯罪,毕竟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犯罪行为被发现,不过就是放弃通过犯罪所得到的好处,但他们有足够的自信,不可能他们的每次犯罪都会被发现。而在报应论看来,功用论的问题是其不公正。从公正的角度看,我们没有理由让一个罪犯通过惩罚得到的伤害大于他通过犯罪对他人造成的伤害,特别是我们不能用这个罪犯作为工具,让他受到过度的惩罚来威慑别人,使他们不敢去犯罪。
笔者曾提出儒家关于罪犯的看法,将这种看法称作康复论(rehabilitative),并认为这种理论比报应论和功用论优越。[注]黄勇:《正曲为直:〈论语〉“亲亲相隐章”新解》, 《南国学术》2016年第3期,第366-377页;黄勇:《关于美德的正义:儒家对桑德尔正义观的修正》,《南国学术》2017年第4期,第568-583页。从儒家的美德伦理的立场出发,一个不道德的人,包括罪犯,实际上是一个人性上有缺陷的、不健康的人,因为正常的人都有仁义礼智,而不道德的人在仁义礼智方面受其私欲影响而受到了伤害。就好像我们在看到一个人身体上有缺陷、不健康、受伤害时,我们根本不会想该如何去惩罚这个人,而一定是如何帮助这个人克服这样的缺陷,医治这样的伤害,并使之健康起来;同样,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人性或其明德受到其私欲的伤害(而去犯罪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也不应该是如何去在身体上惩罚这个在人性上已经受到伤害的人。相反,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去帮助这个人克服其人性上的缺陷,从而使这个人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这种理论跟功用论和报复论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后两种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受害者,因此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为受害者去惩罚罪犯,而康复论所主要关心的则是罪犯,因此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帮助这个罪犯医治其毛病。从直觉上看,这似乎是儒家康复论的一个缺陷:在一个罪犯对他人造成伤害以后,我们当然应该站在受害者这一边,而不是站在加害者即罪犯这一边。事实上,这正好体现了儒家康复论的长处。一方面,这个罪犯康复以后就成了人性上健全的人,即成了有德之人,那他以后就不会再去犯罪,而这正是功用论的目的。另一方面,这个罪犯在康复后,他们自然地会将其通过犯罪得到的好处交还给受害者,而对于其通过犯罪行为使被害者受到的其他伤害也会设法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加以弥补,而这也正是报应论所要达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