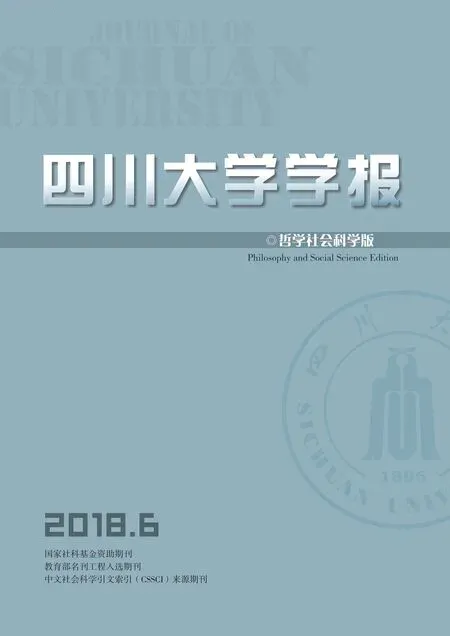论句子最小语义与意义整体论的兼容:公孙龙“‘马’者所以命形也”命题的启示
2018-11-26,
,
自维特根斯坦、奥斯丁、格莱斯引发的语用学转向开始,语境、意图被引入了语言意义的分析之中。一个重要后果即是语义研究中的语境主义潮流。语境主义认为词义、句义都是语境敏感的,即任何词、句的意义只有相对于具体语境才可确定。*F·雷卡纳蒂:《字面意义论》,刘龙根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153页。如:句子“张三个儿高”的意义不确定,因为张三指谁、其身高比较的参照人群(运动员还是儿童)都不明确;“你不会死的”的句义只有在特定语境下(如一个小孩因受了小伤而哭闹时,其母亲说出这句话)才可确知其含义,否则其意义是不确定的;“所有人都准备好了”的意义不确定,因为“所有人”指称的范围未明确,准备好了什么或者做什么也不知道;等等。语境主义的后果是:语义普遍性不存在,语义学不可能、也没必要;甚至一般性知识也是语境敏感的:知识=a在语境C下知道p。*曹剑波:《“知道”的语境敏感性:质疑与辩护》,《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但问题在于:如果语义的确定只能相对于语境,人对世界的认识将承受超重的认知负担——由于语境数量无穷大且瞬息不同,每个人都不得不在每个具体语境之下分别单独解释每句话的具体意义。*关于认知负担问题的例子及讨论,详见M·W·艾森克等:《认知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4-345页。这事实上等于否定了跨语境语义及语言交流的可能性;如是,则语言习得、知识传授皆不可能。这是很成问题的。
语义最小论正是作为语境主义的对立阵营而出现的。他们认为语境主义在方法和内容上都是错误的,求诸于语境敏感性来解释语言意义是个“便宜活儿”,却是“偷懒的哲学”,这不仅会损害建立系统化语言理论的基础,也无法解释日常语言交流,更无法说明书面语意义的理解,即通过阅读获得知识如何可能。*H.Cappelen & E.Lepore,“Précis of Insensitive Semantics,”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ol.73, No.2, 2006, pp.425-434.语义最小论主张:一个句子的最小语义内容就是由其构成词项按句法规则组合而成的规约性意义;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语义理解的先在性,即无论语境多么不同,一个句子都有同样的语义内容,使得相互理解、语言习得成为可能。*H.Cappelen & E.Lepore, Insensitive Seman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152.
但是,语义最小论要立得住脚的话,词语的意义是什么、是否有确定性就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意义整体论对语义最小论构成了极大挑战。本文打算思考这一挑战,讨论可行的理论应对。
一、意义整体论的挑战
意义整体论认为:单个的语词、句子不是意义的承载单位,即没有独立的意义。由于“关于外部世界的陈述不是单个的,而是作为整体接受经验的裁决的”,[注]W.V.O.Quine,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in M.Baghramian, ed.,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ashington D.C.: Counterpoint, 1999, p.156.语言表达式只有作为整个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才有意义,[注]J.Fodor & E.Lepore, Holism: A Shopper's Guide, Oxford: Blackwell, 1993, p.ix.或者说只有相对于一个特定语言框架才有意义。[注]详见R.Carnap, “Empiricism, Semantics and Ontology,” in Baghramian, ed.,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p.64-85.词、句的意义有赖于人的知识信念的支撑。例如,“水是H2O”的意义解释以接受关于化合化分、乃至整个化学体系的知识为前提,即认可化学知识获得的方式、方法及原则,并承认关于化学研究设施所涉及的物理、工学等一系列科学的知识及其实验方法、程序的合理性;而承认这些则意味着接受科学认识的世界观假定(如世界是实在的、可认识的等)及其核心的逻辑原理(如不矛盾律、排中律等)。[注]如莱肯所言,哪怕是日常生活的句子,如“桌子当头有一把椅子”,其意义的理解也要求说话人具有“巨量的假定前提”——诸如知道什么是椅子,假定一系列经验的确定性,如桌椅的位置、进入房间的方位、有光线以及眼睛是睁开的且视觉正常等等。关于杜恒-蒯因原理及本注引用的例子的讨论,详见W.Lyc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2000, p.125.如果信念体系不同,则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必然不同,在一个系统中有意义的表达式在另一个系统中则可能无意义。如,“语言”一词,即便是在语言学领域内也因不同学派的理论体系不同,其意义差异很大:对描写语言学是言语行为、对生成语言学是句法生成系统、对功能语言学则是交际意义选择系统,等等。“语言”是什么,取决于语言学家所持的理论观点。[注]详见刘利民:《“是”与“真”的哲学追问与语言学流派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61-66页。再如,在自然科学信念体系中,“色即是空”没有意义,因为科学信念体系中没有任何陈述能够支持这个句子的理解;而在佛学的信念体系中,同样也没有任何陈述能够支持对句子“光谱分析有发射分析和吸收分析两种原理”的意义解释。总之,“只有在特定语言的语境中一个句子(也因此一个词)才具有意义”,[注]D.Davidson, “Truth and Meaning,” in E.Lepore & K.Ludwig, eds., The Essential David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59.或者具有特定的意义。钱冠连关于弗雷格悖论“‘马’给不出马概念”的论文也支持意义整体论。该文认为,作为主词的“马”无法给出马概念,马概念是述谓给出的;如“马是单蹄的、食草的、家养的哺乳动物;马有平滑的马鬃与马尾、马可供人骑;马用来驼重……直到把所有的述谓说完,马的概念才饱和起来”。[注]钱冠连:《“马”给不出马概念》,《外语学刊》2015年第5期,第3页。饱和是概念内容的充实,所以是述谓把概念送给了主词。钱文说明,马概念包含多维度的意义内容,如马的本质属性、功能用途等。但有两点值得注意:1)马概念作为整体,无法碎片化为任何单一语词指称的对象,所以若要饱和马概念,必定需要数量不确定但足够多的谓词;2)与此同时,谓词也表达概念,这些概念本身也需要由更多的谓词来饱和其意义。例如,说“马是家养的哺乳动物”包含了“哺乳动物”的概念,这本身又需要一个句子,如“哺乳动物是胎生的”,以给出“哺乳动物”的一个方面的意义;而“胎生”概念则又需要更多的谓词予以饱和……如此往复,可至无穷。意义整体论在此得到了具体例证。
意义整体论对语义最小论构成了重大理论挑战:既然单个词、句的意义取决于其所在的整个信念体系,那么讨论最小语义内容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即便可能,那么整体、多维的思想性意义内容如何可能由单维的线性语言符号传递出来?“马”既然给不出马概念,那么这个词能表达什么意义?
或许正因为这一挑战事关重大,J·福多与E·勒坡尔早就以专著批评了意义整体论,揭示了其无法解释的诸多难题,如:如果一切意义都有赖于信念整体,那么鉴于人与人之间的经验、信念差异,语言交流如何可能、语言习得又如何可能?但是这本书却没有能构成对意义整体论的否定。如作者自己所说,他们并不打算证明意义整体论是错误的,只不过是在“清理门背后的灰尘”,说明其论证不足而已。[注]Fodor & Lepore, Holism, p.207.这一回应路径没有奏效,因为事实上人所具有的思想意义确实是复杂的,相互联系的,理解一个概念确实需要以具有其他概念,乃至整个知识信念体系为条件。现代认知心理学也为这一立场提供了一些实证依据。[注]M·W·艾森克等:《认知心理学》,第344-369页。意义整体性无法否定。
另一个回应路径则是所谓“语境化的最小论”。该理论认为句子确实具有最小的语义内容,这个内容是可理解的,但其真值判断只能与语境相关。[注]E.Dokic & J.Corazza, “Sense and Insensibility or Where Minimalism Meets Contextualism,” in G.Preyer, et al, eds., Context-sensitivity and Semantic Minimal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即,句子语义内容提供了真值条件,即可判断真假的条件,但真值的判断本身则是语境依赖的。这一理论把句子的真值条件与对真值的确定分开,认为两者不应混为一谈。这一点很重要,但是该理论最终提出的建议却是在语义最小论理论中接纳“最小量的语境主义”成分。问题是,只要一接受意义的语境依赖性,就必定迅速滑向语境主义结论:所有语义都有索引性。[注]E.Borg, Pursuing Mea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11.这一路径也不可行。
本文认为,意义整体论与语义最小论不必是对立的。前者关于思想,而后者关于语言;两者肯定有联系,但不等同。思想在不同的人可以不同,但语言只要传递出某种“客观的逻辑内容”[注]卡尔·波普尔的用语。他认为存在一个与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并行的“第三世界”,即知识的世界;第三世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同时又超越人而现实存在。参见卡尔·波普尔:《关于客观精神的理论》,载于俞吾金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4页。本文不关注三个世界的本体论证;这里引用他的话是为了突出语言表达式只有传递了客观的内容,才使得公共可理解性成为可能。便具有公共可理解的意义。[注]参见杜世洪:《三个世界,三个问题》,《当代外语研究》2012年第7期。文中引用的一个概念叫“共晓性”。本文则认为“共晓”可以意味着“大家都知晓”,强调关于内容的知识,但知识本身可以是人与人在质和量上都不同的,所以本文认为“公共可理解性”更恰当些。我们需要做的是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接下来从语词与概念的联系入手讨论一个问题:语词的意义是什么?
二、单个语词的确定意义
本文的观点很明确:语词有独立的意义,词义具有公共可理解性。即便是指称个体的专名也是如此。但本文说专名的独立意义不是罗素的与专名相联系的描述语、或塞尔的鉴别个体需要的描述语串的内容,而是把专名的意义作为语言符号承载的公共可理解的内容。什么意思呢?我们从莱肯的一个例子说起。
莱肯举了一个例子来反驳克里普克历史因果论,指出专名并非必然在交往链条中指称特定对象,因为人们常常把人名误认为是机构名,或者反之。如“Emerson Hall”本来是哈佛大学哲学系所在的教学楼的名称,也用于转指该系,但当人们听到句子“Emerson Hall不会喜欢这个”时,通常把专名EH误以为是人名。[注]W.Lyc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2000, p.65.对于本文论题,有意思的正是这个误认,因为误认缘于专名的意义:在人们对专名所指的对象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是专名向他们呈现了一个可把握的公共信息,即专名给出的唯一意义——“这是某对象的名字”。这个意义使得一个/串原本无意义的音成为了有意义的语词。另一方面,尽管说话人可能十分了解EH,即具有关于EH的许多知识信念,但是他使用该专名时,所能给出的也只是对EH命名这一唯一信息,而不能同时给出除此以外的任何其他内容。即是说,专名的意义是公共可理解的对某对象的命名,且此信息是唯一的,不附带任何其他意义。
推而广之,语词是否就是概念的名称呢?很自然我们会这么想。最早由柏拉图提出的语义理论就是命名论,即语词的意义在于命名一类事物共有的本质;而亚里士多德、洛克也认为语词是印象、观念的符号。如今人们依然有此观点:“标签的效果如同‘打开[电脑]文件’,如果顺利,标签则成为信息容器。”[注]A.Vicente & F.Martinez-Manrique,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on Conceptualization: Three Views,” Protosociology, Vol.30, 2013, p.97.语词是形式,概念意义是其内容;自索绪尔以降,这已被广泛接受。但难题在于概念意义是多维的、有赖于整体信念网络的,而语言表达式却是单维的、线性的;既如此,两者该如何结合?求助于概念的本质定义也不可行。普特南早就指出,一个语言社区中只有少数专家能把握概念的本质意义、给出确切定义,而多数人并不见得知道概念的本质定义却仍能恰当地使用语词。[注]这是普特南的“语言劳动分工论”的基本思想。人们关于语言的本质意义并不一定都能把握,语言交流本质上是社会成员之间有条理的合作。他打比方说,在一个社区中,有的人的工作是戴金戒指,有的卖金戒指,而有的则负责鉴定戒指是否真金。戴金戒指的无需知道金的定义而能使用“金”来指称金;当有争议发生时,他们将求助于专家,即负责确定金本位的成员。详见H.Putnam, “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 Baghramian, ed.,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pp.236-238.因此,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语词命名的公共可理解的东西是什么、与概念是何关系?
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哲学家公孙龙的《白马论》对我们很有启发。公孙龙指出,“‘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即语词“马”是用来命名马形的,“白”则命名白色。他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马”所命名的马形不是具体马的形状,因为他做“白马非马”命题的论证,目的在于指出词义不等于对物的实指;“马”的指称不是具体的马,而是马概念。古汉语没有“概念”一语,所以公孙龙只能这样论证:“马有色,固有白马”,但“‘马’无色”;即每一匹马确有其颜色,所以才有“白的马”,但是语词“马”所指的马却是无色的。既然每匹马都有色,那么无色的只能是马概念。因此,他的马形应当是概念之形。其次,公孙龙反复强调,颜色不是马形的内容,马形意义与颜色属性无关,“马”所命名的唯一概念内容只有马形。[注]关于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论证的解读,参见刘利民:《“公孙龙子”重释与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虽然公孙龙只论及了白与马,但沿其思路推之,更一般的理解应当是:既然作为事物属性的颜色不属于马形的内容,那么任何其他属性、功能等也都不是马形的内容;如“马吃草、马跑得快”等句中谓词所描述的都不是马形的内容,甚至“马是单蹄类动物”之类的定义性或曰生物学本质属性也不是马形的内容。确乎如此:这些谓词可以应用于马形之外的其他物之形(兔也吃草、运动员也跑得快、犀牛也是单蹄类动物),并非只是马专有的属性的描写。于是,按公孙龙的思路,在剥离了所有属性描述之后,“马”所命名的只能是马形这样一个基本而纯粹的意义;此意义为区分马与非马所必须,因而是基本的;此意义不包含除了形之外的任何属性内容,因而是纯粹的。[注]这样一种基本而纯粹的形其实很近似于现代拓扑语言学的“简化图式”,即不考虑任何属性参数且由语言所表征的拓扑抽象。参见文旭、赵耿林:《认知拓扑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新趋势》,《东北师大学报》2017年第4期。
这一“命形”思想给予的启发在于,形不是形式,而是意义。首先,形是一个概念必须具有、且仅该概念才具有的唯一内容。此内容是区分此概念与彼概念所必须的意义、且不可再分为更小的成分。但是,形却不等于概念的本质意义,而是与一个概念最简单的、不可再分的内容相联系的意义。如是,语词命名的形就是人们共有的,即公共把握的最小意义。普通人与生物学家都用“马”表达马意义,尽管各自对于马的本质把握可能差异极大。虽然生物学家能给出马的定义(“哺乳纲、单蹄目”等),但这些却不等于所有人公共把握的马形意义,而是对马的本质属性的描述。换言之,人们共同使用的语词“马”的意义并不包含马的生物学定义。普通人无须了解马的科学定义也知道“马”命名的是且只能是马概念,而不是其他物的概念。由于没有现成的恰当术语,本文姑且称这种基本而纯粹的原子意义为“义形”(sense-form)。不光是名词,形容词、动词等实义词都是如此,如“走”作为义形,只给出走的基本而纯粹的意义,与走的速度、方式、距离等相剥离;“红”亦是义形,而与红色的光谱定义、色调、人的辨色力等无关。[注]至于诸如“开门、开车、开会、开荤”之类表达式中的动词“开”,这应属一词多义现象,并不一定是同一动词义形的扩展。所以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关于义形的这一理论设定与意义整体论不矛盾。蒯因的信念网络是复杂的整体,但其成分却是许多陈述,这些陈述相互融贯、支持;即,其中每个陈述都得到网络中其他陈述的支持。对于本文论题,这等于说特定的信念体系对于某一义形将支持一些属性描述,而不支持另一些属性描述。如,生命科学信念体系有足够多的谓词来支持对核酸义形的描述——如“核酸是大分子化合物”“核酸存在于细胞内”等,但道学信念体系却没有任何谓词来形成对核酸义形的述谓,因而道学不支持关于核酸的有意义陈述。另一种情况是,不同的信念体系共有某个义形,但各自支持的属性描述集合中的元素在质或量上却不等同。如,“肾”表达的义形在中、西医信念体系中都能得到支持,因而说“肾是一个脏器”在这两个系统中都有意义,且意义相近;但中医信念体系中还有五行运行、相生相克的陈述,支持“肾属水,水生金”的描述。五行运行是西医信念体系中所没有的,所以西医不支持对这句话意义的解释。同理,马义形是人所共有的,人们都使用“马”来命名最小的不可分的马形内容,以区别于其他义形内容(人、车等)。但是由于经验的不同,人们具有的马概念的属性描述集合却可以不同,如骑兵将马理解为“战友”、生物学家将马鉴定为“单蹄动物”等。须指出的是,属性描述本身也由语词表达,其意义也是义形。即是说,诸如“战友、单蹄动物”等本身也是由语词承载的单维义形,也有待更多的支持性述谓,如“单蹄即趾数多为单数”“战友是生死与共的军队同伴”等等,进而还有“单数(军队)是……”“趾(战)意思是……”等等,以至扩散至整个信念体系。由此视之,本文关于义形的理论设定与意义整体论是兼容的。
关键是,无论信念体系多么复杂,所有信念的陈述却都只能是一次以一个主词-谓词结构的句子来给出该系统支持的意义之一;每个陈述都以义形为主词、属性描述为谓词(暂不考虑修辞因素),表达信念体系支持的一个命题。前述马概念及其他概念的例子已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本文设定的义形在与意义整体论兼容的同时,也为单个语词的意义确立了基础。一方面,义形是概念的原子意义,必定是单维的,故满足语言符号的线性单维性要求,可成为其承载的意义内容。另一方面,义形是概念最小化的但最不可或缺的意义,有资格代表概念。所谓“语词指称概念”本质上应是语词承载义形,义形激活概念,使人做出与掌握了该概念相匹配的适当反应(含言语反应)。[注]达米特曾以“square”为例,说判断一个说话人是否把握square(方形)的概念意义,应该看他是否能够对方形物体做出正确的反应,包括正确地使用“square”一词。参见M.Dummett, “What Do I Know When I Know a Language?” in Baghramian, ed.,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317.总之,义形这一“客观的逻辑内容”使得一个概念能被语词所表征而出场于人际语言交往中。这就是概念多维内容的语言单维化。
至此,本文的结论是:单个语词有确定的、稳定的、公共可理解的意义,即义形。“马”虽然给不出马概念,但能给出公共可理解的马义形,使得关于马的陈述成为可能。
三、句子的最小语义内容及其确定性
既然单个语词具有确定的、公共可理解的意义,那么顺理成章,由语词按句法规则组合而成的命题也具有确定的、公共可理解的意义。由于词义是概念的最小单维意义,由语词组成的句子的语义内容也只能是最小的、单维的命题。即是说,除了字面意义以外,句子并不负责给出任何其他意义,因而句义是跨语境同一的。即便一个句子包含语境敏感的索引词,其最小语义内容也无须取决于具体语境。举个例说,“今天天晴”中的“今天”表达公共可理解的今天义形。无论是在汉语还是英语中,“今天/today”命名的义形就是中国人或英美人公共理解的时间概念意义之一:基本而纯粹的今天。伯格认为这是类型意义,而不是例型意义。[注]Borg, Pursuing Meaning, p.166.但本文认为更有必要强调的是:时间意义是概念性的,不是实指性的。今天义形使得今天概念与昨天、明天等其他概念区别开来,其本质是公共可理解的基本而纯粹的概念意义,而不是对言语交际发生的具体时间的指称。正因为此,在任何时候、任何语境下句子“今天天晴”表达的字面意义都是今天天晴,而不是明天天阴、昨天下雪或猫在席子上。推而广之,所有索引词(如“我、这、现在、所有的”等等)也跟其他词类的语词一样,表达的是概念性形义,而不是实指性意义,其所在句子的命题具有跨语境意义同一性。正是词义的这一性质保证了在不同语境下、甚至缺乏语境条件下,同样的语词按同样的规则组合成的句子表达的必然是同一语义内容。具有跨语境同一性的句子语义内容就是命题。
由此观之,命题不必被当做某种抽象存在的理念式类型意义,有待具体句子来示例。句子中语词的义形内容的公共可理解性足以保证命题意义的跨语境同一性。命题意义本质上是关于某概念的思想的一个维度内容。若用C代表关于概念的思想,K代表义形,而F代表属性描述的集合,那么:C=P(K, Fi(i=1)),其中F={f1,f2,…fn};意即:思想是关于义形K与属性描述意义之一Fi(i=1)组合成的陈述P的总和(),其中F是一个集合,由与可描述概念属性特征的意义元素f构成。如在马概念例子中,“是家养的哺乳动物”“是单蹄的”“可供人骑”等都是马概念的属性集合F中的元素f,都可分别与马义形K组合而成为关于马概念之一个维度意义的陈述。姑且称此为对马义形的“合法述谓”。而“写得一手好字”“是前轮驱动”等描述则不在马概念的属性集合F中,即不是马的属性意义,因而不能与马义形K相组合而构成关于马概念的有意义陈述。姑且称此为对义形的“非法述谓”。这样,对于任一概念内容,一个命题有意义,当且仅当义形得到合法述谓;否则可能无意义、或意义不恰当。[注]这不包括隐喻、童话、幽默等现象。虽然一个谓词应当只用于允许它的义形,但出于特定目的,人们也可以用之于不允许它的义形。这使得诸如“太阳公公睡觉了”“假期中我的智商下线了”之类的表达成为可能。但这涉及另外的问题,本文不予展开。这样一来,命题是否有意义与具体语境无关。
当然,句子的命题意义毕竟是思想性的。一个命题有意义并不等于该命题为真。本文赞同将命题的真值条件与真值确定分开:命题只给出其真值条件,并不保证其意义为真。命题是否为真,即是否符合世界给予人的感知经验需要依据具体事实来确定。非法述谓无需验证也无意义,或者不可能得到任何验证;而合法述谓有意义,但其意义是否为真有待事实检验并予以断定。“张三个儿高”表达的命题是无需任何语境(甚至不认识张三的情况下)都能理解的公共意义:张三是高个儿。作为合法述谓,该命题为真,当且仅当有个人是张三,且这个人个子高;至于其真值的确定,即说话人在具体语境下指称哪个张三、跟什么人相比、是实话还是挖苦……则是在理解了句子命题之后依据该命题内容而进行的固定指称对象、评判并确定真值、推断说话人意图等行动。这些语用活动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并不为句子的最小语义内容增加任何新内容。同理,句子“所有人都准备好了”表达的最小命题就是:x(READY(x,y));其中“所有”表达的不是实指意义,而是义形“任一对象群体的每个成员(没有例外)”;这是公共可理解的、跨语境等同的最小语义。至于“准备好了”,伯格已指出,其意义是句法驱动的,即及物动词“准备”本身就要求某物或为某事作论元;这仍与语境无关。[注]Borg, Pursuing Meaning, p.92.该句子语义内容的真值条件即是:“所有人都准备好了”为真,当且仅当所有人都准备好了。至于所有人指什么对象、这些对象是否都为某事做好了准备,属于具体语境下的语用确定行动,并不为句子语义内容增加任何成分。
句子“你不会死的”稍特殊一些,因为离开语境谈其真值表面上看的确有问题。但此句意义仍可按本文理论做出解释:代词“你”承载的义形可由很多谓词来述谓,但一般情况下理当不包含“永远不会死”,因为这种可能性目前人类的信念体系并不支持;因此,这一谓词与“你”构成的是前文所说的非法述谓,不可能得到任何事实验证。既如此,永远不死之意即被排除。至于“不会死”的指称性意义(你不会因什么而死的事实),则需要依据语境予以确定,但这是认知语用推断,不是该句子的语义成分。
总之,是语言意义确定了具体语境下的语用行动内容,而不是语境确定了语言意义。语言的单维性注定了词与句中没有空间来允许语境、意图因素的融入和参与。真值的确定不是句子语义的职责。句子最小语义无须语境化。
结 语
综上所论,尽管思想意义是多维的、有赖于整个信念体系的,但语义的确定性却不依赖人及语境。人与人之间关于世界的经验和认识都不尽相同,但正因为如此,语言交往才有必要。既如此,语义只有具备了公共可理解性才能保证意义的传递不受具体语境的限制。这才能解释科学命题的合理性,或通过读书求知的可行性。
语言交往不等于思想内容整体的完全表达,交往的成功不在于说出的句子在交往双方之间传递了比特量相等的信息,而是使得交流双方构建、调整思想内容从而趋向于共识。“语言表达式帮助建立并鉴别心理空间元素,但并不指称它们”。[注]G.Fauconnier,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52.语言的性质应当是使得社会成员的交往中使得有条理的认知合作成为可能的客观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