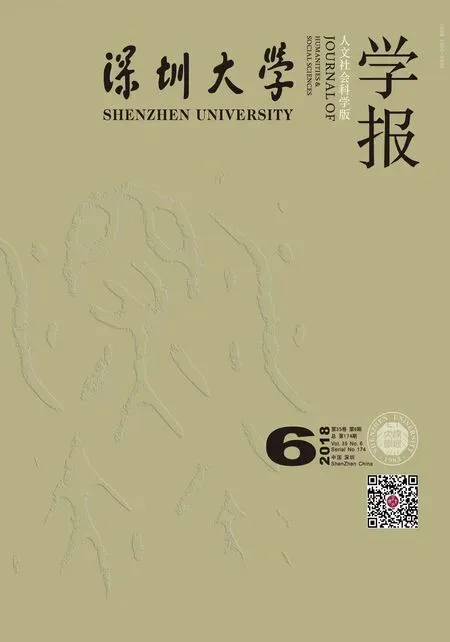“中印学”构建:根基、拓展、走向
2018-03-16朱璇
朱 璇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诞生于中国与印度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历史背景下的“中印学”(Sino-Indian Studies),既是一个构建中的历史概念,又是一个具有探索性、实验性、在场性和交互性的文化语汇。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和印度无数有识之士通过著述与践行,寻求对这一认识的理解和深化,使之能逐渐形成思想体系和文化方法。“中印学”肇始于泰戈尔,既与泰戈尔秉持的世界主义、人本主义和对亚洲精神“独特同一性”[1]持续垂注有关,也与泰戈尔对中国文化的深刻体认有关。在近代中国和印度内忧外患、两国文化交流几近断绝的情形下,泰戈尔从文明互惠的机缘看待两国在思想上的亲缘关系,指出中国与印度也许在地理上和人种上不算密切,但在思想关系上却最为亲密[2]。泰戈尔于1921年创办国际大学,开启了印度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现代汉学[3](P373),同时也催生了以文化交流为基础、以思想会通为旨的“中印学”。“中印学”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其间既有一批知名学者如谭云山、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1898-1956)、蒲罗丹(Pradhana)、巴帕提(P.V.Bapat)等为之撰述,出版 《中印学报》(The Sino-Indian Journal)、《中印学刊》(Sino-Indian Studies)等中印文化交流期刊,又有对“中印学”的实际开拓与践行,如在印度圣蒂尼克坦和中国南京分别设立的 “中印学会”(The 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①,汇聚中印文化界和政界名宿,堪为“中印学”的孵化器。1937年,中国学院(Cheena Bhavana)在国际大学的创立,则标志着“中印学”有了实质性发展。按照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对“中印学”的理解,“所谓‘中印学’,就是把两千多年以佛教为桥梁的中印文化交流突出起来,因为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独一无二的,可以把它当作一门专门的学问,不但研究文化交流,更深入研究中印睦邻关系,研究领域包括地理、历史、哲学、宗教、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诸多方面。用‘中印学’的透镜可以对中国文化发展得出更深层次的了解。”[4]
“中印学”不是既成术语,其学术话语、内容和外延始终处于不断建构和充实的过程之中。正如印度学家郁龙余所言,“‘中印学’对谭云山来说,既是理想又是实践。他为中印学会拟定的宗旨,后来又成为中国学院的宗旨,也是谭云山一生的宗旨。……中印学(中印学术)研究,放在宗旨的首位。”[3](P397)印度当代汉学家墨普德(Priyadarsi M-ukherji)甚至认为,中国作为受惠印度文化最多的国家,“汉学”更当被称为 “中印学”或 “汉印学”(Sindology or Sin-Indology),即中国与印度的融合[5]。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自诸位印度学名家之手的《印度与中国》不仅在印度学界颇有影响,而且也是反映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印学”发展的面相和缩影。
1938年,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中国厅开幕式上以“中国与印度”为主题演讲[6]。1944年,著名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 (S.Radhakrishnan,1888-1975)出版《印度与中国:1944年5月在中国的演讲》,被中村元评价为 “世界上第一本对印度与中国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书。”[7]同年,印度汉学家师觉月的名著《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②出版,被公认是中印交流史领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印度前驻华大使苏杰生(S.Jaishankar)称其是“关于印中两国的历史纽带的伟大作品”[8]。 半个多世纪以后,另两本《印度与中国》问世。美籍华裔印度学家谭中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耿引曾合著的 《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2006)被季羡林评价为“史无前例的文化事业”[9](P2)。而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主席、印度国际文化研究院院长洛克希·金德尔 (Lokesh Chandra,1927-)新撰《印度与中国》(2016)则是已界耄耋之年的作者,对父子两代人在90多年的岁月里,不断寻觅中印在2 300年里相会相契的一次文明探索,正如金德尔所言,“思想与形象、美感与形式以及静默与言语成为历史性分享的形而上学。”[10](P1)这四部《印度与中国》作者都与“中印学”关系密切。师觉月是“中印学”直接倡导者之一;拉达克里希南曾任“中印学会”名誉主席;洛克希·金德尔之父拉祜·维拉(Raghu Vira,1902-1963)于1943年当选 “中印学会”理事成员;谭中则子承父志,其参与筹建的印度中国研究所、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的中文系,为推动“中印学”做出了实质性贡献。他们或探讨古代的文化交流,或谈论现代的文明回应,或尝试建构中印学体例,或着手会通中印思想。其中既有着丰富的史实、史料和交往的确凿记录,也有着极显个人素养、风格和思维特征的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使得“印度与中国”这一古老而弥新的话题不断延续着生命力。
一、“中印学”根基:以交流史为源本
人类文明交流史是一部由点及面的网络地图构建史。交点越密集,经、纬支线越富密,交流地图也就越精细、越广阔。师觉月的《印度与中国》虽不是鸿篇巨制,却完整勾勒出一千多年中印文化交流的宏伟图景,堪为中印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此书以佛教的传布为线索,共分八章,从早期的贸易交往到佛教的传播历程,从佛教的东渐到文化的互渗,他不仅对佛教在中国的诸多派别及所藏佛教文献作了大量的考证,而且对印度雕刻、绘画、建筑、音乐、天文学、数学和医学对中国的影响作出具体的例证。尤为可贵的是,尊重史实的师觉月并不回避印度学界长期以来“尊梵抑汉”的现状。他坦言,“一直以来,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关系似乎更像是一条单行道。正因如此,人们从未认真地去尝试发现中国对印度人生活和思想的影响。事实上,印度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对印度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从未在任何个体身上得到应验。”[11](P163)这一说法切中肯綮,从20世纪20年代直至今日,不论是印度学界还是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始终莫衷一是。“以往有关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研究论著中,有些著作有意无意之间体现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单向性’,即古代中印之间的交流只是从印度到中国而已,甚至有学者说出‘中印古代交流其实是中国单向学习印度’这样的观点。由于印度方面的史料较为缺失,容易给学者或读者造成这一印象。”[12]师觉月深入寻常生活的物质层面,发现丝绸、茶、荔枝、妇女妆点用朱砂、桃和梨,皆源自中国,不仅例证中国对印度的影响,也确证中印之间文化交流并非单向度,而是双向交流的事实。师觉月开启的从物证探索双向文明交流的方式启发了季羡林,他对制糖术、造纸术等专题研究,揭示出历史上中印交流的复杂性和“双向性”,而且在晚年写长文《佛教的倒流》,指出文化交流绝不会是单向的,“而是相向地流,这才是真正的‘交流’”[13]。
师觉月承袭法国汉学传统,重视史料的来源,参考文献以汉文文献为主,辅以东方学家如沙畹、伯希和、列维等的研究成果,史料经甄别、提炼后形成的史论,既体现出一流的史学眼光,又显示出极高的史学素养。在他描绘的千年交往长卷中,既有较为熟知的来华僧人,如竺法护、鸠摩罗什、僧伽跋澄、僧伽提婆、佛陀耶舍、达摩笈多、菩提流支、菩提达摩以及赴印的道安、法显、玄奘、王玄策、义净等,也有不甚为人所知的,如来自安息、粟特、大夏、龟兹、于阗等中亚国家的来华佛僧,以及记录在菩提伽耶汉文碑铭上的中国僧人的名录。为此,他在附录专列“中国译经的印度学者生平”,这部分正好可与耿引曾在《印度与中国》中“高僧一览”之“印度来华弘法高僧”做参照对比③。耿引曾增列“中国赴印求法高僧”以及最见功力的“中印关系大事编年”,将师觉月的工作大大推进了一步,使得交流图卷中的双向和交互的交流显得更为充分和具体。
如果说师觉月和耿引曾以编年史的方式记录文明的交往,那么,金德尔的《印度与中国》则有了些许“当代史”的意味。此书所述时间跨度更长,从佛教传入直至当今社会,历时两千多年。材料来源更为丰富,既有以“物”证史的考据,也融入不少实地勘察的情景、走访、口述和日记,以及不限表达方式的片段式截取 (可以是一个符号或是一段唱词)。记述视角更为灵活,书里的作者其实有两人,一是金德尔本人,二是他的父亲、著名梵学家和汉学家拉祜·维拉教授,时而作者视角,时而他者视角,不仅是对真实历史的记录,也呈现当下的情状和反映,给人以生动、鲜活和真实的感受。
金德尔以散点式的记述方式,呈现给读者交流史中一个个具体的实物与实景。他从“佛教在中国的共鸣”谈起,穿插中国和印度双向交流的点滴印记,如棉花如何引进中国,中亚的僧人如何携带佛经并译为汉语,由迦梨陀娑《沙恭达罗》残片如何界定中国戏剧的起源,以及摩揭陀传入中国的制糖术,菩提伽耶刻的中国碑铭,中国舍利塔和法门寺里的佛祖指骨舍利,敦煌和云冈的石窟和造像,占城的梵文手稿,居庸关的梵刻,甚至可能按照大威德坛场而制定的北京城市规划等等,不一而足。金德尔以他多年的调研,丰富的学识与见解,呈现出交流史中的“个案”,有些已有成熟的研究成果,更多的则是对学者尚未关注或较少论及的,却可能牵扯交流史新发现、新交点、新线索和新问题的大胆假设,这才是值得学者倍加关注的地方。
金德尔之父拉祜·维拉是位了不起的梵学家和中印学家。中国学界长期对拉祜·维拉的汉学贡献一无所知。他曾将几部中文著作译为梵语,包括制作《妙法莲华经》汉梵检索表(此表于1947年遗失);将大藏经中两种《罗摩衍那》汉译④倒译为梵语(1938.8);将公元517年编撰的汉梵天城体辞典《翻梵语》中的地理部分译为梵语⑤;翻译丰子恺《护生画集》(第一集),以中英梵三语合体的形式以《中国诗画中的不害思想》为题出版⑥。1955年12月25日,后三部著作由金德尔赠送给在那格浦尔暂做停留的宋庆龄,宋庆龄边翻阅边说:“太有意思了”[10](P65)。拉祜·维拉的梵学成就不止于此,他还自创一套适用于表达现代科技术语的梵语词汇,为编纂这本梵语科技词典,他曾系统研究中文对化学物质的命名方式。
书中颇费笔墨的是拉祜·维拉和金德尔数次访问中国的见闻与收获。这些见闻带着鲜明的交流“物证”,又有着逼真的场景描述,这种将历史考证与文化游记相结合的方式,正是古代僧人们记录的方式。当下的个体和鲜活的场景似乎与遥远的过去有了某种共契,历史的过程也因融入了个体的情感和满富的生命力,迸发出充沛的想象与美感。1955年,拉祜·维拉及其女儿苏妲莎娜·黛维(Sudarshana Devi)访问中国三个月。他们的足迹遍历大半个中国,从南到北探访数十个主要城市。参观并到访国家图书馆、中央研究院、故宫博物院、颐和园、长城、居庸关、北京大学、西安大学、陕西省博物馆、敦煌、云冈、龙门以及雍和宫、白马寺、塔尔寺、慈恩寺、灵隐寺等各地主要寺庙,详细记录了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灵隐寺飞来峰的各窟情况,手绘居庸关佛塔与拱门上的雕刻。5月1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拉祜·维拉,并对他说:“古时玄奘曾赴印取经,今天你从印度来华取经。你就是印度的玄奘,这些古籍就是你的宝藏。”[10](P142)拉祜·维拉在中央研究院与院长郭沫若讨论“百藏丛书”(sata-pitaka)⑦计划。后乘火车从北京到呼和浩特,张明坦和季羡林不仅陪同他北上,还担任他的翻译。他在敦煌停留的一个多星期时间里,不仅在常书鸿的讲解下静静欣赏和临摹敦煌壁画,而且与当时敦煌研究院的39位工作人员共同工作和学习。他在写给敦煌的留言中不由感慨:“我们得以亲见它、汲取他并将之同化至我的血脉中,我的精神得到擢升。一千六百年前的中国和我的祖国竟有如此亲密的,如钢铁般摧毁不断的爱之纽带。 ”[10](P189)回到新德里后,拉祜·维拉将他所收集的关于西藏、蒙古、西夏和中原其他地域的大量手稿、版画、碑铭模本、绘画、图片等进行整理并举行展览,虽然131箱资料中仅有30箱得以展示,但此次展览获得极大成功。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参加了展览开幕式,来自德里、浦那、艾赫拉巴德、勒克瑙等大学和研究所,以及德国汉堡、罗马、伦敦大学、新加坡马来亚大学的知名学者纷纷致信或留言。拉祜·维拉的访华记录堪为当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收入由中印双方共同编撰的 《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之中。
二、“中印学”拓展:比较意识和方法的凸显
长期浸染于国际大学“中印学”氛围,又与谭云山共事多年的师觉月,不仅希冀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而且寄望发现这些痕迹背后可能互通的内生文化源头。他以比较的视角,探寻道教与古代印度的哲学的相似性。据他推测,最早的佛教护法团可能在道观里得到了庇护,和道士居住在一起,待他们返回印度时,便利用习得的道教知识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11](P166)。这一推测不乏实例,鸠摩罗什撰写的《道德经》评注尝试将龙树的中观派哲学与道教哲学进行会通,而玄奘和道士们在唐太宗旨意下将《道德经》译为梵语,虽无法确认此译本最终有否带去印度,但可以确证的是,佛教的密教派借鉴这个译本,发展出了俱生乘这一派。由此,师觉月在“两个文明——一个融合体”一章中,认为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虽生长于不同的土地,说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但为了一个共同的文明而和谐共进[11](P143)。他从中印共同拥有的“天”道赋予的思想,共有的祭祖传统,儒家与印度法论相似的社会政治理念,道家之“道”与印哲之“梵”的相似性,来探讨两大文明要素之相似性的深层原因,抑或同源性。
师觉月的文化比较仍遵循史学方式,通过具体的实例和合理的推理来探寻现象背后的思想源头,由此发现不同文明之间共有的文化基因。他发现老子之“道”所具有的内敛、彰显权能,周易的“太极”所呈现的“阴”、“阳”转化,皆与印度哲学中的“动”、“静”二相有异曲同工之处。朱熹抽象的“理”与具象的“气”亦是同一本体的两个面向,并指出这一观念可能受印度轮回观念的影响。相比历史梳理,思想的相关性推演显得困难而隐性得多。但师觉月的推演仍提出一个极好的课题,即文化的比较是否一定会追溯至源生性的问题,比较文化学是否还有其他的开展方式?
面对中印文明源生性的问题,谭中的回答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有着完整中国教育背景和数十年与印度政界、学界交道的经验,谭中的精神气质和思维特征早已烙印“中印学”双重文明的痕迹,他的文明比较着重从中印思维方式角度来进行。季羡林在序中赞赏这种比较方式:“中印两国有很多共同的文化特点。我认为最明显、最重要、最基本的是我们实际上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9](P1)
谭中在《印度与中国》“透视景观”章中从中印两国同发源于喜马拉雅的地缘文明来探讨根源。“喜马拉雅亲属关系”指两大文明同依喜马拉雅而生,以喜马拉雅为基点,带有喜马拉雅色彩,可谓喜马拉雅孪生子。同样的地理、物种和植被特征赋予了两国共同的农业文明,其中的大米、丝绸、糖、棉、茶的种植都印有两国同源相生的深刻印记。他指出,这种“喜马拉雅亲属关系”所带来的双面效应可能是文明交往的“镜面反射”,既可通过伏羲-女娲和阎摩-阎蜜的故事、原人(Purusa)和盘古的故事、蛇龙图腾的传说造成成对的镜面效应,同时也会有“背靠背”式的各自发展和互不干涉。“背靠背”虽然少了“面对面”的热络,却也使得两大文明在千年时空里搭建相对和平的空间环境。
谭中的地缘文明范式极富新意,既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路子,也有比较神话学的视野。虽然他尚未回答外部的地缘环境成就文化内生的主要动因,但已打开新的思路。这一思路体现在“下编”从寺庙文化、金轮帝制、风流人物、金玉符号、龙凤双飞等五方面集中描述这些中印在长期文明交往中产生的特殊现象,也是对师觉月所探讨的中国对印度人日常生活和思想影响的延续和扩充。谭中坦言,他的写法不完全是考证式的,而是以欣赏和品鉴的眼光去看待两国文化中最菁华、最出彩的地方,由之开发并探讨这些终在中印漫长交往中深潜于日常生活里“合璧”了的文化现象,从而促进两国的相互理解。这样的写法更像文学的写法,事实与想象的有机结合,进而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与启发。从谭中娓娓道来的“合璧”现象中,我们会发现,它们既表现出印度与中国的各自特质,很难分得清这种影响的理路,又体现出中印在思维偏好、表述方式、审美意象、欣赏趣味等方面的差异。如果简单地将这种 “中印合璧” (Sino-Indic ratna)式的写法视之为缺乏直接关联的主观想象,那就忽视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深意——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特质下,人类的精神活动有多少潜移默化,又难舍难分的交缠和相互影响!在谭中为印度经济学家杰伦·兰密施(Jairam Ramesh)新书作的序中,他认为“中印合璧”尚不能准确表达他的想法,而要用“Chindia”来取代“Sino-Indic ratna”,“因为后者是带连接号的,不如前者把两种文明整合得难解难分。”[14]
如果说师觉月和谭中是从源生文化和文化的动态影响展开比较,那么印度贝拿勒斯校长拉达克里希南则以哲人视角,展开对中印在宇宙观、认识观、人生观等方面的对比。拉达克里希南的《印度与中国》源自其对中国的首次访问⑧。1944年5月6日至21日,拉达克里希南受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邀请,应邀访问重庆、南京、上海、昆明等地,并受到印度驻重庆总代表梅农(K.P.S.Menon)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的热情接待。在短短的16天行程里,他访问大学、学术机构和佛寺,并在国立中央大学、中央军校训练部、中央政治局、中央图书馆、复旦大学、云南大学、中国哲学学会等地发表公开演讲。这本《印度与中国》便是拉达克里希南回国以后,在演讲的基础上对中印文化所做的梳理,其中讲述访问中国的起因和见闻,中国与印度的历史渊源,中国的教育现状,并分述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战争和世界安全等内容。
不同于师觉月和金德尔对两国交流史中“点”、“线”的爬梳剔抉,拉达克里希南的《印度与中国》有了更多比较哲学的意味。此时来到中国的拉达克里希南,已经完成关于东西方文化对比的《东方宗教和西方思想》(Eastern Religions and Western Thought)和关于宗教生活的《理想人生观》(An Idealist View of Life)等奠基性的著作,其旨向生活体验的宗教观业已形成。因此,他带着寻觅宗教精神共契,寄望找到中国宗教实质的想法,与学者和僧人们展开交流。虽然他不懂中文,对中国的认知大多源于英文书籍,他自己形容这本关于中国宗教和文化观的书只是 “暂时的”、“教条式的”抛砖引玉之作,但仍不啻为中印思想比较的开拓性作品。
拉达克里希南对中国文明的理解不限于佛教,而深入儒家、道家、佛教(在拉达克里希南看来是儒教、道教和佛教)的内在理路,进行重思与批判。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拉达克里希南从宗教学角度,对儒家的世俗性、道家的超越性和佛家的精神性所做的对比阐述,字里行间投射出哲学家的敏锐的见悟和精准的洞察。他注意到道家的“道”与《梨俱吠陀》中“黎答”(rta)都具有主宰自然和人事运行的力量。注意到孔子的“天”具有的某种超越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注意到墨子的“天”“人”关系透露出更深的“神秘的理想主义”(mystical idealism),个体的精神与自然精神逐渐实现合一。他将超越经验范畴的“空”、纯粹存有(bhūta-tathatā)与吠檀多不二论的“绝对者”并置而谈,将瑜伽行派的“法身”(dharmakāya)对应奥义书中的“梵”和老子的“道”,并把“法身—受用身(sambhogakāya)”关系与“伊莎伐罗 ()—毗湿奴”(或湿婆) 的关系对比,指出对绝对者象征性的呈现方式的价值判断是比较的要旨。
在认识论层面,他注意到孔子与佛陀的方式一样,谨慎地回避对超俗方面的谈论,“未知生,焉知死?”,即使对人的精神局限性有所暗示,也以沉默来回应。他注意到孟子所言的“知”与呈现精神状态的“心”有区别,后者与奥义书中“全智”(parā vidyā)观念有相似之处。他将朱熹的“理”理解为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融合物,由此产生人的两面属性,即精神性和物质性的对立。
在伦理方面,他注意到孔子的“中庸”和佛家的“中道”,并指出相比宗教观,孔子更关注社会观的建立。在世俗层面,孔子所要恢复的“礼”犹如印度的“达磨”(dharma),既关乎个体,也关乎社会。他注意到佛教与儒家在伦理方面的相似性,均重视子女对父母的孝心, 如 《善生经》(Sin.gālovāda sutta)中六种责任(父子、夫妇、朋友、师生、主仆、异教者和信教者)与儒家“五伦”中的父子、夫妇、朋友关系如出一辙。他极力肯定儒家在道德方面的肯定,但在宗教观方面,他更倾向佛教,认为大乘的教义与《薄伽梵歌》一样,共有“形而上理想主义”和虔诚的信仰。
作为一名出色的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的贡献不仅在于对印度哲学从文献到义理的梳理、消化和阐释,而且在于探索其内蕴的比较哲学思想,《印度与中国》是他印中哲学比较的集中体现。他发现中国人的思维本质是实用和现实的,中国思想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狂热的盲信和宗教的争论,也无不顾本性的,忽视理性和情感的生硬教义,虽然中国人对神学和个人救赎不感兴趣,但不能简单推断其缺乏宗教精神,而有着更纯粹、深厚的精神追求。
拉达克里希南的哲学比较是分析式的,他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哲学逻辑,将各种观念、思想并归这一体系,并从思想史的发展角度,考察各种观念、思想体系的完善程度。他以“最高本体”及其实现方式的圆融为完善标准,从而对儒家、道家、佛教的教义进行评判。他指出,儒家未对深层次形而上问题作解答,道家的“道”纵然唤起对某种超越的不确定,道德行为的深层目的和最终的归属在佛教,并认为佛教是对儒家与道家在禅定智慧和修行等精神层面的补充[15](P109)。虽然中村元评价拉达克里希南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 “误读”,个中原因既受作者使用材料的限制,也由于作者宗教观的局限。但是,拉达克里希南同样发现了值得深入挖掘和探讨的课题,即在思想层面上中印对比研究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实现两者会通的问题。
三、“中印学”走向:探寻思想会通的可能性
思想之会通,实乃近代中印知识界共同致力的一项事业。旅印30余年的徐梵澄因契得中印精神文明之精髓,曾言:“求世界大同,必先有学术之会通;学术之会通,在于义理之互证。在义理上既得契合,在思想上乃可和谐。”[16]在中国有会通中西思想的近代新儒家,在印度有会通印西思想的新吠檀多派,而中印思想之会通,则以倡导“中印学”的“中印学派”为先导。他们试图通过抽绎出中印文化背后的基本哲学观念,将之理论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参照话语,在普遍意义下探讨这些观念共有的哲学价值,从中反映和透析出各自文化的精髓部分。
思想会通的基础在于追求普遍真理,而会通有其分际和限度。当人要表达其精神性时,必通过有限的感性限制和制约来表现,这是牟宗三所谓“一孔之见”[17],也是庄子所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之“察”。会通的分际提醒我们,在探讨哲学问题时,需要注意所谈概念是在哪个层次上讨论的,不能将不同层次的概念并置而谈。如师觉月所谈的“道”与“梵”,拉达克里希南和师觉月将朱熹的“理”和“气”对应印度哲学的“动静二相”,均是在形而上层面的会通,这一层面是相对于“经验实在论”(康德语)层面和中国哲学中“感触界”(牟宗三语)层面而言的。虽然在康德看来,“超验观念论”和“经验”层面无法互通,因人缺乏“智的直觉”,但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则不然,中哲讲究“一心开二门”,孔子的“仁”、道家的“道心”、朱子的“本心”、王阳明的“良知”,大乘佛教的“如来藏心”和“般若智心”,其所蕴含的 “心”既是认识本体,也是道德本体,与印度思想中“梵”、“我”一样,均直接会通感触界与智思界。
西哲从认识论来谈感触界的理路清晰,在这一层面,不论中国哲学,还是印度哲学,多是以消极的方式来表述的,这也是拉达克里希南发现孔子“慎言”的地方,也是印度“遮诠”的方式。但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在智思界则比较积极和通透,“人人皆可为尧舜”,以“转识为智”来肯定人的“智的直觉”。印度的主流哲学相信“自我”和“知觉性”(consciousness)的拔升,这一“知觉性”的擢升,也是拉达克里希南在《印度哲学》中所界定的“宗教意识”⑨。
在道德实践层面上,中印会通有着共同的实践目的,即人性的转化。拉达克里希南注意到儒家的“礼乐”是为获得“善”的人格修养的手段,“教育以诗开启,为道德限制所强化,进而在乐中圆满,一切的目的在于改造人性。强调个体努力,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15](P60)他认为老子和佛陀一样,从表面生活深入更深层的真实。“普遍真实的知觉性影响着我们本性的转化。这是一种新生,塑造新人。达磨的真实不是理论的教条或形而上的假设,他直接面对知觉性。 ”[15](P91)他认为,中国与印度一样,上智的理性和道德并没有对民间的迷信仪式产生影响,形式的崇拜甚于内在的虔诚,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宗教的目的在于培养儒雅、宽容和见识的修养,而非探寻人的终极目的与归属。只有佛教承担起这一任务。因此教育和工作如同印度的智瑜伽和业瑜伽一样,成为了佛教改革的手段,从而实现改革的终极目的——人的精神转化。
拉达克里希南认识到中印思想在转化人性方面的可能性,然而,他以“最高本体”及其实现方式的完善程度来评判儒、释、道的高下,却又阻碍了他对于中国思想复杂性的洞察。他虽然发现了孔子的改造人性的价值导向,却无法在孔子讳莫如深的“天”与张扬的“仁”信条之间建立起联系,因此他在肯定孔子对于善、对于生命价值的追求的同时,发出这一价值的终极归属的疑惑,即高扬道德却不追问人类起源和命运这一终极哲学话题,终会陷入人文主义的缺陷?拉达克里希南提出的问题值得深省。他从宗教的超越性出发,看到了中印哲学在转化人性方面可能会通的意义,但却无法从孔子、老子、孟子、墨子、朱熹的教义中发现转化的逻辑,最后只能求助佛教。他虽敏锐地将中国佛教的希望寄于太虚等身体力行的佛教改革上,但仍缺乏对中哲的深耕,也尚未系统研究宋明理学以及儒家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综摄构造,未尝发现另有一思想改革,以更为理性、综摄、汹涌的姿态进行着。所幸,拉达克里希南终止的地方,也是后来的中印学者,如徐梵澄寻求突破的地方。徐梵澄看到了印度精神的超越性价值,人性转化的途径多样,不论是中国的修身与养性,还是印度的知行意瑜伽,所修的均是身、心、意的整体工夫。他吸收印度圣哲阿罗频多精神进化论,从宋明理学的身、心、性、命之学的主旨在于“变化气质”中,了悟精神哲学也着重在身、心修为的“转化”[18]。正如孙波所总结的,徐梵澄的“精神哲学”在于研究“心灵”与“性灵”的学问,主旨和目的在于变化人的气质,终至转化社会和人生[19]。
中印思想会通的目的在于价值的重建,这也是“中印学”始于文化交流,终于新文明创建的宏大愿景。中印思想会通的方式是多元的,正如“中印学”本身一样,是个开放性话题。近一个世纪以来,以中印两国优秀精神文化成果为研究对象的中印学的内容和方法在不断扩大,史学的叙述、文学的想象、文化的比较、思想的会通,以及更为广阔的领域,不啻理性和言语,亦有神话与隐喻,以及更多有待开启的方向与话题。
注:
①中印学会以“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情感,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总则包括中印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关中印文化的讲座,关于中印文明的宗教、文学、历史、科学和艺术研究,出版书刊,建立文化机构,出售中印文化方面书籍,尤其关于世界问题的书籍等。详见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藏谭云山文献。
②此书主体部分曾于1927年在刊物发表,后于1944年(印度)、1950年(印度)、1951年(美国)、1971年(美国)、1975年(美国)、1981年(印度)、2008年(印度)出版七次。见尹锡南:《印度学者师觉月的汉学研究》,载《国际汉学》2018年第2期,总第15期,第69-70页。
③两部索引均根据汉文佛经文献对从公元67年(耿引曾版提前到公元前50年)到公元1364年(师觉月版记录至1368年)的来华僧人进行了一次详细的生平整理,虽个别年代略有差异,但内容相当,均是翔实的参考。
④大藏经中有两个关于《罗摩衍那》故事版本,分别为公元251年康僧会的译本和公元472年吉迦夜(Kekaya)的译本。
⑤ 包括国家、城市、乡村、寺院、圣地、山脉、河流、水塘、岛屿、花园和森林等诸多词条。
⑥此书具体内容参见黄蓉:《护生与不害——〈护生画集〉在印度》,载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48-52页。
⑦1957年拉祜·维拉及其创立的印度文化国际研究院倡导并主编的藏文文献的编辑出版计划,目前该系列已经出版650种左右。1983年金德尔第一次访华时,曾与班禅喇嘛讨论西藏所藏梵文文献的出版事宜。
⑧早在1942年,拉达克里希南曾受甘地委托准备赴重庆,将泰戈尔的画像赠送给当时的国民政府。虽未成行,但画像后来仍送至重庆,悬挂在中印学会大楼正中。
⑨ 拉达克里希南在《印度哲学》(Indian Philosophy)中将宗教意识分为三个层次——所听(sravana)、思辨(manana)和深层次冥想(nididhyasana),对应宗教崇拜、宗教虔信和宗教冥想这三个阶段,表示意识逐渐内化的过程。